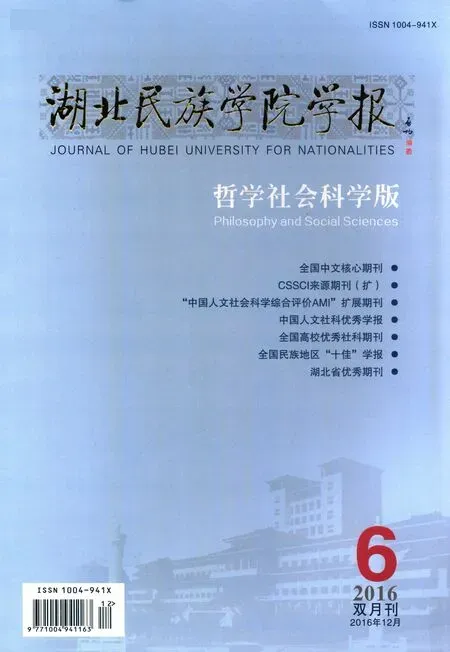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
——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
常海燕,满 珂
(广东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民族文化重构中“知识书写”及其超越性的人类学研究
——以青海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
常海燕,满 珂
(广东医科大学 人文与管理学院,广东 东莞 523808)
民族文化的重构往往要通过精英所操控的“知识书写”才得以确立,而这种“知识话语”与“权力”交织在一起,甚至在认识论结构上就难以避免。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国族主义的学术殖民主义,在尊重历史文化的国族超越性与国族政治格局的现实中探索出一种恰当的书写范式。本文以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力图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出发予以探讨。
撒拉族;文化重构;知识书写;超越性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为世界提供了以“国族”为单位的认知图式。中国边疆社会在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也经由“民族识别”的政治策略逐渐“分族而立”,开始以边界清晰固定的“民族”框架为单位分门别类的重构文化。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业已表明,民族文化重构是一个复杂的能动性社会过程,它是以“现在”为基础被精英群体不断创造出来的[1]。但对于民族精英在文化建构过程中利用知识话语进行文化定位并由此引发“超国族主义”的认知倾向应如何从学理上把握,相关研究还未足够重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现实下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知识-权力模式下撒拉族的“历史建构”
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早已揭示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知识是一种话语实践的历史过程,它摆脱不了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支配力量的制约;同时,权力也正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和结构中形成的,通过稳定的知识形式,对社会生活产生规训与控制[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正是通过民族实地调查研究的知识话语体系展开合法性的“国族政治”权力建构的范例。
大致来说,撒拉族识别主要知识依据有三大部分:
首先是散布在元以后历代官修档案特别是清史籍中的史料,从相关记录可以看出,尽管撒拉人当时自称为“撒喇尔”,但“帝国”对于撒拉族的认知却一直在“番”与“回”或“番回”的族属归类的固化框架中不停变换,对其来源正如乾隆时期循化厅同知龚景翰撰写的《循化志》所言“撒喇回子不知所自”[4]。如果不是由于清中后期撒拉族社会内部“教争”引发了大规模的武力冲突,迫使清廷关注,极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处于“藏”与“回”的“裹挟”中一直被忽视或混同,无法拥有“自我表述”的话语权力与机会。
其次,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北边疆危机又一次引发了内地知识分子对西北边地研究的兴趣,如杨涤新(杨兆钧)、顾颉刚等学者开启了对撒拉族独具特色的语言、族源及其社会组织的初步研究与推测。对于其族源问题,在这一“非常”时期大多学者的研究认可明清文献记载,认同撒拉人是在“元末”或“明洪武三年”“由哈密”迁至内地的,而对于撒拉族民间传说所讲的源自“中亚撒马尔罕”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这一时期相关学者研究,请参见马成俊、马伟主编的《百年撒拉族研究文集》相关文章,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如该文集第3页任美锷在《循化的撒拉回回》论述:“因为撒拉在循化一代最多,所以又称为循回,以别于临夏(河州)一带的回回。……撒拉究竟从哪里迁来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普通有两个说法。第一说谓撒拉由新疆哈密迁来,定居于河州西二百里的撒喇穿(即循化),所以叫做撒拉回回。第二说颇有些神话气味:以为撒拉的本家原在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我们考据文献,自以为第一说为可信。”。尽管大多研究结论后来被证明有误,但这些研究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开启了真正的知识通道。如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杨涤新到循化实地调查后,确认“撒拉语确系突厥语之一种语言”,与其周围藏、回所讲语言都不相同,这个论断后来获得国家民委调查专家们进一步确认,“撒拉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打破了撒拉语是“奇特土语”等错误的认识[3]4-5,为撒拉族的族源研究及其民族识别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最后,是民间传说等口述历史。其实从19世纪末开始就陆续有一些外籍人士在撒拉族社会调查其语言与口述史,但没有得出详尽的研究结论可供借鉴。19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的师生、社会历史调查组等重新召开座谈会,通过对多位撒拉老人和阿訇们所讲述的族源传说进行概括归纳,基本上形成了对撒拉族族源的共识:撒拉族是一支由兄弟俩率领从中亚撒马尔罕迁移来的部族,因为在当地被诬陷偷牛遭到国王迫害,所以举族东迁至循化定居。[3]5-9
这个在撒拉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以及与其相互印证的婚礼仪式“骆驼舞”表演*有关撒拉族婚礼仪式“骆驼舞”参见笔者拙文《撒拉族“骆驼戏”的历史形态探析兼及民俗文化的生存法则》,《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197-202页。都可以视为撒拉人对自身“外来”历史的某种“想象和表达”,或者如哈布瓦赫所说的一种“无文字”状态下用“集体记忆”构建历史的方式。通过日常“口口相传”的不断讲述和婚礼欢腾场合上重复性的仪式表演,把“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重叠起来,强化这种“植根在特定群体社会情境与结构之中的”象征形式,并“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5]
与民间大众用传说、仪式“立体”、生动的建构自己“过去”不同,“历史考证”是知识精英“平面化”、抽象化的建构历史的方式。第一,他们凭借的主要媒介是作为“权力化的表述方式”的文字,而文字在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第二,知识精英根据学术规则进行自主性建构而非情感性想象。他们可以从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获得指导性动力,但并不依赖甚至会质疑社会大众的集体记忆*关于撒拉族的族源历史,相关学者就分了两拨,一拨以撒拉族的相关传说为依据,另一拨以史料文献的记载为依据,民间传说只作为参考。参见马伟的论文《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载《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96-97页。。最后,由于具有比普通民众更大的话语权,知识精英对文化重构所施加的影响至关重要,往往决定着文化的定位。[7]10
如芈一之在梳理中外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把民间传说与历史考辨结合起来,并从语言、体型、习俗等方面进行考察,建构出一套“理性化”、“实证性”的撒拉族“外来说”的历史话语:撒拉族先祖是西突厥乌古斯汗后裔撒鲁尔部的一支,在13世纪前半叶作为西征中亚的成吉思汗的一支签军驻屯循化并由此定居至今[3]25-41。这一“中亚族源论”为撒拉族区别于回、藏等族团建构独立自主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处于当时正在建构国族政治的考量,他特别补充强调了“撒拉族是在中国土地上哺育起来的民族”,其族源外来“只是700多年以前的事实。撒拉人在明代和清代早以中国人自居了”[3]42。可见,通过历史学家选择、撰写出来的制度化的撒拉族“书写历史”,主要作为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内容存在,往往远离大众的生活记忆。[7]16
那天晚上,伟翔小孩子一样跟我讲了很多话。他说:“那段日子,我简直绝望极了,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幸福的生活,让她那么受委屈,我觉得自己是个最窝囊最没有用的男人。我总感觉我欠你的,所以,回到家里看到你的脸色不好,我就连大气都不敢喘……”
撒拉族“外来说”的“学术话语”与饱含“冤屈感”的迁徙传说,在国家权力所主导的“民族识别”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纠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撒拉族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独立的民族地位。尽管在田野调查中,大多撒拉民众至今仍然保持着“我们回民”或“我们和回族一样”的表述与朴素认知。但对撒拉族精英主体而言,在制度化保障的合法框架下定义、确认民族身份的建构就此拉开序幕。
撒拉族学者马成俊教授论述了从1980年代开始的20多年里,通过研究撒拉族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书籍的出现,“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独特语言、独特经济生活方式的民族遂在国家权力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下通过政府、学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被建构起来。”“族群边界愈加明确,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不断具体化并得以加强。”从根本上“改变了撒拉族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边缘的地位”。[8]
二、文化反思浪潮下“知识书写”的权力“矫正”
20世纪80年代后,整个西方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型,源自西方学科内部对殖民主义学术霸权认知观的自我反思和文化批判导致以往“民族志”撰写方式出现了严重的表述危机。以沃尔夫、萨林斯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都试图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在的影响而更具有本土化和自主性的解释模型。并且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实验民族志试图让“文化撰写”更能切近社会现实或文化真相。[9]
在此学科话语的倡导下,一些接受了西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撒拉族年轻学者也开始积极反思自身民族史的撰写,通过叙述汉语历史文献中伤害民族情感的某些“蔑称”和非本族族籍学者的客体化表述,提出撒拉族历史是谁的历史,由谁撰写、如何撰写等问题,并针对汉族学者的研究共识重新提出了自身的看法和认识[10]。而且对于“撰写人”的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在被不断强化,“尤其是由本民族作家和学者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叙事,逐步形成了以青海省文联为中心的作家群和以青海民族学院为中心的学者群,”“对撒拉族文化的梳理诠释和不断地再生产,‘我们是尕拉莽子孙’的祖先认同意识,在撒拉族中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承认。”“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充分利用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完成了撒拉族的历史重构。”[8]
相比学者通过学术话语建构民族身份与认同意识,撒拉族自治县的政府官员和一些撒拉族退休文化干部以及撒拉族企业家等民族精英们则主要是从建筑、服饰、歌舞、饮食、语言等生活实践的层面努力营造所谓“撒拉化”的民族特色,力图与回族文化等其他族群作区分[11],并努力祛除历史上受到的某些藏族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于这种文化重构中的“本质化”行为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后果,相关研究曾有所论及,一是简化或割裂了地方与国家之间以及地方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二是以人群的‘民族’身份来切割地域社会中共有的文化事项,不仅不能使人们获得对地方社会实际历史过程的正确理解,也会在同一地域社会的不同族群或‘民族’之间造成竞争与冲突。”;“最后是旨在强调差异的这种反趋同论的书写方式,或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成为国家之内的少数‘他者’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12]
这些“本质化”的结果在撒拉族文化重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然而,有所不同的是由于撒拉族族源书写的“外来说”表述使得它的“文化”重构的国族超越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宗教超越性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马成俊教授曾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撒拉族地区的宗教政策更加开放,长期被压抑的宗教热情一下子反弹,循化地区又出现了各教派之间的多起矛盾,”尽管现有政府机构比历史上的权力设置更为有效地防止了这些宗教矛盾的蔓延以免引发更大的冲突,但他也认为应该警醒,“最近几年在撒拉族地区传教宣教的现象很严重,这些传教者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会不会引起固有教派之间的冲突,很难预料,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3]
那么,“历史”或“文化”书写如何突破近现代才出现的所谓“国族”概念的藩篱,在尊重历史上“文明体系”的超国族性与现实中“国族疆界框架”的权力格局之上探索出一种恰当的书写范式呢?
撒拉族在历史上一直是介于“番”与“回”的混合族类,但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从清中后期开始直至“民族识别”前,他们作为“回”的宗教特性及社会性不断强化。在获得独立的民族身份与地位后,迫使他们从“回”的混合状态中分割出来,必须重构自身独有的文化。而且整个建构过程明显呈现出与学术-权力话语变迁的相互平行关系,特别是在21世纪伊始的“西部大开发”及当前的“一带一路”的政治话语下,撒拉族文化建构从1980年代“宗教复兴”后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神圣性逐渐转向强化“中亚化”的特征。
从2000年开始,由撒拉族官员、学者、企业家等组成的精英团体就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多次赴中亚土库曼斯坦考察,土库曼斯坦总统每年主持召开的“世界土库曼人人文协会”,中国撒拉族都会受邀,并派代表参加。中国撒拉族被土库曼斯坦官方称为“中国土库曼人”(khitay turkemanler),普通土库曼人视撒拉族为海外同胞*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双方的历史研究,大体都表述了今天的撒拉族与土库曼民族形成的基石是历史上西突厥后裔的乌古斯部落联盟的撒拉尔部。参见马伟的论文《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载《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103页,马成俊的论文《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兼谈撒拉族语言、族源及其他》,载《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100页。。这些不同范畴的文化交流为撒拉族的族源历史、语言及其衣食住行等风俗问题的文化重构提供了更多现实而具体的“参照”[14]。在此基础上,撒拉族学者开始提出本民族族源的历史假设,迁徙至中国的撒拉族先民是来自12世纪中期建立于现在伊朗境内的撒鲁尔王朝的撒鲁尔人。[15]
2004年,一些撒拉族青年人创建了“中国撒拉尔青年联盟”网站,通过网络的新媒介方式致力于推动撒拉族文化复兴和撒拉族文字创制与推广。在网站论坛中他们把撒拉族历史推进到“突厥-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程内,并流露出对这种族源追溯的自豪感;呼吁撒拉族民众过“诺鲁兹节”,这是一个包括土库曼人在内的中亚广大突厥民族后裔最大的传统性节日;对一些虔诚的撒拉族教众所存在的浓厚的“阿拉伯-伊斯兰”观念可能对“撒拉尔文化复兴”造成的思想阻碍表达了痛惜;并对中亚土库曼斯坦保存的传统舞蹈、音乐及其服饰等习俗内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相关内容参照“中国撒拉尔青年联盟”网站(http://www.salars.cn/bbs/forumdisplay.php?fid=130)论坛。
“一带一路”的提出,在权力实践上打开了与中亚交流的政治通道。同时,与此具有共生关系的新一轮“学术建构”也掀起了舆论热潮,撒拉族相关的“学术书写”不可避免甚至颇具优势的和政治话语保持了一致性的表述,“与土库曼人在历史记忆、共同语言等方面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撒拉族“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实现‘民心相通’的潜在条件,”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疏通与中亚各国沟通的心理和民间渠道,使之为国家战略服务”。[16]
由此可见,尽管民族志“撰写人”更换为少数民族主体,但文化表述仍然难以真正摆脱权力关系的影响,这说明“知识书写”所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实质上是权力关系已经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的自我构建和自我呈现的认知结构中,并形成一种先决性模式,预先制定了一整套叙述规则、叙述逻辑以及叙述合法性等系统性的问题[17]。而且,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书写”来说,存在着“西方学术霸权话语”和“中国学术-权力话语实践”的双重互动,少数民族“撰写人”可以利用“西方反思性的学术话语”质疑、批判“国族主义”政治框架下本民族“被书写”的“无主体”的历史事实;也可以在中国“学术-权力话语”的政治许可框架下为本民族“正名”。
但这些“学术书写”对于试图通过“西方学术反思”真正重新建构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超越“非西方”或者所有“地方”知识体系的“新范式”来说,仍然是举步维艰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文化表述”与“历史撰写”的碎片化趋向也许是通向“新范式”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但无论未来理论趋向如何,必须意识到权力的预设确实是“写文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完全有效抵制的结构性话语。对于知识建构与权力相互作用的关系,康纳顿在《导论》中也认为“历史书写”的记忆选择的本质还是权利。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以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18]
三、对“知识书写”的再反思
上述论述是以循化撒拉族历史书写为个案,着重分析相关少数民族“学术书写”背后所隐含的知识-权力对文化重构的作用,但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路径来看,还应该有更深一步的反思。
首先,要防止在认识论上把知识话语化约为权力,片面强调正式话语和制度性反思的外在建构作用,似乎“话语”纯粹是主体被抛入权力网络的“官方表述”,而与主体内在即时性和个人性的能动行为完全撇清了关系。其实,在主体、话语和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作用。正如布迪厄在反驳福柯“知识-权力”路径“把主体和情境从话语分析中驱逐出去”时所指出的,知识是在人们的日常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但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并不总是处于知识的指导之下,更多是一种“惯习”,这种默会性知识与“生存性心态”、“例行化”和“共享现实”相对应。[19]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国家”的现代权力体系也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方言性印刷语言”基础上进行历史叙述和“现代”想象的“文化人造物”。安德森曾就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超越以往表层的政治认识,将民族主义放在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叙述中来理解,把它与人类的“心态史”和文化变迁的历史结合起来,在“民族认同建构”与“历史叙述”之间探寻动因[20]。给予了主体意识“深层次意识建构”的能动性地位。
这种对包括现代性的国族政治在内的所有权力体系背后的“心态观念”及其所塑造的“知识结构”体系的强调,也是知识社会学对现代西方知识论支配下所产生的国族主义主张的颠覆性力量所在。由此对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知识社会系统的比较研究有待重新开拓。[21]
其次,从“心态精神-知识社会”的路径出发,针对在“国族”、“社会共同体”与“西方式世界体系”之间的“文化书写”困境,王铭铭所提出的用冠以“文明”名号的“超社会体系”概念则不失为一个具有正当性的途径。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接近于“地区性关系体系”,是以考古知识-宗教宇宙观的文明板块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知识、制度与‘风俗习惯’。”[22]
最后,回归撒拉族的“知识书写”的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混杂的知识实践一直就处于超越其社会共同体的背景状态中。无论是“番”与“回”的混合认知还是“撒拉尔-中亚”的历史回想,都可以体察到知识撰写主体经验“心态”的介入与变化,并由此形塑着现实的转化。这些心态史的感受和直觉体验也是“文化书写”指向超越性的根本所在。
[1] 方清云.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精英意识与民族认同——以当代畲族文化重构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2]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9-30.
[3] 芈一之.撒拉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4] (清)龚景瀚.循化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155.
[5] (法)英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0-43.
[6]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7]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知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马成俊.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08(1).
[9]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3-159.
[10] 马海云.番回还是回番?汉回还是回民?——18世纪甘肃的撒拉尔族群界定与清朝行政变革[J].李丽琴,马成俊,译校.青海民族研究,2009(2).
[11] 常海燕.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2] 赵玉中.民族文化的“本质化”建构——以白族知识精英有关“本主”崇拜的学术书写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3] 马成俊.1781年教争: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14] 马成俊.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兼谈撒拉族语言、族源及其他[J].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2(1).
[15] 马伟.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J].青海民族研究,2008(1).
[16] 马成俊,于晓陆,王雪.论撒拉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17] 蔡圣晗,黄剑波.权力、阐释和现代性——论阿萨德对宗教的谱系学研究[M]//金泽,李华伟.宗教社会学(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4-126.
[18] 高源.读《社会如何记忆》[J].西北民族研究,2007(2).
[19] 赵万里,穆滢潭.福柯与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转向[J].天津社会科学,2012(5).
[20]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4-17.
[21] 杨清媚.“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围绕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J].社会,2015(4).
[22] 王铭铭.《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前言[J].西北民族研究,2015(1).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07-1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再造与民族格局稳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伊斯兰民族撒拉族为个案”(项目编号:14JYC850003)。
常海燕(1978- ),女,山西临汾人,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民族历史人类学;满珂(1976- ),女,河南平顶山人,副教授,人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民族历史人类学。
C958“232”
A
1004-941(2016)06-008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