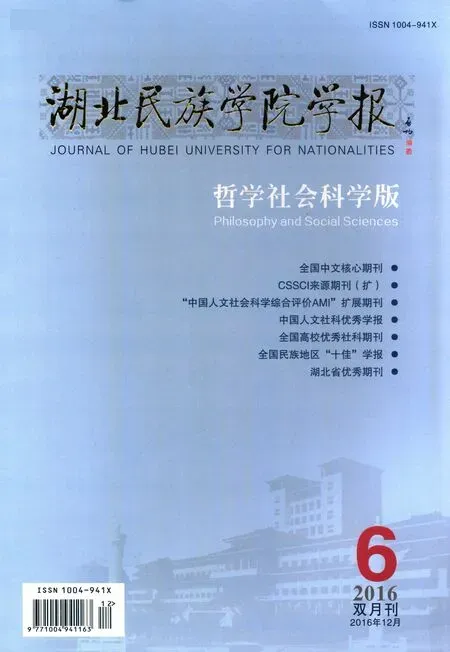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刑事变通立法初探
张继钢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法律系,广西 南宁 530023)
民族自治地方生态环境刑事变通立法初探
张继钢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法律系,广西 南宁 530023)
民族区域自治权、立法权限划分、刑法授权性规定、环境的区域性、动刑保护环境的民族传统、地方环境立法实践以及环境刑事地方立法国外经验,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立法的理据。自治区或省、直辖市的人大可以生态环境污染犯罪为突破口,通过细化违反环境污染管理法规情形、分解污染环境罪罪名、完善非刑罚方法等激活刑法中变通或补充规定条款,尝试制定特别的单行的地方环境刑法,探索积累生态文明建设刑事立法保障的地方经验。
生态保护;环境犯罪;刑事变通立法;民族自治地方
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充分发挥原始禁忌以及传统习惯等所具有的生态保护作用和功能,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但尽管如此,由于生态环境本身较为脆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民族地区不同程度地也存在环境问题,生态污染较为严重。在动刑保护环境已成为世界趋势的当下,民族自治地方如何启动环境刑事立法权,制定符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环境变通或补充刑法,对于加大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力度、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以生态环境污染犯罪为突破口,探讨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立法,以期对建设生态广西、美丽广西乃至生态中国、美丽中国有所裨益。
一、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立法的理据
(一)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行使
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包括民族立法在内的广泛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权首先规定在我国根本大法中,涉及经2004年修正的宪法第4条、第115条以及第116条等,其次专门规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经2001年修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专章即第3章共27个条文(自第19条至第45条)对民族区域自治权进行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包括立法、环境保护等在内。因此,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环境刑事立法权具有合宪性,不仅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权,而且可以使民族法制更能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
(二)立法权限的划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极不均衡的国情决定,立法既注重统一性、原则性,又注重分权性、灵活性。我国奉行中央统一领导、一定程度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根据经2015年修正的立法法第72条、第7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仅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且立法法特别强调,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就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专门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还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作出变通规定。
(三)直接的法律依据
如果说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等是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刑事立法权的间接依据,那么,刑法则是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刑事立法权的直接法律依据。我国刑法第90条*1997年刑法第9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或补充刑法的授权性规定,根据该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行使刑事立法权即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权,应遵循以下几点要求:一是非民族自治地方不可以行使地方刑事立法权;二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权由省级权力机关即自治区或其他自治地方所在省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三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仅限于与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而不是排斥全部刑法的适用;四是民族自治地方省级人大要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制定,不得脱离地方实际,不得与刑法基本原则冲突;五是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变通或者补充刑法规定,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四)环境的区域性
环境一词人们频繁使用。环境首先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在环境科学上,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外部世界;环境科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进而透视到法学中,即环境法学是借助环境科学上的环境概念,也将环境理解人类环境;环境法上的环境概念也大致如此。环境科学、法学以及立法中的环境定义大同小异,可从中抽象其共同意蕴,即环境通常指以某主体为中心的外部,内涵上强调自然因素。最广义而言,环境指人类的环境以及其它生物体的环境结合而成的相互影响的整体。首先,环境法的称谓本身有所不同。如欧洲国家称环境法为污染控制法,日本称环境法为公害法,前苏联称环境法为自然保护法,我国称环境法为环境保护法,源于各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及环境立法重点不同,但本质并无太大差异[1]。其次,环境法中的环境概念相对确定。以我国环境保护法为例观之。2014年修订的环保法规定的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等”。 此前,我国1979年试行的环保法第3条、1989年环保法第2条也规定了环境的含义。比较三者,在人类的外部情况这一核心意义上,三者没有变化,而且始终以自然因素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第三,注重环境要素的系统性,加强环境的整体保护。因为环境问题所侵害的不仅仅是人身或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生态平衡以及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可见,环境的立法概念既一脉相承,又略有变化,表明立法者对环境的概念认识不断深化。环境不仅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也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因为,在各个不同层次或不同空间的地域,环境的结构方式、组织程度、能量流动规模、途径、稳定性程度等都具有一定特殊性,呈现出区域性特征[2]。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已为事实所证明。这里以广西污染物排放量(见表一)为例略作分析。2011~2014年,广西废水排放总量较大,基本稳居全国第13位。其中,2012年广西农副食品废水排放量高居全国第一,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铅、砷排放量均为全国第二,镉排放量全国第三;2013年广西工业废水中汞排放量居全国第二,铅排放量居全国第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砷排放量居全国第一,汞、铅排放量居全国第二,镉排放量居全国第三[3]。这表明,广西生态污染呈现结构性污染,即重金属污染严重,从而显示出生态污染的鲜明区域性特征。

表一:广西污染物排放(产生)统计
(五)动刑保护生态环境的民族传统
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地方,有壮、瑶、仫佬、仡佬、毛南、京、水等12个世居民族。在壮民族语言中,“那”有稻田之意,泛指田地或土地。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壮民族以“那”为本,依“那”而居,据“那”而作,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那文化”,即土地文化或稻作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观念是:“有森林才有水,有水才能种稻,有稻才能活人。”[4]“那文化”中有许多环境保护习俗,包括敬奉土地、尊重水源、保护林木、保护动物等,例如,壮族忌在祭祀场所及神灵出入的森林里乱砍滥伐,忌丢脏东西、解大小便和吐痰[4];村口林木、坟头树和寺庙前后的树木、村前庄后高岗高阜上的树木、房前屋后的树木等不得砍伐[5];祭山祭水时,严禁女人进入、严禁生人过往;不能伤害青蛙等等,这些民俗长期指导和规范着壮民族的生活和生产。“那文化”侧重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体现的是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保护自然的态度和精神,有利于壮民族乃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壮民族通过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祭祀礼仪以及传统习惯等途径,保护生态环境,并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进行规制惩罚。如对于滥砍滥伐林木者,不仅罚款,而且还要补种树木、重祭等。除了壮族,其他少数民族也注重动刑保护环境。瑶族的环境刑事处罚习惯有罚款、赔偿损失、游村喊寨、逐出村寨等方式[6]。壮、瑶等民族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惩罚不仅类型丰富,而且体现出严厉处罚的倾向和立场。
(六)地方环境立法实践
研究表明, 截止1997年9月,针对法律制定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规定共45个,其中,变通规定27个,补充规定18个;主要是针对婚姻法的,共有36个,其它分别为选举法5个、继承法3个、森林法1个;制定变通、补充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涉及除广西外的4个自治区[7]。涉及生态环境的变通立法为1996年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出台的《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变通规定》,该变通规定系民族自治地方关于生态保护的第一个变通规定,其将生态保护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增加许多具有操作性的条款,对国家森林立法作出一定贡献,不仅提升了民族环境立法的地位,也提高了国家对民族变通立法的重视程度[8]。广西虽然欠缺制定变通、补充规定的实践,但具有丰富的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地方立法实践和经验。自2006年起,广西不断加强加快环境保护领域立法,先后制定《环境保护条例》《渔业管理实施办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农业环境保护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广西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广西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基本形成了广西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生态广西、美丽广西建设提供了有效法治保障。广西部分环境保护立法规定有刑事责任,如《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68条、69条第2、3、4款、第74条规定依法追究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涉及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非法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尽管这些只是属于提示性的注意规范,但包含刑事责任条款的民族自治地方环保立法无疑将在国家环境刑事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
(七)环境刑事地方立法国外经验借鉴
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国外有地方立法的成功范例。在澳大利亚,保护和管制环境的主要责任由州承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开创地方制定环境刑法的先河,制定了具有代表性且极具特色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该法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第一,在立法模式上,属于独立的单行环境刑事法规,而且融实体法、程序法于一体,该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诉讼程序,包括环境犯罪一般首先向土地和环境法院提起诉讼,并根据罪刑轻重可先适用简易程序,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有些情况下负有合法许可的举证责任等内容[9];第二,突破原有的过失理论,将环境犯罪界定为故意或过失以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的方式实施的违反环境法律规定的行为;第三,用代理刑事责任替代传统的公司责任原则,规定公司的管理人员、雇员、代理人员在职权范围内实施行为时的意图就是公司的意图,公司对其行为担责;第四,将环境犯罪分为重罪和轻罪两类[10]。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为地方环境刑事立法提供了成功范例和有益借鉴。
二、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立法的建构
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事立法的建构,就是由自治区或省、直辖市的人大激活刑法中变通或补充规定这一沉睡条款,尝试行使地方刑事立法权,制定环境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或补充环境刑法,涉及立法主体、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等方面。
(一)立法主体
立法主体涉及制定主体、批准主体。制定变通或补充刑法的主体为民族自治区或其他民族自治地方所在省、直辖市[11]*根据刑法第90条的规定,制定变通刑法的主体不包括直辖市人大。但是,直辖市与自治区、省为同一级的行政区划,而且有的直辖市辖内有民族自治地方,如重庆市,因此,直辖市人大没有刑法变通权属于立法疏漏。当然,从时间看,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议案与现行刑法修订议案同在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建议未来修订刑法时,对此进行修改补正。的人民代表大会,这表明,第一,非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无权制定变通或补充刑法;第二,非自治区或其他非自治地方所在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无权制定变通或补充刑法,民族自治地方省级人大常务委员会亦无刑法变通或补充权。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变通或补充刑法并不是自动生效实施,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即变通或补充刑法的批准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二)立法形式
这里的立法形式主要是指规范性文件的表现形式,变通或补充规定只能采用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的立法形式。本文主张,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宜采用单行条例的立法形式。因为,第一,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有别。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综合性的规范性文件,主要规定基本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自治机关职权等重大问题;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特点和实际需要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单项规范性文件。第二,与刑法的立法模式或表现形式相关。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三种,由于变通或补充规定是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就刑法典的某种犯罪或某部分犯罪而对刑法典变通、补充所形成,这与单行刑法形式一致或相符,从而,一则不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典的修改即刑法修正案,不宜再视为狭义的刑法典;二则由于仅仅是对刑法典的变通或补充,其仍属于纯粹的刑事法律,因而显然不属于在环境行政法中规定环境犯罪刑罚罚则的附属刑法。第三,本文选取环境犯罪尤其是生态环境污染犯罪,以其作为启动民族自治地方刑事立法权的突破口。这是首先,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现状看,未曾行使刑事立法变通权,制定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使刑法中的变通或补充条款处于沉睡状态。为了增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动性、针对性、民族性、地域性,全面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推进地方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必须唤醒刑法变通沉睡条款。其次,鉴于我国尚无民族自治地方刑事变通立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变通或者补充刑法的规定必须审慎进行,可在较小范围内进行立法尝试。选择环境犯罪作为地方刑事立法权的突破口,这是因为,我国刑法规定对环境犯罪并不完全适用于民族地区,以乱砍乱伐林木为例,有的少数民族并不认为该行为是犯罪,有的少数民族则认为是犯罪,而且应从重处罚。再次,环境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类犯罪或一部分犯罪,是所有危害环境的犯罪的统称,可以分为环境污染型犯罪和环境破坏型犯罪,前者是指向环境中添加某种物质或能量,由于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污染或者有污染风险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增加因素使环境污染”,在刑法中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后者是指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使动物、植物、土地、森林、湿地等生态环境破坏或者有破坏风险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减少因素使环境破坏”,在刑法中表现为破坏环境犯罪。从具体罪名来看,环境污染型犯罪涉及罪名较少,因此,宜将污染型环境犯罪作为突破口进行尝试变通立法。最后,我国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既有水体污染,也有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广西作为壮族聚居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加之经济增长方式仍较粗放,环境压力较大,造成土地石漠化严重、土地退化问题突出,沿海海域以及主要河流部分河段工业废水尤其是含重金属废水污染突出、农业面源由于农药化肥较大强度使用污染日趋严重,空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酸雨频率居高不下等等。
(三)立法内容
民族自治地方环境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要针对当地民族的生态环境实际和特点,内容应限于与自治民族特殊的环境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相关的部分,并且不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具体到广西,就是根据壮民族“那文化”中的敬奉土地、尊重水源、保护动物、保护森林和古树林木等环境保护习俗与传统对现行刑法进行变通,涉及污染环境犯罪的成立要求及其刑事责任,具体包括细化违反环境污染管理法规情形、分解污染环境罪罪名、增设非刑罚方法等实体内容以及相关程序性内容。
1.细化违反环境污染管理法规情形
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涉及到不同世代甚至不同物种间的资源分配,甚至还涉及到如何看待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科技、教育、行政和法律等多元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行政法律规制仍是最基本和最适合的环境管制手段。环境犯罪具有行政犯属性或特征,即其对环境行政法律规范具有高度依附关系,表现为环境犯罪的成立以违反环境行政管理法规为前提。违反环境行政管理法规在各国环境犯罪罪状中存在不同表述:我国刑法规定的第338条、第339条第1款、第339条第2款、第340条、第341条第2款、第342条、第343条第1款、第343条第2款、第344条、第345条第2款等法条仅指出违反的环境行政法律法规的名称或笼统指出违反国家规定;德国刑法规定的第324条、324条a、第325条、第325条a、第326条、第327条、第328条、第329条等指出,犯罪的成立违反环境行政法律法规,或者违反行政法义务或违反行政许可;俄罗斯刑法规定的第246条、247条、248条、249条、251条、252条、253条、254条、255条、257条、259条、262条等法条指出,犯罪的成立需违反环境保护的立法、制度、规则等。这种需要参照其他环境行政法律法规才成立犯罪的规定在理论上称为空白罪状,使得入罪标准不够明确。鉴于我国法源的多样性,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的明确性和司法操作性,并减少对行政规范的依赖,应适度明确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即环境犯罪应进一步细化相关条文表述中的“违反国家规定”、“违反某某管理法规”之具体情形,如将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细化为“违反环境污染管控法律、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行政许可等中关于污染物排放标准、方式等的规定”等。
实际上,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是为保护环境而规定的相应标准,包括全国性标准和地方标准,用以确定行为的危害程度及可能性,如果超此标准即为违反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已然表明行为的违法性。当然,违反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只是环境犯罪刑事违法性的前提条件,即违反环境行政法律法规必须与其他要件结合才能确定环境犯罪的成立。一般来说,危害环境的行为除了要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禁令或许可等外,还要具备造成侵害后果、形成危险状态或者创设风险等其他要件才构成犯罪。关于地方标准,应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地方性环境标准优先,即实施环境标准时,应优先适用地方性标准,地方标准要优位于国家标准适用[12];二是细化地方性环境标准。这与经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一致,该法第15条、第16规定,省级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据此,广西可以结合地方实际,一方面就国家没有规定的制定地方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就国家已有规定的制定更为严格的地方环境标准。具体来说,广西环境保护指标可以包括森林覆盖率、退化土地恢复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降水pH值年均值和酸雨频率、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严格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基于广西结构性污染严重,要严控食品(制糖、酒精、淀粉等)、造纸、化工、制药、矿产采选等重点工业行业的废水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特别是严格矿产采选行业的重金属废水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严格控制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是火电、钢铁、有色冶炼(包括铝铅锌等)、化工、建材等行业工业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及有毒有害废气的排放标准和排放总量;减少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的使用量和强度。
2.分解污染环境罪罪名
我国刑法规定的污染环境犯罪涉及第338条、第339条,前者规定的是污染环境罪*“两高”将1997刑法第338条规定的罪名确定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经2011《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罪名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后者规定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污染环境罪属于混合性罪名,不区分犯罪对象。这种对污染对象或犯罪对象不加区分的混合性立法,既不符合污染对象的各自特点和性质,也与环境保护管理法规不衔接。
从污染对象来看,主要涉及水体、土地和大气。水体既包括江河、湖泊、水库等内陆地表和地下水体即内陆水或一般意义上的水以及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海域水体即海洋,无论是面积、还是组成物质、对气候的影响等方面,海洋与内陆水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将海洋从水体中独立出来,与水或内陆水相对应。其实,我国环境保护立法早已将二者区分,表现在:虽然1979年试行的环境保护法只将水规定为环境要素,没有区分水与海洋,但1982年率先通过了专门防治海洋污染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84年才通过专门防治水污染的《水污染防治法》;在单行环境法的基础上,1989年通过的环境基本法第2条明确将海洋规定为独立的环境要素。首先,污染对象即水、海洋、大气和土地等环境要素不仅性质和成分不同,而且环境容量和环境自净能力也不同。其次,各种环境要素的危害机理、危害后果也有差异:由于大气流动性大、易扩散,污染一般可跨越地理界限的限制,从而难以有效治理;水具有流动性,扩散较快,由于河流、湖泊流域相对有限,较易治理;土地则不具有流动性,污染扩散速度相对较慢,土地自身污染的后果不可能立刻显现,治理较难。正因为如此,对土地污染成立犯罪的要求应该最低,对大气污染犯罪的要求相对高一些,对水污染犯罪的要求最严,即应针对水、大气和土地等不同的污染对象规定不同的犯罪成立要求。实际上,1996年8月8日的刑法分则修改草稿表明了这一点,该草稿不仅用三个条文分别规定3种犯罪:水体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和土地污染罪,而且犯罪成立要求不同:水体污染犯罪成立要求实际危害后果,大气污染犯罪成立要求足以严重污染环境,土地污染犯罪成立既不要求实际污染环境的后果,也不要求足以严重污染环境。[13]
从环境保护管理法规来看,我国是分别规定具体污染环境犯罪的,包括1982年通过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规定的污染海洋罪、1984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第43条规定的污染水罪、1987年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7条规定的污染大气罪。可见,这些环境管理法规即附属刑法采取的是独立性罪名模式,即规定的是具体的环境污染犯罪。然而,我们看到的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污染环境罪无视环保基本法和环境保护单行法,既没有将海洋污染从水污染中分离,也没有区分土地、水体、空气污染,而是将三种环境要素即土地、水体和大气作为犯罪对象合并在一起而不是分开规定,罪状要求统一而不是分别制定罪状,即污染环境犯罪的成立必须具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由此看来,对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独立罪名,不仅符合污染对象的性质,而且与环境行政法相衔接,还有立法沿革支撑。仅以“这考虑到以污染对象的性质来区分规定的立法模式过于繁琐,而且犯罪成立的要求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为由[14],1997刑法就变这些独立性罪名为概括性罪名的依据显然不足。因此,本文建议分解污染环境罪罪名。作为变通刑法的尝试,应审慎进行,不宜完全分解该罪,实际上也做不到;宜适度分解该罪,即在保留原罪名的情况下,将重要的环境要素即水、海洋、空气、土地分离出来,规定独立的污染犯罪,即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污染水罪、污染海洋罪、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二者为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关系。将该罪罪名分解不仅具有理论依据和立法基础,而且利于与国际接轨,还符合实际。从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看,国外多采独立性罪名模式,如德国刑法分别规定污染水域罪、污染土地罪和污染空气罪,俄罗斯刑法将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分别规定,美国附属环境刑法规定有空气污染罪、污染水域罪等等。从区情看,广西是惟一拥有海陆空的民族自治地方,但土地少,分布零星,土层薄易被污染腐蚀,土地肥力差;广西以前属于内陆省份,直到1952年才有出海口和海岸线,即拥有海洋;水对于以水田或稻作为文化传统的壮民族意义重大,因此,考虑对不同环境要素的污染规定不同的犯罪,既符合不同环境要素所具有的各自特点也符合广西实际情况。
3.增设非刑罚措施
污染环境犯罪是对环境的严重侵害,但环境具有一定的可修复性,因此,追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应对环境的修复起到促进作用。换言之,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鉴于环境的修复包括自然修复和人为修复,这里强调的是人为修复,即当被侵害的存在修复可能性和可行性时,通过环境加害方的修复行为,使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回复相对的动态的稳定的平衡状态。显然,作为主要刑事责任方式的刑罚无助于被污染或被破坏的环境的修复,只有作为刑事责任方式之一的非刑罚方法有此功效并可达此效果。因此,对环境加害人配置和适用生态修复性刑事责任方式即非刑罚方法,令其修复环境,不仅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而且利于找到合理有效的修复环境的方法,还有利于加害人体验污染或破坏环境易修复环境难进而改过自新。
修复性司法以及修复的刑事责任根据成为修复性非刑罚方法的存在依据,实务中,司法实践已经探索并积累出一定修复经验,特别是补种复绿或补植复绿的森林资源修复经验。因此,一方面,应将该行之有效的非刑罚方法规定在变通刑事立法中,并扩大适用,可将森林资源的修复方法即补种配置在环境犯罪变通刑法中,并拓展适用于水、空气、土壤污染型环境犯罪的修复、矿产资源犯罪的修复、非法狩猎犯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修复等等。对大气污染型环境犯罪,可采用复植补种方式,通过种植净化空气能力较强的林木达到修复被污染的空气之目的;对土地污染犯罪,亦可用补种林木的方式修复被污染的土壤,如在矿山废弃地污染区种植耐性植物、具有超富集性的植物,如马尾松、桂花、毛竹、速生桉、白茅、飞蓬、马唐、商陆、耳草、芒萁、地瓜榕等,以利于恢复植被。另一方面,发展创设新的切实可行的生态修复性非刑罚措施和方法,并将其规定在环境犯罪变通刑事立法中,如对于破坏矿产资源犯罪的责令被告人补植复绿、渣土回填、人工护坡等方式尽可能地恢复矿区原貌,还可以责令被告人购买至少等量的矿产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并储存起来达到矿产修复之效果;对于破坏动物资源犯罪,陆生野生动物的修复可采取判令被告人对生态失衡地区的野生动物进行巡山管护一定期间,以野生动物不再被猎杀并恢复到一定数量作为修复效果;水生动物如鱼类的修复可通过投放相应鱼苗的方式进行水上生态的修复;关于水污染犯罪的生态修复性非刑罚方式,有补水、投放鱼苗、生物护岸、河道清淤等,投放鱼苗主要是因为鱼能消化一部分水体污染物,从而可达修复被污染的水环境之目的;关于土地污染犯罪的生态修复性非刑罚方法,有表土覆盖、添加营养物质、有机肥料等。当然,可修复与不可修复是相对的。一般来说,矿产资源犯罪破坏的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不可修复的,但是开采矿产资源必然要破坏植被、占用土地,而被破坏的植被、被占用的土地是可以修复的;一般林木是可以通过补种修复的,但重点保护的珍贵林木如红豆杉由于生长周期长而且主要是靠自然成材从而难以修复甚至不可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法律责任部分已有生态修复性非刑罚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补种(第69条第3、5款)、退耕、恢复植被(第70条)、限期治理(第72条、第79条第2款)、代为治理(第72条)、采取补救措施(第69条第1、2款、第70条、第72条、第73条、第76条、第77条、第78条、第79条2款、第80条)。该条例不仅规定了上述非刑罚方法的种类,还规定了相应的操作方式,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以补种为例,第69条规定:对于盗伐林木的补种10倍以上,滥伐的补种5倍以上,砍柴放牧毁坏的补种1倍以上3倍以下;又如限期治理,第72条规定:对于逾期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而且,该条例是保护漓江流域生态环境的专门性立法。因此,可以说,该条例的制定为广西自治立法尤其是制定变通刑法积累了一定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第一,在法律形式上,毕竟该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而非变通法律、法规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第二,在责任方式上,该条例规定的非刑罚方法是作为行政责任方式而不是作为刑事责任方式存在的;第三,在责任内容方面,该条例具有一定可操作性但处罚个别化程度仍较低。因此,建议广西在制定变通刑法时,名称上使用立法法专有的单行条例称谓;将该条例中规定的生态修复性责任方式即相关非刑罚方法直接规定在变通刑法中,以避免有违罪刑法定之嫌;对于具体的非刑罚方法即生态修复性方式或补救措施,由法院综合考虑环境犯罪的类型、危害的环境要素以及个人情况而决定,包括修复方式、修复数量或期限以及修复效果,以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并体现处罚的个别化,如以补种为修复方式,以1000株为修复数量,抚育3年为修复期限,成活率达90%以上为修复效果。
4.包容有关程序性规定
增加程序性规定,使变通刑法成为融实体与程序为一体的综合性立法。程序与实体相结合,既包括行政实体程序与刑事实体程序的结合,也包括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的结合。对于前者而言,由于环境犯罪具有行政犯属性,从而对行政法律法规具有依赖性。由于两者的规制对象具有竞合性,差异只在于危害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二者难以区分,且环境行政处理程序没有刑事程序严格,因此,当行政措施失效时,如何启动刑事程序,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现实中成为有法不依之漏洞。显然,行政与刑事实体程序两者配合协作可有效追究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对于后者,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既离不开环境刑事实体法,也离不开环境刑事程序法。环境犯罪极具特殊性,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性,但环境犯罪的追究仅适用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缺少与环境犯罪相适宜的单独的环境刑事诉讼程序,自然就无所谓程序与实体的结合问题。然而,单靠环境刑事实体法去追诉环境犯罪难以达到保护和恢复环境之目的。环境犯罪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结合,不仅从理论上体现出体系性和协调性,在实践中也可以避免由于实体法的专业性而导致程序法需求的特殊性[14]。这方面有成功立法例,如日本的《公害罪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都是融实体法、程序法于一体的独立的单行环境刑法。毕竟尚无变通刑事立法先例,对制定变通刑法宜审慎把握,变通的范围也不能过大,仅建议对环境犯罪的管辖、审判组织以及法律援助进行变通。关于管辖,可尝试规定设立专门环保法院或环保法庭,集中管辖某一区域、流域等的所有环境案件,包括环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关于审判组织,可尝试规定环境案件审判组织由法官和技术专家组成,以弥补环境司法人员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不足;关于法律援助,可以尝试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环境犯罪被告人以及因环境污染致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1] 林健三.环境保护法规(4版)[M].新北:全威图书有限公司,2012:15.
[2] 郭建安,张桂荣.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10.
[3] 环境统计年报[EB/OL].http://www.mep.gov.cn/zwgk/hjtj/.2016-03-06.
[4] 王明富,严火其.文山壮族“那文化”的现代启示[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5] 张万友.浅析壮族习惯法[J].绥化学院学报,2006(5).
[6] 高其才.瑶族刑事处罚习惯法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9-21.
[7] 袁承东.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补充规定的现状与思考[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8] 乔世明.民族自治地方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26-29.
[9] 徐平.环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93.
[10] 赵秉志.环境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7-198.
[11] 仝其宪.民族刑法变通权的理论境域[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2] 朴光洙.环境法与环境执法[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20.
[13] 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1-562.
[14] 傅学良.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环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78.
责任编辑:胡 晓
2016-05-18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5BFX004)。
张继钢(1977- ),男,河南邓州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犯罪。
D921.8
A
1004-941(2016)06-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