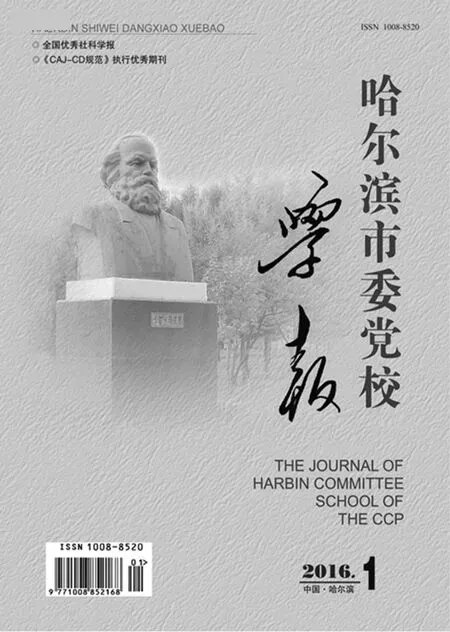参与式预算的中国探索:价值、缺陷及路径优化
谭诗赞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探索:价值、缺陷及路径优化
谭诗赞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公民对传统预算决策体制的不满以及参与式治理在地方治理变革中的运用,直接催生了参与式预算的产生。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政府预算改革引入参与式预算提供了借鉴。参与式预算是我国地方参与式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参与式预算的探索,深化了基层自治的实践,激活了基层人大的预算审议和预算监督功能,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利益调整和社会稳定。但我国参与式预算的探索在制度化和代表性上依旧存在严重的不足,所以参与式预算改革需要针对这些不足,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并结合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这三个主要阶段进行路径优化,以此提升参与式预算在地方参与式治理中应有的治理绩效。
关键词:参与式预算;参与式治理;共建共享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三五”攻坚期必须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意味着在地方治理层面需要社会公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更多地参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共建共享”,因此,参与式治理也成为地方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抉择。参与式治理“是指由地方政府培育的旨在通过向普通公民开放公共政策过程以解决实际公共管理问题的制度与过程的总和”[1],而政府的公共预算同样是地方参与式治理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政府的公共“预算就是政治,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谁获利谁损失或谁受益谁支付”[2],而且“几乎每一项政府决策都有预算含义,因为决策制定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稀缺资源在可选用途中的分配”[3],一般而言,参与式预算是指由普通公民及其代表来决定一部分公共预算支出优先顺序的决策机制或过程。参与式预算的一般程序是由当地居民和社区所有群体的代表,共同讨论支出的优先顺序,提出公共资源分配计划,并且最后投票决定。因此,公共预算过程的透明性、开放性关乎公众“获得感”的提升。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习惯以预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高为由,将普通公民排斥在预算决策过程之外,预算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不透明的预算过程使政府和普通公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容易导致政府官员的寻租和腐败,损害公众在发展过程中的“共享”,对社会大众“获得感”的提升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克服政府在预算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保障公共利益,我国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深入和推广蓄势待发。
一、 国外参与式预算的兴起和实践
20世纪后半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日益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权力,强调议会至上的代议制民主开始走向衰落。先进工业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议会民主走向行政集权的变革过程: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统或总理(首相)的权力得到不断的扩张,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政府首脑通过控制本党的议员控制和操纵国会的立法,国家预算和国家重要政策的制定权实际上由代议机构滑向行政机关。政府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出于预算的专业性考量,主要依靠技术官僚和专家咨询系统进行决策,而将普通公民排斥在预算决策的封闭系统之外。
在传统的预算决策体制中,公民的参与一般都是间接的参与,但这种间接参与在政治实际运行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政府的预算决策由于缺乏社会公众的控制和监督,往往容易产生对民众利益诉求的“无感”现象,时常出现公共资源背离公共服务宗旨的政府预算决策行为。因此,普通公民希望直接参与到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那部分预算的决策进程中。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式预算应运而生。
参与式预算在国外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初期探索阶段(1989—1997年),巴西阿雷格里港市首开先例,这一阶段的参与式预算仅在巴西境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开展;第二个阶段是其巩固发展阶段(1997—2000年),在该阶段,参与式预算在巴西境内迅速扩展,先后有130个城市采用了参与式预算,通过这一形式,城市的普通居民而不是政治精英取得了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公共资源的分配权;第三个阶段是参与式预算的迅速扩张阶段(2000年—),参与式预算从南美洲扩展到全世界,超过1 500个城市、社区和机构开展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试验。
国外的参与式预算在实践中也大致呈现出三种具体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将市级政府预算中的一部分预算交由普通公民和公民社团决定,以巴西阿雷格里港市为代表;第二种形态是将某一社区的全部特定专款交由当地居民和社区所有群体的代表经过协商和投票决定,这种形态以纽约和芝加哥市议员的分配款改革最具代表性;第三种形态是将市级政府预算的一部分预算交由特定人群讨论、投票决定,这种形态以美国波士顿的青年参与式预算为代表。
目前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实施参与式预算。在实践中,各地参与式预算的侧重点也不同,如美国华盛顿特区“公民峰会”、南非的“非政府组织预算监控”、印度DISHA “预算公开和支出跟踪”等都分别突出了其地方特色。参与式预算一般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实行,而且主要都集中在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资本预算,即关于各种公共设施建设投资的预算。也有少部分城市(特别是在巴西的一些城市)将所有的预算资金安排纳入公民参与的范围。在参与环节上,主要是在政府的预算编制环节,同时也有在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阶段存在吸纳公民参与的环节。从理论上讲,政府公共预算的各个领域的决策及其活动都是可以采用公民参与的,但从各国经验来看,公民参与预算主要适用于公共支出的安排即资金的分配,以及预算通过后的项目实施。在支出决策领域,绝大部分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地方都主要选择资本性支出作为公民参与预算的重点领域。
参与式预算的出现有助于推动这一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参与式预算在世界各国中的实践日益增多。随着参与式预算在世界的扩展和传播,其影响也越来越大,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地区也日益增多。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从21世纪初在地方政府层级也开始了其具有本土色彩的参与式预算探索。
二、我国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价值
近年来,在我国的温岭、哈尔滨、无锡、上海、佛山、焦作、淮南等地,在地方党政官员和专家学者的联手推动下陆续出现了公众参与预算的实践尝试。我国的参与式预算缘何产生?首先,其该归因于国外参与式预算实践的民主效应及其在国际上的传播。其次,我国参与式预算的产生离不开协商民主的引入,协商民主理论的引入为我国参与式预算的产生提供了民主理论支撑。再次,中国参与式预算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和博弈:公民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地方政府官员创新的动力、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和大众媒体的宣传推广等共同推动了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探索。
我国的参与式预算起步时间比较晚,但目前参与式预算的探索日益增多,我国的参与式预算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和县(区)这两级。参与式预算的基本做法是将民众代表与人大代表共同参与的公共协商和人大正式的预算审议和监督对接,而在实践中则采取了两种各有侧重的形式。其一,是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相结合。在这种形式中,普通公众主要在预算初审阶段中参与,但公众的建议只发挥预算决策咨询的辅助作用,基层人大代表才具有实质性的预算决策权,这种形式以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最为典型。其二,是由社会精英(如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普通公民代表(包括在籍居户代表和非在籍的常住户代表)共同组成预算参与委员会或大会协商和投票决定预算支出优先顺序,这种形式在哈尔滨、无锡、佛山最为典型。但在街道层面,参与式预算又呈现出了另一种形态,如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启动的民政建设资金项目协商——“参与式立项”,由于街道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没有基层人大的机构设置,其做法比较接近国际通行的做法,就是由街道办事处从税收返还资金中拿出一笔钱作为社区民政资金,交由每个社区自主决定怎么花。为避免变成社区分钱,麦子店决定实施参与式立项,社区要想申请到资金,必须经过项目陈述、答辩、评审团投票。因而随着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探索不断的深入,将来还会出现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参与式预算”形态。
参与式预算在我国探索时间不长,但是随着社会大众参与热情的不断上涨和地方“参与式治理”改革试点的不断推广,其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一定的政策绩效。
(一)参与式预算深化了基层自治的实践
基层民主通常包含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四个“民主”。长期以来,基层的民主政治长期主要集中于基层民主选举的探索,“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长期流于形式。参与式预算是对过去部分农村的“村务民主管理”的深化和扩展,将公民的参与从村一级的财务预算管理延伸到了对政府预算的参与,如温岭市通过参与式预算“把民主恳谈会定位在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上,而且深化的重点放在民主决策方面”[4],参与式预算的探索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普通公民一般难以直接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旧状。
(二)参与式预算激活了基层人大的预算审议和预算监督功能
近年来,各级人大的预算监督功能在不断的强化,但总地来说,人大对预算的监督,依旧处于一个“程序合法,实质虚置”的尴尬境地。参与式预算的第一种类型,以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为代表。温岭市在镇街和部门层级“激活”了人大代表的预算审议和监督权,在会前初审阶段,人大代表通过民主恳谈会将普通公民的建议吸收纳入初审报告中;在人代会期间经过预算初审、联席会议、预算再审、预算修正议案表决等流程集中审查政府预算。在人大审议会后,设立常设的人大财经小组监督政府预算的实施。浙江温岭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实际上最大的功效就是通过参与式预算激活了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推动了基层人大的改革,坐实人大的权力机构地位。因此实施参与式预算,有利于加强基层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外部控制”。
(三)参与式预算同时也推动了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
参与式预算过程中强调的对话和公共协商契合了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因此参与式预算也被看作为地方治理中的一种典型的协商民主形式。参与式预算强调“面对面”的对话和协商,这种协商不仅仅存在于官民之间,也存在于作为非官方的参与者(人大代表和公民代表)之间。在参与式预算的民主恳谈过程中,通过对话和辩论,参与者可以发言,参与者发言以后政府要回应,要解释甚至表态公民意见是否有道理,通过对话来达成协议。通过公共协商,有助于打破政府预算决策的“黑箱”,扩大政府和普通公众之间的共识度,提升公众参与的热情和民主素质。因此,参与式预算通过公共协商扩大了公民的直接参与,推进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发展。
(四)参与式预算有助于提升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性
参与式预算为社会公众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它基本形成了包括自愿参与、邀请参与和随机抽选参与这三种参与的方式,在参与式预算中,不同的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参与方式。普通公民可以通过这三种参与方式进入民主协商程序直接参与预算决策过程中,有效地表达自己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参与过程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了公民参与的平等性,每个人参加民主恳谈会都有同等发言权,都可以发言。同时部分地方比如浙江温岭的人代会中,也设计了能够让非人大代表的普通公民也有可以表达意见的途径。这样激发了公民的有序参与的热情,相应地也就降低了无序参与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降低社会分裂的风险。
总之,参与式预算是地方参与式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普通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公共协商参与地方公共预算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符合了“参与式治理”对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穷人赋权的内在要求,因此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探索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内容,也有效促进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助于社会大众在公共预算决策中形成“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三、实践中与式预算的缺陷
尽管,参与式预算在推动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促进预算透明和民主以及提升地方政府合法性方面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但由于其还处于“试点”阶段,探索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我国参与式预算在实践中依旧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一)参与式预算的制度化不足,容易出现“人走政息”的现象
我国的参与式预算“是作为选举民主程度不足的弥补性改革以及制度创新路径而出现的”[5],我国参与式预算的探索严重依赖长官意志,使得参与式预算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由于参与式预算制度化不足的缺陷,使地方参与式改革容易出现“人走政息”的现象。如北京麦子店街道办事处由于街道工委书记的更替,其参与式立项模式也跟着改变,新上任的街道党工委书记改变了过去社区公众申请立项的方式,改由行政命令的方式,将100万资金平分给五个社区居委会,这笔资金由居民委员会主任决定,导致麦子店街道的参与式立项名存实亡。
(二)参与式预算的代表性不足,容易陷入“合法性”危机
由于大部分地区的参与式预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激活”基层人大的预算审议权,加强人大对政府预算中的部分与民生相关的预算项目的监督,其背后的公民参与其实是衍生出来的。这导致了在大部分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专家和地方精英在项目的最终确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6]。其次,随机的代表选择机制也存在内在的漏洞,实践中往往出现老人群体参与比例高过其他群体,最后社会资源分配也更倾向于这些群体的偏好。参与式预算代表性不足的缺陷容易形成“精英性协商”和利益相关人的“不在场”,容易导致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不公平,无法及时有效地满足社会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偏好和意愿,导致社会大众对参与式预算决策的不满,使参与式预算陷入“合法性”的危机之中。
四、参与式预算的优化路径
地方政府应该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价值取向下,借鉴国内外的优秀经验并结合本地的财政实况,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这三个主要阶段针对现存的问题进行完善。
(一)在预算编制阶段,需要从“非政策分享”型参与逐步过渡到“政策分享”型参与
在参与式预算中,“非政策分享”和“政策分享”的区别标准是“公民是否参与分享政策分析和制定”[7]。在前者,普通民众参与的主要功能是咨询,民众的建议并不具有法定的效力,它有待于政府官员在公共决策时的体察和认可。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实际活动,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就是“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8]。具体而言:在预算决策的信息征集阶段,政府应该通过协商式民意测验、公民会议、互联网公民论坛等公共协商平台加强官员、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普通公民之间实际的或虚拟的面对面的对话协商。在预算方案的选择阶段,地方政府应该推广像云南盐津参与式预算中的群众议事员的按人口比例抽选的制度设计,以此打破政府对民众代表人选的操控,提升公众参与的平等性;除了随机吸纳公民代表进入具有预算决策权的委员会以外,地方政府还可以将通过互联网公示符合条件的预算项目库,让合乎投票资格的居民直接通过互联网平台商议、投票决定参与式预算项目的优先顺序。
(二)在预算执行阶段,要“外部监督与内部控制并重,提高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全面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9]
在外部监督方面,要建立预算执行听证、预算执行联席会议、预算执行信息反馈机制,确保公众的意见能够及时有效的传达到参与式预算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能够确保工作小组的有效反馈。在内部控制方面,要建立规范的预算执行报告制度、项目绩效定期自评机制、面向绩效的内审制度以及规范灵活的支出管理。同时还应该利用网络化的参与平台,通过电话、互联网、公共信箱等交流渠道,使得居民能够在专家的帮助下,参与到财政的去向追踪,考察财政资金是否按照预定的方向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对预算单位形成压力,解决责任虚化的问题。
(三)在预算绩效评估阶段,要建构政府、专家学者、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全方位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具体就是需要在三个部分进行机制和制度创新:首先,督促项目承建方严格按照参与式预算项目的预定标准开展主体自评。其次,建立由政府、专家学者、居民代表和社会组织组成的项目效果评估小组进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外部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其技术指标的完成情况,更要将项目受惠地居民的满意度等效果指标纳入考评指标体系中。必要时还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中立的外部评价,以此作为预算效果评估的重要依据。再次,建立上级政府体系评估机制,上级评估重点应该关注预算投资计划的落实,侧重预算控制与预算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这样通过建构政府、专家学者、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全方位的预算绩效评估体系,引进成本—收益概念,对公共服务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形成科学的预算绩效反馈路径,使预算实施绩效的评估结果纳入下一年度参与式预算项目实施的决策依据。
只有将预算参与和政策绩效相结合,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评估置于一个完整的政策链上综合考虑,才能充分发挥参与式预算应有的效应,促进普通公民在地方参与式治理中的“共建共享”,提升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获得感”,增加地方政府在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进行基层治理变革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张紧跟.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
[2][美]阿伦·威尔达夫斯基,内奥米·凯顿.预算过程中的新政治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3-7.
[3]Arthur Smithies ,Budgeting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in Jack Rsbin(ed.),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F.E.Peacock Publishers,lnc.1975:268.
[4]贾西津.中国参与式民主的新发展——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创新模式分析[EB/O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313/55406.html.
[5][澳大利亚]何包钢.中国的参与式预算概览[C]//[法]伊夫·辛多默,等.亚欧参与式预算——民主参与的核心挑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5.
[6]贾西津.参与式预算的模式:云南盐津案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4,(5).
[7]Simenson,William & Mark D.Robbins.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resource allocation[M].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0:26.
[8][美]亨廷顿,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91.
[9]苟燕楠, 王逸帅. 参与式预算: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9,(1).
[责任编辑:王咏梅]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6)01-0075-05
作者简介:谭诗赞(1989-),男,湖南耒阳人,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