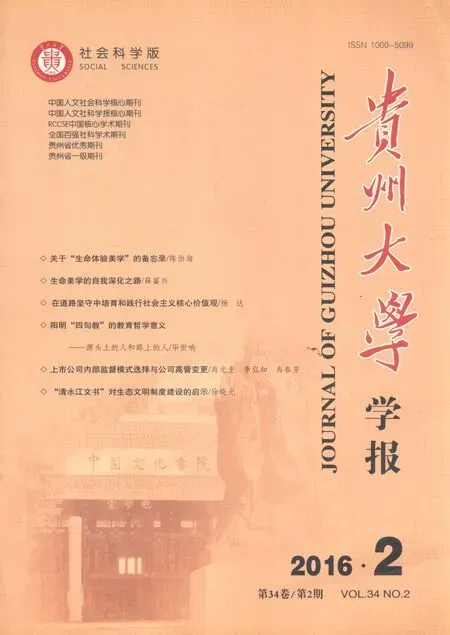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演进思想评析
刘 晗 龚芳敏,2
(1.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演进思想评析
刘晗1龚芳敏1,2
(1.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2.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保罗·莱文森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理论家中的中坚人物。他从媒介技术与现实关系的角度,将媒介技术的演进依次描述为玩具、镜子与艺术三种形态。同时他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理想进程并非所有媒介技术都能幸运地完成,这主要取决于媒介技术演进的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保罗·莱文森从单一媒介技术和媒介技术间两个角度,审视了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认为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是越来越人性化,而决定媒介技术演进的现实力量则主要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理性选择规约了媒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决定了媒介技术演进的可能性。保罗·莱文森深受哲学理性主义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以媒介技术演进为核心问题,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由此使自己在继承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范式的同时又区别于前辈和同辈学者,推动了媒介环境学派媒介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关键词: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形态轨迹;历史趋势;控制力量
保罗·莱文森是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中继麦克卢汉、波斯曼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传播理论家,是该学派第三代理论家中的中坚人物。他同其前辈理论家一样超越美国经验学派、欧洲批判学派开创的传播学研究范式,着眼于媒介对人类认知方式、感受结构、传播模式,以及文化变迁的影响等角度来研究和考察传播学问题,强化了媒介本体的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第三范式”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将该学派的研究触角延伸到了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但他又不同于该学派的前辈学者,他视自己为麦克卢汉的衣钵传人,但在众多媒介理论问题上又不愿与其为伍;他授业于波斯曼,但在价值立场上又与其大相径庭。保罗·莱文森在继承前辈学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媒介技术演进对人类传播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发展了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同时,在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家族相似”的语境中,通过对媒介技术演进问题的集中讨论,使其在媒介环境学派中显得卓尔不群,进而奠定了自己在媒介环境学派中的独特地位。
一、媒介技术演进的形态轨迹
从发展史的角度对媒介技术演进的形态进行阐释,是保罗·莱文森建构自己媒介演进思想的一个基础性和核心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他1977年发表在《如此等等》杂志上的《玩具、镜子和艺术:技术文化之变迁》一文中。在这篇文献中,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技术演进的形态轨迹的描述主要集中于对单一媒介技术的考察,着眼于单一媒介技术自身存在方式以及在人类认识与理解史中的形态变迁。在考察单一媒介技术演进的形态变迁时,保罗·莱文森主要是从媒介技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划分,在此基础上,确定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边界和现实形态。
保罗·莱文森认为,媒介技术在演进的进程中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大致呈现3种状态:其一,媒介技术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这时候媒介技术以纯粹的形式而存在,人们被它的这种奇特的形式所吸引。他说:“在技术文化的初期,技术占主导地位。情节、人物刻画、少得可怜的内容都扮演辅助角色,只是为技术新玩意服务,实际上不过是技术低调的载体而已。在这些初级的形态里,观众的乐趣存在技术的工艺流程中,不在工艺的结果,而在工艺本身。”[1]4这一阶段,保罗·莱文森将之被命名为玩具形态;其二,随着媒介技术自身的发展和人类对技术认识能力的提升,媒介技术不再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而存在。媒介技术成为承载现实内容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它以客观、逼真为准绳,模仿和映照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技术演进的这一阶段命名为镜子形态;其三,媒介技术不再像此前那样忠实地模仿和反映现实世界,而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创造性的表现和重塑,创造了新的现实。这一发展阶段,保罗·莱文森称之为技术的艺术形态。基于媒介技术与现实的关系状态,保罗·莱文森将媒介演进的形态轨迹依次描述为玩具、镜子与艺术三种具体形态。
但是否每一种媒介技术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会经历这3个典型阶段,表征为这3种典型形态?保罗·莱文森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有些媒介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完整地完成三种发展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媒介技术都有这么幸运,很多媒介技术可能就止步于第一种形态或者第二种形态。保罗·莱文森通过历史的考察发现:“许多技术过于适合第二阶段镜子的任务,根本就没有能力完成第三个阶段艺术飞跃的任务。”[1]12诸如,电话技术专注于现实交流的需要,就没有完成镜子形态向艺术形态的跃进。因此,如果一些媒介技术仅仅停留于忠实地再现和记录现实世界,那么它们也可能仅仅止步于媒介技术的镜子形态。而真正能完成第三种形态的,只有它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时既能够复制,又能够重组,进而创造出新的现实世界,诸如电影媒介技术。从保罗·莱文森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在描述媒介技术演进的形态轨迹时,也清晰地认识到,并不是每一种媒介技术都能完整地完成媒介技术演进的全部形态和理想轨迹。
历史地看,对媒介技术演进的考察,有两种基本视角和路径:一种视角是从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考察媒介技术的变化与发展,这种视角我们一般称之为自律论;另一种视角是从媒介技术之外和力量与因素去思考媒介技术变化与发展的力量的因素,我们一般称之为他律论。从思考视角和路径来考量,保罗·莱文森显然是从他律论的角度来审视和考察媒介技术的演进,他认为:“显而易见地,点燃技术发展的烈火往往来自技术之外,社会、经济、媒介甚至是物质条件汇合成为辅助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1]6也就是说,技术能否沿着玩具、镜子与艺术的发展形态进行演进,主要是看这种媒介技术当时存在的外部条件是否营造了其朝下一个方向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在保罗·莱文森的视野中,除外部条件之外,其后期众多的论述还强调了人类的现实需要也极大地决定了媒介技术演进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形态。
二、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
如果说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技术演进的纵向历史描述,主要着眼于媒介技术的存在方式、自身结构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媒介技术的形态学的讨论的话,那么媒介技术的形态演进和发展轨迹在价值论上如何审视,或者媒介技术的演进对于人类是带来了便利还是灾难,对人类产生了何种价值与意义,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如何,便成了保罗·莱文森媒介技术演进思想构建时绕不过去且必须要回答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体现了保罗·莱文森对媒介技术演进的人文反思和价值叩问。在保罗·莱文森的媒介理论建构中,他主要从以下两种思路和视角来讨论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
首先,是基于具体媒介技术自身的变化发展来讨论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在保罗·莱文森看来,每一种媒介技术被人类发明和使用,其初始阶段自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在人类使用的过程中,媒介技术会慢慢地得到发展和完善。这种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是针对其不适应人类的使用习惯和使用特点来进行的。从媒介技术发展史角度来考察,保罗·莱文森发现,媒介技术会越来越适应人类的需要,越来越符合人类使用技术的特点。同时,媒介技术本身也越来越完善,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就是对自身不断的修正和完善。诸如通讯技术,最先发明的电报技术,虽然有利于远距离的信息传播,但却以牺牲传播的真实情景和辅助传播手段为代价,而且互动性比较弱。随后出现的电话传播技术有效地克服了电报的这种局限,但却将人固定在电话机上。再之后移动电话的出现又克服了固定电话的局限,可以实现人类随时随地传播信息的需要。因此,着眼于一种媒介技术来考察,在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媒介技术会越来越符合人类的需要和使用特点。
其次,是从不同的媒介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讨论媒介技术演进的历史趋势。这个角度主要审视不同的媒介技术在技术生态中的竞争性发展格局中的历史趋势。保罗·莱文森认为,一种媒介技术不适应人类或者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因为它自身已经不适应人类的需要,因为“媒介的发展是‘适合人的选择而生存’”[2]427。也就是说,一种媒介技术之所以被另外一种媒介技术所代替,是因为另外一种媒介技术兼具了这种技术的优势同时又克服了其局限与缺点,所以它能够在媒介技术发展的生态中优胜劣汰,在这个基础上补偿前一种媒介技术的不足。在保罗·莱文森看来,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与媒介技术之间的更替和发展基本上沿着这条逻辑与线索来进行。这条线索貌似是从媒介本身的角度来讨论媒介技术的变化与发展,但实际上却隐含着人类的选择与力量,“因为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完美;人既然发明了媒介,就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3]A10
在保罗·莱文森的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趋势中,无论是从单项媒介技术来考察,还是从不同的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其背后均隐藏着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和人的需要的原则与准绳。保罗·莱文森说:“对信息传播效率的追求,无论它叠压在商业、艺术、科学的动机下也好,抑或它没有附加的动机也好,都非常合乎逻辑地(尽管可能是无意识地)走向了合乎人性的动机。”[4]177也就是说,媒介技术都是按照人类的意愿和要求来发展,人的要求和价值尺度成为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好是坏,人的指引对一切技术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130换句话说,媒介技术演进过程中,不是人适应技术而是技术适应人,媒介技术应不断向人类的现实需要靠拢,以向人类献媚的方式来获得自身的发展。基于这两种考察视角,保罗·莱文森形成了媒介技术演进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这其中蕴含两个层面的意涵:其一是媒介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人性化;其二是无论单项媒介技术的自我修正和完善,还是不同的媒介技术之间的淘汰和更替,都服务于弥补自身或者前一种媒介技术的不足和缺陷。
三、媒介技术演进的控制力量
媒介技术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与要求,按照科技理性的立场与主张,技术的演进与发展不一定按照人类的意愿和想法去进行,也不一定在人类的安排下朝某个方向发展。媒介技术自身有其发展的逻辑和张力。在技术自律发展的同时,有时候往往会脱离人类的控制,变得异常强大,最后技术反而会奴役人。这种思考视角往往容易陷入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发展逐渐朝向剥夺人的的全面技术官僚化和技术综合体”[5]81方向迈进。也就是说,人类发明了技术,最后我们自身被技术所控制,人在技术面前无能为力,人成为技术统治和奴役的对象。
但保罗·莱文森显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被技术控制的局面不会出现。因为技术的发展犹如我们每一个物种在世界上发展的情况极为相似:适应自然生态的将会留下来,不适应的将遭遇淘汰。技术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和原则。不过技术与物种生存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如果生物物种面对的是一个自然界,那么媒介技术生存与发展面对的“自然环境”就是人类。人类根据自身的理性原则,将适合人类需要的媒介技术留下来,将不适应人类需要的媒介技术淘汰。“人好比是自然环境,要对技术和媒介做出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媒介存活的条件是满足人的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和心理需要,以及是否能够长期起到社会促进的作用。”[6]30
在保罗·莱文森的视野中,“一切技术都是思想的外化和物化”[4]116,人为技术立法。从这一点来看,保罗·莱文森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衣钵。人类的理性能控制媒介技术的存废和发展方向,换句话说,“媒介进化是在人类理性选择作用下的不断推进,媒介进化最终目的是要使人的欲望和需求得到满足和实现”[7]25。因此,技术脱离人类的控制,人成为技术奴役的状况永远不会发生。“在技术面前,人总是能够依靠理性正确选择和使用技术,并能够规避或纠正技术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从而取得主导地位。”[8]37媒介技术虽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但技术永远是一种工具,永远不可能去奴役和控制人类。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对于媒介技术发展的恐惧和惊慌,大可没有必要。由此,保罗·莱文森显示出其与授业导师波斯曼的巨大差异。如果说波斯曼在这一点上是一种技术悲观主义的话,那么保罗·莱文森就可以贴上技术乐观主义的标签,并因此显得与其前辈学者不同。
从传播思想史的视角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技术演进的控制力量方面显然继承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只有适合人类传播实际和传播发展需要的媒介技术才能留下来。媒介技术的演进与发展以人类的需要为规范和尺度。虽然各种媒介技术是人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如果不契合人类未被技术化的状态,那么这种技术也将被淘汰。在此基础上,保罗·莱文森认为:“一种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的人类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直接关系。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些媒介和真实的传播环境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和环境比较协调的媒介存活下来而没有大的变化,其他媒介包括与之同时代的和后来的媒介,却不得不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地急遽变化。”[1]34因此,一种媒介技术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和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跟它是否适应人类前技术时代的传播模式有关,跟是否通过技术的方式与手段恢复或重构人类前技术时代的交流模式有关。如果有悖人类前技术时代的传播与交流模式,它也将在这种激烈的媒介发展生态中惨遭淘汰。由此看来,媒介技术与人类前技术时代传播模式的契合度也是媒介技术演进的重要决定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功. 保罗·莱文森的媒介演进线路图谱[J].当代传播,2012(2).
[3]何道宽. 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纸媒书和深度阅读?——从纸媒阅读到超文本阅读[N]. 中国图书商报,2005-01-21.
[4]〔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荷兰〕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李小兵,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曾玉慧.数字时代的欢乐颂——保罗·莱文森媒介理论分析[D].厦门:厦门大学,2009.
[7]陈功.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对媒介环境学的超越[J].当代传播,2013(2).
[8]王凤栖.保罗·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责任编辑方英敏)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2.020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2-0142-04
作者简介:刘晗(1976—),男,湖南祁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媒介理论。龚芳敏(1981—),女,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和媒介文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理论研究:一种传播思想史的视角”(12YJA860008);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1YBB319)。
收稿日期:201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