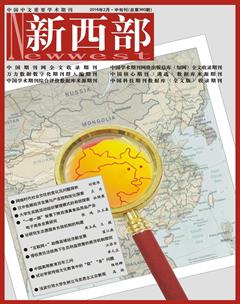中国高等教育百年三问
【摘 要】 文章论述了钱学森、胡适、作者本人关于中国教育百年来的三问。反思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目标方向存在的偏颇,认为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中华优秀的教育传统。作者大篇幅地阐释了中华优秀的教育传统的内涵,从制度基础、功能设计、属性定位、目标价值乃至专业形态和办学模式探索高等教育体制新的选择:重构“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重建主体功能: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重塑目标价值: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个人全面发展;构建职能凌越、思想独立和专家治校办学组织运行机制;深化教育体制法规改革,回归本质属性:国家重器与公器。并探索具体的对策。
【关键词】 教育;三问;教育价值;方向;中华优秀传统;对策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在为国家塑造明天。而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因此,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总是既要站在今天,同时又必须站在昨天和明天的角度来审视思考问题。
一、百年三问
近年来,在不断思考国家、民族、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明天的过程中,对于千年科举、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脑海里萦绕着三个不解的问题——
其一,钱学森之问
2005年,钱老感慨地对温家宝总理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换言之,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大学出了问题?
其二,胡适之问
1937年,著名学者胡适针对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翁文灏力倡培养炼钢炼铜等专门技术人才的来信回复到:“此时我所焦虑的是: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虑……故我以为,中央研究院、北大、中基会一类的机关此时还应该继续注重为国家培养基本需要的人才,不必赶在人前面去求眼前的‘实用人才。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胡适实际在问,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大学出了问题?
看来,这类问题并不是今天的问题,至少是1905年废除科举、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以来“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的问题。
其三,今日之问
拙著《中国私人资本人格》一书指出,[1]但凡健康成人无一不在一定的现代组织——从家庭、企业、城市到国家——中作为“组织人” 而存在。其工作、生活从而命运依存于其中的组织的命运,一方面决定于外部宏观制度坏境;另一方面,就组织内部而言,则决定于组织决策者及其群体的人格(素质)。东西方历史学家研究表明,影响历史重大事件的决定性(60%)因素是组织的决策者及其群体。[2]
今天,中国在快速崛起,为世界所瞩目,对此毋庸置疑,无需赘言。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华崛起面临的一系列危险:社会道德伦理堕落、政治文明的腐败、知识精英群体犬儒化,等等。究其根源:既与百年民粹、极左政治以及缺乏宪政民主和“物欲主义金钱崇拜”等的影响有关;又与社会主导阶层——掌控社会治理权、财富权、技术权、话语权——中部分精英群体的道德伦丧及其示范效应有绝大关系。
问题是,作为“掌控社会治理权、财富权、技术权、话语权的社会主导阶层”,均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这一阶层的世界观价值观基本是在学校,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学习阶段中形成的。于是,自然要问的是:部分社会主导阶层的道德伦丧堕落是否与高等教育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是不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明确地说:在拯救民族危亡,建设独立强盛自由平等新中国的百年奋斗中,对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文明以及中华高等教育优秀传统过程的阻断,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中华优秀的教育传统。
那么,中华民族优秀的高等教育传统是什么呢?
二、优秀传统
纵览历史,就会看到,中华高等教育的优秀传统,集中体现在中华文化文明处于上升期的唐宋科举制度中;在近代,则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近百所高校70万师生为存续中华文脉,历尽艰险,跋涉10余万公里,令举世震惊的“文长征”中。
在1300年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科举制度中,明清时代的科举/高等教育已沦为“豢养奴才的工具”,加剧了中华文化文明的转向衰败,故而不论。唯唐宋科举体现了中华文化文明的勃勃英气、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和文明制度创造,成就了如“贞观之治”那样的帝国鼎盛,建树了“精英治国”体制和“王-士二元并治”的开明民主政治,[3]创造了作为西方文官制度源头的“考官制度”,成为中华文化文明最宝贵的遗产,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4]
这一中华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集中表现为——
第一、科举/高等教育的制度基础是: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时代、国家对统治人才、统治阶级(阶层、群体)迫切需求的产物。自隋至唐,通过“科举取士”,逐步打破社会森严的层级界垒和传统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国家政权向广大寒门庶族开放,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社会层级间开始形成一条自由流动的通道,为士群体提供了共同的生存发展的制度基础和一条走向国家治理和统治地位的法制路径——从“田舍郎”与寄人篱下的“养士”至“暮登天子堂”的宰相仕臣群体,[4]被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赞许为:“人类文明中的佼佼者”。[5]
第二、科举/高等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
自汉唐至宋,科举已成为政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选(考)官制度”。这一制度的首要功能是为国家治理培养具有“天下情怀”的社会精英。 此点尤其体现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策论” 内容中。如唐光宅二年武则天亲主持殿试策问[6]:一政要,二求贤,三隐退,四明王革命,五帝王之道;唐开元二年唐玄宗李隆基主持殿试,策问:立身为官之道;宋绍兴二年高祖赵构殿试策问:中兴之道;等等。
另据考证,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武则天时期为50%;至中晚唐,已高达80%以;至于官员,绝大多数出自科举。
这一塑造培养治国精英的特殊功能,适如著名学者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必须进行的“社会上层的再生产”。这是一条普世的法则,西方姑且不论,就以当今中国而论:
2013年,第18届中央委员中,全部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其中,仅博士硕士研究生就占到约70%。同样,被惩处双规的处级以上干部,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科举尊奉的是以“内圣外王”为最高旨意的儒学“经世致用”理念。不容否认,在儒家学说中夹挟着诸多糟粕,但从蒙训至四书五经,乃至诸子百家,在近二十年的塾庠科举教育中,一以贯之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华文化人奉之为“魂魄”的“天下意识”、“天下情怀”。
当一个国家由具有“天下情怀”的精英治理时,这个国家能不强盛吗?而这也正是秦统一中国之后,伴随科举制度的兴起,中华帝国不断崛起的制度与社会动力基础;同理,当明太祖废宰相,黜仕臣,启用太监,行独裁专制,将科举制度变为培育奴才之工具,精英知识分子成为御用文人、奴仆文人之后,中华文化文明便一转而走向衰败,江河日下,直至晚清。
中华文化文明、政治制度与科举/高等教育亦步亦趋,同盛同衰之三曲线,发人深省。这一史实证明:
以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为首要功能,是中国古代科举/高等教育的首要特征和中华文化文明的优秀传统,是国家民族崛起强盛之本!
——这也是中国古代优秀高等教育与西方近现代高等教育的首要区别。
第三、科举/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价值是“国家社会利益至上”
唐宋科举制度打破传统等级屏障,建立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科考入仕无贫贵之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量中下层知识精英进入国家治理权力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先天下而忧”的天下情怀和“公(共)治天下”的价值追求,被制度化为科举教育的核心目标价值;与同时,唐宋科举将记录“古圣先王”治理天下业绩的圣典“六经”,[7]作为科举教育的基本读物和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既使历史文化经典得以积累传承弘扬,发展形成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博大体系,又以此擢选国家栋梁之才,将此“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目标价值人格化为现实开明政体和“公(共)治天下”的“士人政府”,创建出人类古代史最为先进的精英化国家治理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
——这是中华文化文明和古代高等教育的优秀传统,也是与近代西化高等教育的又一重大区别。
第四、在专业形态上:尊重传统,凌越时俗,思想独立
自汉以后,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整理经典,弘扬百家,立“五经博士”于太学;办学与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和科考中,允许“论见独立”与“思想自由”,鼓励学子阐发真知灼见,提供治国良策。典型如宋嘉佑二年,苏轼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就国家刑法制度问题竟杜撰出一则尧与皋陶论刑宥的“典故”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若无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环境,苏轼绝难卓秀而出,中国也就少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兼政治家。
用现代语言来作诠释,高等教育从事的“上层再生产”——从文化文明凝练升华、制度伦俗精神思想训教风化、科学技能知识传承创新到国家社会最高素养的精英人才培养塑造等——具有一种凌驾、超越于其他社会职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要求其“产品”具有明确的社会公共意识和独立的思想人格,而不是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而是社会“良知”、社会公共权力——从治理权、资本权、技术权到话语权——与利益的代表者。
这一点在西方文化文明体系、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西方文化文明的一个优良传统。而这一点却成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缺陷。
第五、组织运行机制是:教育开放,机会平等,学者治校
唐宋时代,科举教育的组织运行机制具有由名家儒士独立办学、自主教育、因材施教的鲜明特征,并无今天如此分明的官学私学之别;教育组织管理既无近现代严格的办学权审批与垄断,更不存在“计划教育”体制。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已初步实现了创办教育与受教育权力的平等开放、杜绝世袭、机会与权力平等、公平竞争。
上述制度基础、首要功能、目标价值以及职业形态和运行机制组构成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华文化文明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关键与动力。
三、百年西化
如前所述,百多年前,由于明清专制独裁与“草原主奴制度”对承续中华文化文明及高等教育优良传统的阻断,由于唐宋优秀科举制度在明太祖淫威之下变为培育奴才的工具,也由于百多年前中华民族面对的不是大唐盛世的文明与辉煌,而是蒙满贵族专制统治的极度朽败与黑暗,中华民族在抗争与奋发崛起中自然选择了向西方学习,而高等教育也不期自然地走向了“全盘西化”。
在这沉重多难的百年中,中华民族不断奋发崛起,终于走到了辉煌的今天;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局限乃至糟粕,至于“百年西化”的高等教育也未能幸免,而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其一、 “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严重扭曲。
如果说以文化革命及以前,极左的“阶级”标准基本粉碎了 “自由流动”“公平竞争”机制;改革开放在破除“阶级”标准以后,现实高等教育实际又固化和拉大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自由流动机制”依旧严重被扭曲。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再生产》一书中所尖锐指出的:“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为某些等级提供了这种服务”,[8]成为影响新型国家秩序和社会形态建设,导致当前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其二,在主体功能上,淡化漠视了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上层再生产”的首要功能是: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
还在时代巨变,民主共和艰难起步,军阀混战,国难家危,国家急需大批深明大义的报国之士的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却被定格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由此迁延百年,至于今天,又进一步降格降等为“高等职业教育”。
其三、在目标价值上,淡化漠视了 “公治天下”、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优秀传统。
淡漠了培养“先天下而忧”治国精英的首要功能,效仿西方的“个人价值至上”,加之以“产业化”的利益驱动,中国高等教育目标价值的优良特质与传统基本已名存实亡。
其四、在专业形态和组织运行机制上,实际否定了职能凌越、思想独立,以及体现这一特质的专家办学、学者治学,高等学校成为行政性机构的附庸、计划体制严格管控的对象。
总之,近代以来,我们接受了西洋的反传统反权威的“民粹”思潮,像泼洗澡水将婴儿泼出一样,把中华文化文明与高等教育的优秀传统抛到了太平洋里,我们数典忘祖了。
于是,在百年高等教育的主体功能上,只留下“研治高深学问”和“科学工具主义” ;“金钱+拼爹”成为上升为“精英阶层”的阶梯。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传统之魂魄;
高等教育的目标价值走向了文化大革命极致政治的另一极端,不注重培养师生的“天下意识”,而是放纵“个人中心”、“唯我主义”和“物欲主义”在校园中泛滥;
在无限制的权力制度面前,由高校走出的一部分人,抱定极端个人主义及补偿昔日“寒窗困苦”追寻回报的价值观走向权力中心,以其制导示范性负效应,加剧了国家民族精神生态结构的失衡、社会价值取向的迷失、民俗风尚的污浊。
胡适当年所谓“无用之用,知之者希,若吾辈不图,国家将来必蒙其祸”,竟一语成谶。
讲到这里,开首提出的三个问题应该能够回答了。
问题是,怎么办?!
四、选择与核心
千年科举与百年西化的曲折发展业已表明:中国有自己发展的道路。
六十多年前,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预言:“中国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可能想象,现代中国这一人类最大而又最古老的人群,可以纳入任何外国强国(例如俄国、美国或者其他强国)的轨迹之内……”[9]
痛定思痛,今天,需要对高等教育体制作以理性审视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对今天和明天的高等教育体制——从制度基础、功能设计、属性定位、目标价值乃至专业形态和办学模式做出新的选择。
其一、重构“打破政治与教育权力垄断,社会层级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基础
毫无疑问,要从根本上破除现实高等教育实际固化和拉大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重建“自由流动机制”,这显然不是高等教育自身所能够解决的。如同自隋至唐,一种公平公正制度体系的形成走过了几个世纪,新的“重构”俨然是一个巨大的跨世纪工程,需要的是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政治体制、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伦理以及相关法制体系的改革、创新与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创新,这正是中国今天进行战略性转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其二,重建主体功能:培养“先天下而忧”的治国精英
并将这一中国高等教育的灵魂与首要特征首要功能载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贯彻实施。
其三、重塑目标价值: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个人全面发展
并将这一目标价值载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贯彻落实。
其四、构建职能凌越、思想独立和专家治校办学组织运行机制
并将这一运行机制载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贯彻落实。
其五、深化教育体制法规改革,回归本质属性:国家重器与公器
为此,应将这一本质属性载入《中国高等教育法》,以贯彻实施。
其六、在具体创新或重塑高等教育体系过程中——
1)在现行高校中,选择部分高等综合类大学,增设“国家治理”学科(或专业),培养既具有 “天下情怀”和“公共角色人格素质”,有志于国家经济社会各层次领域管理,又拥有不同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级管理人才。
2) 专设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管理学院等在职高等党政干部培训相链接的“国家高等行政管理大学”,以培养国家各级治理系统高等预备人才。
总之,通过深化改革,应使高等教育与民族国家文化文明的内在关系、 “上层再生产”的首要职能及其“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目标价值得以恢复和重建,使得高等教育不仅成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而且真正具有“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10]成为一国之“重器与公器”和“社会的心脏”。[11]
在对“三问”进行思考和探寻答案与解决之道时,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
其一,总览中华文化文明发展、国家政治体制、中华民族国家与科举制度,以及中国古近代士族精英群体的命运曲线,可以看到,作为展现中华文化文明衍生发展转型盛衰运动态势的这一束五条关键变动曲线,竟表现出高度的同步契合——这是中国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的一大奇观。
仅就科举制度与中华文化文明的核心——国家社会治理体制,亦即国家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而论,正是适应了之一文明核心建设的需求,科举制度进一步促成了士族、“士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使这一新阶级带着蓬勃朝气与使命信念,由隋起步,至盛唐,走向中华帝国的政治中心,并通过构建中国古代“开明二元政体”,对中华文化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样,由于明以后中华文化文明核心——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质变,科举制度随之转型变质,导致了士族、“士族文化”、以及“开明二元政体”的败落;由科举与士族精英的“颓化”,反转加速了中华文化文明特别是其核心——国家社会治理体制,亦即国家政治体制的衰败。
简而言之,中华文化文明体系中的国家政治体制的演变,要求进行“上层再生产”的高等教育(科举制度)做出适应性转型变化;高等教育体制的转型变化,通过其培养塑造的国家治理精英的转型变化,影响、再造国家政治体制,进而制导中华文化文明的转型与盛衰。
同理,作为“国家重器”和“上层再生产”的教育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要以国家社会治理制度、政治体制的改革为基础与前提。
其二,在高等教育新的探索实践中,核心、灵魂、首要者,是“目标价值”。现代高等教育不需要每一位教师和大学生都成为政治家,但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和民族的振兴、崛起,需要中国的每一位高等“师表”与学子要有“天下情怀”作“社会良知”!
——历史业已证明:这是中华文化文明走向鼎盛之根本,是中华古优秀传统的本质特征。
此非一日之功,却孕育奠定于大学之中!
近日读到一本好书——美籍华裔学者写的《知识人的黄昏》,[14]内中讲到,近三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界、思想界同样在反省和批判高等教育以及知识分子阶层中否认社会价值理想,极端物欲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泛滥,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此一语中的。
看来,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法天下。
【注 释】
[1] 单元庄.中国私人资本人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6.11.
[3]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P3如钱穆所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4]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京讲学,第一句话就是:“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5] 据两《唐书》列传所载,终唐一代,寒门庶族出身而拜相者为一百四十二人,而高门世族出身的拜相者为一百二十五人。
[6]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和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P529.
[7] 汉文帝时即行次举.
[8] 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又称为“六艺”。 因《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六艺”有两种,另一种为礼、乐、射、御、书、数.
[9] 参见.科举百年.P99.
[10] 读书.2014.3.P71.
[11] 商务印书馆,1873.P4.
[12][13] 尤西林.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高等教育研究,2002.02.
[14] (美)傅铿.知识人的黄昏. 三联出版社出版,2013.
【作者简介】
单元庄,男,教授,现为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