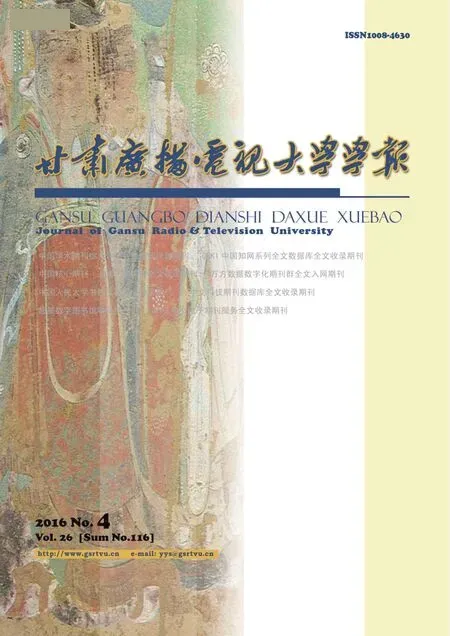浅析《判决》中的反抗与惩罚
王 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浅析《判决》中的反抗与惩罚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卡夫卡的作品几乎都带有精神自传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的折射,与他本人有着相似的人格属性与情感历程。而缠绕他一生的父亲情结,对父亲的恐惧感和负罪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反抗与惩罚,则在他的作品《判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卡夫卡;《判决》;反抗;惩罚
一、恐惧与反抗
《判决》是卡夫卡创作于1912年的小说,情节很简单,围绕着格奥尔格和他父亲之间的冲突展开,表现了格奥尔格的矛盾心理,由对父亲的恐惧与不满,进行消极反抗,到对父亲的负罪感,产生自我惩罚的需要,最终被父亲与自我判决而死。他在1913年的日记中称《判决》是“从我身上自然而然生下来的产儿,满身污垢和泥浆”[1]35。
在《判决》中,格奥尔格的母亲去世前,父亲在经营上独断专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才华得不到发展。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已经精力不济,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商行里的许多事情无法顾及,所以格奥尔格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与意愿管理商行,并且“商行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职工人数不得不增加了一倍,营业额增加了五倍,往后的买卖无疑会更加兴隆”。即使格奥尔格已在商行及别的事情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再受父亲独断专制的阻碍,但他长久以来对父亲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却使他时刻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他与父亲的这种对立的关系,让他有意无意地疏远父亲,并时刻保持警惕。
无疑,格奥尔格对父亲的专制独断是反感的,但同时他的内心又充满畏惧。他想摆脱父亲的控制,反抗他的专断。商行的生意兴隆,与一个富家小姐订婚,使他赢得了一定的自信。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俄罗斯的孤独而生意清淡的朋友时,内心充满了得意。他写完信走进父亲的房间告诉他时,其实也有一种示威炫耀之意,让他强壮的父亲看到他并不是全无能力的。从“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过了”可以看出他与父亲关系的疏远,即使住在对面,也几个月不去看他一次。格奥尔格常常在晚上出去见朋友或者看望未婚妻,即使呆在家里不出去,与父亲也是各干各的,在共同的起居室里坐着,各看各的报纸,更不用说互相问候和谈心了。他们的关系是极其冷淡的,仿佛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互不相关的陌生人。事实上,这种对父亲的疏远与冷淡正是格奥尔格无言反抗的一种手段。他甚至几乎没有考虑过他结婚后怎样安置父亲,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父亲是在他和妻子的生活之外的。他过他的婚姻生活,父亲继续留在老宅子里,独自生活。他们继续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互不相干。一种局外人的冷漠是格奥尔格对性情专断的父亲的间接反抗。
卡夫卡所写的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独白。他在1911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把我整个世界惶恐不安的心情全部写出来,并且像它从我内心深处出来那样,把它写进纸的深处去……”[2]185正如一位奥地利学者瓦尔特·H·索克尔所说:“卡夫卡的作品可称之为由隐喻伪装起来的精神自传。”[2]644因此,卡夫卡笔下的格奥尔格就不可避免地有他自己的影子。与格奥尔格的父亲一样,卡夫卡的父亲是一切事情的独裁者与权威,母亲虽然袒护儿子,但她从来不会因为儿子而站在反对丈夫的立场上。卡夫卡在家里觉得异常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的灵魂一直找不到家的归属感。
卡夫卡从童年时代就形成了对父亲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感。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从小就开始为生活而吃苦、奔波,经历了许多磨难和艰辛,创立了一份家业。他希望卡夫卡像自己一样自食其力,一样强悍刚毅。但他蛮横专断的教育方式却适得其反,让天生敏感脆弱的卡夫卡更加胆怯懦弱。在父亲这个又高大又魁梧的巨人与权威面前,卡夫卡觉得自己就像一座铁塔旁边的一根小火柴棒,并形成一种由外而内的压迫感与恐惧感。父亲对他的威胁与恫吓在他童年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划痕,那种悬而未决的痛苦与恐惧成为影响他一生的致命内伤。
在1919年致父亲的那封著名长信的开头,卡夫卡写道:“亲爱的父亲,您有一次问我为什么总是怕您。和往常一样,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您,部分原因是我怀有对您的这种惧怕,部分原因是解释这种惧怕涉及很多细节,一旦谈起我就说不上一半。”[3]17对父亲的惧怕以及对他粗暴的教育方式而产生的不满,使卡夫卡渴望逃遁,渴望远离这份无处不在的压迫感。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从他父亲身边逃脱出来的一种企图。由此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精神上的逃遁,想摆脱父亲在他心灵上所形成的阴影。在家里,卡夫卡躲避着父亲,除了有时和父亲寒暄几句以外,平时几乎不说话。即使有事问父亲,也要通过母亲传话。他的《致父亲的信》也没有亲自交给父亲,而是要母亲转交,但由于母亲担心父子关系恶化,并没有把信给父亲。卡夫卡和父亲的关系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有一次他和母亲吵架时说:“你们大家对我都是陌生的,存在的只有血缘,但它并不表现自己。”[1]38存在于父亲和他之间,只有表层的注定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的父子血缘关系,以及深层的本质上的疏离感。这种对父亲的外在形式上的疏离表现了卡夫卡对父亲不满的排斥与反抗,他甚至在暗中默默地观察、收集并在心里嘲弄父亲身上滑稽可笑的事情。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与父亲进行抗争,并在精神上获得一些满足感。在《致父亲的信》中,他说:“我的作品写的都是您,在这些作品里我只是倾吐了我不能向您的胸怀倾吐的悲伤。”[3]26
无疑,《判决》是卡夫卡长久以来压抑的情感的一次释放,他通过格奥尔格来诉说自己的心声,表达对父亲专断的不满与恐惧,疏远与反抗。格奥尔格走进父亲的房间时,对光线的阴暗感到惊讶,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走进另一个他所不习惯的、不熟悉的世界。尽管他明知道父亲没有吃多少早餐,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心,而是依旧的保持着在父亲面前无动于衷的态度。虽然此时父亲表现出一个老鳏夫独自生活的孤单无靠,但他“茫然”地看着父亲收拾杯盘,心里想着:“在商行里他可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他对父亲的印象还是商行里那个独断的魁伟的巨人父亲,同时也是他所畏惧与不满的父亲。因为他始终要保持他一贯的冷漠来表达对父亲的不满与反抗。
二、 负罪与惩罚
父亲外形上的魁伟与精神上的强悍让卡夫卡感到恐惧与不满的同时,也让他觉得自惭形秽,总觉得自己不如父亲,没有按照父亲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勇敢强大的人,而是更加自卑、懦弱。所以他感到辜负了父亲的希望,有一种负罪感。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到父亲抚养他的结果是:“在您面前我失去了自信,而代之以无穷尽的罪愆感。”[3]25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与不满造成了他对父亲的淡漠,让父亲指责他忘恩负义、不孝顺、背叛。工作后,卡夫卡除了为保险公司奔波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和家里人很少沟通,也不关心家里的生意,“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1]39。为此,父亲经常责怪他。卡夫卡一方面觉得十分内疚,“我的罪过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不像父亲说的那么严重”[1]45。但另一方面,由于懦弱孤僻的本性使然,他无力改变什么。他在1912年12月29至30日致菲莉斯的信中写道:“家庭的和睦实际上只受到我的干扰,而且随着一年年的流逝越演越烈,我经常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感到自己对父母和所有人都犯有罪过。……只是与你相比我更是罪有应得。以前我曾一夜间走到窗前数次,玩弄着窗把,我觉得我完全应该打开窗子,一跃而出。”[4]这种负罪感根植于他的内心,并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噩梦。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判决》中,格奥尔格起先对父亲十分冷淡,但当他看着父亲“牙齿都已脱落的嘴”,听着他可怜兮兮地说:“我已经精力不济了,记忆力也在逐渐减退,有许多事情我已无法顾全,这首先是自然规律,其次是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比对你要大得多……我求你,格奥尔格,不要欺骗我。” 格奥尔格感到非常困惑,难道这样一个记忆力减退,老眼昏花,牙齿脱落的老人,这样一个轻声地恳求儿子不要欺骗他的无助的老人,这样一个整日生活在对妻子去世的打击中的伤心的老人,就是他平时所恐惧和仇恨的他的专断蛮横的父亲,就是他所一直用冷漠与疏远为武器去反抗的人吗?此时,格奥尔格开始感到内疚,“别去管我的朋友了,一千个朋友也抵不上一个父亲”。他内心的海底所深藏着的对父亲的爱开始冒出水面。于是,他要父亲搬到前面房间去,睡在他的床上,要父亲享受充足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并且要多吃早餐,增加营养。而这些正是他以前所漠然置之的。之所以到现在才提出来,是因为父亲以一种苍老而病弱的形象和体态打动了他。这个父亲并不是他想战胜想反抗的那个独揽一切事务、强大蛮横的人,内疚感与负罪感占了上风。他开始责怪自己,没有好好照顾父亲,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让父亲穿着不干净的内衣,住在黑暗的房间里,靠读报和怀念死去的妻子度日,而自己却几个月都不到他的房间里看望他。
由于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恐惧感还在,当父亲在他怀里玩弄表链时,他仍感到惊恐。 但良心上的负罪感已经紧紧抓住了他。所以,当父亲假装用亲切的目光看着他,狡黠地问:“我现在已经盖严实了吗?” 格奥尔格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提高警惕地提防父亲,他并没有怀疑父亲为什么“特别急于要得到答案”。于是,他掉进了父亲专为他设的陷阱里,憨厚而老实地回答说:“你放心好了,你盖得很严实。”此时,父亲忽然用力将被子掀开,直挺挺地站在床上,一语双关地指责儿子怀着要埋葬他的恶意把他“完全盖上”,并且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而在这之前,他一直说不知道儿子的这个朋友。格奥尔格对“虚弱”的父亲忽然变得如此“骇人”,忽然如此了解远方的朋友而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接着父亲讥讽他与未婚妻订婚是因为无法抵抗她的诱惑,由此侮辱了对母亲的神圣的怀念,欺骗了朋友,并给他加了一个企图把“父亲按倒在床上,不叫他动弹”的大逆不道的罪名。格奥尔格先是本能地反抗着恢复了以前那个专断的权威者形象的父亲,“尽可能地离父亲远一点”,忍不住说父亲是个滑稽演员,嘲笑父亲连衬衣里也有口袋,寻思着如果把这些谈话内容公诸于世,就会使父亲名誉扫地。但内心的负罪感让他“咬住舌头”,“两眼发直,由于咬疼了舌头而弯下身来”,看到父亲身体往前弯曲就担心父亲倒下来摔坏了,不断地忘记原来对父亲的提防和反抗,本来要嘲笑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变了语调,“变得严肃认真”。最后他终于知道了父亲一直在暗中监视他,这证明了他原本的幻想是错误的。
格奥尔格的理想世界忽然之间坍塌了。一直通信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对他的信“连读也不读就揉成了一团”,却拿着父亲的信“读了又读”;生意上的兴隆只是因为父亲“已经做了准备”,为他把生意做成打下了基础,而且他的顾客的名单也在父亲的手中;与未婚妻订婚只是因为忍受不了她的诱惑。正如卡夫卡在日记中所说的,父亲“从那个共同物,即从那个朋友那儿突出自己,并把自己放在与格奥尔格对立的地位,他通过其他那些较次要的共同点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诸如通过母亲的爱和依从,通过对母亲的始终不渝的缅怀,通过最初确实是由父亲为商店争取到的顾客”[1]35。格奥尔格则什么也没有,一无所能。这让原本就被压抑的潜藏在他体内的与父亲对照而形成的自卑感更加强烈。而父亲对他的指责更是火上浇油:“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这句话宣告了格奥尔格的彻底失败。他既没有做到完全疏离父亲、反抗父亲,也没有做到与父亲亲近、得到父亲的认可。他已经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已经完全被父亲打败了,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格奥尔格顺从地投河淹死,这是他对自己的百无一用的惩罚与判决,同时也是内心积淀已久的负罪感使然。
当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投河淹死的时候,他急忙冲下楼梯,迫不及待地向河边跑去。如果说父亲对他的判决是荒谬的,是一种失去理智的非理性行为,那么格奥尔格为什么要如此顺从、如此迫不及待呢?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却想等到公共汽车驶来时再跳水,考虑到了公共汽车的噪音“可以很容易地盖过他落水的声音”这样的细节。这说明了他并没有失去理性,而是非常清醒的。从他“像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桥上的栏杆”可以看出,他把死亡当作了一种解脱,仿佛死亡是他的救命稻草。原因在于,他对父亲的内疚感、负罪感迫使他对自己做出惩罚。而父亲对他的判决就是最严厉的惩罚。正如德国学者赫伯特·克拉夫特所说:“父与子的冲突非常典型地记载了这一社会结构;依赖者有依赖性,不能坚持反抗到底。每种社会制度之所以存下来,这是因为它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谁如果起来反对它,就会觉得自己有罪。”[5]于是,当父亲作为最高权威判决格奥尔格投河淹死时,他便顺从了。
在松手落水的那一瞬间,格奥尔格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这是一个儿子多么无奈的呼喊,被爱的父亲并不理解也没有探究过儿子的这种复杂而矛盾的爱。同时,在这声呼喊里也包含了一个儿子的不满和反抗。一个父亲一直在监视自己的儿子并且让他投河淹死,这也许是儿子最大的悲哀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判决他的虽然是父亲,但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是良心上的负罪感迫使他自我惩罚。他对父亲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和不满仍是存在的、无法消除的。而只要有不满,就会有反抗,矛盾并没有解决。卡夫卡在1914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被判决了,那么我并非仅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决抗争到底。”[1]52格奥尔格的反抗因为最严厉的惩罚而得以无限地延伸。
[1]卡夫卡.卡夫卡书信日记选[M].叶廷芳, 黎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2]叶庭芳.论卡夫卡[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传[M].汤永宽,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4]卡夫卡.卡夫卡文集:第4卷[M].林骧华,主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63.
[5]赫伯特·克拉夫特.卡夫卡小说论[M].唐文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78.
[责任编辑龚勋]
2016-03-17
王霞(1981-),女,江苏赣榆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
I206.4
A
1008-4630(2016)04-0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