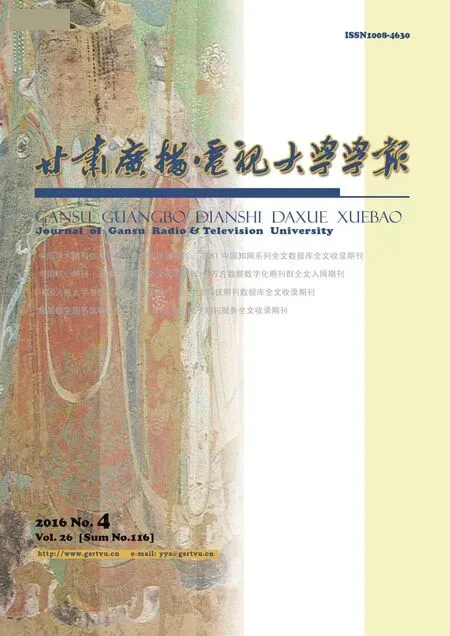绿色英雄的传奇与生态理想的赞歌
——评肖亦农的长篇生态散文《毛乌素绿色传奇》
段沙沙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绿色英雄的传奇与生态理想的赞歌
——评肖亦农的长篇生态散文《毛乌素绿色传奇》
段沙沙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20)
长篇生态散文《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作家肖亦农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肖亦农立足于鄂尔多斯大地,以毛乌素沙漠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的变迁为书写对象,展现了鄂尔多斯人重建毛乌素沙漠生态的艰辛历程。《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表现了万物平等、关爱生命的生态伦理,还表现了作者的生态忧患意识以及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生态理想的渴望。作品是一部绿色英雄的传奇,更是一曲生态理想的赞歌。
肖亦农;生态散文;生态思想;绿色英雄;《毛乌素绿色传奇》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一些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关怀的作家开始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他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生态”主题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等文学作品。当代小说家、散文家肖亦农立足于鄂尔多斯大地,在对悄然消失的毛乌素沙漠进行的历时三年的苦苦寻找中,创作出长篇生态散文《毛乌素绿色传奇》。作品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表达了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谴责和批判,对保护自然、恢复生态平衡以及人类重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想的渴望。《毛乌素绿色传奇》一经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和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全国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2009—2012)和全国百部原创作品奖,并在2014年8月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这些奖项无疑是对该作品的生态思想与艺术成就的肯定。
一、生态思想的表现
生态散文不是单纯地描写自然风光中人与自然的闲适感的作品,而是“描摹自然生态景观、守护自然万物生命、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揭示生态环境恶化、反思人类征服自然行为的散文作品”[1]。《毛乌素绿色传奇》是肖亦农生态散文的又一力作,它由五个章节组成,分别阐述了毛乌素沙漠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的变迁历程,探究了鄂尔多斯走出“寂静的春天”的原因。作品运用散文话语的表达形式传达了作者独特的生态思想。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距今7万年前,今鄂尔多斯地区温暖湿润,水草丰美。天上地下,到处是欢悦的生命。”[2]88人类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里单纯的自然环境,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开始猎杀其他动物”,“把猎物架在火上烧烤,然后分食”[2]88。随着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他们对自然的“强取豪夺”已远远超出了鄂尔多斯土地和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生态容量,最终致使整个地区生态系统完全崩溃,演变成狂沙肆虐的“不毛之地”,这里“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2]3。鄂尔多斯人则“世代被沙所累,世代贫穷”。毛乌素沙漠成了贫穷和荒凉的代名词,“老、少、边、贫它占了个全”[2]3。20世纪展开的“人沙大战”,忽视了沙漠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人类向沙漠索取那仅有的一点点绿色,最终以“沙漠越战越勇,越战越疯,甚至堵门叫板,我们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2]18而结束。毛乌素沙漠变得愈来愈暴戾,愈来愈残忍。如果不能摆脱和消除人类主体性的观念,依然企图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因为自然万物绝不是作为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而存在的,其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那么“为什么人类要将自己的这一小部分利益凌驾于万物的整体利益之上呢?”[3]毛乌素沙漠的暴戾、残忍,即是对人类破环自然生态行为的无情控诉。人类只有承认“人与自然具有相同的生态本位”[4]xx,树立生态整体观念,明确自己的生态地位,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
(二)关爱生命的生态伦理
“生态伦理是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在生态伦理方面,肖亦农认为人类应该持有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物的关怀之心,要重视其他生物自身的内在价值。人类“不仅要关心人,还要关心动物和植物,关心所有生命”[5]。在毛乌素沙漠中,水是最宝贵的资源,但在面对人畜争水的生存局面时,鄂尔多斯人选择的是重视其它物种的生命和生存,并发出“羊命也是命哇”[2]12的呼喊。他们坚持万物平等,将其它物种看作人类的伙伴,“为了救队上的羊羔,用自家的面熬成糊糊,嘴对嘴地将瘦弱的18只春羔全部救活”,并“跳井救山羊”[2]185。鄂尔多斯人认识到:人类既不是万物的中心,也不是万物存在的目的,人和万物是相依相生的同一生命共同体,所以人类没有理由凌驾于其它生命之上,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愿望,任何生物个体本身都是神圣的存在。人类只有在对动物的生命、生存尊重的基础上,和世间万物保持一种亲和友爱的关系,才可能真正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一种真正的生态伦理,体会到生命与自然一体的自由与欢欣,实现人与自然万物诗意栖居的生态理想。
(三)平衡发展的生态忧患
现代工业科技被视为当前环境危机的根源,大多数生态文学作品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而《毛乌素绿色传奇》却谱写了一曲绿色工业的赞歌。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的指导下,鄂尔多斯秉持“用集中开发利用1%的土地换取99%的生态恢复和保持”的生态原则,发展现代化工业,利用企业的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平沙、治沙、开发沙漠资源、发展沙漠循环经济,建设一个个生态工业园区,实现了毛乌素沙漠生态恶化的整体遏制和局部好转。但鄂尔多斯人并没有沉浸在“胜利”之中,当乌审大地到处洋溢着浓浓的绿意之时,他们依然丝毫不敢放松对沙漠的防治工作,他们知道“沙漠生态系统作为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对外界的干扰非常敏感”[6]414,除地上原有的沙漠外,鄂尔多斯地下还沉睡着足有600米厚的潜在沙漠。“乌审旗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会不会唤起地下的沙漠?”[2]255乌审人民千辛万苦所创造出来的“绿色乌审”会不会毁于一旦?他们对这片土地始终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治理、建设的过程中,绿色乌审始终强调生态优先,围绕生态发展经济,依靠经济发展促进生态文明之路。当“不同植物种群之间因争夺水分、养分、光照资源以及生存空间,存在的竞争关系”[6]253越来越激烈时,鄂尔多斯从粗放型的绿色治沙转变为经济性的管沙、用沙,进行林分、草分改造,使沙漠中植物各因子达到平衡,让沙漠能够自由呼吸,真正做到与沙漠和谐相处。
二、绿色英雄的塑造
革命年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红色英雄”人物,他们以艰苦奋斗的坚定意志、崇高远大的社会理想不断地激励着广大劳动人民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进。他们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是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引者和领路人。进入新世纪,他们依然是中国进行现代化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和鲜明旗帜。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建设不仅仅需要过去的“红色英雄”来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需要新时代的“绿色英雄”来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21世纪,中国政府站在战略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共十八大更是将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时代呼唤着更多的“绿色英雄”去担当建设和谐的生态家园的责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
《毛乌素绿色传奇》塑造了一个个以亲身实践治理沙漠、探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途径、成就毛乌素沙漠的绿色传奇的“绿色英雄”形象。他们通过植树、造林、种草,对沙漠生态系统施加影响,进行调节使之达到平衡、优化,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想。他们是具有浓厚生态思想的鄂尔多斯人的绿色代表,用自己的生命、泪水和汗水使得毛乌素沙漠停止了疯狂的移动,书写了毛乌素沙漠的绿色神话传奇。
作者以“草原上最诱人的花香,是那5月开放的玫瑰”为题,歌颂了那些在毛乌素沙漠上苦苦奋斗的绿色英雄们。以宝日勒岱为代表的“愚公们”早在1957年就投入到毛乌素沙漠治理的伟大事业之中。他们发扬“愚公精神”,立志要绿化家乡的大明沙。在这个英雄群体里,有年过六旬的“钢老汉”巴拉珠尔、朗腾等“老愚公”,也有朱拉吉热嘎拉、玉喜、阿拉坦奥古斯等“少愚公”,还有桑洁扎木苏、吉热嘎拉巴图等“小愚公”。他们这群“愚公”发扬革命年代“红色英雄”们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治理沙漠、建设草原的事业中,围封草场,建设“草库伦”,使草原得以“休养生息”,生态得以恢复。十几年里,在沙漠中“栽林20多万亩,种草4万余亩,禁牧封育12万余亩,改良草场8万余亩”[2]159。在治沙的过程中,创造并总结出“乔灌草结合”“穿靴戴帽”“前挡后拉”等科学的治沙方式,使毛乌素沙漠变绿不再遥不可及。但到了20世纪晚期,宝日勒岱和乌审旗的“牧区大寨”却走到了尽头。他们坚持农业治沙的思维模式,虽然实现了沙漠生态的局部好转,但鄂尔多斯的荒漠化面积仍以不可控之势迅速扩大,长期处于“整体恶化,局部好转,治理速度赶不上恶化速度”的局面。严峻的形势再次给乌审旗人民的生存敲响了警钟——如若不改变千年不变的游牧、游种等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滥垦乱牧的现象就永远不会根除,生态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恢复,甚至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如果鄂尔多斯人不能成为“问题出路的一部分,那就只能是问题的一部分了”[4] xx-xxi。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治沙方式注定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新时期的治沙英雄们开始尝试将钱学森的工业化治沙畅想付诸实践,利用公司、企业的力量去治理沙漠,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宁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让沙欺负死”的殷玉珍,不甘心让沙子一寸一寸地吞没自己。为了保家园护田地,给后代留下一片阴凉之地,她二十多年来播绿6万多亩,插树栽子的钢钎被沙漠磨短了一尺多。最终把井背塘建设成为一个绿树婆娑、草语花香的绿色王国。她注册了“井背塘”绿色食品公司并计划创办生态旅游公司,实现了在沙漠中致富。住在河对岸的乌云斯庆带领12位蒙古族姐妹成立了以经济形式为纽带的乌兰温都尔联合治沙站。她们根据乌兰温都尔沙漠的特性,采取“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的方法渐进推开。为了提高林木的成活率,她们采用“拌泥栽植、袋装栽培、地膜覆盖”等节能保墒技术,真正做到了沙漠的“因地制宜”,成功地让沙丘起伏、寸草不生、鸟兽绝迹的乌兰温都尔披上绿装。当年满目荒凉的“火焰山”,现在已是树木繁茂、绿草翻浪、飞鸟鸣啭、野兔出没,成为毛乌素沙漠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治沙的过程中又积极寻求致富的方法,走“依林养林、建设养畜”之路,开发沙漠的经济效益。“治沙疯女”沈腾花,不愿看到家乡成为被现代绿色文明遗弃的地方。为改变家乡悲惨景象,她放弃了城市的体面工作,拉着丈夫一同辞去公职,一头扎进有“疯沙”“恶沙”之称的布日庆大沙漠。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培育树苗产生示范效益之后,沈腾花利用公司力量治理沙漠、恢复沙漠生态,成立乌审旗青浪生态有限责任公司。在对沙漠生态重建的过程中,开辟出一条毛乌素沙漠规模化、企业化治沙的新道路,达到了“沙漠增绿、资源增值、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多重目的。经过8年的努力,如今布日庆沙漠几万亩葱绿的林木“宛如一条条绿色的腰带,将一个个沙丘紧紧缠绕”[2]198,仿佛满目望不尽的绿色海洋。而立志要做毛乌素沙漠里的一株树、一棵草的“造林治沙痴女”徐秀芳,在沙漠里一走就是30年,不仅引进先进的治沙技术,还亲自向农牧民们传授先进的治沙理念,指导他们治理沙漠,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像乌云斯庆、殷玉珍、沈腾花、徐秀芳等这样一群“给沙漠点颜色看看的女人们”,为彻底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给后代留下一片阴凉,几乎将生命的全部都贡献给了毛乌素的治沙事业,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换来沙漠的点点绿色。她们运用工业化治沙的思维模式,在沙漠变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经济,寻求致富之路。在致富的过程中使沙漠变得更绿,实现了“绿富同兴”的目的。
在这一个个绿色英雄的带领下,鄂尔多斯人不仅改善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且保护了家园、造福了后代,遏制了毛乌素沙漠嚣张的气焰,打破了“沙漠是地球之癌”、不可救治的神话。虽然对整个毛乌素沙漠生态系统而言,这些英雄只是作为沙漠生态系统中的某一生态因子在起作用,但是他们在这个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却不容小觑。正是因为他们以及一代代鄂尔多斯人能动地介入,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才使毛乌素沙漠由荒漠再变绿洲成为可能。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新时期毛乌素沙漠的生态系统才得以发生质的变化,毛乌素沙漠变绿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三、艺术表现的探索
《毛乌素绿色传奇》不仅是一个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生态意蕴的散文文本,而且在审美视角、结构安排、话语运用等艺术形式上也具有独特之处。
(一)审美视角
《毛乌素绿色传奇》采用全球视野,以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在美国以及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引出中国的毛乌素绿色传奇,二者的相互映照,宣告了毛乌素沙漠的成功实践在推进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对毛乌素绿色传奇的具体叙述中,作者从与大自然平等和谐共存以及对重建的绿色家园的珍视与守护的视角来审视毛乌素沙漠的生态环境,探究《明天的预言》不可能在毛乌素沙漠上演的原因,表达出作者独特的生态体验。此外,作品所写事件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呈现出复杂性和多面性,所以在对毛乌素生态重建的描述过程中,采用全景式的叙事方式,融入毛乌素沙漠,去聆听它从沙漠走向“绿洲”的铿锵节奏,感受毛乌素沙漠悄然消失的历史事实。在对绿色英雄人物和绿色工业的代表人物的描写上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具有生态意蕴的绿色故事,塑造了宝日勒岱等一个个绿色英雄的人物形象,利用对英雄形象的渲染和感情的抒发谱写了一曲生态重建的赞歌,产生了一种宏大之美。
(二)结构安排
作品以对毛乌素沙漠的“不断的寻找”为主线,从作者的所见、所感、所闻展开叙述,各个篇章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在鄂尔多斯世代相传的热爱自然、关怀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的熏陶之下,以宝日勒岱、殷玉珍为代表的一大批绿色英雄们积极进行毛乌素沙漠的生态恢复建设。在这些与毛乌素沙漠共舞的女人和汉子们的身上,昭示出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治理毛乌素沙漠的艰辛和曲折。进入新时期,鄂尔多斯依托“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用工业化带动生态建设的产业化,在治沙的基础上向沙漠要收益。优良的生态文化以及现代化工业治沙让毛乌素摆脱了“寂静的春天”的命运,实现了“绿富同兴”的目标。作者在毛乌素大地历时三年的苦苦寻找,并未找到40年前诗人郭小川笔下的“浊浪般的沙丘”,而找到的却是几代鄂尔多斯人治沙的足迹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与诗人郭小川的寻绿和寻沙的对比中,展现出鄂尔多斯生态重建的辉煌成就。
(三)散文话语的运用
不断的发问和质询是《毛乌素绿色传奇》散文话语的一大特色。“你何时见到过这般让人醉心的草原?过去的毛乌素沙漠是个什么样子呀?”[2]2“沙漠上真的羊吃羊了吗?”[2]36乌审旗的工业化“会不会扼杀人们千辛万苦换来的满眼绿色呢?”[2]59“你说,把它恢复成原样?”[2]64“毛乌素沙漠真的要在鄂尔多斯境内消失?”[2]52“真的,兀其高的沙漠咋就没了?”[2]69等,作者的不断反问与质疑凸显出毛乌素沙漠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作者对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的生态方式的期待和欣喜。科学性和文学性的有机结合是《毛乌素绿色传奇》散文话语的另一大特色,文章采用具体有效的数据来展现毛乌素沙漠的生态危机和生态前景:20世纪80年代初,乌审旗境内的“各类风蚀、沙化土地已占总面积的94.8%,强度沙化面积比例高达40%”[2]164。在2008年召开的绿色信息通报会议上,“鄂尔多斯境内的毛乌素沙漠森林覆盖率已达30%,植被覆盖率已达75%,绿化面积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10年,毛乌素沙漠将在鄂尔多斯高原悄然消失……”[2]52作者秉持“文字真而不伪”的科学话语原则,用具体的数据资料去追踪毛乌素沙漠消失的痕迹,而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科学表达,更是一种诗意的言说。同时作者还将科学性与文学审美诗意性的原则有效结合在一起,作品的每章标题“毛乌素沙漠的秋天好喧闹”“青色雾霭笼罩的远方啊,那是牧人的梦想”“草原山最诱人的花香,是那5月开放的玫瑰”“骏马似箭掠过草浪,高亢的嘶鸣留在路上”等都显示出作家诗意的表达技巧。此外,为了增加诗意的审美表达,作家还将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相结合,在抒发对毛乌素的审美体验的同时,还在每章标题中配有毛乌素沙漠的生态景观图片,这些图片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生动地展示出毛乌素沙漠的新景象。作者运用图片景观叙事不仅丰富了艺术传达的手段,而且增强了生态散文的视觉审美刺激和作品的感染力。
四、肖亦农生态散文的形成
自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形势已给人类的生存敲响了警钟。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积极投身于生态精神的建构与传达的生态散文创作,如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缪尔的《山间夏日》、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等。这些散文通过对生态危机的揭示,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掠夺的反生态行为,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致力于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重建的散文创作,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强烈谴责了人类滥砍乱伐的行为,并发出“伐木者,醒来”的呐喊;《可可西里》宣扬对藏羚羊以及一切自然生命的尊重,激发人类的生态伦理意识;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和麦天枢的《挽汾河》展示水污染的危机,呼吁人类对水资源的保护,表达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忧患。中外优秀的生态散文作品为肖亦农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他在鄂尔多斯41年的生态体验更是创作这部绿色传奇的内在动力。作者不断地行走在鄂尔多斯大地上,亲眼目睹、感受了鄂尔多斯自然景观的变化。毛乌素沙漠的一沙、一草、一木的变化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促使他去诉说毛乌素的前世今生,书写毛乌素沙漠的绿色传奇。《毛乌素绿色传奇》的问世,不仅对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面旗帜,它的成功将促进当代生态散文创作的进一步繁荣。
[1]郭茂全.约翰·缪尔的生态散文创作[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6):23-28.
[2] 肖亦农.毛乌素绿色传奇[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2.
[3] 缪尔.我们的国家公园:前言[M].郭名倞,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3.
[4]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5] 党圣元.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3.
[6] 赵哈林.沙漠生态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龚勋]
2016-04-22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生态散文研究”(14XZW011)。
段沙沙(1990-),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生态文学批评。
I207.5
A
1008-4630(2016)04-0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