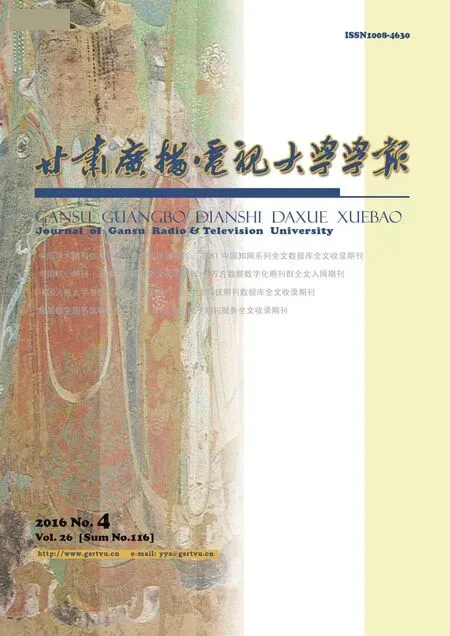针尖上的写作者
——论周晓枫散文写作状态
贾菁岚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针尖上的写作者
——论周晓枫散文写作状态
贾菁岚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周晓枫作为成果颇丰的当代散文作家,表面的顺风顺水容易遮蔽她复杂的写作状态:其作品内核始终有着难以磨灭的焦虑和紧张感。从周晓枫散文的写作状态切入,窥探其写作源头、阐释其写作态度、点明其写作位置,串联童年经历、灰色地带以及对身体的关注这三个写作维度。从贴近作家本身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写作状态蕴含的深层意义和可贵之处。
写作;童年;灰色地带;身体
“写作很少给予我信心。开始阶段就伴随着沮丧,每完成一篇文章后几乎必然涌起的失望使我推迟开展下一篇。”[1]178当读到这一段话时,笔者对它所裹携的写作焦虑与怀疑产生了一种阅读意料之外的惊讶。众所周知,周晓枫是当代散文领域一位不可忽略的作家,其作品每每发表,都能引起关注与讨论;抛开写作,她的人生也是顺风顺水,事业有成,婚姻美满。然而直至中年,周晓枫依旧将自己的人生连同写作一起搁置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暗地向往扮演精神世界里的天使。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只有立锥之地”[1]219,她向往成为那只有立锥之地的针尖天使。
通向罗马的有条条大道,同样,造就一位作家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周晓枫的写作身份是特殊的:既是作家,同时也是一名编辑——不断分裂出另一个自己,审视写作中的自己。不仅仅是动笔前的“不自信”和“不单纯”,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甚至是结束后,周晓枫都处于一种巨大的消耗中:“每写完一个段落就重读,常常懊恼,影响下个段落的进行。然后加剧到句子。最后极端到写下的词被否定,重新琢磨,希望能替换一个更妥帖的。在一个词与一个词之间,我徘徊,犹疑,灰心,蔑视自己。”[1]178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使得她在享受写作的幸福和释放的同时也陷入了逃避不了的磨损和消耗中,就好像是一颗蛀牙,正因为有曾经如蜜的甜,才有现在沁入骨髓的疼。
写作中的缓慢、怀疑以及“自虐式”的失眠、疯狂、神经质,周晓枫挥出的刀刃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失去了破风而出的速度和直击人心的尖利。挥出前巨大的消耗和磨损似乎是为了更加准确而致命地击中靶心,正如一种剧毒的蛇,以生命为交换,给予来者封喉一击。
无所不至的磨损使周晓枫始终处在缺乏安全感的写作状态中,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2],虽然这种不安全感,带给了她得以持久保持的特质——怀疑世界的精神、叛逃现实的勇气、对抗虚妄的力量。这远远不是身份所能带给她的影响,作家的写作始终要踩踏在个人经历的地表,就像她回忆年幼的自己被拴在医生母亲两米以内的范围不能乱跑一样。“作家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多与童年特殊的情感经历与心理类型有关。”[3]92-104童年,这颗种粒早已被埋下,过去的图式秘密地建构着未来的命运。
一、埋下童年齿噬的种粒
作家与童年是个永远逃避不开的话题,对于周晓枫来说更是如此,她的“童年的纯真与不安——那里,窖藏着艺术创作的某种原始生命力”[4]152,易感的孩子在成长中怀着对世界和自我的好奇和敏感,悄悄地打量着。
在某种程度上,周晓枫散文创作的最初动因就是对童年的发现和回望,“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但找到问题的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这是周晓枫在她以童年为题的散文集《收藏——时光的魔法书》中引用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仑斯的一句话。除了以童年为题的散文集外,在她的其他作品里,童年若隐若现、忽明忽暗地出现着,那些年少的经历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她,如同影子一般融进了血肉。
作家的童年经历和他们的精神财富就像一棵树,根与枝叶对应的仿佛就是童年与成年,根扎得多深、根触有多繁茂,枝叶就照着根的样子慢慢生长,土地上下就这样完成了继承与呼应。而周晓枫童年时期的种粒被残酷地埋下:十五岁的一个夜晚,她被开水烫伤,当从灼痛中醒来,当她触碰脸颊的指尖粘上了脱落的皮肤,当她不得不在治疗中自己强制撕掉掩护疼痛伤口的纱布,并且由于先天性瘢痕体质,本来并不严重的烫伤造成了面部毁容,疤痕的产生使得无瑕成为不可能的瞬间——在周晓枫的散文中,十五岁的经历不断被闪回、重复、变形。
九岁的畸胎瘤让她第一次看到了生活透露出来的险恶微笑,身体的耻辱感从此产生;十五岁的意外烫伤带给了她灾难式的吻痕,生命的多米诺骨牌仿佛被推动,一件件身体上的连锁不适和病痛接踵而至;甚至,临近中年的她也暗藏着童年的影子:草率而执拗选择的正畸似乎暴露了年少时就怀揣的对弟弟的嫉妒,对母亲忽略自己的不满。
年少时疼痛的暴露大规模地建设着她未来的人生,这种疼痛不只是身体的,更是心灵上的,她童年的种粒,似乎被上帝咬了一口,带着些微齿痕和磨损。最珍贵的不是苦难的记忆,而是对待这些苦难的心,“爱我的人赐予我礼物,我爱的赐予我伤口——显然来自后者的给予更珍贵,因为只有伤口,与我发生的是真正血肉意义的联系”[5]181。在这个没有触碰到伤口就开始大声呻吟的时代,周晓枫没有因为受伤即兴、发泄地暴露血肉淋漓的伤口,嘶喊受伤的“心得感受”,伤口在沉淀、在结晶、在反刍后将痛楚和不安转化成了尊重内心的精神和旁观的审慎角度——她用超越自身痛感的眼光“越过自恋、唯美和抒情的重重障碍,迫近生存真相”[3]92-104。
这意味着她的写作不会是轻松的,周晓枫也不愿成为一位轻易写就万千篇章的作家。童年带给她的影响是巨大且难以磨灭的,但是她勇敢面对这样的世界、面对这样的自己,不矫情、不遮蔽、不伪装,她在揭开自身的伤口审视内心的同时,也用同样犀利果决的目光扫描整个世界。阅读就像点燃储备煤炭的炉火,即可取得温暖,而周晓枫却成为了开掘矿藏的人,她不避讳弄脏自己,用个体的心灵内容、自审自省的勇敢和面对一切破损和残缺的坦诚,供给了我们温暖的养料,她在的书写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二、直面“灰色地带”的作家
童年——这笔残酷的“财富”,周晓枫带着它走入了创作。自带的焦虑、童年的破损使得她常常处在一种“灰色地带”[3]92-104,她懂得被阳光照耀的事物感受温暖的同时,也会衍生周围的阴影和黑暗。
童话——我们儿时必备的玩伴,简单明快、寓意蕴藉是它的特色,在周晓枫笔下却拥有了一种暧昧难辨的复杂气息。或许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般的致敬,珍藏有关童话的纯洁记忆被她一一拆解。
《黑童话》源自耳熟能详的童话作品,但当叙事间的缝隙和漏洞被发现,华美外衣下的童话便露出血肉淋漓的疮疤。《卖火柴的小女孩》里残酷的天堂哲学;《一千零一夜》里山鲁佐德又一次印证了用身体换取和平的可行性;《睡美人》里沉睡苏醒的公主竟然和强奸她的人永结连理,等待罪行的却是极大的幸福;《白雪公主》中我们故意忽略着字缝间透露出来的白雪公主的挑剔、虚荣、贪婪和报复。
《仙履》同样也是拆解童话的作品,辛德瑞拉在她的人生中展开了一场充满阴谋、步步为营的复仇,预谋留下的水晶鞋象征着这场复仇的最终目的:曾经的失去要以百倍千倍的代价讨要偿还。周晓枫对童话的解读是细致而犀利的,一双跳了一晚都非常合脚的高跟鞋,为何在离开舞会的奔跑中挣脱?只穿了一只鞋的脚还不如双脚赤足奔跑来得快……这两个小小的细节,还原了童话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真相。童话表面的营造有多纯粹,揭开它背后的复杂所获得的隐秘就有多震撼——爱与恨、隐忍与复仇、阳谋与阴谋,童话破裂的碎片映射着残忍的光……
正如她常常自嘲自己是随时都会发现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随时都被理想折损磨耗的理想主义者。需要拆解的真相又何止是童话,需要戳破的虚假存在于各个角落,需要直面的现实暴露在周晓枫笔下。在《焰火》里,她说:“其实所有的庆祝都秘密地建基于某种失败或牺牲。战争胜利,建立在敌军足够多的尸首上;祭祀仪式,建立在牲畜替代的死亡上。”[5]229在《黑童话》里,她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屈死的冤魂,有多少失真的史册,不知道一个光芒万丈的书里英雄,他旗帜一样鲜艳的襟袍是不是掩盖着血和违背的盟誓。”[5]34不是简单明了的孰是孰非,不是泾渭分明的正邪之分,不是非此即彼的道德绑架,周晓枫在她的作品中没有向我们兜售价值观,既不被恶收买,也不向善谄媚,无论面向何事何物,永远不丧失其警觉性。
直面现实全部内容,包括光明下的黑暗以及交界处的灰色,使得周晓枫的散文生长出了立体的触角,拥有着一种毛茸茸的、拒绝漆饰的真实质感,文字的枝蔓在碰触现实世界的同时,震撼了读者习惯性审美的、渐趋麻木的内心。她写嫉妒者温柔背后舌叉上的小毒牙(《独唱》),写需要不幸来烘托的幸福(《独唱》),写在遭受侵害时内心可能产生的隐约快感(《琥珀》)。这种焦虑也让她不断地打量内心、指向写作,她发问:“越过修辞层面,指涉文本背后的操作者:作家本人,能够不再自塑道德完人的蜡像,转而暴露自身的破损?”[5]74缺失了体味的作家、没有虫洞的文字,就像是经过液化、磨皮后的PS图像;像商店里摆放的随时可以拆卸拼凑、东拿西放的塑料模特;像防腐剂、添加剂放置过多的无限期速食食品。
周晓枫在《齿痕》里将切割的刀刃指向了自己,四十二岁的正畸隐含着年幼时因母亲更加喜爱弟弟而难以消磨的嫉妒。她说自己性格上有众多弱点:嫉妒、冲动、盲目,自认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她也并不屑于塑造完美的自己。残酷的自我切割与对外界的观察相互并生,一个更加真诚的世界在她笔下蜕壳。
三、怀抱这棵历经艰辛的树
童年,造就了周晓枫早于普通女孩的身体觉醒,痛楚使得她对身体的关注度和感受力更加丰富,血肉淋漓的十五岁夜晚是周晓枫的重要节点,她不断地从这个夜晚成长,又不断地溯洄这个夜晚。“如果说我今天格外注意身体叙事,那是因为,伴随着青春期的苏醒,我首先体会到的是身体带来的深深屈辱。”[3]92-104烫伤所引起的反应是连锁的,身体成为她不安的源泉。婴儿型的睡姿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四肢蜷缩呈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状态,怀抱身体沉沉睡去。对身体的焦虑使得她一直处在这种不安全的状态中,她的写作正是怀抱着身体进行的。
“所有走过的路都必须经由自己的身体开采”[4]223,周晓枫写自己的身体的不完美与瑕疵(《铅笔》);写身体受到伤害后精神分泌出包裹自己的痛感(《琥珀》);写女性这棵历尽艰辛的树:身体的痛经、妊娠和凋零(《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写蓓蕾般的少女、梨子般的妇人、果脯样的中年女人和垂坠的老年女人(《种粒》)。女性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自我认同过程,无论是少女发育的羞耻和尴尬,还是成年女性生育的蜕变和代价,亦或是老年女性子宫的癌变和凋落——身体被放置在了整个生命过程中去观察和书写,不是简单的身体体验,身体成为通向心灵的通道。
“过往的散文中,不是缺少女性经验的叙事,而是由于受制于女性完美主义的原则,将女性身体内存中不‘完美’的部分加以过滤。”[6]52-55在周晓枫笔下,女性不再是剔除了体味和斑点的完美天使。“写出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痛感……破损使人生动。强迫自己直视镜子,面对痣、刀口和羞于启齿的欲望……”[5]74女性在身体上破损的真实与生动被书写出来。如,由于少女病友凤梅的纯粹生理反应,她没完没了、毫无顾忌地吃、喝、拉、撒,与此相对的是她乱伦的感情期待;我们看到女人的一生,身体仿佛一棵树,成长、繁茂、枯萎、死亡,她唯一的果实培育着生命,周晓枫的散文以对待身体的关注完成了对女性内在生命的审视。
“放弃选材上的洁癖,保存叶子上的泥”[5]74,对自然真挚的生命状态的正视,正是周晓枫写作状态的体现——她用带着体温和痛感的文字创作,没有因为世俗的禁忌而避开这个话题。当“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痛感”被表达出来时,身体的经历就是一个点,由此,女性生命的感悟和内心的真实铺展开来;身体成为女性认识自身的方式、思考情感的通道,没有取悦与展览,而是有尊严、有存在意义的身体。如同伊甸园里的夏娃,当感受到肉体带来的羞耻的同时也获得了由此而生的自尊。
周晓枫一直认为,尊重身体才能尊重内心,在身体和内心世界的交叉映照下,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心理影像,扁平、光滑的女性世界被取代,更加立体和毛茸茸、活泼泼,具有生命气息和体味的世界被建构。她笔下的女性正如贝壳,痛苦地吞咽进沙子,经过岁月的浸染,被抚育成一粒粒形状各异的珍珠;也如神性的环形山,虽然充满苍凉,却激发了我们对美的无限想象。
四、结语
周晓枫就像一枚蕴含着坚硬能量的硬果核,即使遭受外界苦的侵泡、酸的腐蚀,她褶皱凹凸的外壳依旧散发着独属于自己的气息;她也像一只咀嚼桑叶时呈膜拜状的蚕,咀嚼生活中的苦痛,潜存成巨大的精神能量,吐出用生命结晶的丝质文字——这是从身体里慢慢抽出的丝。
阅读周晓枫的文字,会感觉到她的文字只是她的,不像一些文章千篇一律的结果就是抹掉姓名,随意便可加上张三李四王麻子。正如丁晓原对她的评价:“周晓枫的散文超逸了我们以往普遍的关于散文的阅读经验,以至于所谓研究散文的人士,很难用现成的散文批评话语,按部就班地对其指指点点。或者说,面对这样的散文我们简直就是失语。”[6]52-55她的写作深深地扎根于个人经验中,这种状态使得她站立在审视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双重位置。外部世界强大、内部个体脆弱,但是她却独立面对困境,在周晓枫看来,写作永远是她“潜在的救赎之路”[5]101,她不断刨掉表层,露出新鲜的花纹。
当许多写作者与现实握手言和、相谈甚欢的时候,当他们内心的锐角被物质的幸福和名利的满足打磨光滑的时候,挥出的刀匕已经弯折,不痛不痒地扫过。他们太舒适了,他们已经把自己安置在了柔软的沙发上,温暖的炉火旁,在他们写作的世界里不存在那个寒风吹彻的冬夜,拼命用手搓揉被冻坏的自己,取而代之的是香醇的咖啡捧在手心。正如生病才会更加关心自己身体一样,他们丢失了对世界、对自身的关注和反省。
童年经历、灰色地带以及对身体的关注是周晓枫散文写作的三个维度,它们就像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相互联结,建构起了散文写作的稳固底面。针尖,是周晓枫放置自己写作生命的地方,这同时也是一种状态的象征,它意味着一种时刻保持的紧张性、思考力、内省心,意味着“足够敏感的体察和感悟”[4]157。底面和顶点如此美妙地结合在一起。
疾病、不幸、苦楚以及不明朗的往事和尴尬、受挫、悲哀的体验,正是由于这些,使得周晓枫站立在了其他写作者不愿放置自己的位置。当不幸将写作的笔滋养,针尖上所意味的焦虑、不安、内省也承载着文学潜心营造的立体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思想的厚重成为了一笔不可思议的财富,这财富于周晓枫是,于我们这些渴望阅读的人更是。感谢周晓枫,感谢这位针尖上的写作者。
[1]周晓枫.珊瑚红[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
[2]周晓枫,张杰.痴迷的修辞爱好者——周晓枫散文创作访谈录[J].朔方,2009(9):110-116.
[3]周晓枫,姜广平.我的确乐于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J].西湖,2010(11).
[4]周晓枫.巨鲸歌唱[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5]周晓枫.周晓枫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6]丁晓原.周晓枫:穿行于感觉与冥想的曲径[J].文艺争鸣,2008(4).
[责任编辑龚勋]
2016-03-15
贾菁岚(1992- ),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I106.7
A
1008-4630(2016)04-0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