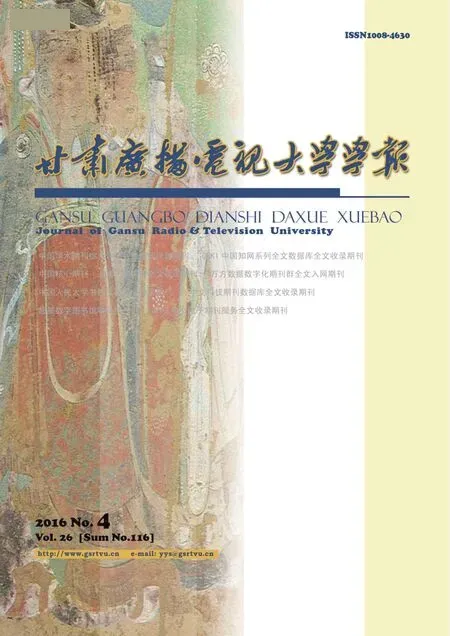“单向度”的青春
——以《绿如蓝》为例兼论消费主义时代的青春形象
宋 敏,李晓禺
(1.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定西分校,甘肃 定西 743000;2.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单向度”的青春
——以《绿如蓝》为例兼论消费主义时代的青春形象
宋敏1,李晓禺2
(1.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定西分校,甘肃 定西743000;2.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青春形象一直是文学书写的主题之一。《绿如蓝》以“历史倒置”的叙事策略及传统武侠小说的书写模式塑造了以章第中为代表的青春群体形象。他们在高考的压力下努力拼搏、勤奋刻苦,盲目认同现实,缺乏批判精神,可谓“单向度”的青春形象。在消费主义时代语境下,这种形象与以《小时代》为代表的身体化、物质化的“青春形象”截然不同,从重建中国文学青春形象的角度来看,无疑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单向度;青春形象;《绿如蓝》;消费主义
青春是一个老话题。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写当中,青春形象一直是作家、艺术家书写的主题之一。孟繁华在谈论中国文学20世纪青春形象书写时指出,中国新文学自诞生始,一直站立着一个“青春”的形象。这个“青春”是《新青年》,是“呐喊”和“彷徨”,是站在地球边放号的“天狗”;是面目一新的“大春哥”“二黑哥”“当红军的哥哥”;是犹疑不决的蒋纯祖;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梁生宝、萧长春,是林道静和欧阳海; 是“回答”“致橡树”和“一代人”,是高加林、孙少平,是返城的“知青”、平反的“右派”;是优雅的南珊、优越的李淮平;当然也是“你别无选择”和“你不可改变我”的“顽主”;同时还有“一个人的战争”,等等。90年代以后,或者说自《一地鸡毛》的小林出现之后,当代文学的青春形象逐渐隐退以至面目模糊。青春文学的变异,是当下文学被关注程度不断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当下文学逐渐丧失活力和生机的重要原因。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于青春有很多种写法,可以青春加革命如《青春之歌》,可以青春加言情如《悲伤逆流成河》,可以青春加残酷如《马粥街残酷史》,可以青春加颓废如《挪威的森林》,可以青春加玄幻如《诛仙》……当然,青春也可以《绿如蓝》。毓新的《绿如蓝》是一部关于青春的小说,这里的青春故事没有革命、阶级等概念,更没有酒吧迪厅,没有香车美女,没有摇头丸,她以西部黄土高原为大背景和底色,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上演着以章第中等人为代表的激情昂扬的青春故事,在以“西部”为底色和背景下的青春故事更显示出坚韧的激情。作者通过章第中等人的求学、高考、恋爱等经历辐射到了西部乡土、西部教育等广阔的社会内容。
一、“单向度”青春形象
《绿如蓝》写了一批青年人的青春故事。很显然,章第中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叙事者以章第中的求学经历为主要线索描写了章第中以及围绕其身边的田园静、杨琴、祁晓春、刘流长、江小兵、曹鹏炜、温捷雅等人,这是一个虽有困惑但充满激情的团体。同时,小说中也写到了鲁一鸣、花花公子、周围、杀人犯等,但小说的主要笔墨和激情都用在了前一个“绿如蓝”的群体上,他们平淡而激情昂然,艰苦却积极向上。章第中是一位典型的、标准的好学生,学习好,品德好,有正义感,几乎无可挑剔,其他几位主要人物也是如此。《绿如蓝》塑造了一群勤奋刻苦、善良纯朴、坚强乐观的学生形象。如今经历了《小时代》的“洗礼”之后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这些好学生太概念化了,甚至神化了。他们的青春生活几乎就是读书,考试,再读书,再考试,甚至偶尔产生的爱情的火花也是为了照亮升学的前景。这样的青春是否会给人以单调甚至是虚假的感觉?在此,我们有必要借用“单向度的人”这一概念来解读他们真实的“单向度”的青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进入发达工业社会以后,无论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甚至生活等方面,都只剩下一个向度,即肯定与维护的一个单一向度,而没有了批判与否定。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也被现代社会所标准化、范式化了,丧失了批判与否定的能力,成为维护这个社会的工具和奴隶,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对社会没有了否定和批判精神,会为了更好地迎合社会的潮流而一味地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心灵深处真正的个性屈服,真正的意识是让自己成为整个社会潮流所能接受的个体。马尔库塞的理论主要以发达工业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这种“单向度”的机制和力量及其表现、后果在这个西部贫穷的沉木县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马尔库塞曾指出,当代极权主义形成的原因是工业技术决定论,在沉木县——其实也是对广大中国来说,目前的教育、就业机制基本上是分数决定论、学校决定论。高分、重点大学不仅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资源,带来家族的荣耀,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毕业后的就业状况及未来发展。在沉木这样一个极度贫瘠的地方,想挣脱贫瘠似乎只有读书考大学这一条路。这是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下的广大中国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现实和真实写照。小说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写出了这个“单向度”的群体以及这种“单向度”青春的形成过程及表现。学生拼命学、老师拼命教,最终拼分数,所有的努力和指向都是分数,分数成了生活这张网的核心。“单向度”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横向上只有一个方向;一是在纵向上只有一个深度,即扁平化、无反抗等。单向度的人就是认同现实、没有批判精神、不反思的人。单向度的青春更重要地表现为被遏制压抑的主体意识。小说中所写到的所有的不合理现象,如,凌云班在为凌云教育基金会审核问题上弄虚作假,刘流长上学的内幕,沉木一中为了获得省级示范中学的称号而采取的系列公关活动,为了解决班级的问题,学校采取大班额分流以及“就地消失”整个高一年级,毕业会考中的抄袭以及老师协助抄袭等等。所有的这一切,最后都被学生默默地承受了,这些“虚假”甚至被当做一个狂欢的节日来享受,以消解紧张的学习压力。是什么原因压制了学生们的批判意识?小说没有更为精细的分析和叙述,也许只能说是他们的青春已经走进了“单向度”的巷道。小说用章第中等人的单向度群体形象为一个时代的教育做了最形象的注解。
显然,作者并不满足于通常的青春小说、教育小说的套路,而试图在青春小说、教育小说的主题之内挖掘更为深广的社会生活,作者通过时空转换的叙事方式以及文体杂糅等手法将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并以此来揭示形成这种单向度青春的原因。但作者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又显得过于温柔敦厚,以沉木一中、二中争夺生源等问题为例,两所学校斗争的书写是有礼有节的,强硬争夺背后有着温情而合理的一面,似乎始终没有脱离“人民教师”的道德底线。罗伟章的《奸细》同样是写争夺生源的事,但人民教师在争夺生源这件事上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卑劣和不可捉摸性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它远远超出了“人民教师”的底线。同样是写传统文化及“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小说里虽有章第中在沉木一中的一次考试失利后竟然惹得她的母亲要到学校找老师算账这样的细节,但整体上看,似乎没有让我们感到愤怒的父母和老师,我们看到的都是充满着情和理的谆谆教诲。当我们对比一下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时就会发现,父亲张红旗在为儿子好好读书一事上的努力、斗争以及失败后的痛苦都显得那么地“忧愤深广”。小说在家族求学史的叙述当中又因笔墨较少和缺乏内在的联系而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历史深度。在具体的人物塑造上,主要笔墨用在了“绿如蓝”这个群体上,其他人物着墨不多,本有再发挥余地的地方却停止了,特别是鲁一鸣、花花公子等人,本大有可为的。很显然,作者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对于这种“单向度”青春的探讨还是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作者写了盆娃(曹鹏炜)一家人的艰辛,似乎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贫穷”。其实,造成这种单向度青春的原因不仅仅是“贫穷”二字所能概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思想,“望子成龙”的亲情诉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在小说里显然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展现,这些都使得这“单向度”的青春有些单薄又异常坚硬。小说也因此丧失了在更深、更广阔的领域探索青春和社会的可能。也许是“绿如蓝”主题的限制,那些“不良的”“不适宜的”青春世界被作者有意无意地删减了。作者在试图超越青春小说的同时发现了很多可供探讨的点,但因其“浅尝辄止”而丧失了更进一步探索的可能,《绿如蓝》也因此而略显单薄。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还牵扯到一个如何评价单向度青春的问题。很显然,作者对此并没有进行太多的反思,他以诗意的笔调和激情告诉我们,“青春应该绿如蓝”。
二、“单向度”叙事策略
内容和形式从来都不是可以简单割裂的,小说所传达和表现出来的单向度青春的效果与其特殊的文体形式密不可分。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看法,西方教育小说主要是指“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在经典成长教育小说中,“未来”与“希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作品情节的主线。所以,研究“未来”与“希望”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教育小说研究的一个核心环节。但从《绿如蓝》的文体特征来看,似乎不能从文体上归为西方理论家所指的“教育小说”,因为小说里的主人公群体基本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单向度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上,虽说章第中、温捷雅等人写得还比较丰满圆润,但是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的趋势以及努力的方向等等似乎都没有任何变化,“序幕”中的尖子生无论在求学的道路上出现了多少曲折(小说中的叙述基本没有什么曲折),到最后都是以状元、榜眼的荣耀结束。也有个别优秀学生,如章第中,虽然中间会出现一些插曲和失误,但其最终结果还是成为了社会、老师、家长眼中的标准好学生。特别是章第中,最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又以全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一所重点大学。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也大致如此,这些出场时的武林高手最终的结果依然是独步天下。青春是充满诱惑和无限可能的,青春的复杂性和无限可能性在这里被章第中等主要人物形象遮蔽了。
从叙事手法来看,这种单向度的“坚硬”叙事特征特别明显。序幕部分就是一幅“胜利”的画面:章第中、田园静、杨琴、祁晓春、刘流长、江小兵等人以优异的高考成绩结束了中学时代,他们流露出胜利者的喜悦,之后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章第中等人的青春故事。巴赫金认为,古代作品中的神话因素,往往以一种“历史倒置”的叙述来表达希望,即“实际上只在将来能够或应该实现的事,把绝非过去的现实而只是目的和应该实现的事,当作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来加以描绘”[2]335。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间观,即借助未来以丰富现在和过去。《绿如蓝》显然也是坚信这种“绿如蓝”的青春神话模式。“因为一切积极的、理想的、应有的、期望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倒置法转向过去或部分地转到现在,这样一来所有这一切就会变得更有分量,更现实,更令人信服。”[2]335这种叙事模式有利于传达作者的创作意图,即歌颂这种绿如蓝的青春精神。但从小说的可读性来看,这种结构模式几乎完全丧失了因期待视野而带来的阅读期待和兴奋。也许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种“坚硬”叙事的弊端,为了弥补因这种坚硬叙事带来的阅读快感的丧失,作者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才子佳人与英雄救美模式,以此来增加文本的可读性。从具体的章节结构安排就能看出这种结构模式的内在肌理和特征,小说从少年天才——章第中的争夺战讲起,到主人公如愿在一中读书,从首次考试失利到收复失地,从遭遇挫折到英雄的定格,无不显示出传统武侠英雄叙事模式的影子。就连章节的命名都充满了战斗的色彩,甚至对章第中的求学模式也刻意设置了一个供其修炼的现代山洞——沉木一中图书馆。被视为现代英雄的章第中与佳人温捷雅的恋情,也是从英雄救美——帮助温捷雅学习的传统套路写起。这种结构模式不仅可以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而且有利于表现这种单向度的青春,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没有遇到学业上的大问题,偶有失误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内省而实现了逆转。社会、外部环境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小说可以与任何历史时代无关,不必有现实时间与之呼应,但其空间自然存在,没有这个空间,小说就不能架构起来。而这部小说在营造这种特殊的空间感时稍有缺憾。“空间感不是地方感,也不是‘背景’。光是有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地点、历史背景,构不成小说的空间。空间感是深入到小说本质的东西,小说中一切情节与人物,都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才具有生命。”[3]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笔墨来书写沉木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当下中国极端化的高考竞争状态,但不够饱满。因为这种神话结构模式已经确定,似乎只剩下一个证明这个神话的形成过程而已。这种结构模式的最大缺点是对“成长”“教育”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刻,更缺乏足够的反思,作者在表现单向度青春的同时,也陷入了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在巴赫金看来,静止、僵化有贬义色彩,变化则富含褒义。变化是成长的表象,成长是时间的本质。他对成长情有独钟,始终以是否成长来判断他的对象的价值。小说对青春的另一个维度——未来缺乏必要和足够的探讨。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是非特定化和未完成的,而正是因为其未完成才给生命、未来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没有教育的教育小说。从文体上讲,这种结构模式是不够成功的。对此,可以参照一下杨争光同样是写教育问题的《少年张冲六章》,这部小说在具体的文体结构上与其所要表达的对青春、教育反思的主题相契合,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六章的内容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类似于词典体小说的结构模式。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点进入文本,也因此感知到不同的“立体”的少年张冲,一个丰满但又难以“冠名”的青春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作者以这种特殊的文体形式诉说青春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其实对青春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未来”的解读。
小说在“青春”“未来”或者说“人生”的丰富性和可能性的书写和探索方面略有不足。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作者可根据叙事内容和创作意图而选择,虽无高低之分但存在合适与否的问题。《绿如蓝》基本上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这种叙事视角有利于在突破青春小说主题的同时辐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但其不利因素也在于其“外视”的角度,不利于写“教育”“成长”中的主人公的“内省”,“他们的声音有时几乎与作者的声音融合在一起”[4]93。如果适当地换用第一人称叙事就能更方便地写出青春过程中的“绿如蓝”群体的困惑和思考,这样的单向度的青春会因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得更为丰满和生动。巴赫金在谈到复调小说时强调:“复调小说的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极度紧张的对话性。一旦这种积极性减弱,主人公便开始凝固和物化。”[4]89当然,视角问题只是造成单向度群体形象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者对单向度青春神话模式的迷恋。
三、结语:消费时代的“青春形象”
青春形象的塑造与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诉求不无关系。在一个消费主义文化时代,青春和青春形象都是可以消费的“商品”。如果说1980年代以前的青春叙事可以简单概括为革命加恋爱模式,1980年代以来的青春叙事也可以概括为奋斗加迷惘模式,那么新世纪以来包围我们的《小时代》无疑将青春形象影像化为物质加身体模式,尽管新世纪文学仍有为数众多的悲伤的“涂自强”,但其受众群体显然无法与郭敬明的粉丝团抗衡,《小时代》系列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系列电影,而几乎同时上映的《青春雷锋》却以“零票房”业绩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媒体时代的影视广告、摄影美术、形象设计甚至是体育运动中的视觉表演所展现的无处不在的“青春形象”更将我们层层包围。这些作品在没有生活土壤的基础上演绎着背离生活逻辑的“青春游戏”,物质、身体、欲望成为书写的主题。当然,青春书写没有“禁区”,关键是这种书写模式与当下平凡而真实的生活无关,是“悬浮”在生活之上的青春符号消费,并与真正的苦难、灵魂的挣扎格格不入。无论是青春加恋爱模式还是奋斗加迷惘模式,其实背后生产机制和思维方式是由与“政治”的亲疏远近所决定的,青春形象是在“政治”的迎合或反抗中形成的。但新世纪以来的青春形象生产模式显然是在“物质”的“要求”下被批量生产的。在这样的时代,“涂自强”的悲伤注定是要被淹没的。法国情景主义者居伊·德波认为,在现当代社会中“最发达的商品形式是形象而非具体的物质产品”[5],尽管居伊·德波的论述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但将之应用于中国今天的消费文化语境也十分恰当,我们也已经处在一个被各种“青春”形象包围的文化当中。同时,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依赖这种视觉符号来认识、了解现实并根据这些经验来“规训”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之更符合消费主义时代“青春形象”的要求。在充斥于各种媒介的众多图像中,青春的脸庞、青春的体态、青春的笑容——青春的身体正在配合着商家的各种青春“商品”和青春宣言,那些宣称能将青春永驻的美容整形机构是这个时代青春形象的最好的注释。现代化的生产模式不仅批量生产影视作品、广告设计、体育运动、演艺节目中的青春符号,更在现实的生活中生产、重塑符合某一明星胸围、腰围的“青春”的身体。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形象、青春符号将“革命”“阶级”“进步”等话语修辞为美丽、自信、成功、幸福、理想的神话模式。在这样一种神话模式的世界里,“涂自强”的悲伤似乎只能是“个人”的,丰富的、个人的、隐秘或敞开的青春经验与青春形象再一次被工业时代“标准”的、“统一”的“青春形象”所遮蔽和消解。这种工业时代消费主义生产的青春形象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吞噬着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青春形象”。毓新所创造的单向度的“章第中”等青春形象与此格格不入,甚至充满“敌意”。尽管在艺术上有着各种各样可以商榷的空间,但这种“青春形象”本身却有着极大的意义,她不仅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和意义,更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抗性”。因为关于“青春形象”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对于“未来”的书写。特别是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现代性的生产和呈现仍具有东西、南北差距的今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孟繁华提出的重建中国文学青春形象的期许和基本诉求[6]。
[1]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18.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
[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5]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2.
[6]孟繁华.失去青春的中国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方面[J].当代作家评论,2014(1):58.
[责任编辑龚勋]
2016-03-04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词典体小说研究”(13YJC751025)。
宋敏(1972-),男,甘肃定西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李晓禺(1981-),男,河南商水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I247.5
A
1008-4630(2016)04-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