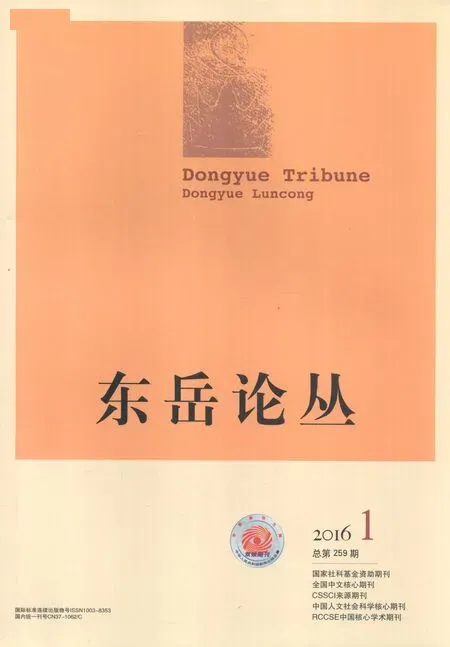章太炎政治思想的学理溯源
赵昀晖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章太炎政治思想的学理溯源
赵昀晖
(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章太炎被尊为国学大师,在政治思想上独树一帜,其本人是终结旧学、开创新学的枢纽性人物,但其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多年以来未曾廓清。章太炎与朴学大师俞樾、孙诒让、谭献的师承渊源、对小学的研究规范的贡献,在学术史上不仅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更从“内在理路”的研究维度,彰显了早年朴学训练为他种下的基本政治观念,成为其政治思想的学理基础。
章太炎;政治思想;朴学;小学;内在理路
章太炎曾言清代朴学隆盛,其缘由在异族入主中原之后的政治压制,正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矣”*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于章太炎而言,以明季排满解释清代朴学兴起可以解释其自身排满的政治意向,作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将政治意向渗入了学术史,反过来又以学术史谱系的勾画来强化排满的政治叙述。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排满之论确如烈焰,来势凶猛,然而褪去亦速*Young-tsu Wong,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1869-1936,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章太炎对排满的政治策略应用不能笃定无疑地视之为其坚决一贯的学问之道,二者虽有关联,却也存在时宜和道体的重大差别。汪荣祖先生素以研究章太炎之民族主义闻名,亦言“他的排满思想为革命宣传所需,是一时的;而多元论乃其学术性的创获,是永恒的”*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多元文化的表述》,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版,第175页。。于是,我们必须暂时放下(但绝非不再理会)排山倒海的政治形势,返诸学术脉络内部,方才能探明章太炎思想的基座所在。
一
章太炎在入诂经精舍随俞樾研习之前已谙熟乾嘉朴学著作,入得精舍,可谓正逢其时。俞樾承自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一脉,精舍则为大师阮元所创,是乾嘉学派的大本营。当时,俞樾已然成为学界泰山北斗。
章太炎在精舍研习八年,受《时务报》邀请离舍赴沪担任撰述,业师俞樾极为不悦,但师生关系并未破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师生二人的观点已有重大分歧,俞樾在学生优秀作业选刊《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中的“序言”中训导学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章太炎已然离舍赴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5页,第34-35页。。先生还在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法先王”,学生已迫不及待地奔向前线去“法后王”。俞樾之不悦恐怕不止于惜才,可惜读书种子入了火堂,而是守成之世界观与开拓之世界观在行动上的交锋。这场交锋终于在章太炎因戊戌变法失败遭到追捕而赴台湾和日本避难达致顶峰:俞樾将章太炎革出教门,章太炎则作《谢本师》回应。俞樾斥责章太炎赴台是入了异域(当时台湾已属日本),“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太炎倒是没有和先生当面顶撞,只是在《谢本师》中以戴震、全祖望的行状为自己辩白*章太炎:《谢本师》,载朱维錚、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123页。。
“谢本师”可谓章太炎一生中的标志性事件,它发生在章太炎由维新转向革命的重要关口。章太炎在经历了逃亡台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多文排满、赴日与孙中山往还等一系列事情之后已经变成了坚定的排满革命者,从日本回国后更是发表《訄书》、割辫宣示与清廷决裂,1901年拜谒俞樾之时,先生显然认为学生已然离经叛道。俞樾接受不了章太炎颠覆清廷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再开明的夫子仍然是夫子。但须注意的是,不能将这场师生决裂涂抹成新旧势力的黑白对决,至少从章太炎一方来看完全不是那样。在《谢本师》中,章太炎对俞樾不仅未加还击,而且谦恭有礼。虽有辩驳,也是借典故说明。在报纸上已然锋芒毕露的革命家章太炎没有将业师俞樾当作革命的对象。这说明了章太炎对传统的高度尊重,即便中华文明必须加以重构,也绝不意味着既往一切全都可以弃如敝履。章太炎对中华文明的这种态度活生生地反应在了他对将自己业师的态度上。世人只道章太炎勇猛凌厉的一面,却不知他素来都有节制温存的一面,而后一面才是他在思想和学术上开拓宏大格局的根基所在。
在政治立场上,同为晚清学林领袖的孙诒让与俞樾不同,在俞樾将章太炎革出教门之时,孙诒让却愿意收章太炎为徒。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生于1848年、卒于1908年。孙诒让所著《周礼正义》世评为朴学杰作;《墨子閒诂》更是至今无人超越的墨子研究经典,章太炎赞孙诒让为“三百年绝等双”!*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孙诒让传》,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同样重要的是,涉及政治的学术问题,章太炎往往会向孙诒让问计。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章太炎听从孙诒让的建议,在维新变法之际并没有公开批判他所厌恶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愿意顾全大局而将文稿束之高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与多遭变故、潜心向学的俞樾不同,孙诒让对时务更加积极,他虽未鼓吹革命,却也同情革命,并亲身参与了保路、教育等时兴事业。所以当俞樾将章太炎革出教门之时,孙诒让愿意收之为徒。在孙诒让和章太炎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朴学一脉在政治上应变前行的气度,古文经学家并非都是固守书斋的考据之士。他们虽反对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但他们绝非消极避世之辈,于政治和社会建设同样是奉己所能,只不过章太炎投入风暴般的排满革命与孙诒让如张謇一般实事谋进不同罢了。
谭献也是章太炎重要的老师。谭献,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1832年、卒于1901年。与俞樾、孙诒让不同,谭献的主要贡献被世人认定为文学而非朴学,《清史稿》把他归入了“文苑”而非“儒林”。他是著名的词人,并在文学理论上多有建树,当然,治经功夫亦不俗,否则张之洞也不会邀请他去主持经心书院*《谭廷献列传》,载《清史稿》(第4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1页。。
章太炎在精舍研习期间,不仅撰写《春秋左传读》的时候经常向谭献讨教,而且他的文风学自谭献,他在《致谭献书》中坦言:
少治经术,渐游文苑。既嗜味小学,伉思相如、子云,文多奇字,危侧趋诡,遂近伪体。吾师愍其懵暗,俯赐救疗,自审受药阳、扁,正音夔、旷,惭恨向作,悉畀游光,寻究斯恉,则宋季孟传已发之*章太炎:《致谭献书》,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表面上,这只是文风的问题,内里却蕴含着章太炎的文化态度。作为古文经师出身,他深刻认同实事求是的规矩,求真而非求美才是学问家的第一要务。在“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两难中,他选择了信,勇敢地走出迷津,在大义明确的前提下,通过谭献的指点找到了承载自己学问的恰当表述方式。章太炎对文风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他所认同的价值是“真”,这个问题既能够充分说明章太炎身上浓重的史学家品质,也能够从侧翼有力地解释他与今文经学家之间的重大分歧。
回顾章太炎与三位老师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精舍学习期间章太炎的诸多基本观念已然奠定。其一,古文经师出身使得章太炎笃信实事求是的朴学原则,求真务实是其学问的首要标准,甚至不惜为此大变文风,而求形实相符。章太炎的这种学术观念在政治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的便是与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之间的争斗。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改良一途遂为革命所取代,章太炎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推手,而转变之义理的辩难背后恰恰富含经古今文学的观念分歧。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下文仔细分辨。但毫无疑问的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师立场是在精舍随先生们研习期间就已十分稳固,绝非入世之后在论战中方才渐次形成。
其二,古文经师绝非泥古不化之学究,而也可能是深察时变的有为之士,章太炎在这方面最为极致地发扬了古文经师入世谋事的实践品格。如果说俞樾只是学术开明、政治保守的学院派,孙诒让已经是学术开明而在政治上挺身入局的实干家,章太炎其实只是在实干的层面上放弃了尊王忠君的政治约束。从古文经师入世实干的师承脉络来看,他们绝不比今文经师保守。“古文经等同于保守、今文经等同于改良”的俗见实乃附会之说。
二
章太炎在小学方面的成就乃世所公认。梁启超评价章太炎的小学,将其来龙去脉和贡献所在都说得十分清楚:
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6页。。
不单是宏观的学术史,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同样也对章太炎的小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民国之后的音韵学、文字学确以“章黄之学”为代称,章自然是章太炎,黄则是章太炎弟子黄侃。尽管黄侃并未写出系统著作便早早离世,但其小学成就显然已得学界公认*关于黄侃的生平故事、与章太炎交往、学术成就,详见刘克敌、卢建军:《章太炎与章门弟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80页。。章黄之学也成为现代汉语音韵学、文字学的先驱。陈平原先生引证了唐作藩、何盈九、裘锡圭三位语言文字学专家的评价,证明章太炎小学在学科内部古今转变的枢纽地位*陈平原:《导读》,载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关于章太炎的小学内容并本文重点亦非本文所能,我们想要做的是发掘章太炎小学背后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品质。
章太炎治小学循自正统的朴学脉络。他在《清儒》一文中对清代朴学发展史予以明快地勾画,而对前辈的小学著作推崇备至。
章太炎钦慕前辈的小学研究既是他认同朴学规范及其背后观念的重要原因,亦是其重要结果。简言之,小学成就和学界楷模与章太炎的观念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共振关系:章太炎越是精研小学,就对前辈成就越是认可,背后的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内化于心;反之亦然,章太炎越是认同小学名著树立起来的学术典范及其背后的原则,他就会越下功夫去钻研,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章太炎自己也在这方面勤下功夫。精舍习作《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不仅贯彻了朴学的规矩,而且也有意模仿先辈的做法。章太炎讲业师俞樾的《诸子评议》模仿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他自己的《札记》又何尝不是对业师的模仿,其中的训诂考订多有卓见,章太炎就其中内容多向俞樾、孙诒让、谭献请益,先生们也从中看到了章太炎的才情。作为精舍学生优秀作业汇集的《诂经精舍课艺》数集当中多有章太炎作品,其中很多就是《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传读》的篇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5页,第31-32页。。后来的章太炎对自己的早年习作并不满意,其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没有收入《章式丛书》*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5页,第31-32页。。
于小学探章太炎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把握其客观、理性的史家品格,即朴学实事求是的圭臬在小学当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以小学见长的章太炎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其中的客观历史观和“科学”世界观。章太炎在写给孙诒让的信中表白自己“惟能坚守旧文,不惑时论,期以故训声均,拥护民德”*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与孙仲容书》,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第119页。。这句话不仅对前辈表达了自己的朴学立场,也从字面上透出小学训练的影响。章太炎总结治学之法,曰“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太华辞”*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与孙仲容书》,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第119页。。章法所蕴涵的朴学精神与章太炎的史家品格是高度一致的,与章太炎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古典著作的方法是一致的。钱穆先生对章太炎卓越的小学与史学之间关系的洞察可谓敏锐,他说章太炎“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载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342页。。章太炎的学问绝非已然全新,落入“学科”(discipline)分化的纪律和规训当中,而是全然一体的“旧学”,这也是今人研究章太炎学问的重大障碍之一。但于章太炎诸学当中,贯穿首尾的是一种史学家求真务实的精神品质,而非哲学家的玄思成理,亦非政治家的政教文宣。小学正是章太炎学术精神的硬起点,从中即可透视其客观求真的自我要求和世界观。
章太炎这种客观精神和治学方法显然与今文经学大异其趣,上述十八字箴言几乎正是针对今文经学的批评。由是,我们可以立足小学这个硬起点来进一步申述章太炎与今文经学家的分歧以及背后的政治意涵。
首先,章太炎极力反对今文经学家的“孔子造经”之说,认为将致疑古风潮。孔子造经之说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学术论点,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当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新学伪经考》主张刘歆、王莽完全篡改汉代以前的经书,后世得传不过是他们所造的伪书,即“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则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载《康有为全集》(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9页。。《孔子改制考》则主张六经非为孔子编订,而为孔子创作,即“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手作,故得谓之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章太炎对上述观点都非常不赞成。今文经学的这种论调势必引致疑古风潮,不仅六经,整个中国传统的神圣性,皆遭动摇。即便今文经学家自己不说疑古之言,“后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章太炎:《今古文辨义》(1899年12月25日),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5页。。章太炎预言并批判了今文经学家对中国传统的破坏,揭示出今文经学的吊诡之处:今文经学家力图通过树立孔子的权威来达成改制的政治目的,即他们预设和极力塑造的合法性资源是中国传统,但他们崇孔的论证却反过来严重地损害了传统的可信度,将世人引向疑古,无异于将自己的事业釜底抽薪。
其次,章太炎全盘反对今文经学设立的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关系基本框架。今文经学强调圣人神道设教,而历史本身是有规律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只要深挖圣人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即可明神道而设新教,据以改造政治。在章太炎看来,这是迷信!这种迷信古已有之,是中国屡遭祸乱的重要根源。他把矛头一直追溯到董仲舒,说“(张)翰凤为义和团之先师,长素(康有为)虽与相反,而妖妄则同,若探其源,则董仲舒、益奉亦义和团之远祖矣”*章太炎:《菿汉微言》,载《章氏丛书》(下),台北:台北世界书局,1982年版,第949页。。中国传统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但子思、孟子又拿出已经衰落的五行学说,贾谊、董仲舒后来发扬光大,巫、医、史、祝的上古遗风“祸民”不断*章太炎:《訄书初刻本·争教》,载《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2页。。章太炎对史实的认定可以再加讨论,但他坚决反对将中国传统归结为玄之又玄的宗教演化这一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则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虽燔炊史志犹可”*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征信论下》,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果如神道一般可测吉凶便能为治乱之大业,则历史不过是旧人之絮叨,政治亦不过是神棍之把戏。章太炎毕生强调“征信”,以史家的态度求“信史”,对于今文经学家言文为教、言教为神的做法一直予以坚决地斗争。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章太炎为什么极力反对立国教之事。
再次,章太炎坚决反对今文经学家提倡的“通经致用”。如若通经与致用之间的关系被截断,那么今文经学家所力行的托古改制自然也就失去了学理基础,而作为托古改制之结果的尊卑有序自然也就不是理想政治的图景。经书载道,是中国传统源远流长的观念,今文经学家们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新道,沿立教以图变革。康有为不遗余力就是要“发明儒为孔子教号,以著孔子为万世教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章太炎的史家式观点无异于对今文经学这种套路的釜底抽薪,他主张“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章太炎:《诸子学略说》(1906年9月),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6页。。经典只是史书,没有什么高深的义理蕴藏其中,而且,古今大异,寻求变革只能是“法后王”,以史上之实况定今变之纷扰,简直就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所以,通经并不能致用。如此一来,托古改制也就没有必要了。古制只是古人应对古势的办法,今时移势易,寻求微言大义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古制当中的尊卑高下并不可取。董仲舒的迷信之学就是要稳定君臣尊卑的格局,而今文经学家们在新社会已然可见端倪的情势下仍大加发挥,实在是逆流而动。归根结底,通经致用为尊卑高下提供了卑劣政治通向神圣叙事的学理和实践逻辑,其实是儒家为稻粱谋的伎俩,即“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与人论朴学报书》,载《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击破通经致用,今文经学上言神道、下倡尊卑的学理-政治格局就会被拦腰截断,而章太炎征信求实、因时为备的学理-政治格局就相应树立起来。
结 论
综上所述,早年章太炎在重小学、开子学、抑宋学的治学路上沿着俞樾的门径前行,他日后的激烈之论,如排满的民族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反代议反政党反国家的理论都尚未见明显的踪迹,还不是“典型的章太炎”。但明确可见的是,他的危机意识、小学通史学的史观、以诸子为切口通观国史的视野、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真理观世界观,都已经比较完整。危机意识驱动他去寻求解决之道,小学为基的国粹是此解决之道的必要组成部分,实事求是要求他排除定见而法后王,诸子学则是他开阔视野、锤炼学术的主战场,通过这一磨砺,他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思想世界。
[责任编辑:韩小凤]
赵昀晖(1970-),女,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D693
A
1003-8353(2016)01-01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