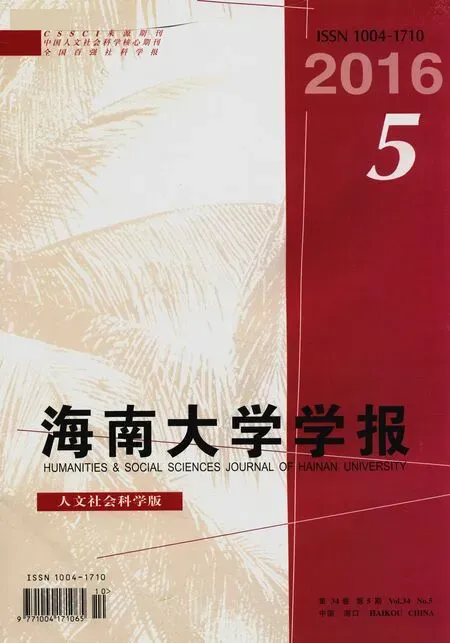人种志遮盖下的政治哲学
——《日耳曼尼亚志》的结构与意图分析
曾维术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晋中, 030801)
人种志遮盖下的政治哲学
——《日耳曼尼亚志》的结构与意图分析
曾维术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 晋中, 030801)
通常认为《日耳曼尼亚志》分成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两部分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个谜。论题打破史学与哲学的樊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审视《日耳曼尼亚志》,初步得出两部分是“质料-形式”的关系的结论,并尝试根据该结论,进一步推测《日耳曼尼亚志》的写作意图为应对基督教的问题。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罗马;基督教
很少人会把塔西佗跟哲学扯上关系,原因很可能是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似乎表示过对哲学的拒斥:“我记得他(指阿古利可拉)经常说到他早年之沉醉于哲学,要不是他母亲谨慎地对他炽热的精神予以遏止的话,他之沉溺于哲学的程度将会使他不适合作一个罗马人和元老院议员了”[1]3。一般认为,塔西佗有着罗马的实干精神,对哲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而,正如多雷(T. A. Dorey)所指出的,阿古利可拉能超出一般的军士水平,到达恺撒与斯奇皮奥(Scipios)的境界,全凭哲学对其理智能力的锻炼。塔西佗曾说,阿古利可拉保持了节制,这得益于他的智慧。多雷认为,塔西佗此处很可能指“可贵的中道”(golden mean),阿古利可拉很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尽管他作为总督所遵循的原则——统治者须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显示出他受惠于柏拉图的《理想国》[2]。由此可见,哲学与塔西佗恐怕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格格不入。
一、非政治性与政治性: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区别
假如放下偏见,再来看《日耳曼尼亚志》就可能发现,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过渡段落,其实已经告诉读者《日耳曼尼亚志》的结构安排的原因:
上面我已经对全部(omnium)日耳曼的起源(origine)和风俗习惯(moribus)作了共同的(in commune)叙述,现在我要谈一谈各个部落不同的组织(instituta)与宗教仪式(ritus),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以及由日耳曼尼亚迁到高卢的究竟是那几个部落。*本文所引《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译文,见汉译《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所引《编年史》译文见汉译《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部分译文根据《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Loeb本、《编年史》F. R. D. Goodyear注疏本调整。[1]60
文中用来描述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主题的词语,并不相同。第一部分是关于起源和风俗,第二部分是关于组织与宗教仪式。初看上去,二者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既然塔西佗用了不同的词语去表述,二者肯定有差别。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组织”(instituta)这个词语——它马上把人带到《编年史》的开篇“路奇乌斯·布鲁图斯(L. Brutus)制订了(instituit)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的制度”[3]1。instituta与instituit词源相同,既然在《编年史》那里奠立的是政治制度,那么在《日耳曼尼亚志》这里,“组织”很可能不是一般的组织,而是政制——第一部分所写的内容,则可能是一种前政治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是家庭(村坊)和城邦,而君王不外乎是家长与村长的延伸。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着重点出:“各野蛮民族至今还保持着王权,其渊源就在这里”[4]6。为了说明这种前政治的原始家庭关系,他还引用了荷马《奥德赛》中的诗句:“人各统率着他的儿女和妻子”[4]6。荷马原本用这句诗来描述独目巨人的生活——食人的独目巨人是最原始、野蛮的部落。《日耳曼尼亚志》第一部分恰好对独目巨人有所影射,那是托马斯(Richard F.Thomas)发现的“用荆棘束衣”典故[5]60,该典故源自维吉尔对阿凯墨尼得斯的描写:阿凯墨尼得斯是奥德修斯留在独目巨人岛上的伙伴,他几乎丧失了希腊性或者政治性。用这个典故来描绘日耳曼人,可能在暗示第一部分中的日耳曼人也缺乏政治性:即便表面看上去他们有政治系统,譬如酋长统治。但塔西佗也许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这种王政不算政治性统治。
要确证这一点,可以再回到《编年史》的开篇。在“路奇乌斯·布鲁图斯制订了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的制度”之前,塔西佗还说到,“城邦罗马(Urbem Romam)最初(a principio)由国王(reges)把持(habuere)”[3]1——这才是《编年史》字面意义上的开篇。布鲁图斯的二次奠基,意味着这个“最初”(a principio)并不完美,这个“由国王(reges)把持(habuere)”的状态并不完美。 如果在塔西佗看来,“最初”意味着不完美,意味着有待修正,那么可以肯定,《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起源”(origine)是前政治状态。但是,第一部分除了写起源,还写了风俗(moribus),那么风俗也是前政治的吗?
在《编年史》卷三,塔西佗考察了人类的法制史(3.26-28)。在这段考察中,最古老的凡人也有风俗,因此风俗完全有可能是前政治状态。但是,在《阿古利可拉传》里面,塔西佗要记述岳父阿古利可拉的习惯——作品的标题就有“习惯”(mos)一词——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一困惑把人带到《阿古利可拉传》结尾处,塔西佗在那里谈到了阿古利可拉的习惯:
并不是说,我反对用大理石或青铜来雕塑您的形象(imaginibus);但是,一切面像都和人的面貌同样的脆弱,它终有毁灭之一日,唯独精神的范型(forma mentis)永恒(aeterna),能够抓住(tenere)它、模仿(exprimere)它的,不是靠其他质料(materiam)和艺术(artem),而是靠您自身的习惯(moribus)。[1]36
塔西佗在此把习惯看成某种中介,连接着“永恒的精神范型”和阿古利可拉的身体。“精神的范型”之说,让人想起柏拉图的理念,如果这一联系可以确证,习惯就是介于质料与理念(形式)之间的东西:人通过习惯来模仿乃至抓住永恒不变的理念,习惯是一个塑形的过程。从最古老的凡人到阿古利可拉,习惯展现了它的延展性——从与质料无异的自发、无意识的活动,到对理念的自觉的模仿,习惯可高可低。《日耳曼尼亚志》第一部分中的习惯,并非阿古利可拉那种对理念的模仿——因为第一部分还没有理念——它是塔西佗眼中单凭自然能够产生的最好的风俗[6]。之所以说第一部分还没有理念,乃是因为它还没有政制,instituta一词包含有组织、构造、建筑等意思,总之,institua是有“形状”(forma)的。
《日耳曼尼亚志》第一部分描写的日耳曼都缺乏“形状”:“谁愿意去日耳曼,那片不成形状的土地?”[1]46-47“一切营造都使用没有形状的木材,没有美或装饰”[1]55。第一部分中的日耳曼人,他们能接触到的有形状东西,只有来自罗马的货币:“他们认识(agnoscunt)并选择我们的货币的某些形状”[1]49,“形状-理念”的获得依靠认知活动。由此也可以理解,第二部分的开端为何有教诲的意味:institua有教育、教导的意思,《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中的“阿沛”(Marcus Aper),正是被多数人指责为缺乏“训练(institutione)与诗文教育(litteris)”[7]。在《日耳曼尼亚志》里,阐明政制理念的同时也是开展教育。
至此,已经考察过27.2中有关主题的4个关键词中的3个(起源、风俗、组织),剩下“仪式”(ritus)。要搞清楚仪式意味着什么,并非易事。它肯定不是第一部分的质料,它与政制也有所差别。后一种关系可能更难以厘清,或许从这里开始,就应该将仪式与政制对比着来理解。这个考察过程会有些漫长,先从一组看似不那么相关的对比入手。
托马斯曾考察过《日耳曼尼亚志》中两条河流的差异,但他并未进一步阐释为何会有这种差异[5]63。这两条河流其实是两个隐喻*塔西佗的其他地理环境描写也往往是隐喻。,寓意着不同的德性,这正是塔西佗经常用拟人手法描写地理环境的原因。莱茵河发源于不可接近的(inaccesso)、陡峭的(praecipiti)山峰(vertice),暗示莱茵河象征着较高的德性;多瑙河发源于和缓(molli)、较低平(clementer edito)的山脊(iugo),表明多瑙河代表的德性较低。莱茵河发源的方式是升起(ortus),寓意莱茵河有向上追求的品性;多瑙河发源的方式是溢出(effusus),暗示多瑙河有放荡的倾向。莱茵河入海的方式是混合(miscetur),且入海口只有一个,表明莱茵河专一、节制;多瑙河入海的方式是爆发(erumpat),且入海口分为七道,六道注入朋都海,第七道“被沼泽吞没/耗尽/喝尽”(paludibus hauritur)[1]46,表明多瑙河缺乏自制,尤其是第七道“沼泽喝尽”,更有酗酒至死之意。与此相应,《日耳曼尼亚志》第二部分描写的诸部落,属于莱茵河流域的明显要比多瑙河流域的德性高。那么,塔西佗在此持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吗?塔西佗以河流、山峰作为边界,来切割、塑造日耳曼尼亚这块质料吗?
河流作为边界,看上去再自然不过,但正如高曼指出的,物理边界并非区分人种的真正界线,各部落经常跨越河流,而这最终使得人们无法判别他们的类别[8]137-138。塔西佗写道,无法区分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组织(institutis)和风俗习惯迄今保持着一模一样”[1]61,这反过来说明,要将人种区分出来,必须以语言、组织和风俗习惯为标准。如前所述,风俗尤其是《日耳曼尼亚志》中的风俗并非真正的“形状”,那么,有理由推测,与风俗位置对称的语言同样不是真正的“形状”,真正能作为线条划分质料的,只有居中的“组织”——政制。政制意味着好与坏:政制由掌权之人所追求的目的而定,目的不同,政制就不同,目的有好坏,政制就有好坏。真正能划分质料的标准,因此是好与坏(bona malaque)。当大河两岸有着同样的好与坏时,大河两岸的部落便无法区分——他们是相同的一类。
这样,河流等物理边界就不可能是不同政制的真正界限,毋宁说,地理环境是一种隐喻,就如柏拉图的洞穴、维吉尔的蜜蜂社会一样,用来辅助建立不同的政制理念。当然,对地理环境的描写完全可以跟史实相合——事实上,塔西佗有可能认为,与史实相合的程度越高,写作“诗化历史”就更加有利:这样可以让一般观众信以为真,从而实现作家的教化目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日耳曼尼亚志》第二部分的开头,就容易理解了:按照27.2,塔西佗打算在论述完各部落的政制、仪式之后,再谈由日耳曼尼亚迁往高卢的部落。但事实上他的顺序相反,在接下来的第28、29节中,马上就开始谈如何区分日耳曼尼亚的部落与高卢的部落。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他要建立区分政制的标准(否定地理环境作为政制的标准),并将日耳曼人从高卢人那里切割出来。高卢人降服于罗马,但塔西佗并不尊重臣服于罗马的部落——臣服于罗马本身就是柔弱、堕落的表现。
二、政制类型学: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
将高卢人排除之后,塔西佗开始谈莱茵河流域的日耳曼人(30-37)。首先是卡狄人(Chatti),他们所处的地区大部分为山脉所盘踞,但地势逐渐下降,将他们包围住的森林也就将他们一直送到平原之上。托马斯注意到,下降(raresco)一词有强烈的坐落或定居(situs)意味[5]70,对比28-29段中喜欢迁移的高卢人,定居意味着稳定,亦即意味着政制水平程度较高,institutum本身就是“定居”——这个词有太强烈的建筑学意味。但下降可能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卡狄人本身的德性也不太高。德性不高的原因在环境描写中也有所体现:将他们包围住的森林也就将他们一直送到平原之上——他们没有能形成封闭的界线,他们敞开了(raresco一词也有“敞开”的意思)。因此,卡狄人的确善战,在这方面接近罗马人,但他们不善于守成。敞开的卡狄人没有居室、没有田地、没有职业,他们并没有真正稳定下来,没有真正“成形”:没有形成良好的政制建筑。
接下来是乌昔鄙夷人(Usipi)和邓克特累人(Tencteri)。这两个部落比卡狄人要更高级一点,他们不仅以勇武善战著称,尤其善于组织骑兵。邓克特累人骑兵的威名不在卡狄人的步兵之下,这说明邓克特累人的政制水平更高。因为“大凡骑兵的特点就是胜如潮涌、败如山崩,迅捷和慌怯总是连在一起”[1]63,而邓克特累人骑兵可以取得与卡狄人的步兵同等的威名,可见其纪律与训练要更为严格。战马的出现也说明这两个部落更为富有。同时,他们也比卡狄人善于守成,“他们的祖先奠立了(instituere)这种制度,后世模仿(imitantur)”,“马,也和奴隶、房屋及其他遗产一样,由儿辈继承”[1]63-64,这是一种形式更完整、更稳定的政制,因此他们的地形相应是“莱茵河的河道已经固定下来,并当作边界了”[1]63。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重嫡也重德,“马不一定由长子继承,而是由特别勇敢善战的一个儿子来继承”[1]64。
如果勇敢的德性继续发扬、不加节制,就有可能走火入魔,这就是卜茹克特累人(Bructeri)的情况。卜茹克特累人或因为专横(superbiae)而遭到憎恨,或因为富有而遭到眼馋,被卡马维人(Chamavi)和安古利瓦累夷人(Angrivarii)赶走或消灭。这几乎就是对罗马人的提醒,无怪乎在这个地方塔西佗会突然提到罗马人,还有对帝国命运的著名预言。罗马人以勇敢德性闻名,而卜茹克特累人象征着勇敢德性的走火入魔。从塔西佗的其他作品来看,罗马人显然已完全具备成为卜茹克特累人的条件:他们足够专横,足够奢侈。塔西佗的预言绝非耸人听闻。如果罗马已经走火入魔,有什么办法去救治它呢?从表面上看,塔西佗似乎相当悲观:他只是依赖祈祷,祈求诸神的福佑。然而,塔西佗通晓哲学,通晓哲学的人会向诸神祷告吗?人们注意到,塔西佗在此用来表示祷告的词是quaeso,而非在其他作品中屡屡出现的prex。quaeso除了有祷告的意思,还有“探索,努力获得”的意思。后文讲到“野蛮人不去探寻琥珀的自然和原因(nec quae natura quaeve ratio gignat quaesitum compertumve)”时[1]71-72,用的正是quaeso的探索之义。因此,与其说塔西佗是向诸神祷告福佑,不如说他是在努力寻找或让这些部落对人们保持友好、或让他们彼此仇视起来的办法。哲学随之登场。
哲学与勇敢表面上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哲学总是大胆的产物。雅典哲学最为繁盛的时候,也是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高曼在这方面可谓眼光独到,他发现,大海作为边界,隔开的不是不同的地区,而是不同的世界:神与人的世界,对这条边界的超越是宗教性而非空间性的[8]138。托马斯同样出色,他认为塔西佗笔下的探索海洋活动是“文化上的大胆”[5]66,大海则被拟人化,抵抗探索者;同时他将探海者与普罗米修斯、代达罗斯联系起来——普罗米修斯和代达罗斯都是因过分大胆而遭难的角色,这似乎暗示着哲学的矛盾性质:不勇敢根本不会有哲学,太勇敢又会招来杀身之祸。同时还可以补充:塔西佗引入哲学来纠正勇敢之偏,在纠正勇敢之偏的同时又要防止哲学自己走偏。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杜路苏斯·日尔曼尼库斯(Drusus Germanicus)在大海面前回头是岸:“与其去认知(scire),倒不如相信神功来得神圣和恭敬”[1]65。
有了日尔曼尼库斯——此人曾被认为是恢复共和国的最大希望[3]30——的回头是岸,就有了考契人的文武双全。考契人起于弗累昔夷人住所的边境,弗累昔夷人所在地区便是上述杜路苏斯·日尔曼尼库斯探寻过(temptavimus)的地区,这意味着,考契人起于杜路苏斯·日尔曼尼库斯式的哲学/文教;同时,考契人止于卡狄人之境,这意味着他们止于卡狄人式的武功。如此文武双全,不偏不倚,难怪塔西佗称他们为“最高尚”的一族。托马斯看得很准确,这是一块“北方净土”[5]68-69,它是塔西佗心中的“理想国”。认为塔西佗只欣赏淳朴勇敢,排斥文化教育的解读路向,都忽视了这个短小的段落,忽视了塔西佗把最高赞誉给予了谁。这样一个理想国完全自足:“他们和别的部落和平相处,不相往来(secretique)”[1]65,secretus甚至有秘密、隐藏、隐居的意思。最理想的部落是最封闭的部落,形式上似乎完全闭合。
凯路斯奇人(Cherusci)在卡乌奇人与卡提伊人的侧翼,这样三个部落似乎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如果从德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三角关系就更明显了:凯路斯奇人代表着节制胜于勇敢,卡乌奇人象征着文武双全,卡提伊人象征着勇敢胜于节制,这三个部落卡乌奇人居中——在塔西佗的行文中也是居中。正如对卜茹克特累人的描写暗含着对罗马帝国的警醒,对车茹喜人的描写同样暗含着对罗马帝国的警醒:罗马人既有卜茹克特累人的骄横毛病(对行省横征暴敛),也有车茹喜人的萎靡毛病。自奥古斯都平定地中海以来,罗马人一度迷醉在甜腻的和平之中:“国内平静无事”[3]4、奥古斯都“以甜蜜的闲暇(dulcedine otii)吸引住一切(cunctos dulcedine otii pellexit)”[3]2,天真的和平主义只能换来覆灭。
塔西佗呈现了勇敢与节制(中间暗含着智慧)的相互消长之后,谈起了青布累人(Cimbri)——谈到这个部落完全是为了引出罗马与日耳曼人的交锋史,因为这个部落现在已经不甚重要。由此出现了《日耳曼尼亚志》中最长的一段插话,这段以历史为题材的插话,到底该怎么理解呢,它是否如一般所认为的那么“离题”呢?
笔者注意到,这段插话出现在莱茵河诸部落的结尾、在多瑙河诸部落的前面——它是一条界线,一条文本内部的界线。正如前面考察河流时指出过的,莱茵河寓意的品质要比多瑙河寓意的品质高,这从塔西佗对这些部落的逐一描写中可以看出,问题是该如何去理解这种品质上的差异?日耳曼人与罗马人210年的交锋史,也许可以给答案:莱茵河诸部落,是可以跟罗马最鼎盛的军事力量打成平手的部落——他们不是一般的野蛮人,而是具有政治制度(甚至最好的政治制度)、从而是具有德性的政治团体。结合前述主题词“政制”与“仪式”,可以推测第二部分的“政制”主题,到这段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交锋史为止,后面的多瑙河诸部落没有“政制”,只有“仪式”。
三、考察犹太教与基督教:希腊罗马政治哲学的新维度
“仪式”显然与宗教相关。与此相反,塔西佗对莱茵河诸部落的描写,明显淡化了宗教主题:除了日尔曼尼库斯回头是岸那一情节,30-37小节基本上没有宗教的位置。塔西佗本人在第33小节的祈祷,已被证明是一种哲学探索;而日尔曼尼库斯的“信仰神功”,与其说是虔敬,不如说是节制。对多瑙河诸部落的描写则不同,宗教在那里是当仁不让、最为抢眼的主题。如前所述,《日耳曼尼亚志》第一部分讲的是质料,第二部分的“政制”讲的是形式,按此推理,“仪式”很可能也是一种形式,一种不完美的形式:最好的仪式可能也比不上最差的政制。
塔西佗在此似乎超出了希腊罗马传统的政治理论,在传统政治理论看来,政制依城邦所追求的目的而定,可以分出追求好或正义的王制或贵族制、追求荣誉的荣誉制、追求财富的寡头制、追求平等的民主制、追求欲望的僭主制,等等,这些目标都是德性(或非德性)的目标。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制类型时,并没有把宗教视为一种区分标准——没有考虑一种以宗教或信仰为目标的政治团体。在他们那里,无论是哪一种政制,似乎都分享着共同的希腊多神教宗教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各政制展开对自己心仪的世俗目标的追逐。倘若传统政治理论并不在意区分宗教的类型,塔西佗对多瑙河诸部落作出“仪式”的考察,就是一种创新,他把一个新的维度带入到希腊罗马政治理论传统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问题的蹊跷之处在于,从政治教育的角度看,政治教育在第37小节之前就已经完成:从荣誉制色彩的、尚武的部落,到文武双全的最佳部落(贵族制),再到拥有迂腐正义观念的部落(此种制度似乎是塔西佗新提出来的),该说的似乎已经说完,如果不是继续谈诸如民主制、僭主制的话。塔西佗为何要花费五分之一的篇幅(9个小节)去谈一些低等部落,难道仅仅是为了猎奇?
塔西佗首先指出,多瑙河诸部落在名字上与莱茵河诸部落不同。他们有一个总称“斯维比人”(Suebi),虽然他们分成许多个部落,各有不同的名称;莱茵河诸部落,只有各个部落的名称,没有总称。如果说莱茵河部落的一个名字代表某一类型,那么多瑙河诸部落既有总称也有分称的特点,似乎意味着这些部落的区别其实不大,它们的分化不明显,它们的形式很不完美,比较接近原始质料,因此可以粗略地归为一类。接下来塔西佗讲斯维比人的共同特征:他们区别于其他日耳曼部落的地方,在于他们将头发束在脑后,绾成一个髻。这种区分标准看上去十分奇怪,因为政制的区分标准在于城邦追求的目的,而非统治者的人数,更不在于外在的装束。现在,塔西佗竟说斯维比的分类标准是发型—— 一个看上去再外在不过的标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疑问很快就被打消,因为塔西佗随后就说到,“这是对形貌的修饰(ea cura formae)”[1]67——原来发型也是形,这种形式同样连接着目的——“但是无罪(innoxia),既不是为了爱,也不是为了被爱(neque enim ut ament amenturve)”[1]67。这种目的毋宁说是无目的,传统政制无论是王制、贵族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都有所追求,都有所爱,而斯维比人的特点就是没有爱。没有爱即无罪,换一种说法,有爱或许就是有罪,这会让人想起哪一个民族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塔西佗称这个发髻是一个标记(insigne),这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词语,尽管并不总是包含宗教意味:“你们……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錾成的石像(insignem)”[9],“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insigne)的角”[10]——塔西佗是否想让人想起犹太教?
塔西佗在《历史》第五卷的确考察过犹太教,那里的说法跟这里的说法的确有些近似。在《历史》中,塔西佗说犹太教的“仪式姑且不论它们的起源如何,它们所以能存在乃是由于它们的古老”[11] 335,而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塔西佗说:
塞姆诺内斯人(Semnones)自称是斯维比人中最古老和声望最高的一支。他们的宗教可以证明他们的古老。[1]67
他们就特别喜欢生男育女,并且不把死亡放到眼里。[11]336
塞姆诺内斯人的繁盛更加强了他们的声望;他们分成了一百个分部,部众的强大使他们自命为斯维比人的领袖。[1]67-68
此外,塞姆诺内斯人将跌倒(prolapsus)视为很要紧的事,在《圣经》中,跌倒(scandalizare)是严重的过错,虽然两者的用词并不一样,但观念是一致的。相似的观念当然还有:“所有这些迷信都是由于他们相信他们种族就起源于此(inde initia gentis),并且相信万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这里的缘故(ibi regnator omnium deus)”[1]67。最后是地理环境的佐证,多瑙河分七道入海,而犹太人最为重视数字七:“他们说他们最初选择第七天为休息,是因为他们的痛苦是那一天才结束的……结果每到第七年也什么都不做了……许多天体的运行和旋转都是和七的倍数有关的”[11]334-335。种种迹象表明,这段对塞姆诺内斯人的描述,即便不是真的在写犹太教,至少也是在写与其类似的宗教。
考察了塞姆诺内斯人之后,塔西佗接着说了一连串的部落,这些部落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那就是他们共同崇奉大地之母纳尔土斯(Nerthus)——又是宗教上的事情。塔西佗对此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一种神秘的恐怖和愚昧的(ignorantia)虔诚,认为只有注定了要死的人才能见到女神的沐浴”[1]68。前面这两种部落,一种崇拜万物之主,一种崇拜大地之母,虽然都迷信(塔西佗毫不含混地指出这一点),但前者人多势众,后者敢于冒险,都取得了政治独立的地位,因此“他们都为河流与森林所围护(muniuntur)”[1]68。
接着塔西佗说到,斯维比人的这部分甚至延伸到日耳曼更为隐闭(secretiora)的地区。塔西佗曾经称考契人的居住方式为隐闭,这里的说法似乎意味着斯维比的宗教迷信渗透到了原本较好的日耳曼地区。接着塔西佗在此突然重复叙述的方式,一如前面沿着莱茵河叙述的方式那样,沿着多瑙河叙述。重提莱茵河,至少让人想起了莱茵河诸部落的德性(30-37),当然也能让人想起莱茵河西岸的部落对于罗马帝国的臣服(28-30)。因此接下来的主题是,原来德性较好的日耳曼部落,如何遭受败坏而逐渐丧失自由。
塔西佗依次考察了几族人:从与罗马平等经商的厄尔门杜累人(Hermundurorum),到受罗马傀儡统治的马可曼尼人(Marcomani)和夸地人(Quadi)(罗马要在这些部落上花钱),再到向异族纳贡的哥梯尼人(Cotini)和俄昔人(Osis),政治独立性越来越低,越来越远离自由。按理说,人种志考察至此已经该收尾了,但塔西佗笔锋一转,将原来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斯维比人分成两半:“斯维比人被一条连绵的山脉隔成两半,在山外还住着许多部落。其中通用范围最广的共名为鲁给夷人(Lugii)”[1]70。这些山外的鲁给夷人,跟山内的斯维比人有何不同呢?塔西佗着墨不多,但已经足够让人判断了:
只有用罗马人对于卡斯托神(Castor)和玻鲁克斯神(Pollux)的说法才能体现这些神的意味。他们所谓阿尔契(Alci)诸神的性质就是这样。他们没有神像,也丝毫没有外来迷信的痕迹;但却把这些神当作年轻的兄弟来供奉着。[1]70
卡斯托神和玻鲁克斯神是著名的孪生兄弟。虽然是孪生,这两兄弟却是同母异父:卡斯托是凡人廷达瑞俄斯(Tyndareus)之子,玻鲁克斯是宙斯之子。在一次战斗中,卡斯托身死,玻鲁克斯不愿独生,向宙斯祈求死亡,宙斯允许他同卡斯托分享长生之乐。从此,这两兄弟一天生活在奥林波斯,一天生活在冥界。据某些传说,宙斯为他们兄弟间的友爱所感动,就把他们化为双子星座。很明显,这两兄弟以跨越人神界限、跨越生死界限的友爱著称。塔西佗也写到,鲁给夷人把他们的神当作年轻的兄弟来供奉,而他们的神并没有神像——这些特点不能不令人想起基督教,尤其是当考虑到保罗前往罗马时,所乘的船刻有“卡斯托的标记”(《使徒行传》)*鲁给夷(Lugii)一名由lugeo[痛哭、举哀、戴孝]化来。[12]。 如果鲁给夷人信奉的是基督教,那么山外与山内的斯维比人的差别就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差别。在塔西佗看来,这个宗教的特点是阴性的:他们的祭司穿着女人的衣服,他们所用的颜色是黑色(黑色的盾,专门乘黑夜交战,像一群阴兵鬼卒)。从摆放的位置来看,塔西佗对基督教的评价要比犹太教低,尽管如此,基督教还可以再分出高低。阿累夷人(Harii)显然还有战斗精神,因此是鲁给夷人当中最强大的一支。在鲁给夷人外面,是哥托内斯人(Gothones),他们由国王统治,但对国王顺从的程度仍然未超过自由的程度,因此他们还有战斗力。
排在第三等的是绥约内斯人(Suiones),他们拥有很强的海军,而且他们的船只形式(forma)很特别,两端都是船头(prora),随时可以靠岸。众所周知,船是希腊罗马政治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比喻,最著名的当属柏拉图《理想国》卷六中的船喻,他把船比喻作城邦,把船长比喻成哲人。绥约内斯人的船形式特别,有两个船头——两个船头意味着两个执政者,这岂不是在说罗马双头执政官制度?但是,双头执政非罗马独有,塔西佗难道不会在影射别的国家,譬如斯巴达?这个疑问很快被打消,因为塔西佗马上写到,“绥约内斯人更重视财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一位唯一的至尊所统治着(eoque unus imperitat),这位统治者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他”[1]71。罗马帝国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正是一种军事上的大权(imperium),他的统治方式正是这里的imperitat,而罗马共和国因重视财富而堕落、失去自由,“转变”是帝国的形态,也是从撒路斯特(Sallust)以来罗马史家一直书写的主题。塔西佗关注的是绥约内斯人的自由状况:绥约内斯人比哥托内斯人还要糟糕,哥托内斯人自由的程度起码大于奴役,他们起码拥有兵器。不让国民拥有兵器,甚至组建一支由外邦人组成的卫队,是僭政统治的重要特征,表明僭主与臣民之间互不信任。在这段描写的结尾,塔西佗干脆称这个一人统治者为国王,这与《编年史》的开篇完全一致。克劳斯(C. S. Kraus)发现,《编年史》开篇关注的是政制变迁问题,塔西佗有意让奥古斯都的元首统治(principatum)与王政时期相互呼应[13]。在塔西佗看来,帝国的元首不过是僭主塔尔克维尼乌斯的化身。
塔西佗是公认的描写僭政的专家。不过,尽管人们知道他将罗马帝国视为僭政,但很少人知道罗马帝国在塔西佗心中地位竟如此之低,排在莱茵河诸部落、山内维比人后面,在山外斯维比人当中也排到第三位,在所有山外斯维比人当中,这是倒数第三的位置。难怪塔西佗在《历史》《编年史》当中,对罗马帝国充满了忧伤、愤懑之情,尽管他声称自己既远离愤怒,也远离狂热。如果对自己祖国的评价如此糟糕,也确实只能通过这样的寓意笔法来含沙射影了。
绥约内斯人外面是海,正如前面在日尔曼尼库斯的探索行动中见过,海洋是世界的尽头。塔西佗推测,这个海环绕地面一周,因为海上落日的余晖一直延至日出时才消失,其光辉甚至盖过星辰。有传言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太阳神所驾诸马的形状(formasque)及其头上的光轮。对于这些传言,塔西佗评价说,“就此而言,传言是真的,正如自然一样(illuc usque,et fama vera,tantum natura)”[1]71。自然、真实,在漫长的宗教考察中重新出现,似乎提醒,这段话同时是塔西佗这番考察的界线。毫不奇怪,这里再次出现了“形式”一词:前面的绥约内斯人本来拥有一个双头执政官的“形式”,但却因为贪婪财富而被一个僭主凌驾其上,“形式”遭到严重破坏:《编年史》开篇的王政是一种接近质料的状态。这里的“太阳神所驾诸马的形状”[1]71,塔西佗说要从自然的角度去理解,表明他接下来将要考察这些迷信民族最后的自然认知界线*迷信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丧失自然认知,正如他们的政治状态虽然接近质料,但并非一点形式都没有。。
斯维比海的右岸是伊斯替夷人(Aestii),他们的仪式(ritus)和服装属于斯维比人,但语言接近不列颠语,表明他们相较前面的山外斯维比人更等而下之:因为不列颠臣服于罗马,他们的自由度更低。与此相应,他们的宗教崇拜更加迷信:他们崇拜一位神的母亲(matrem deum),这种迷信的标志(insigne)是一只牝野猪的形象(formas)。也许在塔西佗看来,山内斯维比人虽然崇拜生命的源头(阳性源头或阴性源头),他们的崇拜对象好歹是人格化的神,而伊斯替夷人却将崇拜对象具体化为野猪标志,这就更低了,这种“形式”可能就是斯维比人中最低的一种形式。伊斯替夷人相信这个标志的功效,认为只要带上它,即便在敌人包围之中也不会有危险,这种崇拜简直愚昧不堪。他们的智力低等还表现在工具上:他们通常使用木棒,铁制的兵器很少,这与塔西佗对木的贬低相一致(对比16.3)。最后,塔西佗谈到了伊斯替夷人对琥珀的认识:他们丝毫不曾探究过琥珀的自然(natura)和成因(ratio),只将琥珀搜集成堆,不加塑形(informe)就交给了罗马人;得到了罗马人所给的高额报酬后,反而感到惊异(mirantes)。mirantes的宗教色彩十分强烈,《圣经》里频频出现的“奇迹”便是用这个词来表示。伊斯替夷人对琥珀这样一个简单事物也缺乏认识,他们的认知能力处于最低水平,他们的形式仅比纯质料状态好那么一点点。正如高曼指出的,随着塔西佗将琥珀融化,斯维比人的形式就完全瓦解[8]147-148。
最后一族斯维比人是昔托内斯人(Sitones)。这族人其他方面都与绥约内斯人一样,但比绥约内斯人更糟糕,他们竟受女人的主宰,塔西佗说“他们不独丧失了自由,简直连奴隶也不如”[1]72。
至此,斯维比人就说完了。剩下的部落不再谈政制与仪式,而是重回《日耳曼尼亚志》第一部分的主题:习惯和起源。这里不再出现“政制”与“仪式”的字眼,反而出现习惯:“维内狄人(Veneti)从萨尔马泰人(Sarmatis)那里染上了许多习惯(moribus)”[1]72。
四、余论:通向《编年史》
《日耳曼尼亚志》的结构大体如此。这个结构留给人们最大的疑问是:为何塔西佗要花如此多笔墨去写一些宗教迷信的部落,尤其是为何他把罗马帝国放在山外斯维比人中间,而且是倒数第三位*前面描写莱茵河诸部落时,也过影射过罗马,但那里的影射只是论及某种德性的时候顺带对罗马的警醒,而不是直接给罗马帝国“定位”。罗马帝国的定位是在山外斯维比人这部分。。 山外斯维比人信奉基督教或者类似基督教的宗教,这跟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必须转向《编年史》。笔者注意到,塔西佗描写山外斯维比人时,沿着一步步向外走的线索,越往外、越开阔,也越迷信,而《编年史》的题目——“神化的奥古斯都升天之后的编年史”(Annalium ab excessu divi Augusti libri),其重点词excessu,字面义正好是“向外走”。
[1]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M].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Dorey.T. A. Tacitus[M].London:Routledge,1969:10.
[3] 塔西佗.编年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5] THOMAS.R.F.The Germania as Literary Text[M]∥WOODMAN.A.J.,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acitu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6] 曹为.自由的得与失[J].古典学研究.2011(冬季卷):69-85.
[7] 曾维术.演说术中的哲学与宗教[D].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0-61.
[8] O’Gorman.No place like Rome: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Germania of Tacitus[J].Ramus,1993(22):135-145.
[9] 圣经:利末记[M].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0:195.
[10] 圣经:但以理书[M].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0:1423.
[11] 塔西佗.历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 圣经:使徒行传[M]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北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0:261.
[13] Kraus.C.S.The Tiberian hexad[M]∥WOODMAN.A.J.,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acitu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00-103.
[责任编辑:郑小枚]
Political Philosophy Covered by Ethnography: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and Intention ofGermania
ZENG Wei-shu
(College of Marxism,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801, China)
The traditional view holds thatGermaniafalls into a pandect and a sub-pandec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m two has always been a riddle. Breaking through the hedging-in tradi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paper tentatively concl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ivision of its two parts ar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material and form”. Furthermore, it assumes that the intention ofGermaniai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caused by Christianity.
Tacitus;Germania; Rome; Christianity
2016-05-20
曾维术(1984-),男,广东广州人,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史研究。
B 502.49
A
1004-1710(2016)05-0005-08
——《理想国》卷八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