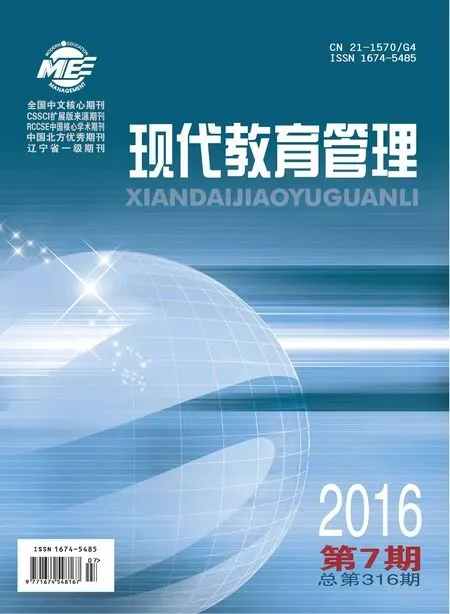国外多校区大学典型管理模式及启示①
刘晓筱
(大连工业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4)
国外多校区大学典型管理模式及启示①
刘晓筱
(大连工业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4)
国外多校区大学兴起较早,有相对较长的多校区办学和管理经验,形成了三种主要管理模式:联邦分权型管理模式、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和模块型管理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标准。借鉴国外经验,我国需坚持因地制宜、因校而异的原则确定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注重学科融合,扩大分校区的办学自主权,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平衡。
国外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学科融合;办学自主权
从世界范围上来看,不同国家多校区大学的形成过程有很大差异,有的是因为学校发展需要自然发展而成的,有的则是外力作用的结果。由于有着不同的国家政体、社会背景、办学条件,国外多校区大学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研究和探讨国外多校区大学典型管理模式能够对我国多校区大学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国外多校区大学的形成与发展
国外多校区大学发展得比较早,二战以后多校区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实现教育公平、促进教育资源均等、弥补教育资源不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多校区大学的形成有独特而深刻的社会背景
多校区大学的形成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广阔的教育发展空间,有的大学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有的大学是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还有的大学是为了实现高等教育办学的国际化而形成了多校区办学。
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些多校区大学,其中伦敦大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伦敦大学最初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两所大学合并而成,合并前的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各自为单独大学,两所高校在办学和管理方面具有很高的自治权,而合并后的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作为伦敦大学的两个下属学院,直接由新成立的理事会负责统一管理校务。[1]
德国二战后为了适应经济领域和社会工作的需要对原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政府和教育界普遍认为综合大学是德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最佳类型。[2]1868年创建的慕尼黑技术大学由位于市中心的主校区、加兴校区和魏恩施蒂芬校区三个校区组成,各校区主要因学科的发展要求进行布局。建筑学、土木工程与测量学、企业经济学、地球科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医学(临床教学中心)等位于主校区;加兴校区有化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机械、物理等学科;魏恩施蒂芬校区则兴办营养学、土地规划与环境科学、农业与园艺、生物科学、林学、景观设计与景观规划、营养学、食品工程等学科。
二战后为了满足急剧膨胀的公民入学需求,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度增加对高等教育和科技的投入,各州也大力发展公立高等教育,这些措施极大地满足了美国公民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1960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The California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诞生出第一个多校区大学系统——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正如加利福尼亚州一位高等教育权威人士说,20世纪60年代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不像别的,主要是想用一种有纪律的方式扩大入学机会,机会、入学、参与是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得以实施的熟合剂”。[3]美国发展多校区大学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利用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州立大学基础,在各地开设新的分校;二是新建一批州立大学。因此,多校区大学系统主要有两种演变:一种是“自我扩展型”,即一个学校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实行扩张,创办新的校区,各校区本身都属同一个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另一种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多校园院校系统”,专指分散在本州、本县或本市的公立高等院校的互不隶属的集合体[4]。
(二)多校区大学已经逐渐成为国外高校的主要办学形态
国外多校区大学发展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顺应学科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而不断壮大和发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多校区大学成为各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形态。当前在两年或四年制公立大学和学院注册就读的学生中,大约有80%的学生就读于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的下属院校[5]。多校区大学主要以联合型和合并型为主。联合型是由多所学院或多个分校在具有相同大学名称前缀下运行,如美国特有的“多校区大学系统”和英国的学院制。学院制是将多个独立运行的学院统一在一个大学名目下,如伦敦大学。多校区大学系统是将多所大学置于一个地方政府所属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下进行管理,形成所谓的多校区系统,其中的大学称为旗下的分校,各个分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多校区大学系统只是一个政策协调者、公共事务提供者以及政府与各个分校之间的代理者。合并型主要是一些强校为了扩展实力,如增加学科、增大办学规模等需要,合并其他学校,日本的许多多校区大学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澳大利亚的多校园大学形成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将一些高校合并完成的。20世纪80、90年代,澳大利亚通过对院校的合并而形成多校区大学。通过院校合并,政府将16所大学与60所院校逐步合并为36所大学。创建于1850年的澳洲天主教大学通过逐步合并多所学院而成多校区大学,该校在布里斯班市、悉尼市、堪培拉市、巴拉瑞特市、墨尔本市等设有8个不同的校区。格里菲斯大学也是多校区大学,是联邦政府投资承建的高等学府,也是通过逐步合并多所学院而成的,有六个校区,包括Nathan,Mount Gravatt、黄金海岸校区、劳根、昆士兰艺术学校和昆士兰音乐学校[6]。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是法国多校区办学的典型代表。1968年由于学生抗议课程落伍及教育资源不足,要求学术自由和校园民主化,法国政府便对巴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由13所大学共同组成的巴黎大学。这13所大学各自独立没有隶属关系,数字只是一个序号,并不代表它们的质量和排名。这些学校在学科设置上都具有多科性的特点,第1、2、4、8、9、10校区主要是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而第5、6、7、11、12、13校区不仅有人文学科,还有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其中巴黎第11、12、13大学还设有工科。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多校区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经济社会和广大民众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科研和公共服务创造了机会,促进了大学多样化发展和大学与大学间的合作,提升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大学正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
二、国外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的主要类型
管理模式是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内外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直观、简要的表述,不同的管理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标准。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国对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的选择也不相同。即使同一国家,不同大学对多校区办学模式的选择也会不同,比如美国的加州大学采取的是联邦分权型管理模式,而康奈尔大学采取的是模块型管理模式。无论选择哪种管理模式,各国都希望借此实现高等教育管理的高效化和规范化,优化学校权利结构,最终实现等教育质量、规模、效益协调发展。
(一)联邦分权型管理模式
联邦分权型多校区管理模式主要以英美国家的高校为主,它又被称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是国外多校区办学中为了解决由于校区组织规模扩建及多样化办学的需求而形成的多校区管理模式[7]。它依照学区的功能来划分校区,每个校区依照自己的功能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事业部,学校对各校区实行统一管理和行政规划,各校区基本上具备独立办学的条件,这种管理模式比较适合校区之间距离相对较远,学科功能差异大的多校区大学,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纽约州州立大学系统。
联邦分权型的管理模式主要由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在大学中设立大学董事会,大学系统的校长由董事会通过选举任命、选拔校长,校长要对各个分校区实行统一的规划管理;二是大学董事要负责制定整个大学宏观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制定要符合各个校区的发展要求,并保证该政策及计划能在各个校区顺利实施,但不会对各分校区的具体事务进行干涉;三是在财政方面各校区完全独立,由整个大学统一对各校区进行一次性拨款,对各校区财政支出及使用权不给予干涉;四是为保证大学系统质量与效益平衡发展,大学系统还要对各校区提供能满足公共利益的服务,如法律支持,数据库,采购教学用具等。通过上述表述我们发现,联邦分权型的管理模式既保证了高层宏观政策调控的有序进行,又调动了各个学院主动配合的积极性,大学系统对各学区的财政、学术和科研上都不进行干涉,只行使监督权。采用联邦分权型的管理模式,既能保证各个学院组织结构的稳定,又能保证各学院的教学质量。分权型管理还能够较好地发挥大学系统对各个分校区的领导和指引作用,通过政策的引导来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在大学系统的帮助下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和学术环境,有利于促进学术氛围和科研水平的发展,既保证了高层的决策权,又调动了各校区的积极性。
美国加州大学全校设立董事会,是学校最高的权力机关,根据各分校的情况,从整体上把握全局,制定加州大学系统的战略决策。学校董事会选举校长,主要负责全校的行政管理、学术管理等。分校有自己的职能部门,校长主要通过二级职能部门对分校进行管理,在分校中还设有自己的院系,二者相互制约,形成双轨制管理体制[8]。加州大学的组织机构包括总校(学校董事会)、分校(校长、校务委员会等)、学院和系所四层架构,大学的管理机构是加州大学董事会,董事会主要负责处理整个大学系统的行政规划、法律事务、财政、资金分配等问题,除此之外还对各个校区的学术、教学等专业领域享有问询权。加州大学系统一共有10个分校,各分校区都有自己的校长以及校务委员会,各分校的校长对自己学校的内部事务具有自治权,尤其是在人员招聘、专业发展、财政支配、采购及开展学术会议方面。每个分校下面又设有不同的院、系,配合各个分校进行管理,这样就做到了行政权与学术权,统规学校董事会负责,各分校作为事业部,辅助总校进行管理[9]。
在分权管理模式下,分校区的权力得到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管理权力分散,会弱化学校的统一管理,再加上各校区重复设置管理机构,容易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并且资源共享不充分,机构设置庞大,也会造成运行成本高,办学效率低下等弊端,由于各个校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因此考虑问题往往不能从学校的整体出发,忽视整个学校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校区间的协调,不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二)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
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是指大学对自己的各个校区所担负的主要功能和责任进行全局统一的设计和安排。功能定位型管理是指以校长办公室为首的校级管理机构集中在某一校区内,各个校区只设置一个校区管理办公室,它打破了各个校区的管理体系,实行一个校本部、一套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的运行机制。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通过总校区校长向各分校区派常驻机构及人员,代理总校行使管理职能。这种管理模式主要适合校区之间距离相对较近,规模不大、分校区层级相近、综合性表较强的大学,如日本东京大学、美国的华盛顿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东京大学一共有三个校区,本乡校区是东京大学的主校区,主要是研究生教学、本科高年级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基地。驹场校区是东京大学的分校区,主要是以基础教学为主,承担中、低年级本科生的基础课教学任务。六本木校区是另一个分校区,主要是以应用型科研为主的校区,主要是对研究生进行培养,并承担重大的科研项目,但不进行教学。三个校区分工不同,但各具特色,由总校引领,互相联系,互相合作,在学校管理下有序运行。在这种方式下形成的管理模式一般经过扩建后大学办学主体不变。2004年起,日本迎来了新一轮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国立大学的法人代表由校长担任,旨在为一个庞大的综合大学设定一个向社会负责的法人,同时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管理、约束国立大学,那就是每年国立大学法人要向政府提出一个中期报告,计划下一年办学的各项目标。政府通过各个大学中期目标的达成程度给国立大学分发预算。如此一来,国立大学法人校长的选任方式也随之改变,国立大学法人的校长肩负着经济上的重大责任,其在校内的权力随之也更大。法人化以后,原本一刀切的预算在各个国立大学之间产生了一些竞争的空间,稳坐学术榜首位的东京大学反而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资源,这与行政中枢“校长室”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学校的行政管理系统为:总长一人,不设副职,通过总长室两名特别助理与事务局、学生部、图书馆、各学部、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进行协调。[10]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共有4个校区,最古老的校区是霍姆伍德校区,占地面积约140英亩。其他3个校区分别是东巴尔的摩校区、巴尔的摩市校区、华盛顿特区校区。近些年来,霍普金斯大学也把触角伸向了海外,在意大利、新加坡以及中国都有校区。霍普金斯大学各分校区的决策权掌握在总校手中,各校区的独立性相对较小。与联邦分权型的管理模式不同的是,学校的高层管理机构对各分校的财政、学术、科研机构都有管理权,学院院长和教授在管理中的作用非常有限。每个学院都有一个教授管理团体,有些称为教授理事会(Faculty Senate),有些称为教授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这些委员会就教师聘用、晋升提出建议,决定开设哪些课程。而所有其他行政决策都由校长来进行管理[11]。在其他一些大学,教授会甚至要决定教室什么时候关灯,使用什么样的计算机系统,财务支付系统等事情。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主要精力是做研究,他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行政事务上,他们更关心怎样做出成就以获得晋升。
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可以将总校区制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到分校中去,形成统一的规章制度,有利于学校的统一管理,相对于联邦分权型若干校区、若干管理机构而造成的管理效率低、管理跨度大、成本高的现象,更有利于大学多校区的管理。但是由于在集权管理模式下,各校区虽然相互独立,但是难以形成校区之间良性的竞争机制,不能形成互相竞争共同提高的办学实体,这是功能定位型管理模式的弊端。
(三)模块型管理模式
模块型又称为“综合管理模式”,它结合了分权型与集权型的优势特点,适用于有多种类型、多个校区和多种层次的大学,强调学术服务、人力资源和配套设施由分校区具体需要自主管理,而整个大学系统采用集权式管理[12],如英国伦敦大学、澳大利亚新摩纳西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
伦敦大学与学院的关系结构为大学机构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的联合模式:其一,在传统大学之外开辟获得大学学位的另一条道路,从而使新兴学科、专业计划、和专业技术学院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此类差异性归功于文化下移的时代需求,因此,伦敦大学的校外考试计划和开放教育制度为向社会、民间推广科学技术作出重要贡献。其二,大学董事会与大学理事会构成二院制决策制度,相比传统大学伦敦大学董事会掌握更多管理大学实权,学术事务由大学理事会及其所属的众多学术委员会管理,董事会则掌握财政和资源的管理权[13]。其三,大学与各分校区的行政关系更为松散,表现为松散联合的形式,大学主考试,学院主教学和科研,学院自治在某种意义上是授权模式的核心。
美国康乃尔大学包括伊萨卡校区、纽约校区和散布在全州各地的教学与研究基地。康乃尔大学从成立之初就兼具公立和私立的双重性质。在管理上体现公私合并、一校多制的特点。康乃尔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董事会由40多人组成。康乃尔大学还有一个经董事会推荐、由400多名社会知名人士和著名教授组成的议事会,帮助学校制定各种重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或对学校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校长是大学的最高行政管理者,另外还有16名校级行政管理者分管教学、科研、规划、财务、法律、投资、大学关系、校园事务、信息技术、学术方案等事宜。[14]
在模块型的管理模式下,院校自主权显然是贯穿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归类与定位分析的一条主线。其内涵构成涉及所有学术事务中各项人、财、物管理的自主管理权限。其中教师权力在大学管理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形式和功能的演变构成了院校自主权的重要体现:一是一流大学越来越被政府和公众要求形成引领先进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动力源泉;二是由大学自己管理内务,意味着学术管理制度中去行政化成为必需之举。此外,现代大学管理在持续走向有限的、渐进的和多元整合的自主管理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校构成现代大学管理成败的关键。采用模块型的管理方式更好的结合了分权型和集权型的优势特点,扬长避短,即加强了学校资源的统一调控,又促进对各校区之间的积极性。但是模块型管理模式也有一些弊端:一是资源的重复建设、交通和通信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都相对提高了管理成本;二是由于各个校区管理委员会缺乏对人财物资源的调控权和校区管理委员会与驻区各个单位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协调的难度较大,也降低了管理的效率。
三、对我国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启示
多校区大学的发展满足了来自不同地理位置的学习者和受教育者的需求,为大学间校际合作和办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示范。
(一)坚持因地制宜、因校而异的原则确定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
国外多校区大学管理模式都不是单一的集权型或者分权型,往往是将集权型和分权型办学模式结合在一起,这是单一校区办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各校区在大学主校的领导下,统一办学,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各学院发展各自不同的学科优势,促进各校区的专业化水平,各校区均衡发展实行分区管理,总校区总领全局。而在我国,多校区办学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合并而成,主要是以块状管理模式和条状管理模式为主,形成庞大的多校区办学系统,但是由于缺乏行政上的配合以及学科设置重复造成多校区办学的效率低下。单一块状的集权管理模式也使分校失去的自身办学特色,重复办学也加剧了办学的成本。美国和英国多校区大学强强联合,旨在打造主校区的品牌优势,主校区与分校区共同成长,分校区注重效率,总校区注重公平,这样做不仅体现了分校的自身特点,还实现了学校整体的品牌效益。不仅注重主校区的宏观管理,更注重各分校区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多校区大学管理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搞好多校区大学管理最重要的基点,即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因此,我国多校区大学管理中应将分校和总校看成一个有效循环的整体,减少管理上的漏洞。主校区的作用在于激发分校区的潜力,分校区则以自己的发展促进总校区共同发展。
(二)注重学科融合,扩大分校区的办学自主权
国外多校区管理过程中,每个分校区都具有很高的自治权。总校区要依据学校的自身发展和政府对人才的需求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在分校区的专业设置方面也是权衡学科结构与学生需求之后有针对性地开设,不会因为教学成本高而降低对专业设置的要求。各分校区是一个相互独立的个体,在专业设置方面也各具特色,但它们也设置交叉学科,或者网络课程,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消除隔离在已有学科范围内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促进学科的纵深发展[15]。虽然校区在地理空间上不相连,但是通过网络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还是把各校区的学生和教师联系到了一起,为综合学习、学科融合创造了条件。多校区管理模式改革是每个大学寻求发展与扩张、竞争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上的期待和需求,丰富与拓展办学特色,成为必然现实选择。[16]
(三)根据多校区大学自身实际,把握集权与分权的动态平衡
在大学多校区办学过程中,我们要首先明确各校区的功能定位,在明确各校区的功能定位后,确定各校区在整个学校系统中的作用和位置,在坚持促进整个学校系统发展的前提下,用发展的眼光,理顺学校、院、系之间的关系,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采用集权型管理模式,有利于协调各部门之间的活动,便于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决策的针对性,但是集权模式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这就限制了中下级管理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机构设置重复,延长了指令的传达,使学校组织缺乏灵活性。采用分权模式就避免了这一问题,管理层减少,管理权下放,信息沟通方便,分校区的自治权加强,有利于组织内部保持动态平衡,但是由于各校区的自主性加强,外部的控制力减弱,各校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比较难进行。我国也有许多类似加州大学这一类的庞大的多校区办学体系,但是由于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分校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整个体系就是一个联邦,大学有高度的自治权,实行分层管理。
[1]肖朗,袁传明.伦敦大学建立与近代英国高等教育改革——以第一特许状为考察中心[J].现代大学教育,2013,(6):32-39.
[2]邓志伟.战后德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及其变化[J].外国教育资料,1993,(6):76-77.
[3]Callan P M.Time for Dicision:California's Legacy and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A]. Goldstein B.California's Master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San Francisco: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996:86.
[4]Gaither HG.The Multicampus System:Perspectives on Practice and Prospects[M].Sterling:Stylus Publishing,1999:152-153.
[5][美]杰拉德·盖泽尔.美国多校园大学系统:实践与前景[M].沈红,曹赛先,陈运超,赵欣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0.
[6]James,R.H..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Universities[R].COE Publication Series,2004:52-77.
[7]KossamDhliwayo.The Internal Customers Perceptions of AMultiCampus University System In Zimbabwe.A Case of Great Zimbabwe Univers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Technology Research,2014,(2):325.
[8]Clark Kerr,M.L.Gade.The Guardians:Boards of Trustees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 Washington,DC: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1989:123-125.
[9]M.Ardis,E.Hole,J.Manfredonia.Creating a Marketplace for Multidisciplinary Multi-university System Engineering Capstone Projects[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3,16(1):1036-1042.
[10]许为民,张国昌,沈波,等.学术与行政:中外大学治理结构案例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09.
[11][美]威廉·布罗迪.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与管理[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2):5.
[12]Harman,G.,Harman,K..Institutional Mergers in Higher Education: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J].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2003,9(1):29-44.
[13]王承绪.伦敦大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30.
[14]Cornell University.Sustainable Campus[EB/ OL].http://www.Sustainable-campus.cornell.edu/land.
[15]钟恩升,华菊翠,葛继平.自主发展型各校区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J].现代教育管理,2010,(12):50.
[16]华菊翠,葛继平.中国各校区大学与差异化发展[J].现代教育管理,2013,(5):40.
(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于翔)
Typical Management Mode of Foreign Multi-campus Universit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LIU Xiaoxiao
(Dal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116034)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ulti-campus universities has a long history,and therefore there is relatively long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Multi-campus universities have three major management modes: federal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mode and module management mode.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ls embody different values and standards.Learning from foreign experience,we should follow the due conditions with flexibility to select management mode of multi-campus universities,focus on academic integration,expand the scope of branch campus autonomy,and grasp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foreign multi-campus universities;management mode;academic integration;autonomy
G649.21
A
1674-5485(2016)07-0046-06
①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高校研究生课程国际化现状评价研究”(DIA150298)。
刘晓筱(1983-),女,辽宁沈阳人,大连工业大学助教,主要从事高校艺术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