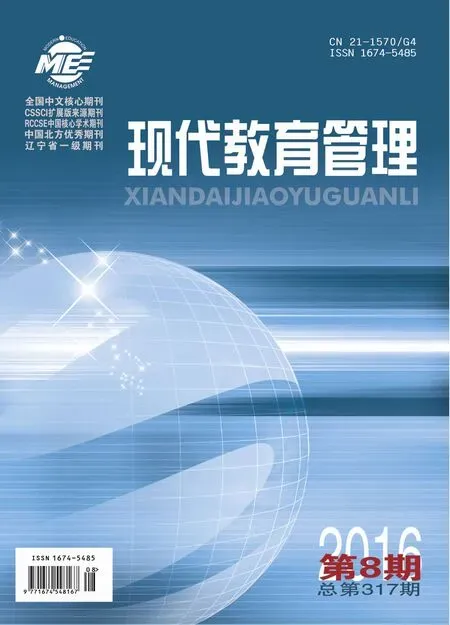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
张晋,刘云艳
(1.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苏州215131;2.西南大学,重庆400715)
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
张晋1,刘云艳2
(1.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苏州215131;2.西南大学,重庆400715)
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强调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提升学前教育质量、解决社会供需矛盾、为国家创造财富是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依据。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面临着以下问题:政府职责失范,责权配置模糊;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地域间、园际间差距显著;公民办园结构失衡,学前教育属性摇摆;师资队伍结构失范,核心素养薄弱。为此,必须从理念维度、目标维度、制度维度与结构维度构建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保障机制。
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保障机制
学前教育发展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关涉到质的飞跃问题。近些年,为了完成“保基本、广覆盖”任务,我国学前教育行为往往以扩大规模为主,相关评价亦主要以投入金额、园数、入园率、师幼比等量化指标为参照。如2011年以来中央财政已投入700多亿元,2014年新增园舍13784343个,总计达229985220个,[1]到2016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5%左右。[2]随着量化指标的激增,“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以初步缓解,转而“入园差”难题逐渐映入公众视野,频发的各类教育、安全、卫生事故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新要求。鉴于此,本研究以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为起点,从内涵式发展视角出发,分析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现实依据、阻碍因素与保障机制。
一、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涵
“内涵”反映着事物的本质属性,在逻辑学上相对于“外延”而言。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3]因此,相对于“外延式发展”的数量积累、规模扩大与空间扩展,“内涵式发展”从本质上强调促进事物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与可持续发展。“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作为逻辑学上“内涵——外延”逻辑范畴的衍生,是描述事物两种不同发展的路径,二者不存在性质上的区别,重点在于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契合。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两种发展方式往往是共存的,两者的有机融合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关键。《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2014-2016年学前教育的重点任务是扩大总量、调整结构、健全机制与提升质量,[4]其中,调整结构、健全机制与提升质量是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集中体现。可见,促进学前教育由增加数量、扩大规模为核心的外延式发展向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实现规模数量与结构、质量、效益和谐发展,成为学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二、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现实依据
内涵式发展是学前教育外延式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提升质量、解决社会矛盾以及为国家构筑财富的迫切需要。
(一)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自身需要
质量是全民教育的核心所在。[5]优质的保教活动需要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作为基础。然而全民教育全球监测发现,“正在致力于保障所有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众多国家,因偏重教育机会而忽视了质量问题”。[6]近些年,随着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学前教育发展规模、园数、入园率等量化数据不断刷新,如2014年全国幼儿园园数总计达209881所,较2010年的150420所,增加了39.53%;2014年全国在园幼儿数为40507145人,较2010年的29766695人,[7]增加了36.08%;在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之后,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67.5%,到2016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预计达到75%左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以初步缓解。然而,大数据的背后却是部分地区以降低学前教育机构准入标准,甚至频发各类教育、安全、卫生事故等深层次问题为代价,“入园差”难题日益引起公众关注,成为“办人民满意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推进机会供给过程中,提升学前教育质量,实现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解决社会供需矛盾的现实需要
资源的高使用价值是供需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优质的学前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将对儿童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伴随着经济、社会观念的发展与更新,公众学前教育需求尤其是优质学前教育需求激增与优质学前教育资源有限性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幼儿园数量为209881所,其中,民办园数量达到139282所,[8]占据幼儿园总数的66.36%。然由于受到传统社会观念与现实因素影响,“公办园=优质园”、“民办园=低质园”的认识在多数家长观念中已演变成一种刻板印象。这就意味着半数以上幼儿园保教质量无法满足家长需要。在此背景下,“上好园”、“择园热”、“公办园热”愈演愈烈,部分家长更是发出“上个公办园比考大学还难”的感慨,可见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家长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期盼。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已变成公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解决“上好园”问题,扭转“民办园=低质园”局面,不仅是保障起点公平的需要,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三)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战略需要
人是社会、国家的核心。国际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间的竞争,而发展学前教育则是提升个体素质、适应国际竞争的战略需要。脑科学、心理学研究显示,幼儿期是各类敏感期形成的重要时期,幼儿期的健康发展将对儿童的未来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反之,幼儿期的负面影响将会对幼儿产生无法挽回的后果。此外,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是“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阻断代际贫困传递、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詹姆斯·汉克曼证实的那样,学前教育投资回报率高于其他阶段的教育投资。因此,投资学前教育,提升学前教育质量,不仅具有强烈的个体价值,更是投资未来、为国家创造财富的需要。
三、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阻碍因素
由于受传统量的发展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学前教育在转向内涵式发展道路上面临着诸多阻碍。
(一)政府职责失范,责权配置模糊
1.各级政府职责失范,政府主导力孱弱
政府主导是世界各国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学前教育的普遍经验。在我国,由于受到传统历史因素的影响,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作用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学前教育发展责任由政府转嫁至市场,2003年《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在此政策导向下,学前教育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力量为主体的发展格局。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明确政府责任,建立政府主导的办园体制”。同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至此,在政策文本层面,政府责任得到初步的明确与规定。然而多数规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缺乏实践力。具体而言,一是缺乏针对政府主导的硬法规定,多数以“意见”、“建议”、“主张”的口吻进行规定,具体责任指向不明,并且缺乏相关的问责制度。二是各级政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一项研究显示,2010-2012年各级政府(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学前教育支出占公共教育(主要是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53%、1.88%与2.98%,其中,中央政府投入占各级政府投入的比重分别为0.78%、0.30%与0.33%。[9]可见,政府主导尚停留在“文本层面”,缺乏实践层面中实实在在的践行力。
2.政府部门间责权配置模糊,执行力不足
学前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教育系统,其发展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支持,更离不开社会各子系统的协作。《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幼儿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并对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财政部门、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编制部门、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妇联组织的相关职责进行初步规定。但由于对各部门的规定缺乏细化与针对性,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各部门频发责任定位不清、多头管理、批管分离等现象。如有研究指出,城市街道幼儿园在行政上由街道办事处管理,业务上由区托幼办指导,在人事工作的衔接上由区妇联主管。当幼儿园经费陷入困境时,谁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10]再如,由于缺乏针对幼儿园审批注册的详细规定,民办园既可以在教育部门注册,也可以在工商部门、民政部门等多部门注册,出现非专业人员管理审批幼儿园的现象,最终导致“非达标”幼儿园层出不穷,形成错综复杂的管理局面,影响学前教育健康发展。
(二)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地域间、园际间差距显著
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观念的差异,使得不同区域儿童个体在受教育起点阶段上存在着明显的非自我选择且无法避免的“人格资源”或(Personal Resources)“原生运气”(Brute Luck)差异,这种不公的“原生运气”使得个体在对“资源”或“基本善”的“转化率”上存在重大差异,[11]从而导致不良“原生运气”的代际传递。学前教育公平作为保障教育起点公平、甚至是人生起点公平的关键环节,理应成为解决“原生运气”不公的有力手段。
然而,在实践中,学前教育并未真正担负起补偿起点不公的重任,不同地区间、城乡间、园际间学前教育发展存在着显著差异,集中体现为经济投入差异。如2003-2007年,张家港市政府为学前教育共投入了2亿4100多万元,[12]而同为县级市的山东利津县每年投入的经费仅为50万元。[13]2011-2013年中央财政学前教育项目投入500亿元,实现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然而,此前中央政府针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几乎为零,各地政府较多地将有限的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到城市幼儿园的发展中,而且是数量极少的由政府或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14]相反,缺乏稳定充足发展资金、师资流失严重、保教质量偏低的农村幼儿园却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经费补助,从而形成城乡间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实现。宁波市2006年教育部门、机关及其他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数仅占全市适龄儿童总数29.3%,但全市当年90%的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到了此三类幼儿园,其生均享有政府财政经费分别为3417.8元、3161.8元、1856.7元;占入园幼儿总数70.7%的各类集体办、民办幼儿园生均享有政府财政经费仅为124.8元。[15]可见,政府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间的分配极不均衡,极大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性。
(三)公民办园结构失衡,学前教育属性摇摆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错误的政策导向是公民办园数量结构失衡的主要缘由。2003年是公民办园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转折点。2003年之前,在我国四种不同类型幼儿园(教育部门办、集体办、民办与其他部门办)中,以教育部门办园与集体办园为主。2003年之后,由于受到“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政策导向的影响,民办园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在2003年里,民办园数量达到55536所,比教育部门办与集体办幼儿园总数多出3762所,此后,民办园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截止2014年民办园数量占据幼儿园总数高达66.36%,民办园成为幼儿教育的绝对主体。民办园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源有限的问题,为保障学前教育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然而,由于民办园特殊的办园体制,使得民办园的办学属性始终徘徊于“教育性——经济性”之间。一方面,《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举办幼儿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16]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民办园运转遵循市场规律,自负盈亏,以赚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这就导致以民办园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属性摇摆不定,往往游走于“经济人”与“教育人”、“社会人”之间,影响学前教育公益性、教育性的实现,严重制约其内涵式发展。
(四)师资队伍结构失范,核心素养薄弱
“在任何复杂程度和组织水平的社会系统中,人都是主要的要素。”[17]师资队伍作为学前教育发展中的“软件系统”,是促进学前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主动力。然而,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发展主要存在队伍结构失范与专业核心素养薄弱的问题。
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结构失范主要体现为性别结构失范、学历结构失范与职称结构失范。性别多样性团队通过开放性合作、观点整合,促进产生新的思维方式,避免思维趋同,提升创造力,[18]从而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团队绩效。[19]以此类推,学前教育作为一项团队事业,同样需要性别多样化的队伍。然而,在实践中,学前教育师资队伍性别结构严重失衡。数据显示,2014年,学前教育女教职工占教职工总数比例达到91.69%,其中,女性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人数比例达到97.94%,[20]可见男幼师的极度稀缺性。学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师资保教质量水平。当前,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仍主要以专科及以下学历为主。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2080317人,其中,专科及以下学历人数为1646255人,[21]占总人数比例高达79.13%。提升幼儿园教师学历层次,促进幼儿园教师终身发展,是保障学前教育“软件系统不软”的关键环节。职称体现着教师专业发展方向、内容与需求,对教师专业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当前,幼儿园专任教师职称评审远远落后于现实需要。具体而言,一是缺乏独立专业的幼儿园专任教师职称评审体系,教师评审主要参考中小学职称体系。二是未评职称人数比例较大,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014年,幼儿园未评职称教师为1480369人,[22]占总人数比例高达71.16%,这一比例比2001年的47.97%[23]增加了23.19个百分点。可见,职称在学前教育发展中并未真正发挥出专业引领与发展导向作用,幼儿园教师更多以自发欠理性发展为主,难以保障其专业性。
“人”是教师与幼儿的类属性,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因此,“人”是教育的核心,“培养什么样的人”则成为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的根本问题。我国学前教育师资主要以专科人才为主,其培养以实践为导向。然而由于对实践导向的片面理解,在落实中,往往简单地将实践等同于机械的“做”或重复的“操作”,使得专科人才培养过于强调技能训练与职业教育,更多地将师资培养定位为“技能之师”、“示范之师”而忽视了“人格之师”、“师范之师”,这一培养模式最终导致“师范性”与“职业性”、“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二元背离以及对幼儿教师核心素养——专业理念与师德理解内化上的薄弱,严重制约师资队伍全面健康发展。
四、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保障机制
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规划,基于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理念维度、目标维度、制度维度与结构维度构建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保障机制。
(一)理念维度:落实公平、优质、高效理念
公平、优质、高效理念是学前教育在不断发展、深化变革中凝聚而成的。这既是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对学前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既是学前教育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要求,也是实现教育由粗放式发展走向集约式发展的重要环节。第一,落实落细学前教育公平。公平是学前教育发展的首要指导思想,并且在“文本层面”与“话语层面”得到高度的重视。然而,在实践中,公平理念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因此,丰富学前教育资源,优先将学前教育资源向处境不利地区、幼儿园倾斜,聚焦“雪中送炭”,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首要价值追求。第二,创造优质的学前教育。伴随着学前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家庭与国家对学前教育不仅仅是量的要求,更期盼着更多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人是国家间竞争的根本要素,而“只有依赖教育,人才能成为人”,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优质学前教育是“使人成为人”以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一环。第三,提升学前教育发展效率。高效的学前教育不仅体现为规模、数量的日益扩大,更表现为质量的提升与内涵的发展。近些年,我国学前教育规模、数量正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数量激增的背后却是对质量关照的不足。促进学前教育由量的高效向质的高效转型成为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理念向导。
(二)目标维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质的师资队伍是高质量学前教育的核心。近几年,我国学前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师资队伍急剧扩大,在量的激增过程中往往缺乏对质的有力监测与保障。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确保学前教育队伍高质量成为推进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目标。首先,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男性幼师数量严重不足是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发展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政策引导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成功经验。例如,江苏省通过“经费+就业”双重保障积极扩大男幼师招生。省财政出资承担男幼师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生活补助;此外,获取毕业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的免费男幼师,往往到生源所在省辖市范围内公办园任教并纳入编制系统。这一举措有力扩大了男幼师数量。终身学习是教师适应时代需要与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针对学前教育师资学历整体偏低的问题,一方面,要厘清“实践导向”的真正内涵,坚持以“人师”培养为主,以“经师”培养为辅;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继续学习,充分利用“互联网+”、慕课等,开展具有个性化、主动性的学习,变革消极“输血”学习为积极“造血”学习,将学习权真正还给学习者。其次,建立与优化教师资格认证与评价体系。幼儿教师与小学教师所面临的教育目标与任务存在显著差异,简单化地参考小学职称评价体系,不仅无法体现出幼儿教师的独特性,而且极易导致幼儿教师资格认证与评价的“小学化”。因此,建立独立专业的学前教师资格认证与评价体系迫在眉睫。此外,伴随着幼儿教师身份由传授者、照看者向观察者、支持者与合作者的转变,幼儿教师评价由依据教学活动单一评价向依据生活活动、游戏活动、教学活动等综合评价转变成为必然,评价时空将不断泛化,评价活动逐步走向全面化与科学化。
(三)制度维度:优化学前教育管理制度
制度均衡是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间的平衡状态,是实现制度帕累托最优的必备条件。与此对应的是制度非均衡,主要分为制度供给过剩与制度供给不足。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制度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真空、制度低效、制度无效乃至制度负效等现象普遍持久存在,优化学前教育制度建设迫在眉睫。[24]第一,建立学前教育专项财政制度,优化财政资金分配。伴随着民办园逐步占据幼儿园的半壁江山,家庭成为学前机构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悬殊的家庭收入使得不同群体所接受的学前教育质量层次不齐,形成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鉴于此,一方面,要建立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财政投入制度,尤其需加强中央、省和地市三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公共性与稳定性。第二,落实各级政府权责,践行联席会议制度。学前教育是一项需要多级政府参与、跨部门治理的教育事务。政府主导是世界各国发展学前教育的重要经验。相比而言,我国“政府主导”尚停留在“文本层面”,缺乏针对各级政府具体权责的规定与落实,因此,明晰与落实各级政府权责成为实践政府主导的前提。政府部门内,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而且离不开财政部门、卫生部门、妇联、工商部门等部门的协同合作。应建立起以教育部门为核心、其他各部门为支撑的联席会议制度,从而达到强化部门协作、提升合作效率的目的。
(四)结构维度:平衡幼儿园属性结构
教育性与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基本属性,亦是学前教育发展必须坚守的根本底线。然而,伴随着民办园数量的激增与超越,经济性逐步成为学前教育的主导属性,教育性与公益性日益受到侵蚀。鉴于此,首先,要加大财政投资,兴建公办园,扭转公民办园数量结构失衡的局面,另外,加大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调控学前教育收费,从而保障学前教育非营利性特点。其次,构建参与主体多元、奖惩并重、以评促改的学前教育质量监控保障系统。监控主体上不仅要发挥幼儿园管理者与教师等内部监控者的作用,而且迫切需要建立独立专业的第三方监控体系,保障质量监控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将监控质量结果与额外支持资金、荣誉、等级考核、教育工作者待遇、办园资质等挂钩,通过这种“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促使幼儿园质量提升,从而达到保障学前教育教育性的目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20项惠民政策织密教育扶贫网[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 xwfbh_2015n/xwfb_20151015_02/151015_mtbd02/2015 10/t20151016_213788.html,2015-10-16/2015-11-25.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3327/201411/t2014110 5_17831 8.html,2014-11-03/2015-10-11.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2.
[5]冯晓霞,周兢.构筑国家财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幼儿保育和教育大会简介[J].学前教育研究,2011,(1):23.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全民教育,提高质量势在必行(摘要)[R].2005:18.
[7][8][20][21][2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4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http://www.moe.gov. 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4/,2015-06-03/2015-10-10.
[9]郭晟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3):101.
[10]周红.实行归口管理确立幼教改革的制高点[J].学前教育研究,1999,(2):32.
[11][印]阿玛蒂亚·森引.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8-263.
[12]张家港市教育局.强化责任激活机制,促进幼儿教育健康和谐发展[J].学前教育研究,2007,(1):13.
[13][14]王海英.学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表现、产生机制及其解决的可能途径[J].学前教育研究,2011,(8):11.
[15]陈文辉.宁波市教育局优秀调研报告集——宁波学前教育调研报告(内部资料)[R].2007.
[16]中国政府网.幼儿园工作规程.[EB/OL].http://www.gov.cn/bumenfuwu/2012-11/15/content_26004 25.htm,1996-03-09/2015-11-05.
[17][苏]B.F.阿法纳西耶夫.社会:系统性、认识与管理[M].张凡琪,韩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6.
[18]Amabile,T.M.,Conti,R.,Coon,H.,Lazenby,J.,Herron,M.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6,39:1154-1184.
[19]Stapel,D.A.,Koomen,W.,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me[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5,88:1029-1038.
[23]刘占兰.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201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51.
[24]刘云艳,张晋.学前教育发展中不同主体间利益博弈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5,(9):22.
(责任编辑:赵晓梅;责任校对:徐治中)
The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ZHANG Jin1,LIU Yunyan2
(1.Suzhou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ollege,Suzhou Jiangsu 215131;2.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mphasizes on improving quality,structural optimization,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society,building wealth for countries are the realistic basises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At present,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following problems:the nonstandar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ambiguous assignmen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 and existing significant gap among different areas or kindergartens;unbalanced structure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and non-public kindergartens,swinging of the nature of preschool education;nonstandard structure of teachers,weakness of the teachers' core literacy.Giving this,this research builds security mechanism for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from the idea dimension,target dimension,institutional dimension and structure dimension.
preschool education;connotative development;security mechanism
G610
A
1674-5485(2016)08-0038-06
张晋(1988-),男,安徽滁州人,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管理研究;刘云艳(1962-),女,重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师与儿童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