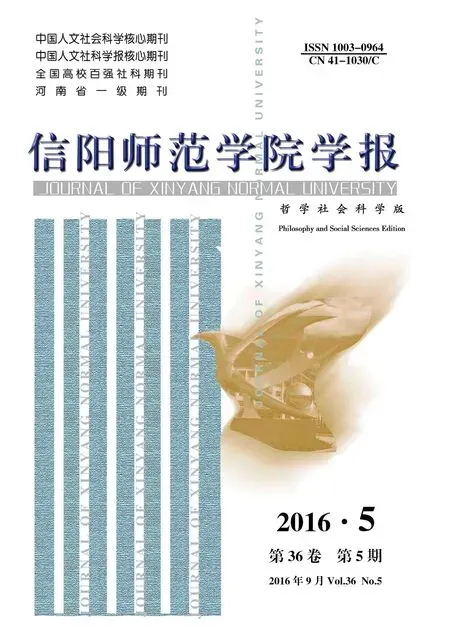“黄泥地”归去来
——论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黄泥地》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河南当代文学研究·
“黄泥地”归去来
——论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黄泥地》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黄泥地》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各色人等相互纠缠构陷的故事。小说对乡土中国的生存情状进行了隐喻式的书写,在描述其相对封闭性、稳定性的同时,又以现代乡绅房国春形象为载体书写了乡土中国的疏离性、瓦解性力量。小说直面现实、叙述细密,同时带有浓郁的挽歌气息,写作旨趣也倾向于“为乡土中国保存一个肉身”。
《黄泥地》;隐喻式书写;现代乡绅;疏离性力量;挽歌气息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新作《黄泥地》叙述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普通村庄的各色人等所生发的寻常故事。故事虽然寻常,其间蕴含的来自生活深处的乡村存在状况以及作家牵动肝肠的省思却不同凡俗,这使得《黄泥地》在乡土书写热度不减、佳作迭出的当今文坛,具有深入讨论的价值。
一、作为乡土中国隐喻的“黄泥地”
书名“黄泥地”,很明显具有隐喻的意味,而且这一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时对中国文化反思的浪潮中所经常使用的“黄土地”等意象群,也自然地让读者接续起80年代甚至是鲁迅以来的现代文化传统中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在小说中,作者花费许多笔墨对“黄泥地”的特性做了隐喻性的描写,特别是小说对村民们看客心理的透视及呈现直追鲁迅,令人拍案。作家刘庆邦在接受采访时也不否认自己对国民性的关注和思考:“我们向鲁迅学习,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也许不少人都发现了,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识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回顾过去遍地涌起的匪患,还有后来的多次所谓群众运动,都与国民性中泥性的泛滥不无关系。”[1]从“黄土地”到“黄泥地”,刘庆邦所强调的就是国民性中这种“泥性”,即所谓“纠缠性”和“构陷性”。和鲁迅的国民性表述相比,“泥性”似乎强调了动态的或者说是能动的因素,而非鲁迅所强调的冷漠的、一盘散沙式的国民心理。但即便如此,发现国民性中的泥性,也很难说是作家刘庆邦的一个创见。而且,所谓“国民性”话语,源自世界近代化历程中殖民者对于殖民地民族状貌的概括,这种概括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殖民的信息需要,因而是整体化甚至是本质化的,不可能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做细致的历史化描述,也不可能做到所谓的“理解之同情”。因而,当时所产生的关于国民性的话语表述,大多是一种本质化的概括,里面包含有浓重的意识形态霸权色彩。反过来,殖民者出于美化自身、确证种族优越的需要,也致力于建构自我民族的国民性,只不过这种国民性主要是其优越性的自证而已。这样一种文化逻辑在当下的后殖民语境中依然存在。晚清以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今天看来,这种话语只不过是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或主动或被动地为确认自我身份而舶来的一种文化表述而已,其间的文化转译和国族的隐痛交织在一起,长久以来成为一种近似本质化的文化事实。无论如何,今日的思想文化界已经不会再把“国民性”话语本质化和客观化了,但这并不妨碍作家用泥性来描述他所认知的乡土中国的存在状态。
《黄泥地》中所描写的名叫“房户营”的村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北方村庄。里面的人物也都是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庄权力的掌控者村支书房守本也是一个普通的乡土精英,没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权威,不像李佩甫《羊的门》中所塑造的呼天成那样的拥有强大心力、宗法权威和驭人之术的卡里斯玛型人物。这使得房户营更具有乡土中国的典型样态。刘庆邦在《黄泥地》中用大量的看似与主体情节相疏离的片段呈现了房户营村村民鲜活的生存场景,叙述描写从容有致、心理刻画体贴入微,不能不令人赞叹。通过这些浮世绘式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房户营的权势格局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房守本的权力是大集体时代自然过渡的,这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他把支书的位置传给自己儿子房光民时,这种合理性受到了村民们的质疑,这无疑显示了现代民主精神的普及度,尽管村民们的心理不是那么阳光。房光民的高调强势消耗了他权力继承的合法性,增添了村民们对既有权势格局的反感,也使得反对派的力量迅速汇合起来。房守本、房光民捍卫自己权力的方式是:一方面通过行贿获得乡镇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利用现有的权力和能量对反对者进行攻击。对于后者,值得讨论的是房守本老婆宋建英这一形象。作为一个有着权力支撑的泼妇,她的铺天盖地、气势汹汹的骂街是权力的示威,同时又是权力真正掌控者的策略性的替代性的出击,泼妇的语言暴力巧妙地撕裂了权力的温情假面,暗示了权力的杀伤力。
汇聚起来的反对派房守现、房守成、房守彬、房守云以及高子明并没有高尚的动机,各自的谋求也都是并不见得正当的利益。这些反对者就其个人而言,都没有力量也不愿承担风险去直接反对房守本、房光民父子。在乡村知识精英高子明及富有政治经验的房守成的指点下,他们集体利用了房国春的虚荣心,把房国春推到了乡村权力斗争的一线。坐收渔翁之利的房守现同样用行贿手段获得了乡镇政权的支持,从而把自己的儿子房光金推上支书的位置,开始了新一轮的乡村统治,同时也在生产新的反对的力量。小说的叙述似乎告诉我们,房户营村经过一番波荡,乡村权力格局似乎没有得到大的改变,房国春所做的牺牲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轮回之感并不能支持关于国民性的本质化的想象,农民利益的分子化、个体化也并不总是历史的常态。透过小说中的不经意之笔墨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不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形态,在此之前的大集体时代,乡村权力格局及利益分配并非如此。虽然自私自利是人性之常,但安顿并塑造人性的社会结构场域却因时而变,仅此一端就足以消解关于国民劣根性的本质话语的言说。
小说的笔墨除了聚焦于乡村权力斗争之外,还描绘了乡村礼崩乐坏的生存图景。比较突出的是对于男女关系之混乱的描写。老一辈的房守现、高子明都有“相好的”,房守现甚至认为一个男人没有相好的就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后来则寡廉鲜耻地进行妇科病的非法诊治并借机猥亵妇女;而新一代的支书房光民肆意与村长房光和老婆偷情,继任支书房光金则公开去村里外地女人家里嫖宿。男女关系是传统乡村伦理之大防,作者用笔于此,显然也有着深远的文化关怀。
无论如何,以“黄泥地”为意象对乡村进行隐喻式的书写,反映了作家整体化地透视乡村的文学抱负。如果我们悬置关于国民性的宏大叙述话语,会发现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就农民利益分子化、个体化的农村现实而言,“黄泥地”的隐喻还是比较合适的。虽然这个隐喻还可以无限扩大化,只要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利益个体化、分子化,不管这个共同体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国度,这个共同体都可以视之为“黄泥地”,不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使然。
二、现代乡绅的“归去来”
《黄泥地》和现时代的其他乡土小说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其塑造了一个独特的现代乡绅形象——房国春。用乡绅来定位房国春,来自小说中的人物房光东之口:“房国春之所以热衷于管村里的事,是他有乡绅情结。乡绅情结房国春的父亲就有,到房国春身上反应更强烈。他在外面当不上官,管不了别人,就只能回到村里找话语权,希望能当一个乡绅。”[2]295这其实是作家对乡村文化的一种思考,也反映了近年来思想文化界中国乡村文化讨论中的一些意见。传统社会的乡绅,大部分集文化伦理权威、经济政治优势于一身,有的还是告老还乡的高官所化成,在乡土社会的伦理维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如此,绅权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是有限的,绅权与政权相得益彰时,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当绅权与行政权力相冲突之时,绅权往往会受到打击和削弱。关于此,《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冲突就是绅权与政权的一个冲突,我们从其中可见一斑。
房国春作为从房户营走出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县高中教书,虽然拥有不少有出息的学生,但也只能算是仅仅具有文化上的权威,并不具有真正的政治经济优势,他在农村的家庭并不富裕,他的家族儿女并不强势。他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帮助村民们在县城做一些辅助性的事情,而回到房户营村,只能在与村支书房守本相配合至少是不冲突时才能显现自己的作用,比如他在过年时组织村民慰问军属、帮助村里联系修桥、帮助村里矿工家属向煤矿索要抚恤金等,这些作为村级政权的辅助和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绅权的显现。村支书房守本也很注意维护与房国春的关系,这能够进一步增强其行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还能够巩固其利益,更何况尊重房国春并不需要多少成本。这是房国春在村里享有尊崇感和优越感的重要原因。但当房国春的意志和村支书房守本父子相冲突时,他所仅有的辅助性的文化功能就显得虚弱了,而且这种虚弱的文化象征资本被宋建英的辱骂击得粉碎。房国春在谋求学生帮助的道路上也同样遭到了惨败。在一个以物质利益为基础而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房国春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如果不能兑换为物质资本,就只能是一个空壳,如同房光民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泥胎。房国春站在了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就无法将自己的象征资本与行政权力拥有的物质资本相协同以顺利实现价值的兑换,他只能孤身上路,为其所仅有的文化信念而斗争。在传统中国,由于伦理习俗在村民社会生活运行中的协调作用比较重要,绅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显现得比较充分,它常常和宗法权力融为一体,替代了行政权力的发挥。但到了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变革将传统社会的绅权、宗法权力几乎荡涤殆尽,行政权力成为覆盖性的权力,绅权或者说文化象征资本只能成为行政权力征用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新的权力结构中,房国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只能是处于被敷衍或者被打击的命运中,无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其学生担任掌控者的乡镇政权。
房国春真正的身份是一个中低级知识分子。当他通过自己的奋斗跳出农门走进城市之后,本该继续在城市打拼或者安于自己的小市民生活,就像房光东兄弟的生活一样,与乡村彻底隔开。他之所以与乡村难分难舍,上演一番归去来的故事,是因为:一是可能确如房光东所说在城市里境遇不佳转而在乡村寻求话语权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二是在对自己能力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割舍不掉知识分子的淑世情怀。对于房国春的虚荣,小说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尤其是通过侧面描写,活画出一个自我感觉膨胀的小知识分子形象。对于房国春自恃文化优越感而形成的对妻子、儿女生命灵魂的威压,以及对高子明等曾经受难者或道德卑贱者所形成的歧视,作者也做了批判性的书写。这令人想起《白鹿原》中腰杆硬挺的白嘉轩对鹿三及黑娃的威压。这其实是文化象征资本的权力压迫,对于掌控行政权力者构不成伤害,而对于连文化权力都不曾分享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压迫。小说留意于此,是对知识权力异化的一种批判,这种权力如果与行政权力沆瀣一气,乡村的空气无疑将变得令人窒息。
所幸或者所不幸的是,房国春还有自己的坚守,面对邪恶势力敢于进行一个人的抗争。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写的是房国春不断上访、不断斗争的故事,虽然谋求的是个人的公平正义,但个人的受难无疑是为全体村民利益而起,虽然他受难的崇高性在获利者房守现乃至多数村民那里几乎被完全消解。小说写房国春最后返乡时的形象在村民眼里就是一个类似鬼的形象,这又接续起了鲁迅以来的先知先觉者“狂人”形象的书写传统。但也正是在村民的不理解和疏离中,房国春才显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所具有的可贵意义。如果说最初房国春的挺身而出还带有出于虚荣而跳进房守现构陷的圈套的话,那么在洞悉了这一切之后的不懈抗争则纯粹是为公平正义而战,为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价值观而战。正是在这一点上,房国春和乡村知识精英高子明区别开来,回乡后的房国春也由此鄙视并驳斥高子明的劝说:“你少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坏在你们这些爱耍小聪明的人手里。”[2]302鄙视“小聪明”,体现了房国春对自己文化使命的自觉,也支撑了自我生命的顽强存在。怀着文化使命回到乡村,决定了房国春是乡村的异端,不可能认同乡村的利益逻辑并与之同流合污,也不可能真正融入乡村,尽管他无可奈何地终老于此。房国春之于房户营的归去来,实质上是无法忘怀乡村、却也无法改变乡村、无法融入乡村的悲喜剧。这悲喜剧既寄托了作家刘庆邦的知识分子省思,又牵系着作家乡土改造的梦想。
三、乡土之变与文学书写
在小说中,与房国春形象有可比性并被作者对照着写的人物有三个:织女(张春霞)、高子明、房光东。织女的形象是当代文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形象,也是作者应该进一步深入挖掘和书写的形象。她作为“大跃进”落潮时被淘汰疏散到农村的纺织女工,对自己的城市生活经历一直无法忘怀,她珍视着自己的一张在城市时拍摄的容光焕发的纺织女工的照片并希望带入坟墓。可是,曾经的城市生活带给织女的只是虚荣心态和贪图享受的生活作风,她虽不甘于农村生活,但内心缺乏积极的力量,只能被乡村生活的黑暗面所吞噬,进而沉沦于乡村。高子明曾经在县城中学读书,因为被打成右派而遣返乡村,他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虽然不曾丧失,却无法生成一种健康的力量,只能转化为自我生存的精明,或者在某种情势下为投机者贡献计谋。而房光东则洞悉乡土生存的逻辑,认为自己不但无力改变房户营,而且与房户营保持联系只能给自己带来难以摆脱的困扰,因而在成功离开乡土之后则始终把自己与乡土隔绝。房光东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个人物一方面寄托了作者自我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另一方面也隐含了对包括自我在内的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的批判。总的来说,这三个人物显示了乡土中国强韧的运行逻辑,一个人只要进入乡土权力斗争,就如同深陷泥泞,难以自拔,最终遍身泥污。
但房户营村真的就只能是一个亘古不变、自行其是的泥泞式的或者说“染缸”式的存在吗?只要我们考究现实,就会发现不是的,作者虽然对房户营的生存样态进行了活灵活现的描绘,但并没有对之进行非历史化的定位。作家拈出“黄泥地”作为乡土中国的隐喻,但并没有对乡土中国进行本质化的书写。他笔下的房户营村,并非像鲁迅笔下的未庄那样与时代大潮相隔膜,而自成一个独立不变的小天地。在小说的叙述中,房户营村是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时代变革中去。房户营的乡村权力结构虽然难以被房国春所改变,但外在力量的强势侵入还是会带来一些新质。比如乡镇政权领导者的作用,乡镇党委书记杨才俊和分管副乡长尹华的作为就深刻影响了房户营村的权力更迭,杨才俊提醒房守本“房户营村不是孤立的”[2]152,讲的就是外在力量对房户营村的影响,至于这种影响能到什么程度,则只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定。房国春多年坚持上访,所带来的对房户营的改变就是证明。小说中还讲到房守良不满父亲的作为,对自己的被动处境感到无奈进而出外打工,也讲到房光民被免去支书之后在村里觉得无意思于是带着老婆出外打工,而打工之后的他们几乎没有在小说中再出现过,这可视为时代发展的力量已经召唤年轻人疏离村庄。被年轻人所疏离的村庄,逐渐丧失活力,虽然房守现等人享受着礼崩乐坏所带来的狂欢,但这种狂欢总是带有末世的意味。小说的结尾写了房守本、房守成、房国春、房国坤、皇甫金兰等人的相继死去,尤其是对于皇甫金兰的死以及其所象征的传统善良柔美的妇德的消亡,作者充满了痛惜。与此相对应,泼妇宋建英虽然没有死去,但也衰病缠身、卧床不起,凌厉的骂声也不再具有力量,注定要成为“绝唱”。这些人的死去或衰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远去,一种乡村的生存样态的销声匿迹。小说中被作家寄托自我情怀的人物房光东返乡时寻找到房国春遗留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房户营的村史。这个情节可能也暗示了作家刘庆邦的一个冲动,即记录下这个村子的历史,为它的行将消亡做一个永恒的纪念。小说叙述至此,似乎一下子赋予了整部小说以伤感怀旧的气息。不管黄泥地如何的让人憎恨,一旦消逝,还是让人感慨不已。由此反观整个小说对于乡村场景的精彩绝伦的描摹,倒有一种存留风景的意味,这些场景里所隐藏的作者的目光似乎是欣赏式的,作者的批判锋芒暂时隐匿了,倒像是在欣赏一幅绝版的民俗风情画卷,尽管欣赏的心情可能不是愉悦的。这种对于乡土的情绪可能不独刘庆邦所有,其他作家比如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也被批评家认为“不仅是在为日益衰败的乡土中国唱一曲文学挽歌,更重要的,他是在为乡村历史保存一个肉身”[3]。
的确,在乡土变革愈来愈剧烈的当下,回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对平静的乡村,不免有些追忆的意味。作家刘庆邦在接受访谈时对此也坦承告白:“故事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切入,时间的跨度将近二十年。我写长篇都是向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态。越是熟悉的事情,越不能急着写,须放一放,沉淀一下。”[1]回忆作为叙述的视角,能够给叙述者带来相对裕如的心态,也使得叙述者能够自信地展开自己的思考。相对于刘庆邦以往的作品来说,《黄泥地》中所展现的作家的思考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充分的。尤其是刘庆邦长期以来作为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作品并不以思力见长,近年来逐渐转向长篇小说写作,长篇小说的结构设计会向作家提出思辨方面的要求,刘庆邦也在小说的思想探求方面做了可贵的努力。但即便如此,《红煤》等长篇小说的格局依旧不够阔大,往往着眼于一个人的人生进退来展现城乡的纠葛,对时代的整体性思考是不够自觉的。而《黄泥地》则树立起一个核心意象作为一个时代乡村生存样态的隐喻,无疑展现了作家整体性书写的抱负。而这种抱负,在叙事碎片化、感官化成为书写时尚的今天,则显得不合时宜。但不合时宜,并不意味着整体性书写的价值消解,相反,它可能以不容置疑的生活真实来拆解那些关于整体性之虚妄的碎片化论述。著名批评家陈晓明在讨论201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时,曾对盛行的碎片化论述做出反思:“今天我们说碎片,还为时过早。也许在局部上、在我们可感知的视野范围内,它是碎片式的、分裂的、琐屑的;而在更大的背景上,今天的世界被重新整合,已经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形式,更具有深度性和内在性的整全。用齐泽克的话说,或许那是重新生成的大他者,宏大的崇高客体。”[4]陈晓明的论述提醒我们,当流行文化逐渐把时代定义为碎片式的、分裂的、琐屑的“小时代”时,可能对自我的感知过分沉迷,同时也可能放逐了对时代生活的深入体察和艰辛思考。刘庆邦是有生活实感的作家,他也因此能够跳脱流行的论述,直面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独立的思考。
当然,肯定刘庆邦在《黄泥地》中所做的思考,并非意味着认同他的结论。如前所述,“黄泥地”的隐喻很容易使作家的思考落入本质化的国民性话语的窠臼。但好在刘庆邦始终对生活有一种直面的态度,这决定了他既洞悉乡村生存的逻辑并深感绝望,同时又通过房国春形象捕捉到了乡村的抗争性、疏离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外在来源。当下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被蚕食的状况,刘庆邦不可能感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写作《黄泥地》,如果仍然保持对乡村权力格局绝对化、恒定化的想象,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黄泥地》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犹疑不决的,刘庆邦既感受到非正义、去道德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的稳固并对之充满忧虑,同时也意识到多重力量冲击下乡村变革的到来并对之无法做出确定性的褒贬。因而,《黄泥地》与其说是对乡村文明进行批判的作品,不如说是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生态的一曲挽歌抑或是“为乡村历史保存一个肉身”的写作。面对乡村之变,面对“黄泥地”的归去来,刘庆邦在沉淀经验之后将会开启新的或许是更精彩的文学书写。
[1]舒晋瑜. 刘庆邦: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N].中华读书报,2015-07-08(11).
[2]刘庆邦.黄泥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3]谢有顺.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精神[J].文学评论,2015,(1):18-26.
[4]陈晓明.文学的时代难题与碎片化的疑虑[J].读书,2015,(5):77-84.
(责任编辑:韩大强)
Yellow Land i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On the Latest Novel Yellow Land by LIU Qingbang
LYU Dongli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LIU Qingbang's latest novel Yellow Land tells the story of all kinds of people in an ordinary Chinese village in 1990s. The novel narrates rural China's survival circumstances in an metaphor type writing, describing the relative closeness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the spring alienation and disruptive forces of rural China with modern squire images. The novel faces reality with strong flavor of elegy. Its' writing purpose also tends to "save a flesh for rural China".
Yellow Land; metaphor type writing; modern squire; alienation force; flavor of elegy
2016-04-21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11);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5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支持计划项目
吕东亮(1980—),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003-0964(2016)05-01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