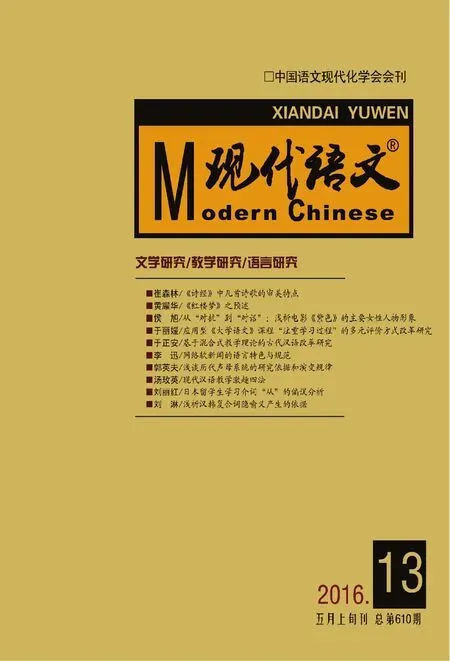玫瑰的“绽放”
——谈谈《玫瑰门》的女性成长
○杜颖莹
玫瑰的“绽放”
——谈谈《玫瑰门》的女性成长
○杜颖莹
如题眼的喻言所示,《玫瑰门》以苏眉的叙述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在“文革”这一特殊年岁中沉潜的、色彩各异的三代女性形象。所有的门都是冰冷的拒绝又有一种妖冶的诱惑:司猗纹如同妩媚狰狞的罂粟花,在向男权社会的谄媚中耗尽一生;竹西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彰显了卡门式女性形象,邪恶地反抗父权;叙事者苏眉则以分裂式成长的代价企图为痛苦中挣扎的女性寻找出路。铁凝《玫瑰门》的女性文学以审丑的态度书写了男权中心社会的女性遭遇,恰恰隐射出人道主义温情背后的苦楚,以及女性在寻求“第二性”姿态的艰难性。
玫瑰门 女性 母性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开始了“何处是归程”的探索,并企图以爱情自由、婚姻解放为旗帜,找到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传入,文坛中又一次掀起了关于女性自我价值认识的浪潮。第一次的初步觉醒彰显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要求个人解放、幸福的倾诉;而新时期的女作家显然更勇敢、客观地叙述了女性文化,“女性”亦自觉地成为被审视、控诉的对象。以《玫瑰门》为例,铁凝以超性别的写作方式,以倒叙和顺叙穿插运用的方式,塑造了一个特异的女性群体,并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女性生存的三种方式,真实挖掘了玫瑰门——女性之门的诱惑与压抑。当这些畸形的心灵深处被挖掘,读者恍然大悟,这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实的女性。更加残忍的是,作者让一个未成年女孩作为目击证人,亲眼见证这个昏天暗地的世界,被动地成长。无论是罂粟花司猗纹、卡门竹西,还是成长中的苏眉,都在压抑中全力挣扎,又互相压迫。玫瑰之门如何打通女性自身与社会的对接,以健康的姿态绽放,社会又应如何触摸扎人的玫瑰,应该成为女性文学写作的意义。
一、司猗纹:黑暗中的罂粟花
“她几乎都是过着挖空心思的耍着种种手段以求获得被认同、被承认的生活。”[1]作为小说中极富奇特光彩的祖系女性形象——司猗纹,这个小院的“元老”,一生都在渴望被承认,渴望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最终只能沦为一朵盛开在庄家的“恶之花”。这个“顽强得令人作呕又使人心酸地要在时代的巨变中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2],如同那妖媚而狰狞的罂粟花,“绽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长廊。玫瑰门,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画廊中女性真身的一大发现,同时亦是揭开男权铁幕的一个切口。
司猗纹出身在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是一个旧官吏家庭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从小便受到良好教育:“这种和睦更多地启发了她的聪慧和开朗的天性……当她长到十六岁,已经熟读过四书五经,并开始阅读二十四史了。”两年的教会学校生活又让她碰触到现代文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更让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在新诗里,她模仿的是湖畔诗人那一派。”十八岁,她遇见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华致远,并被他感化。才子与佳人的相遇,却因华致远的离去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但就是这朵集传统女性聪慧与现代女性开放思想的花儿,在一生中面对不幸所积聚的畸形心态,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苦痛变得清醒,而是变本加厉地力图在新一代的身上赎回自己曾经受过的苦痛。
为了自主式的爱情与婚姻,司猗纹曾进行过不挠的抗争,但努力并没有让她从不幸婚姻中解放出来,而只是在她的额头上永远留下了一弯月牙形的疤痕,司猗纹开始不断制造虐待自我和他人的行为:性欲的压抑、尊严的丧失,逼迫她甚至以性为武器来报复她无能的公公;面对竹西,她替代过去庄老太爷和丈夫的角色,费劲心机窥视竹西和大旗的奸情。解放后,随着政治革命的纷至沓来,司猗纹又在那个院子里演绎着一出出精彩的“人间喜剧”:为了“不被打倒”,她勇于“站出来”,精心策划交家具时的一场演讲,又在挖掘金如意中充分调动“阴谋论”;面对“内查”“外调”,她出卖妹妹,做一些落井下石的假证材料,揭发达先生,把智慧与邪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只求在“文革”中能够苟且偷生;在与居委会罗大妈交往的过程中,她又能极尽阿谀谄媚之事。当孙女眉眉长大成人后,还不断骚扰、窥视和跟踪眉眉……一系列偷窥行为将司猗纹的形象以“招人憎恨”的最大特点立体地树立起来。畸形的心理优势,让司猗纹从男权制度的受虐者转变为施暴者。自然母性的光环已被作者夺取,女性的卑鄙、丑陋使读者更全面地认识女性。但是,铁凝欲图通过女性形象的颠覆达到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讨伐的目标,让女性的母性形象同样受到了重创。
综观司猗纹悲剧的一生,昙花一现的初恋正是其不幸命运的导火索,让她从一个纯良有情的少女沦为一个对子女、亲人都充满了恶意的、极端的施暴者。这个充满韧性的女人一生都在寻找冲破枷锁的可能。最终,她“找到了”,以施暴者的身份存在;她也“没找到”,长时期地与命运交锋并未让她收到任何成效,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挫败中以畸形的心态终其一生。
作为文化载体的女人代代相传,互相折磨,司猗纹女性意识的觉醒终究还是束缚于社会长期的男权文化传统。当得了褥疮而全身萎缩的她被毛巾裹住,气若游丝地枕在外孙女的胳膊上,在出租车里几个小时地等待十八岁的情人,当那个穿着中山装的矮小老人进入她的视野,“她的眼睛异常地明亮,脸上出现了明显的惊讶,然后是瞬间的羞涩。”然后将头转向车内,脖子松软地将头放在了苏眉的肩上。她脸上失去了任何表情,她闭了眼……读到此处,读者终于愿意原谅、宽容这位曾“不折手段”的女人。说到底,这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我们在质疑司猗纹自身的恶意与残忍时,更惋惜时代的悲剧。从积极努力的反抗到无法选择的迎合,女性终究无法顺理成章地被承认为独立社会身份的角色,司猗纹——盛开在黑夜里的响勺胡同里疯狂的罂粟花,也是为数不少的女性经历的宿命般的人生轨迹。
二、竹西:自赏的玫瑰
如果说,司猗纹是《玫瑰门》中祖母形象的代表,竹西代表的则是承上启下的母亲人物。这位充满生命活力、洋溢迷人魅力的女性,既是玫瑰门的敞开者,却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悲剧女性。可以说,竹西就是在充满艳丽与伤痛的玫瑰门里,演绎了生动而疼痛的传奇一生。
像所有60年代初的大学生那样,他们“相信生活,关心政治,遇事能为他人着想。”不久后,竹西便“被庄坦带进响勺胡同,结婚了。”在《玫瑰门》中,作者对竹西婚前生活叙述十分简单,对意识形态的自然顺应使她摈弃了亲情,主动断绝与父母的关系,从不回父母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信件。此时的竹西还是生活在政治形势的框架里,尽管从无不适,但潜藏的女性意识也因这种麻木而变得平静。良好的教养、令人羡慕的职业、旺盛的精力……然而,婚后的竹西并不幸福,她嫌恶丈夫的孱弱,认识到“人只有爱自己,才能尊重与生俱来的各种需求”,想要获“精神上的浩瀚”与“人格上的独立”,必须 “摆脱外加于人的奴性、依附性抗争。”正是基于此,竹西面对婆婆所代表的男权文化的强大阴影,依然坚持自我,勇敢去爱。在丈夫过世后,竹西诱惑了比她小八岁的大旗,被婆婆揭发后,索性与大旗结了婚,过起了两人的家庭生活。当她体察到丈夫在他们的婚姻中,“总在揣测”“十分紧张”,她又主动与大旗离了婚,把目光瞄向了放在抽屉里侧信封里的那个“已经没味儿可闻的”的烟头的主人——叶兆北,力图获得身心纯美的爱情生活……竹西一生都在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中,精神上的醒悟和行动上的独立彰显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在玫瑰门里执着追求本我自由的女性。
在庄家,男性全部缺席,非病即亡,竹西和司猗纹无疑是肩负起家庭生活重担的人物,共同对抗来自门外世界的压力,但关起门来,两人又上演着一出出精彩的“婆媳斗”,不动声色地反抗着婆婆的压迫:“竹西和婆婆之间也许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能’与‘不能’。”[3](P26)面对婆婆做出标准的端碗、持筷、咀嚼等系列动作,竹西会故意作出些“不标准”……事实上,竹西是最懂吃的标准,对吃的标准胜过婆婆。苏眉后来才领悟到,婆婆对眉眉的过分挑剔是因为庄晨扔给婆婆这个“困难”,而“困难”的收留者是竹西的自作主张。显然,竹西在这里扮演了一位侠者的角色,保护女儿、保护苏眉(尽管不是主观目的),义无反顾地反抗司猗纹的压制。司猗纹僵卧病榻后,竹西不动声色地将这具躯体毫无意义地延续了五年,她会“照顾婆婆的饮食,处理婆婆的大小便”。在照顾婆婆的各种理由中,却没有一种是常人能够窥探得到的:竹西对司猗纹“无微不至”地照顾了五年,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温情,而是基于儿媳对婆婆的报复心理。被家庭伦理观重重压抑的竹西,终于找到发泄的出口,她给司猗纹讲美国电影《舞会皇后》中让所有人为之倾倒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观察躺在床上的一向坚强的司猗纹的烦躁不安与跃跃欲试的焦灼,让其内心备受煎熬,让曾经带给她种种委屈、伤害的婆婆逐渐丧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竹西用她定义的“道义”帮助婆婆的生命得以延续,借道义的幌子进行暴力的铺陈。“我不爱她,才用我的手使她的生命在疼痛中延续。”无疑,这是一种人性的邪恶,更是人道主义的悲哀。
竹西一生都在反抗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戕害,在温情中透露着人性的邪恶与黑暗。如果说,铁凝在《玫瑰门》中借助对竹西出浴进行细致的身体描摹,来讴歌女性对自我尊重与热爱,以一生执着追求爱欲表达对女性自由本性的欣赏。那么,“承担儿媳、医生的双重角色”照顾“浸染着毒汁的罂粟花”司猗纹,尽是作为对婆婆的报复与变态残杀,无疑展现了竹西作为人本身的人格的扭曲与异化。显然,女性在寻求自己拯救的道路上走向了歧途,这朵“身上永不消退的洁尔灭溶液的味道,向人们证实着她是明白无误的化身”的玫瑰,并未在男权文化中获救,充盈着冷峻理智的背后逐渐丧失了作为“人”的本体意识,而走向了异化。
三、苏眉:分裂的成长
“眉眉,叫婆婆。”她不叫,还把脸一扭,小黑脖子梗着,很直。她跟她第一次见面就不愉快。(《玫瑰门》第二章)
苏眉要去响勺胡同。她下了车,捏着信封站在胡同口想,是现在进去还是下次再来,虽然她早就作过现在进去的决定。她还是上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下次吧。她想。(《玫瑰门》第一章)
响勺胡同——苏眉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又走进了少年时代,逃离后又再次回来见证着这里的一切。作为作品的主要人物及叙述视角,作者以苏眉的眼睛看玫瑰门里女人的生活、争斗;同时,苏眉又深受胡同生活的影响,以致在她今后漫长岁月里长久地存在着。在刚刚接近生命的第一个十年,原来生活在小城市的苏眉因为父母被劳改无力照顾,只能送到在大城市生活的婆婆司猗纹家里。离开父母双亲的荫护,苏眉进入了一个新的以婆婆司猗纹为中心的家庭,以新的目光、新的态度重新感知生活,认识周围的人:婆婆司猗纹、舅舅庄坦、舅母宋竹西、邻居罗大妈……童年时期,苏眉便经历了超越她年龄的人情物事、淋漓鲜血中的惨淡人生:司猗纹为求自保与自我表现,不惜出卖异母妹妹、主动交公又留一手,在雨中狼狈遮盖交公的家具;默许罗家兄弟对姑爸、大黄的虐待与伤害;在司猗纹的设计下,眉眉承担了竹西与大旗秘密关系的发现者和见证人……这些荒谬扭曲的行为、卑鄙龌龊的场景总在“不经意”间闯入苏眉的视野,尖锐地磨砺着苏眉敏感的少女之心,给苏眉的成长道路播下了痛苦不安、绝望恐惧的种子。可悲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是可怜的旁观者,也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在对革命“积极向往”中,在司猗纹“艰苦朴素”的宣讲者“专心”而“坚定”地吃下红糖窝头,表现出“香甜感”;一次次重复着对领袖像的临摹,惊恐地发现自己失去了真正的观察力与创造力。
成长过程的重重威胁与伤害,终于让她决心挟带妹妹逃离北京、投奔虽城:在火车站,她终于“来了”。这一次的逃离,无疑是她成长路上的一次蜕变,似乎也是几代人中唯一的对现状的僭越者,但并未因此消弭年少时代的惊吓与困窘,反而凝刻在苏眉的记忆深处。随着时间的流失,成年后的苏眉开始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封存的记忆与少年的自己。
在阅读《玫瑰门》的时候,以对话形式出现在部分章末的段落不得不引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内心隐秘的话语交流,对话双方相互应答,而对话的对象便是——成年眉眉与少年眉眉。当苏眉成年后,一次次地向后回头,试图寻找成长中的困惑、焦虑:“你知道我是苏眉”“你就是我的深处”“我对你的寻找其实是对我们共同的深处的寻找” 成年后的苏眉追寻着少年的眉眉,在眉眉的自我辩白中发掘隐匿内心深处的更加残酷的自我剖析,试图还原一个更真实、更本质的自我。“我”分裂的两种声音、两个主体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人性的反思。记忆深处的细微痛楚重新发掘,直逼心之恶,这种理性的思考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的崛起。然而,苏眉却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在文革的惊恐与祖母的阴影中“歪七扭八地成长起来的”苏眉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婚姻和家庭,却可以无视丈夫的冷漠与疏离,与叶兆北的再度重逢也无意撩起她心中的悸动。欲望、权力、自由,这些原本应该出现在苏眉——现代女性身上的词语并未呈现任何的号召力。就像自我对话在第十二章后再未出现,当少年的眉眉与成年苏眉吸收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位事业有成的女性是否真的获得了玫瑰的健康姿态,跨越了男权社会的那道门槛?这位与祖母不仅在容貌相似,在行为举止上亦有如出一辙的特质的女性真的在一次次痛苦挣扎之后获得了新生?小说的结局冥冥之中给了读者一个答案。
“有人把女儿托给苏眉看,她一眼便看见了那颗硕大的头颅。她迫不及待地想亲亲女儿的大脑袋,她想给她起名叫狗狗,她发现狗狗额头上有一弯新月型的疤痕,那是器械给予她的永恒。”(《玫瑰门》第十五章)
为争取女性生命自由,司猗纹的头上留下了“一弯新月形的疤痕”,苏眉的女儿——《玫瑰门》的第四代女性,头上也有“一弯新月形的疤痕”,无疑带给读者无力的挫败感。这种相似的新生轮回,预示着女性企图抗拒男权文化的精神解放还是陷入了永恒的死循环中:是否每一代女性都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文化这所器械赋予让人讨厌的永恒?
世界上所有的门都以冰冷的拒绝姿态诱惑着门外的人打开,玫瑰之门内是女性要求绽放的诉求,门外是社会对玫瑰的压迫,任何的痛苦挣扎被熟视无睹。门内外的拒绝让女性只能痛苦挣扎,生命延续之中的我们依然陷入了文化循环中。“提问,一种轮回;睡觉;一种轮回”,女性的抗争似乎也在这一种轮回中。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形成的。”[4]作为第二性主体的女性显然陷入了命定的文化圈套,在既定的男权文化中失去了健康的独立姿态。
“她爱她吗?”作者以一种调侃的反诘结束了叙述,也为读者设置了疑惑:生命延续中,我们能否给下一代真正的爱?女性的价值、妖娆的玫瑰,究竟该如何有意义地得到绽放?
注释:
[1]赵景芝:《拷问个体生命欲望诉求下的女性生存状态——浅谈铁凝长篇小说〈玫瑰门〉》,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年,第2期。
[2]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05期。
[3]朱敏:《异性与回归——铁凝小说论》,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页。
(杜颖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0234)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