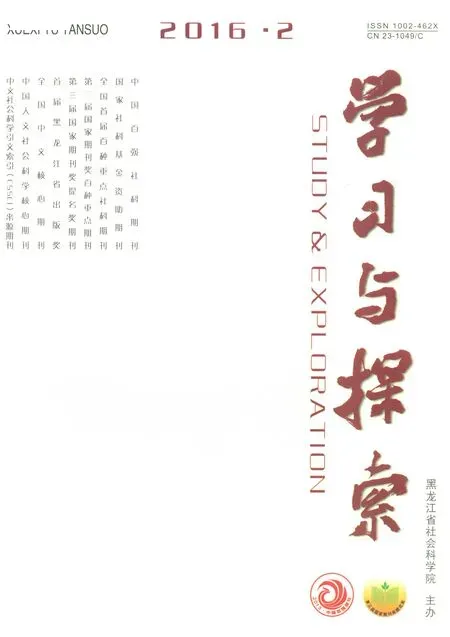知识与信念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问题
许祖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知识与信念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问题
许祖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主体——中国现代作家们智慧的基础是知识,他们智慧的核心是经过实践、理性和良知确证了的信念。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文化、思想的创造性成果就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之上的。中国现代作家们的知识及其结构的最显著特征是实践性品格和价值化倾向。他们的信念类型主要有原型信念、模型信念和德性信念,这些信念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也在主体智慧的层面保证了他们的知识创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与信念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开辟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这种研究方法对其他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具有示范性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知识;信念;学术增长点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虽然只有三十余年,但在这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它所凝聚的种种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问题,形成的各类人文的、艺术的规范,展示的思想和审美的非凡魅力,却犹如一座座蕴含丰富的矿山,不仅在过去吸引了海内外探究者的目光,而且今天也同样牵引着成千上万研究者的心灵,像清泉向往海洋一样追逐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座问题的富矿、艺术的富矿、人文的富矿的矿脉,不断地将它们的价值挖掘出来并向世人展示。在这一座座思想和艺术的富矿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系统及与之相关的信念、确证问题,在我看来,也是其中的一座富矿,而且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富矿。这一富矿如果得到相应的开采,不仅能丰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更能从一个特殊的方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魅力。
一、问题的提出
扫描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但在这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中,基于知识学尤其是现代知识学的层面系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却迄今未见。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迄今为止没有一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具有明确而充分的知识学意识。以往的研究成果尽管有些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作家的知识积累与知识学研究问题相关的内容,但毕竟不是从知识学的层面展开的研究。例如,中国现代各种文学思潮的本体研究及与传统和外国文学思潮的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求学经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学术成就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作品与宗教、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形成的传统渊源与外来影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文化观、社会观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及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以及近些年十分火热的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等等。
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十分有效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特征及其思想、文化、文学的巨大成就,也在实际论述过程中涉及了包括中国现代作家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中所包含的知识学问题。譬如,关于中国现代作家人生经历的研究就涉及了中国现代作家经验知识的获取状况及其对作家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这种影响对于形成一个具体作家创作个性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研究,尤其是像对鲁迅这样的作家的思想研究,则不仅涉及了他们的哲学知识、政治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心理学知识、文学理论知识等,而且涉及了这些知识得以建构的各种信念(关于信念问题,下文要专门探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成就研究,则涉及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各种文化知识及这些知识的现代品格与传统品格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成就研究包括流派、思潮的研究等,则关涉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知识问题等等。这些研究虽然都关涉知识问题,而且也是在相应的知识(如文学知识、美学知识乃至于时髦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知识等)的基础上展开的,得出的各种判断(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判断、反传统的判断、中国现代文学应该用民国文学来称谓的判断等)及形成的各类命题(如中国现代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现代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性思潮等),也都具有知识性。因为知识本来就是以命题的形式存在的,命题所反映的不仅是研究者的思想,而且所揭示的同样是文学对象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意识,而“意识的存在方式是知识”[1]。尽管研究者的思想和所要揭示的研究对象的思想意识各不相同,有些所谓的思想意识的揭示也不一定具有说服力(如关于“民国文学”的认识),但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是知识,虽然有的是可以确证的、在逻辑框架里或在经验事实中可以得到说明的“真”知识,有的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假”知识,但无论它们的属性如何、形态怎样,它们毕竟都具有知识性。当然,这些研究无论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还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固然都具有知识性,但都不是自觉地在知识学层面展开的研究,所进行的分析也不是知识学的分析,而是文学、文化、哲学等的分析;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是知识学的结论,而是传记学、人物学、政治学、宗教学、民俗学、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等的结论。有的研究成果则借用了法国现代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谱系”概念,如最近出版的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知识谱系》一书,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些研究仅仅囿于知识与权力的规范,借用福柯的思想观念,甚至是只借用了福柯的某些概念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虽然意图令人钦佩,但不仅在借用的过程中存在十分明显的“穿新衣说旧话”的问题,而且借用本身还存在“框套”的问题,即都没有自觉的知识学意识,当然也没有进入普通知识学层面,更没有自觉地依据知识学的范式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并对现代中国作家的知识系统、知识结构及其特征展开相应的研究。
第二,迄今为止没有一项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使用过知识学的核心概念——“信念”,并在这一概念的范式之内展开研究。有的研究成果虽然也使用了“信念”这一概念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作家(如鲁迅)进行研究,但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从研究展开的实际状况及相关语境来看,这个概念的所指也不是知识学层面的,而是政治学或社会学层面的,有的甚至是宗教层面的。所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一些重要的作家,特别是像鲁迅这样一些伟大作家的信仰问题、观念问题,如鲁迅的生命信念与个性信念,周作人的人的信念等问题,而不是知识学所关涉的信念问题,也不是知识学应该关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信念问题。如信念的真与假的问题,这是知识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宗教学等则并不关注这一重要问题,它们所关注的是信念的“有”与“无”的问题以及信念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更何况从本质上来讲,政治学、社会学等关涉的信念,有很多本来就不是知识,特别是宗教性的信念,尽管它们也很丰富,影响更是非凡,但却与知识无关,只是一些不需要证明的信仰,“属于对某种人生意义、精神境界的认同,而不属于科学认识的范畴,因此并无真假可言,从而也不受科学知识分析的限制”[2]53。
正是由于以上这两个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知识、信念的确证问题探讨的缺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缺失,并不是研究者们的无能,而是由知识学研究的自身逻辑导致的。因为不涉及知识学的信念问题,自然无法对知识学的核心问题即信念的真或假的问题展开研究,确证哪些信念是真的,哪些信念不真。这也就使得在实践的层面,无论我们搜索的眼光向空间的哪一维度——中国的、外国的展开,也无论我们思维的触角在时间的连环上是伸向过去还是缠绕于现在,也的确难以寻索到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蛛丝马迹。确证的问题虽然是知识学的重要问题,不过因为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与信念的问题,所以,也只能将这个重要问题悬置,尽管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也只能“储芳待来年”了。
正是从国内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出发,笔者才认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与信念的问题(事实上还应该包括确证问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富矿,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开辟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不仅可以从知识学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众多作家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的主体条件及知识结构问题,从而形成我们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新看法、提出新的判断,而且,这种研究对其他文学,如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作家、外国作家的研究,也应该具有示范性的价值与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及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如果以时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形成的结构;如果以空间为标准,可以分为中国知识与外国知识形成的结构;如果以获得知识的途径为标准,则可以分为经验知识与书本知识所形成的结构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主要由三个维度构成:经验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中国现代文学这三个维度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在时间上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的全过程,在空间上则关涉中外,在本体形态上则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它们直观地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作家及其创作的优秀作品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特征,如鲁迅及其创作的小说、杂文等。
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知识。这一类知识主要由中国现代作家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的自然、社会等的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的认知构成。这些知识关乎自然、人情、风俗以及各类具体的人或事,如关于故乡、国外、北京、广州、上海等的风土人情的感受与认知;关于自己亲人的往事、关于师生之情、同学朋友之谊等。中国现代作家很多都是教师出身,或者曾经做过教师,如鲁迅、闻一多等;或者一生都从事教育事业或关注中国教育问题,如叶圣陶等。这些知识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品格的基本知识。同时,正是由于经验知识的不同,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保证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世界的丰富多彩,也直接地规约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个性特色及他们所创作作品的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书写相同的题材、用相同的体裁进行书写,其作品却千姿百态的知识学根据之一。
第二,自然科学知识。这类知识主要由某些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等所习得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地质学等知识构成。之所以特别将这一类知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结构中的一维来强调,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首先,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有很多都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尤其是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大多最初都是学自然科学的。①这些作家作品不仅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某一个时期所达到的最高艺术境界,而且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还产生了直接影响,如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郭沫若及其诗歌所形成的浪漫主义艺术规范和艺术精神等。如五四时期登上文坛的鲁迅与郭沫若是学西医的,成仿吾是学兵器的,等等。这些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史实。其次,从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观念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自己艺术世界的建构过程中,汲取了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很多新颖的观念,但正如拙著《五四文学思想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思想、新学说中,有两种最为醒目的思想、学说,也是被先驱们谈得最频繁的思想、学说,它们就是民主与科学思想。当时先驱们根据它们的英文读音,形象地称民主为‘德先生’,称科学为‘赛先生’。”[3]2-3这两种被五四新文学先驱们特别青睐的观念、学说,不仅直接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学的建构,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影响深远的。如果说,民主的观念及与之相关的学说还是属于人文、社会知识的范围的话,那么,科学的观念及学说,则不仅意指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综合客观之现实,诉之主观之理性”[4]),而且也直接意指科学知识本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老前辈李何林先生就不仅认为科学指的就是科学知识,而且认为它所指的还不是普泛的科学知识,而是意指“进化论”的知识。即五四时期“在文学思想方面,主要的是进化论的思想”[5]。因此完全可以说,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不仅打开了中国现代作家看世界的眼界,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主体即中国现代作家的思维方式及相应的价值观,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同时,也在最为醒目的层面,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面貌,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思想与艺术面貌区分开来。②因为中国传统作家的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有限,即使有的作家有中医知识,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但也仅限于此。他们不仅没有西医学方面的知识,更没有较为完整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等,这也就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世界的面貌。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中国现代作家建构得最为完善、宏伟、丰富的知识系统。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这个系统的知识可以划分为几大门类:文学、艺术(如戏剧、美术等)、语言文字(汉语、外语)、政治、哲学、社会(包括都市、乡村)、宗教、教育、经济等等。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文化、思想等领域的创造性成果,如他们的文学作品、杂感、学术研究成果等,都直接与他们所具有的这些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有关。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智慧的话(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用“双重智慧”来形容他们的智慧结构[3]10),那么,这些丰富的知识则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创造成果的丰满血肉,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创造性智慧的坚实基础。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所保有的知识及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具有什么特点呢?在我看来,主要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而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不仅本身学术意义丰富,而且迄今也还没有人进行过相应的研究,所以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一,实践性品格。无论从中国现代作家汲取知识的目的,还是从中国现代作家知识系统存在的基本状况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尤其是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所积累或储存的知识都不是束之高阁的展览品,更不是“掉书袋”的炫耀品,而是进行思想、文化、文学创造的基本材料,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这种实践性品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代作家包括一般的作家,他们汲取知识是有切实的现实目的的。例如,鲁迅学西医就是为了救治像他父亲一样的普通人,为国家服务等;至于他们汲取其他知识,如进化论、宗教、现代主义文学、潜意识学说等,也有很强的现实目的,并也都化为了他们作品的血肉,如潜意识学说之于“新感觉”文学等。此外,中国现代作家在认知活动中积累知识,总是将现实的知识与历史的知识相结合,将中国的知识与外国的知识相结合。正是在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中,我们发现,中国现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常常是新与旧、中与外的有机统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此同时,中国现代作家汲取知识常常以解决现实的某些问题为目的。例如,鲁迅读古书汲取古代知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刨一些坏种的祖坟”;郭沫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为了给现实的中国文坛以帮助。这种实践性品格当然赋予中国现代作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现代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知识以鲜活的生命力。但有时也会形成一种复杂的局面,例如,鲁迅对“中医误人”的认知就属于经验知识的范畴,他一生都没有再认识,更没有从自然科学知识的层面进行解释,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这也与其恪守知识的实践性密切相关。
其二,价值化倾向。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特别是优秀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钱钟书等,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既不是刻板的结论或命题,也不是作为真理存在的不变依据,而是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食粮,具有明显的价值化倾向。这种知识的价值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现代作家汲取知识往往不太重视知识的本体形态是否宏富或时髦,而是着眼于这种知识是否“有用”。如鲁迅对阶级论的认同、郭沫若对“泛神论”的认知、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等等。尽管作为知识,这些理论良莠不齐,但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拿来”,就是因为他们发现用这种知识能有效地说明很多先前无法说明的问题;他们的文学、文化、思想的创造性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们重视知识的有用性,即知识的价值化。其次,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知识结构中,有些知识的功能主要是满足自己的精神享受(这其中有着十分丰富、复杂的内容)。例如,鲁迅并不进行美术创作,但他却积累了丰富的美术知识,他积累这些知识很重要的价值追求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欣赏古今中外美术作品的需要;郭沫若并不以书法家自称,但他在书法方面积累的知识却十分丰富,而这些知识的积累从主要用途来看,并非为了现实文学创作,而主要是满足自己的某种精神需要。同时,中国现代作家知识的价值化倾向还常常具有反思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固然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汲取知识,但也常常怀疑各种以理论、常情和其他方式存在的知识。如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所发出的“从来如此就对么”的疑问就是集中的表现。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之前所积累的知识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后,都会将其抛弃,如郭沫若对“泛神论”的抛弃和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的抛弃等。这固然使他们知识系统的价值化倾向更为复杂了,但也正是这种反思,使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知识系统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力及与时俱进的发展动力;也使他们的知识系统的价值化更具有了知识学的理论意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的知识及其结构的这种特征才很值得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信念类型及特征
信念作为知识学的核心概念,对它的含义学术界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就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目前,国内外哲学家给信念所下的定义分歧较大,主要有以下五种: ( 1)信念是心灵的一种状态。西方大多数哲学家持这种观点。( 2)信念是一种行动。英国哲学家A.贝恩认为,信念是行动,或一有机会就准备行动。( 3)信念是兼有心理和身体两方面因素的一种。英国哲学家罗素举例说,当你相信“汽车来了”的时候,你的信念就是由肌肉、感官和情绪,也许还有某些视觉意象所构成的某些状态。信念就是这些状态的集合。( 4)信念是理念客体化的主观手段。这是苏联学者柯普宁的观点。在他看来,信念和信仰是一回事,它是一种对于改造世界有工具价值的精神形态。( 5)信念是人对某种现实或观念抱有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这是国内学者从价值意识角度给信念下的定义[6]135-136。
如果进行概括,或者说选择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说,则似乎可以引用这样的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把信念视为某种特殊信息产生的状态。”[2]37也就是说,知识学中所说的信念指的是认识主体对某个对象(包括自然对象、社会对象、理论、学说、审美对象等)认可或不认可的心理状态。信念在知识中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学者们的这样一些论述就可以直观地看出:“信念是知识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是说,知识一定是信念。”“没有信念就没有知识”[7]。正是因为信念对于知识来说如此重要,所以,它自然成了知识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学问题,自然也应该探讨信念的问题。
人类创造的知识,无论具有什么形态:经验的、理论的、书本的等等,也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定性: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等等,都是十分丰富的。与此一致,信念类型也是十分丰富的,甚至是难以穷尽的。因为如果从“信念是以命题为其内容”[2]37的角度来归类信念,则完全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命题就有多少信念,而命题又是如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过来的,所以,在从知识学的层面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时,我们也只能对信念进行相应的归类,尽管这种归类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但也只能两相对比取其轻了。在这里,我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信念主要归为三类,并对这三类信念的特点进行相应的说明,以此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三类信念的特征。
第一,原型信念。所谓原型信念,也就是主体从直接与对象的接触中获得的认可,即信念。虽然这种类型的信念是认识主体,具体来说,是中国现代的作家们由经验观察而得到的对客观对象属性的一种认可所形成的初级信念,但却是中国现代的作家们实现其知识创新,即文学、文化、思想创新的基础性信念,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信念。就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原型信念来看,它们大多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性是客观性特征。这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们的原型信念主要不是依凭逻辑形式,如演绎法的形式,从理性或一般观念出发间接得到的,而是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在主体与客观对象面对面的过程中,如鲁迅面对自己的故乡、郭沫若面对庄子的学说、巴金面对封建大家族及青年、张爱玲面对形形色色的男女等,都是通过对自己感性经验真实性的认可而直接获得的,因此,它是一种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信念,是经过了主体验证的信念,是与认识对象的面貌和感性存在方式、本质存在方式基本相吻合的一种认识成果。毋庸讳言,这种认识成果,有时是有着片面性的,如鲁迅对“汉字”的认知、郭沫若对庄子的认知、闻一多对“死水”的认知等,就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先驱们曾认为中国的汉字太难了,这正是中国不长进的一个重要而根本的原因。后来的鲁迅更是认为,汉字不灭亡,中国就会灭亡等等,这些认知及所形成的命题,就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性、武断性。但也不能说它们没有揭示客观对象的某一方面特征、面貌,事实上,它们也的确揭示了对象某一方面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也许是负面的特征,如汉字的难,但却是可以被经验的事实证明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些中国的繁体字,要掌握它的“形”,的确很难),也就是说是具有被经验的事实验证的客观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的一系列思想与文化成果,特别是他们从现实出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成果,既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原型信念的客观性特征,又体现了这种原型信念在他们知识创新中的重要意义。第二个特性是充分的个人性。原型信念由于是个体在实践中对经验和事实的一种认可,所以,个人性是其又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个人性特征正是中国现代文学能在既有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的重要主体因素,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之所以能丰富多彩的主体性的原因。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的文学创造活动及所取得的成果以其客观存在,充分说明了原型信念的个人性魅力和其重要性。
第二,模型信念。所谓模型信念指的是认识主体思想(包括情感)世界中所储备的既有观念与认识。这种类型的信念,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的作家们创造新知识的逻辑性信念。它是经过中国现代作家的认知结构对外界的信息进行加工、建构而形成的某种认知图式,如鲁迅的“进化论”图式、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图式、赵树理的“通俗文学”图式等等。它是中国现代作家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对经验观察得到的信息进行选择、思考而形成的各种理性信念,是中国现代作家们理性地整理各种经验知识的思维准则,是把经验知识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是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中介。中国现代作家的模型信念虽然与知识学所认可的模型信念一样具有主观性、普遍性、公共性及主体间性,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们的模型信念是在接受各类知识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的结晶,所以,它们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如,在鲁迅的模型信念中,思想文化领域的“中间物”“无物之阵”“希望—绝望”“自性”等四大信念、文学领域的“高义的现实主义”信念,都是最具鲁迅特征、最有代表性的模型信念,是人类思想、文化、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信念,是鲁迅独立创造的信念。如果说鲁迅正是运用这些个性卓绝的模型信念看待各种现象、分析各种问题,所以才使他发人之未发、见人之未见、创人之未创,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文化与思想成果的话,那么推而广之,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模型信念,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模型信念的内在作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第三,德性信念。所谓德性信念,是在传统的知识论基础上新创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当代“德性知识学”的重要概念,“其基本的思路是,首先,就像伦理学的德行论用道德主体的规范性质来理解行为的规范性一样,德性知识论试图用认知主体的规范性来理解信念的规范性”[2]280。这一信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来说,是他们进行知识创新的保障性信念,是他们的良知与知性之知的有机结合体,具有道德学与知识学的双重意义。通俗地讲,这一信念指的是中国现代作家们强烈而鲜明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道德层面关涉态度和品性问题,而在知识层面则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是直接关系到知识的合理与不合理、真与假的确证的问题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们所获得的众多信念中我们发现,它们常常能得到合理辩护与证明而很难被解构。例如,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为人生”而创作的信念、为个体而创作的信念、为启蒙而创作的信念以及“人文学”的信念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任何知识、形成自己的任何信念都自觉地遵循着责任伦理的准则,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的文学、文化、思想创新之所以能得到普遍认可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能实现创新并使创新的成果生命常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中国现代作家也是人,而且,首先还是普通的人,他们当然会由于自身条件或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形成某些信念或者接受一些信念的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解。如鲁迅对中医、对汉字、对现代主义绘画的误解;解放区的文学家们对文学民族化问题的狭隘化理解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但他们的这些误解不仅是正常的,有的也是切合当时的时代需要的。如解放区作家对“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理解,就是如此。而且同样是有意义的,即使是一些具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理解,如创造社同仁对“为艺术”与“为人生”的理解等,它们的意义我们也应该特别注意,正如英国哲学家赖尔所说:凡有可能误解,就有可能理解。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这样一些误解,我们正应该从“可能理解”的角度来理解。更何况,他们的有些误解还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例如,鲁迅对进化论这种知识体系某些方面的误解就是一个例子。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仁指正。
参考文献:
[1]鲍宗豪.论无知——一个新的认识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2.
[2]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许祖华.五四文学思想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1( 1).
[5]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6.
[6]鲍宗豪.知识与权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7]胡军.知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7-58.
[责任编辑:修磊]
作者简介:许祖华( 195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16)02-0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