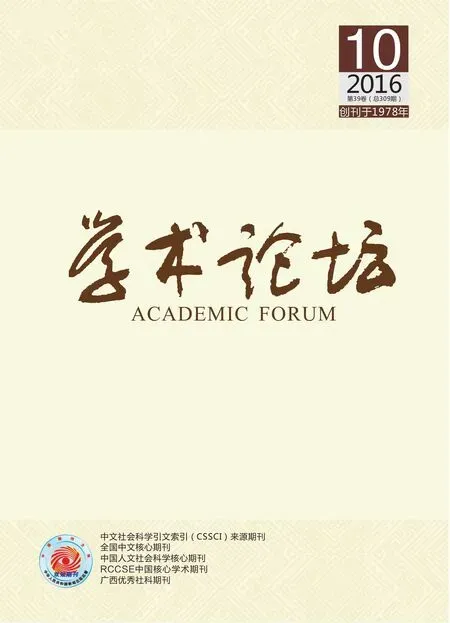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双重叙事时空与竹内好的判断
刘旭
鲁迅小说的双重叙事时空与竹内好的判断
刘旭
文章借助叙事学文本细读方法,发现鲁迅小说有双重叙事时空并存的 “彷徨体叙事模式”。《在酒楼上》等小说建构了以“我”和对立物分别为主体的第一叙事时空和第二叙事时空,意义上的深层指向分别是作为启蒙者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作为文学家鲁迅的绝望辩证法。启蒙与文学的矛盾投射为叙事时空的分隔,意味着自我与非我、自我与对立物/异质物间的矛盾与博斗。文本最后回归“我”的第一叙事时空,完成自我的“分裂-生成”循环。文章将叙事学分析与竹内好对鲁迅的评价相验证,从新的角度审视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第一人的地位。
鲁迅;双重叙事时空;彷徨体叙事;竹内好;绝望辩证法
竹内好①本文参照了竹内好《鲁迅》的两个译本,一个是李心峰译本,一个是孙歌译本。在划时代的《鲁迅》中对鲁迅的价值作了学理化的甚至是哲学化的高度评价。但一开始却认为鲁迅的小说“不漂亮”②李心峰译本译为“鲁迅的小说差劲的”。原因是“作品中没有自己的世界”,“兴趣只局限于对过去的追忆,这正是作为小说家的致命伤”,见[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1页。本文采取孙歌本的译法。——这是竹内好对鲁迅唯一的不满意之处,原因是“作品不具备有序的世界”,而且“兴味只囿于追忆过去,作为小说家仅此一点便是致命的”[1](P13)。简言之,以整个世界文学体系为参照,竹内好并不认为鲁迅的文学性有多高,因为中国缺乏现代文学基础。整体来看,竹内好的判断没错,鲁迅的作品不是完美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品都不能说是完美的,但鲁迅一出现在文坛就表现出了很难超越的、高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结合,而且是把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从文本的形式层面来看,鲁迅的叙事营造的现场感和意义层面的深刻性相当完美的结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在启蒙和文学之间有着永恒的矛盾,但却又统一在鲁迅精神之中,“鲁迅精神”一词的产生即昭示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精神象征位置,它的产生是一个重大的民族事件。它由“鲁迅”这一专有名词加“精神”这一抽象名词组成,抽象名词最新研究称其为“外壳名词”,因为需要一个定语来填充,以作为其内容。“鲁迅”本来是人的名字,一个笔名,属于特殊的专有名词,它处于定语位置,起到填充外壳名词的作用,这种填充往往是为了激发人类群体的某种想像,而“鲁迅”一旦与“精神”相结合,就上升为类化了的专有名词,成为一代或几代人的象征,如“雷锋精神”一样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精神抽象物,鲁迅对文化的影响应该比雷锋要大得多,因为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他的影响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另一方面,“鲁迅精神”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化的定位,把启蒙及国家民族的前途捆绑在一起,成为爱国作家的文化代表。这也是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一出现就备受批判的原因,他们因为政治色彩的模糊而被排除在“爱国”这一命名之外。而鲁迅的文学特征却更可能是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光辉亮点,竹内好在70年前已经作出了精当的判断。当然本文的出发点并非力图证明竹内好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从文学文本的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出发,分析鲁迅文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原因。
一、双重叙事时空:启蒙者的国民性建构
竹内好称鲁迅“不愿意在作品中讲述自己”[1](P27),他的意思应该是鲁迅不像郁达夫那样把个体的成长、欲望及价值那么直接地与个人经历和体验相联系。鲁迅几乎从不以抒写个体化的现实体验为主要目标,即使从个体经验出发,也必然抽象出一个宏大的主题,且这个主题必然服从于一个更宏大的深层结构。如果把“自己”换成“自我”,自我意识的凸显会造成叙事的主观化特色的增强,虽然鲁迅的小说中没有郁达夫的那个自己,即“小我”,但鲁迅的“自我”却充溢着整个叙事世界,从鲁迅小说语汇的修辞效果能明显看出其主观化色彩。这种主观化在今天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鲁迅的一生都有着对“国民性”的执着。从小说到杂文,从崛起于文坛到逝世前,鲁迅始终把国民性作为写作的关键点,把“自我”与国民性相联系,意味着鲁迅的“自我”更接近“大我”。鲁迅小说的结尾很能看出其文学的叙事特色,下面看《祝福》的结尾:
①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②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③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小句标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隐含作者以第一人称视点描写除夕之夜的鲁镇,这种来自西方的限制叙事视角更像戏剧中的独白,而且此处使用了欧化长句,看似进行风景描写,其实同时夹杂了相当多的情感,表现出强烈的主观化色彩。单独看会以为它是最合小说题目“祝福”之意的片段,但如果放在整个叙事结构之中则会发现表层的“祝福”之下是另一种情感。先从叙事结构上看,鲁迅的不少小说结构中都包括两个叙事时空,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孤独者》《祝福》等,总有两个叙述人的存在,而且两个叙述人一个作为隐含叙述人讲别人的故事,另一个作为显性叙述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如《祝福》中包括“我”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我”的故事构成第一叙事时空,主要内容是“我”回鲁镇过年并遇到祥林嫂,祥林嫂的故事构成第二叙事时空。上述叙事片段是从以祥林嫂为主体的第二叙事时空重回第一叙事时空,为以“我”为讲述者的单一叙述,且更接近隐含作者的叙述话语,给两个叙事时空的共同终点带来深刻意义空间。第①和②句中是“我”所看见和听见的,其中的情感投入不明显,只有②句中的“拥抱”一词似乎有些温暖之意;片段中的③句却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反讽,白天的“疑虑”真的被“一扫而空”了吗?诸神真的在给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吗?与第二叙事时空中重点描述的祥林嫂遭遇和恰在此时的死去相比,明显地能感到普遍喜庆中暗含对祥林嫂命运的同情,指向对封建制度的控诉——这一主题至今已经被不同的后来者重复了千万遍。同时更多的是对祥林嫂的不觉悟的批判,即痛惜一个以“封建”命名的中国农村妇女的愚昧和麻木,这正是鲁迅式“国民性”批判的核心之一。
更进一步,从上文中天神的祝福来看,给芸芸众生赐福是群体化的,并非特意指向某一个体,但从文中来看,这一祝福的内涵却并非善良意愿,隐含作者以讽刺的口吻表达着对群体的不满,因为群体共同得到神的福祗的同时却是一个生命的默默结束。强烈的对比修辞意味着强烈的批判情绪。鲁迅的群体观与“看客”批判直接联系,《药》《示众》《阿Q正传》及杂文中的看客无处不在,对群体的不信任也是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重要表现之一。启蒙的困难,现代的难以实现,直接导致鲁迅对群体的怀疑乃至厌恶,而命名其为“看客”,之后虽然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认同无产阶级的力量,但在更多时候还是执着地表现对国民的不信任。就是说,只从《祝福》来看,鲁迅既不赞同祥林嫂,也不赞同戕害祥林嫂的“群众”,祥林嫂是国民性的麻木愚昧的代表,群体被命名为“看客”,这也是国民性重要特征之一,那么,鲁迅到底赞同什么?鲁迅的所有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杂文书信——都未说明。从各种文本各种表象之下所能概括出的,就是绝望。这也是竹内好率先发现的鲁迅的伟大价值之一——不是右翼和自由派冠名的“虚无”,而是绝望,成为鲁迅的主要特征。
其实,早在1921年的《故乡》的结尾,鲁迅就已经直接推出了他的希望——绝望辩证法,它意味着鲁迅的终极修辞的完成:改造国民性。“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叙事片段与上面所引《祝福》中的片段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相似,都是在第一叙事时空与第二叙事时空同时存在的结构中,最终回到第一叙事时空,此叙事终点建立在两个意义深远的对比之上:一是第一叙事时空的老年闰土和第二叙事时空的少年闰土对比,它造成了叙述人美好回忆的彻底破灭;二是同在第一叙事时空中我对少年闰土的快乐回忆与侄子宏儿和闰土的儿子的少年约定的对比,形成对绝望历程可能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恐惧,前一个对比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形态能否培养现代人的绝望,后一个对比意味着对孩子的未来的担忧。两个对比的产生,最终意味着鲁迅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向度彻底否定了希望,从而形成了这百年不衰的希望辩证法,看似说希望,实际在说绝望,但又在绝望中留下了希望的可能,最终却是希望是相对的,而绝望是绝对的。正如鲁迅引裴多菲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2](P183)一切都是虚无,这是鲁迅的绝望辩证法的核心。但他的绝望是一个哲学化的绝望,绝望是结果,同时也是过程,鲁迅更看重的是过程,所以会有不断的寻找和挣扎。
从鲁迅在《故乡》中的表述来看,绝望的符号意义是明晰的,都指向中国人的国民性——闰土式的麻木不仁与那个制造无数个闰土的千年不变的封建环境。阿Q、孔乙己和祥林嫂们的死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对应的真实事件,闰土从充满活力到麻木成“前现代”朽物的国民性代表更是比比皆是,都能让人们在此逻辑下走向绝望。鲁迅一直坚持的启蒙立场也是针对国民性而来,但这个“启蒙”经过鲁迅的叙事建构就不再是那么简单。启蒙的本意是给本民族的“前现代”之民灌输现代思想,其结局应该是光明的,但鲁迅式启蒙的结局却是复杂的,更多的是阴暗。鲁迅看似一生执着于启蒙,但一直不相信启蒙的价值和效果,甚至在去世前一个月的《死》中又推出了“一个都不宽恕”[3](P635)的决绝态度,那是对人性的何等不信任。鲁迅几乎把国民性扩展到所有人那儿去了,是什么样的信念能让鲁迅几十年如一日地执着?
如果跳出文本表层进入文本深层的主题结构来探讨隐含作者如何建构叙事,则会发现,这一“国民性”建构更多的是一套有预设前提的话语,和被神化的“鲁迅精神”一样都不具有真理性。尽管鲁迅的思考显然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逻辑在文化领域的机械投射,但鲁迅作为启蒙者的那部分却被鲁迅自己及后来者从政治、文学和思想方面不断强化,即由阿Q和祥林嫂们不断抽象化,形成了百年的国民性母题。从这一母题的叙事建构来看,鲁迅作品在认知上呈现出封闭性,与文本本身隐含的封闭性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固化了的鲁迅精神。从叙事表层来看,鲁迅的封闭性也是有迹可寻的,它最明显的表现是其小说人物角色的最终结局往往只有一个,就是毁灭;其封闭性还表现在毁灭的原因惊人的一致。就是说,从启蒙的意义层面来讲,鲁迅的文学文本的深层主题结构相当简单,即国民性母题,执著于中国人的精神改造,几乎所有的小说及散文、杂文都以此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国民性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面临不断的反思和质疑①可参见杨联芬:《晚清与五四文学的国民性焦虑》,《鲁迅研究月刊》,2003,(12);刘禾:《跨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国民性理论实际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种族主义殖民理论,而中国的国民性理论的始作俑者正是严复和梁启超。
二、自我的分裂与生成:绝望之环的叙事建构
梁启超作为政治和文化启蒙的集大成者,对鲁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前就已经摆脱了梁启超,如周作人所说:“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4](P447)
从政治科学转向文艺,似乎鲁迅选择了文学性,摒弃的是文学相对于科学和政治宣传的附属地位。或者可以说这是鲁迅与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差别:避开了唯政治论。梁启超的政治功利性在后来共产党的左翼文学那儿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延续,而鲁迅是在文学中蕴含了政治部分——是自然蕴含而非刻意,与其他多重意义指向相合,形成了鲁迅叙事的复杂和几乎无人可比的深刻。
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世界是“混沌”的[1](P14),鲁迅的复杂也正是其价值所在。竹内好所认为的鲁迅叙事世界的“无序”[1](P13)状态与“混沌”相应,同样代表着鲁迅一生的矛盾。我们看发表于1924年的《在酒楼上》的开篇:
①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
的家乡,就到S城。②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③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④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⑤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作为一个经典文本的叙事起点,这个叙事片断与《故乡》和《祝福》的开篇很相似,都是“我”的与现实极相合的游历,由某个机缘而回到家乡,并由此引入第二叙事时空。而且叙述人或隐含作者对家乡的感觉总是一开始就埋下阴影,第③句的“风景凄清”和第⑤句的“多事”已经直接表达了鲁迅常有的“多余人”感觉。故乡在鲁迅的叙事时空中始终是个异质化的存在,它在鲁迅的叙事中代表着过去,某种程度上映射着鲁迅一直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地点的命名也显示了鲁迅的奇怪的矛盾,主人公的家乡被命名为“S城”,为什么不像《故乡》一样以类名词替代专有名词从而避免命名?此处却又偏偏命名为“S”;如果“S”城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相干的小城倒也能显示鲁迅的虚构意识,但紧接着的种种描述直接显示这个“S”正是鲁迅的家乡绍兴。鲁迅曾主张汉字拉丁化,“S”正是绍兴之“绍”拉丁文第一个字母,这种西化的隐讳叫法也蕴含着那个现代的“我”。尽管隐含作者煞费苦心地绕了三十里,后来却很随意地露出的“绍酒”,不正是隐含作者的出生地的标志性符码?紧接着上个叙事片断的点菜话语:“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不正是活脱脱的孔乙己故地重游吗?隐含作者这样半掩半藏地为家乡“讳”,意味着其重点不在于这个命名,而在于他另有更深层的矛盾:“故乡”是哪儿不重要,故乡永远是自我生成的源头,同时是永恒的如骨梗在喉的存在。一个不断地与自我战斗的文学者鲁迅才会在叙事中留下如此多的自我斗争的蛛丝马迹。鲁迅所斗争之物可以外在于自我,也可以内在于自我,鲁迅自己甚至不断制造对立物并将其排除。如双重叙事时空中的两个叙事时空是对立关系,有“我”的叙事空间多是现实理性且清醒的绝望化空间,无“我”的空间是别人的故事,里面隐藏着另一个我,即作为历史的、对立物的我。再看《在酒楼上》遇上吕纬甫的场景:
此叙事片段中第③句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外貌描写,细看就会发现,那脸型、发型和神态都像极了是在描写鲁迅自己,随便找一张鲁迅当时的照片,就更会强化这种鲁迅在自我描摹的感觉。末句中吕纬甫对废园闪出的“射人的光”又多么巧地映射叙事起点的“我”看到废园时的“惊异”感。两个人从长相到心意居然都是相通的,这种奇异的巧合从何而来?其实它来自隐含作者的叙事建构,鲁迅化身的那个叙述人的思维是如何的缜密,他如何会留下这样多的破绽让读者去猜度?正像把《铸剑》中助人复仇的黑衣人的外貌也写得和他自己很像一样,他甚至是有意如此。鲁迅的一生充斥着自我与非我、自我与异质物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外部的,但更是内部的,如同鲁迅塑造了阿Q形象,阿Q精神不仅被鲁迅当成是全体中国人的“非现代”特质,同时也是鲁迅自身的另一面,这意味着他在不断地与自己斗争。
鲁迅身上的矛盾,那种“我”与“非我”“我”与异质物之间的对立,甚至被发展成类宗教的“原罪”意识,即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自己产生于传统文化的自责,既批判别人也在批判自己,反思中国的阴暗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阴暗,直至形成了一种宗教性“原罪”感弥漫于鲁迅的所有文本之中,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甚至书信,无不充满着绝望感。先知式的痛苦和无法把救世辞传播众生的痛苦堆积成越来越大的绝望。更痛苦的是他觉得连自己也无法超越。他所认为的传统文化的积习让他深恶痛绝,他一生力图改造的就是传统文化造成的各种“反现代”的特征,具体外化于他建构出的阿Q精神,但他自己却按传统礼仪给祖母葬礼,1903年回国还装假辫子,力主现代自由爱情却还是娶了朱安,且之后朱安一直作为原配长房存在着,与许广平却一直隐婚,不敢公开。作为革命者或文学者的鲁迅,这些事实都是无法绕开的痛苦甚至是耻辱,真如自啮其身的长蛇,以痛解痛,其痛自知。概言之,鲁迅的绝望就像一个永恒的痛苦之环,愈久而
弥新。这个“绝望之环”是不是鲁迅总以循环论看待中国历史和“国民性”的根源?汪晖即认为鲁迅的循环论认知观造成把现在也当成过去的经验来对待,变化被忽视[5](P163)。换句话说,鲁迅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静态的眼光看待一切,无论现实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绝望不变,变的只是绝望的具体方式。但是,鲁迅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着另一面:作为文学家的复杂又时时让他对这一判断作出质疑,那种异质物的对立在他身上奇怪地同时存在,且保持诡异的平衡。我们看在《在酒楼上》的结局:
①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②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③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这个叙事片断作为整个文本的叙事终点,和《祝福》一样在之前产生了双重叙事时空,“我”回S城的故事和吕纬甫讲述的故事(迁坟和买剪绒花的故事),“我”的叙事时空是隐含作者的“现在”,吕纬甫的叙事时空代表“过去”,过去和现在,展示出一个昔日的革命者在理想破灭与之后的庸俗化。叙事终点的到来是故事讲完回到第一叙事时空,同样以风景描写结束,里面夹杂着叙述人的感觉。第②句中居然会“倒觉得很爽快”,本来是一个革命者的理想破灭之后成为营营苟苟的世俗之人的阴暗故事,为什么会有解脱感?“我”的故事和吕纬甫的故事有什么关系?这正是鲁迅的复杂之处,鲁迅之所以伟大,也正因为他的意义指向不仅于一个破灭或解脱,再看《孤独者》的结尾:
①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②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③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④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⑤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孤独者》中同样存在着双重叙事时空,即以“我”为主体的第一叙事时空和以魏连殳为主体的第二叙事时空,到达叙事终点之时,叙事时空与故事时空合一,那个“我”实际指向作为隐含作者的鲁迅本身。第③句在悲痛之下突然出现了风景描写,不是悲痛,而是月亮发出“冷静的光辉”。为什么是“冷静”?原来悲痛在④⑤两句中,曾经“沉重”,有“愤怒和悲哀”,但⑥句中却显示悲痛突然被化解,以致“我”竟然毫无征兆地“轻松”起来,“坦然”地走在月光下。这种结局安排的巧妙与深意几乎所有的后继者都遥不可及,这正是竹内好所说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混沌之处。鲁迅不会给自己的作品一个过于明晰的终点,而是潜藏着各种可能,这种可能在鲁迅那儿也不是明晰的,而是一片“混沌”,他看到的也是文学式的隐隐的光明。对于百年来的各种接受者,其解释的可能同样是复杂的。再看这一叙事片段中,“清冷”的“圆月”与“轻松”“坦然”之下是鲁迅化身的隐含作者的“冷静”修辞,魏连殳在第二叙事时空中的形象是越来越消极的,对革命越来越失望,那种失望过于实体化而导致行动者精神的崩溃,而第一时空体的“我”却并未如此简单,而是在观察和隐含的实践超越了他,虽然同样失望但不放弃希望,月亮式的冷静的光明也不是因为已经找到了希望,而更因为“我”还有余力和能力去寻找希望,那个“希望”是什么,却正是混沌不清的。这种“混沌”,与鲁迅自我的分裂与重新生成逻辑有着隐秘的联系。之前的《在酒楼上》的双重叙事时空中的两个人也正是隐含作者的两面,“我”和吕纬甫相互映射,互为他者,觉得多余的是“我”也是吕纬甫,那个自比为“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到原地点的“蝇子”吕纬甫也是“我”的写照。《孤独者》通过一个革命者的死,结束了一个循环,生与死的循环,在鲁迅那儿是“希望-绝望”的循环,然后又重新开始,生的自觉的获得即寓意于此。《在酒楼上》等小说可以说是旧我与新我、自我与异质物之间的挣扎历程,鲁迅的选择也惊人的一致,都是让旧我死亡,新我重新“彷徨于绝地”,开始另一段绝望历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绝望之环。
鲁迅的绝望之下是一个诡异的矛盾平衡物,即启蒙的简单化指向与文学的复杂指向,前者是功利性的,而后者是多重向度的。启蒙者鲁迅是一个执着的国民性理论的建构者,文学家的鲁迅则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客。与现实相应对,鲁迅的矛盾更难以捉摸,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在日本不加入同盟会也不加入光复会,对那些暗杀团体,他更不参加,事实上他又和这些团体的成员关系很好。周作人对此的态度是无法理解[4]。或者鲁迅的这第三重怪异可以看作是对个体生命的珍惜,不愿为某个看似宏大的
目标牺牲了自己,不愿成为历史的祭品,而是要寻找更复杂的价值。这种对个体生命的过于珍惜,或者可被称为“怕死”的怯懦行为,该如何解释?它源于西方现代思想中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还是来自中国小农伦理中与自私相混杂的对生命的敬畏?这是迄今为止都很难分析的问题,鲁迅的混沌之处也可见一斑,他的文本表层所对应的深层来源,恐怕鲁迅自己也不清楚。混沌是文学家自我的常态,拒绝过于明晰也正是鲁迅作为文学家的重要表现之一,他不愿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瞿秋白那样斩钉截铁地宣称启蒙的目的是建立新中国,也不会像左翼作家那样直接把启蒙当成发动革命群众的工具,在他眼中,这个世界无比复杂,如同老子和孔子的哲学和思想世界,不可穷尽的世界在一个天才那里就会生成不可穷尽的自我和不可穷尽的语言,最终建构出一个不可穷尽的叙事。或许正是这种近于道家的混沌、高度的批判性和超常的自省能力造就了鲁迅式的绝望之环。
三、结 语
竹内好预言了鲁迅去世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停滞[1](P18)。他认为鲁迅过于强大的身影是对现代文学的遮蔽,这不是一语成谶而是事实的确如此,鲁迅之后的现代文学几乎完全笼罩在鲁迅精神之下,“国民性”一维直到21世纪都属于主流地位。同时“鲁迅精神”背后是一个日渐被固化、被神化和被革命化的鲁迅。今天我们对鲁迅的认识越来越突破政治化的“鲁迅精神”的限制,延伸到人性、民族性、现代性和文学性等更复杂的领域。本文从叙事学入手,发现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可超越的原因之一,即鲁迅的独特叙事模式,且把他们这种双重叙事时空同时存在的结构方式称为 “彷徨体式叙事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首创,鲁迅式的第一时空体与第二时空体的共存对于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运作有着很大的方便。从形式层面来看,由隐含作者化身的“我”直接操控第一叙事时空体,方便隐含作者直接抒情和议论,以最自然的方式进行强大的叙事干涉,第二叙事时空体为被对象化的“非我”或异质物的故事,它代表着历史和回忆,通过回忆而否定现实,最终回到第一叙事时空,在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否定中完成一个叙事的“绝望之环”。从意义层面来看,双重时空并存的“彷徨体式叙事模式”也代表着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整体性变化趋势,即越来越隐藏希望和召唤的冲动,犹豫越来越明显,彷徨式思路也是去青年化的思路,它应该意味着成熟而不是保守,隐含作者/叙述人投射的“我”的存在与作为“他者”的“非我”的存在互为对立物,它是鲁迅的文学自我与启蒙自我不断斗争的结果,最终形成一个无限接近文学家的、复杂和冷静的鲁迅。同时也应该看到,“希望-绝望”辩证法和国民性批判的稳定性造成鲁迅叙事的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隐含的,他的文学天赋让他不断避免简单化,其文学文本表现出远超国民性批判的多维意义向度,这一复杂向度借助双重叙事时空体得到了更好的实现,隐含作者、叙述人、第二叙述人和人物角色等作为不同层次的自我的投影,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超越,最后的叙事终点是作为隐含作者的鲁迅完成了“非我-新我”的超越,完成了与鲁迅式世纪辩证法同构的“自我分裂-生成”的辩证之环。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与鲁迅同时代及追随鲁迅的知识分子做不到的,它与鲁迅的真正文学特质遥作冥冥之合。竹内好一开始就说:“我的目标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1](P8),甚至直接说,“先验地把鲁迅规定为一个文学者”[1](P129),同时竹内好也承认,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实际是始终合一的,鲁迅的绝望正因为混沌才总是如此强大,文学面对政治的无力也正生成了文学的无用之大用。永恒的矛盾使伟大的思想与高度的文学性结合在一起,铸就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
[1]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孙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鲁迅.野草·希望[A].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死[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A].钟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汪晖.反抗绝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戴庆瑄]
刘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上海 200241
I210.96/97
A
1004-4434(2016)10-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