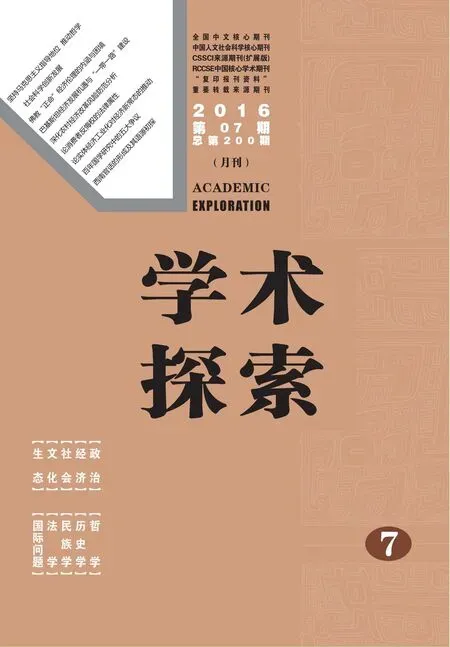主体性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弊端及哲学分析
邸俊燕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主体性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弊端及哲学分析
邸俊燕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主体性理论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系置身于“主体—客体”对象性关系的认识论模式下,以知识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规训式教育作为保证教育实施的手段,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人的失落、生命的遮蔽和生活的疏离。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活动必须突破原有思维模式,以“主体间”思想作为其哲学基础,实现主体式交往向主体间交往的转换。
主体性;交往;知识教育;规训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非单向度的“教授”或“接受”就能完成,而应放置在一定的关系和互动之中,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对话与沟通中共同创造意义、提升信仰、形成价值追求。在主体性理论影响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受到对象性关系的认识论模式的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置身于“主体—客体”关系模式之下,教育者在发挥主体性的同时忽视受教育者自身主体性的发挥,单个主体从个体的视域出发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考虑到其他交往主体的存在,没有关注其他主体在教育中的主体性的发挥,也就无法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有效性。因而,转换原有的思维方式,从哲学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弊端,打破线性关系模式而从多元关系的向度出发发展交往关系,使单一主体的交往走向多元主体的共通融合,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交往的前提。
一、主体性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及其本质
“主体性也就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特性。”[1]纵观哲学界对主体性问题的理论成果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主体性问题的关注,迄今为止,关于主体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教育者主体说、受教育者主体说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为主体说。从以上三种观点所表达的基本含义来看,侧重点不同,但从内在逻辑上分析,却都遵从线性的思维模式,都是“主客二分”模式下的产物。
从古到今,关于道德教育的教与不教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从道德生成的内在机制探究,首先需要道德知识的增长和道德思维的增强,因此‘道德是可教的’,其次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道德境界和道德能力的提升,因而道德又是不可教的,或者准确意义说‘道德教育是有限度的’。”[1](P112)这就是说,道德教育始于道德知识的教育,而道德知识内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才是道德教育的终极目的,因为在真正的道德实践中,决定道德实践的最终因素在于道德意义的自我获得。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受教育者个体发生的过程经历了“知、情、信、义、行”几个阶段。其中“知”是基础。“知”包括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知,从知识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储备以及在知识储备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认知能力的提升过程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贯穿相关的知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获得是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的积累,人们难以区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善和恶,也就难以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判断能力的形成更为重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累积,受教育者获得公认的价值和标准,在更深的层次上,受教育者通过自身的思考和实践,实现了价值和真理的内化,获得了正确的判断,实现了思想政治素质的自我升华,形成了判断能力。在面对问题时,他不仅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和感受,而且是为了特定的理由和信仰才这么做,能够经过理性思考后做出价值判断,体现出知识和思维向现实生活迁移的能力。
但是,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单纯定位于知识教育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往的本质是价值的交往。从交往过程看,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知识的传授是交往的表象,也是交往的最初阶段,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授,使学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终极意义——人的自我实现,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的。从受教育者自身来看,就是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也就是从潜在的思想道德素质向现实素质的转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政治自觉,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即由知之到信之的态度或情感的养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对于受教育者的价值不仅在于由不知向知的转化,更在于从知到行的迈进,即实践。而实践的过程,正是受教育者对于所获得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自我体验,是知的素质向行的素质的自觉转变,是教育交往的最终目的,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在主体性理论的指导下,无论是教育者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受教育者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缺乏交往中的意义融通和交流,其本质上都是“知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教育交往模式把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看成是向受教育者灌输思想政治规范的过程,重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传递;而以受教育者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又将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看成是智力训练过程,重在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获得。无论是以教育者还是以受教育者为单一主体的交往过程,他们在交往中的共同点在于重知识而轻价值,重外在形式而轻内在情感,割裂了人的知识情感的统一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特别是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中的作用,因而都是一种以“知本”式为特征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从对于教育结果的现实评价来看,更多的是沿用“知识文化观”而不是“智慧文化观”的评价模式,最终只会扼杀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本真,使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的人沦为教育的“旁观者”。
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交往模式中,教育的本质被定义为知识的传递,而规训就成为保证知识有效传递的手段。由此,“教育成为一种事先谋好的、科学或艺术地控制人们心智的技术,成为一种人们必须服从的机制”,[2](P4)目的是将受教育者塑造成驯服的、被动的、适应现存压迫结构的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教育者是内化了“压迫者意识”的压迫者,其任务就是作为知识的存储者、任务的发布者、权利的拥有者以及规范世界进入受教育者头脑中的方式。受教育者则被当作教育过程中的客体,接受以该社会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知识,适应该社会的行为模式,失去了人成其为人的生命特质:批判精神与创造力量,从而淹没在“沉默文化”之中。受教育者“越是认为自己一无所知,越是自我否定,越是依赖于教育者的权威。在这种教育专制中,教育成为一种巨大的监护、督察、修正、压制个人的力量,并且这一力量是具有绝对权威的、无微不至的。它力图使人归顺于一种设计好的道路,处于一种被规定的发展之中。教育对人的支配、处置、压制、型塑等是其主要特征”。[2]这是一种霸权式的宰割,体现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持有的强烈的塑造心态,而这种塑造,是教育本身赋予教育者的,而教育者就成为实际的塑造者。首先,规训的道德价值的灌输性。由于教育者的强烈的塑造心态受到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所赋予的教育权利的保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成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道德灌输过程,意识形态的钳制话语成为教育交往活动的内容。其次,规训的人格人性的设计论。这种设计是把人塑造成某种权力意志所需要的工具性的人,导致人格的培育遭到忽视,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化人实现外在教育目的的工具。
二、主体性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弊端
传统认识论哲学延伸到思想政治领域并构建了一个完整而高深的“基因图谱”。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教育,教育交往成为对象性活动,教育直接指向的是知识的获得而非知识的价值化或者情感内化。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教育者习惯于把科学主义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贯穿于课程的决策和设计、课程内容的选择基准之中,主观地从外部设定一个高而又高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机械地对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坚持用“我打你通,我说你听”的方法硬性灌输,教育内容变得不切实际,而在考核中,也是惯用一种量化的手段——考试去衡量知识教育的最终结果。而受教育者出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教什么、怎么教、如何教?教育者完全把持着整个教育过程,把教育内容单向灌输给受教育者成了教育者的最高责任,而受教育者只需接受教育者的“教诲”就是完成了任务,从而形成了主导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化的、便于量化的秩序系统。整个教育过程沦为冷冰冰的压制和灌输,教育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受教育者压抑个性,充满着泪水和辛酸。教育者以为这样的教育就达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教育是关乎人的精神发展的内在实践,是与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的。因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交往活动的实践与其他社会性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性实践过程中所面对的是物,因而形成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对象性实践关系。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具有各自人格特征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用对待物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关系,就会出现“撇开了实践主体之间的物质关系或社会关系,使实践中的主体、结构和关系单一化,将实践活动自觉不自觉地视为没有‘主体—主体’介入的片面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3](P31)实践主体之间的物质关系的思想应用到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体—主体”关系被诠释为“主体—客体”关系。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缺失,成为被支配、顺从的客体;而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绝对化和权威化,凭借知识和话语的优先地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知识情感的双向互动交流过程沦为教育者单向指向受教育者的直线式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不再是自由、平等,不再是“诗意的栖居”,而开始沦为“一言堂”式的布道、训练甚至是强制,人被物化、被对象化、被规训、被压制,丧失了他本该有的独立尊严与价值。教育的意蕴不再是“成人”而悲惨地沦为“育器”,充满人性魅力、促进人们精神生产和进行自由创造的教育活动却在培养人的旗号下丧失了个人的自主、独立、自尊与个性自由。这种教育实践最终扭曲了教育的功能,把应然的人际间交往变成了单向的灌输,最后必然造成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导致自我中心、情感疏远和教育意义的丧失。其次,从知识和能力素质的关系来讲,知识的获得不能转化为直接的能力和素质,知识只有通过内在的知、情、信、意、行的内在体认机制的合理转化而与个体原有素质相结合,才能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下生成人的基本能力。这就说,教育对象的由知而行并不是直接的,还取决于诸多现实的条件,有很多影响的因素。而单方面的知识灌输和空洞说教只会形成“假接受”,教育者难以形成思想政治的相关认知,更难以内化为自身品质,只会导致言行不一和普遍的虚假。杜威认为:“所谓知识就是认识一个事物和各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决定知识能否适用于特定的环境。他认为,如果将知识与应用隔离开来,则知识就完全在意识之外,或者变成审美沉思的对象,这种沉思的态度具有审美的性质,但却不是理智的性质。”[4](P10)忽视体验、践行和主体性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违背了教育交往过程的本质要求,自然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效果。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过程应该是由“知道”“悟道”再到“体道”的过程,这一切依靠智育的方式是无法企及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论述了人类实践中知识因素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一切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所有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一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P60)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智育化倾向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弊端正是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特性的理解偏颇和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的教育偏废而导致的。这就要求把教育理解范式从“知识传输”转向“思想品德实践”,实现从“制器”向“育人”的转变,即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并非是教人以“知”,而是启人以“思”。因此,主体性教育交往模式试图通过智育教育来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显然是片面的。最后,从道德发生机制来看,人的思想品德发展蕴含着人对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认知和感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过程,而人的这种反应,并不是单纯由世界自发地给予人的,它同时也是人以主体的方式对世界的直观的、思维的乃至心理的主动追求和把握的过程。在人的自觉的道德建构活动中,意识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意识的作用,人在分析已有道德生存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理解文化社会环境和社会的道德发展与融合的要求,通过不断政治社会化,形成自身对道德的内在需要,从而形成一定的价值选择能力。而知识的灌输是压制接受的方式,压制的结果必然不能萌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感应,即便是伪善的接受,也是表面的出于某种压力的应和,一旦出现道德选择的机会,要么摇摆不定,要么走向极端,。
三、主体性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弊端的哲学分析
作为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认识论哲学是一种以主客二元对立为主要标志的“主体性”哲学,“从笛卡尔主客二分的二元论开始,经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而到康德,是个探讨主体和客体联系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不断得以张扬的过程”。[6](P227)从本质特征上对主体性哲学进行分析:首先,强调“占有性”。主体性哲学从个体的“我”的角度定义主体性,把主体的存在与单个主体的“共在”对立起来,把自身以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强调的是对客体的支配和客体的为“我”所用,主体的“占有性”的人的关系把人与人关系指向为对象性的“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物与物的关系。其次,“自我”主体性。从“类”的视角看待主体的,把主体看作是简单的某一“类”,而在主体关系中的主体是对应的,是与客体相对应的主体,这种简单的划分,使得主体成了抽象意义上的孤立的、单独存在的主体。最后,理性主义至上。表现在教育上的工具理性主义以知识为基础,通过非人格化教育,实现对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的控制。
在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因为“确定主体的优先地位,有了对主体的肯定和主体认知的肯定,就有了衡量客体的标尺。主体是自明,不需要证明的,客体是主体活动指向的对象,主体的主体性是活动的出发点和条件,客体是主体加工的对象,是活动的终点,这样主体就优先于客体”[7]。于是,教育活动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交往关系就成为一种“改造”关系,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是客体,主体处于支配地位,客体处于从属地位,客体要服从主体的改造,教育者就是支配和发号施令的改造者,受教育者则沦为顺从和受支配的被改造者,教育交往活动就演变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训练式改造和强制性塑造。“这一过程颇似一对华尔兹的舞者,一个自主变动姿势、步伐的‘主体’支配着一个顺从旋转的舞伴‘客体’,呈现单一中心结构。‘主体—客体’对象实践观从一开始就将教育者奉为主体,似其为真理的化身,有先在的话语权,成为绝对权威,充当‘灵魂工程师’”。[8]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人的生存本质的丧失。传统认识论视野下的“主体—客体”认识论模式秉承对象性的实践观,强调的是“主体—客体”之间的改造、征服和利用的关系。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看作是“主体—客体”关系,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本真的存在论关系彻底让位于认识论关系。于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就成为一种简单的对象性关系,控制就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力量,而控制意味着对人强行的压制,意味着被控制者个性人格的丧失,“控制是双方力量的对峙抗衡,以一些人强行压制另一些人,并有计划地安排,怎样使这种对抗着的力量在控制者任职期间相互作用”,因为“控制并非爱,控制固守着人与人心灵无交流隔绝状态的距离,使人感觉到控制者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在使用诡计,并以被控制者个性泯灭为价值”。[9](P5)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的控制中,人被物化和工具化了,人失落了,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成为一种改造、控制和型塑“物”的活动,本该是作为教育主体的受教育者沦落为一种被训练和规训的“物”,“他不是他自己,他除了是一排插销中的一根插销以外,除了是有着一般有用性的物体外,不具有什么真正的个性”。[10](P42)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中生命体存在的遮蔽。主体性哲学的关注视点局限于主体—客体的关系范畴之中,从本体论层面来看,缺乏从“主体—主体”视角的理解,因而也就看不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本身是关注活生生的生命体的存在,然而在理性主义的宰制之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成了一个规训的过程,一个使教育中生命被遮蔽的过程。理性主义的科学化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了精致规训技术控制下的活动,受教育者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生产必须遵循统一的要求,必须遵循共同的标准,必须达到一致的目的,总之,受教育者的一切都必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然而,“‘规训化’教育的恐怖就在于对生命价值自主性的轻视。教育成为一种事先谋划好的、以有效方式控制儿童心智和身体的技术,成为一种必须服从的训练机制”。[11]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规训化,使教育中那富有活性的生命成为了僵死的和呆板的,使那充满着主动性的生命成为了机械的和被动的,使那充盈着创造性的生命成为了苍白的和封闭的。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与生活世界的背离。认识论哲学视野中的主体是占有性个人主体,“我”作为主体,“他人”都是“我”作用的对象,都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和手段,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降格为人与物的关系甚至物与物的关系,导致人性的扼杀和主客体的分裂。思想政治教育是精神教育,是人格教育,关乎人的成长。从交往本身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充满意义的对话和价值的融通。“主体—客体”关系崇尚理性,膜拜科技,这种关系应用于交往活动中,使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本身理性化、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交往就为科学世界所掌控。而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不同,“科学是枯燥的,生活是诗意的;科学奉行本质主义,生活主张生成性思维;科学是知识,生活是体验;科学是认识的,生活是实践的”。[12](P49)因此,一旦以理性的尺度,以理性的唯一标准,以理性崇拜的心态,来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也就不再是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交往也就不可避免地与生活发生了断裂。
认识论哲学的缺陷和矛盾,使它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系置身于“主体—客体”对象性关系的认识论模式下,以知识教育作为主要内容,以规训作为保证教育实施的手段,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失落、生命的遮蔽和生活的疏离。因此,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交往模式,必须突破原有思维模式,以“主体间”思想作为其哲学基础,实现主体式交往向主体间交往的转换。
[1]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张立杰.比较与整合:中国当代“主体间性”道德教育理论的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金生鈸.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卢风.人类的精神家园[M].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7]金生鈸.超越主客体:对师生关系的阐释[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8]闫艳.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7.
[9]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
[10]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1]金生鈸.“规训化”教育与儿童的权利[J].教育研究与试验. 2002,(4).
[12]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The Drawbacks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DI Jun-yan
(School of Marxism,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710054,Shaanxi,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or and the educate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fits in the epistemology of“subject-object”.In this mode,knowledge is the main content,disciplines a means to ensure its implementation,which results in lost humans,covered life,and alienated living.Hence,communi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ust change its original thinking pattern based on the inter-subjectivity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etween subject-and-object to subject-and-subject.
subjectivity;communication;knowledge education;discipline
〔责任编辑:李 官〕
G410
A
1006-723X(2016)07-0031-05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1YB098);西安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2013SY11);西安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15SZ316)
邸俊燕(1981—),女,陕西三原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交往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