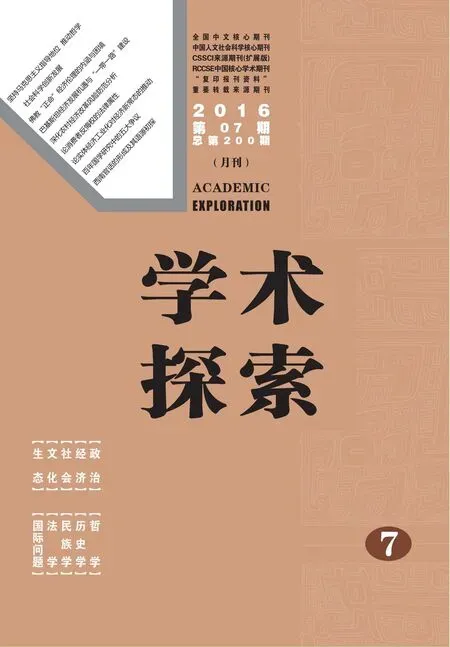语言生态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母语磨蚀——以云南石林大紫处村为例
冯 佳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语言生态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母语磨蚀——以云南石林大紫处村为例
冯 佳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城市边缘的彝族社区语言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彝汉语言接触频繁。受汉语及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云南石林县西街口镇大紫处村语言社区不同年龄层次群体的母语技能出现退化、磨蚀,本文主要从语言生态视角探讨语言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大紫处彝族母语磨蚀的影响,并以其为基点试图解决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少数民族母语退化问题。
语言生态;彝族;语言磨蚀
大紫处村是云南省石林县西街口镇下属的一个自然村,海拔2037米,国土面积 15.23亩。全村有农户250户,乡村人口990人,该村以彝族为主,是汉彝混居地,其中,汉族306人,彝族684人。大紫处村的彝族皆通汉语,其所使用的彝语为撒尼彝语,村中汉族有少部分通彝语。我们前期对大紫处村彝族在不同交际环境中语言使用、语言选择、语言态度等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大紫处村彝族母语保持良好,但不同代的撒尼人在彝语语音发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村里设有小学,为彝族孩子接触和学习汉语提供了保障;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青年彝族外出求学、务工的趋势越来越强,对于汉语(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和使用更加理性,汉语能力较为突出;不同语境下,大紫处村彝族对彝语与汉语的使用有不同分工,彝汉双语人在村里及家中主要使用彝语,在村外及与不懂彝语的汉人交际时会根据汉人语言情况选择使用汉语方言或是普通话。在调查中我们还观察到,受到语言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影响,大紫处村彝族母语能力尤其是中青年彝族的母语能力在强势语言的影响下初步呈现出退化、磨蚀的现象。
穆尔豪斯勒(2003)指出,“语言环境”涉及语言与现实世界和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等方面;世界上现存的各种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1]语言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语言的生态环境(linguistic ecology)。语言的生态环境,是指以语言为中心,对语言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元的空间环境体系。它一方面包括了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语言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也包括语言本身及语言的主体即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微观环境因素。目前,由于语言与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语言的生态环境可视为是由语言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的综合。本文将以大紫处村彝族的语言为考察对象,从语言的宏观生态环境和微观生态环境两方面来分析语言生态学视野下少数民族母语的磨蚀现象。
一、语言的宏观生态环境与彝语母语磨蚀
语言的宏观生态环境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少数民族而言,民族人口数量、生活地域封闭性、生活方式和经济发达程度、生活地语言和文化的传播方式、受教育的程度、本族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往中所占有的地位、国家对此民族及民族语言的政策、民族的人口年龄结构、宗教、文学、民间传说等都囊括在语言的宏观生态环境下。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民族语言的生存和延续。
(一)分布格局与彝族母语能力磨蚀
彝族是云南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云南彝族支系众多,自称、他称繁杂。主要的支系有诺苏、纳苏、聂苏、罗罗、腊鲁、撒尼、阿细、阿哲、葛濮、朴拉、勒苏、他鲁等。石林县境内的彝族有撒尼、阿细、白彝、黑彝、阿彝子等支系。石林彝族中语言文字保留最好的支系是撒尼。它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撒尼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阿细彝族主要分布在板桥镇冒水洞和大可乡的小河新村,他们保留了语言,没有文字。白彝支系主要居住在路美邑、干龙潭、芋头斗以及大可乡的岩子脚、小河新村。白彝已经转用汉语,语言处于失传状态。黑彝主要分布在西街口镇威黑村,圭山镇亩竹箐、红路口、格渣、石字场,也是处于有语言无文字的状态。阿彝子支系主要集中在石林镇爱买龙村,本民族语言已基本失传,已转用汉语。
石林境内的部分彝族支系已经发生了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如白彝、阿彝子,他们已经自愿或被迫地、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转用了交际功能更强的汉语。只有撒尼人依然保持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可见,石林境内的彝族中,撒尼人的母语保持明显优于其他支系的彝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相比石林境内的其他彝族,撒尼人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相对而言不够开放,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较落后。闭塞的分布格局无形中保持了撒尼人母语生态环境。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撒尼人传统聚居区格局发生了改变,其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得到了改善,其母语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
(二)人口比例与彝族母语能力磨蚀
语言使用状况的变化与不同的语言群体人口比例的改变有着密切联系。就此,我们初步考察了石林大紫处、路美邑、岩子脚、威黑、冒水洞等几个彝汉杂居行政村的人口状况,见下表1。

表1 石林彝汉杂居行政村的人口、语言状况
通过对大紫处、路美邑、岩子脚、威黑、冒水洞等几个行政村的彝族和汉族人口状况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路美邑、岩子脚两个行政村汉族人口已经占了绝对优势,但这两个村的彝族语言处于失传状态,都已经转用为汉语了;而在威黑、冒水洞两个村,彝族人口占了绝对优势,相应的,威黑村的彝族尽管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仍然保留了彝族的语言;冒水洞的彝族主要由两个支系组成,一个是阿细,另一个是撒尼,阿细人口相比汉族人口数量优势并不是很大,他们保留了语言,没有文字;但是较之汉族人口,居住在冒水洞的撒尼人占了绝对优势,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字。至于大紫处,彝族人口是汉族人口的一倍之多,居住在那里的撒尼人是石林彝族语言文字保留最好的彝族支系,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文字。
石林彝族的人口及分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区域内不同语言群体的人口比例,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语言的使用状况。不同语言的通行、使用范围以及使用程度往往跟语言群体成员的数量有着密切的关联,占人数优势的语言群体其语言容易获得较强的使用功能。人数较少的语言群体,其语言在使用上容易受到限制。
(三)语言群体失散与彝族母语能力磨蚀
语言具有社会性、民族性,每种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群体,若该群体消失,那么该语言也将随之消失。语言群体的消失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语言群体灭绝;二是语言群体失散。语言群体失散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语言使用者被迫离开原居住地而与其他语言群体混合,在获得新的语言的过程中造成的包括语言在内的群体特征和传统文化的消失,例如在我国,畲族有近百万人口,但由于各种原因,散居在浙、赣、闽、湘、粤、桂等省区,形成了众多的语言孤岛。现今,99%的畲语区已被汉语方言同化;其二是发生在语言使用者原居地,由于大量外来者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群体的生存状况,致使当地群体的群体特征和传统文化随之丧失,例如中印边界藏区的僜人所说的格曼语,在藏语、汉语、达让语的包围下,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由于民族间的婚姻关系,有的家庭已不再使用格曼语,语言传承出现断代,继而引发语言走向濒危。
语言群体的失散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态环境会受到不同层次的影响与冲击。在石林的彝族村寨中,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以及外来汉族人口的增加,不可避免地给当地的彝族语言带来冲击。当人数较少的本地彝语群体淹没在外来的汉语群体之中时,他们的语言就有可能失去地区通用语的地位,让位于使用人数更多的汉语,而且在本族群体内部的使用也可能逐渐被削弱,从而最终导致语言群体的失散。某种角度来说,少数民族双语生活的构建也反映出民族语言群体特征正在发生的变化。
在不断深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大紫处村也由一个相对闭塞落后的村寨变得开放与包容。彝语使用者外出求学、务工以及汉族外来者的加入改变了当地群体的语言状况。作为彝族母语的彝语,其传承或传播大多采用个体小范围自然交流来实现。基本上,大紫处村彝族都兼用汉语,只有少数年长者只能用撒尼彝语进行交际,这是汉语历史传播的结果。历史上,汉语常常作为一种强势语言被少数民族主动地学习和使用,往往少数民族在同汉族的长期接触过程中大都会去主动学习和掌握当地汉语,从而能够适应并融入主流文化中。随着大紫处村的彝族交际交流范围的拓展,学习和使用汉语以及汉文化成了他们的生计需要,从而也使他们对其生存文化环境做出主动适应,语言模式由最初的一元母语模式向二元彝汉双语模式转化。
(四)汉语普及的环境与彝语母语磨蚀
汉语在大紫处村的普及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来加以实现:其一,通过语言的自然传播来习得汉语,大紫处村的彝族与当地汉族自由交流中自然习得汉语官话方言;其二,在国家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下,通过学校语言教育有意识习得普通话;其三,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下,对汉语的自然习得。
汉语方言及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在大紫处村的传播与普及改变了大紫处村彝族的语言生态环境,汉语必然会与大紫处村的撒尼母语形成竞争。我们参考马学良先生的《撒尼彝语研究》编写了撒尼彝语200核心词,[2]对大紫处村的受访者进行了调查与测试,要求被试即时用彝语表述调查表中的词语。调查结果显示,很多被试已经不能够即时用母语来进行表述,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母语能力退化程度越高,大紫处村村民的母语能力退化与其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如下表2所示。

表2 大紫处村彝族母语能力退化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关性分析(N=168)
对表2进行分析可知,大紫处村彝族的母语能力与其受教育层次高低有相关性,受教育层次越高,母语磨蚀程度越高,而相应的汉语程度越高。汉语方言及汉语普通话的传播、普及与使用对彝族母语能力的影响十分明显。调查发现,接受过汉语教育的彝族青少年汉语能力呈上升趋势,而其母语能力呈现下降趋势。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其语言里已经开始掺杂大量的汉语借词,有些母语发音也受到汉语语音的影响。考察老、中、青三代人的彝语发音可以观察到,有些彝语特有的音已经在发生变化。学校作为汉语传播的阵地,在语言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学校教育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是汉化教育,得到强化的是汉语、汉文化、主体民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学校的汉语推广与普及使得彝汉语言融合的步伐也随之加大。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语言传播速度加快,传播方式多元化,少数民族可以通过新兴媒体接收信息,同时也自然习得权威媒介语言与语言规范。
二、语言的微观生态环境与彝语母语磨蚀
语言的生态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包括人的心理、生理因素等)相互交叉渗透、融会贯通的复合生态系统,也可视为是由语言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的综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大爆炸,语言现代传播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而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下,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也会随之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时代要求。
(一)信息的大众化传播对彝族母语的影响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快速,互联网通用语呈一体化发展态势。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的民族共同语承载了大量科技、文化信息,学习好普通话这一交际交流媒介就等于掌握了通向信息社会的密码。大紫处村彝族对于学习和掌握普通话的主观愿望较强,期望值也比较高。绝大多数被试者认为学好普通话能够方便与外界交流,外出打工时能够方便找到工作。
信息的大众化传播,加快了汉语的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使得汉语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汉语的地位都牢不可破,尽管国家有一系列政策对民族语进行了保护,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使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使得民族共同语言的地位逐步缩小范围,成为一个社区或者家庭内部的交际语言。
在大紫处村,随着通信设施的完善,很多人由原先的只会一些汉语方言变成既能说汉语方言,又能讲普通话。在与汉语的语言接触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汉语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彝语形成一个正向的压力,使得大紫处村村民主动学习处于优势地位的汉语以提高竞争力。大紫处村的彝族基本都是双语者,但是彝汉双语影响却不是双向的。村民对汉语的学习比较积极与主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语言所产生的新词已经进入大紫处村彝族的交际领域,尤其是年轻人的言语交际系统,庞大的数据体量与丰富的信息类型,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社交网络等影响着大紫处村村民的生活,改变着大紫处村民原有的语言生态环境。
(二)语言生态环境的改变与彝语母语态度转变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紫处村彝族封闭的生存状态被打破,在外来强势文化冲击下,作为交际交流媒介的语言首当其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通话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自然地占据了有利地位。
在“对普通话学习的态度”上,82%的被试都希望自己能说标准的普通话,对学校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持肯定态度。在“保护本民族语言”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有过半的受访者表示需要保护,需要语言传承,有部分受访者认为顺其自然,能保留与传承固然好,实在不行也没办法。只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无所谓。①这少部分人主要是已移居县城或省城,而且有些家庭呈现出民族语言逐代消失的现象。
对于彝语母语的期望多数被试表示,母语主要是家庭内部或者村里同民族间交流使用就可以了,在外上学或者务工还是要选择汉语作为交际工具。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紫处村彝族对汉语以及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汉语的被动或主动选择,使得彝族母语功能变得弱化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语言生态环境的改变与彝语语音系统内部的调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方言也呈现出边缘化趋势,而少数民族的双语社区及双语人也在缩小与减少。汉语的国内国际传播,促使一些年轻的少数民族对非通用的民族母语以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主动地抛弃。在这个语言竞争的过程中,民族语内部也在进行着调整与适应,语言系统内部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对石林大紫处村村民的语言调查显示大紫处村的撒尼彝语隔代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三代相比第一代,声调上有了一些变化,第一代的[33]调到了第三代有的还是[33]调,有的变成了[31]调,[31]调有的变成[33]调,有的还是[31]调;声调情况比2001年孔祥卿等人的调查显得还要复杂一些,有时出现曲折调。大紫处村的撒尼彝语,元音和辅音都有不同的变化。例如,对于辅音而言,有的脱落,有的清化,对于元音而言变化又更复杂一些,鼻化元音有朝非鼻化发展的趋势,有的元音发音时比较第一代的发音,舌位下降,紧元音松化,但同时也有松元音紧化的现象发生,总的看来,紧元音在减少。很多特色音被相对比较容易的发音方式所取代,比如:第一代的唇滚音[β]到了第三代直接变成了浊辅音[b]。
语言生态环境的改变加大了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间的竞争力差距。一方面,权威官方语言汉语普通话通过大力的推广以及各种传播媒体强化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使用的范围,提高了其与民族语竞争的优势,民族母语的使用空间受到挤压,逐渐退缩到更小的家庭或者社区范围。另一方面,民族语本身在传承及传播过程有些自身缺陷。有些语言因为缺乏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及标准给其传播带来了障碍。而有的语言本身有其相应的文字,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承,在众多的新生代中,出现了普遍的能听说母语,却不能读写记录母语的文字的状况。例如在对大紫处村语言生活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爷爷辈能熟练地听说读写母语及文字,到了孙辈,能听,基本能说,①有些话语不能像祖辈一样准确地用彝语母语表达,而采用汉语词进行表达。不能读写。加上民族语的传播与汉语传播比较起来仍然无法突破小范围的人际传播瓶颈,在与汉语的语言竞争中形成了强者越强弱者更弱的趋势。随着新生代少数民族“汉化”趋势的加强、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在坚持国家语言政策前提下增强少数民族母语的语言竞争力、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以传承,保存其所负载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
三、结 论
石林大紫处村彝族母语磨蚀只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少数民族母语磨蚀的一个掠影。通过对大紫处村原住彝族母语能力的观察与研究,我们至少能看到这样一些现象:一是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语言的生态环境亦发生着“共变”。城市的扩张迫使城市边缘的民族社区语言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母语的保持与传承;二是城市边缘少数民族社区语言出现单极化发展趋势;三是城市边缘少数民族母语使用出现代际断层趋势,族群年轻一代母语能力有减弱迹象。
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打破了少数民族原本的分布格局,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护“语言”而去阻止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去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不走上濒危的道路。如果我们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那么少数民族母语磨蚀就不会是社会城市化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首先,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位”。语言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发生着“共变”。美国语言生态学家萨利科科·萨夫温指出:“生态环境是语言演化和形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3](P171)语言生态的变化是复杂多样的。在语言生态系统中,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生态位。就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而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因生态位即将丧失而处于濒危状态,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发生了语言转用,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因语言接触其活力正在减弱。石林彝族社区的不同的语言表现给我们提供了少数民族语发展的几条脉络。白彝支系、阿彝子支系的彝族母语已经发生了转用,阿细支系、撒尼支系彝族语言处于语言兼用状态,只是相对而言,撒尼人语言文字保持稍好。不同的民族语言处于不同的语言生态位,即使是同一民族语言内部也有分化,如石林的彝族语言。作为语言研究者,我们需要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所处的语言生态位,制定与其相应的语言生态政策。尤其要重视处于语言兼用阶段的少数民族语言保护。要准确把握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位,需要整合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资源(包括已有的研究成果、专业的研究队伍等),加大财政支持,重新深入民族地区,做好田野调查,尤其是跟踪调查。
其次,建立完善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监测与评估体系。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数据库。该数据库除了语言的本体描写外,至少还应该涉及:一是该民族语语言分支情况、数量、人口分布、使用人数等;二是一定时期内影响该民族语的环境要素记录,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语言使用情况等调查记录;三是该民族语语言群体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等调查记录。数据库涉及的调查项目应该定期做周期性的调查,从而把握语言变化趋势。然后建立语言生态评估标准,培养监测人员,尤其要培养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才,便于更好地深入其居住地展开调研。
再次,从宏观上使语言协同进化具有可能性。城市化一方面加快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就语言而言,它也会加大语言间的接触。语言接触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强势语言向弱势语言输入词汇。通过对石林彝族语言使用状况的调研,我们发现其语言出现单极化发展趋势。语言之间的接触会引发不同语言间的相互竞争,其结果之一就是语言使用者由双语或多语状态逐步变成单极化。语言的单极化发展使族群传统交际域出现频繁的语码转换成为必然。大量非母语成分的借入,强势语借词的直接移植会造成语码混用现象,随着混用的扩大,语言传统功能域收缩,最终出现语言转用。对大紫处村原住彝族家庭三代人的调查显示第三代有些话语表达已不能像祖辈一样熟练准确地运用彝语母语进行,而是采用汉语词替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宏观上给予条件,给相对弱势的民族语言生存的空间。我们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包括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①萨利科科·萨夫温认为研究语言演化生态学,“不光要关注一种语言所涉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人种环境(其外在生态[external ecology]),还要关注语言系统在变化前及(或)变化中各个语言单位和规则相互共存现象背后的本质(其内在生态[internal ecology])。外在生态和内在生态在决定一种语言的演化轨迹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3](P216),要解决信息时代语言传播的不对称问题,制定和落实相关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授和传播,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同时注重少数民族母语教学,同时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新媒体运用与传播,重视语言之间的共生机制及语言的多样性价值,使汉语、民族语能协同发展,形成良好的语际关系。
最后,重视家庭环境因素,保留住民族语的最后领地。从对大紫处村彝语母语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族群年轻一代母语能力有减弱现象,母语使用出现代际断层趋势。提高少数民族族群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使其有效地代际传承,是改善语言生态的关键。民族母语的代际传承主要是自然获得,父母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对本民族语的认知和态度对孩子习得语言至关重要。部分彝族因移居城市而对自己的民族母语持消极态度,这些家庭的孩子已基本不会本民族语言,而调查显示,少数民族的民族语获得主要是通过家庭内部传承的。
因此,我们一是要尊重民族语使用者的群体意愿,要加强语言群体成员对本族语的使用和保留意愿;二是要重视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尊重他们的语言权利与语言诉求。解决新生代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提高其母语自身传播能力,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增强民族语活力。在坚持语言、教育权利平等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给弱势语言群体一个自主选择的自由空间。加强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与忠诚。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过程中,要关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的保护,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维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一方面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良性循环。
[1]Mühlhäusler,P.2003.Language of Environment,Environment of Language:A Course in Ecolinguistics.London&New York:Paul&Co Pub Consortium.
[2]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3]萨利科科·萨夫温.语言演化生态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Minority Native Language Attr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inguistics—A Case Study of the“Dazichu”Yi Minority Speech Community in Shilin County
FENG Jia (School of Humanities,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650214,Yunnan,China)
With the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Yi community in the urban fringe has changed,and the language of the minority Yi contacts with Chinese frequently.Influenced by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the native language skills of Yi minority groups in different ages in Dazichu village of Shilin country has degraded and abraded.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the abrasion of Yi native language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language.Finally,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nority mother tongue degradation caused by language contact.
linguistic ecology;Yi minority;language abrasion
〔责任编辑:黎 玫〕
H217
A
1006-723X(2016)07-01510-06
冯 佳(1980—),女(彝族),云南昆明人,昆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