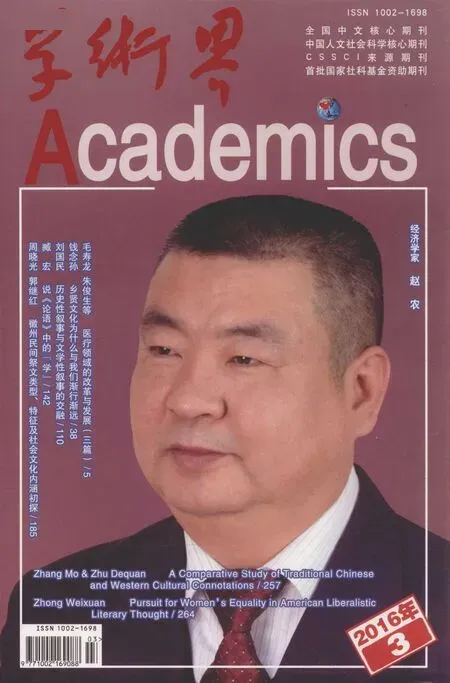清代桐城学术文化与马瑞辰《诗经》学研究〔*〕
○ 于春莉
(1.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2.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00)
·学人论语·
清代桐城学术文化与马瑞辰《诗经》学研究〔*〕
○于春莉1,2
(1.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225000;2.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马鞍山243000)
以清代《诗经》学名家马瑞辰为对象,由桐城学者的学术表现,探讨桐城学术的重心在于汉宋兼采、以汉辅宋,具有通脱豁达的学术品格。马瑞辰治《诗经》以小学为工具,关注《诗经》的文学阐释,表现出独立求实、不偏于一隅的学术性格,展现出与桐城学术文化相近的学术品质,可见桐城学术对他的重要影响。此研究除有助于了解马瑞辰《诗经》学的渊源及其与清代桐城学术的关联性之外,对于清代学术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了解,亦具有参考价值。
桐城学术;马瑞辰;《诗经》;独立求实;文学阐释
马瑞辰(1777-1853),桐城人,字元伯,又字献生,是清代嘉道年间著名的《诗经》学家,所著《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成就甚高的作品,学术界对该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通假、训诂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至于《毛诗传笺通释》与桐城学术的关联性,似乎还未见有专文讨论者。但事实上,这类与地域学术关联的个案研究,不仅能比较有效地了解马瑞辰的学术观,同时也是从微观视角把握清代《诗经》学走向的重要切入口。这对于清代学术、清代《诗经》学,以及桐城学术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拟从马瑞辰与桐城学人交往的情况出发,论证桐城学术文化的内涵,再分析《毛诗传笺通释》表现的内容与桐城文化的关联,最后反思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希望对清代区域文化及《诗经》学研究,提供某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资讯。
清代的“桐城派”,不仅文学创作浩如烟海,文学理论更引发赞成与反对者长期的争辩,从而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学界已逐渐认识到,桐城派不只作为文派,其作为经学流派、诗派的重要价值亦不容忽视。〔1〕而桐城的地域文化就是这些派系流衍、学风流播的基石。生长于此学术昌盛、文学繁茂的文化名乡,马瑞辰自幼便受到地域特色文化的熏陶,并与这三派中的学者都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首先,马瑞辰之父马宗琏是姚鼐的外甥,马宗琏就是在其门下接受古文词教育。〔2〕马瑞辰曾自称:“余幼秉义方,性耽著述;愧群经仅能涉猎,喜葩词别有会通”,〔3〕可见马瑞辰幼时即接受父亲的教导,不只涉猎群经,对词章之学亦别有慧心。父亲的教导是马瑞辰接受桐城文风熏染的起始,其后马氏又与方东树、姚莹、刘开等桐城派文人,及习宋学的桐城学者密切联系,因此其受桐城地域文化的影响自无疑义。马瑞辰文集已亡佚,然通过清人诗文集的记载,亦可大致获知其交游情况。根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的考述,可以把马瑞辰的交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桐城派学者,包括方东树、姚莹、刘开、张际亮、马树华、徐璈、姚元之、姚柬之、陆继辂、朱雅、王灼、陈用之、李宗传、左朝第、张聪咸、张泰来等;一类是桐城其它学人,包括光聪诚、朱道文、吴云骧、方潜、方葆馨、光聪谐、吴孙珽、方遵巘等。马瑞辰和他们的交往,除了乡土之谊外,当也有学术气味相投的因素在内,相互间的学术交流自也难免,这是马瑞辰承接父亲的教导之后,继续接受桐城文风熏染的另一个事实。
一、桐城学术文化内涵简论
关于桐城地方学术文化的发展脉络,马其昶有相当精辟的概述,其云:“桐城以盛文物推天下名县,自前代多慷慨伟节之士,而密之方氏(方以智)倡俺雅之业,望溪侍郎(方苞)以古文显。侍郎学深于经,其先则田间钱先生,后叶书山庶子(叶酉),三家于经皆不专训诂。姚姜坞编修(姚范)为学务征实,姬传先生(姚鼐)恢其绪而益肆于文。流风大煽,后生习传,彬彬皆被儒雅。当是时,天下竞言考据,文胜而敝,说者谓视前明强执之气,殆不侔矣。桐城先大师皆涉义理为教,其渐染考据者寡。”(《赠道衔原任工部员外郎马公墓表》)〔4〕桐城一域鲜明的地域学风,便是对宋以来理学的传承,学者们皆宗义理之学而少有纯粹的考证学家。例如明末方氏家族学者辈出,即多以理学名家,是以廖大闻编《续修桐城县志》,即将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照、方以智等四代人,皆归入“理学传”之内。〔5〕方苞高倡“学行继程朱之后”,〔6〕姚鼐再申“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7〕在清代汉学炽盛,严重威胁宋学之时,桐城派乃以高扬程朱理学之帜、复兴宋学传统为己任,这同时也彰显了桐邑乡风一脉相承历久不衰的传统学风。
桐城学者虽以宋学为根柢,然在汉学研究上仍然成就斐然。方以智、钱澄之都是在学术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公然承认方以智以“考证名物、象数、训诂、声音”为主的著作,对清初学术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而有“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的赞赏之词。〔8〕钱澄之著《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四库总目》称其“持论平允”,〔9〕“考证切实”〔10〕。由此可见《四库总目》认定方、钱两人为明末清初开汉学风气之先的学者,其后方苞、姚鼐、刘大櫆等学者继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盛大、持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文派“桐城派”于焉成立,文章博兴,异彩纷呈。桐城文派固以文名世,但在经学研究方面亦有可观的成就,开山祖师方苞即有《周官集注》《礼记析疑》等专著。刘大櫆虽无著作,但也是相当有名的经师。姚鼐著有《九经说》《三传补注》等,较方苞、刘大櫆成就更高。吴孟复的评价是:“《三礼》在考据家视为绝学,而方苞实开其先;其校订讹误,又开王(王念孙)、段(段玉裁);刘大櫆‘理欲观’,亦与戴震言性,符节若合。姚鼐之善审文理语气,亦开王念孙、俞樾之端。是方、姚未尝无助于汉学。”〔11〕虽或不免稍嫌夸大,但也不能否认三者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桐城学者治学,虽以宋学为宗,然尚能持汉宋之平而无绝对偏隅之失。众所熟知,姚鼐立“桐城家法”,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为一事,说:“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复蒋松如书》)〔12〕这种以宋学为主汉学为辅的主张,代表了桐城宗宋学者的一般性思想。胡承珙《寄姚姬传先生书》陈述自己阅读姚鼐经说的心得云:“伏读先生经说,县解冥悟,得诸自然,时复援据,动出意表,虽多撮举最凡,而大含细入,融会贯通”。〔13〕可见姚鼐治经尚能兼采汉宋,但与考据学家有所不同,其更重视以意旨为统摄而融会贯通,即更注重经典内在的义理性。梅曾亮回忆姚鼐之言云:“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吾之经说如是而已。”〔14〕姚鼐的学术观点固然主宋学而以汉学为辅助,虽不满于汉学家对宋学的排斥,但仍然承认考据的价值,治经尚能持汉宋之平。姚鼐的学风经由马宗琏而对马瑞辰当有着深刻的影响。
刘开为学同样主张汉学、宋学兼采。他承认“汉学未尝无裨于人也”(《学论》中),〔15〕又云:“其兼取汉儒而不欲偏废者,非悦其博也,将用以参考异同,证明得失,可以羽翼夫圣道也。”(《学论》中)〔16〕可见刘开之所以主张汉宋兼采,主要是以汉学为治学工具,以求取义理、辅佐圣道,最终达于宋学之境。又云:“善治天下者,去其已甚而不必尽事更张;善论学者,本于至公而不必尽同己见,择善而从,使不善者归于善而已矣。”(《学论》中)〔17〕开明豁达的学术精神见于言外。刘开曾论及清代《诗经》学研究云:“我朝治教休明,淹通宏博之士,相继而起,一改前代固陋之学,……于《诗》则折衷《小序》、《集传》,而兼核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其用意可谓勤矣,援据可谓富矣,然详于名物度数,而或略于义理之是非……”(《学论》上)〔18〕这里刘开总结清人治经详于考证疏于义理探究的缺欠之后,具体谈及《诗经》的观点很有见地。马瑞辰与刘开的交情甚深,则刘开的治学观点对马氏当有影响。
姚莹认为汉学与宋学具有联系,虽然最终依然归宿于宋学,却也没有完全抹煞汉学的价值,故曰:“汉儒谨守师法,训诂略备于前;宋儒讲论修明,义理大著于后。”(《与张阮林论家学书》)〔19〕可见姚莹的学术观与其从祖姚鼐一脉相承,亦主宋学而兼采汉学。姚莹赞同钱彝抱持的“悉心折衷而兼采之,以泯是非而明经义”的著书意图;更赞赏他“编辑诸儒先之说,择善而从,以示折衷,而不参论辨”的态度;同时也认同他“其间出已见,稍有异同,则别而出之”的处理方式。(《钱白渠七经槪叙》)〔20〕姚莹认为钱彝《七经概》反映了治学者平心静气,不妄发论辩、不以攻击为意的为学态度,这正是姚莹一贯的治学主张。所以,其《与张阮林论家学书》明确提出“说经硁硁,贵渊通不在攻击也”,对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一书的命名颇有微词,认为他的经学著作名称带有批判攻击的火药味,故难以赞同。又提及马瑞辰之父马宗琏的经学名著《春秋左传补注》,谓其指摘杜注的说经方式并不合宜,是以建议张聪咸加以借鉴。〔21〕可见,去其戾气、平心而待、严谨笃实、渊深通融,正是姚莹为学的一贯追求,同时也是桐城文化中相当重要的学术观。
方东树虽甚不满于汉学诸家“欲以扫灭义理”的霸道,故以《汉学商兑》为旗帜,对汉学进行攻击,其中激烈反对汉学之词所在多有,但却也能客观肯定汉学的价值,认为:“其大者,毛音郑简与道相扶;其次者,名物典章于政为辅。历世既远,著述转纷,通才硕彦接踵而出,使来学者变学究,破伧陋,以炳于经籍之府,其用亦可谓宏矣。”又云:“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其著书专门名家者,自诸经外,历算、天文、音韵、小学、舆地、考史,抉摘精微,折衷明当。”(《复罗月川太守书》)〔22〕对清代的音学研究,更是不吝惜地高度赞美,云:“近世有陈、顾、江、段、戴、孔诸家,追绝学、寻坠绪,迭兴继起,驰精入神,几于补捉出八荒,而后古音大著,伟矣哉。”(《二十一部古韵序》)〔23〕其曾云:“苟其说足以扶经义而裨来学,不妨并存,以俟后贤之择从。”(《七经纪闻序代》)〔24〕治学理念同样具有通脱的桐城特点。方东树这些肯定汉学价值的言论,相对于《汉学商兑》的极端攻击,更可以反映出桐城学者们在治学上的共识。
马树华系马瑞辰的族弟,二人交往甚密。刘声木说他“师事姚鼐,受古文法”。〔25〕马树华在《论修县志与人书三》中提到修县志之事,欲将理学家、经学家并列入儒林传中,但方氏的后裔却认为此举有损其祖的声名。马树华却认为二者当并入儒林传:“濂洛诸儒固儒林之宗子也,其汉唐诸儒独抱遗经。守先待后,其所得精粗虽殊,而其为儒家则一也。盖一则发明圣贤修己治人之旨,可以见诸行事之实而非托诸空言。一则修明六经之训,可以因之推阐圣言而非图存古义。斯二者有浅深而无内外,有本末而无异同。”〔26〕马树华此种汉宋兼采互补、以汉辅宋的学术观,当是导源于姚鼐,而与姚莹的学术观相近,甚为开明、通达,不愧是姚门中人。
综上,可知汉宋兼采、以汉辅宋的学术取向,实是桐城派学者们的共同学术观。从桐城学者们理性的论述、诚恳的语言之中,可看出折中汉宋的观念实乃桐城学者们内心豁达通脱的学术追求使然。虽然,现在一般都以为清代汉学博兴,因而宋学颇受压抑,但实际上未必如此,因为直到清朝灭亡,官学依然以宋学为主,汉学主要还是为辅助义理而被重视。纪昀《丙辰会试录序》即提到“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27〕《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也有“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卷首)〔28〕之论。《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更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卷一)〔29〕显见“经义明”才是传统学术最终的结穴,是以桐城学者汉宋兼采、以汉辅宋,“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以明经典义理的学术观,正是不偏于一隅的正当学术共识。调和汉学、兼采精华而为宋学追求义理所用,是桐城学者主动的历史选择,反映了他们通达的学术价值观,展现出桐城学术文化的开明、豁达的特质。
二、桐城学术文化对马瑞辰的影响
在亲近宋学,择取汉学补苴宋学,总体趋向汉宋兼采的清代桐城区域学术文化的影响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内容表现,体现了哪些与桐城区域学术文化相近的观点,因而展现出独特的学术风貌?根据初步的归纳,大致有下述几点。
1.汉宋兼采、独立求实的治学风格
《毛诗传笺通释》引用了诸如朱熹、程大昌、欧阳修、严粲、王应麟、范处义、王质、吕祖谦等很多宋人的学术观点。马氏尤为重视朱熹的《诗经》学说,共引用朱熹学说89处,其中87处均引自《诗集传》。从引证内容上看,属于文字训诂的达到45处。朱熹《诗集传》摆脱《序》《传》束缚,从文本出发,以己意说诗,但清前期除王夫之、钱澄之治《诗经》持汉宋兼采的观点,因而较能平实的对待《诗集传》,至于深受《诗经》学研究复古之风浸染的学者,如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等则皆攻朱熹《诗集传》,尤其以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为甚。入清以后《诗经》汉学逐渐复兴,乾嘉时期汉学大兴,汉学考据于是成为时髦之学。马瑞辰处于乾嘉考证学大兴之后,却能重视朱熹以文字训诂为主的学术观点,虽然时有驳正,但也不能否认桐城文化崇重程朱思想对他的影响。若与同时代治《诗经》大家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胡承珙的《毛诗后笺》相比,马氏更加注重从《诗经》的文本出发,时而能跳出汉学家的藩篱,是以或批评毛《传》,偶尔也反对《序》义,可见桐城学术继承的宋儒怀疑、批判精神,对马瑞辰的《诗经》学具有启发诱导的功能。
《通释》分三十二卷,卷首设有“总论”者共计八篇,马氏在其中详细评述了有关诗篇的思想内容,表达了马氏关于国家现实社会政治的深刻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桐城学者追求义理与考据相结合,以作为经世实践根柢的鲜明特色。
《通释》一书称引的清代学者达77家,凡有不同意见,马氏都勇于驳正。甚至对段玉裁这样的考据学大师,马氏在征引的222处说解中,属于直接批驳者竟达六十五处之多,足见其大胆就实的治学风格。马瑞辰治《诗经》以毛为主,兼取《三家诗》说;尊崇汉儒而不拒宋学;征引学者观点绝不盲从,也绝不党同伐异,都能鲜明反映出马瑞辰独抒己见的学术追求。总之,马瑞辰治《诗经》,不仅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比较平正通达的判断力,而且深刻体现了兼容并蓄、汉宋兼采、独立求实的桐城学术文化特质。
2.重视以小学为治《诗经》工具
桐城派学者对小学相当重视。姚鼐肯定“小学实经义之一端,为论经始肇之事”的观点(《小学考序》)。〔30〕以为小学乃学者治学的入门基础,人人必当掌握,须臾不能离开。小学即训诂、字形、音韵之学,显然小学在姚鼎的心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又云:“孔子古文既亡,惟《说文》可正文字之体,舍韵书难定音读之讹,非训诂莫通经文之义,则三者实六经之阶梯门户也。”〔31〕方东树更是曾盛赞汉学家在音韵学方面的重大成就,谓其居功至伟。
解经重视从语言文字角度诠解,虽是乾嘉以来多数经学家的共法,但马瑞辰治《诗经》特别重视小学的解经方法,当也有受到姚鼐等桐城学者学术观点影响启发的因素在内。马瑞辰于《毛诗传笺通释自序》即表明“以古音古义证其伪互,以双声叠韵别其通借”。〔32〕该书主要依据《说文》推求本字本义,贯穿以双声、叠韵、通转等音学理论以发明假借字的训诂方法,这方面的表现构成了此书最鲜明的特色。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诗经》学史上如此大量而全面地以声寻求通假的方式考释经义的学者,马瑞辰算是先驱者。”〔33〕虽然对乾嘉汉学丰硕成果的全面性继承,乃是马瑞辰《诗经》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桐城一域重视小学的文化风气的熏陶、熟识学者之间的切磋砥砺,对马氏将因声求义的治学方法发挥到炉火纯青地步,应该也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3.关注《诗经》的文学阐释
马氏治《诗经》也注意到体悟《诗经》文学性的必要,例如针对《大雅·荡》“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一句的训释: 《笺》:“饮酒号呼之声,如蜩螗之鸣;其笑语沓沓然,如汤之沸、羹之方熟。”瑞辰按:诗意盖谓时人悲叹之声,如蜩螗之鸣,忧乱之心,如沸羹之熟。淮南王《招隐》曰:“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五臣《注》:“蟪蛄,夏蝉。”刘向《七谏》曰:“身被疾而不闲兮,心沸热其如汤”,正取此诗之义。〔34〕
马氏此训准确生动地道出了诗人以蜩螗之鸣喻人悲欢之声,以沸羹之熟比人忧乱之心的文本内涵。同是比兴说诗,相对于马瑞辰对诗歌隐喻修辞手法的体会,郑《笺》就显得很不贴切,显然未若马氏通观全篇立意说诗来得准确。马氏又举《招隐》《七谏》以反观《诗经》在文辞、立意方面对后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已踏入了文学接受的领地。再如马氏训解《小雅·天保》“不如友生”云:“生,语词也。唐人诗‘太瘦生’,及凡诗‘何似生’、‘作么生’、‘可怜生’之类,皆以生为语助词,实此诗及《伐木》诗‘友生’倡之也。”〔35〕训释《周南·桃夭》“有蕡其实”,谈到:“古以华喻色,以实喻德,此魏人‘春华秋实’之喻所本。”〔36〕可见马氏在涵泳诗义的时候,常常会不经意地联系后代的文学作品。他时而将《诗经》作为诗歌来读,能够摆脱《序》《传》的政教束缚,从文学欣赏、文学接受的角度看待《诗经》,与甚为尊《序》的胡承珙和墨守《毛传》的陈奂相比,马瑞辰显得文学领悟力更强、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可见马瑞辰“喜葩词别有会通”的自许,实非虚言。
桐城一域,自古以来,里中学人多以文章诗歌相切磋,以学问道德相标榜,以文学行谊相砥砺,形成了浓郁的文化风气。姚莹的《北园燕集诗序》回忆前代的盛况说:“吾桐昔时,风气淳朴。友朋聚处,上者相劘以道德,次者相励以文章,然皆彬彬各有礼叙”,又提及当时的状况云:“笃学敦义,养誉乐道,盅粹之情盎于面背,兴逸气峻,各为诗歌”〔37〕,这就为生长于当地的马瑞辰,当其精研《诗经》章句,涵泳诗义之时,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马氏本有诗集存世,并受到过方东树等人的盛赞,文学作品的著述情况,请参看拙文《桐城经学家马瑞辰著述考》。〔38〕受到桐城文风的熏染,马瑞辰亦擅长辞章之学,故他能在训释《诗经》时结合文学修辞手法,方法新颖,结论可喜。显然,马瑞辰以文学角度诠释《诗经》,桐城文学风气对他的滋养尤为重要。
三、余 论
刘声木梳理桐城文派的发展脉络,以归有光“抉宋儒之义理”入文为始,称方苞“研究程朱学术至为渊粹”,其后桐城文派“蔓衍百余年益盛”。认为桐城学人“皆由义理以育文章;文章虽未必遽能传世行远,而言坊行表皆大半不愧为正人君子,其成仁取义,慷慨捐生,堪与日月争光”。(《补遗序》)〔39〕刘氏又举桐城派的马树华、马三俊等人,叹云:“皆大节凛然,足与日月争光,汉学家无一人焉,谓非宋学之明效大验乎?”〔40〕刘声木一再强调的显然是程朱理学与文事相结合之后,确实足以彰显重修身养性、尚敦行立节的宋学对桐城派文人提升人格境界之功。刘声木没有指明的另一个人,则是咸丰三年太平军之战爆发后,同时与族弟马树华、少子马三俊等誓死不降、杀身成仁的马瑞辰——这位被归类为典型汉学家的桐城学者。马瑞辰生长于宋学兴隆的文化之乡,深受此种区域文化思潮的启迪,不只促使他以更开阔的学术视界研究《诗经》,更砥砺了他“成仁取义”的士大夫精神。马其昶云:“公之治经,笃守家法,义据坚通,人以此为公之锲力于经者深乎。呜呼!自知道者观之,彼其遘危难,较然不欺其志意,是乃所为深于经者也。”(《赠道衔原任工部员外郎马公墓表》)〔41〕马其昶所谓“遘危难,较然不欺其志意”之事,即指咸丰三年(1853)马瑞辰宁死不屈,殉太平军之难。马瑞辰治经“志存译圣”,〔42〕即以恢复经典的价值与意义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舍生取义的壮举,完成了他对儒家经典最后的却也是最有力的诠释。这正是马其昶称颂马瑞辰“深于经者”之故。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渊源与内容表现,根据前述的论证说明,可知确实与其生长的乡邦桐城学术文化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桐城学术文化,才造就了这位清代的《诗经》学大家,才造就了清代这位舍生取义、壮烈牺牲的士大夫。通过前述的研究,相信对于马瑞辰的学术、《毛诗传笺通释》的内容和桐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可以获得更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区域文化与学术研究间密切的关联性,从而也对清代的《诗经》学研究,以及清代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部分值得参考的答案。
注释:
〔1〕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2页;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40-46页。
〔2〕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40页。
〔3〕〔32〕〔34〕〔35〕〔36〕〔42〕〔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42、505、56、1页。
〔4〕马其昶:《抱润轩文集》,《续修四库全书》(15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6页。
〔5〕廖大闻:《续修桐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1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22-524页。
〔6〕苏淳元:《方望溪年谱序》,《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6页。
〔7〕〔12〕〔18〕〔19〕〔20〕〔3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2、95-96、92、61、92、63页。
〔8〕〔9〕〔10〕〔28〕〔2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28、36、131、18、1页。
〔11〕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13〕胡承珙:《求是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5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14〕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6页。
〔15〕〔16〕〔17〕〔18〕刘开:《刘孟涂集》,《清代诗文集汇编》(5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01、500、501、500页。
〔19〕〔20〕〔21〕〔37〕姚莹:《东溟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5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9、328、338、389页。
〔22〕〔23〕〔24〕方东树:《考盘集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5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2、179、187页。
〔25〕〔39〕〔40〕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61、17、6页。
〔26〕马树华:《可久处斋文钞》八卷本,清线装刊本,卷五第十六。
〔27〕纪昀:《纪文达公遗集》,《续修四库全书》(14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7页。
〔31〕姚莹:《识小录》,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232页。
〔33〕黄忠慎:《清代诗经学论稿》,台湾:文津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38〕于春莉:《桐城经学家马瑞辰著述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6-19页。
〔41〕马其昶:《抱润轩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7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0页。
〔责任编辑:陶然〕
〔*〕本文系2015年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招标项目“吴汝纶教育改良思想研究”(SK2015
A139)的研究成果。
刘燕(1971—),安庆师范学院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