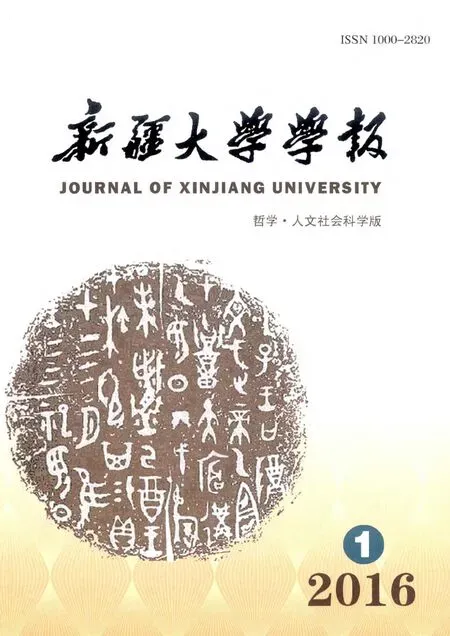汉语方言“VC了”可能式的语法化*
王自万
(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河南郑州450064)
“VC了”可能式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关于其形成过程,柯理思认为可能补语中的标记词“了”和“得”具有平行性,两者都是从表示实现义转到表示可能义的[1],辛永芬结合“V得C”的演变过程,推测可能式“VC了”是实现式“VC了”用于未然语境而造成的[2],孙利萍提出标记词“了”虚化过程为“完了”义动词→结果补语→动相补语→可能补语标记[3],王衍军结合历史语料,具体论证了“VC了”可能义的派生过程[4]。综观已有论述,“未然语境说”获普遍认同,然而“了”本身表示完毕、实现意义,它如何运用到未然语境当中,未然语境是一个时间概念吗?再有,动相补语和可能标记之间的具体演变过程如何,“了”如何从作补语的实体成分转化成了纯粹的可能式标记成分。本文拟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从近代汉语和方言中的“VCO了”结构、方言中“了”标记动趋可能式的语序、可能标记“了”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发展及认知动因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讨论,最终是要回答什么性质的“了”如何成为了可能标记这个问题。
一、可能标记“了”语法化前的句法性质和功能
(一)近代汉语和方言语料中的“VCO了”中“了”的性质
在使用“VC了”可能式的北方方言中,该式带宾语的语序通常为“VCO了”①由于各地方音不同,“了”在不同方言语料中使用的汉字并不一致。,如:
聊城:他买起彩电喽他买得起彩电。(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285页)
利津:我拿动这些书哩我拿得动这些书。(同上)
开封:我吃完仨馍喽我吃得完三个馍。(自拟)
和普通话中“V得C”可能式带宾语的情况相比,这种结构语序很特殊。“V得C”通常是将宾语放在最后,形成“V得CO”结构,而“VC了”可能式是将宾语放在C后“了”前,形成“VCO了”结构。普通话中,陈述实际发生的“VC了”如果带宾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宾语置于“了”后,形成“VC了O”结构,和方言“VC了”可能式带宾语的语序不同,因此不可能是这种“了”演化为了可能标记;另一种和方言“VC了”可能式带宾语语序相同,也是“VCO了”结构,但此时“了”是语气词“了2”,也不可能演化为“VC了”可能式中的标记词,因为语气词的语义比可能标记虚,不符合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即语法化一般是从实词到虚词而不是相反。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VC了”可能式也不可能是今天普通话中某种格式演化而来的,而应形成于近代汉语的某个阶段。在动词“了”的虚化过程中,曾经存在一个语序为“VCO了”的发展阶段,这种语序的同类结构在今天的一些方言中仍然存在。作为和可能式“VC了”带宾语时语序相同的结构,其中“了”的性质代表了可能标记“了”语法化前的状态。只有通过观察历史和方言语料中语序为“VCO了”(其中“了”既不是动词后缀“了1”,也不是语气词“了2”)的用例,才能从中确定是何种性质的“了”演化成了可能标记。
1.近代汉语语料
从南唐时期的《祖堂集》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中,都有这种“VCO了”结构存在,如:
雪峰放却垸水了云:“水月在什摩处?”(《祖堂集》,曹广顺用例)
读尽昨所讲经文了,讲师即读次文,每日如斯。(《入唐记》卷2,孙锡信用例)
又上大树望见江西了,云……(《祖堂集》,孙锡信用例)
如梨树极易得衰,将死时须猛结一年实了死。(《朱子语类辑略》,孙锡信用例)
方才叫住郭立,相问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军令状了去。(《碾玉观音》,孙锡信用例)
施恩道:“请吃罢酒了同去。”(《水浒全传》28回,孙锡信用例)
对于这些例句中“了”的性质,多位学者都有分析。曹广顺认为“雪峰放却垸水了”中的“了”为“了2”的形成创造了条件[5]88;孙锡信认为,其中的“了”既难以看做动态助词(或称词尾),也难以看做句末语气词,妥当的办法是仍旧看做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结束,其性质与“VO了”中的“了”一样,是实词作补语,所不同的是VC代替了V[6];蒋绍愚认为“又上大树望见江西了”的“了”是表完成的动相补语,离完成貌词尾已很近了,但它要发展成完成貌词尾还必须再跨进一步:紧贴在动词后面,即使出现宾语,也不被宾语隔开[7];杨永龙认为《祖堂集》中的“雪峰放却垸水了”虽然“了”前面是述补结构带宾语,“了”比较虚,但这是一个背景小句,“了”用于说明前后关系,不是告诉新情况的“了2”[8]。各家的论述普遍认为此处的“了”既不是“了1”,也不是“了2”,而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动词,是处于行为动词向助词转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语法功能是作“VCO”的动相补语,表示“VCO”整个事件的完成、有结果。
2.方言语料
河北昌黎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词尾“了”的读音是liou,《昌黎方言志》中写作“”,可以用来表示完成、过去、条件、也可以用在命令句中,同时可以组成“VC”可能补语结构。《昌黎方言志》中这样描写“”表示条件的用法[9]25:
例中“看见”为瞬时完成的动作,没有延续性,“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补语,整个结构不宜看做“VCO了”,但根据文中说的“‘’表示条件,位置可以在宾语后头”,带补语的两例也可以这样说:
河南安阳方言也存在类似用法,王琳提到安阳方言中有一个普通话中没有的助词(其文中记作“咾2”),黏附于动词性结构,表示事态的实现,有一定的“完毕”义。其例句中有一例“VCO了”语序[10]:
安阳:你用罢我嘞书咾2还给我你用完我的书之后还给我。
同样,安阳方言中也用“咾2”作为可能标记,即“VC了”可能式中的“了”:
安阳:你搬过来诺桌的咾2吧你能搬过来那张桌子吧?
在开封方言中,也存在“VCO了”语序的结构,例如:
开封:考上大学喽给你买个手机考上了大学给你买个手机。(自拟)
这句话用于对未来的许诺,“考上大学”和“买手机”之间可以理解为先后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条件关系,其中的“喽”相当于昌黎方言的“”、安阳方言的“咾2”,同样,“喽”在开封方言中也用作可能标记:
开封:我吃完喽吃得完。(自拟)
以上现象说明,在这些方言中,相关结构还保留着近代汉语的语序,其中的“了”(、咾、喽)可以看做是“VCO”结构的动相补语,表示该结构事件的实现和完成。普通话中,意义相近的“了”常常要放在宾语之前,紧跟着动词和补语,虚化程度更高一些,方言中存在“VCO了”语序,是其发展与共同语不同步的表现。
总之,从形式上来说,上举历史、方言语料中的“VCO了”格式就是今天“VC了”可能式同类语序结构的前身,演化为可能标记的“了”是一个作动相补语使用的动词,演化完成的时间应该是在其成为动词后缀和语气词之前,方言中所写的“”“咾”“喽”是同一个可能标记“了”在各地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
(二)从方言动趋可能式看标记“了”的虚化程度
在普通话中,动趋式加“了”可以有两种语序:“动+趋+了”和“动+了+趋”①“动+了+趋”格式中“趋”一般是双音节,单音节限于“来”“去”,这些限制条件我们不作讨论。,两种形式语义有一定差别,也反映了“了”从动词虚化的不同结果。如:
他爬了上来。
他爬上来了。
根据吴继章的研究,“动+了+趋”格式在近代汉语、山东、山西等地方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整个河北方言中都不成立[11]。在开封方言中,表达实现意义只有“动+趋+了lə”式,相应的可能式也只能用“动+趋+了lou”,没有“动+了+趋”的实现式或可能式。如:
开封:他爬上来了。(实现式)
他爬上来了。(可能式)
方言中“了”在动趋式中所处位置说明其语义相对实在,地位相对独立,还不完全是词尾“了1”,河北、河南等地的方言中不能说“动+了+趋”,说明这些方言的“了”没有虚化到动词词尾(必须紧贴动词)的程度。在普通话中,动趋式的可能式标记词“得”位于动词和趋向动词之间,如“爬得上来”“咽得下”;在北方方言中,动趋可能式标记词“了”只能放在趋向动词后,不同于普通话可能式标记词“得”的位置。这种现象说明这两个可能标记的虚化程度不同,“了”没有“得”的虚化程度高。
可能标记“了”在动趋式中的位置和可能式“VC了”带宾语时的语序(VCO了)这两个现象反映了同一个本质,就是可能标记“了”的前身和动词的关系不像动词词尾和动词之间那么紧密。
二、可能标记“了”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发展
近代汉语和方言中“了”作“VCO”结构的动相补语时,均出现在背景事件中,这种语用环境清楚地表明了该结构演化为可能式的具体条件。在前引语料中,“VCO了”结构所在的句子都有后续小句②另有结句的“VC(O)了”结构,其中的“了”倾向于认为是“了2”的前身,见石锓《浅谈助词“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辑),巴蜀书社,2000年第90-105页。,根据句义,后续小句中的动词才是整句话的焦点,这种语境和位置是其句法意义和功能发生变化的基础和条件。由于历史文献中可能标记“了”出现时间较晚,出现次数较少③根据王自万《可能式“V得C”和“VC了”的文白层次》,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274-278页,“VC了”可能式最早见于关汉卿杂剧,仅在明清时期几部白话小说的人物对话中有少量使用。,而动词“了”虚化的历程研究得较为充分,路线基本清楚,所以可以将可能标记“了”的形成置于“了”虚化的大背景下讨论。笔者认为“了”从动词到可能标记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以下两次重要的语义转变:(1)从先后关系到广义的因果关系,(2)从广义因果关系到可能意义。
(一)从先后关系到广义的因果关系
历史文献中“VCO了”结构的出现依赖于动结式“VC”后接宾语和动词“了”的虚化。现有研究表明,中古汉语当动词(V)后同时出现宾语(O)和陈述性成分(C)时多为“VOC”顺序,如蒋绍愚所引各例[12]:
故揩玻璃山碎。(贤·卷4)
今当打汝两前齿折。(贤,卷11)
以梨打我头破乃尔。(百·以梨打破头喻)
即便以嘴啄雌鸽杀。(百·二鸽喻)
风来吹叶动。(玉·沈约:咏桃)
这些例子中的“C”并未完全与前V复合,因为中间还隔着宾语O,某种程度上还是动词,语义上具有独立性,是对O的陈述,可认为这些“VOC”结构是VO和OC的复合形式,其间的O合二为一了。
与此相一致的是,“了”初为动词,早期“了”虚化的用例也多呈现为“VO了”的语序[5]16,其中“了”在句中作谓语,与上述VOC用例类似,其中“了”相当于C,不同的是这时的“了”并非对O的陈述,而是对整个VO事件的陈述,早期出现在复合句前分句末尾的“VO了”中“了”都是这种用法,并且此种用法后世一直存在,如曹广顺[5]79引用的例子:
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水浒传》,二四)
你且去买一道了来。(同上,二五)
当动结式VC逐渐凝固为一体之后,对事件的表述更加精细化,VC可以出现在VO结构中V的位置,即VC结构带宾语,这样便很自然地有了“VCO了”结构,与此同时,该结构中的“了”也不再是前分句中具有陈述功能的实义补语成分,而是倾向于表示前后分句所述事件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林新年认为,《祖堂集》中“VCO了”和“VCO后”在构成和表达的语法意义上具有很大相似性,而“后”是时间副词,表达动作和事件的完成,与表达完成的“了”在语义内容上十分相近[13]。如:
又问:“有善知识言,学道人但识得本心了,无常来时,抛却壳漏子一边著。
直饶剥得彻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你不可便将当纳衣下事。(以上两例转引自林新年《〈祖堂集〉的动态助词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24页)
我们认为,这时的“了”在功能上逐渐变为前后分句间的一个连接成分,按照语法化的滞留(persistent)原则,在保留原有意义特征的基础上,成为表示分句间某种逻辑关系的一个关联词。
杨永龙谈到,表因果关系的“V了,V”是从表先后关系的“V了,V”发展来的[14];陈前瑞、张华认为在《祖堂集》中用在前分句末尾的“了”能理解为因果、条件关系的情况还不多,而到了《三朝北盟汇编》中,用在前分句末尾的“了”更多地表示因果关系[15]。先后发生的两个事件往往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这就造成先后关系会非常自然地演化出其他的逻辑关系。如果是述实的,二者表现为并列、承接关系,无主次之分,但如果陈述的重点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是包含说话人主观看法的一种道理、前提,则向偏正复句演化。“汉语的动词后缀‘了’和印欧语动词的过去时词尾不同。印欧语动词过去时表示说话以前发生的事,汉语的‘了’只表示动作处于完成状态,跟动作发生的时间无关,既可以用于过去发生的事,也可以用于将要发生的或设想中发生的事。”[16]作为动词后缀的前身,演化中的“了”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正因如此,“了”逐渐成为广义因果关系复句前分句末尾的标记词。
(二)从广义因果关系到可能意义
太田辰夫在分析“了”表示变化和表示假定的用法时说:“表变化和表假设两者在古代大约不是那样截然分开的”[17],但是我们认为,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关系,“了”从表示先后(即变化)到表示条件、假设的中间环节就是因果关系,而“假设、条件都可以认为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18]427。
假设、条件等分句中的“VCO了”的语义可以理解为实,即“真正实现了VCO”,也可以理解为虚,即“能够实现VCO”。两种理解对全句表达的意义没有太大影响,实现与可能这两种语义在逻辑关系上是不矛盾的,已经实现蕴涵有能力实现,有能力实现在适当的条件下又可转化为真正实现,如果有更多的上下文背景,很容易确定到底是实现还是可能,反之,当语境不明的时候,就无法确定是陈述实际发生的事件,还是说一种无时间特征,具有恒常性的道理,而这样就会造成两可的理解。
如果说是假设、条件等句式赋予了“VCO了”结构可能意义,那么其中的补语“了”原有的实现意义在“能够”意义的支配下就显得多余了,原本其作用在于标示状态实现,而在可能意义中无需标示此种意义;而且,补语C表示动作达成的状态,本身就有完成、实现的含义在其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句式使其产生的可能意义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即必须有相应的语境才便于理解,这不符合该结构使用面扩大的要求,因而该结构亟需有一个独立于语境之外的能够标示可能意义的成分,于是,“了”就从具有一定实义的补语成分转化成了一个纯粹的标记词。可以说是特定句式、实现和可能之间的语义关系特征、特定结构使用面的扩大等因素共同促使“VCO了”中的“了”从动相补语成分转化为可能式的标记词。
三、可能标记“了”形成过程中的认知动因
(一)可能语义属于虚实范畴而非时间范畴
“VC了”可能式在现代汉语中主要见于北方方言口语,由于方言完成体标记的地区差异、方言语法现象的文白层次等因素,“了”标记的形成过程目前还无法使用通语文献进行完整的论证,由于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历史语料,现有讨论中普遍存在例句较少的缺陷,已有的关于“了”标记可能式形成过程的讨论多借用“V得C”可能式的形成来类比,关于“V得C”可能式形成过程,代表性论述是吴福祥所说:“表示某种结果(/状态)实现的‘V得C’,如用于叙述未然事件的语境里,那么就变成表示具有实现某种结果(/状态)的可能性。”[19]“未然”意思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20]1359,研究者通常所说的“未然”是与已然、实现相对的,“已然”是“已经这样,已经成为事实的”[20]1538,这些解释很容易让人将“未然语境”理解为一个时间上的概念,其实并非如此,已经成为事实的事件也可以有可能意义的说法,如“可能已经下雨了”,从本质上说,“可能”并非时间概念,并非“将来”(未然),而是所述事件的着眼点不在于其是否真正发生,而在于是否具备能力、条件发生,如吕叔湘的归类那样,属于虚范畴的一种[18]258。沈家煊明确指出吴福祥所说的未然句即非现实句[21],“非现实”这种说法较“未然语境”更准确具体了。在非现实语境中,真正实现和能够实现(具有能力和条件)之间的语义界限是模糊的,这也就形成了从表实现到表可能的转化条件。但为什么能够实现转化,深层的认知动因还需进一步寻找。
(二)主观视点沟通虚拟与现实
造成假设、条件等句式偏句位置所述内容虚实模糊的深层原因是说话人的主观视点,邢福义在分析汉语复句格式和语义之间关系时曾详细论述虚拟句中的虚实关系[22],其基本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实现和可能两种语义之间的转换。
从句式的作用上来看,非现实句中偏句的位置能够起到化实为虚的作用,表现了说话人的主观视点。邢先生指出,复句语义关系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反映主观视点,在虚拟句中,主观上虚拟为真,客观上不一定非真,最典型的虚拟句式“如果p,就q”中,句式上所标明的虚跟客观实际的虚也没有绝对的必然的联系,即“如果”之后,仍然可以接真实的事件,而句式体现的只是说话人主观上化实为虚。以这种观点来看处在假设偏句位置的“VC了”(或“V得C”),既可以是真正实现了的,也可以是尚未实现的,但进入了这个句式之后都被说话人从主观上化实为虚,不仅假设语境具有这种功能,表示让步的分句也可以将现实和虚拟沟通起来。如:
师曰:“见即见,若不见,纵说得出,亦不得见。”(《祖堂集》168页①据(南唐)静、筠二禅师编纂,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
纵使青春留得住,虚语,无情花对有情人(欧阳修词,引自王力《汉语史稿》301页)
这里的“V得C”一般倾向于理解为可能意义,让步句偏句位置反映的也是说话人的主观视点,这两句的句式虽相同,其中“V得C”的语义有些区别。“说得出”既能理解为实现(说出来了),也可以理解为可能(能说出来),二者在假设语境中界限模糊。而“青春留得住”即通常所说的反事实条件,假设意味明显,更凸显了说话人的主观视点。即使是实现意义,进入该句式后也会变成一种虚拟的情况,而虚拟语义的性质则和可能意义的性质是一致的,即都反映了说话人的主观认识。说话人利用特定句式对语言结构固有意义施加影响,进而使其语义发生转变,是语言主观化的具体表现。
不仅近代汉语中有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中,“VC了”出现在假设语句偏句位置也容易造成语义理解的模糊,如:
忙得饭也顾不上吃,赶上了,跟人家吃一口两口饽饽,赶不上,稀里糊涂的也过去了。(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49页)
雅洪托夫认为:“在这个句子里,可以在书面上把可能形式‘赶上了’和过去完结时的形式区别开,这只是根据有着和它相反的形式‘赶不上’的缘故。”[23]但我们的理解是,由于这里二者均出现在假设偏句的位置,此处“赶不上”不一定包含“不能”的意思,或“不能”的意思很不明显,而只表示“做了某个动作,但没有取得某种结果”[24],那么与之相对的“赶上了”也未必就是可能式。将其作为可能还是实现,对于整个复句语义的理解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位于假设句中偏句位置的动补结构表达实现和可能语义的模糊性。
四、结 语
第一,可能标记“了”源自于近代汉语中位于复合小句前分句末尾的“VCO了”结构中的“了”,这种“了”源于动词,已经发生虚化,但不是纯粹的语气词或动词词尾,在方言中尚存这种功能的“了”。
第二,北方方言中“了”标记动趋可能式的结构也说明标记词的来源以及虚化程度。
第三,“VC了”可能式的形成是在“了”逐渐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标记词“了”的语义经历了从时间先后关系到广义因果关系、从广义因果关系到可能意义两次转变。
第四,说话人化实为虚的主观视点是促使“VC了”可能式产生的认知动因,这种解释同样适用于“V得C”可能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