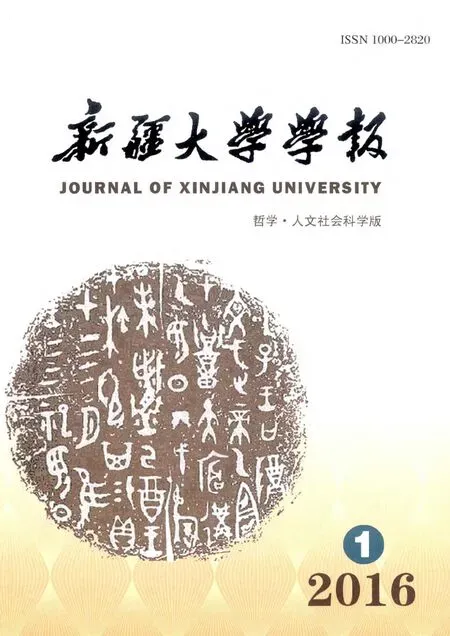动补结构的重构机制*
邱 峰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本文仅讨论补语指向宾语之类的动补结构①我们之所以用“动补结构的重构”而不用“动补融合”这种学者们常用的术语,是因为后者仅关注补语前移,而前者还关注宾语后移,虽然最终演变而成的句法结构一样,但由我们本文的分析可见,动补机构的演变包括补语前移和宾语后移两个方面。当然为行文方便,我们有时仍采用‘动补融合”这种说法。,因这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动补结构,且其演变涉及本文要讨论的语序变化,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说的动补结构均是指这种结构。关于此类动补结构的来源,前人有较多探讨,我们认同石毓智的观点,即直接来源于“可分离动补组合”②属于此类结构的具体实例的形成时间有早晚区别,如“炸死N”自然不必经过“炸N死”阶段,但表达这类动补语义的最早的语法结构是可分离动补组合。,如例[1]46—65:
(1)(世说)饮酒毕。 →饮毕酒。
本文要探讨的是动补结构的重构机制,即最初的可分离动补结构是如何演变为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的,即(1)中宾语“酒”为何后移、补语“毕”为何前移的?
一、目前关于动补结构重构机制的解释
关于动补结构的重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或单独或联合起作用的因素,下面我们先简单分析下这些因素:
(一)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
双音化趋势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动补结构重构的最重要因素,但这个因素是否能单独起作用,学者们并未深入探讨。
王寅将双音化列为动补融合的三大因素之首(其他两个因素是“结构匀称”、“意义密切”[2]240),认为,因汉语构词的双音化趋势的影响,触动补语前移,与动词结合为双音节组合[2]239—240。即在(1)中,“毕”在汉语词汇双音化趋势作用下,前移和“饮”结合为双音节组合。这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石毓智的解释稍有模糊,他认为双音化是动补融合的最根本动因[1]66,语义相关性、共现频率等都是非根本动因。在双音化趋势作用下,单音节的动词和单音节的补语中间若无受事间隔,就会融合[1]76。他又认为,动词和结果融合就会将中间的受事成分外移[1]80。根据石的分析,可以看出,他认为动补受双音化影响而融合的前提是中间无受事成分间隔,但又认为动补中间受事成分外移的动因是动补的融合。
从王和石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或许认为双音节趋势可以单独起作用,但实际上,若不考虑节奏模式和动补之间的语义关系,将动补的融合仅仅归为双音化的影响,很容易让人提出以下疑问:如在(1)中,为何是“饮”和“毕”结合,而不是“饮”和“酒”结合(“毕”也可独自双音节化)?亦或“毕”和“酒”结合(“饮”也可独自双音节化)?亦或者“饮”、“酒”、“毕”这三者均各自双音节化?无论哪种方式都不影响表义。这样,很自然令人不得不考虑到动补之间的语义相关性。这表明,无论双音化趋势对动补融合多么重要,仅仅这一因素本身是很难对动补融合作出充分解释的。
(二)动补之间的语义密切相关性
对于动补之间的语义关系在动补融合过程中的作用,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石毓智认为,动补融合后,因补语语义普遍性及动补之间的语义密切关系会促使一些补语进一步发展为语法标记(即体标记)[1]67。结合上面谈到的石的关于双音化在动补融合中的作用的观点,可以看出石似乎认为动补之间的语义相关性仅在动补融合后才发挥作用,让补语进一步发展为语法标记。
王寅认为,因动作和结果之间存在密切的语义关系,概念距离紧密,故动补组合到一块,使得其句法距离象似其概念距离[2]240。在王的理解中,没有处理好这一因素同“双音化”、“结构匀称”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解释仍存在很多问题,见下文分析。
刘辰诞认为动词表动作过程,补语表终点边界,二者语义上紧密联系,促使补语靠近动词[3]235。这种解释并不严密:一是因为脱离受事宾语的动词本身并不能表达与结果相对的完整的动作过程;二是由我们下文分析可见,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比动词和补语的关系要紧密。有学者可能会认为“砍”和“倒”经常共现,故语义关系密切,所以会融合;但据“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显示,“砍倒”225例,“砍树”333例,故仅从共现频率上来看,也不必然得出“砍”和“倒”之间的语义关系比“砍”和“树”之间的更密切的结论。由我们后文分析可见,“砍”和“倒”语义关系密切并不是因为经常共现,而是由可别度造成的。
结合上文对双音化趋势的分析,我们认为,促使动补融合的最终动因是概念上的或语义上的,但起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动补之间的所谓的密切语义关系或概念距离,原因有两个:
一是若动补之间因概念距离相近而融合,来源同汉语相同的英语中的动补结构[2]140应当也有类似的表现,但事实是英语中的大多数动补结构中动补并未融合,其间仍要被受事隔开,概念距离观点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二是在最初的动补结构所表征的动补概念结构中,动作和结果这两个概念成分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最近的,动作和受事、受事和结果才是距离最近的,如下所示(以“砍树倒”为例):

在“砍树倒”这个动补初始结构所表达的动补场景中,施事动作“砍”首先作用到受事物体“树”上,一般要经历一个砍的过程,最后树才会“倒”。这是典型的、自然的动补场景,由此决定了我们对这种动补场景的感知形成的最自然的概念结构就如上图所示。说它是最自然的认知结构,是因为它模拟了现实场景的变化情态:右向箭头代表发生/感知顺序。
这不仅可以解释汉语动补结构的初始结构为何是石毓智所说的“可分离动补组合”以及当代英语中的动补结构为何也多是“可分离动补组合”,同时也可说明在我们对动补场景的感知所形成的概念结构中三个概念成分之间的距离关系:“动作”和“受力对象”距离最近,“结果动作/状态”和“受力对象”距离最近。
在汉语中,后来“倒”前移和“砍”组合并融合为双音词,我们认为“砍倒”最终固化成双音节模式的双音词是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但导致“倒”前移的很显然应该是概念距离之外的其他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我们后文所谈到的“可别度原则”。
(三)结构——边界原则
这个原则由刘辰诞提出,他认为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是人类的感知规律——完型趋向律影响下的作为人类基本认知模式的结构——边界原则在语言结构组织和识解过程中运作的结果[3]221—246。
具体说,刘认为例(1)之类的结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饮”和“毕”作为动词与动词整体双音节模式不和谐,故在其所谓的“相似原则”(类比双音节动词)作用下,“毕”前移和“饮”结合为双音节动词;之后又在“相邻原则”(“饮”表使役,“毕”表结果,二者语义相邻)作用下被识解为一个整体;之后“包容原则”(将封闭区域感知为整体,动词和补语分别表动作的起点和终点,构成封闭区域)将“饮毕”作为一个闭合整体[3]235—236。
刘的解释有点复杂,实际上是糅合了上述双音化趋势和概念距离两个因素,另外添加了“包容原则”。前两者我们已做分析,而“包容原则”实际上并未增加新的信息,因据刘的解释,“相似原则”和“相邻原则”似已足以说明动补融合的动因了。
我们认为以上三种解释的缺点有三个:一是不简洁,往往需要几个因素共同起作用,但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处理;二是不具有普遍性,不能同时解释英语和汉语中动补结构的情况;学者们在为汉语中动补融合提供解释时,基本上都忽略来源同汉语相同但发展结果却差别很大的英语中动补结构;三是仅仅是假设,无法直接得到形式上的证明。
二、可别度与动补结构的重构
我们认为,汉语动补融合的首要原因是可别度原则的作用,在此原则作用下,补语前移、宾语后移导致动补组配,之后动补组配才有可能最终融合为以双音节为优选模式的词(当然最终还需双音化趋势的作用,其作用后文还会谈到)。宾语和补语的可别度区别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宾语和补语的相对复杂度
汉语中动补融合已经完成,英语中动补结构仍停留在源结构阶段,但个别用例已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探讨动补融合的原因很有启发性,先看两个例子(选自BNC语料库):
(2)Keep away from him.He can spit hard enough tokknnoocckka manddoowwnn.
(3)Nevertheless,the blast from a cruise missile wouldkknnoocckk ddoowwnnhouses several kilometers away and kill people up to 6 km away.
一般认为,英语中动补结构的宾语位于补语之前,如例(2)所示(这是动补结构的源结构状态),只有少数例外情况,如例(3)。但是,在我们检索的实际语料中,这种宾语居补语后的用例并不少见,又如(选自COCA语料库):
(4)He tries towipe aawwaayythe mud to look at them,but……
(5)Wipee ooffffdust with a tack cloth.
(6)No lions or tigers had escaped.The rhino?He’d justknock ddoowwnnthe wall.
当然,这些用例相对比例可能并不是很高,但考虑到英语动补结构的源结构也是VOR(动宾补)式的,我们可以认为,英语动补结构的补语也发生了前移趋势;当然,这个趋势的进展比汉语要缓慢得多,原因我们后文还会谈到。但另一个重要的与动补融合相关的现象是,学者们也许很少重视到,在英语中,当宾语是长而复杂的成分时,绝大多数用例中宾语最自然的位置都是在补语之后,如例(3)所示①虽然目前未见学者对英语中这种用例中宾语和补语相对位置的频率统计,但据我们对COCA语料库相关用例的观察以及我们的语感,绝大多数这种用例其宾语都是居句尾的。。
这些例子和现象给我们两点启发:一是,汉语和英语的动补结构在历史发展中都发生了相同的补语前移、宾语后移趋势,为这种变化提出的任何解释应该能同时适用汉语和英语。学者们为汉语动补融合提出的双音化、概念距离、结构-边界等解释很显然不适用英语;二是,从宾语和补语的相对复杂性及其句法位置这个角度入手,或许可以找到动补融合的原因。
着眼于宾语和补语的相对复杂性及其句法位置,就涉及到了可别度原则,即“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低的成分。”[4]什么是“可别度高的成分?”我们的理解是,组构句子成分时,其表征的信息越容易确定,这种成分可别度越高;所谓的“新旧、生命度、数量、有界性”[5]等都是确定信息可别度的不同角度。那么,可别度原则可以简单表述为: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越容易确定的信息,其相应的句法成分位置越靠前。
可别度原则是人类语言普遍遵循的一种句子信息组构原则。张伯江、刘丹青认为,人类的语言普遍遵循“重成分后置”原则,重成分是相对于相邻成分而言长而复杂的单位[6][7]。我们认为“重成分后置”的本质其实就是可别度低的成分后置,体现的仍是可别度原则。陆丙甫认为句法成分的排序遵循“内小外大”的原则,即小块成分会向内移动,而大块成分则会向外移动[8]。很显然,“内小外大”和“重成分后置”原则的本质是一样的,体现的都是“可别度”原则。
下面我们看一下“可别度”原则对动补融合的解释,先看上述例(3)中相关动补结构:
……knock downhouses several kilometers away.
很显然,宾语的长度远大于补语,就其所包含的信息量而言,毫无疑问也是宾语要远大于补语;就可别度而言,自然是补语要大于宾语。这样,当我们组构这个动补结构时,最自然的组构顺序应是先补语后宾语。这是为何在英语中这类句子最常见最自然的顺序是补语居宾语之前的原因。
既然可别度原则是人类语言普遍遵循的原则,汉语中动补结构无论古今自然也应遵循可别度原则,如(现代汉语的用例选自北语语料库):
(7)打破大滑石千许,乃可得一枚。(抱朴子)
(8)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子挺签破窗寮上纸。(金瓶梅词话)
(9)先是撞倒一骑三轮车的60岁老汉……
(10)战不群就差点撞倒一位匆匆忙忙从门内冲出来的大肚婆……
假若将这四例转换成动补结构的源结构,即可分离动补组合,就是:(*表示句子不成立)
(7*)打大滑石千许破,乃可得一枚。
(8*)悄悄向窗下用头上簪子挺签窗寮上纸破。
(9*)先是撞一骑三轮车的60岁老汉倒……
(10*)战不群就差点撞一位匆匆忙忙从门内冲出来的大肚婆倒……
很显然,无论从组构句子的角度还是从理解句子的角度看,宾语越长,转换后的用例就越难以接受,原因就在于违背了人类语言组构句子信息时普遍遵循的可别度原则。在古汉语中,当动补结构是VOR这种源结构时,O基本上都很简短,像“打汝前两齿折”[9]这种O较复杂的用例在传统中土文献中很难见到,原因就是可别度原则的制约。但是因为我们下文谈到的感知难度不同(详见下文分析)的原因,O相对于R来说又有变得长而复杂的内在需求,而可别度原则又要求长而复杂的成分靠后,短而简洁的成分靠前,这样就促使VOR演变为VRO,此时,O才会据表义需要肆无忌惮地变得长而复杂,如(9)(10)所示。
就是说,从整体上看,在动补结构中,宾语倾向于比补语长而复杂(相反的情况很难见到,原因就是我们下文所说的我们对补语表征的动作或状态的感知难度整体上大于对宾语表征的名物感知难度造成的,详见下文分析),造成宾语的可别度比补语低,在可别度原则作用下,宾语倾向后移,补语倾向前移。另外,有的例子中宾语并不复杂,如(1)(4)(5)、(6),为何也要后移呢?这与宾语、补语与动词共现频率有关,下文就分析这一问题。
(二)宾语、补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
造成动补结构中宾语可别度比补语低的原因还在于二者与动词的共现频率不同①虽然学者们也经常从动补高频共现解释动补融合,但并未见学者们对动补为何会高频共现做出详细解释。,从而造成二者的可预测性不同,也就造成可别度亦不同。整体而言,宾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比补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要低得多,原因如下:
宾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分析(为便于分析,仍以动补源结构为例):

这个替换分析说明,在“撞O倒”这个现实场景中,受事可以是能被撞倒的各种不同事物及以不同形态出现的这些事物,其数量难以估计(当然,因为“语法结构的非递归性”[10],受事也不会无限长)。这样,在动补结构中表征受事的宾语的数量也相应难以估计,这就导致每一个具体的宾语和动词“撞”的共现频率要比下文分析的每一个具体的补语与“撞”的共现频率低得多。
补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分析(补语用例来自北语语料库):

就这个例子而言,我们在北语语料库利用综合检索仅得到这三个补语,就算还有其他补语未出现在北语语料库中,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补语动词本就是一个封闭的类[11]。(注意:虽然多数性质形容词也能直接做补语,但若动词和宾语确定后,能做补语的性质形容词就很少了,如“煮熟饭、修好车”等,“熟、好”的可替换性很弱;相反,若动词和补语确定后,宾语的可替换性就很强,其数量是难以估计的。其结果同此处分析的“撞树倒”没有不同,均可证明补语同动词的共现频率要远高于宾语同动词的共现频率。)。
结合上面的动宾共现频率分析,可见就“撞”这一动词而言,与其共现频率较高的很显然是数量有限的“倒、断、毁”等几个补语,虽然宾语中也有共现频率的差异,但均很难与这几个补语比较。若是将汉语中能带宾补的动词均如此分析一遍,其结果应该不会有明显不同;我们认为这是由我们对补语表征的动作或状态的感知难度整体上大于对宾语表征的名物感知难度造成的;因名物相对形象,动作或状态相对抽象,形象事物较易感知,故易于形成丰富复杂概念,对应语言形式也丰富复杂;抽象事物不易感知,故形成的概念也相对简单,对应语言形式也简单得多。
因此,可以说整体而言,在动宾补即VOR结构中,V和R的共现频率要远高于V和O的共现频率;这样,在组构VOR结构时,当V出现时,与其高频共现的R自然要比O具有更高的可预测性,从而更容易确定;据可别度原则,越容易确定的成分位置越靠前,这就促使R前移与V组配,O因相对不易确定,自然只能后移。
上面我们从“宾语和补语的相对复杂度”及“宾语、补语与动词的共现频率”两个方面论证了在VOR这个结构中,R的可别度要比O高得多,促使R前移与V组配、O后移居尾。但是,这仍然留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何在英语中V和R未普遍融合?二是,为何汉语中V和R融合的结果多是双音节的?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都与汉语中存在而英语中没有的词的双音化发展趋势有关。
三、双音化与动补结构的重构
可别度原则决定了无论汉语还是英语中的补语最终都要前移与动词融合,汉语已完成动补融合,而英语只有部分用例发生动补融合,我们认为这种进度的巨大差异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双音化趋势造成的。双音化伴随着汉语词汇的形成过程,将新形成的词汇固化为以双音节为优选的模式;词汇化的形式是临近高频共现的单位融合,其认知机制是“组块的心理过程”[12];我们认为“组块”其实就是将经常关联的概念成分组成更大的概念结构,以便有效地组织信息,这同可别度原则的功能是一样的。当然目前学界仍无法解释为何组块的结果多是双音节的。
据我们上文,动补共现频率远高于动宾,那么,可别度推动下的动补融合,形式上也是临近高频共现的单位的融合,也是一种概念上的“组块”过程,由此可见动补融合过程其实也是词汇化过程。(注意:可能一般学者不会把“撞倒、踢倒”等看作词,我们认为原因在于“V倒”具有“平行周遍性”[13],即V可平行周遍到每一个表施加外力的及物动词,但这只是将“词”处理为有限单位的策略,动词和补语的融合过程和构词成分融合成词的过程,本质是一样的,即都是概念上的组块过程。)既然是词汇化过程,那汉语中的动补融合就必须受到汉语词汇发展的双音化趋势的制约,其最自然的、最优选的音节模式就只能是双音节的,以便同汉语词汇整体上以双音节为主的音节模式相和谐。
要特别注意的是,补语前移和动词组配后要进一步发生融合才能算是开始了词汇化,并进一步顺应词汇整体的双音节模式而固化为双音节的词。这里关键的一步是发生融合,但是,高频共现的单位不一定就会发生融合,如“买菜、种菜、看小说、看新闻、听音乐、拿过来”等虽然也是高频组配,但却均能轻易扩展,并未紧密融合;而不融合就不会发生词汇化,自然就不必以双音节为音节优选模式,更不必以稳定的双音节模式出现。学者们借助双音化解释动补融合时均没有解释为何动补组配后又发生了融合而词汇化了。我们认为动补组配后之所以能发生融合,是由两点原因造成的:一是,补语的语义角色是补充性的、辅助性的,即配合核心动词表义,这就造成补语容易倾向于成为核心动词的紧密依附成分;二是,补语表义功能的专门化;我们前面论证了补语同动词的共现频率相对较高,另外,同一个补语往往还可以同多个动词组配,以“倒”为例,可以有“砍倒、劈倒、勾倒、撞倒、踢倒、推倒、碰倒、吹倒、掀倒、扳倒、撂倒、射倒、打倒、砸倒、震倒、迷倒……”这些动补结构表征的是不同但又有相似特征的场景,相似特征由“倒”表现;这样,与不同动词的高频组配,也促进了“倒”发展出紧附动词后(“倒”与动词间只能被“得”、“不”隔开,或构成“一V就倒”等固定格式)专门表达某一类补充语义的功能。这如同某一实词,因能专表某一类语义,后发展成为词缀,便只能紧密依附核心成分;“了、过”由实词经补语阶段进一步发展成为只能依附动词的体成分,就是因为这两个成分相对于其他补语可以同更大范围的动词组配表达某一类语义,从而演化为更为专门的表义功能即体标记。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上文留下的两个问题:汉语中的动补融合首要的触发因素固然是可别度原则,但又因汉语中存在词汇发展的双音化趋势,故因补语的辅助性语义角色和语义功能的专门化而发生融合,并进一步词汇化的动补组配,最终形成以双音节为最优选音节的结构;故双音化趋势对汉语动补融合起着强大的制约和整合作用。在可别度原则和双音化趋势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汉语动补融合比较快而规整。而英语因为没有汉语那种强有力的词汇发展的双音化趋势来整合动补结构,只有可别度在起作用,故其动补融合进度比汉语缓慢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
四、总 结
汉语中动补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制约人类信息组构的可别度原则,在此原则作用下最终可别度相对较大的补语前移、可别度较小的宾语后移,从而促进了动补的高频组配;而之所以最后形成以双音节为最优选的音节模式,是因动补组配中补语的辅助性语义角色和补语表类义的专门化功能而导致补语同动词发生了融合,这个融合过程也是临近高频共现的单位融合成词的词汇化过程,受制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双音化趋势,最终才形成以双音节为最自然、最优选音节模式的动补结构。而英语中因不存在双音化的词汇发展趋势,只有可别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故其动补融合进度没有在两种力量作用下的汉语那么快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