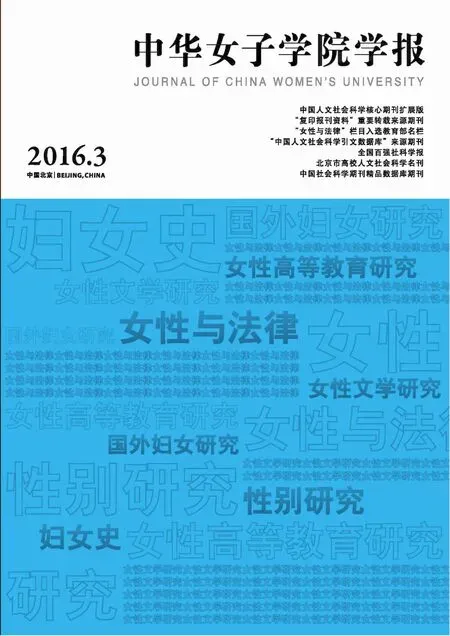婚姻是艘摆渡船
——河野多惠子《回转门》中的女性形象
肖霞
婚姻是艘摆渡船
——河野多惠子《回转门》中的女性形象
肖霞
主持人语:日本女性文学的“文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一种有自觉意识的女性的发言,因为就写作女性的观念而言,她们始终处于社会的前沿,能够感知社会跳动的脉搏。虽然说文学文本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经过加工浓缩的东西,但这属于一种艺术范畴的人类的精神产品,所以说,女性文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女性文化结构的钥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作为艺术的女性文学“文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从女性文学文本的写作价值取向来看,埃莱娜·西苏认为:“女性的文本必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像火山般暴烈,一旦写成它就引起旧性质外壳的大动荡,那外壳就是男性投资的载体,别无他路可走。假如她不是一个她,就没有她的位置,假如她是她的话,那就是为了粉碎一切,为了击碎惯例的框架,为了炸碎法律,为了用笑声打碎那‘真理’。”这就是说,女性的写作就是回返她们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曾经被男性文化所收缴,不仅被收缴,还被比附成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象。
这里刊发的两篇文章,都从文本研究出发,深入探讨了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存在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等问题。河野多惠子的《回转门》针对潜藏于人之内心深处的性欲望与性幻想,通过对性的升华去触摸女性从正常到异常、从此岸到彼岸的人的自然属性及其隐秘性,集中展示了被“不生产的子宫”所掌握的女性们各自不同的真实形象。小说构思新颖、主题鲜明,其内向性的浪漫以及独特文体酿就的怪诞和滑稽给日本现代文学带来一股新风。《浦岛草》以宏大的空间设置和场所转移追述战争,将历史与现代、国家与个人,男人与女人联系在一起,通过对登场人物夏生、雪枝和马莱克的描写,以民族记忆的形式凸显战争、暴力与女性问题,揭示了大庭美奈子文学的流亡主题和试图探讨的回归意识。
当然,女性文学文本的解读亦是基于每位阅读者的自身修养和个体体验的一种批评性阅读过程,每一位读者的艺术感受力、艺术推想力、知识储备力以及社会认知能力都是有区别的,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亦各不相同,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
摘要:河野多惠子的小说《回转门》以真子的视觉和感受,描写了婚姻带给女性的存在感和生命体验,以及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反思。小说看似平淡,实则通过草根女性的人生经历探讨了现代婚姻的意义和价值,进而揭示了婚姻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况、生命价值和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读后发人深思。
关键词:日本文学;女性;形象研究
河野多惠子(1926—2015),日本现代小说家、艺术院会员。1961年发表处女作《捕捉幼儿》,受到文坛的关注。其后在长达50余年的文学活动中,发表小说40余部,其作品受到文坛高度评价。1961年《捕捉幼儿》获新潮同人杂志奖,1963年《蟹》获芥川文学奖,1966年《最后的时候》获女性文学奖,1977年《谷崎润一郎与肯定的欲望》获读卖文学奖,1980年《一年的牧歌》获谷崎润一郎奖,1991年《木乃伊的猎奇谭》获野间文艺奖,2000年《日后之谈》获每日艺术奖,2002年《半所有者》获川端康成文学奖。河野多惠子很好地继承了近代唯美派大师谷崎润一郎的文学创作风格,作品多描写女性的受虐与异常性爱,进而描写女性的性欲望与身体解放,其大胆的性爱描写体现了其独特的文学性格,故在日本文坛独树一帜。在河野多惠子的众多作品中,1970年11月发表的长篇小说《回转门》颇具代表性,小说针对潜藏于人内心深处的性欲望与性幻想,通过对性的升华去触摸女性从正常到异常、从此岸到彼岸的人的自然属性及其隐秘性,集中展示了“被‘不生产的子宫’所掌握的女性们各自不同的真实形象”。[1]239-240小说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构思新颖、主题鲜明,从而倍受文坛关注。小说家日野启三曾将其称作改变日本文学风土本质的作品,认为它是当年日本文学的重要收获。小说的新颖性主要表现在对文坛既有的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创新,促发人们思考如何处理小说中的现象与观念之间的问题。作者旨在通过主人公日常的性动作与心理的现实描写表现女性的深层心理,以感觉观念化、观念感觉化的相互交汇形式表现女性存在的意义。
一、在平淡婚姻中寻找女性生存的意义
长篇小说《回转门》主要以女主人公真子再婚后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描写了她极为普通的人生经历,揭示了成年女性的家庭生活以及心理需求和对人生的思考。“回转门”,顾名思义是一半里一半外,寓意小说通过对婚姻现实生活的描写,管窥人们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心灵世界。事实上,婚姻更像是生活中的一艘摆渡船,虽然有的人不曾涉足婚姻,但绝大多数的人都离不开它,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来回往返。已经步入中年的女性真子就是婚姻渡口的常客,她曾经历过两次婚姻,离异后过着自由的单身生活,后经别人介绍认识了现任丈夫金田。金田是位普通的公司职员,两人交往了一年后结婚。结婚七八年来,夫妻两人过着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日常生活。只是丈夫有些好色,与多位女同事甚至是朋友的妻子有染。真子也一样,除了丈夫之外还与他们夫妇共同的朋友长泽有染,后在丈夫金田的操作下,上演了“互换夫妇”的闹剧。
小说共有两大部分构成,前半部分为小说部分(1—5章、终章),后半部分(别章)为戏剧部分。舞台也和其他作品一样,限定在女性生存的场所——家中或是房间内。小说第一章由金田夫妇从金田工作地九州返回原来居住的“社宅”,不久后又忙着搬回自己的家写起。他们自己的房子在他们去九州之后就借给了朋友的朋友佐伯夫妇,现在已经提前空出来了,在他们忙着搬家之际,佐伯夫妇也来帮忙。作者以自己生活中的搬家经历为蓝本,对此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从搬家来看,丈夫金田在家说一不二,拥有大丈夫的特权,妻子真子为人随和,作为受支配的女性,按照丈夫的要求行事。二人之间看似平常无奇,实则经常发生矛盾和对立,结果也都不了了之地过去了。例如,在收拾好家具用品等待搬家公司和帮忙的朋友到来之时,金田提议说,自己随搬家的一起先去,要真子把这里清扫后再去。这一安排与真子的计划完全相反,她也想和行李一起到达,原因是她感觉到达的行李被无计划地搬进去,会很麻烦。如果不从一开始就考虑好收纳的场所和顺序就会二次费事,而费事的工作还需由她来完成。尽管她有自己的想法,但丈夫不听,直接告诉她: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按照命令去做就可以了。这看似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家庭的普遍形态,即丈夫的大男子主义和妻子的被动地位。可以说,小说就是在这样貌似平常、实则极为不平等的状态下展开情节的。真子作为女性,虽然看上去被动,但她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作者就以她的视角描写了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对自我生存的思考。
当真子回到二层清扫完毕后还没有下楼,就听到关闭车门的声音。当她下到房门口时,看到丈夫乘坐的卡车晃动着高高的后影,拐过弯开走了。被安排留下来打扫卫生的她开始清扫房间,清扫完毕后提着垃圾袋去扔垃圾,明明看着贴着的告示:“回收日之外,请不要往这里放垃圾。”当天并非回收日,她却毫不犹豫地将垃圾袋放在告示的旁边。然后回到二层去擦榻榻米,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真子的意识渐渐沉浸到自我的遐想世界,她想到了这个空旷的房子、运走的行李,感到这个家自己一个人居住也不错。“她想象着什么也没有的房间,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布置的情景。买个小橱柜、小饭桌,用小锅如同过去那样再做一个人吃的饭菜,一个人默默地品尝,或是看电视或是读书,之后躺在地板上以人生的一天得到满足的心情进入睡眠。那样的生活还有什么不满足吗?如同与金田的婚姻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一样。”[2]14她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两次“单身生活”,第一次是在姑娘时代,她认为那是自己一段时间的经历,当时单身生活并没有不好的感觉,她并非完全不懂,但由于未婚意识产生的期待与不好意思导致她爽快地品味单身生活受到牵制,使她犹豫不决。第二次“单身生活”就与第一次大相径庭,她在不知不觉间能够爽快地品味单身生活的情趣了。当想起与金田的婚姻时,“她对单身生活并没有特别的留恋。她虽然沉下心了,但考虑到自己的过去,还是怀着感激之情与金田再婚,另外,她与他之间的再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陷入到后悔的境地。”[2]14但是,她却“在现在的婚姻生活中意外地如同那天突然被单身生活所吸引。……单身生活的情趣——她很想再自觉体味一下那种情趣”。[2]15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她感到这样过是人生,那样过也是人生。她对人生问题的看法与众不同,认为人不应该关注生活方式,而应该仔细体味细节。“她从很早就认为,人生并非在于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才有人生,只有细节才是人生本身。她对目前的生活不是感到特别不满,以及突然被单身生活所吸引,或许皆是与之有关。”[2]15由于自己过分关注以往的“单身生活”,在空无一人的大房间里,她甚至想到乘坐卡车搬运行李的金田如果在途中与那些行李一起“融化”在天空中,她也不会特别地惊慌失措,因为那样之后,自己就可以开始单身生活了。不仅如此,她还想起了一人单身生活时如何使用家具的愉快。进而想起了从很晚的洗澡堂心情爽快地回来,打开房间的电灯,发现要走时一直睡着的睡床时所产生的满足感,以及没有外出的预定,也在没有来客时的周末下午,一个人自由度过的轻松时光,等等。这些生活的细节在她看来,并非毫无意义,而是人生本身。正因为她持有独特的人生观,她才认为单身生活并非那么令人讨厌,从而越发想要体味其中的奥妙。她把目前与丈夫金田的生活看作为另外一种人生,并感到离自己相当遥远,其遥远甚至让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十分思念的感觉。
当真子乘坐出租车赶到自己的新家时,看到卡车上还有衣橱和桌子没有搬下来,同时遇到了前来帮忙的佐伯夫妇。当收拾行李告一段落时,大家纷纷离去,只剩下佐伯的妻子滋子留下继续帮忙。搬到新房子的喜悦促使金田对真子表现出两人特别的亲昵,使得真子全身紧张,似乎感到金田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进而想到,自己的紧张他知道吗?她更加感觉到脊背的灼热。然而,当她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时,金田却很认真地要求她外出购物,并补充说要一个小时左右。这时,真子“感到他的真正的想法这次似乎明白了一半。他垂涎欲滴的是佐伯的妻子滋子。他的意思难道不是为了他们两个人,希望她暂且把家给空出来吗?看着他将视线移向别处,她的视线也转向一边。两人都沉默不语。她的沉默是因为自己的推测不会有错。他的沉默肯定是因为感知到她有所觉察,而不是她的胡乱猜疑。他们两人相互沉默,又相互开导。由于相互间都明白,双方就更加沉默不语。”[2]22真子在短暂的思索之后终于同意自己去购物,“她要一边留在这个家里,一边要将为购物而走在外边的自己表演到最后”。[2]22也就是说,真子毫无抵触地接受了金田的指示,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金田实现欲望的帮凶。
真子坐在楼下长椅子上听着两人上楼梯的声音和其后楼上的动静陷入了自我的深层思维之中,她要给没有根据的事情按上证据。她觉得孤独的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通往二层的空气了,而现在,那凝重的空气和寂静的家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令她深感窒息。“他们在那里,自己完全被排除在一边,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凝重、寂静的空气,头脑里只有这种意识与感觉,使她的想象失衡,因此使她呼吸困苦。……我已经外出购物去了——拿着篮子和钱包正走在商店街上——就要到鱼店前了……但是,商店街和鱼店丝毫没有浮现在脑海。还不如自己那么告诉金田时的印象容易返回到脑里,使她暂且感到呼吸顺畅。”[2]28-29虽然这么说,但金田与佐伯夫人两人在楼上这一事实很快又萦绕在她的脑海,“迫使她更强烈地意识到、感觉到,不得不又陷入到新的窒息之中”。[2]29她甚至想到:“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自己穿过商店街必须有所作为。她的存在并非消极地藏身,而是积极地隐身,这就是与他们之间的关联。她为金田同意的、自己的积极愿望而感到可怜”。[2]29其后,真子咀嚼着残酷的快感,在矛盾与困苦的煎熬中陷入性的回忆与妄想之中。在她的想象世界里,与丈夫金田发生关系的女性或是自己或是别的女人,金田谋求的动作五花八门。她只感到自己被任意玩弄,但被玩弄的是肉体的哪一部分?她搞不清楚。除了五体之外,好像生出了自己未知的新的部分。在三人混杂的性欲关系中,她感到自己在拼命发出欢快的叫声时,咽头被堵住不顶用,她处于痛苦之中。后又感到:“从她痉挛的口腔中流出的只是自己的液体,眼泪与痛苦的眼泪溶为一体。……就连自己也这样,那个人该如何忍受呢?”[2]31她不停地再三追问自己。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坐在客厅休息的真子,在丈夫与其他女性上了二层楼以后引发了她的多层想象,在她快速回转的意识中,肆意将性爱演绎到顶峰。她衷心期待自己何时能借佐伯夫人的身体,与丈夫融为一体。可以说,作者借再婚的中年女性真子性的幻想与想象,揭示了这一年龄层的女性那不为人知的潜在的性意识,展示了女性表面平静实则发达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人无法窥视的异常心理。之后,虽然金田与真子之间再也没有谈过那天的事情,但“真子的心情并非不想触及”。她觉得自己“不能触及,就以不能触及的姿态,力求在不予触及中探究其意义了”。[2]129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之间多次产生默契。但其中多数都是心理游戏罢了。当然,其心理游戏都是非常快乐的。”[2]129回顾这种默契带来的快乐,真子认为并非在于二者之间有什么强有力的关联,而似乎是与并不充实的婚姻生活有关。她发觉自己一直都在那自嘲性的安慰中寻求弥补。然而,金田与佐伯妻子滋子其后的关系,真子一直非常惦念。“她未必没有陷入意外的困境。但其结果,在描绘第三次过着单身生活的自己的姿态时,她又在陶醉感中将其作为奇妙的纯洁的世界加以看待了。”[2]132
这个曾经住过的房子曾借给佐伯家居住。在此期间,滋子曾经多次流产,真子想起这事后为了试探她的心理,主动就女性的“生育”与“人生”问题提出话题。她说:“私人企业的社长,即使儿子并非特别优秀,只要认真地一起工作。早晨开车与儿子一起去办公室上班的路上,在谈论工作的时候,不是会霎时感到很幸福吗?他会感到自己的一生并没有错,自己的人生完成了。——同样,是女性的话,生育几个孩子,有几个孙子的老奶奶。不管是年轻时被男人甩掉的人,三十岁就成了寡妇的人,四十岁就离婚的人,还是现在老头泡妞的情况。……尽管如此,只要孩子和孙子没有出现被刊登在报纸社会栏上的人物,那样的老奶奶就会面色知足。即使不太富裕,从那个儿子那里得到的零花钱给这个孙子当压岁钱,说:‘奶奶给你压岁钱!’不是很幸福吗?我也感到那是很好的。自己的人生完成了——老奶奶虽然不会那么想,一定会有那种心情!没有孩子的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完成了,那也没有搞错。——虽然是这么说,有孩子不管结果是怎样完成人生的人,我都不羡慕。”[2]26佐伯妻子表达的看法更为彻底:“你所说到的那些人,就是他们的人生也并非完成。我认为人生原本就没有完成一说。”[2]27经过这段谈话,真子突然感到滋子的年轻与从容,更加引发了她的无限想象。两人上楼后,她便情不自禁地使劲地干起活来,她知道自己处于亢奋状况,而这种亢奋“大半并不是因为佐伯妻子被绑架了,而像是刚才还在这里的佐伯妻子诱发的亢奋的继续”。[2]27也就是说,作者借助“搬家”这一日常行为,使前来帮忙的其他女性登场,通过与丈夫的简单对话,仔细品味丈夫的意图,由此引发自己对男女之间建构的婚姻关系、性关系,以及女性完美人生的思考。这样的构思深化了河野多惠子初期作品的共同主题,表现为受虐的女性进而面向男性和孩子,通过与其交涉展示自己的存在。因为只有男性与孩子才是女性传统的正当的生命和生活的领域,对其进行否定或大胆地表示异议,无疑就是在否定传统女性的生存方式,以展示女性的人生。对于她们而言,不能生育、生产的女性并非是女性的失职或处于劣位,而是“将女性的性与性感觉从女性所负有的生殖功能中割裂开来,通过对快乐的追求使其自立。在这样的尝试过程中,不孕并非是事实,不孕的感觉才确实让女性体味到性的真实存在”。[2]241
二、“性”之自然与人性的追索
小说的第二章至第五章主要描写了真子对过去日常生活的回忆及生活感受。她与金田结婚七八年了,两人之间没有孩子,但交往的朋友不少,仔细数来,有佐伯夫妇、久米夫妇、过去学校的学长杉野,以及丈夫金田的部下宇津木夫妇,金田过去的朋友——夫妻两人都做律师的殿村及其同僚长泽夫妇等。小说通过夫妻两人与周围男女之间的交往,在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展示真子的内心感受和心理世界,表现了再婚女性独有的心理状态。作者的意图是通过描述真子夫妇的过去生活,管窥导致现在存在的各种生活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纠葛。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把遮阳伞,外人看上去美丽而又优雅风光,但是,这把伞遮挡住的仅仅是阳光,但是却遮盖不住那些见不得阳光的、那些人欲横流的阴风淫雨和反社会、反传统的怪异性爱心态。
对此,小说描写到最近以来,金田夫妇的性生活在欲望的驱使下越发缠绵、执著,从性欲方面看,真子的性欲并非那么贪婪,但在精神和肉体方面膨胀的欲望却使她有些贪婪。她在思索该如何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同时对金田的内心世界充满好奇,热切希望走入其内心深处去探个究竟。她与金田之间的关系,不仅通过性交获得的感性认识,而且通过心理作用产生的“猜想”去做各种推测。在欲望的驱使下,真子与其认识不久且交往不多的律师长泽发生了肉体关系。其后,她将自己至今经历的三个男人(前夫、金田和长泽)做了对比,认为与前夫的性交让她鲜明地了解了男人是“另外的种类”,给她一种移居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与金田的再婚,使她意外地再一次“怀念初婚的那个夜晚”;与第三个男人长泽的关系,使她感受到自己过去就有的“对性的全身心的憧憬”。[2]64对她来说,这种体验越是鲜烈、意外,就越像是有某种预感似的。她猜想金田与久米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在日常交往中用巧妙的心理战术去验证,感触久米夫人的诡计多端与巧妙伪装,并从中得到一种偷窥的愉悦。
真子回顾自己与金田的关系,她认为,“结婚时,两人都没有特别想断绝与异性朋友之间的交往,而且也不相互指责。当时的金田有将认识的女性介绍给朋友,或是带到朋友家的毛病。但真子也没有要责备过他。……夫妇吵架离家出走的女朋友,深夜从宾馆打来电话时,金田也会立即换好衣服前往,她总是毫不介意地将他送出门。”[2]107而她自己也是一样,彻夜地打麻将,以前的男友来电话邀请她去看戏也会欣然前往。有时“金田回到家,她正与前来参加选举运动的男朋友谈得起劲,但金田对这一切从未表示过不满。”[2]107两人之间一直很好地保持“默契”。这种松散的夫妻关系与各自交往的异性朋友交织在一起,混沌、复杂而又互相看不透,真子经常处于深层意识的想象之中,过着现实与虚空交错的日子,她甚至对眼前晃动的树木以及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在她看来,“树梢的晃动好像是因为风,也或是太阳的光与热的缘故,它们冬天也在窃窃私语,春秋嬉闹,夏天充满挑战,为此树叶给人一种摇晃的感觉。”[2]118因此,真子认为,只要阳光充足,人就能体会到活着的幸福,她为此全身感到喜悦。不久又突然感到心情沉重。“被太阳的光辉和热量揉搓到现在的自己,难道不是带有一种人不该具有的懒惰性格吗?还是有一种不该过分亲近太阳、使人堕落的奇怪力量呢?她感到之所以有夜晚,有阴天、雨天,不是因此地球就能够有生物,而是天的关照,目的是不让人完全堕落于太阳。尽管有这种感觉,那天天气晴朗,下午很早她再次感到喜悦。”[2]119也就是说,真子的感觉是对生命与他者的希求以及贪念品味受虐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不是先前那种肉体性的,而是表现在心理方面,即所谓的“心理性的受虐”。
“终章”部分颇具特色,以前去剧场看戏的真子为中心,以现实生活与舞台表演两条线交叉进行的形式,集中展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之社会关系的复杂,以及在复杂关系中体味到的人的生存问题。三个月后,真子接到佐伯夫人打来的电话,她在帮人推销戏票,希望他们能购买戏票和大家一起去剧场看戏。故意晚到的真子在剧场遇到了佐伯夫妇和自家开餐厅的宇津木。戏票由滋子直接寄给金田,金田说好前往但始终未见踪影。按说,宇津木也应该是夫妇前往,但未见其妻子颖子的踪影。确认“只有宇津木一个人来了,真子暂时放松的心情已经所去无踪了。她明显地感觉到,他来了,颖子暂且不说,金田至今也没有露面。”[2]133当戏演到一半时,真子与宇津木两人离开剧院最后去了宾馆的酒吧。不知是宇津木算计真子,还是两个男人之间约好了准备“夫妇交换”呢?小说以读者难以推测的语气提出了倡议。宇津木直接告诉真子:“今晚,颖子委托给金田了。”“那么,颖子也会这样……”“你如果被委托给我的话,你家里就没有人了。或许他们已经去你家了。”[2]148听到这话,“真子感到羞耻,觉得全身就像是被榨得热烘烘一样”。[2]148宇津木的计划与安排似乎很见效。她觉得,“即使被提示的倡议是欺瞒,但自己并没有被欺骗;即使是事实,但自己并没有相信,为了拒绝更为可怕的结果,要清楚地传达自己的意图。”[2]154正是为了要挑战这个“意图”,她同意其倡议。其后,她跟宇津木去了十层的客房,意想不到地接触第四个异性。她认为,“即使宇津木的倡议是事实,对于两个男人来说,或是对于颖子来说,或许都是一场游戏。不管是事实还是欺瞒,如果是事实的话,对于金田来说不论是否是与宇津木夫妇同样的游戏,对她来说都一样。”[2]162真子认为,像自己一样一直过着并不充实的婚姻生活的夫妇,其信赖关系的最后发展就是这样,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自嘲性的感慨使她想到与宇津木的性关系时,似乎“全身充满干劲”,由此越发坚信自己的看法。她觉得,“自己即使被金田杀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的心情就是要拼命穷尽一切所能来审视像自己这样的夫妻的未来发展。”[2]164抱有这种意图的真子在床上越发紧张,那些凌辱性的姿势以及凌辱的想法使她“出乎意料地感到新鲜”,顿感欲望的冲动。然而,“在那一瞬间,真子感到自己背叛了意图,背叛了金田。在忘却意图的瞬间,她出乎意外地被绑架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她觉得好像都一样。她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意图,就要背叛意图,不是为了自己与金田之间的信赖关系,而是因为并非金田的这个男人与自己之间的性的期待,只好背叛金田了。她似乎看到了像自己这种夫妻关系发展的未来。”[2]164-165想到这里,真子感到一阵强烈的悲哀袭来,无法控制地呜咽地哭起来。也就是说,真子在与其他异性交往的过程中,过多地依存于自己的思维,感触欲望的发展。随着深层思维中的欲望发展,她将虚构的快乐置换成现实的快乐。期间虽然自觉到“对意图的背叛”和与宇津木发生性关系的丑恶,但最终不能自我否定。之所以默认“夫妇交换”的行为,是因为对她来说,不在于欣赏自己与别人丈夫之间的性行为,而在于在想象丈夫与他人的性行为中获得快乐,自己分明是在享受这种性的快乐。当然,这一层面上的受虐,即是指超越肉体性行为的幻想。在幻想的世界里经历诸多煎熬和刺激后,真子不得不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自己应有的存在方式?对此,水田宗子指出:“此处的受虐如果是观念性的话,由此唤起的性的感觉也就是观念性的。通过‘不能生产的性’的性感觉获得生的真实感,河野多惠子作品主人公的终点归根结底就是观念的世界。”[1]242
三、河野多惠子文学的特色
可以说,小说《回转门》独特的结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打破了时间的自然发展,按照真子的思维与想象向纵深拓展;二是采取故事情节与戏剧表演并行发展的形式,二者的结合很好地突出了人世间存在的痼疾与黑暗。尤其是在“别章”的戏剧部分,作者以反自然、反现实的想象力,怪诞地将主人公置于一般夫妇、兄妹无法达到的世界,描述了“人工兄妹式的夫妇”关系,可谓是对主题象征意义的进一步深化。作品最大限度地探求想象力的可能性,以双重结构的形式进一步点名主题,可谓是作者的匠心独运。总之,作者通过这部作品旨在探求女性的内心现实,以“夫妻交换”这种乍一看是风俗小说的情节将读者导入另一空间,在虚构与现实相互交汇中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以反自然、反现实的怪诞手法集中展示了女性的深层意识,表现了河野多惠子文学的独特性。对此,作者曾指出,小说“表面咋看什么也没有,与其底部的存在,与回转门的哪一侧都不能说是表与里的关系相似”。[3]可以说,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真子的日常生活,在人际关系的纠葛中展示女性的深层心理,欲在幻想的世界里探求女性的主体性的性和与生殖割裂后的性感觉,在性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性幻想构图中,表现被压抑女性的性的回音,叩问处于“并不充实的夫妻关系”中的女性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可谓寓意深刻。
文艺评论家佐伯彰一曾指出,通过这对夫妇形象建构的小说,是如何深入地反映出女主人公的感觉与心理蒙受浸润,并“被关联”下去的,此处是这部长篇的独创性。……这样自然而抽象地描写性爱的小说,无与类同。小说并非靠小题大做的情节与背景,虚构对这对夫妇来说,既是游戏也是核心,作者以不容否定的确切性探讨了其所具有的双重性。这部作品“可以说一边描写女性,一边直面普遍的人性问题,在此给女性文学带来深度与宽度”。[4]日本学者近藤功也曾指出,河野的文学不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极为重视的“求道性实践者”的文学,而是“人间性认识者”的文学,她通过创作证实文学的本质,其作品对于评论家来说是富于诱惑性的。[5]可以说,河野多惠子的作品是在“用一般道德中涌现出来的日常性的视角和悠闲的无机文体描写受虐、施虐等男女之间的异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象征性,这是分析和认知河野多惠子文学的基础”。[6]
河野多惠子的初期作品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正值日本战后写实主义小说走向低谷且迎来变革的时期,她以崭新的视角和娴熟的叙事手法连续推出了多部表现同一主题的作品,引起文坛的巨大反响。其创作观念中明显带有的自我满足倾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处于过渡期的现代作家的苦恼。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新一波女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河野多惠子的作品受到女性研究者的重视。女性学者多从女性主义视角,认为其文学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以及明显带有的“不孕的感觉”、“反母性”、“女性性的新发现”等构成其文学基础,凸显了河野多惠子文学的女性主义特色。总起来说,河野多惠子的作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女主人公具有被动性和非伦理性,围绕性本能的性爱描写,展示了女性的嗜虐性;二是女主人公恋爱、结婚,但几乎不生育,且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三是从弱势群体的女性视角表现现代人的自我意识与痛切的孤独感;四是确信灵魂存在,以反写实主义手法(幻想的、超自然的)描写女性的深层心理和非合理的情感世界,冷静、客观地关照生与死,探索现实人生的心理奥秘;五是重视日常性,通过精细的生活现实状况描写,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总起来看,河野多惠子以内向性的浪漫和独特文体酿就的怪诞的滑稽感给日本现代文学送去一股新风,从而受到文坛评论家的高度赞赏。
【参考文献】
[1]水田宗子.フエミ二ズムの彼方:女性表现の深层[M].东京:讲谈社,1991.
[2]河野多鳪子.回転扉[A].河野多鳪子.河野多鳪子全集(6)[Z] .东京:新潮社,1995.
[3]河野多鳪子·川村二郎.対谈:『回転门』をめぐって[J].波.1970,(11).
[4]熊坂敦子.近代女流文学の轨?と现在[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6,(7).
[5]近藤功.河野多鳪子この蛊惑的存在[J].三田文学.1971,(5).
[6]神田由美子.研究动向:河野多鳪子[J].昭和文学研究.1999,(9).
责任编辑:杨春
Marriage Is a Ferry——On Female Images in Gouno Taeko’s Swine Door
XIAO Xia
Abstract:Swine Door, written by Kouno Taeko, describes the sense of existence and life experience that marriage brings to female, and the cogni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female on self-identity from the vision and feeling of Masako. Though the novel looks dull, it reall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modern marriage through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grassroots female, and then reveals their living situation, life value and all kinds of social problems in marriage. The novel makes readers have deep thought on the female image.
Key words:Japanese literature; female; image research
DOI:10.13277/j.cnki.jcwu.2016.03.009
收稿日期:2016-01-10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059-07
作者简介:肖霞,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女性文学。250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表达与价值取向”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JA75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