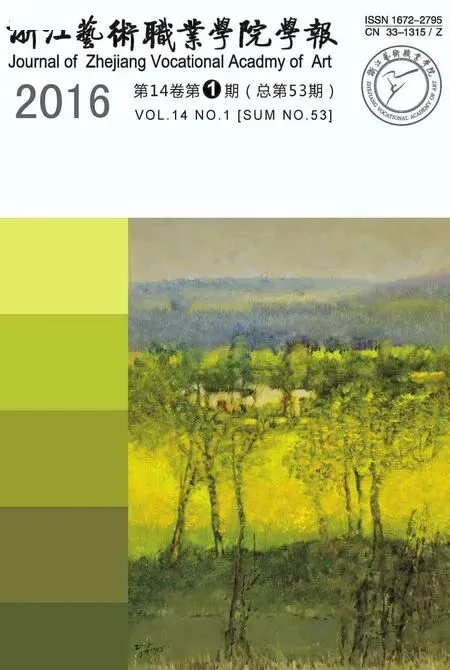重释“大团圆”与“一桌二椅”:中国戏曲美学再认识
沈 勇
重释“大团圆”与“一桌二椅”:中国戏曲美学再认识
沈 勇
摘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戏曲很多体现中华美学精髓的内容与形式被误读、甚至于抛弃,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于当前戏曲的发展来说,搞清楚什么是戏曲的美学精神,在戏曲中哪些能充分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容与形式,这些内容与形式又是在怎样的哲学观照与美学精神指导下形成的,这不仅对于当前戏曲的传承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戏曲今后的发展与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更是具有不可估量之功。
关键词:中华美学精神;戏曲美学;大团圆;一桌二椅
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凝结了远古中华文明的精髓,蕴藏着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和审美基因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集体审美意识,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变和在空间维度上持续交融的历史性结果。“结合新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既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更是民族振兴的一个重大举措。
一、重释戏曲概念:新时期构建戏曲美学体系的关键
非固态形质的中华美学精神,其集体性的审美创造与意识集中体现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戏曲等领域中。而中国戏曲文化因其“血统”的多元性与成熟形态的“晚出”,造就了吞吐万殊、包容万端的特有品质。“大器晚成”的中国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一座丰富的宝库,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多侧面、多层次地映照出中华美学精神的神韵及风采。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戏曲很多体现中华美学精髓的内容与形式被误读、甚至抛弃,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于当前戏曲的发展来说,搞清楚什么是戏曲的美学精神,在戏曲中哪些是有价值的,能充分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容与形式,这些内容与形式是在怎样的哲学观照与美学精神指导下形成的,不仅对于当前戏曲的传承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戏曲今后的发展与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更具有不可估量之功。
应该说,戏曲美学的研究一直受到业界重视。从古代一些专著、序跋、评点、笔记、尺牍中,我们可以看到,前人提出了许多戏曲审美范畴和论断。比如,道与理、精与气、神与形、意与趣、虚与实、真与假、意与象等范畴,以及“传奇皆是寓言”、“因物赋形”、“多虚少实,真假相半”等论断。有很多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已论及戏曲的审美意识。在对戏曲审美的探索中,前人逐步形成了戏曲审美意识的理论化。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戏曲美学的研究逐步走向一个高潮,涌现出了一大批理论著作。比如,张庚先生的“剧诗说”、沈达人的《戏曲的美学品格》、苏国荣的《戏曲美学》、朱恒夫的《中国戏曲美学》、吴毓华的《戏曲美学论》、杨非的《中国戏曲演剧美学导论》及陈多的《戏曲美学》等等。这些戏曲美学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对戏曲的审美价值、审美表现、审美本质等方面作出了论述。
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与不同地方的戏曲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特别是现当代的戏曲本身就缺乏内在的统一,这无疑增大了由感性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难度,再加上“西学东渐”所带来的以西方戏剧审美标准解读、衡量中国戏曲等问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美学体系目前还没有建立。尽管新时期以来戏曲理论界花了很多精力构建现代化的民族戏曲美学体系,戏曲的发展仍然缺乏指路的明灯,创作实践仍然缺乏美学的引领与哲学的关照,这也必然会使我们在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时产生困惑——戏曲中哪些东西是真正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和审美基因的。这是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要排除很多干扰。
应该说,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戏曲,并不具有代表性。最主要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缺少戏曲美学的指引,没有一个明确的专属于戏曲的“美”的标准,结果造成当前戏曲创作乱象丛生、缺少头绪。为此,要传承与弘扬戏曲中的中华美学精神,尽快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戏曲美学体系势在必行。而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一些蕴含了大量中华美学精神信息但又被误读、误解甚至抛弃的戏曲概念找出来,并作出符合其本意和时代要求的重释。本文以当下最为人诟病的戏曲“大团圆”与“一桌二椅”为例,尝试探讨它们与民族的哲学观、美学观之间的关系。
二、大团圆:审美趣味与戏剧结构
“大团圆”既是是一种审美趣味也是一种戏剧结构。以“大团圆”作为结局,是中国戏曲视为必须的、理所当然的、至美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民族性格与哲学思想的程式。这种“圆满”的概念,不仅体现在创作中也体现在观众的审美期待中。李渔认为:“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色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1]。李渔显然是从戏曲创作的要求,把“团圆之趣”视为戏曲之必须。中国的十大古典悲剧,名为悲剧,实质上其最后追求的都是一种团圆的情感寄托。如《赵氏孤儿》满门皆死,独留孤儿,其最后则大仇得报;《窦娥冤》,窦娥死了还以冤魂形象出现,借父亲窦天章之手沉冤昭雪;《祝英台》两人死后还双双化蝶,比翼齐飞,求得团圆;就是原本在十大古典悲剧中唯一没有团圆因素的《桃花扇》,后人仍觉得不满足,而出现了“补恨”的《南桃花扇》,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戏曲创作与审美的一个重要特征,历经数百年而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是,这样的“团圆之趣”近代以来却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先有鲁迅先生的“这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2]的论断,他说“这因为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的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2]。后又有胡适“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的说法。他反复强调“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3]尽管鲁迅与胡适说的是小说,但是也一样适用于追求“大团圆”的中国戏曲。到了当代,在西方戏剧观的影响下,为追求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突出戏曲强大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这样“简单”、“不能引人反省”的戏曲内容与结构自然遭到了更多人的鄙弃。于是戏曲舞台上“团圆之趣”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而貌似深刻、引人深思的“哲理剧”则越来越多。
“大团圆”的戏剧结构与内容果真如胡适所言是中国人“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原因吗?事实上,从鲁迅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鲁迅先生说“这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国民性”等同于“国民劣根性”(尽管鲁迅先生的本意是指“国民劣根性”)而是把“国民性”理解为国民性格或者国民思想品质的话,那么恰恰可以说明“大团圆”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大脑简单没有思辨能力的人随便搞的创作,更不是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审美意识的观众几百年瞎看的戏。这种“大团圆”的创作思想与审美意识恰恰是受到了“国民性”的制约,是在“国民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为什么喜欢团圆?为什么必至如此?为什么不能让观众最后感到不快乐?为什么要当场报应?我想这肯定不是简单的“劣根性”可以说明的,也不是“脑经简单”所致。这里面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的哲学观,更是体现了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
首先,戏曲“大团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循环人生观是“大团圆”产生的心理基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经济,春夏秋冬四季轮换周而复始的自然,形成了中华民族循环发展的理念。并于循环发展中,总结出周而复始的“圆”及物极必反的“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汉书·乐志·郊祀歌》说:“阴阳五行,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人不仅用周而复始的“圆”来解释自然变化的现象,而且引申为社会与人生的变迁发展。是故,“悲者必终之以欢,离着必终之以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戏曲“大团圆”程式,就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而让人快速感应到这种历史必然的就是舞台上的“大团圆”。尽管这种只能在戏台上制造并实现的“大团圆”,多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与臆想之中,但观众却靠着这种臆造的“大团圆”与宇宙人生的大圆相协调,以弥补现实生活的不足,让不完美的人生借戏曲得到慰藉。
其次,“大团圆”是儒家“中和”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指异质因素的融合达到最佳限度,“和”则指异质因素的共处,“中和”突出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与融会贯通,表达的是和谐、适中、均衡有序的美学思想。《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在儒家眼里,“中和”才是人和万物存在的状态,只有行中和之道,最终实现和谐大同的理想境界。在这里,事物对立面之间不再是冲突而应该是和谐的。也就是说,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不同因素其融合与发展变化都应该遵循适当的“度”,最终的指向应该是“中和”。李泽厚对这种“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有过这样的论述:“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4]这种“圆满”、“和谐”的审美意识使中国戏曲走上了与西方戏剧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即:不以宣泄悲愁为目的,而首重团圆之趣。如王季思所言:“如果说西方戏剧将悲剧的崇高和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极致……中国戏曲则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相互调剂、衬托……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节,达到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后的超越。这既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又带有道家阴阳相激、刚柔相济的哲学意蕴,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传统心理的积淀。”[5]
工整、匀称的戏曲结构、悲喜沓现的情节处理、以充满喜庆的“大团园”结局,对观众因现实生活不满而形成的悲观、压抑、愤懑心里的平和关照,正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起着统领作用。通过回避冲突、调和矛盾来达到和谐目的的戏曲,尽管情节有悲有喜,有苦有乐,不论剧情如何起伏跌宕,主人公命运如何坎坷,遭遇厄运后一定能够再次“大团圆”的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生动体现。
再者,“大团圆”是审美伦理道德化观念投照于戏剧结尾的必然结果。中国戏曲历来就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行“高台教化”之能。因为戏曲要表现的是世态人情,而这必然给戏曲打下深深的道德印记。孔子提出仁要尽善、乐要尽美。仁属于道德范畴,乐属于艺术范畴,仁与乐的统一,就是道德与艺术的统一。中国戏曲之所以“贵浅显”,把戏做给“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目的就是能把道德伦理寓于戏中,让所有人能看懂并受教,从而实现艺术与道德教化的完美统一。而在这种统一中,明确的道德判断是极为关键与重要的,不管是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在整场戏的斗争后,必须给观众一个明确的判断结论。中国古人认为善恶应各得其所,极其看重“天理”、“公理”的应验,认为天只福佑有德者,即“惟德是辅”,对恶人一定要施以灾报。因此,在戏曲中剧作者好恶判断一目了然,直观的通过脸谱、服装、行当、程式动作进行表达,或者通过“副末开场”、“自报家门”或是“打躬背”、“唱独白”等等方式直接告诉观众“我是坏人”。如“吃喝嫖赌爱风流,花街柳巷日夜走”也往往成为花花公子、小偷等坏人的“自报家门”。而到了最后,一定要实现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报”,如果最后坏人得不到惩罚,好人得不到好报,那总以为戏未演完。为此,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成为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图”结局。而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皆以惩恶扬善的方式,让恶人得到天理报应,或雷劈、或横死、或遭惩,好人则成仙得道、冤案平反、高中状元、喜结连理……,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之寓,告诫人们要为人以善行。而这一切,既符合人心向善的人性特点,也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可以说,“大团圆”扬善惩恶的结尾,恰恰成了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显示屏,是审美伦理道德化观念投照于戏剧结尾的必然结果。
可见,戏曲“大团圆”的结尾,不是前文鲁迅说的“国民劣根性”,也非胡适所言的“脑筋简单”、“思力薄弱”之故。无论是道家的“道圆”、“和合”、“运转”思想,或者儒家的“中和”、“中庸”、“天人合一”思想,抑或佛家的“默照理圆”、“圆融之境”等观念,在戏曲“大团圆”的处理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戏曲产生并长期流传于民间,从一定意义上说,观众的审美心理制约着戏曲的创作与演出。所以,“大团圆”不仅仅是创作者遵循中华美学精神的结果,更是观众的选择结果。虽然在当下我们应该有更丰富的戏剧结构,带给观众更多的选择,但是,“大团圆”这种深切反映民族心理与民族风貌,真切表现人民自然平淡、和谐朴素的愿望追求,体现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哲学关照,彰显和谐、中和之美,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完善的艺术处理与表达方式,是否不能简单的因为“俗套”、“简单”而遭我们抛弃,是否应该把这精神内核传承下来,并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弘扬呢?窃以为,答案是肯定的。
三、一桌二椅:“空”意境与诗意传统
同样因不了解、不研究而被不断诟病与抛弃的还有戏曲“简陋”的“一桌二椅”。
中国戏曲舞台一桌二椅式的空灵和写意舞台面貌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息息相关。我国古代一直把人看成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把人和宇宙看成互相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而不视为外在于人的对立物。《孟子·尽心》中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是相通的,即天之性即人之性,而人之性也就是天之性。但是,其主体不是天而是人,人在宇宙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宇宙的出发点与归宿,是宇宙的灵魂。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决定了人在时空中的支配地位。人与天地自然既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个整体,那么理解宇宙万物的方式就应该是主观的,而不是主客两分。看待宇宙万物的方式也就不是以单一的视点精确再现宇宙的秩序和物象空间的比例关系,而是着眼于整体,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表现人对自然的感受。这正是我国戏曲表现时空的方法。在戏曲舞台上,不管是时空转换还是现实场景都必须通过演员的表演动作来显示。空的舞台没有是没有任何明确的时空概念的,但是如果演员一上场,做了一个摸黑再开门的动作,时间与空间就马上明确了——“晚上”、“家里”。戏曲的时空观是是一种主观的时空,是一种“我说有就有”的主体的心灵感受,它不追求物象比例的精确再现,也无法做到精确所带来的真实感。其真实,是一种情感的真实,而非物象的真实。也正是这种主观的时空观才能与戏曲的诗性精神相融合,才使得中国戏曲最终走出了一条带有哲学意味的空灵、诗性的道路。
戏曲的诗性精神,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在仪式和庆典中演唱,其创作的目的也是为了以美的声音、不同于生活态的语调与神灵进行沟通,所以,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权威紧密相连而成为上古中国社会的最高秩序。有的诗歌则是与日常生活文化与节庆礼仪紧密相连,“诗歌是一种传统的、集体的创作,是一种在集会、农业节庆、约会、求子、求福等等场合的即兴创作。”[6]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往往都可以从诗歌文化类型中得出。“从《易经》、《诗经》、唐诗、宋词到中国新诗,一部诗歌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在所有文化艺术体式里面,诗是最集中、最形象、最精到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它的确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体式”。[7]“中国文化是一种以诗性智慧为深层结构的文化形态”[8]。刘士林进一步诠释,“诗是民族的‘基因库',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8]“诗性”文化统帅戏曲,便变得顺理成章。可以说,不管是体现在诗化语言的文本“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①王世贞.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页.可见,戏曲乃与诗词一样,为中国一脉相承的文学,在戏曲的创作与理论研究中,强调的往往也是戏曲的诗歌的性质,也就是“曲”。虽然北曲可分为“剧曲”与“散曲”,但是,此中的所指应该是“剧曲”,也就是“戏曲”。所以,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叫做曲论,“曲律”、“曲藻”、“顾曲杂言”、“曲品”、“曲话”等等也被收录在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还是如苏国荣所说:“我国戏曲,从剧本文学到舞台艺术,都有浓郁的诗意,甚至观众的审美观照也带有诗的欣赏性。因而,我们把戏曲称作剧诗,不是单纯指的剧本文学,也包括舞台艺术,甚至观众的审美方式”[9],都说明戏曲的本质属性是“诗性”。这种“诗性”精神绝非仅如文学本所现,舞台上看到、听到的一切,直至于观众的审美心理都是“诗性”的具体体现。然而,新时期的戏曲改革与实践,有很多都背离了这种属于戏曲本质属性的“诗性”要求,原因就在于对中国戏曲诗性精神的认识不到位。把空的舞台与“一桌二椅”看成是物资贫乏的象征,就是一个典型。
空的舞台与一桌二椅,绝不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肇因于当时“路岐人”要“冲州撞府”携带装置不便,更不是因为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因为剧团太穷,只能将陋就简。如果真是这样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现存清宫极尽奢华的皇室大戏台,也只用一桌二椅,而没有多放几张桌子呢?中国戏曲的一桌二椅是与诗性的戏曲美学精神相适应的一种舞台景物造景形式。很多人认为,一桌二椅是戏曲舞台上的道具,事实上,这不是道具,而是舞台装置,是一种充分体现戏曲以简代繁、以简约行诗化的舞台装置。它不仅区分了舞台的内外场——桌子在舞台的正面靠后摆着,它的作用是桌前为外场,桌后为内场。一把椅子放在桌子前面,名为“外场椅”,表示的是客厅或进大门的一间;放在桌子后面便叫“内场椅”表示的是书案、内室书房以及筵席之类。它还能起到“隔离”的作用——戏曲中的“虚下”。如某一脚色在演完了前面的戏后,暂时没有他的戏,可是在剧情行进中他马上又要加入唱念,下场后再上,会把剧情打断,就可以向桌子里边的右侧一站,以背部对着观众,这张桌子,便成为墙壁或者是屏风,把这个脚色和在桌子前面正在演戏的一些脚色隔离起来,表示这个脚色当时并未在场上的“虚下”处理。至于以这一桌二椅模拟造型,以符号式意象,表现不同地点、环境,那更为丰富,可以说只要你想得到,这一桌二椅就能化得出。“山、楼、床、门、阴、阳、殿、堂”皆可通过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想象完成。其摆放样式之多,以浙江绍剧为例,就有“十七把椅子”之说,如在金殿、公堂,放“案位椅”、“阁老椅”;客厅、中堂放“当场椅”、“对面椅”、“三仙椅”、“上下把椅”;校场、辕门放“将台椅”、“辕门椅”;表现阴阳凡间间隔,出鬼魂或者神仙的,放“阴阳椅”、“神仙椅”;表现特定场景的有“寒窑椅”、“牢监椅”、“囚犯椅”、“井台椅”、“石凳椅”、“床帐椅”、“上吊椅”等等。除了用不同的摆设表示不同的剧情地点和人物关系外,还通过围在桌子与椅子上的“桌围椅披”对剧情展开的地点、人物身份进行暗示。如桌椅是黄色色系且有龙凤纹饰,那说明是帝王之家;如为红色色系,即说明剧中这户人家非富即贵;当然如用白色色系,则代表是平民百姓;如果用青色、蓝色等清新亮丽的色彩,则代表是公子的书房或者小姐的闺房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说得很形象:“一把简单的椅子,就代表了高山峻岭和人物所处的情景,青山、白云、乱石嵯峨的山峰和崎岖不平的山路,都一一在演员身段上给表现出来,让观众随同演员身历其境地一起生活在这幻景中。”[10]“简单的一桌二椅遵循的正是戏曲的诗性特征,它弱化了物的因素,强调了人的存在,简约、空旷的舞台,加强了人的主观性,使戏曲的诗性特征能得到极大地发挥,更是突出了戏曲‘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11]“无穷物化时空过,不断人流上下场”。空灵的舞台,正是通过不断的有人上场与下场与程式动作的表演,舞台的时空意义才能显现,才能勾勒出故事表达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布置”出亭台楼阁、河流山川、家里家外……。反之,如果没有这空灵的舞台,这一切也无法实现。
中国传统戏曲舞台因为要表达“诗韵意境”,所以选择了“空”,“空”不是“无”。“空荡荡”的戏曲舞台以“不断人流上下场”的分场方式,为“有无相生”的戏曲之“道”提供了极为丰富广阔的艺术空间——“举步千里,转眼老少”的“时空紧缩”;“想你就能出现”的“异地时空并现”;一声“啊呀且住”的“时空停顿与扩张”等等使得戏曲舞台能搬演出异彩纷呈的场景和千姿百态的人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相送》在方寸舞台不仅走了十八里路,还在观众眼前描绘出了十八里路上树木花草、庙宇水井、河流船埠、樵夫白鹅等等山水人文景观,均是以艺术中的“无”表现生活中的“有”。在空间表现上避实写虚,从而达到有无相生之境,“九尺台五湖四海;三更天七朝八代”①摘录于嵊州市陈侯庙戏台。的戏台楹联形象地说明了戏曲浓郁的诗意抒情倾向和主观时空观。
随着科技的进步,戏曲舞台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桌二椅”俨然成为了贫困、守旧、传统、过时的代名词。在戏曲的现代转换过程中,首先被鄙视并抛弃的就是““一桌二椅”。于是,满台的布景装置、半台满的台阶、比例精确的生活用具等逐渐成为了当前戏曲舞美的标配。更不用说复杂的灯光布置与运用了。动不动就用“定点光收光暗场”,使得传统戏曲丰富的下场法成为了历史,满台的大色块布光,让人恍然置身于晚会现场。把戏曲“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反物质主义与“简约以行诗化”的美学追求,弃之如敝履。满满当当的舞台设置,不仅制约、影响和破坏了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和诗意传统,而且严重地束缚、淡化了演员的表演。很多戏除了唱,演员几乎没什么身段与表演,“描景、抒情、写人”浑然一体的表演模式被残暴的割裂,空灵的意蕴不再存续,戏曲韵味尽失;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戏曲造景、描景的程式不再传承,新一辈的演员能力直线下降,这对戏曲美学精神与演员技艺的改变和颠覆是根本性的。随着时代的进步,把一些科技的手段运用到戏曲舞台,以丰富视觉呈现,这是戏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不能“喧宾夺主”、“主次不分”,更不能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与方法改造戏曲。这一点梅兰芳在30年代就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旧剧有其固有之精彩与好处,不能加以丝毫改变。余年前赴欧洲各国及苏俄,观剧多次,西洋戏有西洋戏之妙处,但与中国旧剧,不能合二为一,此敢断言者。至中国旧剧,原则是不利用布景,若利用布景,反减去剧中之精彩,譬如旧剧中之登楼,系作一种姿势,即可完全表示登楼之状,且甚美观,若依布景言,则剧中布景楼梯,演者一步步上楼,非仅有着衣不合宜,且不好看,转失剧中精彩。②久别故乡之梅兰芳昨偕其夫人自沪飞来.群强报. 1936年9月3日.北平新闻。周贻白也在论著中明确:“中国戏曲舞台布景的原则:第一,不能妨碍脚色们的上下场;第二,不能和演员们的动作有矛盾;第三,不能使空间与时间有所冲突;第四,不能使舞台布景超过剧情。”[12]现在有些作品以“一桌二椅”作为宣传亮点③成都川剧院排《白蛇传》标题就是“青春版川剧《白蛇传》将上演一桌二椅呈现原汁原味”。,作为“向传统致敬的中国传统美学回归之旅”④张艺谋执导的京剧《天下归心》标题是“京剧《天下归心》还原一桌二椅坚持传统”。之举,这至少证明有一些人已经看到了舞台的大场面、越来越复杂的新手段与戏曲诗性的美学精神是相冲突的。“我将用京剧独特的美学体系来创作这部作品,它的简约、象征、寓意、程式化、中国古典的情怀等,我认为这些才是京剧持久的生命力。作为一个跨界导演,面临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让京剧呈现出它最本质的美,而我认为一桌两椅是京剧的起点,所以这次我将用一桌两椅来做一个简约和象征的舞台,用它来传递这样的美感。”[13]张艺谋在《天下归心》中的实践,也至少说明了空的舞台与“一桌二椅”对于戏曲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舞美装置的问题。也许黑格尔说的:“艺术愈不受物质的束缚,愈现出心灵的活动,也就愈自由,愈高级”[14]这句话能很好地概括戏曲秉承诗性原则而千百年不变的本质。
戏曲的“大团圆”与空灵舞台的“一桌二椅”仅仅是戏曲美学宝库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其他诸如戏曲的表演、音乐、服装、化妆、行当、乃至于乐器等等都包含着中华传统美学的精神。在当下,厘清、发现、分析戏曲中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很重要,更重要的则是要把这些好的东西诠释好、表现好,让观众能看明白并且接受。“传承”所要做的是接续中华文化和美学精神源远流长的丰厚脉络,而“弘扬”则是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里,创造性地发展“中华美学精神”的价值,而这既离不开戏曲从业者与研究者的努力,更离不开观众的互动与参与。
参考文献:
[1]李渔.闲情偶寄[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69.
[2]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16.
[3]胡适文存卷一[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207-208.
[4]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36.
[5]王季思.悲喜相乘[J].戏曲艺术,1990(1).
[6]葛兰言(marcel granet),赵丙祥.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M].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
[7]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32.
[8]刘士林.中国诗哲论[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4-7.
[9]苏国荣.中国剧诗美学风格[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
[10]盖叫天.谈表演艺术中的身段[A]/ /演员经验谈:第4辑[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6.
[11]沈勇.在当代传播中‘失真'的中国传统戏剧[J].民族艺术研究,2015(5).
[12]周贻白戏剧论文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81.
[13]天天新报.我有话说[M/ OL].[2013-11-13]. http:/ / ent. sina. com. cn/ j/2013-11-13/16204042222. shtml.
[1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12.
(责任编辑:李 宁)
Reinterpreting“Reunion”and“One table and Two Chairs”:Rethinking on 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SHEN Yong
Abstract: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it is sad that a lot of contents and fo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reflecting Chinese aesthetics essence are misunderstood or even abandoned.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opera,it is important to figure out what is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opera,which contents and forms can fully reflect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and th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acting on the formation.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opera tradition,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opera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 as well.
Key words:Chinese aesthetic spirit;aesthe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reunion;one table and two chairs
中图分类号:J801 I207. 3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沈勇(1968— ),男,浙江杭州人,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教授,主要从事戏曲表导演理论研究。(杭州3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