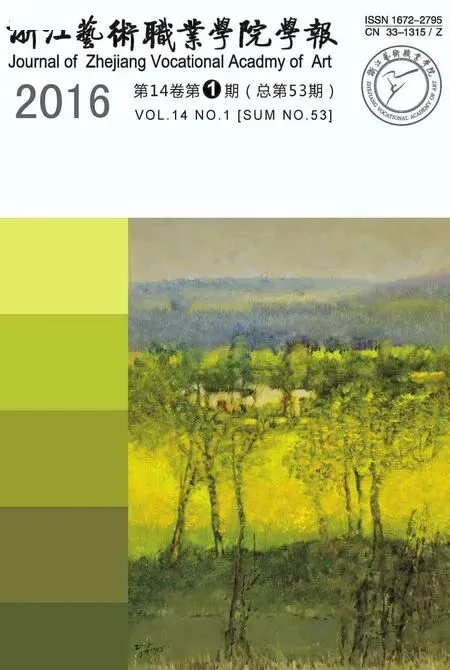从《申报》看昆剧传习所的发展流变及其社会影响
吴 静
从《申报》看昆剧传习所的发展流变及其社会影响
吴 静
摘要:昆剧传习所在昆剧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昆剧“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特殊时期为其传承发展积存了力量。昆剧传习所在近现代昆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后继团体“新乐府”、“仙霓社”与传习所一脉相承,对传统昆剧的保存及表演形式的丰富有突出贡献。昆剧传习所及新乐府、仙霓社在与《申报》的互动中发展壮大直至消亡,从《申报》看昆剧传习所的发展流变及其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为昆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对当下昆剧的发展具有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申报;昆剧传习所;新乐府;仙霓社
发源于江苏昆山地区的昆剧①昆剧、昆曲、昆腔三者有很大区别,不可混用。“昆腔”侧重音乐,相当于乐理中的旋律;“昆曲”是昆腔与唱词的统一,类似于歌曲;“昆剧”则是融合音乐、唱词、舞蹈、美术等部门的综合艺术,是王国维所谓的“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形式。拥有六百余年历史,在明清时期一度风靡全国,并对其后产生的京剧及其他地方剧种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故而被誉为“百戏之祖”。昆曲本是昆山地区的民间小调,流传范围较小,在宋元时期与“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并称“南戏四大声腔”,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汲取南北曲之长改昆山腔为水磨调,从此昆曲异军突起,在其后的二百多年间称霸剧坛,一枝独秀。及至清朝康熙中叶,各地地方戏曲纷纷涌现,更加通俗平易的地方剧种与占统治地位的昆剧展开旷日持久的“花雅之争”,弋阳腔、秦腔先后与昆剧争胜,至乾隆晚期四大徽班进京之后昆剧最终不敌“花部”而败下阵来。一度兴盛的昆剧日渐式微,在清末民初时已滑落至舞台的边缘,仅存的“文福班”、“鸿福班”等几个昆剧戏班生存维艰。为了存留昆剧的一脉香烟,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于民国十年(1921年)在昆剧的发源地苏州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得到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鼎力支持。传习所聘请“文福班”的老演员执教,先后培养学员五十余人,在昆剧濒临灭亡的生死关头保存了“火种”。尽管昆剧传习所仅维持了五年时间,但是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传”字辈艺人,他们在传习所解散之后又组织了“新乐府”、“仙霓社”等昆剧演出团体在沪、苏、杭等地演出,为昆剧的传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昆剧传习所在昆剧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昆剧“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特殊时期为其传承发展积存了力量。尽管存在时间较短,但是其历史性意义不容低估。近百年后的今天,昆剧的生存状态依旧不容乐观。本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剧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昆剧再次濒危成为不争的事实。以史为鉴,回顾昆剧传习所的历史,从中寻求当下昆曲突围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申报》作为民国时期存续时间最长、发行数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报刊之一,当中所贮藏的关于昆剧传习所的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通过对《申报》中相关资料的研读不仅可以梳理出昆剧传习所的发展流变,更能从中窥见其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对于研究昆剧传习所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昆剧传习所创办前后及其社会影响
清末民初,昆剧衰微,仅存留的几个昆剧戏班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如挂着“全福”招牌的文班昆剧演员总共仅有三十余人,不足风头正劲的一些京剧戏班的零头。而且“全福班”等昆班普遍演员年龄偏大,演出市场萧条,这岌岌可危的局面让一批热爱昆剧的吴中人士深感焦虑。出于保守的乡土观念以及对昆剧这一古老戏曲艺术的挚爱,为昆剧保留“火种”的任务就落在了苏州人士的肩上。当时苏州地区私塾渐废,“传习所”作为一种新的传道授业之所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所谓“传习”,《论语·学而》中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顾名思义,传习即传授与实习,传习所区别于传统私塾之处在于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操演。当时吴中地区私人出资开办传习所的多是颇具实力的地方绅士,其中不乏酷爱昆曲的文人雅士,他们有感于昆剧的没落,决心设立专门机构教授昆剧以免这门传承数百年的古老艺术失传。
1920年至1921年间,贝晋眉、徐镜清、张紫东等人发起创办了“昆剧传习所”,地址选定于贝家旧业的西大营门“五亩园”。传习所聘请“文福班”的老艺人授课,招生广告遍布苏州大街小巷,然而由于当时伶人地位不高,因此学员多为贫苦子弟及老艺人的后代。昆剧传习所于1921年秋正式开课,课程设置分为专业课和文化课,不仅由老艺人传授昆剧表演技艺,还特聘文化老师教学员们识文断字,且坚决杜绝传统戏班对学员的体罚。另外,传习所还提供食宿,负责学员们的生活费用,按时发放补贴,由此可见“昆剧传习所”的确是创办者为了保护昆剧艺术免遭灭绝之厄运而倾尽全力。从1921年秋至1922年春,陆续进所学习的学员达到五十余人,人数的增加也让创办者的经济负担更加沉重。为了保证传习所的存续,三名创办者通过昆剧曲家徐凌云的引荐联系到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穆藕初早年留美,思想开明,对戏剧戏曲艺术十分热衷,也曾出资创办戏剧学校,当他了解了昆剧传习所的状况之后便慷慨出资,负担了绝大部分日常费用。除此之外,穆还建议传习所扩大影响,并于1922年初邀请所中师生前往上海演出。由于昆剧市场不佳,其他剧院不愿接纳昆剧传习所的师生演出,穆藕初特地联系了上海夏令配克剧院,这座剧院之前以放映电影著称,鲜少举办剧场演出,为了吸引观众穆藕初亲自登台为昆剧传习所募集资金,此事在上海轰动一时。《申报》对这次演出也有大量报道,于二月初起连续多日刊登广告,从3日持续到演出结束后的14日,每一场演出的前一天必有预告,后一天必有评论。这次演出以会串的形式(类似于折子戏演出),邀请数位名家前来表演自己拿手的折子,如当时名家俞振飞、徐凌云等纷纷登台,穆藕初本人也特地温习数月而出演了《折柳》、《阳关》等片段。据记载这一连三天的演出十分成功,场场爆满,好评如潮,在昆剧衰微、几近无人问津的时期,这此演出让昆剧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不仅如此,组织者还赠送给每位捐款者一本昆曲曲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推广、普及昆曲知识的作用,演出后所募集的经费一并捐赠给昆剧传习所。
此次演出成功与穆藕初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密切相关,正是穆的鼎力支持使昆剧传习所的影响范围扩大到上海,之后从1923年底昆剧传习所陆续在上海的各剧院表演,与此同时穆藕初也会以“参观成绩”为名邀请各界名流前来观看传习所师生的演出。从1924年起传习所的学员们定期在上海“徐园”演出昆剧,前辈名家徐凌云对小学员们给于艺术上的指导使他们的功夫更加精进。在穆藕初、徐凌云等人的在支持下,昆剧传习所的学员们获得了更多实践机会,表演水平大幅提升,演出时常常座无虚席。据《申报》记载:“连日昆剧传习所表演成绩、曲友加串名剧、嘉宾满座、蜚声洋溢、后至者、无容膝之地、或抱向隅而归、昨日主其事者、以四方人士、或有已经胜券而未克入座、与闻风戾止、票额已满、致失迎迓者、议决商请笑舞台主再假一天、添演星期日日戏一天、已得台主允”[1]。由此可见当时昆剧传习所的演出已是一票难求。同年,传习所的第一届学员已跟随“全福班”的老艺人们学习三年,老师们为了让学生们的演艺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遂为其摘选艺名,这一批学生统一定名三个字,中间一字为“传”,末一字根据不同行当以“金、玉、花、水”为名,其中外、末、老生、净等行当名“金”(以金为偏旁),小生行为“玉”(以斜王为偏旁),旦行为“花”(以草头为偏旁),付、丑等行当为“水”(以三点水为偏旁)[2]408-410,这就是昆剧发展史上著名的“传”字辈。
从1924到1926这两年间,“传”字辈学员们在上海、杭州等地频繁演出,仅1925年《申报》上有所记载的就多达数十场,且获得了甚高的评价,《申报》载文称:“昆曲一剧由来已久,迨乎民国日渐衰落,今昆剧传习所能力挽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难能而可贵者也。所有演员皆十余龄之儿童,声调高朗,词句清脆,其中尤以饰时迁之儿童为最佳……”[3]传习所中尚在稚年的小演员们为昆剧舞台注入了新鲜的空气,使观众对几乎被遗忘的古老昆剧又重新燃起些许热情。从1925年12月起,昆剧传习所的学员们定期于每周一二四五下午在“笑舞台”演出,后又于周六加场以满足上班族的需求,这样的定期演出一直持续到1926年底。当年为“传”字辈学员制定的“学戏三年,帮演两年,五年满师”的培养计划已接近尾声,昆剧传习所在昆剧极其艰难的状况下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昆剧演员,让古老的昆剧艺术免于灭亡的厄运,也正是这批演员让昆剧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两年的实习演出期间努力在上海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然而就在“传”字辈即将满师之际,传习所的赞助人穆藕初经济力量有所不济,无力续办下去。就这样,昆剧传习所培养了一届学员之后就难再存续,习得一身功夫的“传”字辈学员开始自己组班在上海演出,于是昆剧传习所时期悄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这批“传”字辈学员开启了职业化的“新乐府”时期。
二、新乐府的凝聚分化及其社会影响
“传”字辈的学员们在传习所学戏的五年里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满师之后他们决定一起组班演出,开始了职业生涯的“新乐府”时期。“新乐府”由严惠予、陶希泉主办,学员们请原先昆剧传习所的所长孙咏雩继续负责戏班的日常事务,邀请俞振飞担任顾问,在上海知名的笑舞台、新舞台、大世界等剧场演出。1927年底,新乐府在笑舞台盛装演出之前,《申报》曾特别刊文宣传:“笑舞台新乐府不日开演昆剧。昆剧一道既具高雅词句又有通俗寓意,去岁昆剧传习所开演于新世界,每日观众满坑满谷,继复在徐园举行,虽地址偏西,上座仍盛。后以他种关系停演,迄今各界致函沪上,著名曲社赓春集者日有数起,足见社会人士雅爱此道之深。近有昆剧家张某良、俞振飞、吴我尊、沈吉诚诸君组织維昆公司,即以笑舞台原址加记新乐府,斥资二万元將院内建设佈置完全改革,金壁辉煌,富丽精雅,所有昆剧传习所全体角色,如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周传瑛、华传萍、施传增等四十余人每日登台。一应服飾行头添置費银四千余元,将来计划除收集整本剧陆续演出外,每星期并恳沪上名剧家轮流会串其拿手杰作,不日开幕定有一番盛况也。”[4]可见昆剧传习所的“传”字辈学员们在帮演的两年及其后徐园的演出过程中,因过硬的舞台表演功夫积累了一批忠实观众,听闻这批原班人马组建新乐府戏班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予支持。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戏剧界,剧院的选择一般都直接代表观众的选择,剧院的包装与宣传是戏班、伶人们职业生涯的晴雨表。犹记昆剧传习所成立之初,上海各剧院不愿接纳昆剧演出,穆藕初只好动用个人关系找到夏令配克剧院;仅仅六年时间,昆剧传习所的师生们就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观众,剧院方面看到了昆剧艺术的生机,为新乐府重新装修、置办行头,这也表明新乐府成立之初即在上海戏剧界占得一隅。
由于新乐府的成员们都是传习所时期的师兄弟,因而在舞台上彼此配合十分默契,而且这份特殊的情感关系也使得戏班内部成员更加团结。从1927年底到1931年中旬,新乐府先后在笑舞台、大世界等剧场演出,演出形式多样,既有整本剧也有会串,有时也会应堂会之邀。为了使戏班的特色更加鲜明,赢得更多的观众,新乐府请来京剧演员指导武戏,开创了传统昆剧角色行当中没有的武生、武旦等,使向来以“文绉绉”著称的昆剧也可以和文武齐备的其他剧种比肩。另外,为了迎合观众的欣赏习惯,新乐府还排演了一批小本戏,短小精悍,剧情更加紧凑,戏剧冲突更加鲜明,深受欢迎。尽管这一时期新乐府演出较为频繁,拥有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但这并不表示昆剧重回昔日独领风骚的地位,此时的昆剧依旧扮演着被边缘化的角色,其受欢迎程度不可与京剧同日而语。
1930年,新乐府内部出现了分化,首先是“传”字辈不满领班严惠予、陶希泉在戏班收入上大量抽成及其捧角作风,演员们辛苦演出却拿不到应得的报酬,领班不仅剥削演员还通过捧角离间了师兄弟之间的感情,故而戏班内部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其次是因为“传”字辈师兄弟之间的思想变化以及对未来发展规划产生分歧,焦点在于顾传玠的离开。他是新乐府功夫最好的小生之一,由于不满昆剧演员待遇差、社会地位低而执意转行,意图进入高等学府深造,同门师兄弟们多次劝阻未果,顾传玠在1930年离开了戏班[2]412。顾离班后,其他成员与领班的矛盾更加尖锐,于是“传”字辈的骨干组织大家离开了新乐府,回到苏州组建“共和班”。失去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也从新乐府时期被领班剥削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新组建的共和班采用合股合作的形式,“传”字辈骨干自由集资,用募集的资金购买行头,推举了两位师兄弟主持班内事物并接洽演出,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调动了演员们的积极性,很快共和班的发展就走上正轨。然而苏州终究地域狭小观众有限,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共和班决定重回上海,从此开创了昆剧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三、仙霓社的盛衰及其社会影响
1931年9月,共和班回到上海后决定更名为“仙霓社”,为了尽快获得知名度,聘请仙霓社的剧场连续数日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荣记大世界提倡高尚娱乐,重金礼聘全中国硕果仅存之昆剧团体新乐府原班人马,特制全新行头另行改组取名仙霓社,十月一日起新三层楼日夜登台。三日內连接要求重聘新乐府之函件有一千余封,五次派人到苏联接洽磋商,结果增加包银再现色相:
十月一日 日戏金雀记 夜戏全本貂蝉
十月二日 日戏大翠屏山 夜戏全本呆中福
十月三日 日戏金印记 夜戏全本风筝误”[5]
仙霓社的“传”字辈亮出昔日“新乐府”的金字招牌,从1931年10月1日起连演三日,“传”字辈的忠实戏迷们纷纷响应,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新乐府的黄金时期。在之后的五年里,仙霓社在上海各大剧院频繁演出,尤其是1933年一年中其演出消息几乎每日见诸于《申报》。这一时期的仙霓社虽未曾大红大紫,但是在京剧占绝对优势的上海依旧操着古音古韵偏安一隅,依靠一批忠实观众的支持不温不火地存续着。
及至抗战爆发前夕,社会动荡不安,仙霓社生存维艰,剧院演出不再能吸引观众,为谋生存不得不前往杭嘉湖等地区跑码头,颠沛流离,风餐露宿,状况十分艰难。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传”字辈的舞台表演艺术却更加精进,进入到创作成熟期。然而时运不济,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在炮火中仙霓社的行头悉数被毁,这一毁灭性的灾难让仙霓社再难坚持,走上了穷途末路。一起学艺演出十数年的“传”字辈艺人们不愿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仙霓社,在极端困苦的条件坚持演出,于1938年底在东方饭店演出几场,效果不佳,及至年底不得不各奔东西。至此,从昆剧传习所一路走来的“传”字辈随着仙霓社的解散最终零落四方。1939年后,《申报》上陆续登载仙霓社的演出信息,事实上这一时期是某几位“传”字辈演员与剧院签订合同,以仙霓社的名义演出,例如1939年3月张传芳经多方奔走联系了仙乐大戏院,几名尚在戏班的演员前去演出。所幸还有挚爱昆剧的观众在炮火纷飞的岁月中依旧不忘怀于他们心仪的戏剧和演员,面对寥落的舞台他们不吝赞美:“以今日仙霓社言,寥寥十余人,颇见精彩,武剧有汪传琦、方传芸,跌扑甚为卖力;传淞以阴静胜;周传瑛以风流儒雅胜,俱极化境。所望该社,同舟共济,力持残局,料天地淸而后,文风振作,曲必驾趣而上。”[6]正是因为有这些忠实观众的支持,部分“传”字辈演员们才能继续活跃在舞台上,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也是缘此才为解放后昆剧艺术的复兴保存了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仙霓社解散前后《申报》上接连刊载了数篇评论性、反思性较强的文章,对昆剧艺术及仙霓社的兴衰进行深入的剖析。以1938年11 月5日起连载八期的《红白斋剧说》为例,作者笔名畸人,以“红白”为题取红面杀白面之意,全篇专论昆剧,对昆剧的发展历史、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大声疾呼要改善昆剧现状,且提出了相关策略。在最后两期的连载中作者用大量篇幅评述仙霓社,一方面对仙霓社的成绩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对其每况愈下的发展现状进行反思,指出原因,作者认为:“当初穆先生在经济方面所费的力量大概的确很不少了,可是在精神方面似乎用的力量还不够,换句话说,就是长久的计划当初似乎并不曾有。”[7]作者将仙霓社发展不力的原因归结于昆剧传习所时期穆藕初没有长远的规划,此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将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剧种的衰败归结于个人难免有失偏颇。1941年之后《申报》上陆续刊登了几篇为仙霓社发展出谋划策的文章,如《对仙霓社的期望》、《昆腔班的女伶问题》等,多数为热心观众针对仙霓社存在的问题积极地建言献策,唯恐仙霓社这一“硕果仅存”的昆班彻底从舞台上消失。这一时期“传”字辈当中张传芳、朱传茗、郑传鉴等坚持以仙霓社的名义演出,王传淞、周传瑛后加入其他团体担任教师。上世纪40年代中期“传”字辈曾一度试图恢复仙霓社,但终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申报》被称为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变化。《申报》对于昆剧这门古老的艺术予以关注,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反映出近现代昆剧艺术的发展状况。昆剧传习所在近现代昆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后继团体“新乐府”、“仙霓社”与传习所一脉相承,对传统昆剧的保存及表演形式的丰富有突出贡献。昆剧传习所及新乐府、仙霓社在与《申报》的互动中发展壮大直至消亡,从《申报》看昆剧传习所的发展流变及其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为昆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对当下昆剧的发展具有启示性意义。
21世纪伊始,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首位,在这一契机下,古老的昆曲艺术重新焕发青春,一批新排演的作品在舞台上大放异彩。其中,白先勇团队先后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在昆曲艺术被日益边缘化的21世纪,这两部作品的问世使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不仅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昆曲美学的新样式。与80多年前穆藕初等有识之士支持昆剧传习所相似,自称“昆曲义工”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奔走于两岸三地积极推广昆曲,并集结顶尖的创作团队制作出两部具有当代示范意义的高水平作品。这两出戏不仅在表演上传承于“传”字辈的老师们,更在美学精神上延续了传统昆曲艺术的精髓,进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昆曲新美学观念。可见近百年前的昆剧传习所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而且其影响力波及至今,对当代昆曲发展无论技术还是观念仍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今日昆剧传习所补演日戏[N].申报,1924-5-25(22)
[2]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凉月.记徐园之昆剧[N].申报,1925-10-21(20).
[4]剧场消息[N].申报,1927-12-9(19).
[5]荣记大世界预告[N].申报,1931-9-30(21).
[6]秋平.昆曲复兴之感想[N].申报,1939-5-21(18).
[7]畸人.红白斋剧说[N].申报,1938-11-23(12).
(责任编辑:周立波)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Institute and the Social Impact from Shun Pao
WU Jing
Abstract:Kunqu Opera Institute(Chuanxi Suo)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It accumulated streng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in the special period. Kunqu Opera Institute has the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modem history of kunqu opera,followed by the group“New Music Troupe”and“Fairy Society”. They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kunqu opera and enriching the forms of performance. Kunqu Opera Institute,New Music Troupe and Fairy Society developed and finally vanished while having an interaction with Shun Pao.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unqu Opera Institute and the social impact at that tim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kunqu opera,and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kunqu opera.
Key words:Shun Pao;kunqu Opera Institute;New Music Troupe;Fairy Society
中图分类号:J820. 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28
作者简介:吴静(1990— ),女,山西大同人,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硕士,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方面研究。(杭州3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