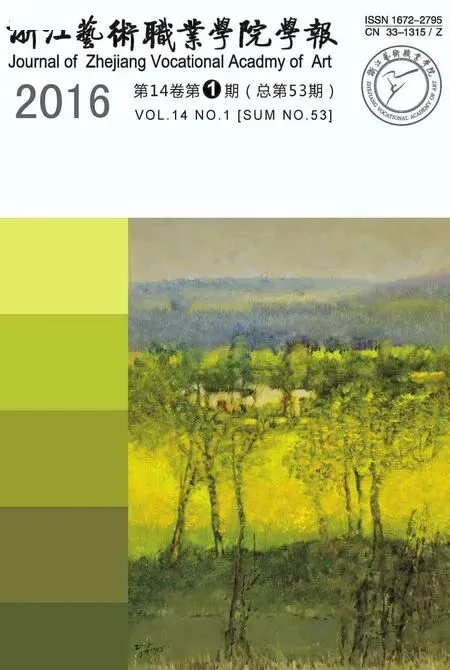晚明戏曲本色论对阳明心学的继承∗
周立波
晚明戏曲本色论对阳明心学的继承∗
周立波
摘要:阳明心学对戏曲本色论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助一定的桥梁,对其产生影响;而这一桥梁正是晚明阳明后学者们缤纷斑斓的思想观念。由“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理论派生出来的各家理论,较之王阳明的学说,则更加重视对自然状态的认识,更加重视对本我内心的体验,更加重视思想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这些正是晚明戏曲本色论的特质。从表面来看,晚明的戏曲本色论只是对戏曲语言的规范,只是要求语言的通俗化;但从深层意义上来看,晚明的戏曲本色论已远远超出其表面意义,是对晚明戏曲的总体认知,既是对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宏观体认,更是对晚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的解读与革新。
关键词:晚明戏曲;本色论;阳明心学;阳明后学
作者简介;周立波(1964— ),男,江苏沭阳人,文学博士,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戏曲史论方面研究。(杭州310053)
∗本文系2015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明浙东戏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NDJC301YBM)
晚明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肇始于张居正的变法,结束于崇祯帝的煤山自缢。在这一时期里,尽管政治局面异常颓废,但经济却十分繁荣,文化相当发达,思想非常活跃。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派生出来的戏曲,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尤其是思想的影响,直接导致戏曲观念的变化。在戏曲观念的变化过程中,戏曲本色论应运而生,并指导着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
一
最早使用“本色”一词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云:“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1]很显然,这里的“本色”就是本来的颜色的意思,以兰、茜提炼青、绛来比喻纠正浮夸、遵循本色文风的重要性。到了唐代,《晋书·天文志》则沿袭了刘勰的用法,曰:“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顺时应节,色变有类:凡青皆比参左肩,赤比心大星,黄比参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应其四时者,吉;色害其行,凶。”[2]指青、赤、黄、白、黑五星虽历经四时变化,却仍能保持原来的颜色。而值得一提的是,此后“本色”一词则更多被用在艺术批评和记载中,如武则天时制定的《定伎术官进转制》一文有“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3]崔令钦《教坊记》有“《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随其衣本色”[4],施肩吾《西山群仙会真记》中有“闭之千息以炼五脏,五脏各出本色”[5]之句,南卓《羯鼓录》有“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6]一说,等等。至此,“本色”一词由本来的颜色归纳为事物最根本的特质。到了宋代,无论是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7]之“本色”,还是严羽《沧浪诗话》中“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8]之“本色”,已经将“本色”纳入到诗歌创作语言的评价体系之中,尤其是严羽的本色观,在强调“悟”的前提下,将“本色”与“当行”共举。因此,王骥德认为:“当行本色之说,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盖本宋严沧浪之说诗。沧浪以禅喻诗,其言‘禅道在妙悟,诗道亦然,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聲愈远',又云‘须以大乘正法眼为宗,不可令堕入声闻辟支之国'。知此说者,可与语词道矣。”[9]
而以“本色”论戏曲则始于明代中期,兴盛于晚明。明中期戏曲本色论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开先、何良俊、徐渭和王世贞。
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说:“国初如刘东生、王子一、李直夫诸名家,尚有金元风格,乃后分而两之,用本色者词人之词,否则为文人词。”[10]他将戏曲语言分为“词人之词”和“文人之词”两类,前者则是“本色”之语言,后者则是非本色语言。同时的何良俊也提出了自己的本色观,明确提出“本色语”概念,对一直以来饱受推崇的《西厢记》和《琵琶记》持不同意见,认为:“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11]何良俊对《拜月亭》尤为推赏,认为它“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理由是施君美“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剧中的拜新月两折,以及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等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尤其是《赏春惜奴娇》的“香闺掩珠帘镇垂,不肯放燕双飞”,以及《走雨》内的“绣鞋儿分不得帮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根”等语,“正词家所谓‘本色语'”。[3]12是否“本色语”成为他评价戏曲的最高标准。稍后的徐渭则极大地丰富了本色论体系。他首先对以时文手法作曲的弊端进行批判,认为“其弊起于《香囊记》”,作者“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话,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南戏之厄,莫甚于今”。相比之下,像《琵琶记》《玩江楼》《江流儿》《莺燕争春》等剧,则“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无今人时文气”。[12]在徐渭看来,真正的本色是“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糠衣”(《酹江集·昆公奴》眉批)。他以“相色”与“本色”相比照,曰:“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湿'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13]明确提出自己“贱相色,贵本色”的观点。王世贞的本色论则以史学家的眼光加以审视,评论马致远,说他“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14];评论冯惟敏,谓其“独为杰出,其板眼、务头、撺抢、紧缓,无不曲尽,而才气亦足发之;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为白璧微瑕耳”[6]37。很显然,王世贞的本色观较之前人,提出了“本色”的“度”的命题,马致远能成为元曲第一,正与他适度掌控创作语言的“本色”密切相关;而冯惟敏的创作语言却超出了“本色”的“度”,反而成为一种瑕疵。
自万历以后,诸多戏曲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本色观,其中,以屠隆、沈璟、徐复祚、王骥德、吕天成、臧懋循、祁彪佳等人的本色论较具代表性,他们的本色论基本上都是在承袭明中期诸家的本色观基础上将这一理论丰富和完善,表现出具有晚明时代特征的个性特质。
屠隆在评价元曲时认为戏曲应以“语语当家”为要,“传奇者,古乐府之遗,唐以后有之,而独元人臻其妙者何?元中原豪杰,不乐仕元,而弢其雄心,洸洋自恣于草泽间。载酒征歌,弹弦度曲,以其雄俊鹘爽之气,发而缠绵婉丽之音。故泛赏即尽境,描写即尽态,体物则尽形,发响则尽节,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故余断以为元人传奇,无论才致,即其语语当家,斯亦千秋之绝技乎”[15]。这里所说的“当家语”,一者要求“多创新意,并不用俗套”,二者要求通俗谐趣,“不用偏僻学问、艰深字眼”。[16]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词“丽而婉”、调“响而俊”的“不悖于雅音”的本色语。[34]很明显,屠隆的观点与王世贞的很接近,一方面强调“谐俗”而“尽情”,另一方面又主张“不悖于雅音”。
徐复祚也是本色论的重要支持者。他对王世贞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王弇州取西厢‘雪浪拍长空'诸语,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为南北之冠。”[17]他在评价《拜月亭》问题上观点则何良俊相一致,他认为:“《拜月亭》宫调极明,平仄极谐,自始至终,无一板一折非当行本色语,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18]
王骥德出于徐渭门下,在戏曲观上继承了徐渭的“本色”论,认为:“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如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19]他同样把“本色”与“当行”并提,在他看来,本色就是“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5]154
沈璟明确标榜自己“鄙意癖好本色”,认为“北词去今益远,渐失其真,而当时方言及本色语至今多不可解”(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词隐先生手札二通》)。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色语具有时代性的命题。沈璟的本色观在当时形成了很大反响,吕天成、臧懋循、祁彪佳、冯梦龙等人都响应沈璟的观点。吕天成的戏曲理论中,本色当行论是其重要论点。他指出:“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第当行之手不多遇,本色之义未讲明。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段,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勒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缋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今人窃其似而相敌也,而吾则两收之。即不当行,其华可撷;即不本色,其朴可风。”[20]他不但明确了本色、当行的概念,而且能够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臧懋循在推崇元曲的基础上认为“填词者必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元曲选序二》)。祁彪佳则通过具体的作品评点,发表了自己的本色理论,如他说《合纵记》“时出本色,令人会心”,《白璧记》“词近本色,白亦恰当”,《檀扇记》“幸其词属本色,开卷便见其概,不令人无可捉摩”,《红蕖记》“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色,正惟能极艳者放能极淡”……
至此,我们可以对晚明戏曲的本色论作一归纳,“本色”与“当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用吕天成的说法就是本色“只指填词”,当行“兼论作法”。而定义来说,冯梦龙的说法较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本色就是“常谈口语而不涉于粗俗”,当行则是“组织藻绘而不涉于诗赋”。[21]区分了二者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把握“本色论”的特质。较之以前,晚明的“本色论”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本色论的内涵趋于完整,在掌握一定的度的基础上,要求戏曲语言尤其是曲词通俗易懂,按照生活中本来的样子来表达,能够更能接近于普通观众;其次,本色与当行是戏曲创作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二者有个重要的共通之处,即要求创作回归本源,更接近生活中的真实;再次,要求戏曲家遵循本色规律,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要让普通观众看得懂,听得明白,从而达到戏曲的教化效果。
本色论至晚明之所以具有如此特点,与其他艺术形式,乃至整个文化内容一样,与晚明的思想变革是分不开的。
二
说到晚明的思想变革,在不能不从明代中期王阳明谈起。“心学”至王阳明已发展到新的高度,他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构成了“心学”的基本内核。王阳明一贯标榜自己:“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22]又说自己“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23]。因此,他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24]对此,阳明学家张新民解释说:“‘是非之心'是人的内在道德判断能力,而‘好'与‘恶'则表现为道德情感。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相互映证,彼此发明,灌注一切万有,参赞宇宙化育。这种廓然大公,作为心性本体的良知,是人人具有的,既是‘学问大头脑',又是‘天植灵根',应当无量扩充,生生不息,同时还要依此‘天植灵根'践之行之,落实为具体的道德生活,使内与外、静与动、知与行融合一体。”张新民先生进而通过王阳明对“行”在“致良知”学说中的重要性加以分析,认为:这种“内与外、静与动、知与行融合一体”实际上就是要“产生心灵秩序与人伦秩序、宇宙铁序合一的和谐化道德美感”。[25]那么,将“致良知”思想实践于艺术中将会是怎样的呢?王阳明认为:“《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24]113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反朴还淳”的命题,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去除“妖淫词调”,突出“忠臣孝子”主题,用通俗易晓的语言和内容,使百姓在潜移默化中“良知起来”。
此后的王学的发展虽出现众多分支,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仍是各学派的思想内核。无论是“论证悟”的王畿,“研归寂”的聂豹,还是“乐高旷”的王艮,“穷主宰流行”的刘师泉,虽“各有疏说”,但他们的学术仍然“指点圣真,真所谓滴骨血也”。[26]聂豹是江右学派的代表,他认为良知是“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而知无不良也”[27]。他提出“良知本寂”的命题,要实现“良知”,必须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意”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人的道德品质好,不是天生的,要通过养心,通过修养,才能达到。季本承袭“知行合一”说,强调“虽若以知行分先后,而知为行始,行为知终,则所知者即是行,所行者即是知也”。[28]王艮提出的“万物一体,宇宙在我”,“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把着眼点放在平民身上。罗汝芳的“当下功夫说”,认为“当下即为用功之地,直下作真切功夫”,只有这样才能“驰求闻见,好为苛难者引归平实田地”[29],然后,“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拣择一条直截路径,安顿一处宽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咏优游,忘年忘世”[30]。颜钧则主张要顺应自然,所谓“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31]。这些学术观点是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革新,将眼光逐渐放在了普通民众身上。
到了晚明,阳明心学得以进一步变革,尤以“狂狷”自我标榜的李贽为代表,将“狂狷”与“乡愿”比列,认为:“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与耿司寇告别》)这一观点恰与王阳明的“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传习录》)的观点相吻合。到了王畿那里,则大加发挥,把“狂者”抬高到“志存尚友,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的地步,将“狂者”看成是“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之人。[32]此后,无论是“不淫不屈不移真”的颜山农,“从心所欲”的何心隐,还是“只主见性,不拘戒律”的邓太湖,提倡“三教并行”的管东溟,都为李贽童心说奠定了基础。
李贽的学说的内核则在于他的“童心说”,他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不真,全不复有初矣。”[33]“童心”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与人的性情分割不开的。他在《读律肤说》中用“童心说”阐发其对艺术的看法,他认为:“拘于律则为律所制,是诗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谐;不受律则不成律,是诗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夺伦。不克谐则无色,相夺伦则无声。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性情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34]他将人的性情与自然并列起来,并认为只有自然的才是最美的。李贽的“化工说”则通过对戏曲作品的比较提出了“化工”与“画工”的命题,他认为:“《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35]罗钦顺曾批评传统理学说::“先儒以‘去人欲'、‘遏人欲'为言,盖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严,但语意似乎偏重。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36]他明确认为人的欲望与情感是相互依存的。王廷相同样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能:“人心亦与生而恒存,观夫饮食男女,人所同欲,贫贱夭病,人所同恶,可知矣。谓物欲蔽之,非其本性,然则贫贱夭病,人所愿乎哉?”[37]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在评价潘见泉时曾用到“本色”一词,谓其虽因受到“道学之习”的影响“犹有酸气”,但仍“时时露出本色”,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其天者全也”。[38]
晚明的“三教合一”观非常盛行。“三教合一”观并不是要将儒、释、道三者简单地相加,而是要以阳明心学的理念将三教融会贯通。罗汝芳曾师从颜钧学习理学,师从胡清虚学习道学,师从玄觉和尚学习佛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而林兆恩则是共认的“三教先生”,他认为:“窃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为儒则儒,欲为道则道,欲为释则释,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他把“心”作为为核心,认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心”,三教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天地与我虽有大小之异矣,而我之本体则太虚也,天地之本体亦太虚也,其有小大之异乎?惟其不可得而异也”。[39]他的观点与高僧蕅益不谋而合。蕅益同样强调“心”的重要性,提出了“仁民爱物之心”的命题。他认为:“大道之在人心,古今惟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汇乎至同,非儒、释、道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儒家强调的是“保民”,道家强调的是“疵疠万物”,释家强调的是“度尽众生”。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40]“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像管志道、李贽、屠隆、公安派的三袁、汤显祖等人曾都受到这一思想影响。袁宏道在《三教图引》中认为:“一切人皆具三教,饥则餐,倦则眠,炎则风,寒则衣,此仙之摄生也。小民往复亦揖让,尊尊亲亲,截然不紊,此儒之礼教也。唤著即应,引著即行,此禅之无往也。触类而通,三教之学,尽在我矣。”[41]屠隆也认为:“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释、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实而至其妙处本虚,释、道用虚而至其妙处本实。”[42]“三教合一”思想透露出来的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以道、释思想来抗衡传统儒学,道家、释家思想具有和儒家思想同等的地位;二是“三教合一”观念既是思想的融合,也是文化的包容。
晚明的心学思想在继承阳明心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自然本真的探究,更加重视对自我本体的探寻,更加强调各种思想观念的融合。
三
从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开始,这些戏曲理论家既是这一理论的标帜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李开先、何良俊、王世贞、徐渭等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接受心学家的观念,以自己的戏曲创作验证戏曲本色论的实践价值,并直接影响着晚明的戏曲本色论。
何良俊一生与心学家交往颇盛,他自小仰慕王阳明,曾“杖策渡浙江,欲走见阳明先生”[43]。后来拜在聂豹门下,其思想大受聂豹影响,但他又非一味盲从,在他看来,对聂豹的“谈心性而黜记诵之学”,他认为:“苟师心自用,纵养得虚静,何能事事曲当哉?寻常应务犹可,至于典章仪式名物度数,其亦可以意见处之哉。故一经变故棼集,则茫无所措。遂至于率意定方,误投药剂,非但无救于病,其人遂成沉痼矣。可无惧哉。”[44]他反对空谈,提倡务实,尤其对泰州学派的心学提出了批评,说他们“创立门户,招集无赖之徒,数百为群,亡弃本业,竞事空谈”[45]。因此,他抑《西厢》《琵琶》扬《拜月》的本色论能从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戏曲作为舞台艺术而不单是案头之作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徐复祚则基本继承了何良俊的本色观。
对王学的分化,王世贞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迨文成之铎振,而遗响为聂、为邹、为欧阳,复为罗,而今树赤帜者三矣。夫其分门户,张颐颊,云蒸风从,岂不伟然钜观哉?十仞之垣,三仞之□,而狐鼠托焉,亡他,其中虚也。”[46]他虽批评王门后学,但对王学却有继承,一方面,他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极为推崇,认为阳明的“致良知”,“与孟子之道性善,皆与动处见本体,不必究析其偏全,而沉切痛快,诵之使人跃然而自醒”(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读书后·书王文成集后》)。另一方面,他继承王学的“人情事变”说(王阳明《传习录》上),认为“人生之用皆七情也”(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说部·札记内篇》),重视切身体验。作为王世贞的弟子,屠隆对其师倍加推崇,认为:“读元美诗如入武库,不胜利钝;读元美文如览江海,终成大观。”[47]他在继承王世贞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对王学左派的三教观重新认识,提出了“三教并立”观,认为:“故儒者,譬则谷食也;释、道,譬则浆饮也。以释道治世,若以浆济饥,固无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释道,若食谷而不饮浆,如烦渴何?故三教并立,不可废也。”[42]12尤其是“当家语”一说,将戏曲观念纳入到“本色论”的范畴,不仅要求“多创新意,并不用俗套”,而且要求“不用偏僻学问、艰深字眼”。[16]1213
徐渭《自为墓志铭》曰:“山阴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词,及长益力。既而有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宗……”[48]季本曾师事王阳明,他提出了“龙惕说”,认为以龙言心而非以镜言心,强调个体主宰的意义,反对脱离主宰而论自然。徐渭曾跟从季本求学,在他思想里有“龙惕说”的成分。据徐渭记载:“时讲学者多习于慈湖之说,以自然为宗。先生惧其失师门之旨也,因为《龙惕书》以辨其疑似。诸同志稍不以为然,则遗书江之邹、聂,暨乡之钱、王四先生,再三往复而未定,先生亦自信其说不为动,久之诸先生亦多是之。”[49]徐渭提出的“自然惕也,惕也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于自然也”[50]的观点则明显可以看出对“龙惕说”的继承。徐渭除了接受“龙惕说”外,也认同王畿的良知自然说,认为“自然故虚位也,其流之弊,鲜不以盲与翳者冒之矣”。[6]678因此,对于戏曲,徐渭通过反对传统道学来宣扬自己的本色观。他曾经指出:“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12]243他的“本色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作为徐渭的弟子,王骥德的本色观则完全继承了徐渭的论点,甚至认为只有以“本色”“作剧戏”,才能“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
汤显祖十三岁就跟随罗汝芳学习,罗汝芳的“当下功夫说”和“赤子之心”说对汤显祖影响很大。在罗汝芳看来:“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51]又说:“夫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实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静后,本感物而动,动则欲已随之,少为欲间,则天不能不变而为人,久为欲引,则人不能不化而为物。甚而为欲所迷且没焉,则物不能不终而为鬼魅妖孽矣。”[30]罗汝芳的学说对汤显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认为:“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诚明谓之性',赤子之知也。‘自诚明谓之教',致曲是也。隐曲之处,可欲者存焉。致曲者,致知也。”[52]汤显祖并由此直接提出了主情观。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53]并提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54]汤显祖的戏曲观虽未言及“本色”,但他所说的“真色”,究其本质,实乃“本色”,他在评论《焚香记》时认为此剧“填词皆尚真色”,因此才“入人最深,遂令后世之听者泪,读者颦,无情者心动,有情者肠裂”。[55]因此,王骥德在评价《南柯记》与《邯郸梦》时,说它们“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19]165,因此,他甚至认为:“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3]170陈继儒则非常赞同王骥德的观点,认为:“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56]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中曾对本色作过定义:“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57]如果以唐顺之的本色论观点来衡量,那么,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则完全符合本色论的要求。
由此可以结论,阳明心学对戏曲本色论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借助一定的桥梁对其产生影响;而这一桥梁正是晚明阳明后学者们缤纷斑斓的思想观念。由“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理论派生出来的各家理论,较之王阳明的学说,则更加重视对自然状态的认识,更加重视对本我内心的体验,更加重视思想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这些正是晚明戏曲本色论的特质。从表面来看,晚明的戏曲本色论只是对戏曲语言的规范,只是要求语言的通俗化;但从深层意义上来看,晚明的戏曲本色论已远远超出其表面意义,是对晚明戏曲的总体认知,既是对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宏观体认,更是对晚明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的解读与革新。拿汤沈之争来说,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曲意与曲律之争,实际上,这更是一场学术观念之争,是一场阳明心学(或者说阳明心学的变异)与传统理学的争论。本色论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要用实践加以验证的。沈璟虽标榜自己崇尚本色,却在作品中充斥着传统理学观念;而汤显祖虽不曾标举本色大旗,却在作品中用新的思想观念对本色论予以推赞。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273.
[2]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卷十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175.
[3]周绍良.全唐文新编:卷九五[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112.
[4]崔令钦.教坊记[M]/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4.
[5]施肩吾.西山群仙会真记[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173.
[6]南卓.羯鼓录[M]/ /秦献.词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04.
[7]陈师道.后山诗话[M]/ /商浚.稗海:第四册.台北:大化书局,1985:2982.
[8]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2.
[9]王骥德.曲律[M].陈多,叶长海,注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95.
[10]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M]/ /郭银星.唐宋明清文集:第二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890-891.
[11]何良俊.曲论[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6.
[12]徐渭.南词叙录[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3.
[13]徐渭.西厢序[M]/ /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佚草.北京:中华书局,1983:1089.
[14]王世贞.曲藻[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8-29.
[15]屠隆.玉合记叙[M]/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2743.
[16]屠隆.昙花记凡例[M]/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1213.
[17]徐复作.三家村老曲谈:关汉卿补两厢记后四出[M]/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卷.合肥:黄山书社,2006:263.
[18]徐复祚.三家村老曲谈:何良俊、王世贞论拜月亭与琵琶记[M]/ /历代曲话汇编:明代卷.合肥:黄山书社,2006:256.
[19]王骥德.曲律[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37.
[20]吕天成.曲品校注[M].吴书荫,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23.
[21]冯梦龙.太霞新奏:卷十二[M]/ /冯梦龙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10.
[22]钱德洪.刻文录叙说[M]/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575.
[23]王阳明.寄郑宪男手墨二卷[M]/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990.
[24]王阳明.传习录下[M]/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1.
[25]张新民.良知·内省·自律——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人格三题[J].贵州社会科学,1995(6).
[26]黄宗羲.教谕胡今山先生瀚[M]/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330.
[27]聂豹.赠王学正之宿迁序[M]/ /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四.明嘉靖四十三年刊本.
[28]黄宗羲.知府季彭山先生本[M]/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278.
[29]罗汝芳.旴坛直诠:卷下[M].台北:广文书局,1977:151-152.
[30]罗汝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易[M].熊傧,辑.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31]颜钧.自吟[M]/ /颜钧.颜钧集:卷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73.
[32]王畿.与阳和张子问答[M]/ /王畿.王龙溪全集:卷五.清道光二年刻本.
[33]李贽.童心说[M]/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98.
[34]李贽.读律肤说[M]/ /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
[35]李贽.杂说[M]/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96.
[36]罗钦顺.困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0:28.
[37]王廷相.慎言:问成性[M]/ /王廷相.王廷相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766.
[38]李贽.追述潘见泉先生往会因由付其儿参将[M]/ /李贽.续焚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99.
[39]林兆恩.三教合一大旨[M]/ /林兆恩.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明万历刊本.
[40]蕅益.儒释宗传窃议[M]/ /灵峰宗论:卷五之三.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30。
[41]袁宏道.三教图引[M]/ /三袁随笔.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172.
[42]屠隆.冥寥子游: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43]何良俊.书王槐野先生书[M]/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152.
[4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4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
[46]王世贞.邓太史传[M]/ /弇州山人续稿:卷七十三.明崇祯间刊本.
[47]屠隆.论诗文[M]/ /屠隆.鸿苞集:卷六.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48]徐渭.自为墓志铭[M]/ /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638.
[49]徐渭.师长沙公行状[M]/ /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646-647.
[50]徐渭.读龙惕书[M]/ /徐渭.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678.
[51]黄宗羲.泰州学案[M]/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764.
[52]汤显祖.明复说[M]/ /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1165.
[53]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M]/ /汤显祖.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1050.
[54]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 /汤显祖.汤显祖集:诗文集.徐朔方,笺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8.
[55]汤显祖.焚香记总评[M]/ /王玉峰,秋堂和尚.焚香记·偷甲记.吴书荫,张树英,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首.
[56]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M]/ /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明天启四年张氏著坛刊本.
[57]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M]/ /唐顺之.唐荆川文集:卷七.明万历元年刊本.
(责任编辑:李 宁)
Inheritance of Yangming's Innate Knowing Philosophy from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OU Libo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s innate knowing philosophy o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s not direct,but with the help of certain bridge,which are the colorful ideas of Yangming's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mparing with Wang's philosophy,various theories derived from the“conscience”and “combining knowledge and action”theories have more emphasis on the awareness of natural state,pay more attention to inner experience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monality and combination of ideas,which are the essence of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Superficially,the theory is just the specification of opera language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language;but in a deeper sense,it is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oper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is the macro understanding of the art form traditional opera,and is als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eory;Yangming's innate knowing philosophy;Yangming scholars
中图分类号:J80-0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