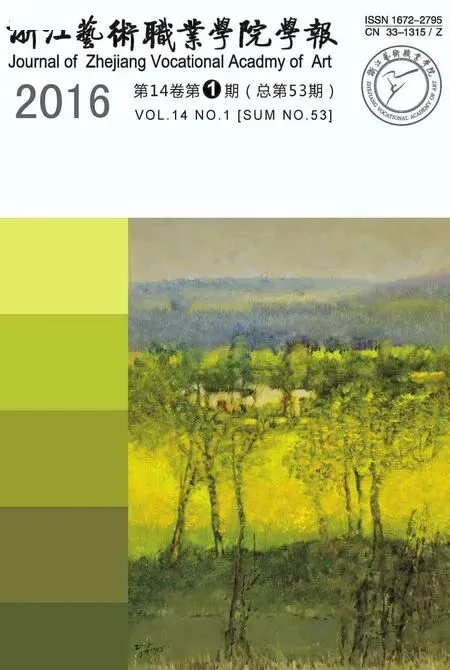“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考释
——明末清初“画学道统”衍化及其思想、政治隐喻
韩 刚
“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考释
——明末清初“画学道统”衍化及其思想、政治隐喻
韩 刚
摘要:通过对明末清初“画学道统”衍化及形成原因的较详细梳理,认为,前此关于董其昌至王时敏、王原祁“画学道统”之“直贯型”重要命题是不符合画史实情的,实则由于王时敏在明清易祚语境下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导致董其昌与王时敏之间“画学道统”之“断裂”,直至王原祁才真正接续上董其昌血脉,明末清初“画学道统”应为与时代思想、政治文化衍化合拍之断裂后重建,或可谓之“转折型”,而明清易祚中思想、政治巨变又是其出现的主要原因。王原祁所说“华亭血脉”“金针微渡”微言之大义“在此而已”。
关键词:画学道统;直贯型;转折型;“华亭血脉”;“金针微度”
一、解题及缘起
清初王原祁《烟峦秋爽仿荆关图》跋有“六法中道统相传”[1]703云云,“六法”者,画学也,故本文称“画学道统”。
在古代,道主要有儒家之道、佛家之道、道家之道,此“道统”与何家之道最为接近?儒道也。如王原祁《题仿董、巨笔》:“画之有董、巨,犹吾儒之有孔、颜也”[1]706;王原祁之著名弟子唐岱《绘事发微》论“正派”时已和盘托出:“如道统自孔、孟后,递衍于广川、昌黎……画学亦然。”[2]
明末清初画史中,王时敏是董其昌之亲炙弟子;王时敏既是王原祁之祖父,也是他的画学导师,由于有这种师学授受关系存在,加之三人在画学思想上均主张“复古”等,故学界普遍认为自董其昌至王时敏、王原祁之间的“画学道统”是顺次直贯而下的(本文称为“直贯型”),如清安歧(1683-1745?)《墨缘汇观·名画序》:
入明,徐幼文、王孟端、刘完庵、沈石田、文徵明皆宗之,则又远接衣钵矣。明末,董文敏继起华亭,秀润天成,不落蹊径,宗风为之一变。至我朝,太仓王奉常雅好笔墨,遂出王圆照、王石谷二子,故吴下有三王之称,迄今知有倪、黄、董、巨之传,赖有于斯。[3]
清张庚(1685-1760)《国朝画征录》云:
(王时敏)于画有特慧,少时即为董宗伯、陈征君所深赏。于时宗伯综揽古今,阐发幽奧,一归于正,方之禅室,可备传灯,一宗真源嫡派,烟客实亲得之。[4]
清秦祖永(1825-1884)《桐阴论画》云:
思翁于画学,实有开继之功焉,明季画道之衰端赖振起,文、沈虽为正派大家,而其源实出梅道人、倪、黄一派。至思翁独得心传,开娄东正派,故必以思翁为冠首。[5]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均谓王时敏为直接继承董其昌“画学道统”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王原祁为轮美作《仿大痴设色图》题跋:
大痴画以平淡天真为主……学者得其意而师之,有何积习之染不清、细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时得闻先赠公大父训,迄今五十馀年矣,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1]708
画史上著名的“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论盖出乎此,一般会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在原祁看来,自黄公望、董其昌、王时敏至自己这一系谱才是“画学道统”正宗,自己通过五十馀年的勤苦学习才掌握了这一系的真精神、真血脉。而实际上,即便仅就字面而言,恐怕这种理解也是不确的,即如果能作是解,“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中“华亭血脉”“在此而已”足矣,何须“金针微度”?故“金针微度”很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隐喻,尤其是“微”字,于国族文化中,不正有喻示“微言大义”之本领吗?
如果“知人论世”地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文化原境中去理解这段话,则有另一番意味在。
二、“画学道统”系谱之儒学语境
中国传统社会中之“士”是“以道自任”的。一般而言,周公(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又名周公旦)以前,“天下有道”,“道”(或德)与“位”(或势)是一致的,有德者居其位,两者不可或缺,是一种和谐均衡之关系,即《中庸》所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6]
周公及以后,“道”与“位”之均衡被打破,有德者不一定居其位(如周公、孔子便有德无位,故孔子有“素王”之称),因而,“德”(其崇尚与践履之主体为儒、士)与“位”(主体为君、王)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如果居位者有道有德,儒、士来集,反之则去,互不亏欠,如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8]、“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9]曾子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10]显然,于此不难体会出,“以道自任”之儒、士表明了一种“自贵”、“自高”之情操,“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所任之“道”的尊贵,毕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斗转星移,为了保证“道”之纯正性,随“自贵”思想而来的必然是“道统”与“道统”中的“正统”问题。儒家“道统”论在《论语》中已露端倪,如《论语·述而》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2];《中庸》亦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3];孟子自云:“乃所愿,则学孔子也”[14]、“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15]。可见,孟子是以继承孔子之道为矢志的。孟子之后,儒家“道统”后继乏人,直至唐代韩愈起而重提道统,其《原道》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6]
至宋明,儒学大阐,濂、洛、关、闽各有自己之道统论,大同而小异,南宋朱熹为道统论之集大成者,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有云: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孔子)……及曾氏(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孟子)……程夫子兄弟(程颢、程颐)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17]
因必须维护“道”之尊贵、纯洁,故排他性自然成为“道统”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包括排外与清理门户两项内容。就排外而论,如“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距杨墨”;韩愈所言“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朱熹、陆九渊等辟佛、禅;等等。就清理门户而言,如荀子、扬雄本为大儒,但韩愈却曰:“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朱熹认为陆九渊的思想空疏、简易,陆九渊则认为朱熹之“道心”是支离事业;等等。
三、董其昌“南北宗”论
这种“道统”论必然会影响到以士人为创作主体之“士人画”上,正如唐岱《绘事发微》论“正派”时云:“画有正派,须得正传,不得其传,虽步趋古法,难以名世也。何谓正传?如道统自孔、孟后,递衍于广川、昌黎,至宋有周、程、张、朱,统绪大明。元之许鲁斋,明之薛文清、胡敬斋、王阳明,皆嫡嗣也。画学亦然。”[2]887而画史上对此论述较早而完整者为明末典型士人画家董其昌等提出之山水“画学道统”——“南北宗”论,董其昌《画旨》中有三处涉及道统问题: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18]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18]76
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文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如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18]76
须先做说明的是,董其昌所谓“文人之画”实乃“士人画”、“士夫画”之谓,对照体悟“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云云不难领会;“南北宗”论中,董其昌对“米家父子”极为推崇,而《画旨》中有“米家山谓之士夫画”云云;另如徐复观说:“董氏所谓文人画,实即赵子昂之所谓士夫画或士气。”[19]
按上述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其画学道统人物可列为下面两个系统:
南宗:王维——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李成、范宽、李龙眠、王晋卿、米芾、米友仁、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文徵明、沈周。
北宗:李思训——李昭道、赵幹、赵伯驹、赵伯骕、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可见:“南北宗”论除元初赵孟頫、高克恭等外,基本上囊括了唐中叶以来的山水画大家;绘画创作之主体除北宗赵幹、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为职业画家外,其余“南北宗”成员均可谓为以“以道自任”之士大夫,而之所以将赵、李、刘、马、夏等列入,主要是因为他们“又有士气”。尚可议者如下:
其一,“南北宗”论之内核虽为儒家道统①阮璞《画分南北宗说实具外禅内儒性质》通过分析认为:“莫董当明之季世,比附禅分南北二宗之历史,倡说画亦有南北二宗之分,其学说之形成与揭出,非止源于禅宗之影响,而别有更为深厚之根柢在,斯即吾国固有之儒家宗法、正统、道统观念,以及此观念演绎于诗、文、书、画积久形成之派系、师承理论是已。”(载氏著《画学丛证》,页27,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结论虽有理可从,论证却浮于外围、表面。愚以为,之所以说“南北宗”论之理论内核是儒家道统,是因为:一是该论是以“士气”奠基的;二是就画家思想文化身份而言,南宗画家虽多通禅学者,但从本质上说均为士大夫(或儒家思想对他们影响更大),北宗画家则多为宫廷画家与画院画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很难说与禅宗有瓜葛;三是董其昌本人是以儒道自任的士大夫。,但不可否认受到了明末十分流行之狂禅思潮深刻影响,禅化严重。
其二,“南北宗”论主要是士人画、宫廷画、画院画谱系,排斥了民间画、工匠画、文人画,意在维护士人画、宫廷画、画院画“画学道统”正统地位。
其三,“南北宗”论为山水画学谱系,排斥了人物画、花鸟画学等,意亦在维护长期以来“夫山水,乃画家十三科之首也”[20]之山水“画学道统”正宗地位。
其四,为了进一步维护“画学道统”之纯正,即便在“南北宗”论这一“画学道统”内部,董其昌也明确表达了清理门户意识,即崇南贬北(即推崇士人画,贬抑宫廷画、画院画),如谓南宗:“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谓北宗:“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如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仍值得注意的是,虽玄宰明确表达了“崇南贬北”,但他“并不严格排斥北宗”[21]。
其五,董其昌“南北宗”论中并未涉及到他自己是否为此画学道统系谱中成员之一,其《夏山图》云:“董北苑画,为元季大家所宗……余自学画几五十年,尝寤寐求之……余因托收三种……不胜自幸。岂天欲成吾画道,为北苑传衣,故触着磕着乃尔,然又自悔风烛之年,不能恳习,有负奇觏也。”[22]此段跋语为了表示谦虚,虽屡下转语,但其中“岂天欲成吾画道,为北苑传衣”云云却表明了董其昌将自己纳入士人山水“画学道统”正宗之意愿。士大夫“以道自任”的“自尊”、“自贵”情怀,在董其昌这里表露无遗。虽然如此,玄宰毕竟不便将自己直接纳入“南北宗”论。
其六,由“南北宗”论排斥元初山水画大家赵孟頫、高克恭等尤可见作为“以道自任”士大夫之董其昌的“自贵”、“自尊”与清理门户情怀。赵孟頫本为赵宋宗室却折节仕元,这违背了士人所应遵循之最根本道德规范,如《论语·八佾》云:“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23];《左传·成公四年》云:“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4];南宋为元所灭后,郑思肖撰《心史》云:“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种孽气,生为夷狄,如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等,其类极异,决非中国人之种类。”[25]可见,在郑思肖那里,“夷夏之辨”已严重到了兽、人之分的地步。朱元璋于北伐灭元战争文告中云:“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26]、“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26]402;丘浚(1421 -1495)云:“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与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27]蒙元,夷狄也,赵孟頫不顾此大防,“奉夷狄为帝王”,遭到明代“以道自任”的士大夫放逐是自然而然的,如李东阳(1447-1516)《麓堂诗话》云:“夫以宗室之亲,辱于夷狄之变,揆之常典,固已不同。而其才艺之美,又足以为訾之地,才恶足恃哉!”[28]明代艺苑对赵孟頫折节仕元批评甚力,如沈周(1427-1509)《题赵文敏渊明像并书归去来辞卷》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归去自嫌迟”;项穆(约1550-约1600)云:“子昂之学,上拟陆、颜,骨气乃弱,酷似其人”[29]、“若夫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29]532;等等,在此语境下,就不难理解为何董其昌们画学道统“南北宗”论里没有赵孟頫了。
至于高克恭,本为西域人,蒙元高官,虽受“米氏云山”影响,但当时既本属夷狄,被董其昌们逐出“南北宗”论更属自然。
四、王时敏之“画学道统”系谱
至清代,承接明末董其昌等“南北宗”论,以士人为创作主体的山水“画学道统”论愈演愈烈,以“四王”为代表,尤以王时敏、王原祁等一系娄东派为最。以正统、正派、正脉自居,贬逐外道、邪派。“六法中道统相传”(画学道统)一语本身即是王原祁提出来的。
从董其昌与王时敏、王原祁画学传承关系来看,作为士大夫家族之王氏接续董其昌“南北宗”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主要体现在王氏“画学道统”论与董其昌“南北宗”论之相同点上,如董其昌“南北宗”论所提及之“南宗”画家,王时敏家族“画学道统”基本承继;董其昌、王氏家族均崇南贬北;等等。这些相同点还不是理清王氏“画学道统”的关键与重点,关键与重点是相异处。
王时敏《西庐画跋》云:
书画之道,以时代为盛衰,故钟、王妙迹,历世罕逮;董、巨逸规,后学竞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时风气使然也。唐宋以后,画家正脉,自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吾吴沈、文、唐、仇以泉董文敏,虽用笔各殊,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30]
然赵(孟頫)于古法中以高华工丽为元画之冠,此尤以淡逸见奇,笔墨兼妙,从董、巨伐毛洗髓得来。[30]
王时敏“画学道统”论(系谱)与董其昌“南北宗”论相异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南北宗”论之延续,如时敏将董其昌正式纳入了“南宗”系谱,解决了董其昌自己不便入谱之尴尬。此容易让人朝直接继承方向理解,最具迷惑性。
其二,将明末以来的士人画学道统“南北宗”论中之禅化倾向剥离出去,还士人画学道统以本来面目,使之更纯净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身就是对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反动,因为董其昌“南北宗”论的理论内核是明末以“尊德性”为特色的心禅之学(以陆王心学为主),而时敏在其“画学道统”论中强调的却是“刻意师古”,充满了浓郁的程朱理学“道问学”特色。此外,与此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非但时敏“画学道统”论中不见“南宗”、“北宗”、“南北宗”这样的语汇,就连他的《西庐画跋》与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中也难以找到这些语汇,他的“画学道统”论在实质上与玄宰“南北宗”论的决裂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崇南贬北”更甚,不,应该说近乎直接罢黜“北宗”。不但董其昌“南北宗”论中尚存的对北宗有限度的肯定(如“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等语)已经近乎销声匿迹,而且以“画家正脉”等用语推尊“南宗”。由此可见,时敏“画学道统”系谱与董其昌“南北宗”论不是顺次直贯而下继承式的。
其四,倡导“刻意师古”,这是时敏画学的一贯立场与终极目标,而董其昌画学从总体上看虽也强调“师古”、“复古”,但最终却是以“师心”、“更新”为归趣的,在“南北宗”论中也未见提及“师古”。由此可见,时敏“画学道统”系谱走向了董其昌“南北宗”论之反面。
其五,清理门户。吴讷孙简括“董其昌之后”说:
由于南宗运动的结果,中国绘画遂分两路发展。我们可以称四王所走的路为右翼,在偶像破坏运动后,再造山水;另一派就是独行画家(包括著名的八大山人和石涛)所走的左翼,继续发挥南宗所提示的可能性——“表现自我”。[31]
照此理解,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按:照本文的理解,吴纳孙恰好将“左”、“右”搞反了),似乎均为“南宗”同根所生,可是在王时敏家族山水“画学道统”系谱里,左翼却被无情放逐了,如王时敏《西庐画跋》云:
近世攻画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夸巨手;然多追逐时好,鲜知学古。即有知而慕之者,有志仿效,无奈习气深锢,笔不从心者多矣。[30]
迩来画法衰谮,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药。[30]
引文中“追逐时好,鲜知学古”、“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云云,当针对所谓“左翼”以石涛等为代表的“表现自我”的“文人画”而言。王时敏清理门户实质上是将董其昌画学中富有创造性与“表现自我”的那一部分清理掉了。当然,考虑到他“一以贯之”的“复古”立场,这是必然的。由此可见,时敏“画学道统”系谱走向了董其昌“南北宗”论之反面,因为他把董氏“南北宗”论中作为目的与根本的(即“更新”)那部分清理掉了,只留下了作为手段的“复古”,即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其六,与“南北宗”论相比,王时敏“画学道统”中将被董其昌放逐的赵孟頫纳入并大加赞扬,谓:“自元季四大家、赵承旨外……皆刻意师古,实同鼻孔出气”、“赵于古法中以高华工丽为元画之冠……从董、巨伐毛洗髓得来”。王时敏将失节仕元的赵孟頫纳入“画学道统”正宗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考虑到当时思想、政治环境这又是不难想象的。
明清易祚之后,王时敏、王原祁家族画学在成为满清画学正宗之前,大致经历了顺治(1643-1661在位)、康熙(1661 - 1722在位)、雍正(1722-1735在位)、乾隆(1735-1795在位)四任皇帝。从大体上看,康熙平定“三藩之乱”(1681)之前,在以儒家道统自任的、死守“夷夏大防”的汉族士人主持下的反清活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连绵不绝。思想、政权、人心、社会等还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清廷虽然随即宣布了“平定江南捷音”,公布了“剃发令”,但江南军民的抵抗依然十分坚决(如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长达两月之久等)。
稍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清热潮,建立了各种抗清政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抗清斗争。
就抗清政权而言,如顺治二年(1645),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同年,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顺治三年(1646)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键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同年,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等等。
就抗清斗争而言,北方如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义师风起云涌,抗清高潮迭起,甚至一些已经降清之明朝将领也纷纷再次倒戈抗清。南方如顺治二年,李自成农民军余部与明总督何腾蛟联合抗清;顺治六年(1649),张献忠农民军馀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部与永历政权会合,共同抗清;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领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在此次战役中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郊外;同一时间,郑成功率水军攻克舟山;等等,直至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也先后去世,方告一段落。
虽然如此,满清政权并不太平,如清康熙八年(1669),拘禁权臣鳌拜;十二年(1673),由于“撤藩”,引起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精忠的“三藩之乱”,直至二十年(1681)十月,吴世璠(吴三桂之孙)自杀,平乱达八年之久。
反过来,从满清应对“以道自任”的汉族士人的抗清策略来看。
明清毕竟已经易祚,满清兵强将广,万马千军,气势如虹,有恃无恐,除了上述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外,还积极推行了收买、拉拢士人之手段,效果十分明显:重用汉族士大夫;入关后即祭祀“先师孔子”;打出“翦灭闯寇,入承大统”之旗号,承诺承继中国文化正统(满清第一个年号“顺治”即含此意);编修《明史》(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正式开馆修纂,虽然实质上并不具备修纂条件,但从文化统续上宣告明室的寿终正寝,给抗清的汉族士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政策作用极为巨大);顺治二年为孔子加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尊号,恢复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大规模整理传统文化(如《佩文斋书画谱》等);以及其他及时、合适策略之实施。其实,这些效果明显的策略均是建立在满清(夷)对儒家道统(夏)之认同与奉行基础上的,从汉族士人方面看,则标志着“以夏变夷”的逐步取得胜利。这集中反映在当时的“经筵会讲”中。在古代,士为君师。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与宋太祖誓约“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更是彰显了“以道自任”之“士”的尊严,而“经筵会讲”则是士践行教化君王之责任的基本途经,明代之“士”在这方面虽不及宋,但保持了“经筵会讲”的传统,大体上维系着士为君师的尊严。如王时敏祖父王锡爵充任侍讲学士时,穆宗曾褒扬他“讲书明爽切直”,并要求“今后讲官讲书,都要如他讲”。即指此。又如文徵明之曾孙文震孟任经筵日讲官正开讲时,崇祯皇帝为了舒服,翘起了二郎腿(“帝尝足加于膝”),震孟虽已察觉,但未动声色,当讲到“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时,便故意“以目视帝足”。皇帝察觉后,不好意思起来,随即在衣袖的遮掩下慢慢地放下了二郎腿(“帝即以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震孟为“真讲官”。①明·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五十一《文震孟列传》云:“震孟在讲筵,最严正……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据百衲本《二十五史》(8),页663。清初皇帝既然宣布入继明室大统,“以道自任”的士人便急切地要求君王恢复“经筵会讲”,以期将以儒家经典教化帝王之责任落到实处,而实质上顺治皇帝对“经筵会讲”并不关心,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形式化严重。这反映出当时汉人士子以“道统”与满清君王之博弈中,势力互相交织,孰能胜出,难以分辨的情况。康熙帝亲政以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他不但对儒家经典十分痴迷,而且极为重视经筵会讲,康熙九年始讲时是间日进讲,十二年下令改为每日进讲(据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卷》款署“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王原祁奉敕恭画”可知,原祁曾担任康熙经筵日讲之“日讲官”[32])。这反映出当时士、君之间关系由博弈开始趋于和谐,“以夏变夷”开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须注意的是,康熙经筵日讲与宋明时代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即开始时康熙帝是“老实”地听士人讲,可随着对儒家经典的熟稔与自信,却“不老实”起来。十四年,康熙帝要求讲官讲后,自己也要“复讲”,以达到“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33]之目的;十六年干脆改“复讲”为自己先讲了以后,讲官再讲。如此这般,康熙实际上将士为君师颠倒了过来。这又反映出汉族士人“以夏变夷”的任重而道远。
如上述,开始时,士、君双方势力互相交织,孰能胜出,难以分辨,随着时间之推移,满清在实质上接受华夏思想文化正统(即儒家道统)之形势愈来愈明朗,汉族士人与满清政权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也逐渐得到了缓解。时敏卒于康熙十九年(1680),他是经历了上述入清以后士、君关系由博弈走向和谐之整个过程的。早有“出城迎降”②详细情况请参见陈传席:《“四王”散考》,朵云编辑部编《清初四王画派研究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之举、八面玲珑、善于审时度势、精于谋划之时敏深知,满清与蒙元同为夷狄,若将赵孟頫纳入“南宗”正统,即相当于“委婉地”表达了作为“南宗”嫡传的自己承认满清政权“入承大统”之合法性。之所以说他是“委婉地”表达,是因为其谨慎态度:时敏卒时,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尚未结束,此前,社会、政治、人心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汉族士人“以夏变夷”能否胜出,也颇费思量,尽管形势越来越明朗。退一步讲,即便时敏承认满清“入继大统”态度甚为保守,但这一观点加上他本为明代“大臣之后”、本有的“国朝画苑领袖”地位与显耀的社会身份,也有着巨大影响与作用。
其实,时敏的上述立场,也可由同一时代之“遗民”傅山(1606-1684)对赵孟頫书法评价的微妙变化中看出。满清入主中原的开始阶段,傅山是强硬的反对派与十足的“遗民”,曰:“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34]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权、人心与社会的稳定,民众的安居乐业,“康乾盛世”的逐步展开,尤其是汉族士大夫“以夏变夷”的渐趋成功,满清在实质上对华夏文化正统的认同。越到晚年的傅山越意识到应该扬弃以前的立场,其晚年《秉烛》诗有“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35]之句,“赵厮”者,孟頫也;“管婢”者,孟頫之妻管道升也。对赵孟頫夫妇书法之佩服溢于言表。
站在“以道自任”的士大夫立场,董其昌“南北宗”论是严防死守夷夏大防,董其昌亲炙弟子王时敏的“画学道统”论却在最大程度上显示出取消“夷夏大防”之势,故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
综上述,有理由相信,时敏“画学道统”系谱与董其昌“南北宗”论表面上看来是继承与发展,实质上却是反动与“重起炉灶”,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瞒天过海”。与其说时敏继承了董其昌“南北宗”论,还不如说他使“南北宗”论转了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极大的创新性。
五、王原祁之“画学道统”系谱
王时敏长孙、画学亲炙弟子王原祁(1642 -1715)有关“画学道统”的言论颇为丰富,现先胪列于下,再作分析。
1712年王原祁作《画家总论题画呈八叔》云:
画家自晋唐以来,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发其蕴,至宋有董、巨,规矩准绳大备矣。沿习既久,传其遗法而各见其能,发其新思而各创其格,如南宋之刘、李、马、夏,非不惊心炫目,有刻画精巧处,与董、巨、老米之元气磅礴,则大小不觉径庭矣。元季赵吴兴发藻丽于浑厚之中,高房山示变化于笔墨之表,与董、巨、米家精神为一家眷属。以后黄、王、倪、吴阐发其旨,各有言外意。吴兴、房山之学,方见祖述不虚;董、巨、二米之传,益信渊源有自矣。八叔父问南宗正派,敢以是对,并写四家大意汇为一轴,以作证明。若可留诸清秘,公馀拟再作两宋、两元,为正宗全观。[1]707
原祁自题《仿宋元笔意山水册》云:
画中山水六法以气韵生动为主,晋唐以来惟王右丞独阐其秘,而备于董、巨,故宋、元诸大家中推为画圣,而四家继之,渊源的派,为南宗正传。李、范、荆、关、高、米、三赵,皆一家眷属也。[36]
原祁《烟峦秋爽仿荆关》跋云: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痴之笔,用山樵之格,便是荆关遗意也。随机而趣生,法无一定,邱壑烟云,惟见浑厚磅薄之气。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用浅绛色而墨妙愈显,刚健婀娜隐跃行间墨里,不谓六法中道统相传,不可移易如此。[1]703
原祁为沛翁殷大司马作《仿黄子久设色》题云:
画自家右丞以气韵生动为主,遂开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赵概四家俱宗之。用意则浑朴中有超脱,用笔则刚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饰而神彩出焉,不务矜奇而精神注焉,此为得本之论也。[1]115
原祁自题《仿黄公望山水图》云:
明季三百年来,董宗伯仙骨天成,入其堂奥。衣钵正传,先奉常一人而已。余幼禀家训,耳濡目染,略有一知半解。①清·王原祁:《仿黄公望山水》轴,1706年,美国华府佛瑞尔美术馆藏。图版见郭继生《王原祁的山水画艺术》,页180,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版。
原祁为轮美作《又仿大痴设色》题云:
大痴画以平淡天真为主,有时而傅彩粲烂,高华流丽,俨如松雪,所以达其浑厚之意、华滋之气也。段落高逸,模写潇洒,自有一种天地活泼隐现出没于其间。学者得其意而师之,有何积习之染不清,细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时得闻先赠公大父训,迄今五十馀年矣,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时流杂派,伪种流传,犯之为终身之疾,不可向迩,特作此图以授轮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过人,自能为宋元大家开一生面,无负我意,勉旃勉旃。[1]708
原祁与时敏“画学道统”论相异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承其祖父时敏“画学道统”论,将明末以来的士人画学道统“南北宗”论中之禅化倾向剥离出去,使士人“画学道统”更纯净了,但剥离的程度与时敏相比要弱,主要表现在被时敏彻底抛弃的“南宗”一语又回到了原祁的“画学道统”论中(如“南宗正派”、“南宗正传”、“南宗法派”等,而“北宗”、“南北宗”等仍不见)。这反映出原祁为士人“画学道统”清理门户之意识不及时敏强烈。
其二,一如时敏将董其昌正式纳入了“南宗”系谱,王原祁又将时敏(“衣钵正传,先奉常一人而已”)纳入“南宗”系谱中。然值得注意的是,时敏“以复古为更新”中之“更新”实非一般意义上画学内部合逻辑之新变,而是由于“逢迎”、顺从画学外部环境(如政治、文化与思想等)之逼迫而来的“复古”即“更新”,是一般意义上“以复古为更新”之变体②清末民初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云:“论画之意‘以复古为更新',海内识者当不河汉斯言耶。”概括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关论述,此处不宜展开,请参见拙文《复古”即“更新”——王时敏绘画考论》(刊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研究》第1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因而,从究竟上看,时敏不应当被纳入“南宗”系谱。原祁将祖父列入“南宗”,有为尊者讳之嫌,表达师承与孝心而已。关于此,不但原祁“金针微度”云云已做了较清晰表达;王原祁族弟、弟子王昱《东窗论画》云:“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笔便有书卷气,盖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黄衣钵”[37];原祁著名弟子唐岱在《绘事发微》中所说:“余师麓台先生,家学师承,渊源有自。出入蹂躏于子久之堂奥者有年。每至下笔得意时,恒有超越其先人之叹。”[2]887也是很清楚的。而原祁表面上将时敏纳入“南宗”的更深层意蕴盖在于迎合满清孜孜以求入继明室大统的政治策略。
其三,时敏“刻意师古”,王原祁虽也强调“师古”,但更强调变古,即“传其遗法而各见其能,发其新思而各创其格”,更注重“更新”。
其四,原祁之“画学道统”论的排他性与崇南贬北比王时敏的更强、更明确。不难从其明确使用“南宗正派”、“南宗正传”、“六法中道统相传,不可移易”、“南宗法派”、“渊源的派”、“荆关遗意”、“皆一家眷属”、“所学者大痴也,所传者大痴也。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此而已”云云窥见一斑。
其五,清理门户。这一点,除上引原祁谓“时流杂派”为“伪种流传,犯之为终身之疾”外,他在《雨窗漫笔》中更有明确表达:
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竞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38]
王原祁将“广陵”、“白下”之画家与浙派相提并论,斥为“习气恶派”。“白下”指南京,“广陵”指扬州。当时在南京及扬州的著名画家有石涛、孔尚任、屈大均、龚贤、卓尔堪、张潮、费密及曹寅等,充满创新精神,极为活跃。原祁认为要对这一批画家“切须戒之”,贬斥之严厉,可谓无以复加!
其六,时敏将失节仕元的赵孟頫纳入南宗系统后,王原祁不但承继了其祖父之观点,而且更进一步,将高克恭等也纳入了进来并大加赞扬,谓:“元季赵吴兴发藻丽于浑厚之中,高房山示变化于笔墨之表,与董、巨、米家精神为一家眷属……吴兴、房山之学,方见祖述不虚。”如果说时敏将本为赵宋宗室却折节仕元的赵孟頫纳入“南宗”系统,还有赵毕竟是汉人与在某种程度上之被迫无奈等原因,尚可原谅的话,那么,原祁将本为夷狄之高克恭纳入画学道统“南宗”便似乎难以原谅了,但考虑到当时思想、政治、社会环境这又是可以原谅的。最初,满清虽与蒙元同为夷狄,但后来已不可同日而语,汉族士大夫“用夏变夷”对蒙元而言近乎无效,对满清来说却已基本取得成功。原祁画艺得到康熙帝赏识,蒸蒸日上,逐渐成为满清画学正宗时,从总体上说,汉族士大夫与满清政权已经消除宿怨、隔阂。他承续祖父时敏而来的“画学道统”论自然要取消夷夏大防,与其说这种做法有讨好满清政权之意,还不如说是大势所趋,“以直抱怨,以德报德”不正是圣人之教吗?
可见,由于时局之变化,原祁“画学道统”论不但与董其昌“南北宗”论已甚为不同,即便与时敏的也不可同时而语了,它不但是在大势所趋下对时敏“画学道统”论的发展创新,极具时代特色,而且打通了董其昌等“南北宗”论、王时敏“画学道统”之间的壁垒,超越王时敏“画学道统”,与“南北宗”论“暗通款曲”,让祖父创立的、自己发展的,且逐步成为满清画学正宗的娄东派接续上了作为中国画学正统之董其昌血脉,功莫大焉!“华亭血脉,金针微度,在次而已”,此之谓乎!
六、结语
行文至此,不难见出(本文《解题》部分所述),清人安岐、张庚、秦祖永等及后此学界所谓董其昌、王时敏之间“画学道统”直贯而下当是难以成立的,实则在明清易祚的思想、政治语境中,明末清初“画学道统”在王时敏这里发生了转折,或者说在王时敏、王原祁祖孙这里有一个断裂后重建的过程。而这些之所以可能,端在时敏的精心策划、刻意安排,深谋远虑,通过时敏奠基,原祁接力,娄东王氏家族画学走向有清一代近三百年画学“正宗”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三百数十年之后的我们,不得不为娄东王氏的心思缜密、深于谋划拍案叫绝!或许,我们只有知道了这些慎密谋划,才能更深入、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在清人心眼里王时敏为“国朝画苑领袖”[4]426。
参考文献:
[1]王原祁.麓台题画稿[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703.
[2]唐岱.绘事发微[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887.
[3]安歧.墨缘汇观·名画序[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
[4]张庚.国朝画征录[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425.
[5]秦祖永.桐阴论画[M]/ /画学心印:卷八.清光绪四年刻朱墨套印本:28.
[6]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庸》[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34.
[7]论语注疏:卷八《泰伯》[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87.
[8]孟子注疏:卷一三下《尽心上》[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70.
[9]孟子注疏:卷一○下《万章下》[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45.
[10]孟子注疏:卷四上下《公孙丑下》[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94.
[11]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孔丛子:卷二《居卫第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9:94.
[12]论语注疏:卷七《述而》[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81.
[13]礼记注疏:卷五三《中庸》[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634.
[14]孟子注疏:卷三上《公孙丑上》[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686.
[15]孟子注疏:卷六下《滕文公下》[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15.
[16]韩愈.原道[M]/ /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0.
[17]朱熹.中庸章句序[M]/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883:14-15.
[18]董其昌.画旨[M]/ /于安澜.画论丛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75.
[1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43.
[20]荆浩.画山水赋[M]/ /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六朝-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196.
[21]俞剑华.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M]/ /张连,古原宏伸.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248.
[22]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一[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十二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379.
[23]论语注疏:卷三《八佾》[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66.
[24]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四年》[M]/ /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01.
[25]郑思肖.心史·古今正统大论[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3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68.
[26]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吴元年十月丙寅”[M]/ /明实录:一.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1962:401.
[27]丘俊.大学衍义补:卷144[M]/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3册之子部儒家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66.
[28]李东阳.麓堂诗话[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5.
[29]项穆.书法雅言:资学·附评[M]/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20。
[30]王时敏.西庐画跋[M]/ /秦祖永.画学心印:卷三.清光緒四年刻朱墨套印本.
[31]郭继生.王原祁的山水画艺术[M].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30-31.
[32]王原祁.王原祁精品集:著录八一.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349.
[3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四“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辛亥”[M]/ /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702-703.
[34]傅山.字训[M]/ /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679.
[35]傅山.秉烛[M]/ /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258.
[36]吴聿明.四王画论辑注[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162.
[37]王昱.东窗论画[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420.
[38]王原祁.雨窗漫笔[M]/ /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710.
(责任编辑:周立波)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ve Writings“Both the Inheritor of Huating School and the Slowly Spread of Good Tradition are Just in There”of Wang Yuanqi —Derivation and Political Metaphor of the Painting Philosophy Orthodox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HAN Gang
Abstract:From the deeply analysis the derivation of the painting philosophy orthodoxy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it is not the reality of history that both Wang Shimin and Wang Yuanqi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painting philosophy orthodoxy of Dong Qichang. The fact is that Wang Yuanqi is the real inheritor of Dong qichang's painting school whose name is Huating School,whereas Wang Shimin is not,as his ideas have a lot of inconsistencies with Dong Qichang who he had pretend to advance along one path of painting while secretly going along another in the alternation of dynasties. All in all,the painting philosophy orthodoxy had changed with the alternation of dynastie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and it had resulted the change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houghts. These kinds of changes are the real reasons why Wang Yuanqi had wrote“both the inheritor of Huating School and the slowly spread of good tradition are just in there”in his inscriptive writings.
Key words:painting philosophy orthodoxy;inheritor;change;Huating School;the showly spread of good tradition
中图分类号:J20-0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1-23
作者简介:韩刚(1971— ),男,四川仪陇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方面研究。(成都61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