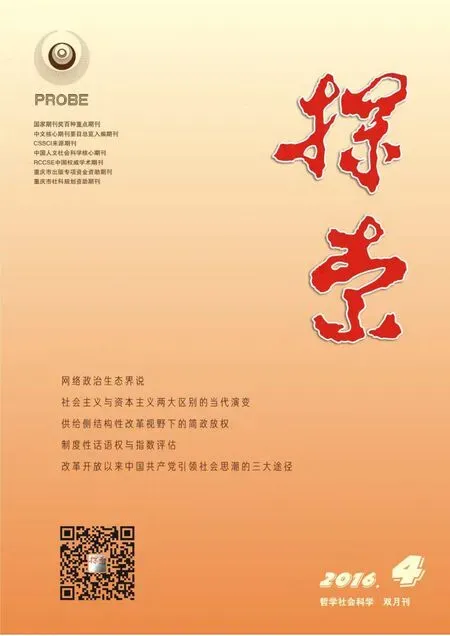考核国家:国际“治理指数”的福柯式视角①
[以]奥代德·勒文海姆著,朱剑编译
(1.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耶路撒冷91905;2.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上海20162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如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等,开始发布不同的指数和报告。这些指数和报告旨在根据国家在不同治理领域内的政策和能力来进行排名。“联合国发展计划”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当前关于治理方面——如政治腐败、公民自由、性别平等、人权、经济竞争力、新闻自由、政治稳定、环境表现、人类发展——的指数共有165种之多。尽管就其实践本身来说并不新鲜——第一个关于主权信誉的国际评级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发布,但针对国家的评级确实构成了近十年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上述的165种指数当中,83%的指数是在1991年到2006年间研发的,50%的指数是在2001年到2006年间研发的。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文章也已大量出现。近来关于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即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信用评级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或是对夸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家和私人投资者的经济和金融决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批驳。而另一类重要的文献则是关注“善治”概念——通常会被操作化并利用不同的治理指标来进行衡量——对援助国和被援助国相关政策的影响。这些研究旨在分析为什么诸多援助国会倾向于选择性援助,并强调善治与经济增长、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上述的研究通常是经验导向的。它们会探讨测量的问题,分析影响评级机构的因素,研究评级体系的出现,争论治理指数对决策制定的真实影响。尽管会涉及其中的一些问题,但本文试图将治理评级实践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更大的理论背景之下。基于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作者对治理指数的政治意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在作者看来,这些指数和报告作为一整套考核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或者说再次确认了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制结构及大国权威。
考核不仅反映了关于“善治”的特定知识及理念,并且还渗透进了权力,因为其试图形塑并引导被考核国家的行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强大的行为体(如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需要对他国的治理情况进行考核。而这些行为体可能会采用其他机构(如“透明国际”“自由之家”“传统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的考核,以此来使它们针对被考核国的政策合法化,或者,它们从一开始就会根据这些考核制定相应的政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际考核只是一种隐性的权力形式。作者强调,这种隐性特征基于的是行为体的“责任化”战略。也就是说,将被考核国建构成一个能自由地负责任选择的道德主体。如此一来,那些恶劣的、不受欢迎的行为,就是被考核国的责任,而非权力持有者或是考核者的责任。本文认为,考核作为统治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可以使强大的行为体无视或是弱化它们对诸多全球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所应负的责任。
本文的第一部分关注的是作为治理术其中一种形式的考核。第二部分将会探讨考核是如何渗透进权力及等级制关系的。并且,该部分还会展示考核如何建构出了一种合法性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弱国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无法忽视的。此外,在这一部分,作者将通过各种治理指数和报告来证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理由及技巧。本文的第三部分试图指出将被考核国建构成一个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1 考核与治理术
国际治理指数和报告类似于正式的考核。它们是由一组专家根据标准化的方法、准则及问卷,通过直接驻在该国或收集整理一、二手信息,例行监测并分析诸多国家的实践及其能力。而后,根据特定的知识体系,它们会按照国家在相关方面的表现,对国家进行打分或分类。其中,一些评级体系可能是对诸多专家和组织创建的指标和收集的数据的整合。尽管如此,即便是整合性的指标体系,它们在衡量政策或能力时,也是基于“权威”的知识体系。
在诸多评级中,有些采用的是排名表的形式,即根据单一降序的方式对被评价国家进行排名,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有些则是按得分数值来评价国家,如“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指数”。此外还有根据确定的定性分类来评估国家表现,如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划分的四级体系。不像统计性的数据库或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库那样根据“硬”数据来对国家进行评级,上述的评级已经掺入了一些经过精心表述的定性评价,且试图对国家在相关问题领域内的表现,进行本质上带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评判。
一些国际行为体发布的相关评估和报告并未包括一套关于评级的标准化体系,如“国际特赦组织”关于140多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相对来说,标准化的评级可能更加简单、清晰。这样能够帮助考核者、被考核者以及第三方迅速把握复杂现实。而且,量化与正式的分类能够产生一种方法严格、科学客观的表象。尽管相关治理评级的研发者有时会承认他们的体系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但其还是强调他们在尽可能地提供最为准确的分类。尽管如此,按照福柯的观点,所有的知识都是政治性的,尤其是在评价国家治理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所有的基本术语和问题都是具有高度价值倾向并富有争议的。
譬如,“世界自由指数”在评价以色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时,将以色列和以色列占领地区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导致以色列被评为“自由”,而以色列占领地区则被定为“非自由”。但在现实当中,以色列与其占领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如此明确的区分。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更像是国内冲突而非跨国冲突。
作者认为,考核既可以作为一种规训行为,也可以作为治理术的一种方式。而根据福柯的理论,规训行为是由以下三种进程结合作用的结果:1)根据不同的惯例训练个体;2)将其置于全景式的监控当中; 3)对禁止行为或越轨行为进行惩罚。通过创建惯例,收集信息,并对被考核者进行分类,考核变成了一种能够揭示并控制问题行为的工具。规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它通常被应用于正式的、限定性的等级制结构当中(如监狱、学校、军队等),以此来培养温顺的个体。另一方面,治理术则希望通过个体自由和选择自由来推动主体的自我优化。有基于此,自由的行为体一般会默许,有时甚至是主动请求其他行为体对其进行测试。这就使它不同于那些在规训情况下被强迫进行考核的行为体。考核作为一种规训工具在国际政治中并不常见,因为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等级制关系不够正式,而国家作为主权行为体能够拒绝考核。
在规训的情况下,任何通过考核揭露出来的越轨行为都会遭到惩罚,但是如果按照治理术,那么表现较差的被考核者则不会受到惩罚。尽管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但这并非惩罚。相反,考核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被认为是(至少考核者会将其塑造成为)被考核者能力低下的副产品。所以,关于被考核者的负面评价应该由被考核者自身来承担,未来的改进也需由其自身进行,尽管指导原则是由权力持有者来提供的。这就是治理术所谓的对个体的“责任化”。相反,如果进行惩罚,那么惩罚机构就需要对改善问题负责,因为惩罚被认为是权威机构的制度化实践。而该权威机构被赋予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式责任。
从治理术的角度来看,国际评级的相关指数和报告将被考核国家塑造成为道德主体,需要为其境内发生的事件负责。在这些考核当中,“国家”既是研究的客体,又被认为是具有行动能力的行为体,能够为其选择及政策,进而是考核中的得分负责。如此一来,考核就催生出了一种期待:即国家(尤其是表现较差的国家)应当改善它们的行为。但是这也模糊了(即使并非有意)其他行为体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责任。
2 权力和国际考核
2.1 知识等级
许多国际评级体系的研发者都认为:他们的指标能够被各国政府和其他行为体用来评估特定的国家政策,实现可欲的变革。即使这种判断纯粹出于善意,但需注意的是,权力并未在此过程中消失。事实上,考核至少在两个层面涉及了权力:第一,考核反映了知识的等级关系,根据这种等级关系,考核者确立了理性和正确行为的边界;第二,即使主权国家无需被强制接受考核或考核者的建议,但它们,尤其是穷国和不发达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考核或者考核者的建议。
尽管在评级标准的制定和评估方法的运用上,被考核者有时候会得到咨询。但从一开始,就是由考核者来决定需要考核哪些方面,包括哪些信息来源,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评价的具体操作办法。这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与“真理”的产生密不可分。按照福柯的理论,它们也与权力相互关联。事实上,权力在考核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尤其是与更具平等意义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机制相比,更是如此。因为对于那些将会成为国际行为准则的概念界定,国家有法律权利就其进行磋商。
相反,“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的特许借贷机构)曾经声明:即使它试图在评级的过程中——以确定是否具备贷款资格——提高国家的参与度,也要“确保这种参与会被看做是一种单向度的咨询,而非双方平等的协商”[1]6。“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开发的“经济自由指数”同样揭示出了知识的等级性。该指数宣称“旨在逐年记录(国家和地区的)进步或倒退……并使健忘的政治家重新记起经济自由的好处……本指数遵循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没有衡量就没有进步”[2]x-xi。然而,正是指数的研发者才能决定经济自由的涵义,以及进步或倒退的标准。
2.2 考核中权力与知识的联结
如果国家可以无视国际考核中的“责任化”效应,那么考核中所反映出来的知识等级关系本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事实上,国际体系中的考核并不具有强制性。主权国家完全可以拒绝考核,或是限制考核者的考核能力,再或是无视考核者的建议。如果说治理术旨在建构一种能够形塑并指导国家行为的真理,那显然有些国家会拒斥反映这种真理的理念或意识形态,抑或是直接反对这种真理本身。而国家确实可以阻碍考核者在其领土上的活动,并质疑考核者对其进行评价的权利。
譬如,喀麦隆在1998年曾强烈谴责“透明国际”的“傲慢自大”。因为该机构将喀麦隆评为当年腐败感知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2003年,阿尔及利亚拒绝了一些“自由之家”工作人员的签证,并要求该组织在开展相关活动时,应事先递交计划,获得政府许可。200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初步通过了一项议案,旨在严厉限制外国非营利性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作为一个极端的案例,朝鲜不允许任何国际组织收集关于它的经济信息。
尽管如此,许多被考核国家还是发现很难拒绝考核。因为霸权国家、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私人投资者,或是自己来进行考核,或是将其他机构的考核结果纳入自身的决策过程当中。这就使考核成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当然,它并非是唯一的影响因素。例如,研究对外援助的埃里克·诺伊迈尔发现,像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挪威这样的援助国并不总是基于治理指数的结果来选择援助对象,即便其宣称它们的选择性援助是按照善治的标准来进行的[3]81-82。托马斯·安德森等人则认为,在1993年至2000年间,美国的政治利益影响到了“国际开发协会”的借贷政策,尽管该机构的决定本应基于相关治理指数的评价结果[4]。
即使这样,这些国家还是逐渐意识到了考核的重要性。譬如,美国审计署研究发现:针对《人口贩运报告》中被评为同一级的国家,美国的相关政策并不总是一致。不过,美国国务院事实上早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在对其加以改进。这说明了作为一种治理技术的考核正在扩散。随着考核“心态”的扩展,即使在被考核者的表现与考核者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考核确实建构出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并在其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常态标准。结果就是出现了新的政治行为动机与界限,由此产生的争论和辩护也随之而来。
考核逐渐被强大的国际行为体所接受,使得一种新的关于合法性及正确行为的话语体系出现。如此一来,限制考核过程,或是公开反对考核,都将会承担被贴上“不透明”“失职”“专制”“无赖”等标签的风险。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得不同意考核,并承诺对考核较差的方面进行改进。而有些国家甚至会主动要求考核。
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千年挑战账户”为例,它是美国于2002年宣布启动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项目,由千年挑战公司运营。这家美国政府公司基于治理的16项指标,判断候选国是否享有获得援助的资格。而其指标多是取自像“自由之家”、世界银行研究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传统基金会”的相关指数。“千年挑战账户”已经逐渐被认为是向穷国分配援助的典范。有影响力的观察家因而会大加宣传、推荐该项目。
确定无疑的是,治理指数正在慢慢地渗透进发展援助的话语体系中。澳大利亚最近一份关于海外援助政策的政府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的对外援助正在不断增加。而从中获益的一个条件就是治理的改善和援助的有效性。对于那些达到预期表现的国家,澳大利亚将会给予额外的资源,以此来增强这些国家改善治理的动能。”[5]另外一个案例则是“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该计划是在“八国集团”的鼓励下于2001年提出的。现在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欧洲联盟提供支持。这些北方国家给予援助的条件就是治理的改善。而治理的改善是通过“非洲国家相互审查机制”——25个非洲参与国就相互之间的治理情况进行考察——来评价的。该机制不仅会将北方援助国的评价纳入其中,还会吸收外部考核者研发的“更可测量”“更加客观”的指数评价结果。
治理术适用于可自主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同样会受到强大行为体的限制的行为体。它被用来确定负责和理性选择的界限,引导行为体按照权力持有者希望的方式行事。还是以“千年挑战账户”为例,其所采用的选择性援助原则,意味着寻求援助的国家在申请项目时,必须同意根据千年挑战公司使用的评级体系来进行考核。如此一来,申请国等于接受了考核设定的行为界限。而这也就说明了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或明或暗地承认了考核所反映出来的知识等级关系。并且,因为“千年挑战账户”的指标直接取自几种不同的权威指数(如世界银行研究院的“治理指数”和“自由之家”的相关评级),所以随着它的指标作为一种评价工具获得越来越多的合法性,那些构成其指标来源的指数的权威性也就得到了增强。
对此,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斯里·穆尔亚尼·因德拉瓦蒂就曾反复宣称,“千年挑战账户”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所提供的认证,因为它为私人投资者提供了强大的投资信号[6]27。尼加拉瓜驻美国大使萨尔瓦多·斯丹达格也认为:“除了援助数量外,获得资金援助本身同样意味着是对我们的认可。而这对投资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7]
考核已经开始成为被考核国家寻求权威性认证的工具。它们显然意识到了知识和权力在考核中的结合。例如,土耳其对其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由“世界经济论坛”研发)2006—2007年度排名中提升了12位而颇感自豪。并且,它还意识到像“全球竞争力指数”这样的国际指数往往是投资者的第一参照。
认证效应在信用评级中尤其明显。在蒂莫西·辛克莱尔看来,信用评级机构事实上就是“新的资本的主人”。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在较小程度上)的信用评级在决定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的能力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克里斯托弗·布鲁纳和拉维·阿布德莱同样发现:“许多主权国家政府试图通过信用评级来证明它们的公开透明和对市场的亲善。”[8]192考虑到主权国家需要为评级支付费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们已经将考核的知识等级关系内化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且,这一趋势还得到了美国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的鼓励。“联合国发展计划”在2002年发起了一项特别企划,旨在资助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评级。随着低收入国家对评级的日益接受,它们越来越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这些评级,即使它们自己需要为此支付费用。因为一旦国家接受了这些评级,那么评级的缺乏本身就有可能被视为是负面信息。
按照辛克莱尔的看法,信用评级机构本身就是强大的国际行为体。当这些机构采用相关评级来评判国家的治理情况时,那些考核的权威性也会随之增强。事实上,“腐败感知指数”和“世界自由指数”就被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拿来作为决策的依据。康斯坦丁·梅里奥斯和埃里克·佩吉特-布兰克发现,“腐败感知指数”对于信用评级有着极强的影响力[9]。而坎迪斯·阿彻等人也发现信用评级机构会用“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和政府责任、政治稳定程度、暴力节制能力、政府有效性、管理质量、法治和腐败控制能力”[10]359。
“腐败感知指数”事实上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表明考核的知识等级关系是如何因为强大国际行为体的采用而得到强化。除了信用评级机构外,“腐败感知指数”还被许多发达国家的财政部所采用,以此在为出口商提供出口保险时计算保险费。并且,西方国家的商务和贸易部长在为公民提供关于外国商业和投资环境的信息时,也会经常提起“腐败感知指数”。此外,像“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这样的私人援助机构也会采用“腐败感知指数”。
2.3 考核“心态”扩散的理由
每一个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理由来考核国家,但一些普遍性的因素解释了为何评级在当今已经扩展到如此多的领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特定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对考核感兴趣并且有需要。对此,尼日利亚前财政和外交事务部长恩戈齐就说:“政策制定者及改革者试图对治理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严格度量。而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作为一种无价工具,可以在任何领域内当作评估进步的基准。”[11]
尽管如此,考核扩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具体来说,首先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大幅上涨,促使投资者寻求更多的信息以减少投资风险。其次,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弱化,突显了第三世界糟糕治理的外溢作用及负面影响。再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世界政策改革及外部援助的失败,导致援助者因为资金被浪费而感到沮丧。最后,道格拉斯·诺思以及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学者的著作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对于国家成功的重要性”。
更大的动能来自于美国在“9·11”事件后的认识:第三世界的善治、发展与减贫和消除反美恐怖主义是相关的。这种理解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透明国际”“自由之家”这样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腐败、缺乏民主、不尊重人权、善治的普遍缺乏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并导致外部援助的无效。在此背景下,考核在霸权国家、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结,这一联结产生并再生了国际政治的权威。
当美国或欧盟采用世界银行或其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考核结果时,非国家行为体就有机会参与设定国际议程,甚至可以按其支持的路线来指导被考核国家的行为。同样,考核使强国不仅能够形塑被考核国家的行为,并且通过宣称考核基于的是客观的、技术性的标准,而使这种形塑变得合法化。即使被考核者发现考核带有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色彩,但鉴于考核所宣称的专门性、客观性、严格性和公正性,它们仍有可能将其看作是一种不那么具有强制性和对抗性的推进权力方式。
当然,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可能确实会公然使用点名羞辱的方式,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在反洗钱运动中不合作国家和地区的名单。但通常来说,考核者或第三方在使用具有潜在羞辱性的信息时,总是宣称他们并不会以此来羞辱被考核国家。在他们看来,考核仅仅是反映了被考核者的真实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得到了西方的认同,但形成国际考核的基本理念并未获得普遍认可。所以,考核试图在评价过程中融入“专门性”和“技术性”,以使考核更加客观和自然,或者说是“非政治化”。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考核者与被考核者之间的关系:考核者并不是对被考核者发布指令或命令,而是提供建议和意见。当然,这不是说在互动过程中,权力并不存在。只是如此一来,弱国宣称强国在它们身上强加义务的合法性就消失了。而且,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考核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被考核国家进行自我改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被考核者的“责任化”。也就是说,被考核国家如果想要获得由强国控制的国际资源和福利,那就必须证明它的政策质量及能力。
3 被考核国家的“责任化”
国际考核并不总是能够按照考核者希望的方式来形塑和指导考核对象的行为。丹尼尔·考夫曼等人发现:他们自1996年开始发布“治理指数”,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情况因此有了显著改善”[12]18。并且,他们还注意到,尽管一些国家的治理情况得到了改善,但这些变化往往是表面上的(如仅仅是建立了反腐机构,但这一机构没有有效的权威),只是针对国际压力的权宜应对罢了。
尽管如此,考夫曼认为积极的改善还是存在的。从2005年开始,“治理指数”改为每年发布。这是为了能够更加及时地监管全世界的治理情况。尽管许多国家在治理方面的年度改变是很小的,但是通过观察年度数据的变化,可以帮助使用者发现并监管那些在短期内发生巨大改变的地方。这其实说明了世界银行研究院认为它的指数有能力改善国家的治理情况。而且,一些国家确实会根据相关考核的结果来改变政策。譬如,道格·约翰逊和特里斯坦·扎伊翁茨认为:“即便是在千年挑战公司初创阶段,一些国家也会为了获得它的援助,而确实改善它们在一些指标上的表现。事实是,相较于那些贫困的非候选国家,‘千年挑战账户’的候选国为了获得援助,超过25%的指标表现得到了明显改善。”[13]2-3
即便如此,还是应该认识到:考核建构出了一种新的关于国家责任的话语体系。它将被考核国家变成一个需要为其政策及能力负责的道德主体。反过来,这又为强国针对被考核国家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辩护,或是为其制定新的政策提供了依据。也正因如此,对于被考核者的决定和建议并非是基于权力,而是根据考核揭示出来的真实情况加以决定的。这样就创造出了一种客观公正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责任化”策略使得考核者或第三方可以指导被考核国家,而无需为此负责。
前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曾敦促柬埔寨要大力遏制腐败,否则它将面临来自世界自由贸易市场的孤立。沃尔芬森说道:“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世界贸易中成为可靠的竞争者,那么它只能责备自己。”[14]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则试图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参加由美国和“联合国发展计划”资助的项目,并以此去获得信用评级。他说:“没有评级的国家更为神秘,因此更加危险。一旦获得主权信用评级,你们的国家就能减少风险并鼓励外部投资。主权信用评级能给资本以信心。”[15]
这些案例涉及不同的领域,但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考核揭示了国家的真实情况。评价较差是被考核国家自身作为的结果。考核者也许能够提供帮助和指导,但最终的责任还是应该归在被考核者身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国家应该为其政策及能力负责。但问题在于:
第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大为不同。这就意味着治理情况的改善(按照西方标准)将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但考核者总是期望能够迅速改进治理情况。如此一来,国家不仅需要比较它们的政策及能力,并且还要对比它们迅速变革的能力。即使一个国家表达了改进的愿望,并且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它也仍有可能因为“落后”于他国而招致负面评价。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被考核者的“责任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考核者的责任,即便被考核者的糟糕情况完全是由于国际行为体的压迫或诱导所致。譬如,腐败至少包括两方——贿赂者和受贿者,事实上,除了“腐败感知指数”,“透明国际”还发布了“行贿指数”排名。它被用来衡量工业化国家公司在外行贿的程度。然而,在“行贿指数”中排名较低的代价要远小于在“腐败感知指数”中排名较低的代价。因为后者已经在各种决策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前者却还默默无闻。
在人权和人口贩运问题领域也存在着类似情况。例如,“自由之家”在2005年的评级中将约旦定为“部分自由”,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现了“虐囚事件”。尽管并未弱化约旦的责任,但评级没有正视美国的责任。因为正是美国的压力,才使约旦开始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在人口贩卖问题领域,巴西在《人口贩运报告》中被归入倒数第二级。排名这么低的一个原因是在巴西的旅游地区,针对儿童的性剥削现象十分严重。墨西哥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它与美国交界的地方及一些旅游地区。这份报告只是大致提到了(在导言部分)美国的色情旅游对人口贩卖的推动作用,在正文中却根本没有谈及此事。然而,据估计,超过16 000名儿童卷入了墨西哥旅游胜地和边境城市的色情行业当中,而美国的儿童性旅游者是主要的剥削者。
4 结论
本文的目的不在批评考核本身。有些时候,考核确实能够帮助推动积极的价值,如民主、人权、法治和责任政府。尽管如此,正如治理术所揭示出来的那样:知识与权力是分不开的。本文强调国际考核不是单纯为了服务政府,或是国家可以任意接受或拒绝的建议。这些评价体系嵌入了权力和统治关系中。被考核国家如果不冒特定的风险,是不会断然拒绝这种评价的。因此,考核应当被看作是国际等级制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中,权力和知识在霸权国和特定的非国家行为体间相互流转。
虽然如此,国际政治中的考核不是为了强迫国家做其不喜欢做的事情。相反,它建构了一种话语体系,并由此构成了国家正常性和国际合法性的一种决定因素。事实上,考核还削弱了霸权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使用权力时的任意性,而被考核国家的决定和政策也日益需要得到考核的结果来证明。不过,这却造成了对每个被考核国家特定背景的忽视,从而导致了决策制定的“机械化”。此外,考核还推动了针对弱国和穷国的“责任化”,结果造成考核者和第三方的“非责任化”。而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国际体系中的非正义和剥削。因此,对这种趋向的反对必须包括对考核的批判性分析。
参考文献:
[1] World Bank,Disclosing IDA Country Performance Ratings[EB/OL],2004.at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DA/Resources/disclosingIDACPR.pdf,accessed October 11,2007.
[2] Tim Kane,Kim Holmes and Mary Anastasia,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2007[R],Washington/New York:Heritage Foundation/Wall Street Journal,2007.
[3] Eric Neumayer,The Pattern of Aid Giving:The Impact of Good Governance on Development Assistance[M],London:Routledge,2003.
[4] Thomas Andersen,Henrik Hansen and Thomas Markussen,US Politics and World Bank IDA-lending[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2,No.5,2006.
[5] AUSAID,Australian Aid:Promoting Growth and Stability[EB/OL],Canberra:AUSAID,2006.at http://www.ausaid.gov. au/publications/pdf/whitepaper.pdf,accessed October 12,2007.
[6] John Danilovich,Fostering“Champions of Development”: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J],Issues of Democracy, Vol.11,No.12,2006.
[7]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Assessing Nicaragua’s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Compact[EB/OL],at http://www. cgdev.org/doc/event%20docs/NicaraguaMCAccountevttrans.pdf,accessed October 10,2007.
[8] Christopher M.Bruner and Rawi Abdelal,To Judge Leviathan:Sovereign Credit Ratings,National Law,and the World Economy[J],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25,No.2,2005.
[9] Constantin Mellios and Eric Paget-Blanc,Which Factors Determine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J],EuropeanJournal of Finance,Vol.12,No.4,2006.
[10]Candace C.Archer,Glen Biglaiser and Karl De Rouen Jr.,Sovereign Bonds and the“Democratic Advantage”:Does Regime Type Affect Credit Rating Agency Rating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1,No.2(Spring, 2007).
[11]World Bank,World Bank Releases Largest Available Governance Data Source[EB/OL],at 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NEWS/0,contentMDK:21050333*pagePK:64257043*piPK:437376*theSitePK:4607,00.html,accessed October 10,2007.
[12]Daniel Kaufman,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Governance Matters V: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5[M],Washington:World Bank Institute,2006.
[13]Doug Johnson and Tristan Zajonc,Can Foreign Aid Create an Incentive for Good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EB/OL],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96293,accessed October 11, 2007.
[14]Woodsome,World Bank Warns Corruption could Destroy Cambodian Economy[EB/OL],Voiceof America,February 11, 2005,at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archive/2005-02/2005-02-11-voa21.cfm?CFID=111976039&CFTOKEN= 67341335,accessed October 10,2007.
[15]Colin Powell,Remarks at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Conference[EB/OL],Washington,DC,April 23,2002,at http://www. 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2002/9634.htm,accessed October 1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