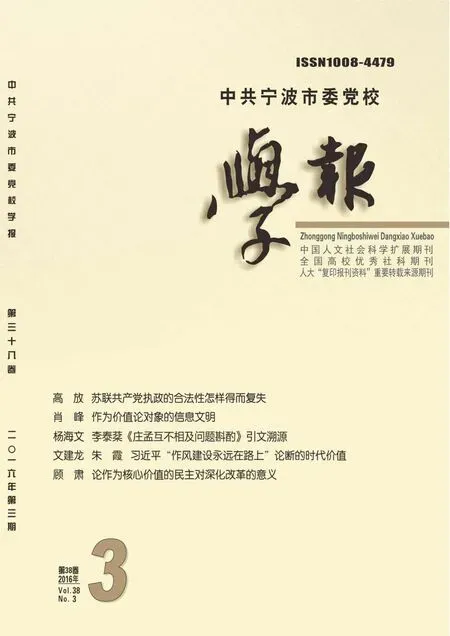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
——基于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理解
郭美华(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44)
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
——基于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理解
郭美华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基于现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来理解孟子哲学的自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性角度而言,孟子证成了其自身之为自身,即自我不是作为普遍概念的例子而是切己之自身而存在;并且,孟子从自我“内在固有”之思出发,以能思能觉的主体之展开自身作为自我,是逐渐生成的精神性作为自我属己世界的主宰和本体根据,这都与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另一方面,孟子的自我又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心所同然”的普遍性承诺,他具有很强烈的“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就容易走向文化或道德英雄主义,而有悖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因此,对于孟子哲学中的自我,需要经过创造性的阐释才能真正成为平民化自由人格。
[关键词]孟子哲学;自我;普遍性;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
孟子哲学无疑可以有很多不同样式的诠释,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基于个人的特殊阅读与思考经验,本文瞩目于从“自我”来解读孟子的一些思想。这个“自我”的观念,“从价值论角度来说,对自我认识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自我’既是具体的存在,同时也具有作为自我之本质。对人生的真理性认识,要求把人作为主体,人生是‘我’作为主体的活动。作为主体的‘我’,首先是个实践主体。”自我就是那个具体活生生的行动。就当下而论,“我”在书写“孟子”——这里面有两个纠缠的“自我”:孟子作为其自我,以及书写孟子之自我的自我。通过揭示孟子哲学中“自我”的特殊意蕴,我们将拒斥普遍主义的概念式理解,而走向单一或独己的自我之活生生的存在。
孟子是一种特异的“骨气”,我们不能、更不必把他归类为某种“流派”,以获取先于其自身作为“独特个体”的“先在规定性”。尽管语言的叙述与论证总是显得处于“普遍性的窠臼”之中,而我们对孟子的“当下阐释”,总是受制于诠释学自身的普遍主义“冲动”。伽达默尔说“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但是,他却又说,人通过教化而不断“向普遍性提升”,“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毋庸置疑,在脱离直接性与本能性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成为具有共性的“人”或“人类”的分子,并非是每一个人接受教化、进行学思修德的最终目的;接受教化与学思修德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一个“不可名言”(语言对对象的把握就基于概念的普遍性)的“自身”——一个具有自身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造就自身成为一个具有个性的“人格”。人格的理想或理想的人格,是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之一。当代哲学家冯契将哲学史上认识问题归结为四个,认为第四个就是理想人格的培养问题,即:“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也可以换一个提法,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冯契这个看法是对中西哲学史的总结,他以理想人格作为第四个问题纳入认识论视野,称之为“广义认识论”,具有了统一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生存论”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存论意味上的理想人格,于冯契而言,其基本内容,就是“自由”。这种自由的人格理想,结合近代以来的哲学革命,与拒斥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相一致,冯契称之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近代人对培养新人的要求,与古代人要使人成为圣贤、成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普通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我们所要培养的新人是一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并不要求培养全智全能的圣人,也不承认有终极意义的觉悟和绝对意义的自由。不能把人神化,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人有缺点、会犯错误,但是要求走向自由、要求自由劳动是人的本质。人总是要求走向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不是遥远的形而上学领域。理想、自由是过程,自由人格正是在过程中间展开的,每个人都有个性,要‘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来培养。”拒斥圣贤、拒斥英雄是近代哲学革命的内在要求,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平凡而普通的、是自由而个性的。这样的人格,是过程中的个性,不能以抽象的外在普遍性来“形塑”每一个人,而是因其自身内在的个性而成就每一个人。
在冯契看来,近代关于自我的理想人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按照传统的看法,如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禅宗讲‘即心即佛’,王阳明讲‘满街都是圣人’,都是有一个划一的标准,要求人成为纯金一般的理想人格。近代的观念不是用一个划一的标准来衡量人,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那种毫无特色的‘醇儒’(朱熹语),而是提倡多样化的人才。”从近代以来追求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这一理想出发,否定整齐划一的千般一律而注重多样化的具体个性,我们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就具有了一种新的意境。我们就不再会将个体之人不断地回溯到、还原为脱离了具体存在的超越天道,以虚幻的“天人合一”论来确定人的所谓“真实”存在——湮没了个体之后的天人合一状态所谓真实存在状态,实质上反而是虚假的存在,那是以虚假当作真实;从而,我们将对孟子哲学中关于自我的双重性加以显露,一方面,既显露其潜蕴的、指向自由个体人格生成的内容——即具有内容的“自我”;另一方面,也显露孟子哲学中对于自我的遮蔽,即为普遍本质压垮了的作为无内容的虚妄自我。简言之,我们既经由创造性的诠释而彰显孟子哲学中蕴涵的“自我”,也揭示其中对“自我”的湮没。
一、绍三圣与学孔子:“孟子”作为自我的“历史性”生成
孟子的思想体现在《孟子》中。《孟子》的文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仅仅是“孟子”那个独一个体的言说;一方面,《孟子》作为文字流传物具有脱离于“孟子”那个独特个体的独立性。因此,在我们对《孟子》文本中所说的“孟子”加以阐释时,就要力图避免因为文本的独立性而将“孟子之自我”解释为脱离孟子的“普遍自我”。当然,由于语言文字的“公共性”以及不同个体生存的“相与性”,“孟子自我”与“普遍自我”之间,具有着某些内在性关联。由此,《孟子》对于“孟子自我”的“言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性相通”。
史称孟子“好辩”,《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孟子解释自己何以“好辩”的文字。《孟子》中,孟子本人将“好辩”视为“绍三圣”的自我贞定——“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继承,一方面是创新。结合起来说,孟子以三圣之所为为自己之为作为自己的历史性前提,即在历史变迁中确立“自我”。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
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谋。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自许所承的“三圣者”,不是尧、舜、禹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任何其他三个“圣人组合”,而是禹、周公、孔子这一特殊的组合(尤其孟子本人还特别突出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这个脉络)。这是有深意的。在《孟子·万章》中,禹其实是一个标志性的“圣人”:他受禅让而得天下,但是,他开启了传子不传贤的非“禅让”之制。这一制度在孔子降生之先,已然运行良久,是孔子之为孔子的“天命”——即让许多后儒唏嘘不已的孔子不得其位,在孟子其实已经视之为天命。所谓天命,孟子理解为“莫知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禹还是某种具有神话传说性质的“神圣道德与权力”的统一物,因此,他也就活在某种抽象而模糊的“统一状态之中”,即禹经过“疏浚水流”,使水回到水所应当去往之地(江河湖海)而显露大地,让大地成为“人”可以安家之地。这个“人”具有抽象的整体性,或仅仅是抽象的整体性的人。
水流之去往其所而让大地显露,却并不仅仅是让“人”可以生活在大地上,人之外的禽兽尤其威胁人自身的猛兽乃至于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夷狄)还羼杂于大地。于是,对于周公而言,其自身便在于将大地上混杂于人的禽兽与夷狄驱逐出“人群”,使得人能无杂于“非人”而在大地建立家园。然而,人群作为一个群体聚居在大地,人群内部却有着败坏人之为人的存在者,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手握权柄者,本来应该成为人之为人的最高实现,却成为人之为人的最大败坏者,孔子作《春秋》不外乎就是要用“语言的叙述”来揭露于“彼”,并昭示人之为人敞露于“此”——“文在兹”(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彼而在此)。
孟子好辩是对孔子“文在兹”的“历史性”继承。禹“拥有权力”,周公可以拥有权力而还政于成王,孔子有德而文,孟子之所愿则是“学孔子”。学孔子的前提就是从“权力”场自觉地撤回,所以孟子明确以对土地的争夺为表现的权力争斗,是“率兽食人”,作为孔门之徒“羞比于管晏”、“不道齐桓晋文之事”。在孟子看来,如此退却于“权力场”而开启儒家本真的“道德教化场域”,这是儒家之为儒家的“天命”必然性——不必更不可再究诘的起点。因此,疏远于“权力”,便有了最为基本的自我要素——即让思想摆脱于力量而拥有“自由”。自觉地摆脱权力束缚,不是说在“现实”中不受权力的侵夺,而是说,作为思想者,我们让自身的思想成为与权力迥然相异的力量。孟子明确具有的这种自觉疏远于权力的意识,使得思想能“由其自身展开”而有的“自由”,是自我的首要涵义。
自觉摆脱权力束缚而学孔子,其要义就是走向真正的“自我”。《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公孙丑与孟子由讨论“不动心”到“知言养气”,转到讨论“学孔子”,其具体文本有很多东西值得深入分析,我们仅仅注意公孙丑将孟子与孔子学生相比孟子表示不屑之后,公孙丑又提出孔子之外的其他圣人来论圣人之同异,孟子此际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道德的普遍原则通常以否定性戒令为表现,孟子认为孔子与伯夷、伊尹等圣人“一样地”不去做“行不义杀不辜”之事。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人类的本质,往往表现在这种普遍性的道德律令之中。作为否定性的规定,这些普遍律令只是消极地划出“人之所不能为者”,而并不积极地给出“人之所能为者”。普遍律令表现了人类的普遍本质,只有遵循这些普遍律令,一个存在物才成为“人”;但是,成为人只是区别于禽兽(当然包括区别于神),而并未使得人成为一个“自己”或“自我”。在孟子看来,学孔子的意义却是要“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作为人并成为自己之“自我”。
孟子所自觉“承继”三圣人的历史性与“学孔子”,其实质是指向对自我的一个更高的要求:一个人作为“自我”而活着,不要单单成为普遍概念所描述的一般“存在物”,而要经由自身活出一点“盛于”历史、“盛于”他人的东西,一种是经由自身的存在才有的东西、一种属于自身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这在冯契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中,就被强调为“自由个性”:“在无机界,个体间的差别人们往往加以忽略,因为对人来说,这种个体性往往并不重要。当然,与人关系密切的,如地球、太阳、长江、黄河等,其个性仍为人们所注意。在有机界,一般也主要注意其群体、类、族,只是对人关系密切者,如手植的花木、家养的狗、猫,才注意其个体特性。但对于人类本身,情况则不同。我们不能像对待木石、猫狗那样对待人。人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每一个人本身都应看作目的,都有要求自由的本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我,是孟子以大禹、周公、孔子为历史性先导而彰显真意。经由历史性而成就自身的具体性,就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者:“人作为具体存在要求被看作个体,而不仅仅是类的分子和一个社会细胞,也不只是许多‘殊相’的集合。人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是‘单一’的,而殊相是指一般的特殊化。”这意味着,孟子的思考,就是成就了孟子之自我本身。生存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自我,而不是成为一个某种普遍本质的例子或某种超越存在物的表征乃至更不是成为某些现实中的大能者(英雄或伟人)的“炮灰式工具”。就此而言,我们对于那种将政治权力上的帝王或英雄作为最重要的伟人来加以崇拜的说法,就要表示严厉的反对。
二、四端与思:自我的内在生成
作为自我,它有其历史性根据,更有其自身内在的根据。历史性根据,突出了其“时间性”上的历史文化背景;自身内在根据,则是其非时间性的心性或本体根据。这种根据,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谓良知良能,是不依赖于学习、思虑的,有着先验主义的色彩。不过,孟子强调的是仁义的内在性。在孟子与告子的争论中,有一个仁义之内外的争论。告子认为是仁内义外,认为爱发乎本然,是内在的,而义对于本然之爱的约束,对于爱自身而言,是外在的。但孟子认为:“行吾敬,故谓之内也。”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出乎人之自觉,发乎人之自愿,源乎人之自得的——基于道德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意识状态的自觉自愿自得才有真正的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关联着人的心和身的关系。孟子用“天之所与”来说明身心二者之间的统一而内在的关系。孟子认为,人作为心和形(身)的统一体,二者都是天生就有的,但在二者之间,心作为主宰者支配着形体或身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身心之统一,就是一个真正道德行为主体——“自我”。在自我中,能思之心与能感之官有着主从、大小的关系,能思之心是大体,能感之官是小体。身体或小体由心体或大体所主宰、感觉由思所支配,这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大人”。二者的这种关系,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以为思是能自得其自身的力量,而身体则不是能自得其自身的力量,这是自我内在性的突出之点,表达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某些意蕴。
身心的内在统一关系,使得道德意识、道德法则显现为“天生固有”之物。孟子用四端之心或四心来表达这种天生固有的内在道德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提出了作为真正道德行为的几个要点:1)作为具体道德内容的仁义礼智,根源于固有而非外铄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能思之心与所思的内容是一体而统一的。并不存在一个能思之心从自身之外去引入、袭取外在规范或原则的问题。2)固有而非外铄,体现在能思之心实际地“运思”之中,而“运思”关联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具体活动。3)在具体求则得之的活动中运思,便能“即事集义”——彰显“有物有则”。
在具体的行事活动中运思而获得“义”(道德规范或原则),是自我内在性的很重要的内容。这一点,使得我们不滑入一个错误的理解之中。这个错误的理解就是:以为道德观念、道德原则是作为超越的东西,存在于一个先验的作为实体的心灵之中。在孟子,自我首先是在具体行事活动之中的运思或运思在具体行事活动之中。这就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的意思:“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据焦循《孟子正义》,“正”训“止”,“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就是行事不止而心思相俱。心即是思的力量,思与行事的一体相融不离,一方面不能舍而不耘(心忘而无思);一方面是不能揠苗助长(心脱离具体行事而自私用智杜撰一个抽象的理智世界)。心思在行事中,义在事中,行动的展开就是不断实现着的真实“自我”。如尼采所说,不要行动之外去虚构实体:“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就是一切。”
孟子以思和行动的融而为一来说明道德的自我,放在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论中来理解,更能显其真意。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一方面强调,以自我意识之思为主要内容,有一个“我”作为主体:“从现实汲取理想。把理想化为现实的活动的主体是‘我’或者‘自我’,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一个‘我’——自我意识或群体意识(大我)……‘我’既是逻辑思维的主体,又是行动、感觉的主体,也是意志、情感的主体。它是一个统一的人格,表现为行动的一贯性及在行动基础上意识的一贯性”;但是,另一方面,冯契强调基于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交互作用过程,作为主体的自我又不是源初固有的实体,而是不断生成的:“精神不是离开物质的另外一个实体,精神是贯穿于意识活动之中的有秩序的结构。所以在现实的精神作用之外并没有潜伏着一个心(精神)的实体。但在所有现实的精神作用之中,贯彻着一个昭明灵觉的‘我’,这就是意识主体,就是良心、良知。黄宗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工夫’是指精神修养、精神活动,心的本质就是工夫所达到的有序的结构,此外别无精神实体。”自我是基于觉悟之思与自主行动相融而有的逐渐生成物,它由自身成为自身。每个人都运思,每个人都活动,每个人都生存,他造就自己与自己的世界(作为境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是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人格“也体现类的本质和历史联系,但是首先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自由的个性就不仅是类的分子,不仅是社会联系中的细胞,而且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间保持其独立性。‘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我所享受的精神生活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这样,‘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我自为目的活着,我的活着的全部就是我活生生的思修学行的属己性。
不过,孟子的良知、良能,用平民化自由人格的观念来看,有其先验主义的倾向:“孟子讲性善说,以为人的天性中有善端,通过后天的学习、修养,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人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孟子的这种学说,是一种先验论的复性说,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皆备于我’,人本来即有仁义礼智,而这就是天性。”用先验性的良知良能之善,来担保所有人趋向善的普遍性,一方面掩盖了现实的个体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就忽略真正的行动与真实自我的实现,从而走向普遍性,并易于陷入英雄主义圣人观的窠臼。
三、舍我其谁与无父无君:从神圣走向平凡
孟子有很多豪气而迂腐的话语,这些话语显示,作为古典儒学对自我人格的阐述,距离近现代化之后的“平民化自由人格”,尚有一段距离,需要我们加以分析。
孟子说自己的志愿是“学孔子”,孔子之学,下学而上达,下学是具体的学思修行,这可以是每一个自我或个体的事情。然而,就上达而言,其目标却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个性成为抵达普遍性的环节或手段,这却不是真正的自由自我。自由人格的人,不是一般的本质,也不是符合某个典型的样式,而是“一个个的人”,“道德行为所要对待的,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不把一个一个的人视为目的,即离开了道德的根本原则——人道原则。”孟子那里,成为像圣人一样的人,而不是成为自己是目的:“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这就把自我淹溺了。
在孟子看来,有一种在少数个体之间神秘传承的东西:“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本来是五百年必有王者起,但孟子说他时间上、空间上距离孔子都那么“近”,但那个尧舜禹汤至于孔子的“之”,都没有了,他按耐不住要起来“传承”、“担当”、“彰显”。这个说法与《论语·尧曰》有继承性,成为后来韩愈肇端、宋明理学大张其说的“道统论”。这个说法,也被张载说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在今天都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很值得忧虑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遵循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性,服膺康德所说的“成熟而自觉地运用自己理性”之说。不能经由理性运思而公开、透明展示自身的这个神秘的“之”(道),便是应当受到拒斥的。
道统担当,总是在有限自我与无限天道之间,正如余英时所分析的,构筑了一个神秘的“通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人的内在之心,与超越的天之间,有一个神秘的通道,使得心思可以抵达天。心思能通向天,勾销了现实行动自身的必要性意义,反过来以天作为超越实体的“预置”诠释“心(思)”本身。而天的预置,使得自我的一切现实生存活动及其展开内容,都没有新意。现实的活动,不过就是“固已有之”之物、“原本具有之物”的显露——“扩而充之”而已。没有什么创新和个性的造诣,一切原本就具备于我——“万物皆备于我”,只需反求便一切皆得。从自我心思走向天,反过来从天解释自我,最后又归之于“反求诸己”。在天的赋予与人的求索之间,如此神秘关联,显得逻辑紊乱、秩序混淆。
有这个内在于自身之内的“天”,这个即我即天的存在者,便容易走向自由与力行的反面,而表现出谩骂妄断:“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有普遍主义倾向,就容易走向英雄主义圣人观;圣人观就容易忽略不同的观点意见的“平等自由而有序”的争论与多样性绽放而“自居评判者”。如此,孟子思想就走向权威主义的天命世界观:“‘天命’就是真善美的本体,‘知天命’、‘顺天命’、与天命合一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最高的人生理想;而体现‘天命’的尧舜三代就是‘王道乐土’的理想世界。”如果将“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与“人皆可以为尧舜”结合起来看,一方面只有某些英雄式个体可以在其自我与天道之间交通,而一般人无与于天道;一方面又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尧舜不过就是那为数不多的列于英雄榜的圣人),这样可以得出的结论就很令人疑惧——要么是欺骗式许诺给每个人成圣的希望,要么是以普遍化的一律式存在样态吞灭个体自我。这种没有多样性的自我实现的“自我”,是某些人的膨胀的自我。这种膨胀了的自我,引天以自雄,进而反过来把自我僭越为天。英雄主义圣人观,不外乎就是这样的把戏,以为圣人就是这个世间的光明火种,众人就是等待圣人/英雄点燃的燃料而已。在孟子以伊尹为例所说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言说中,尽管我们可以从广义的文德教化意义加以诠释,但孟子主要是在“政治教育”意义上来说的,在政治权力影子下的“先知先觉”对于“后知后觉”的关系,无疑就是光明和燃料的关系,这是悖于自由人格的英雄主义主张。平民化自由人格的基础,是广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意见之平等而自由的广泛讨论”。冯契先生特别重视意见的自由争论,强调认识论的充分展开是本体论和真理观的基础,强调自由的百家争鸣是认识论展开的重要乃至本质性环节。
基于此,就相应地拒斥超越的英雄。
拒斥英雄是近代以来哲学革命的一个自觉意识,现代大儒熊十力就明确说要“黜英雄”。就哲学自身的本质而言,它从思自身的展开以获得自身的本质和内容,并不可能以自身之外的任何力量作为自身的依据。孟子尽管突出思,但是,在根底上,他还是带有鲜明的独断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色彩。权威主义意义下的自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即我即天或即天即我的存在者,有点神人结合的色彩,实质上只是少数人“专断”的东西。但是,“自由人格是平民化的,是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人格也体现类的本质和历史的联系,但是首先是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自由的个性就不仅是类的分子,不仅是社会联系中的细胞,而且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间保持着其独立性。‘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我所享受的精神世界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这样,‘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样的自由个性,作为其自身价值世界的“本体”,也就是自身多样性的全面实现,“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不单单是说每个人“天生与人不同”,而且是“后天生成与众不同”,这就要求每个人将自身的个性全面发展出来,“个性不全面发展那就不是自由发展”。如果任何一个人的现实人生都已经被“先定地给予了”,那么,现实之人的无比丰富多样性,还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因为他能将自身造就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者,一个不可入的、不能为抽象普遍的概念简单概括的“自我”。只有允许每个人自身的差异性、多样性如其自身实现出来,自由而真实的“自我”才是可能。
冯契对孟子关于自我的观念有一个基本的论断,他说:“孟子很强调个性尊严,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个‘我’可以成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但他讲性善说,人性来自天命,个人是宇宙的缩影,故一个人由‘尽心’、‘知性’而可以‘知天’。这样讲人性论,注意的还是在于人之异于禽兽的本质,是个人所从属的本质。在儒家那里,个人的具体的存在从属于本质;伦理道德关系是人类的本质,对这种本质的认识才是真理性的认识,这就多少忽视了个人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以尧舜为楷模的英雄主义倾向,还是以天道为僭称的“欺骗式”堙没,孟子哲学中的自我,都很容易沦为虚无之物。在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论看来,就人的存在而论,“个性是人这种精神主体有别于其他物质的东西的本质特征,离开了精神主体,就谈不上自由的个性。在自然界中,个人被看作类的分子、群的细胞,这严格说来都不是个性。自由人的精神才真正是个性的、或要求成为个性的。”因此,拒斥了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英雄,这是孟子儒学的宝贵之处;但是,在文化之思的领域,又陷入文化“圣人观”(文化英雄主义),这又是孟子儒学的可值得警惕之处。因此,需要经过很多转化,才能抵达我们期望的自由个性。
[注释]
责任编辑:郭美星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6)03-0032-09
[收稿日期]2016-01-22
[作者简介]郭美华(1972-),男,四川富顺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儒家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