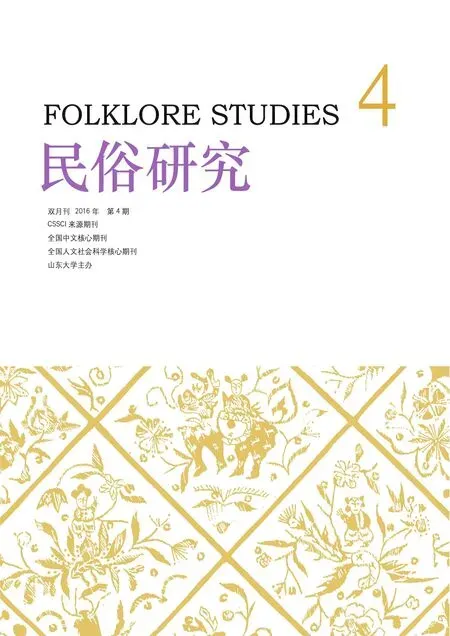“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
——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王杰文
“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
——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王杰文
摘要:21世纪以来,在对民俗学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形成了自反性的共识之后,国际民俗学界倾向于把“遗产化”看作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认为“遗产化”具有相当久远的“传统”。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被广泛推行之后,具有自反性意识的民俗学家更加关注围绕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互动的具体过程,尤其关注“遗产化”过程中可能形成的社会交流模式与增进理解的可能性途径。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遗产化;后现代生活世界;表演;知识格式;公共民俗学
21世纪以来,中国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转向文化遗产研究,“文化遗产”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关“文化遗产”之构成、保护、利用、评估、批评的研究成果成批量地涌现在各类学术性、大众性报刊杂志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直接相关。该公约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道,成为教科文组织为保护世界遗产做出的两项最为重要的决议。
在教科文组织的话语框架中,世界遗产包括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类型。所谓“文化遗产”包括了古迹、建筑群与遗址,而“自然遗产”则包括“自然景观、动物和植物生态区”。与上述两种“物质(material)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intangible)文化遗产”则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表演艺术;c)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手工艺。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2014年,第5页。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上述所谓“遗产”意味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为特定民族所保有的具有历史价值与旅游文化价值的物质文化、景观、纪念物与建筑等;另一方面,它又指一套共享的价值与集体记忆,它是继承而来的习俗与累积起来的共有经验,它被建构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通过特定的语言或者文化表演表达出来的。
然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遗产”,其背后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对某种特定文化财富的“丧失之虞”或者“留恋之情”,正是基于这样两种怀旧的情绪,特定社区、群体与个人从其日常生活实践与习惯性活动中选择出某些内容作为“遗产”并予以特别地推崇与保护,使之“成为”遗产;相应地,与这些受强调的内容相共存的其他日常行为活动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与遗忘了。这一“选择”的过程被民俗学家们称为“遗产化(heritagisation)”。“遗产化”这一概念意味着“遗产”并不是固有的存在,而是一种“发明”。换言之,当社会与政治格局变动时,人们思考自身及其与“过去”的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过去”的某些社会与文化行为及其成果会被看作是本真的、有价值的、值得细心呵护的,而保存它们的理由与方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变革及政权交替之际,针对“遗产”的话语争夺被不同群体用于建构、维护、交流某种特定的“遗产观”。总之,遗产的建构与实践,内在地是一种政治行为。*王杰文:《遗产即政治——关于“文化遗产”的表演性与表演“文化遗产”》,《“作为记忆之场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第125-129页。
然而,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声称,该公约参照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尤其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66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2014年,第3页。
换句话说,教科文组织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要在保护人权,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前提下实施,这是教科文组织的良好意图与指导原则,但是,良好的意图与指导原则毕竟不同于具体的实践。既然“遗产化”的过程涉及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缔约国、缔约国内部的相关权力部门、文化产业机构、相关社区、群体或者个体等,而上述不同主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范围、保护方式、保护目标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围绕“遗产化”的实践就必然地涉及到抵制、协商与妥协等不同的互动形式。基于民俗学学术史研究的成果,民俗学家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倡导的保护性实践(无论它在基本立场与原则上是多么地强调普遍性的价值与世界性的意义),从历史的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都不是新世纪人类的首创性发明。换句话说,“遗产化”的行为很久以来已经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特定社会需要的创造性“再生产”。
一、“遗产化”是一种传统
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遗产”之所以值得保护,完全是因为其审美的、科学的、文化的、人权的普遍价值,而这种普遍价值对于全世界、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可事实上,“遗产”从“文化”中被挑选出来,既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强调普遍价值的时候,有意无意间屏蔽了“遗产化”实践背后历史的与社会的斗争过程。
“遗产化”的问题正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民俗学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民俗学界先后反思并解构了“伪民俗(fakelore)”*Richard M.Dorson, 1976. Folklore and Fakelore: Essays Toward a Discipline of Folk Stud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民俗主义(folklorismus)”*Hermann Bausinger, 1986“.Toward a Critique of Folklorism Criticism”, in J. Dow and H. Lixfield(eds.), German Volkskunde: A Decade of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Debate and Reorientation 1967-1977.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传统(tradition)”*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1983.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本真性(authenticity)”*Regina Bendix,1997,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等概念,这些概念无一不与“遗产化”的实践相关。民俗学家们发现,民俗学学科及其研究对象(民俗或者传统)的形成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发明,民俗学学科、作为象征性文化资本的“民俗”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证明的关系。
人类有意识地珍视某些“文化传统”既是一项与“现代性”相关的历史性创造,又是一种社会性表演。一方面,在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启蒙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近代博物馆的勃兴,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都为一波又一波“遗产”的发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现代性主体意识的强化与对于“传统”的意识的深化是同一历史与社会过程的两个侧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芬兰民俗学家安尼东奥·佩勒蒂强调“要透过现代性理解传统”*Pertti J.Anttonen, 2005, Tradition through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Studia Fennica Folkloristica 15.)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因为“传统”是因现代性而被发明的,相反,现代性也正是通过发明“传统”来建构自身的。另一方面,从“遗产”被发明的历史顺序来看,特定社会之统治阶层的文化传统更可能被优先“选择”出来作为“遗产”予以对待,其所属阶层之审美的、价值的标准也更可能被当作普遍的标准而被采纳。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人类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统治阶层的遗产,一切优先被当作遗产的挑选标准都倾向于自动被当作判定后来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是否可能被作为“遗产”的“普适性标准”。当然,愈到近现代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主体性意识的普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文化元素也被纳入到“遗产”的目录当中。但是,在这一文化进程背后,显然存在着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斗争。总之,意识到“遗产化”实践是一种历史的与社会的发明,意味着一种具有深刻“自反性”的意识已经沉淀在民俗学的理论中了。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民俗学认为,“遗产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它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文化实践”。在这种文化实践中,一方面,它是特定主体(可能是民族国家、社区、群体或者个人)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运用特定的文化资源,选择、重组某些文化元素并称之为“遗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些作为符号与文化资本的“遗产”,这些主体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生产并攫取了政治的、经济的与象征性的文化资本。
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科森布莱特·吉姆布莱特把“遗产化”的过程称为“元文化的运作(metacultural operations)”*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2004, “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Vol.56, Nos.1-2, p.59.。在她看来,尊重、珍视、保存并最终视为“遗产”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元层次(metalevel)”的文化创造过程,即把一种原本是日常生活“惯习(habitus)”的东西从惯常的视角中充分地剥离出来,开始反思性地凝视它,并从中剔取出某些片断,赋予它以特殊的价值。换句话说,“遗产化”的文化实践,乃是一种基于“现在的”需要而创造性地挑选、命名、重组“过去的”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活动。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同的主体,基于当下与未来的不同需要,总是会选择与重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文化元素,并竭力赋予其“真正的遗产”的地位,并试图使这一“真正的遗产”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产生想望的影响。
“遗产化”的文化实践是“后现代生活世界”的普遍行为*Sherry B.Ortner,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Culture,Power,and the Acting Subject,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and London, 2006.,也是一种“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芬兰人类学家居卡·西卡拉教授认为:被“发明的传统”的表演是客体化的、经过反思的,但是它们是艺术作品,在其背后找不到任何东西。正如库克群岛的例子所展示的,文化中只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民族文化的创造与发明,与此同时,其他部分通过其“反表演”的活动对抗着“传统的发明”,民族主义者的发明计划并不能耗尽他们所知的全部资料,当然,人类学也如此。参见王杰文编著:《北欧民间文化研究(1972-2010)》,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或者文化遮蔽*关于“文化遮蔽”的问题,赫兹菲尔德提供了类似的思想,他称之为“文化隐秘(Cultural Intimacy)”,是相对于“文化表演”而言的。所谓“文化隐秘”是指一种仅仅为群体内部所分享的而不愿为局外人知晓的文化传统,因此,它是不会被公开展演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相当于居卡·西卡拉教授所谓“反表演”。然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表演研究者认为,“不表演”本身也是一种“表演”。参见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的行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正是特定社区、群体与个体试图表演或者遮蔽(不表演)其文化传统中某些元素的行为;也是强调(或者遗忘)、重组、整合其文化传统元素以建构后现代生活世界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其日常生活,又以“变异”的形式被纳入与重组到其日常生活当中来。
二、“遗产化”是一种文化实践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教科文组织“所倡导并希望带来的就是一种以人权为基础和旨归的新型文化实践”*户晓辉:《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人权文化——对UNESCO三个文化公约的政治哲学解读》,未刊稿。当然,户晓辉教授所谓“文化实践”的概念与本文中所使用的概念显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与教科文组织倡议某种抽象的“意图”不同,民俗学则描述围绕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主体借助对同一话语资源的不同理解,或者借助不同的话语资源所从事的“遗产化”的具体实践。事实上,即使仅仅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文件文本来看,尽管教科文组织广泛地吸纳了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想观点,但是,从当下具有强烈自反性意识的民俗学学术立场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提供的决议框架在某些概念与思想上仍然落后于,甚至有悖于当下国际民俗学所取得的共识。
二战以来,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公约,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等。但是,在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文化遗产”中,具有考古价值、审美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被优先保护。尽管教科文组织一再声称,这些被优先保护的“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从客观上讲,这些被优先保护起来的“文化遗产”却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富裕国家,而南半球许多国家却没有符合受保护条件的相应的“物质文化遗产”。换句话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受保护的范围之外了。这种不平等现象让人们对教科文组织所声称的“普遍标准”产生了怀疑。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制订草案到正式公布的“难产”过程又一次印证了“南北”之间固有的不平等关系,印证了“南北”之间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难产”过程的描述,可参见Noriko Aikawa-Faure, 2009,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Routledge.pp.13-44.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出现的相关政治语境,即在全球化的环境观念、环境哲学、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主导下流行起来的。而这种观念、哲学与意识形态本身也是西方世界主导的霸权话语,其所谓“危机”意识被伪装成全人类生存的危机。
在既定的不平等话语框架内部寻找保护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的策略,对于非西方的、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意味着要在多个层面上进行“博弈”,比如,如何保护诸如讲故事、音乐、舞蹈表演这样的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性行为?它们可以像保护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被保护吗?民俗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口头传统”的学科,民俗学家们如何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的思想?当特定“口头传统”的存在环境不再存在时,民俗学家们搜集与记录它的工作还可以“保护”它吗?
众所周知,教科文组织最初确实是按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思维着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20世纪80年代初,教科文组织首先想到的是通过法律手段(版权与专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专属于特定的个体,或者甚至无法认定其创造者与传播者。而且,对于没有版权概念的社区与群体而言,运用知识产权法去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不仅显得荒谬可笑,而且是赤裸裸的话语霸权。
当下民俗学把全球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解为一种“文化实践”,首先是揭示了隐藏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话语框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次,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地方性层面的具体实践,民俗学依据其反思性的概念与理论,可以深入地对其中的关键性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质疑。
1.作为关键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82年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1989年,在《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草案》中被正式界定。芬兰民俗学家劳里·航柯直接参与起草了该《草案》。在该《草案》中,“传统文化、民俗”两个概念是“非物质遗产”的“前概念”,甚至是可替换的概念,《草案》暗示了它们之间的互通性。
在宽泛的意义上,民俗等同于传统文化,是群体或者个体以群体为指向、以传统为基础的创造,在社区预期的控制之下,作为对其文化与社会认同的充分的表达;其标准与价值被口头传播,或者以其他方式被模仿。此外,民俗是一个完整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变化与发展的长期状态中是一种活生生的现象。它表征在大众的、民族的、地域的和国家的多种多样的层面上,它经常还是综合性的。传统必须被正确地搜集、保护、储存、档案化、出版、研究与应用,在国家及国际承认的标准手段的指导下予以特殊保护。在一系列人文社会的与科学的规则指导下进行,既要避免忽视、歪曲与滥用现象的发生,又要保护传统携带者的合法权益,满足民俗学家、民俗数据的使用者、档案馆、博物馆与其他研究机构的需要。*Lauri Honko, “UNESCO Work on the Safeguarding of Folklore”,NIF Newsletter:1-2, 1982, pp.3-4.
此后,在《活态人类财富计划》(1994年)《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97-1998)等一系列法案中,“非物质遗产”的概念被连续使用,最后,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被明确予以界定。在本公约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经过多次修正,教科文组织已经从强调保护“传统文化”“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向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Bortolotto, Chiara, “From Objects to Processes: 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ournal of Museum Ethnography. 2007, vol.19.pp:21-33.,强调每个国家、每个社区借助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促进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理想。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史可以看出*依据巴莫曲布嫫的介绍: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概念,随着时间的嬗递,在用词或术语上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参见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第8页。,这一概念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社会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民俗学、人类学学术争论的结果。显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看,1)“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非物质(intangible)”的概念是十分模糊的。虽然教科文组织试图用这一概念来指称一种文化中那些并不具有物质外形的、即时呈现的层面,但实际情况是,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层面,在许多情况下,是很难予以区分的。事实上,所谓“物质”与“非物质”的划分方式本身已经带有西方二元论思想的痕迹,这对于某些非西方国家是以难以理解的、僵硬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科文组织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出发点本是为了弥补之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忽视,可是实际的效果是,它恰恰可能会因为其政策与措施本身所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潜在地深化“南北”之间的文化区隔与不平等。2)“文化”概念的固化。传统的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稳定的功能性单元,它被视为同质性的、时空界限明确的地域范围内的知识总体。但是,这种观念已经遭到上述学科的质疑,它们已经接受了作为一种过程的、互动性的、实践的“文化”概念。在“实践论”的指导下,创造、发明、建构、生产、生成、表演等概念已经内含在“文化”的概念中了。“文化”不再是一个稳定的对象,而是一个由相关行动者借助文化元素进行社会互动的过程,这里充满了动态、矛盾、协商的交互性。然而,这一作为“实践”与“过程”的文化观念与教科文组织所谓“保护”的观念根本相左。尽管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定义中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不断地再创造”的特点,但是,既然要保护它,其倾向仍然是要固化它。3)“遗产”被固定化的危险。尽管教科文组织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存在的复杂性,意识到了其传承性与变异性。但成功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要依赖于该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原创性”与“独一无二性”等。而一旦入选“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面临着被“固定化”的危险,其变异性的内在倾向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文化产品,他还具有相当的能动性。当特定社区、群体与个体在“表演”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他们并不只是文化产品的客体(作为非遗的传承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的能动者。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是“表演性”的,是具有“社会效能”的,它不仅会改变了表演者主体与他们的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也会改变文化生产与复制的基本条件。这种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内部的“绵延性”再生产机制是教科文组织未能详及的。换言之,教科文组织对《公约》本身的“表演性”潜力缺乏必要的反思性意识。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其传承人的身体展示(知识、技术与表演)分不开的,这就意味着“身体”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承是至关重要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保护方式内在地要求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方式不同。所谓“活态的人类财富”便意味着对于传承者之作为传播媒介的“身体”的强调,他(她)们的身体成为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储存器。可问题在于,个体的技艺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社区或者群体的代表?这个只有有限生命期限的血肉之躯怎么可能被永久地保护起来呢?而且,他(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必然地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就意味着,他(她)既是他们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但同时又是“代理人(agent)”。作为代理人,他(她)是一个有意识的、反思性的主体,是具有自身的主观意志、意愿、情感*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仅仅关注其物质性材料,并最终堕落到仅以保护这些物质性材料为目的,就是把“过去”“传统”“遗产”非人化。这种所谓客观或者客观的立场,否定了作为情感主体的表演者或者传承人与前人、观众交流的潜力。仅以“材料”为目标的保护是“变形”的暴力,把“材料”从其社会语境中切除,掏空并改变它,留下的只是却除了情感的事物自身。参见Denis Byrne, “A critique of unfeeling heritag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Routledge. 2009, p.247.与创造性能力的主体,他们的每一项实践都是带着他们自身的观念印记的。在当代民俗学看来,每个个体都是积极的、表演性的主体。个体的身体、身体实践以及展现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存储器”,而且,在具体的表演活动中,这些“作为传统的存储器”的主体使得被存储下来的传统得以活态地传承与传播。*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Studies: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2002, p.22. 理查德·谢克纳认为,特定个体的任何行为永远只能是“二次行为化的行为(twice-behaved behavior)”或者“储存的行为”,那么,在本质上,无论仪式表演还是日常生活,我们都无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习俗与传统,不得不遵循已经建立的模式。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强调语境、意图、传统资料、惯例以及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强调人类行为的“表演”层面,强调主体借助文化资源从事现实实践的过程,强调人类行为的意图与表达的层面。与“表演”相关联的核心词汇,比如“表达”“体验”“阐释”等都是在强调他者对主体表达的体验,强调主体对于他者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个交流互动、循环往复的永恒的过程,这是任何固定化的记录与保存手段所不可能捕捉到的。
2. “民俗”与“非物质遗产”
对照《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草案》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可以发现,“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草案》并没有获得多数国家的认同,而《公约》却获得了161个缔约国的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2014年,序言。。其间的差别何在?显然,从当代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民俗”的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特定“民族群体”或者其中的“社会下层群体”,自然而然地把民俗与乡村、前工业社会以及农业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一术语背后的浪漫主义色彩容易让人们把与它相关的社区想象成一个保有和谐传统的桃花源式的“自然-社会”空间,这里没有社会冲突,没有现代化工业的污染,当然也根本不存在个体的自由与平等等问题。在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民俗”容易被借以去想象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共同体。而且,在强调前工业时期乡土社会形象的同时,“民俗”这一概念还一厢情愿地忽视了现代都市化、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现实,理想化地强调文化被“传承”的一面,而忽视其被“变异”的一面。换句话说,民俗在被浪漫化地想象的同时,也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阻力。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清除民俗传统的过程。
在当下国际民俗学界,民俗之“民”可以是任何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使用“民俗”这一概念时,习惯性地延续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传统含义,即把“民俗”之“民”与“精英”对立起来使用与理解,其背后隐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与沙文主义的思想。事实上,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也隐含了这一被民俗学抛弃的世俗化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教科文组织抛弃“民俗”而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步”显然只是表面性的,因为它之所以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他者”没有相应的意识、能力与资金去保护。在缔约国内部,“民俗”与“非物质遗产”两个概念被或隐或显地等同起来加以运用的情况更为普遍。其中某些社会群体为了强化身份认同,或者为了寻找安全感,甚或只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应用“民俗”。他们常常习惯性地把“民俗”等同于民族国家的、传统的(前工业时期乡土社会的)的文化传统。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社会群体中的精英与民众也可能因为“民俗”而团结起来,尽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但是,当他们面对共同的“他者”时——比如其他民族群体——他们会强调共同的民族风俗,认为这些“民俗”代表了“真正的”民族传统。比如,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德国社会与文化地位的区隔被人们忽略了,德国人——无论穷富——普遍地认为自己区别于其他“非传统的、不纯粹”的德国人。
借用“民俗”以建构社会与文化区隔的行为早就受到了民俗学的严肃批判与反省,因此,具有自反意识的民俗学特别关注民俗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践过程中可能被“固化”的理解与行为,因为特定的文化现象极容易被转化为固化既定社会不平等秩序与社会偏见的工具。同时,民俗学也特别关注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可能从一种阻碍社会进步的元素而被转化为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过程。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保护行为很可能会“火上浇油”(或者“锦上添花”),很可能会保护一些在社会与文化网络中“春风得意”的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相反,其他边缘性的文化现象却可能因为被视为“非传统的、非社区化的、非本真的”而不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可能是妨碍地方社区发展的阻力,而无助于实现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教科文组织意识到了这一点*教科文组织清楚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是因为人类拥有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它可以让相关社区、群体或者是个人以一种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设计他们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关社区、群体认同的源泉,是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全人类多元文化类型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参见Janet Blake, “UNESCO’s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implications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Routledge. 2009, p.49.,它明确地鼓励不同的社区与群体展现其文化中精选的内容与形式,并在一种无争议的基础上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促进特定社区与群体推进自身文化与思想的提升。然而,尽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旨在于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但是,恰恰是那些在多元文化交叉融合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形式却往往又不在受保护的范围之列。比如,那些借用传统元素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的行为方式就不在受保护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其背后仍然明显具有本质主义的民俗观在作怪。
此外,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草案》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的确提升了,然而相关研究者的重要性却被淡化了。包括民俗学家在内的研究们为教科文组织的“民主化”努力欢欣鼓舞,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既然教科文组织强调“保护”,而缔约国也同意去“保护”,那么,在具体实践的层面上,便往往只有那些符合既定条件的社区与群体才会被邀请来参与相关机构所开展的相关活动。试想一下,如果一位书呆子气十足的民俗学家坚持说某个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是一项晚近的“发明”,这对于缔约国及其相关机构,乃至于对它们所认定的相关传承人会是多么扫兴的事!即使这位民俗学家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研究人员,可他还有可能被邀请参与其保护工作吗?
尽管教科文组织也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固定不变的,但是,它的界定工作本质上是鼓励一种稳定化的、具有明确特征的界定,换句话说,这仍然是“本质主义”民俗观的延续。这与自反性民俗学所谓“实践、过程、表演”的观念相对立。换句话说,在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当民俗学已经反思并批判了前工业的、乡村的、传统的、民族国家统一体的“民俗”观念之时,作为实践主体的缔约国及其内部的社区、群体或者个人却还在以一种强化的方式理解并运用这一概念的陈旧含义。
3. “社区”与全球移动
教科文组织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群体”之间的关联,要求缔约国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社区的参与度。然而,“社区”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以界定的概念。民俗学、人类学竭力避免把社区等同于具有明确边界的地理空间,但是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的界定显然倾向于保留这样的理解。一个现实的难题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的群体或者社区并不一一对应,比如,有些文化现象是为许多群体所共享的,或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的。换言之,在经验的层面上,对于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在许多情况下是超越地理空间范围的。但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教科文组织却倾向于支持那些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对于那些超越固定地理空间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倾向于简单地把其中某个被挑选出来的社区命名为“代表”。*特别需要注意“代表”既可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也可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在这种颇为“草率”的命名中,更遑论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了。*基于人权法案的一般规定,一切群体对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身份)享有自主的权利。然而教科文组织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认定“社区与群体”,而不是相反。可是,社区与群体内部很可能是异质性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权利与个体的权利就有可能产生矛盾。
考虑到“全球化与现代化”是教科文组织倡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背景,那么,“社会变迁”的问题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教科文组织如何兼顾“文化多样化”与本土社区的“社会变迁”?在一个全球移动的时代,文化移动、混杂与新传统的流行等问题十分活跃,然而教科文组织却几乎没有顾及。但无论如何,恰恰是这些杂交的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教科文组织强调“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2014年,第5页。问题是,保护“文化多样性”会不会有可能与人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权相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决定文化实践,决定社会规范与公正等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来看,要保护某一特定的文化实践,必得先保护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safeguarding)并不只是防止它的“消亡”,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行为,赋予它连续的生命力,包括创造条件,使它能在某种情境下,连续地被创造、维持与传播。那么,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那些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群体及个人要按照各自守护的社会文化系统去生活吗?他们必须得延续他们的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吗?在全球化时代,当其他人都在享受现代文明创造的成果,谁有权力、有能力仅仅为了“文化的多样性”而要求他们继续保持这些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与经济“语境”?况且,现存的许多文化形式与现代意识上的人权观念并不相符。当社会生产力已经大大地提高之后,单纯地保护某些文化形式,客观上会弱化文化形式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淡化文化形式的社会意义与实际功能。“去语境化”的文化形式被博物馆化了,对于其文化实践者而言,这些传统的文化形式已经不再具有建构身份认同的文化价值与功能了。
换句话说,面对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者与教科文组织之间的看法不同。教科文组织当然可以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提倡并培植一种无争议的、传统的文化形式,并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个理想世界的形象,一个稳定的、统一的社区的形象,可事实上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并在创造着多样化的冲突。显然,这种基于政治立场而决定的文化遗产并不是由相关社区与群体出于最大限度的自主与自决而决定的,它服从于另一套逻辑,即服从于国际政策法案的逻辑,但它可能完全有悖于特定社区与群体的社会逻辑,尽管社区负有传承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4.新媒体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内在地会把保有这一文化遗产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按照本雅明、麦克卢汉与波兹曼等人的观点,现代社会不再是口头传播的时代,而是文字、图像与电子传播的时代。而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恰恰是在保护“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因此,从一开始,这一概念就是沿着乡村与都市、普通人与精英、手工艺与现代化工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原则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界定为上述二元对立中的前者。传统与现代被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二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如前所述,正是现代社会“发明”了对于“传统”的需要,“创造”了身份认同的需求。所谓“传统”“遗产”之本真性与稳定性的特质,完全是通过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媒介化、全球化才得以存在的。没有后者,前者是无法存在的。
与教科文组织强调“地方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正相反,特定缔约国的现代化进程恰恰是与“全球化、流动性、革新以及流行文化的盛行”相关的。现代化进程与构建传统的进程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侧面。教科文组织强调保护口头传承的文化传统,可是,理解现代社会恰恰需要超越口头传统,或者正如波兹曼所说的那样,要深入理解文字、图像以及电子传媒的潜在“意味”。超越教科文组织的话语逻辑可以发现:新兴交流媒介的存在并不只是导致传统的消逝,而且也在积极地激发灵感,刺激多元化传播方式的创新。依赖这些新兴媒介,文化传承的渠道实现了多元化,多媒介技术的共时传播影响了人类的不同感官,并把不同的感官关联起来,共同起作用。现代主体在自主地挑选与利用多种媒介,并已经积极地参与到传播传统的洪流当中来了,新兴的文化传承模式诞生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互联网及相关的数码技术已经极其明显地显示了文化媒介使用的潜力与可能性。
面对新媒介技术的广泛传播与被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主义者”引述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的观点:一方面为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艺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为艺术之“光韵(aura)”的丧失而忧心忡忡。这种恐惧感也流行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声音中。“独一无二性与光韵,这是两个与寻找祖源与根脉密切相关的概念,通过借助时空维度来区分原本与复制品,这些概念被用于去界定文化产品的最重要的价值。”*Walter Leimgruber, “Switzerland and the UNESCO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10, vol.47, No.1/2, p.180.然而吊诡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比附于精英艺术的所谓“独一无二性与光韵”的价值,在口头传统流行的社会中并不重要;在大规模机械复制的时代也不重要。事实上,深入理解新媒介技术在生产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可能性与潜力,对于理解其相应的实践群体与个体的价值观、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在具体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大多是在基于传统的、前现代的、乡土社会的“民俗”概念上被宣传的,许多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被交替运用;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相违背的,尽管教科文组织的本旨是“顺应可持续发展”。正像民俗学的草创阶段,民俗学的先驱者们注意到了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转而关注民俗,倡导人们搜集、记录、保护民俗文化现象一样,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驱们又四处奔走,试图说服人们去保护那些可以抵制全球化进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次不再是依赖民俗博物馆与档案馆,而是依赖数据库与名录。然而,必须提醒的是,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忽视了如下三个重要方面:1)那些处于流动中的文化形式,尤其是那些跨国的杂交性文化形式,因为它们很难被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国家或者群体;2)媒介化传播的流行文化;3)文化中的表演性元素。教科文组织所提供的保护方式倾向于把多元性的文化从其日常生活中“去语境化”,并被进一步美化与提纯,其本属群体中大多数参与者反而被国际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给边缘化了。伴随着这一现象的是新一轮“民俗主义”的流行。缔约国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挑选了他们想要的文化元素加以强调,那些有违其意图的文化实践被认为是不值得保护的,进而遭到历史的汰洗。遗产的政治正是通过强调国内亚群体之间前政治的文化纽带,削弱民族国家及其公民之间的关联,转而强调并塑造新兴的与全球政策相关的全球公民的形象。至于它是否能够成功,这可能要因具体缔约国的性质、意图、推动的力度来决定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强调对文化多元性开放与包容;一方面给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及群体以一种传统与稳定的形象,另一方面给外来旅游人士以一种作为娱乐的文化消费品的形象。然而,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传统”都不会被当作是参与身份建构、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的参与性平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两个后果是:一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他的源出地之间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关系,一旦被“遗产化”,这种文化传统便会与源出地之间丧失关联,这些被“遗产化”的文化现象对于源出地而言就变成了“他者”,具有了自身的生命,一种“本真的传统”的幻觉在源出地被创造出来了。*Ahmed Skounti, “The authentic illusion:Humanit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Moroccan experience”,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Routledge. 2009, p.77.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员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文化产业的强大推动下,被“遗产化”之后的文化现象有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被迅速复制。教科文组织所引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猎奇心严重的旅游大众的热点景观,对于相应社区、群体与个体的生活方式却少有关联,也许唯一的关联是这些相应的社区、群体与个体必将成为热点景观的一部分,他们因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与表演者而重构了自身的身份,重塑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结构与意义。
三、后“遗产化”时代的民俗学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被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当代民俗学关心的是人们在赋予“遗产”以新价值的过程中,围绕着这些“新价值”的正反争论是什么,是由谁在何种语境下肯定或者反对“新价值”观念的,与这一“遗产化”过程相关的所有利益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图景是什么样的。在全球化大移民以及互联网全覆盖的时代,等到“遗产化”的热潮退去之后,民俗学家从中学到了什么?换句话说,当“遗产化”的行为已经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方式时,当下民俗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应该做出何种调整呢?的确,“非遗保护的所有这些实践特点都为民俗学反思自己的学术出发点和学科性质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页。
如上所述,当代国际民俗学的理论前提是“文化实践论”,是把“遗产化”作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与文化实践处理的。具有反思意识的民俗学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相关条款如何已经成为相关利益群体挪用与批判的话语资源,如何把非物质遗产物质化,并运用“最小投入与最大收益”的逻辑,排他性地参与竞争,实践社会、经济与文化资本的最大利益化。在这一“文化实践”过程中,基于竞争的逻辑而引发的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已经引起民俗学、人类学的严肃批判,然而,民俗学并不仅仅满足于“批判”,他们还发现,“遗产化”的过程同时也打开了新的机遇,比如它完全有可能促进相关社区的环境改善,促进其能源开发与旅游业的发展,实现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革新。超越于这一经验表象之外的实践意义甚至可能是:“非遗保护不仅是一种地缘、身份和权力的实然政治,更是一种以民主参与的公民社会为旨归和游戏规则的应然政治”。*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20页。
在这一理解中,《公约》
“不是为了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做经验的认识和归纳,也不是单纯为了对它们进行登记、注册或保护,而是为了从实践原则和自由意志出发来展开并创造新的实践(包括新框架、新伦理、新思维和新举措)。《公约》本身就是实践原则、伦理律令(ethical imperative)或自由意志的内在目的,而世界各地保护非遗的活动则是在《公约》的实践原则指导下对自由意志的贯彻或实现。也就是说,非遗保护不是对既有的东西进行经验性归纳和认识,而是要按照《公约》规定的实践原则和自由意志从无到有地开辟崭新的实践……”*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页。
注意到教科文组旨在用确保社区、群体或个人的权益和参与为核心的实践原则以及以国际人权文书为前提的自由意志,又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呼吁缔约国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国际协作的框架内,来激发相关社区、群体与个人积极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意义在于把保护工作的措施与责任转让给社区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要保存在档案馆或者民族博物馆里,而是要保存在社区中,其成员要实践与展示其形式。如果传统仍然在社区中鲜活、重要并可以持续下去,这就是保护了。参见: R.Kur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factors in implementing the 2003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2007, vol.2: pp.12-13.,还注意到教科文组织相关申报与评审机制的相对公平性,这使得特定文化社区与群体中的某些部分,因为其具有特殊的价值,从而有可能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反过来,正是因为这些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财富符合教科文组织权威机构的某些评价标准而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相关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珍惜相关称号,就像成熟的商业公司重视自身的品牌一样;如果“遗产化”可以带动配套的旅游服务业,并出于珍惜自己声誉的愿望,能够带动普遍的竞争与质量把控机制,那么,“遗产化”机制就会为地方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机遇,一种基于质量把控与审计的自我管理型文化理念就会广泛地渗透进日常生活。在某些乐观的民俗学家看来,“遗产化”正是这样一个领域。*Regina Bendix, “Heritage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An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Routledge. 2009, p.264.
在促进非遗参与竞争时,那些社区、群体与个体已经预先接受了竞争机制与可能的结果;非遗项目的筛选过程又是相对透明的;相关社区、群体与个人可以比较清晰地把那些具有自由价值的文化财富转化为具有特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家可以由此分析出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要素,从而理解特定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官员则要基于教科文组提供的框架,赋予相关社区、群体或者个人以相应的尊重与权利。换言之,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围绕着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保护框架,各缔约国及其相关机构、专家学者、政治官员、文化产业管理人员以及地区、群体或者个人,都面对着一个重塑身份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一“遗产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文化实践”的过程,而这一“文化实践”的过程又蕴含着“民主化”的种子,它为多种社会力量重塑角色与形象提供了平台,也提出了要求*户晓辉:《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人权文化——对UNESCO三个文化公约的政治哲学解读》,未刊稿。。比如,缔约国在承诺《公约》的相关条款时,它就把自身置于一个国际化的舞台,需要自觉接受全球社会对于其本土人权、经济与社会发展权及文化权利的处理方式的监督。
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在人类的心中树立和平的信念,而教育、社会与自然科学,文化与交流活动只不过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途径。那么,民俗学在研究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的精神及相关实践时,关注该公约如何影响了缔约国、社区、群体与个体,如何影响了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因此而建构起了新的意义之网,这都是民俗学经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人们可以同时看到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权力斗争以及道德教化,可以看到对于相关实践的形形色色的批评与攻击。毕竟“遗产化”的实践是后现代社会存在秩序的一个剪影,它是当代社会人类运用碎片化的文化资源谋取经济及社会利益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准确理解与阐释“遗产化”的政治及其复杂的利益冲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揭示同一过程中的竞争性与评估性机制也许更为重要,因为教科文组织借助《公约》赋予地方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以相应的权利与责任,肯定了相关责任主体的能动性,明确了相关责任主体理论上应该明确的角色与权利,这些相关约定赋予这一新时代的“遗产化”文化实践以更多可能性与机遇。
总之,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实践中,一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着现存的权力模式;另一方面,《公约》所倡导的“遗产化”框架又携带着某种机遇与可能性。超越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之外可以看到,整个后现代生活世界充斥着“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如前所述,既然一切“文化实践”或者“(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表演”都不可能不是挪用“传统”的行为,那么,“未来民俗学”*在中国,“未来民俗学”这一概念由户晓辉提出。但是,以户晓辉、吕微、高丙中为代表的中国民俗学家更常用的概念是“实践民俗学”。户晓辉甚至主张,“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唯一的康庄大道”。除了扮演批判者的角色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
在国际民俗学界,德国民俗学在历史上的沉痛教训使得整个德语区的民俗学家们痛定思痛之余,竭力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不再直接参与社会与文化实践,而是洁身自好,做一名社会与文化的批评者。这就是德语区民俗学家们的学术定位*王杰文:《超越“日常生活的启蒙”——关于“经验文化研究”的理解与批评》,《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第9-20页。。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定位会使得整个学科被边缘化,比如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中,民俗学家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学术术语被滥用,却除了“批判”之外无所作为*Hermann Bausinger, “Disengagement by Engagement:Volkskunde in the Period of Change”.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1999, vol.36.Nos.2/3,p.147.。尽管德国民俗学家恪守着“不介入”的学术伦理,但是,面对“民俗主义”的经验性现象,德国民俗学家同样积极反思了民俗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问题,他们同样对民俗学自我再生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比如德国民俗学家沃尔夫冈·卡舒巴明确地提出了“知识格式(knowledge formats)”的概念,他发现
“表征类型与知识格式(knowledge formats)——即传播的媒介——是由目标观众的可观察的预期指导的,是由知识场所(knowledge venues)(诸如博物馆、公开演讲或者大学的研讨会)形成的。“知识格式”反映了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规则;它们存在于物质文化的多种审美形式之中。作为科学的基本工具,知识格式结合了知识生产、表征与传播的不同实践,比如界定、搜集、排列、阐释与表征。其形式、物质、审美文化、内容、表演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知识格式反映了作为实践的思维方式、权力关系、文化规则与理想。”*Michaela Fenske, Antonia Davidovic-Walther, “Exploring Ethnological Knowledges”,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10, vol.47, Nos,1/2, p.2.
显然,“知识格式”的概念体现了以为卡舒巴为代表的当代德国民俗学对于民俗学“表征”行为的高度自觉。
与德国民俗学家“通过不介入而介入”,且明确自我界定为“启蒙者”的民俗学立场不同,美国公共民俗学家主张积极地参与传播民俗,他们直接参与文化表征与文化经营的工作,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民俗的“实践者”。但是,他们同样关注“表征”的问题。在面对“文化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的伦理困境时,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表征”的有效形式与媒介,目前,“文化自我呈现的乡土模式(vernacular modes of cultural self-presentation)”*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Folklorists in Public:Reflections on Cultural Brok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2000, vol. 37, No.1, p.8.受到了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青睐。因为他们发现本土人已经不再停留在展示那些过时的民俗文化的层面了,相反,他们已经把“文化作为自身的生活方式本身”,这种乡土模式的文化表演与民俗学家传播专业知识的意旨殊途同归。
日本民俗学家同样意识到了“遗产化”的普遍性,认为“今天的民俗学将要为此承担起重大的任务和自己的责任”*才津裕美子:《民俗“文化遗产化”的理念及其实践——2003年至2005年日本民俗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综述》,西村真志叶译,《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27页。。深受美国公共民俗学影响的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提出了“新的在野之学”*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明确承认,“研究者的建构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不如带着一种自觉的意识去理解这样的建构过程,应当对作为一个民俗学者所采取的行动作出选择。”“建立新的公共民俗学,可以说是现在的民俗学者的使命。”。参见菅丰:《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道路”——文化保护下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陈志勤译,《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第68页。的概念,他不再把学问当成职业研究者的工作,不再只是通过共同的研究、实践以及应用以加深对地方的理解,不再把民俗学仅仅定位为发现地方的问题从而进行解决的知性活动,而是强调1)应用性与实践性,以“有用”作为目标,并在社会上接受评价;2)摆脱学问的领域,走出学术界的小圈子,充分地参与社会活动并贡献自身的睿智;3)摆脱立场与属性,与来自不同群体、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士合作;4)共同协作,即与不同的行为者基于平等协作的理念共同“治理”;5)在地方性的当下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感同身受的问题,选择采用基于现场的方法予以归纳与理解;6)不断反思这一合作过程中所应用的知识与行为,以维系后续的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菅丰(Yutaka SUGA):《面向“新的在野之学”的时代——日本民俗学的一种选择》”,2013年5月30日北京“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报告会”主题发言。转引自王杰文,《“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关于民俗学“元理论”的思考》,《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第14页。这里,民俗学者作为生活文化的专家参与其中,成为沟通地域社会内外的中介与桥梁。
区别于德、美、日民俗学家对于“未来民俗学”取向的定位方式,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以高丙中、吕微、户晓辉为代表——首先意识到美国(包括深受美国公共民俗学影响的日本民俗学)
“公共民俗学实践之所以能够开展协商、妥协等一系列民主操作细节,恰恰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民主大前提和公民社会的自由意志,因为他们已经凭借这种自由意志建立了fairplay(公平游戏)的游戏规则。美国公共民俗学恰恰昭示出民俗学的实践前提在于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从公民社会的精神出发来进行民俗实践和民俗学的实践”。*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27页。
在意识到美国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大前提”之后,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主要借助于哲学以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的理论资源。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实践民俗学”的(唯一)合理性、合法性。认为“民俗学本来就是实践民俗学”,也就是说,
“实践民俗学的根本在于完全放弃实证科学的客观认识范式及其对理论与应用的划分,完全从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来看待民众的民俗实践并以此进行民俗学自身的一切实践”*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第28页。。
吕微总结道,
通过对主体实践(民俗)的经验现象的先验条件的演绎还原,推论(生产)出并(现象学地)直观到实践主体(俗民)自身作为自由主体纯粹观念的先验目的,并以此民俗学的实践范式(方式)所提供的纯粹观念,用作民俗学的社会实践。以此,民俗学者才能够有把握地断言:我们学者“加给”“放进”老百姓心中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学者从老百姓的心中“看出”“找出”“取出”“学到”并“受教”于他们的东西。*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79页。
的确,有谁会否认“实践民俗学家”有关普遍主义价值论的主张呢?然而,又有谁会认为这一作为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之学术伦理与学术宗旨的主张可以代替民俗学呢?与德、美、日的民俗学家比较起来,非常明显,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把太多的精力聚焦于论证与还原民俗学的终极目的、哲学根源以及这一哲学根源所包含的潜在意义上。这一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中国特色,显然是由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语境造成的。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欣喜地看到当下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重新赋予长期被贬低的文化以积极的价值”,高丙中说,
“在中国实在正在造成社会变化的奇迹。分析奇迹发生的原因,当然首先要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应该是它所代表的新的文化话语包含着化腐朽为神奇的思想力量”。*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第150页。
显然,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而言,认识到并着手去解析、背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是十分睿智与重要的,它对于盲目套用欧美民俗学理论并妄图解释与解决中国民众生活问题的经验研究是一种强有力的拨乱反正。然而,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又有意无意间贬低了经验研究,并试图以民俗学的学术伦理取代民俗学的具体研究,这种明显的霸权话语又是十分偏激的。事实上,德、美、日民俗学同行们的研究成果证明:
第一,当下国际民俗学界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民众与民俗学者同时作为实践主体的身份,都相当自觉地注意到了作为实践主体的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
第二,这些普遍的意识与理念已经具体化为国际民俗学的学科伦理,成为一切国际民俗学者普遍遵守与践行的职业伦理。
第三,在遵守学科伦理的前提下,国际民俗学家仍然延续并坚守民俗学作为一门经验研究学科的定位,努力探索着民俗研究的新方法。比如,德国民俗学家坚守作为“启蒙者”的立场;芬兰民俗学家主张“批评者”的立场;而美国与日本公共民俗学家探索“实践者”的立场。等等。
第四,除非中国的“实践民俗学”能够提供质疑、批判、超越前述国际民俗学家经验研究的思想与实践,否则,中国民俗学没有轻易放弃经验研究传统的理由。
总之,意识到“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生活世界的日常行为,意识到民俗学者的研究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表征”的行为,意识到民俗学研究的模式与过程对于民俗知识及其主体的“建构”作用及其实际影响,以德、美、日民俗学家为代表的国际民俗学已经在为民俗学重新定位。无论民俗学家主观的愿望如何,民俗学“介入”现代社会并会产生实际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换句话说,民俗学研究的是“文化实践”,民俗学自身也是“文化实践”,那么,作为文化实践者,民俗学家如何为实现美好社会愿景做出某种努力就不能不是“未来民俗学”思考的内容了。中国的“实践民俗学家”已经为未来民俗学奠定了良好的哲学基础,但是,中国民俗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辨与思想倡导的层面上,中国民俗学还应该广泛借鉴国际民俗学已有的探索成果,在坚持经验研究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实践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国民俗学具体的实践策略。
[责任编辑刘宗迪]
作者简介: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