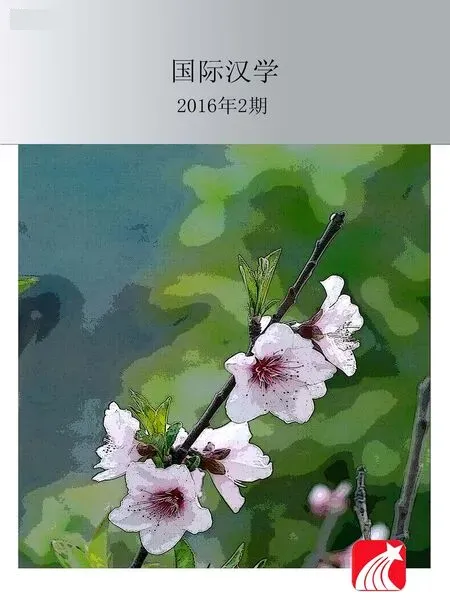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民国学界对国外汉学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中国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关注国外汉学。于是,在学界兴起了国外汉学研究的热潮,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对于中国学界的国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总结。①如韦磊的《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关于美国的中国研究之译介》(《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吴原元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2期),朱政惠的《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等。国内学者的这些总结,均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对于1949年之前,中国学界的国外汉学研究总结不够。虽然有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外汉学研究有所涉及②如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孝迁的《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但是,这些论著均存在着遗漏一些中国学界的重要成果或对有关成果定位不准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的国外汉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补充。
一、翻译了一批国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著
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研究首先是继续进行基础性的译介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19世纪下半叶业已开始。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开展起来的。1868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这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万国公报》自创刊至停刊期间不仅刊载了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花之安 (Ernst Faber,1839—1899)、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谢卫楼(Davelle Z. Sheffield,1841—1913)、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传教士的中国研究的论著,而且还翻译了上述有关传教士的中国研究成果,如:《中美关系略论》《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等。其中,《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是国内较早翻译的介绍西方论述中国语言文字的论文。③古吴居士笔述:《西士论中国语言文字》,《万国公报》1892年第52期。这些西方传教士撰写的中国研究的论著在中国得以发表或翻译,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而且对于国人认识国外中国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进入20世纪,随着国外中国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汉学逐步进入国人视野。为了解国外中国研究状况,吸取其中有益成分,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外的汉学研究进行大量译介,翻译了一批研究国外汉学的成果。1911年,潘树声、叶诚翻译美国《世界杂志》刊载的《美人吉包尔奈之中国观》一文,同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8卷第3期。该文虽然是翻译美国杂志刊载的美国人对于中国近十年间所面临的政治形势的认识。但是,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有关内容给予了评论。这就使该文超越了纯粹的翻译意义。①如在翻译到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时,译者以英国泰晤士报和列强的实际行动相互印证,强调了形势的危急。在翻译到革命前途时,译者对作者的革命难以成功的一大障碍是中国当时的立宪思潮的观点予以赞同,同时,译者也指出:“然若敷衍粉饰,则恐未足以然若敷衍粉饰,则恐未足以饜民望耳。”参见潘树声、叶诚:《美人吉包尔奈之中国观》,《东方》1911年第8卷第3期1917年,《新青年》第3卷第3期发表了署名J. H. C.生翻译的桑原骘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②该文于1947年由方今兹翻译在《中国青年》(南京)第9期附刊中以《中国学研究者的任务》为名再次发表。1921年《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了张其昀译的《美国人之东方史观》(“Why Study Far Eastern History---and How?”)一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对国外汉学研究论著的翻译开始进入高潮阶段。首先,中国学界开始了对国别汉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在早期的国外中国研究史上,法国是处于前列的。因此,中国学界首先翻译了有关法国汉学史研究的成果。1929年11月《新月》发表了署名为幼椿(即李璜—笔者注)翻译的法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的《法国支那学小史》。这篇译文不仅是国内学界翻译的较早的国外汉学史研究成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国外汉学研究的观点。这主要体现在李璜加写的引言部分。③沙畹著,幼椿译:《法国支那学小史》,《新月》1929年第二卷第九号。该文与李璜其他相关的法国中国学研究译文和研究论文于1933年一起集合于《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对法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外,中国学者还对德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1933年《新中华杂志》发表了王光祈翻译的德国海尼士(Haenisch,1880—1966)对于德国中国研究的总结论文。在文中,海尼士介绍了德国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政治、地理、民风、美术、宗教的研究状况,同时海尼士总结了德国中国研究的方法经验。此外,海尼士还回顾了汉学作为学科在德国的沿革。该文对于国人认识德国的中国研究具有导引意义,使国人基本上可以了解和认识德国的中国研究历史及其基本人物和著作。关于研究德国的中国研究的成果,还有1937年《史学消息》发表的梁学华翻译的石田干之助的《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德国方面》,该文主要是以德国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为线索展开介绍的。④石田干之助著,梁学华译:《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德国方面(二)》,《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7期,该文并未完成,后面部分也未见翻译发表。
其次,翻译了石田干之助的相关论著。除了前述梁学华翻译的《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德国方面》之外,还有朱滋萃翻译的《欧人之汉学研究》,⑤该文分别在《中法大学月刊》1933—1934年连载。北平中法大学于1934年12月出版了朱滋萃译的《欧人之汉学研究》单行本。汪馥泉翻译的《中国研究在欧美》。⑥载《学术》1940年第1期。《欧人之汉学研究》主要分析了近代之前欧洲关于中国的研究。该书共分为七个部分:一、绪论;二、古代和中世纪初期关于中国的知识;三、中世纪后期阿拉伯人的中国知识;四、蒙古人勃兴时代关于中国的知识;五、第14、15世纪(从元至明初)欧西底中国知识;六、东印度航路底发现和欧人东航: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和汉学底成立;七、附录。该书重点研究了新航路开辟后诞生的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在这一部分里,石田围绕人物及其著作,较为系统完整地描述了传教士中国研究的学术传承。他将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分为三个时期:明清鼎革时代到康熙初期;康熙中期以后,到雍正末年时代;乾隆时代。在上述三个时期里,石田重点介绍了曼特刹(Juan Gonzales de Mendoza,今译门多萨,1545—1618)、鲁德照(Alvare de Semedo,今译曾德昭, 1585—1658)、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哈尔特(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冯秉正(Joseph Anne-Marie de Mailla, 1669—1748)等人的经历,及其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和观点等。最后,石田专门重点介绍了法国的兰米刹(Jean-Pierre Abel-Rémusat,今译雷慕沙, 1788—1832)和德国的克拉泊洛脱(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的生平和著作及其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等。①石田干之助著,朱滋翠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京:北平中法大学出版,1934年,第144—269页。不仅如此,石田在分析有关人物时还介绍了相关著作的主要内容,而且石田还分析了近代欧美研究中国的缘由,梳理了汉学在欧洲的发生和发展。因此,这一部分不仅对于当时国人认识国外汉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今日研究传教士汉学的学者也具有提供线索的意义。该书的附录部分是由译者编译的由岩井大慧编写的“研究东洋史者必读的欧西书”一文。该文长达77页,汇集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以及日本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其中包括了多部欧洲和日本汉学研究的书目,同时,该书目还附有对相关书籍作者的简单介绍。该书目对于了解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中国研究在欧美》一文主要分析了近代之后欧美的中国研究。该文分析思路基本与《欧人之汉学研究》相同,共分五个部分:绪言、加特力传教师的中国研究、欧洲学者的中国研究、从19世纪初到最近的欧美的中国学、欧美的中国学的现状。该文的前四部分基本上与《欧人之汉学研究》的第六部分相同,是后者的简编部分。《中国研究在欧美》的第四、五部分主要分析了19世纪以后的欧美中国研究。其中,在第四部分中,石田分国别以中国研究专家为中心介绍了法国、英国、德国、荷兰、俄国的中国研究情况。在第五部分中,石田继续分国别介绍欧美国家的中国学。其中关于法国部分,石田重点介绍了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以及中国研究的机构—东方语学校、设在越南河内的远东法兰西学院、设在中国上海徐家汇的耶稣会江南传道部、河北献县的旧直隶东南传道部;关于德国部分,石田重点介绍了柏林大学、莱比锡等地的中国研究;关于英国,石田重点介绍了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研究,以及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伦敦的东方语学校、设于上海的皇家亚细亚学会的华北分会;此外,石田还简单介绍了荷兰、瑞典、挪威、丹麦、波兰等国的中国研究。最后,石田介绍了美国的中国研究。关于美国的研究,石田认为,虽然其中国研究资历较浅,但经过积累,加上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其前途颇值得注意”。②石田干之助著,汪馥泉译:《中国研究在欧美》,《学术》1940年第1期。这里,可以看出石田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洞察力是比较强的。此外,石田还介绍了美国的庐公明(Justin Doolittle,1824—1880)等人,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高校的中国研究和国会图书馆等图书馆的中国研究资料。③1949年,中国学者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一书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观点和论述框架等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石田干之助的相关研究成果,莫东寅的独创研究很少。
二、搜集、整理国外汉学的资料和信息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不仅翻译了一批国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论著,而且非常重视国外汉学资料和信息的整理工作。在这方面燕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史学消息》等期刊着力较多。就搜集、整理的资料和信息内容看,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基本上涉及了国外汉学研究的所有内容。
(一)关于国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的资料搜集和整理
中国学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国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的资料、信息的搜集和整理。第一,翻译国外有关学者整理和搜集的资料,这也是当时中国学界获取国外专家、学者资料的主要渠道。《史学消息》自1936年创刊后,基本上每期都刊发国内学者翻译的国外汉学专家的资料。而且介绍国外汉学专家,也是这份刊物创办时就定下的计划。“关于史学界人物的介绍,本刊预算逐期介绍各国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分别介绍日本‘支那学’学者,欧美的汉学家,俄国的汉学家等。”①《编后》,《史学消息》1936年第1卷第1期。自1936年创刊至1937年,《史学消息》共计出版8期,基本上都刊载了国外中国研究专家、学者的资料译文。主要有:1936年第1卷第1期刘选民译的《俄国汉学家帕雷狄阿斯之生平及著作概略》;②原文载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 Vol. XI, 1929, No.4, pp.173-177.1936年第1卷第3期刘选民译的《俄国汉学家华西里夫之生平及其著作概略》;③原文载Ibid., Vol. XII, 1930, No. 1, pp.15-20.1937年第1卷第4期罗秀贞译的《俄国汉学家伯西聂德之生平及著作概略》;④原文载Ibid., Vol. XIII, 1930, No. 5, pp.246-250.1937年第1卷第5期汤瑞琳译的《俄国汉学家雅撒特之生平及著作概略》;⑤原文载Ibid., Vol. XIII, 1930, No. 6, pp.325-331.1937年第1卷第7期黄培永译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之生平及著作概略》。⑥原文载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 1931, No. 1.第二,中国学者搜集、整理的国外汉学专家学者的资料。《史学消息》在1936年第1卷第2期和1937年第1卷第6期刊载了冯家昇整理的《现代日本东洋史家的介绍》。在文中,冯家昇介绍了那珂通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等人的生平、中国研究的经历,以及他们的主要成果等。第三,报道国外中国研究者的活动动态。民国时期,不少杂志都积极报道国外中国研究专家的活动、消息。特别是有关重要的中国研究专家逝世,中国杂志都给予及时报道。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五号报道了苏联、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以及日本的桑原骘藏等人逝世的消息。《时事旬报》于1934年第10期、1935年第25期分别报道了英国中国研究专家白鲁士(Joseph Percy Bruce,1861—1934,即卜道成—笔者注)和迦尔斯(Herbertty A. Giles,1845—1935,即翟理斯—笔者注)逝世的消息。《现代周刊》1945年1卷创刊号发布了伯希和逝世的消息。在报道国外中国研究专家逝世的同时,这些报道往往都附有对对象生平的简单介绍。
(二)关于国外中国研究机构的资料整理和介绍
民国时期,国外中国研究已经进入科学研究阶段。相应地,在有关国家均有相关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也成为民国学界关注的对象,进而对这些机构的设立、结构、研究工作等也进行了资料的整理。1928年,《东方杂志》刊载了《德国之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中国学社—之情况》一文,详细介绍了德国成立的中国学社的目的、工作内容、工作活动的形式,以及入社的手续、社员权利和义务等。⑦颂华:《德国之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中国学社—之情况》,《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8号。1932年,《中国新书月报》刊载了《日本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一文。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东洋协会等机构的设立、内部机构设置、主办的刊物等情况,简单介绍了东亚同文会、东洋文化学会、中日文化协会、东亚经济研究会、东亚研究会、支那时报社、支那事情研究社、汉学会、支那文学会、东洋史讲话会、支那学会、东亚事情研究会、支那协会、斯文会、怀德堂、东京王学会等十九家机构。⑧《日本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9—10期。1937年,《史学消息》刊载了刘选民整理的《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该文“介绍日人研究‘东洋学’的主要机关,略述其严格,组织,和事业”。该文将日本中国研究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法人财团机构,该文详细介绍的主要有:东方文化学院、东洋文库、东洋协会、东亚经济调查局,简单介绍的有:东亚考古学会、考古学会、大山史前学研究所、东亚研究会、东亚同文舍等。第二类,日本大学内设立的中国研究机构:九州帝国大学支那学研究会、东京帝国大学东京人类学研究会、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谈话会、东京帝国东洋史同好会、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学社、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谈话会、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学会、东北帝国大学支那学会、早稻田大学东亚学会、早稻田大学东洋史学会、大谷大学东洋史学会、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东亚经济研究会、大阪外国语学校东洋学会、大阪外国语学校支那研究会、庆应大学东亚事情研究会、大仓高等商业学校东亚事情研究会等。第三类,专攻“满蒙学”的机构:日满文化协会、满洲学会、青丘学会等。①刘选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机关》,史学消息1937年第1卷第4期。1948年,《亚洲世纪月刊》刊载了其资料室整理的《日本研究中国的团体》一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研究会、有邻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专科以上学校的中国研究会等机构的设立、机构设置、人员组成、研究活动的形式、主要研究成果等。②本刊资料室:《日本研究中国的团体》,《亚洲世纪月刊》1948年第3卷第2、3期。
(三)介绍国外中国研究论著,编写论著目录
民国时期,学界不仅开始大量翻译国外中国研究的成果,而且开始较大规模地介绍国外最新中国研究的成果,并开始编写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目录。当时一些图书馆主办的期刊在就大量介绍国外中国研究书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在每一期的新书介绍与批评一栏中均有海外中国研究论著的介绍。《史学消息》每一期则对国外中国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专门进行介绍。其中,在1936年第1卷第1期、第2期、第3期连续刊载了《日本‘支那学’论文提要》、1937年第1卷第4期、第5期、第6期《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1936年第1卷第1期、第2期、第3期和1937年第1卷第4期、第5期、第6期、第7期连续刊载了《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在上述介绍中,包括了相关欧美国家中国研究的期刊介绍和主要论文内容的简介,其介绍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即及时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主要杂志刊载的主要论文。在书报评介一栏中,每期均介绍国外最新出版的中国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1936年第1卷第2期中,刊载了刘选民编译的《现代苏联邦的东方学文献》,文章主要介绍了苏联中国研究的相关论著的主要内容。1936年《文化批判》刊载了署名健一的《日本著作界研究中国问题之活跃》一文。该文介绍了的《中国农业经济的各问题》(田中忠夫)、《中国的农业恐慌与农民状态》《中国经济读本》《1935年中国经济年报》《中国农业经济论》《中国的农业与工业》等著作的内容。1940年,《图书季刊》专门开辟专栏介绍西方中国研究著作。③《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4期。
除了编辑国外中国研究最新论著的内容介绍外,民国学界还开始编辑国外中国研究的论著目录。首先是翻译国外学者编辑的目录。《史学消息》在1937年第1卷第6期中刊发了藤枝晃著,刘西明编译的《东洋史“学界展望”与“论文目录”一览》一文。该文分类编辑了日本中国研究的主要论著。《史学消息》于1937年第1卷第4、5、6、7期连载了该刊编译的青木富太郎辑的《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分为:通史、时代史、地理、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等项。除编译外,中国学界还开始自主编辑国外中国研究目录。1936年,《史学消息》在第1卷第1、3期就编发了《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该目录的主要内容是欧美方面的中国研究书目,其特点是以外文形式编辑目录。《华商学志》也在1945年第10期刊载了裴化行(Henri Bernard)编写的《欧洲著作的中文编译—葡萄牙人来华及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的编年书目》。
(四)追踪和报道国外汉学动态
民国学界对于国外汉学信息的关注还表现在对国外汉学动态的追踪和报道方面。除了前述1928年《东方杂志》对于德国的中国学社活动的追踪和报道外,④该文介绍了当年中国学社在德国举办的中国书籍展览会的情况,以及之前学社发布的促进德国注意研究中国的通告等。(颂华:《德国之中国文化研究机关—中国学社—之情况》,《东方杂志》1928年第25卷第8号)。20世纪30年代学界对国外汉学动态的追踪更显积极。其一,是对日本中国研究的及时追踪。1943年,《学思》刊载了《日本最近研究中国学的动向》一文。该文首先介绍了日本中国研究机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京都两研究所的分裂,以及两个研究机构本身结构方面和研究人员、研究内容方面的基本情况。此外,该文还报道了研究人员宇佐美诚次郎和牧野巽的研究选题等。其二,欧美的中国研究动态。1929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刊载了《美国大学的东亚课程》一文。本文虽属新书介绍性质,但是在介绍该书时,实际上报道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动态:“本书是太平洋讨论会美国支那部于1928年调查美国高等学校所授中国日本各课程的报告。按照本书,美国一年前有一百一十所学校开东方课程的班,大体注重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至于纯粹东方学在美国尚少研究之机会。按美国学者近来颇欲研究中国之国学,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已再三讨论此事,大约一二年后当有确实办法云。”①《美国大学的东亚课程》,《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1929年第3卷第4号。1940年,《图书季刊》集中报道了美国等国家的中国研究情况。在《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近况》一文中,介绍了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授课、研究、研究资料的收藏情况等。不仅如此,同期还报道了法国河内远东学院的机构性质、研究范围,关于中国研究的资料、研究人员和成果等。此外,还有关于捷克的布拉格东方学院的中国研究课程、研究人员和成果的详细介绍。②《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近况》《河内远东学院工作近况》《捷克东方学院工作近况》,《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4期。在同期中,还专门报道了哈佛大学远东语文学部、哥伦比亚大学中日语文学系、夏威夷大学东方学院等三个机构的教学、资料收藏、研究成果等情况。1948年,《读书通讯》报道了美国设立研究远东问题的亚洲学院的情况。其三,苏联的中国研究动态。1925年,《东方杂志》介绍了苏联关于中国研究的情况,以及《世界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等七部专著的主要内容,并重点介绍了《中国与苏联》一书。③齐水:《苏俄的中国研究与东方杂志(赤塔通信)》,《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7号。1935年,时事类编第3卷第8期介绍了苏联的远东科学研究工作情况。1943年,《中苏文化》报道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进行的中国研究的情况。同年,《图书季刊》在新第4卷第3—4期介绍了《苏联东方学》杂志刊载的最新论文的主要内容。
三、学界权威关注和重视国外汉学及其研究
民国时期,国外汉学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学术大师更是率先关注和重视。这又进一步推动整个学界对于国外汉学的关注和重视。
(一)学界权威重视对国外汉学成果的译介
在翻译国外汉学成果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学界公认的是冯承钧。冯承钧翻译的主要是法国研究者的著作,其中以伯希和的著作最多。由此,“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把他列为‘近四十年最大的史地译家’”。④《前言》,《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3页。在民国学界中,大凡学术权威均对译介国外汉学成果给予高度重视,甚至有学者还直接参与翻译。王国维于1923年翻译了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⑤《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胡适于同年翻译了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⑥同上。此外,赵元任也直接翻译了国外汉学的成果。他于1927年翻译发表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谐声说》一文。⑦《国学论丛》第1卷第2期。1930年他又翻译了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⑧《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卷第4期。同年还与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学界权威除了重视翻译国外汉学成果外,还积极参与推介国外汉学中的名著。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完成后,即引起国内学者关注。“我国人士治语文之学能读法文者,亦无不引为学术上之幸事。”据傅斯年所言,当时中国学界就有赵元任、刘半农、胡适等欲将此书译介到中国,而傅斯年本人也非常希望能将此书翻译出来。所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之初,即有意迁译此书,虽译书不在本所计划范围之内,然为此书不可不作一例外”。此后,经过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经济赞助和中研院史语所的共同努力,该书最终翻译成功。而且在翻译之初,傅斯年与胡适就曾商定二人为该书共写序言。①傅斯年:《序》,《中国音韵学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1页。傅斯年在该书序言中,还极力推介该书,并号召中国学者学习高本汉的治学精神:“今此书将流传汉土,吾愿国人之接受此书,一如高本汉先生之接受中土学人之定论也”。②同上,第2页。可见,当时学界权威对于国外汉学成果的推介是十分用力的。
(二)国外汉学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得到了学界权威的认可
民国学界对于国外汉学成果翻译的译介和引入,不仅对当时中国学术的进步(特别是史学)起到促进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也具有长远意义,这一点得到了学界的认可。王国维因此而成为国内学界最先受国外汉学影响的一代大师。1925年,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 一文中,述及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沙畹等人对于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以及斯坦因、伯希和、狩野喜直、羽田亨、内藤虎次郎等国外学者对于敦煌文献的搜集和研究。③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学衡》第45期。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国维在该文最后,附录了该文所引的国外中国研究参考书目一份。该书目还简述了有关中国研究者的活动、生平,国外中国研究的期刊。在这篇文章和参考文献中,其引用的国外中国研究资料有一半为法国学者的论著,而且王国维对法国学者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由此可见,王国维是十分重视法国当时的中国研究的。因此,王静如说:“静安先生,人称一代大师,其成就之来源固多,然法国汉学家之影响,实占一重要位置。”④《王静如先生在中法汉学研究所讲演》,《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2卷第8期,第16页。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明确指出:国外汉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助力”:“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⑤顾颉刚:《引论》,《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页。季羡林在1991年回顾当年冯承钧对国外汉学成果的翻译时,也充分强调了其作用:“国内从事于西域南海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老一辈的学者们,定都还能记得,五六十年前冯承钧先生翻译了大量的法国中国学家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这些译文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⑥《季羡林文集》第十四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第三,重视与国外汉学界的学术交流。首先,学界权威注重与国外汉学界的学术交往。民国学界的学术权威但凡前往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基本都与国外汉学界学者进行学术探讨。陈寅恪应聘清华时,该校报道称:“陈先生留学德法两国最久,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Sylvalne Levi)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捻。”⑦《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张元济于1910年访问巴黎,就曾与沙畹畅谈。⑧张树年(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89页。胡适于1926年8月24日下午在巴黎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对与伯希和的谈话评论为:“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⑨《胡适日记全编》(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1931年,吴宓在欧洲“还与一些外国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及汉学家,交流学术。有新交,也有旧识。”⑩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当时法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以及学界权威,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均有着密切往来。⑪关于这一点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有极为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其次,邀请国外汉学家来华进行学术交流。民国时期,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的伯希和。1932年底,伯希和再度来华。在北平期间,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对伯希和这次来华,媒体也给予广泛报道。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为题,对伯希和来华以及中国学界的欢迎给予了详细报道。①报道伯希和这次来华的还有:《法国著名中国学者伯希和来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伯希和氏来华》(《华年》1932年第1卷第37期)、《法国汉学家来华》(《文艺月刊》,1933年第3卷第11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读书月刊》,1933年第2卷第5期)等。此外,1930年,法国中国研究专家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es)来华访问,多次受邀演讲欧洲的中国研究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②关于马古烈来华及其学术活动的报道还可参见:《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政治训练部旬刊》1930年第20期;《佛教评论》1931年第1卷第1期;《湖北教育厅公报》1930年第1卷第3期;《史学》1930年第1期;《中央日报》1930年4月10日。对国外汉学家予以隆重欢迎、报道,足见当时学界对于与国外汉学界交流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反过来又会推动中国学界重视对国外汉学的研究。
再次,中外学界的人才培养方面。中国赴国外留学生中出现一批师从国外中国研究专家的学生。其中,前文提到的李璜,以及杨堃、王静如等,据桑兵所言,均“曾受教葛兰言”。③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冯承钧在留学法国期间更是与伯希和、沙碗等进行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1936年, 在《新中华》上发表《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一文的姚士鳌(即姚从吾—笔者注),也曾受教于德国汉学家奥托·佛郎克(Otto Franke,1863—1946)。这些留学生师从国外汉学家学习,自然就会对国外汉学有所了解和认识。因此,他们回国后在从事学术活动时,对于国外汉学的介绍或研究就是轻车熟路的。李璜、杨堃回国后撰写了有关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研究的论著。王静如则于1943年在中法汉学研究所以《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中国学术之影响》为题进行讲演。冯承钧对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不能不说是他在法国留学时与汉学家交流的直接结果。除了中国学生前往国外留学外,当时也有不少国外学生来华进行中国研究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些学生往往都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热情帮助。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1932 年费正清抵达北京后不久就受到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等中国学界名流的热忱欢迎。④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46页。之后不久,经人介绍,费正清结识了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在蒋廷黻帮助下,费正清不仅获得了研究所需要的资料,而且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第一次来华期间,费正清还结识了中国学界的一批重要人物,如梁思成夫妇、金岳霖、陶孟和周培源等。费正清的这次来华对其以后所进行的中国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学界对国外汉学给予了高度关注。这种关注的结果不仅是国人开始了解和认识国外汉学,而且直接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学者的成长。民国学界之所以能够关注国外汉学主要在于:第一,在20世纪上半叶,以法国汉学为代表,国外汉学界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外学界取得的这些成就往往是中国学界所落后的方面。这点正如季羡林在1991年所说明,当年之所以关注国外汉学的原因:
五六十年以前,我们对西域南海的研究水平,远远比不上外国学者。原因是,这些地方的古代语言文字,我们多半不通;与这些地方有关的其他资料,我们多半不能掌握。我们除了能读中国史料以外,缺的东西太多,而且说句不客气的话,不通语言文字,不能掌握必要的资料,能读懂古代汉文典籍吗?因此,当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出版的时候,我们都由衷地感谢他,法文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的。⑤《季羡林文集》第十四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第二,民国学界的开放性则是推动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才能够使学界看到国外汉学,也才能使学术大师能客观地认可国外研究,同时能够诚挚地吸收对自己研究有益的成果。在这方面,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人无疑是杰出的榜样。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才能够推动中外学界在中国研究这一共同的领域内进行学术对话。也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学界能够造就一批学贯东西的大师。民国学界大师的学贯东西不仅是对西方学术有着深切的认知,同时更是善于汲取国外汉学的营养。第三,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推动学界关注国外汉学。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加深。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学术界在意识到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有必要了解、认识,乃至研究国外的中国研究,以掌握对手的情况。所以,1936年王古鲁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自费出版后,有人在书评中就写道:
现在一般人常说:‘中国与日本,真有不共戴天之仇了。我们应该立即与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试问我们要和日本人拼,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军备、人情、民族性……是不是应该有透彻的研究和深刻的认识呢?可是我们反躬自问,对于日本的研究和认识,实在不多,甚至可以说,还是隔膜得很!我们再看日本人对于中国之研究和了解这又如何呢?从前还没有人做这一类的详细的研究与整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日本人对于我们中国,曾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罢了。而不知道她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到了什么程度。①吴成:《评王著〈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中国新论》1936年第2卷第4期。
正因如此,王古鲁的这部著作出版后,在学界、政界均得到广泛重视。由于学界对于国外汉学认可和重视,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开始注意研究国外汉学。在这一时期,韩奎章、季羡林等撰写了研究德国汉学的论著;王古鲁、周一良、梁绳袆、贺昌群等撰写了日本汉学研究论文或专著;李璜、杨堃、王静如发表了有关法国汉学研究的论著;方豪、孟宪承等对欧洲汉学进行了研究。②限于篇幅,关于民国学界的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具体论述,笔者将另外撰文探讨。这些初步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学界国外汉学研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