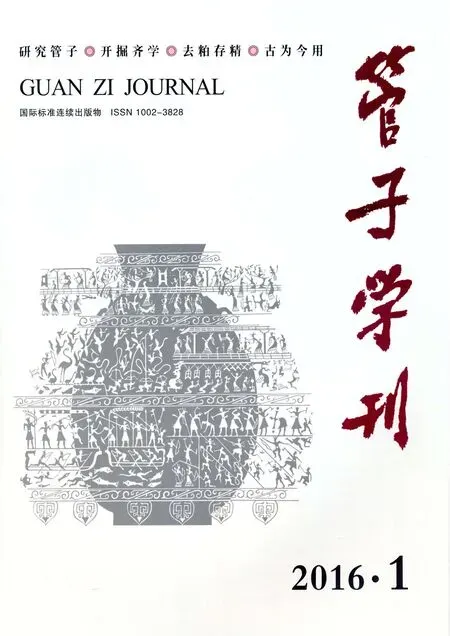《齐物论》解读
——以“一”为主题
张丽萍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学术考辨
《齐物论》解读
——以“一”为主题
张丽萍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齐物论》是《庄子》内篇之一,基本属于庄子的思想。它以“道”为最高范畴,主题是“一”,内含“道通为一”“物通为一”“知通为一”三个方面。关于“齐物论”的涵义,历来有“齐物”论与齐“物论”之争,但从全篇来看,二者都有论述,物与物论都是齐的对象。可以说,“齐”即是“一”,根本方法是“吾丧我”,最高境界是“至人”。
关键词:道;一;物;物论
一、问题的提出
在《庄子》中,“道”是天地万物的“真宰”,是万物形成、变化的根据,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而其本身“有情而无形”,真实存在,却又超越时空,无形无象。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因得道而有生命,有形、有性。从而,人就处于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物关系中,人“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本文所引《庄子·齐物论》原文均来自郭庆藩撰的《庄子集释》(全三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后文不再注明。,人有形后整个身心都沉溺在物上,将人、物对立,劳心伤神,无止尽的作用于物。结果是既没有获得对物的认识,也没有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经过反思的,不知道生与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是对人与物的关系的深化,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以语言为基本的交流媒介。人的语言所言的就是“物论”,不同的物论者彼此各执一词,引起了相互的言辩,从而滋生无穷的是非。这样的学术态度,使语言没有了意义,从而使“道”被天下分,无法获得真理。这样,人在这两种关系中迷失了自我。为了更好的认识自我,需要从认识与修身上来提升。
二、认识物与物论
1.物与我
宇宙万物,因“道”而成,各有其形,各有其性,如天地间有秋毫、大山;人有百骸、九窍、六藏;有殇子、彭祖等。彼此各不相同,有大、小,长、短,高、低,动、静等之分;人有思维,有情感,有语言。但万物有“分”,不等于万物有贵贱之别,而是万物为“一”。
颜成子游问南郭子綦何为“天籁”,子綦说“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万窍都被风吹过,但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窍。只有风没有窍,或只有窍没有风,都不会有声音;如果所有的窍都一样,也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风与窍是相互依赖的,从发声来说,风是主体,窍是客体,是风作用于窍,从发出的不同声来说,窍是主体,风是客体,而这也正是“自取”之义。“自取”不是说万窍都绝对独立存在,各不相干,而是各有其性,都顺其“道”。所以,天籁不是地籁、人籁之外的第三种,而就是地籁、人籁本身,就是肯定不同的窍,彼此相“齐”。
更进一步说,物的本质是“道通为一”。“道”是无“私”的,以“道”观万物,从静态看,万物都得“道”,“道”蕴含万物之中,“故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万物相“齐”。从动态看,万物相“化”,成为一个链条,无穷止尽;但从万物本性来说,成与毁都是“物”本身,“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物通为一,是因为“道通为一”。“道”是“物”的本体与根源,“通”是对“分”而言,由“化”而生;“一”是“通”的必然结果。这实际是“一”与“多”的统一,“一”以“多”为形式,“多”以“一”为内涵。那么,人与物,二者没有根本的不同,可以归结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天地万物超越时空,超越历史,在逻辑本原上相通为一。
但不同的物,对人有不同的功用,被按照有用、无用、用处大、用处小作出区分;而人会依据自己的需要与目的,在知识的界限内,作用于不同的物,以满足身心的欲求。这样,“我”就产生了,物我关系形成。在这种关系中,“我”是主体,是形与心的统一,“心”随“形”动,“物”是客体,二者相对立。“我”陷于对物的无止境的追求,劳心伤神,并企图去驾驭物,为“我”所用。这样,物不再是其本身,人也迷失了自我,“其形化,其心与之然”,不知生命的意义何在,人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不知这种对物、物我关系的认识是否合理。总之,这种认识只停留在“我”的阶段,没有经过反思。
2.物论
物论是人对宇宙的认识,但不是所有对物的认识都属于物论。“物论”之“物”,不是限于具体的“物”,而是一个较广泛、较抽象的概念,涉及到天地、人伦、秩序等方面;“论”,《说文解字注》释为“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1]92,强调逻辑性、系统性、思想性。所以,“物论”是指有哲学内涵的思想,属于认识论,涵盖了伦理、政治、科学、宗教、价值等方面。
春秋战国之际,儒墨是当时主要的两大学术流派,并称显学。儒家以“仁”为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认为爱有差等,以亲人为起点,由己及人,“泛爱众”;重视周礼,要求“克己复礼”,倡导厚葬;不言鬼神、天命。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认为爱是无差等的,爱以利为出发点;反对厚葬,要求节葬;“尊天事鬼”(《墨子·非命》)。此外,还有名家惠施,以善辩著称,有“历物”十事等。诸多的物论必引起论辩。
论由言而成,言由心而成,心由道而成。道是人生命的本原,使人有“心”,从而人可以思维,认识。但在现实中,人往往是用“成心”去看世界。“成心”,成玄英释为“凡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2]31,即是被“情”所困而产生的偏见。这样,对物所形成的认识就不是客观的,并且也是不全面的,是“我”的认识。如果所有人都以此为出发点,“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那么每个人都有标准,都以自己的认识为“是”。“成心”是一般人都会具有的,儒墨之所以会无休止地争论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是因为他们的认识有着自我预设的前提,“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成心”是是非产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有是非肯定是有成心,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没有反思到自己有“成心”,从而也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说的“道”不是天地之“真宰”。
“成心”是是非产生的一个内在原因,言由心生,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是“辩”形成的一个外在原因。“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在《经典释文》中有“崔云吹犹籁也”,指自然而为,而语言是专属于人的,具有一定的意义,是沟通言者与所言者的媒介,其中言者是主体,所言者是主体的对象。语言本身的作用在于表达,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就在于言者的动机与目的,和语言的性质。如果言者出于“成心”,用“荣华”之言说“道”,则“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语言的意义没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3]12,所言说的只是偏见,而不是真正的“道”。如果用这样的语言相互辩论,就会导致没法判断是非,只能各持己见。这样,“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不同物论相对而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从而“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无穷。这样的智慧是“滑疑之耀”,这样的言说“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有言等于无言。
三 、修养“无己”
1.“吾丧我”
万物被区分、人与物关系对立、不同物论相互辩论使“道”被分真伪,都是因“我”的“成心”所致,所以要解决“我”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必须从“我”入手,进行反思,“吾丧我”。
“我”源自道,有形有心,形为外,心为内。有我必有彼,“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彼我不是各自独立,而是相对待而存在的,“我”之所以为“我”,不是因为“我”是什么,而是因为“彼”是什么,这是“真宰”所为。“道”并不否定万物之分,而是反对将“我”孤立,与“彼”对立,强调万物为“一”。
认识到天地之道相通为一,就要反省人心,以“吾”丧“我”。“吾”“我”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二者没有概念上的区别,但二者指示着人不同的存在状态[4]。“我”是现实主体,是有形、有情、有欲、有成心、处于一定关系中的存在;“吾”是对“我”的否定,是真我,具有绝对性、完善性。所以,“吾”丧“我”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能自我反思。那么,何为“吾丧我”?南郭子綦“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说“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由此可见,“丧我”包括两个方面:形与心,即是不被个人情、欲所困,去除人的成心,不以成心为出发点,劳神费心,不以知为荣耀,用天地万物,争是非之名。
“吾丧我”看似是一种负的方法,从道来看,也是一种正的方法,不断地丧,也在不断地正,迷途知返,“虚”心应物,不断的趋向“道”,最终达到“知通为一”,认识到宇宙“自己”也,万物是一,物我是一,物论是一。
2.“两行”
不同的物论的争辩引起无穷是非,这样就陷入一种坏的无限循环,所以必须对此反思,认识到不同的物论都相通为一,达到“以明”的状态。
从物来说,“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物是言说而成的,内含着名与实的统一,有着种种诠释的可能性。所以,物论可以不同,但前提是语言必须指向一定的意义,不能陷入无穷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枢”是指圆环中空,“道枢”取消了彼此相对立的是非状态,虚心应对,贯通彼此。即“因是”,钱穆释为“圣人独因是而无所非”[5]13,对于各种物论不会妄加否定,而是“和以天倪”,止于自然,做到“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和是非”则“化声之相待”,是为是,无需辩论;“休天钧”则承认万物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承认物论的某种真理性,这样存在、语言、真理三者达到了统一。从而,“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以不用为用,使万物都各有所成,使不同的物论都保持在一定的合理性范围内。
3.“ 知通为一”
宇宙之大,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对象不同,认识的层次不同,最低的要求是不对某种言论妄下判断,承认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将人的认识限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内,这是认识的最高界限。但知“不知”还是一种“知”,这样“知”与“不知”就没有了界限,“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觉而后知其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所以,在知识本身上必须“因是”,认识到“知”与“不知”相通为一,肯定知识有着种种可能性,不能被“知”“不知”本身所局限。
对于“道”来说,“道”是“一”,但表述出的语言与“一”为二;并且退一步来说,“大道不称”,但却又不得不言“道”,否则无法知“道”,这样“道”自身就陷入了“知与不知”“言与不言”的悖论。“道”与语言必须都存在,这是人认识的必要条件,否则二者都不存在;同时,这个悖论又必须解决。这样,必须破“言”。庄子“今且有言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这样没有一种言论是绝对真理,即便是关于道的“真”言也只是与众物论为一。这样,破除了对“知”的执着,才能达到至人的境界。
至人,是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至人无己”。他以“道”为真宰,虚心认识自然,将言与不言相通一,知与不知相通一,用与不用相通一,物与我相通一,彼与我相通一。至人即是“真人”,与庄子梦蝶的状态相通,“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完成了由“我”向“真我”的转化,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爱莲心.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M].周炽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陈静.“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J],哲学研究,2001,(5).
[5]钱穆.庄子纂笺[M].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
(责任编辑:张杰)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6)01-0092-03
作者简介:张丽萍,女,山西文水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思想文化比较。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认知科学视野下的道家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XZX024)。
收稿日期:2014-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