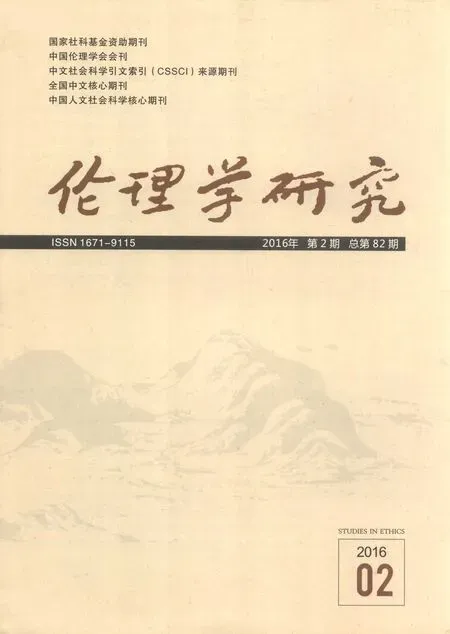虚拟品质与道德教育
——兼论基于虚拟现实之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颜青山
虚拟品质与道德教育
——兼论基于虚拟现实之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颜青山
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关于人的发育和成长的争论区分了先天/后天因素、遗传/环境,这个区分转化到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上,可以作出能动/习就因素的区分。人的道德品质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虚拟情景当作习就因素,那么人的虚拟道德品质是可能的,即是在虚拟情景中形成的道德品质;因为虚拟品质和真实品质共享同一能动性因素,它们的性质和伦理学地位就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而其必要条件是:第一,在虚拟和真实之间建立无间隙的连接;第二,受教育者认同虚拟现实中的行动和感受。
虚拟品质;虚拟现实;道德教育
一、问题引出:从两个著名的争论说起
关于人的发育与发展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两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中,究竟是先天因素重要还是后天因素重要?究竟是遗传因素重要还是环境因素重要?事实上,后一个争论是前一个争论的精确化和科学化。然而,这样的争论很容易堕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的争论,更严重的问题是,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
在遗传学于20世纪初兴起之前,先天因素常常是指胚胎发育期间就起作用的因素,而后天因素则是指胎儿出生之后才介入的因素;也就是说,先天/后天的区分是胚胎学或渐成论(epigenetics)的概念,而遗传/环境的区分是遗传学或预成论的概念。从生物学史上看,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渐成论与预成论的争论阶段,在渐成论看来,胚胎和个体的发育都是物理化学因素作用的结果,精子或卵细胞中并不存在如中世纪流行的预成论所主张的“小人”[1](P253-295)。
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发育成长中,先天因素是否可以脱离后天因素而起作用?第二,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是否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
从争论的角度看,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无非是比较相同的先天因素在不同后天因素作用下造成的差别,或者,比较不同先天条件在后天因素作用下的差别。如果先天因素相同,而在不同后天因素作用下造成了“巨大”的差别,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后天因素更重要;反之,如果后天因素基本相同,但因为先天因素差别而造成了“巨大”差别,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先天因素更重要。如历史已经表明的,争论的双方都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好证据或理由。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讨论本身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些。如果先天因素是指胎儿胚胎发育时期起作用的因素,那么胎儿的妊娠环境差别是否是先天因素?例如,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两个来自同一受精卵的胚胎细胞分别植入不同母亲的子宫后发育成胎儿,它们的先天因素是否相同?如果根据先天因素的前述说明,不同妊娠环境也是在胎儿期起作用的因素,它们也应该被看作先天因素。但是,很显然,我们可能直觉上不会如此认同。那么,我们的这种直觉持有了一种什么样的先天概念呢?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遗传因素的概念,即如果遗传因素相同,那么先天因素相同。
使用遗传因素的概念确实比先天因素的概念更具有物料上的明晰性,也可以在现代条件下得到更精确的生物学支持。在当今遗传学基础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似乎能够清晰地区分开来,遗传因素就是基因或DNA决定的那些过程,环境因素则是对DNA作用产生调节控制影响的因素。但这样一来,后天因素的概念就不合适了,因为像妊娠环境这样的因素肯定不是后天的,但也不是遗传的。因此,后天因素的概念就被环境因素的概念替代了。
但是,从相互作用的方面看,或者从日常直觉看,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区分却比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区分更模糊。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区分有一个明晰的时间界线,即出生。逻辑上,胎儿出生前的那些因素完全可以独立地促进人的发育成长,因为那些因素本身已经能够促成人的胎儿发育,如果让人继续处于那样的状态,大概也可以发育到成人。但是,遗传因素却不能单独促进人的发育生长,即使在胎儿时期,也必需环境因素介入才可以,即,人的发育成长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共同作用模式下比较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作用,无疑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评论上述两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更无意于给这种争论一个结论。我们的目标是探讨人的道德成长过程中,在品质的形成时如何类似地区分两种相关的影响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将上述两种区分替换性地转换到道德成长过程中去,并最终讨论基于虚拟现实而形成的品质是否可以对道德教育有所贡献。
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上述争论中,我们更关注两类因素的区分及其转换,并将这样的区分最终转换到能动因素和习就(habiting)因素的区分上。
二、道德品质形成中的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
在人的心理发展和道德成长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上述争论的争论,例如,人的心理或道德品质的形成究竟是先天因素重要还是后天因素重要?不过这里的先天因素很显然不仅仅指生物学因素,也包括人的可发展的能力范围或限度,并且主要是指后者。
这个问题的争论更接近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哪个更重要的争论,而与先天因素与环境因素的争论距离则更远一些。
必须指出的是,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是有区别。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表明,道德品质不同于情感等心理因素,心理品质像身体品质一样,属于自然品质,而道德品质则是一种意向性品质或实践品质,具有无时间性的认识论特征[2](P288,366)。由于本文的目标是考察道德教育,因此这里只谈论道德品质相关的问题。
主张先天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之重要性的人可以有三个方面的论据。第一个方面涉及品质形成的限度和范围,即无论人的后天训练如何强大,有些品质都不可能形成,例如,无论一个田径运动员后天如何训练,都不可能拥有像猎豹那样奔跑的卓越品质;第二个方面涉及生物学因素对道德品质的作用,例如,某些遗传或发育因素可能影响人行为倾向,从而对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涉及品质的可能性问题,即有些道德品质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形成,例如,即使在一个说谎成性的诈骗团伙中生存,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智能力反思到这些品质的恶,并形成相反的诚实的品质。
相反的观点大概不会直接挑战第一个方面的论证,但会将那种限制看作是环境的因素。首先,那种奔跑的品质并不是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与这种基于物种遗传因素所形成的身体品质的直接关系非常微弱,相对于人的道德能力而言,它应该属于环境因素。其次,在讨论后天因素对人的作用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后天的实践训练对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在第三个方面中的理智能力才是人之作为人的先天品质和能力,而那个团伙的实践训练才是后天的因素。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行为遗传学是否可能的争论,而不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
由此,相反的观点会更看重对上述论证对第三个方面的反驳。他们会援引亚里士多德反驳苏格拉底的论述,即,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什么是善而不行善,他也不可能具备相应的道德品质,犹如一个知道医学知识的人不会自动健康,一个知道建筑知识的人也不会自动成为建筑家;一个在诈骗团伙中生活的人,即使他能够反思到诚实品质的重要性,他也不可能具备实践诚实行动的机会,从而也不可能最终形成诚实的品质。
既然我们并不关注争论的最终结论,而只关注这种区分,我们就不会对这种争论的结论作出评判,而会倾向于考察相反观点的区分是否合理。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当涉及道德品质的形成而区分两类因素并争论它们何者重要时,这种争论想表明什么?这种争论像前面的两种争论一样,无非是想表明,有一类因素是固有的,而另一类因素是可变的,如前面争论中的先天因素/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争论的焦点则是,固有因素作用大还是可变因素作用大。其次,我们要弄清楚,当我们在讨论道德品质形成中将遗传因素纳入考虑的时候,意图何在?很显然,这种纳入无非是把它看作影响人的道德品质的固有因素。
但是,将遗传因素纳入影响道德品质形成的固有因素会产生如下困难:
首先,遗传因素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这样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诚然,如第二个论证表明的,一些遗传因素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倾向,由此而影响道德品质的形成,在此意义上,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程度确实是可以争论的。但这种争论并不具有普遍的道德哲学意义,道德哲学关注的是对所有人而言都具有意义的问题。那些对道德品质形成产生足够影响的遗传因素,一般是个体性的,即是某些特定个体固有的因素,并不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固有的因素,因此,即使它是一个问题,也不是关于道德品质形成的一般性问题。
其次,如果一种品质如果与遗传因素关联起来,这种品质是否属于道德品质?这样的争论最后可能演变成行为遗传学是否可能的问题,赞成遗传因素足够影响“道德品质”、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人,无非是在主张关于人的行为遗传学是可能的,而反对的人无非是主张人的行为遗传学不可能,即人的行为不受或少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关于上述困难,辩护者可能认为,既然前面两个问题可以成为普遍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成为普遍问题。确实如此,但这种辩护所说的普遍性是行为遗传学的普遍性,而不是道德哲学的普遍性。当我们在道德哲学的范围讨论道德品质的形成的时候,如我们前面强调的,我们并不是将道德品质看作一种自然品质,而是一种认识论性质的实践品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或许我们应该承认,当我们争论固有因素和可变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时,这个问题存在着歧义:它既包括遗传因素还是非遗传因素的争论,也包括其他意义上固有因素和可变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
遗传因素与非遗传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属于前面的问题,即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对人的发育和发展之重要性的争论。既然我们想把问题引向纯粹的道德哲学,引向虚拟品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问题,我们就不必理会遗传因素与非遗传因素的区分,而应该集中关注另一种意义上的争论及其区分,即使它可能在哲学史上不曾成为主流。
这种区分体现在上述第三个方面的事例,即一个生活在诈骗集团中的人是否有可能形成诚实的品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伦理品质是选择的结果:“德性与固有功用相联系……伦理德性…是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3](P121)“首先让我们承认,这些品质就其自身是受到选择的。因为它们分别为灵魂部分的德性。”[3](P134)因此,德性应当首先是出于人的自主性。人的自主性是每个正常人都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普遍特征,或者说是人的一种具有事实性基础的普遍规定性。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因素看作是影响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能动因素。从前述的第三个事例来看,这种能动性因素就体现在反思到诈骗作为恶习并认知到诚实作为德性品质。
至于那些可变因素,则是指不同人处于不同环境中所获得的与品质训练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得道德品质能够被习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道德品质或伦理品质不是天生的,是习得的。这些因素带有被动的色彩,中性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习就因素。在前面的事例中,诈骗团伙的行为或文化环境就是习就因素。
如果选择因素属于理智能力并相关于理智品质的话,那么,大致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影响道德品质的因素就可以区分为两类因素,固有的能动因素和可变的习就因素。或许,我们可以将能动性因素促成的品质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而习就因素促成的品质对应于其伦理德性,不过,这种对应也可能直接将德性品质区分为两个类型,仿佛它们是不相关的。但在我们这里,这两类因素在形成品质的过程中是共同作用促成道德品质的形成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坚持德性的整体性[2](P364-367)。
当然,还必须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动因素是固有的,而习就因素是可变的。能动因素确实有一个一般的遗传基础,这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能力,每个人虽然有所差别,但在人作为物种的范围内,可以看作是差别不大的;即使存在差别,我们也会看重它们共有的特征,而不是差别的特征,即考虑其作为人的类特征的一般性;尤其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识的存在,我们就会接受,这种能动性在形式上虽然具有生物学基础,但其能力的内容并不需要生物学基础,相反,其内容是独立于生物学基础的,例如,理性推理和论证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等等——道德哲学中坚持自由意志的主流伦理学家不会认为逻辑论证和自主选择是基于生物学的。习就因素就不同了,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接受不同的教育和文化培养,行为方式也大相径庭,这些影响因素必定是可变的。
如果能动性主要是一种与获取知识的认知因素的话,那么,前述的关于固有因素与可变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作用的争论就变成了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争论,即知识(认知)与习得(或习惯)之间争论。
一般而言,能动因素虽然也可以由教导训练而成为一种品质,但这种品质与人的行动的关系很间接,也就是说,行动性的训练并不是这种品质的必要条件。道德品质则必须基于行动的长期训练而形成一种习惯或习性,这种行动性的训练必然与我们的身体相关,而我们的身体发育显然包含了来自遗传学的因素,如动作的灵敏性、耐受的持久性等等,它决定着我们形成道德品质的效率。例如,一个天生热情的人比一个天生冷漠的可人能更容易培养出友善的道德品质,但冷漠的人通过更多的行为训练,也是可以培养出友善品质的。因此,这些生物学因素恰恰成为了影响我们道德品质形成的习就性因素之一,即作为影响训练效率的可变因素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个体多样的遗传因素与文化因素一样,都是习就因素。
从上述所有论证,我们看到,从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争论到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争论,有一个颠覆性转换,即将胚胎发育中所有实际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所谓先天因素)都归并到了后者的环境因素中,而所谓遗传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特立出来的新的因素类型,它并不是一个实际地发生作用的因素,即不是一个现实的因素,而只是一种引导现实因素起作用的潜在力量,例如,DNA并不实际参与身心的发育成长,它只是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并进而决定细胞、组织和器官的形成,从而间接影响身心功能。而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争论到能动因素/习就因素争论也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换,即将前一个争论中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归并到习就因素中,能动因素则是一种新的因素类型,是人所独有的理智成分。
三、虚拟品质是否可能
区分上述两类因素的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是否存在虚拟品质?虚拟现实世界是否可以对道德教育产生作用?
自网络技术兴起之后,网络伦理学一直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关于网络伦理的讨论似乎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网络社会作为一个虚拟社会,在其中是否会形成特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如果会,这种品质会虚拟到什么程度?即与虚拟品质相关的能动因素和习就因素中,哪些是可以虚拟的?
目前,比网络技术更高级的虚拟现实技术正在紧密锣鼓的部署中,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揭示虚拟现实世界的根本的伦理问题。
在虚拟社会中,虚拟人格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技术上,虚拟社会是指,一个真实的人关联于一个具有某种程度智能的设备(可操作的电脑或可感知的穿戴设备)与其他类似的设备-人的联合体所连接而成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并不特别设定那些设备就只是工具,或许在强人工智能成熟的时候,它们就是一个人格存在。
根据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的区分,我们可以将前面的问题分解为:如果能动因素可以虚拟,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而如果不能,仅仅是习就因素的虚拟,虚拟社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伦理学功能?
将两类因素与虚拟和真实两种情景分别组合,逻辑上可以得到四种类型的社会:第一种是能动因素和习就因素均真实的社会,大致相当于我们的日常世界;第二种是两者均被虚拟的社会,这样的虚拟世界将是一个纯粹的强人工智能的虚拟现实社会;第三种是能动性因素虚拟但习就因素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强人工智能与我们人类共享一个真实世界的社会;第四种是能动性因素真实但习就因素虚拟的世界,这是一个弱人工智能的虚拟社会,人类生活在一个通过智能设备相互交往的社会中。
既然第一种情形是我们的日常世界,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作出讨论。
第二种情况是颠覆性的,貌似会产生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一个颠覆性的虚拟人格似乎应该是指智能设备具有的人格。在这种颠覆性之下,这些设备不是人的工具,恰恰是一个自主的人格,而真实的人则处于这个人格之后,反倒成为了附属物,因此,一种颠覆性的虚拟伦理学就是处理这些智能设备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学。
这样一种虚拟的人格及其道德品质是否可能呢?如果这样的虚拟人格是可能的,那就意味着这样智能设备具有人格特征并能够形成道德品质,它就必须具备能动因素,它可以作出选择,真正地理解道德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等等。然后,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在虚拟环境中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当他熟练该角色之后,他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相关的道德品质。不过这种讨论与人类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强人工智能产物之间的伦理学。如果这样的强人工智能具有能动性因素并生活在一个虚拟社区中,只要它不干扰人类的生活,即使我们替它们讨论了伦理问题,它们是否接受却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这种讨论就缺乏了现实的意义。
第三种情况依然具有颠覆性意义,而且具有与人类相关的现实意义。这种虚拟表明,我不仅与强人工智能设备共享同一个文化,还可能共享同一个身体,即强人工智能设备借助我的身体去感受世界并获得经验、生活的意义和人生价值。
这种情况,我们要讨论的首先是,强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根据塞尔的,依据图灵机原理构造的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心灵能力,其缺乏最重要的理解能力[4]。一个可行的强人工智能只能是与生物学因素结合起来才可能,因此,这里的最初的道德难题是,这种结合是否在伦理学上被允许?如果这样的人格平等于我们或者道德地位上低于我们,那么人类就是在制造人格存在,是仅仅将人格作为手段;而如果被制造的这些人格道德地位高于,那么我们将会仅仅作为它们的手段。无论如何,这是道德上不允许的,因此,我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应当禁止基于生物学活性的强人工智能。
赞成强人工智能的人可能会辩护说,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它只是获得了能动性因素,但并没有获得各种完备人格所需要的品质结构。但是,如果能动性因素的虚拟在物理上可以实现,那么,这样的智能当然可以利用我们的环境和身体获得特定的道德品质,甚至是超出我们的道德品质,例如道德超人。况且,道德原则禁止的是人格意志仅仅被作为手段,而不是人格整体;当一个具有能动性因素的对象被制造出来之后,我们就制造出了一个意志体,而这样被制造的意志一开始就是不自由的,应当在道德上被禁止的。
这种情形的伦理问题会有很多,也会很重大,但与我们论题的相关性不太紧密,暂且就此打住。
第四种情况是我们着重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的虚拟社会中,我们是否会获得相关的虚拟品质?
最简单的一个这样的虚拟社区就是我们目前的网络社区。在网络社区里,人们主要依靠文字、图片、视频或声音进行交往,最经常的是文字交往模式;设想一个人进入一个这样的虚拟社区,一开始他于社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可能在某些交谈中会与某些人产生共鸣或发生争执。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这种交往,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在社区中会给所有成员形成一个特定印象,并且这种印象会大致一致。很显然,这时他已经具备了在该社区的角色品质,这就是他在虚拟社区的虚拟品质。
虚拟品质与真实品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表现都是某种特定的可预测的行为倾向。一个人的虚拟品质与他的真实品质表现上可能大相径庭,其中有些可能只是不同真实能力差异导致的,例如,一个平时拙于文字表达而强于口头表达的人,在真实社区里可能具有能言善辩的品质,而在网络社区中则会形成沉默寡言的品质。这种差别也正表明了身体能力因素是一种习就因素,并且会影响品质的形成。如果此人的行为倾向稳定的话,这种虚拟品质也是其真正的品质,而不是一种假象。
问题来了,我们是将能言善辩归属于这个人,还是将沉默寡言归属于这个人呢?很显然,这两种品质是相互冲突的,一个道德上成熟的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冲突的品质。
我们宁愿将这两种品质看作是不同情景下形成的差异性品质,而不是冲突的品质。品质的形成是能动性因素与习就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很可能主观上愿意选择一种品质,但由于习就因素的限制,他却形成了另一种品质。例如,一个口头表达能力有限的人,也许在他年少的时候非常羡慕能言善辩的同伴,也希望获得同伴的能力,但由于能力的先天限制,他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或许他可以通过艰苦的训练达到这一点,但因为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他很可能就会在反思平衡后适应这一点并理智地认同它,最后形成沉默寡言的品质。
虚拟品质的可能性也可以从品质的情景依赖性来理解。品质的获得必需习就因素,而习就因素是高度情景化的。
设想一个人一开始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介入性较高、并偏好言过其实的豪言壮语的人际文化氛围(例如长沙)中,当他转换到一个强调尊重个人空间、说话委婉拘谨的文化(例如上海)中,他一开始就会很不习惯新的文化氛围,或许一开始他会表现出原文化的品质和行为,但每当他如此表现总是受到无声的抵制时,他就可能开始封闭自己,拒绝与周围的人交往,这样,久而久之,他实际上就习得了一种接近于当地人的品质,不再强烈介入他人的空间、也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被动性如果得到主动的理智认同,就会成为一种实践品质。但是,只要他回到原来的氛围中时,品质的情景依赖性会立即激起他原有的行为倾向。相反的过程也可能发生。
因此,从品质形成中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看,从品质的习得性和高度情景敏感性的角度,虚拟品质和真实品质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属性。
当然,人们可以争论说,这种出于能力和情景限制而不是出于自愿选择形成的品质不可能是一种德性品质,更可能是一种恶习。我并不打算否认这种看法,但将其称为恶习可能太过分,它更可能是一种不完善的德性品质;无论如何,它确实构成了一种道德相关的品质。并且,在此意义上,如果它是恶习的话,我们也将认同一种拓展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恶习出于无知和无能;或者可以说,恶习还只是一种心理品质,高阶的调节性对其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的条件
由于网络社区的行为能力有限,仅仅是文字交往和远距离的声音视频交往,其所形成的虚拟品质,结构也相对单一,丰富性程度很低,而即将到来的虚拟现实交往则可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它将会促成全面而丰富的虚拟品质结构。这样的虚拟现实社区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取代目前以课堂形式为主的学校道德教育体系,而将学生推向虚拟现实社区,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道德教育。
那么,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是否可能呢?换句话说,要使得其成为可能,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简单涉及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的性质和目的。
首先,道德教育不只是理智教育,其目的不只是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性因素,而是最终要让受教育者获得恰当的道德品质。因此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其目的是在于习得品质,而其过程则主要是实践性训练。
其次,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不只是形成在虚拟社会起作用的道德品质,而是要让在虚拟社会中获得的好的道德品质成为我们真实世界的道德品质,即让品质的情景敏感性变成情景普遍性。因此,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情景敏感性。
在前面的品质形成中,我们提到品质形成具有情景敏感性,而在这里又要求去情景敏感性,这里是否存在矛盾呢?
情景与品质的关系是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道德怀疑论者质疑品质之存在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一方面,假如一个人只在特定情景下诚实,而不是在所有情景下诚实,我们很难说他具有诚实的品质。道德怀疑论者正是利用情景主义的心理学事实来反驳品质的存在性的,他们发现在关于诚实的测试中,受试者可以高概率地保持同一情景中行为的一致性,但交叉情景的行为一致性却很低。例如,受试者可能在考试中坚持不作弊,但却在上课迟到时说谎[5](P1-5)。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的品质,我们就很难说他是有德性的人,例如,机智和勇敢就应当运用于不同的场合,否则就是滑头和怯弱。
任何品质都是在特定情景下形成的,但这种品质还只是一种受制于时空的自然品质,是一种心理品质或道德品质的心理学方面,其表现具有自发性,仿佛行为主义主张的刺激-反应模式;一种实践品质必须体现行动者的自主性或自由意志,只有当一个人也能够运动其理智德性将这样的品质运用于需要但他从未如此行动过的其他情景时,这种品质才可以称为实践品质。在这里,关于自然/心理学品质与实践/道德品质的区分,参考了康德关于情感/病理学态度与实践态度的区分;在康德那里,自发的态度是情感或病理学态度,出自自然的禀好,如爱你的邻人,而自觉的随意的态度是实践态度,出自原则或义务的要求,如爱你的敌人[6](P15)。因此,实践品质不同于自然品质的地方在于,它必然包含了理智的或能动的因素。
同样地,当一个人面临不同情景需要时,他运用不同的品质,也是在对自己具备的各种心理学品质进行选择,这也是一种理智品质的作用,这种随着情景差异而运用不同品质的能力或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品质。
因此,道德品质的去情景敏感性是去除自发的情景敏感性,而不是去除基于理智自觉的情景敏感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的是,道德品质作为一种习性品质,必然也具有自发性倾向,因此,去自发敏感性不是完全抛弃自发性,而是让自发倾向符合德性的规范性要求。例如,一个人在紧急情况下自发地作出敏捷的反应,就是一种符合德性要求的自发性,而此时如果他自发地处于惊呆而无所作为的状态,则不是符合德性要求的自发性,是一种恶习。在此意义上,如笔者已经强调的,德性品质是一种高阶的调节性的实践品质[2](P288-292)。
要获得这种去自发情景敏感性效果,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虚拟社区中逐渐添加足够丰富的真实因素,让受教育者体验足够丰富的情景并使得他们训练出适时调整品质运用的理智品质。
如果虚拟现实让受教育者有置身事外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虚拟现实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因为这样的系统与游戏系统没有差异,至多是训练人的反应能力,而无法养成一种习性品质。
诚然,反对的意见认为,游戏系统对儿童道德形成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表明游戏系统也具有道德教育功能。然而,这个反驳误用了“道德教育”的概念,教育,一定是指一种目标指向良善结果的活动,如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游戏的负面影响应当不属于教育,而是心理品质的自发形成,基本上属于恶习形成的范畴——按照我们前面的论述,恶习至多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品质。
继续的反驳可能是,通常的模拟训练系统能够促成卓越的技能品质,相信它也能够促成德性品质的形成。不可否认,这种训练确实可以形成某些动作倾向,熟练某些技术过程,但因为被训练者并不将训练场景的任务看作真实的,他就不太可能给予道德关怀,从而也很难说能够形成道德品质。
虚拟现实技术使用可穿戴设备并且与网络(尤其是物联网)联合,可以形成一个真实与虚拟无间隙对接的虚拟社会。按照翟振明的设想,这样的虚拟社会包含主体、人替、人摹、物替和物摹等要素。
在一个教学训练系统中,主体即是受教育者,而人替则是一个由物理要素构成的“假人”(例如一个橡胶人),但是人替可以接受真实刺激并通过网络将这些刺激传递到主体所穿戴的具有感知这些刺激之能力的设备上,同时,这个人替也可以接受主体的行为指令,并根据其指令行动。人摹则是人替在纯粹虚拟空间的对应的电子形象,其功能严格相似与人替。物替是真实物体的物理“假体”,它可以向主体输出其所替代的物体的所有可感知物理属性(例如颜色、光泽、硬度、手感、气味等);而物摹则是物替在虚拟空间中对应的电子形象。
在这样的系统中,一个人无法区分与他交往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感觉与真实感觉并无差异,最重要的是,由于行为和感知的对应性,他会认同人替和人摹就是自己的身体。厄森(Henrik Ehrsson)通过一系列实验表明,当一个人无法区分一只连接于他的肩膀的橡胶手(相当于人替)和真手的时候,尖锐物即将扎向它们时,他会有相同的心理体验和生理反应;而当在纯粹虚拟现实环境中,当尖锐物扎向他的人摹时,他的感受和反应类似自己的身体受到的刺激[7-10]。
我们的品质形成来自于我们的行动经验和感知经验,而这些经验的产生依赖于我们的身体认知感官和行动感受,当我们将人替和人摹认同为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将会将它们的“行动”和“感受”认同为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感受,这样,我们就将通过虚拟现实中人替和人摹拟的行动和感受形成我们自己的道德品质。
因此,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在真实与虚拟之间建立一种无间隙的连接;第二,受教育者对在虚拟现实中的行为产生自我认同,即让他们相信,这样的行为是我的行为。
[1]洛伊斯·玛格纳.生命科学史[M].李难、崔极盛、王水平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颜青山.价值道义论的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塞尔.“心灵、大脑与程序”[A].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哲学[C].刘西瑞、王汉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5]颜青山.挑战与回应:中国话语中死亡与垂死的德性之维[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Petkova,V.I.&Ehrsson,H.H.,PLoS ONE 3,e3832(2008).
[8]Guterstam,A.,Petkova,V.I.& Ehrsson,H.H.,PLoS ONE 6,e17208(2011).
[9]Van der Hoort,B.,Guterstam,A.&Ehrsson,H.H.PLoS ONE 6,e20195(2011).
[10]Ehrsson,H.H.Science 317,1048(2007).
颜青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虚拟现实的实验研究对试验哲学的超越”(15ZDB01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课题“实践知性与行动动机”(2015YJA72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