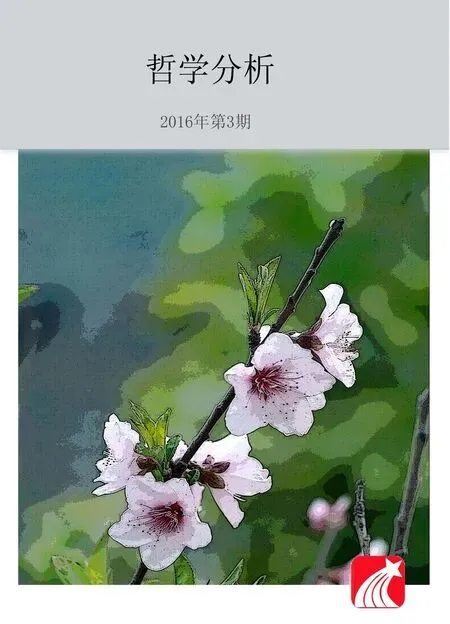认知实用主义问题
[法]让-米歇尔·怀尔(Jean-Michel Roy)/黄远帆、胡杨 译
认知实用主义问题
[法]让-米歇尔·怀尔(Jean-Michel Roy)/黄远帆、胡杨译
摘要:上世纪50年代,随着认知主义假说的提出,关于认知科学的讨论聚讼纷纭。由于认知主义假说面临着诸多问题,如今,认知科学正经历着一场改造运动。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认知实用主义是重要的竞选者。认知科学需要一个认知实用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可以通过“行动核心性假说”来刻画,这一假说既是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需要考察对该假说可能的反驳:一种反驳质疑这一假说的充分性(代表是皮埃尔·施泰纳),另一种反驳诘问该假说的必要性(代表是杰瑞·福多)。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讨论刚刚起步,在行动理论、实践知识理论等方面还进一步开拓这个议题。
关键词:认知科学;实用主义;行动;实践知识
一、 定义认知实用主义问题
(一) 问题的语境:认知科学的根本危机
宽泛而言,认知官能所指涉的能力或多或少与知识相关。认知官能主要包括:知识习得能力,比如感知能力(perceptive faculties);知识储存官能,比如记忆力;语言使用能力,比如语言(事实上,语言作为一种能力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尽管人类能够最为淋漓尽致地展示这些能力,它们却不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试图在认知物种与非认知物种间划出清晰界定是万难的。一些当代理论家主张具备认知能力可以与生命实体等量齐观*这一观点由认知生成论者(enactive)提出,参见E. Thompson,MindinLife:Biology,Phenomenology,andtheSciencesofMin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如果他们所言为真,那么认知与非认知的界限可以通过生命实体与非生命实体来区分。照此,我们将那只掉落于牛顿头上的著名苹果归属到认知系统内,是不合理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任何试图以认知官能来解释苹果的运动的理论都极富争议。
尝试给出一个认知官能的科学理解的雄心由来已久。或者说,自人类开始在科学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科学家已悄然埋下这个雄心的种子——构建立足于科学界广泛使用术语基础上的认知理论或认知科学。此外,长久以来,哲学便与认知问题如葛藤般互相纠缠、系连。因此,哲学史上也充满各种对认知官能科学解释的远见卓识。然而,随着时代前进,科学范式几经变更,大多哲学史上的尝试已为当代的科学标准所摒弃。
虽然有稍许争议,但学界一般都为,对于认知的科学探索的汗漫历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遭遇了剧变。从那时起,由于认知主义假说(cognitivism关于认知的信息理论或计算理论)的提出,历经洗礼的认知科学终于步入正轨。当时,这一认知研究领域的惊天之变得到诸多响应,尤其是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ner)对这一想法的普及做了可观的工作*参见H. Gardner,TheCognitive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此外,也有认知主义者粗泛地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小写的类别名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些鼓吹制造了一个幻象:人类开启了对于认知官能科学知识史无前例的探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应当将“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大写,是为了强调它只是众多试图探索认知现象的道路之一。“认知科学”的“新”至多只是类似与伽利略物理学的“新”,换言之,以伽利略自己的话来精确表达:“以新的对话来讨论旧的话题”。
当然,我们并不就此认为认知主义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不认为在它全面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问题。但认知主义确信,他们已经获得关于认知现象(隐含地被理解为对认知感官的运用)正确的科学解释基本原则。换言之,以当代争论语境中的标准术语来表达,我们终于找到关于认知的科学的适当的基础。然而,这一美好愿景很快破灭。不久,认知科学便开启了充实的改造历程,期间的各种复杂、坎坷仍待进一步澄清。改造历程中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对认知主义理论诸多局限和困境的批判推动了对认知科学的改造。其二,认知科学对自身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这些改造让我们重新反省认知主义解释的一些基本教条,包括:它如何界定计算的概念、大脑的角色作用、意识现象以及身体或者外部环境。许多人宣称认知主义假说已是一潭死水。虽然,严格意义上的认知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落幕,但故事并未就此打住。如今,仍有不少认知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活跃在认知科学的舞台上,杰里·福多(Jerry Fodor)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对于改造后的认知科学给出了系统的批判*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外,又有另一股新计算主义的浪潮滚滚而来*参见M. Milkowski,ExplainingtheComputationalMind, Mass.: MIT Press, 2013。。毫无疑问,关于什么是认知科学基础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一轮新的论辩已经拉开帷幕,时至今日,这个话题可谓历久弥新。很难说在认知科学改造进程中没有一个理论选项能够凝聚认知科学共同体。要判断是否存在这个理论选项,取决于我们如何剖析与解释认知科学的发展进程。
事实上,如若要接受存在一个团结认知科学共同体的理论选项,我们只能将这些候选者理解为那些对新正统的挑战者。新正统是在认知科学进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有时我们将之称为神经认知转向(neurocognitive turn)。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90年,认知科学内部对于批判认知主义达成了共识。这一批判主要关涉认知研究中的大脑探究。从那时起,神经维度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认知主义。神经科学研究与认知主义不同,前者主张一个充分的解释模型应该通过新的理论假说限制认知主义的现有假说:其倡导的新假说阐述的是认知官能施行过程在大脑神经系统中的施行方式,而现有假说则是针对认知官能施行过程、由心智词项表述的高层级假说。神经科学研究将这些认知官能运行过程的神经生物维度纳入到了认知科学中。虽然认知主义秉持着大脑承载认知过程这一的自然主义信条,但他们并未涉足神经领域研究。事实上,认知主义者认为,关于大脑执行这些过程的研究并不属于认知科学的范围。认知科学仅关注认知任务在某个抽象层面执行时,大脑中发生了什么。所以,它必然是更为普遍的。神经认知维度进路是对认知主义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个进路一度盖过了认知主义的风头,从而将认知科学转化为如今盛行的认知神经科学。
无论如何,对于认知主义的修正并未止步于此,我们可以说,这项事业任重而道远。该事业的后继者不断,例如,帕特里夏(Patrica)与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的著作都将矛头直指经典神经认知科学*参见P. S. Churchland and T. J. Sejnowski,TheComputationalBrain,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2。,他们批驳经典神经认知科学在激进的外表下,实际与“认知主义”是一丘之貉。认知神经科学要么仍旧诉诸表征主义,要么忽略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具身进路),要么误解了外部环境的作用(新外在主义),还有的则低估了“行动”的重要性(生成主义)。
正是在这些特定语境下,当代认知实用主义浮出水面,成为竞争“心智的新科学”*参见M. Rowlands,TheNewScienceoftheMind:FromExtendedMindtoEmbodiedPhenomenolog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0。头衔的众多候选者之一。与其他竞争者一般,认知实用主义有着内部多样性,同时呈现出各种程度的激进主义。
然而,认知实用主义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中产生是一回事,而它与之有内在联系则是另一回事。事实上,这些问题是所有尝试解释认知官能的理论都会遇到的根本问题,其中不仅有当代的认知科学,也包括它的各类变种。鉴于此,区分广义的认知实用主义与当代语境下特殊的认知实用主义极有必要。本文将聚焦于后者,但本文并不给出一个最终答案,而是尝试做一个比其他文献更为精准、确切的刻画,而这一刻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要做出这一刻画,无法跳过认知实用主义的一些普遍问题和认知实用主义的其他特定形式(比如二十世纪哲学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复兴)。虽然,实用主义思想复兴并不分享当代认知科学的理论旨趣,但在他们思想中却自然而然地涉及了认知官能的科学理论的基础。
(二) 问题的内容
从最宽泛层面看,认知实用主义的问题是他们应当采纳何种基础的理论问题。这个基础应当具备足够的科学性。这个基础应当既是建构的,也是规范的。具体来说,实用主义维度如何与这个基础相关联。有必要强调,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这一理论内容的基本概念与原则,这样只会陷入对科学理论基础解释的狭隘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关注这一基础的其他关键面向,例如这一理论研究的界限,判断哪些问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判断这一理论应当依据哪些科学概念等。一个关于认知的实用主义理论可能在上述各方面都不同于非实用主义理论,而这些方面恰是构成一个科学理论的关键要素。
除去建构维度和规范维度,认知实用主义问题还有一个批判维度,这个维度关系到实用主义进路能够多大程度介入到认知现象的研究。这尤为关键,因为认知现象也许已经被纳入认知理论研究的领域。这是一个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这些认知理论是否在实际层面(de facto)上隐含地或明述地采纳了实用主义资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是以何种形式采纳的,以及采纳了多少程度?
建构层面(规范层面)与批判层面休戚相关,任何对认知实用主义的透彻考察都应当顾全这些维度。要回到以上这几个问题,我们从批判性评估对这些问题的已有答案入手。此外,一个健全的理论应当能够精确显示与其他理论的差异,以及彰显其本身的优势。
如前文所述,通过考虑认知实用主义问题与认知科学的确切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限定这个问题。从建构层面而言,这种限定能够决定认知科学是否应当采取实用主义进路,以及通过何种形式采取。从批判层面而言,我们审查实用主义维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到认知科学,以何种形式介入,以及已经取得了那些成就。
从批判层面而言,存在诸多先天可能性。有可能,认知科学拒绝认知实用主义的指导作用,而这一抉择是正确的。或者,这种排斥是一种谬见,因此需要得到修正。或者,认知科学接受认知实用主义,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融合。又或者,他们只是选错了实用主义的种类,那么,他们无须全盘抛弃实用主义,而只需要做出一些更正。事实上,这些可能性正是当代关于认知科学与认知实用主义关系争论的峥嵘处。
有一事毋庸置疑,如果认知科学发生转变,哪怕只是部分变化,那一定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所致。几乎所有认知科学的信条都与认知实用主义的观念(暂不论其最终定义)互为扞格。鉴于此,认知实用主义问题与认知科学紧密相关,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在认知科学对自己早期基础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实用主义转向?如果是,它是以何种形式发生的,并且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
下文中,我们抽取出这个争论中最具代表的一例。福多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是这场对峙的主角,他们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事实上,约翰逊的立场颇为复杂。他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中叶起,认知科学踏步前行,迈向对认知官能的具身维度研究,而在这一方向上,它无法避免与美国经典实用主义相遇,典型代表如詹姆斯和杜威。有鉴于此,他认同认知科学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实用主义转向,而且是和早期实用主义的交汇。他将其描绘为从“第一代”认知科学向“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过渡。第一代认知科学“与实用主义的设想背道而驰”*参见M. Johnson, “Cognitive Science”, inACompaniontoPragmatism, edited by J. Shook & J. Margolis, Cambridge: Blackwell, 2005。,此外,“他们理论所依据的一些二元分立和错误的哲学假说,恰是实用主义几十年前竭尽思虑所要挑战的”*Ibid., p.372.,而第二代认知科学则“与实用主义共享诸多信条”*Ibid.。由于这只是对经典实用主义观点的重新发现,而非在全盘接受的意义上回到经典实用主义,所以,这一改造更多的只是实用主义转向的序曲,而非华章。只有当第二代认知科学自我意识到与古典实用主义的切近,并且古典实用主义的继承者也关注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才可以说第一代认知科学到第二代认知科学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维度转向。这一转向正于当下发生着,约翰逊认为,这一转向还有更多的可发挥空间。他指出,我们可以发现“在哲学语境中,美国实用主义者(如詹姆士和杜威)最早给出了对具身性的恰当阐释”*参见M. Johnson & T. Rohrer, “We are Live Creatures: Embodiment,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the Cognitive Organism”, inBody,LanguageandMind, 1, 2008, pp.17—54。,经典实用主义对具身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澄清与深化认知实用主义对认知主义的取代。
福多与约翰逊在很大程度是能达成共识的,尽管这些共识是表层的。在福多2009年的著作中,他对认知主义的捍卫可谓有解惑之效*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他也认为认知科学发生了一个隐含的实用主义转向,之所以为隐含转向,是因为这个转向并未明述地诉诸经典实用主义资源。他认为这个转向早已有所酝酿,并且福多描绘的转向规模远远大于约翰逊的描述。事实上,福多认为实用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是通过人工智能“对计划与行动”的重视,才得以进入认知主义的城门的。最终,认知科学被实用主义侵蚀殆尽,“无论是人工智能、哲学,还是认知心理学,如今的主流已经被实用主义占领”*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p.8.。在福多看来,这个绵长的实用主义转向,更多的是实用主义影响的传递,而非对经典实用主义的再发现。这一传递间接地影响着其后续者,且这一传递是离散的,很少打着“实用主义”的旗号。
福多与约翰逊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这一转向的态度。约翰逊主张,我们应该进一步推进这个转向,并且更直接明述地将之与经典实用主义关联起来。而福多则提出,我们应当抛弃这一转向,“实用主义也许是哲学发端以来最糟糕的观点”*Ibid.。
(三) 界定认知实用主义本质的初步工作
在一个清晰而精确的定义阙如的情况下,无论是理论还是批判层面,我们都很难满意地解决认知实用主义的问题。如要明确一个认知理论能够容纳实用主义维度,以及以何种形式容纳,那么我们势必要知道什么是认知实用主义维度,以及它的各种可能变种。至少在理论层面,认知实用主义的定义优先于认知实用主义的建构。理论而言,我们可以把定义工作作为这个问题最原初的构成元素,而非一个分离的准备阶段工作。
无论我们如何建树理论优先性,我们仍旧无法忽视认知实用主义的批判维度。要在实际层面严格解决认知科学的实用主义维度的研究问题,定义工作将起引导作用。因为,认知实用主义义理探究完全依附于我们如何理解认知实用主义,这是它运作的基础,这点在福多与约翰逊的争论中已经显明。如果有人像福多与约翰逊那样,认为古典实用主义与认知实用主义之间有内在关联,那么这一关联只能通过剖析认知科学的进化过程与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之间的理论相似性,以及实用主义运动对认知实用主义的启发性等层面上得到揭示。如果我们割裂认知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的关联,那么就无须考虑这些因素。
(四) 认知实用主义转向问题的陈述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通过从具体的认知科学维度来考量,认知实用主义的问题能够更精确地表述为认知科学的实用主义转向问题。我们可以从下述三方面来理解:
1. 定义问题:如何在最普遍层面刻画一个关于认知理论基础的实用主义假说?
2. 解释问题:在认知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它在多大程度采纳了这个实用主义假说,从而施行了实用主义转向?以及它是以何种形式采纳的?
3. 规范问题:认知科学是否应该坚持采取各种形式的实用主义(其中它可能已经采取了某些),或者它是否应该采取某种可能的实用主义形式,如果是,具体应是那种形式?
可以说,即便我们作出了如上规定,这仍是一个持续生成、不断展开的问题:福多与约翰的论辩;同一时期,福多与布兰顿(Robert Brandom)的纷争;施泰纳(Pierre Steiner)在法国也发起了令人瞩目的讨论。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过于局限,并不如其他认知科学基础论题那么影响深远。此外,他的局限性还体现于:如果仅仅通过古典实用主义来诠释它,它的核心问题并未能全盘托出。如此一来,一些更根本的议题(例如行动核心性假说、认知科学的生成性维度等)则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这些议题既没有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表达,也没有引用古典实用主义资源,但他们是认知实用主义不可剥落的面向。换言之,这之所以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因为它并未被充分阐释,而其已经阐释的部分也没有一个可恰当识别的范围。此外,认知实用主义的本质也仍待界定。鉴于此,对认知实用主义的这三个关键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审查是当务之急,而这对重新开启认知科学基础的讨论尤为重要。
由于愈发意识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性,以及注意到仍有许多待做的工作,我逐渐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投注到了这个领域。从2008年起,通过一些个人或合作研究,我展开了认知科学实用主义转向的研究。这些研究很大部分都在社会与科学研究院(JoRISS)主持下进行,这是一个里昂高等师范学校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立的中法合作平台。而其中的知识与行动中心实验室(KAL)主要致力于处理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实用主义与理智主义在认识论领域的争论的复兴。我们可以区分出这个研究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这四个阶段为当前的研究起了补充作用,有必要在此对之作出简要概述,以便更好理解当前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尝试以行动作为意向性的本质来展开实用论意向主义(pragmatist intentionalism)的定义。实用意向主义被视为大多数认知状态与过程的基本要素(作为状态的一个序列)*主流认知科学哲学主张一种改良的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十九世纪维也纳哲学家)理论,他们宣称意向性是认知属性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他们将意向性理解为对某物的关联,而这一关联是一种客观实体。,此外,这一阶段还致力于区分这一本质的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立足这些工作,我们可以检验行动的认知神经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能够解释为对这一定义进行支持(实用主义意向性提出者认为能够支持)*参见J. M. Ro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the pragmatist approach to intentionality”, inNaturalizingintentioninAction, edited by F.Grammont, D.Legrand & P.Livet,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行动的认知神经研究旨在揭示行动在自然认知系统中的优先地位。实用意向主义既是一个定义,也是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类型学,第二阶段中,通过实用意向主义这两个特征,我们既能拓宽研究的范围,又能够通过聚焦知觉意向案例来缩小范围。同时,我们又将生成性理论作为主要批判性检查对象,尤其是诺伊(Alva No⊇)的版本。*参见KAL Workshop: Cognitive Pragmatism, June 2011,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第二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诺伊关于行动与视觉感知关系的生成主义多大程度能够支持认知实用主义,它的接受度又有多少?*参见J. M. Roy, “Pragmatisme cognitif et énactivisme”, inIntellectica:Pragmatisme(s)etsciencescognitives, edited by P. Steiner, Vol.2013/2。在第三阶段,我们继续关注行动理论的研究。不同于第二阶段仅限于行动认知神经科学的特定领域研究,第三阶段将研究扩展到整个当代行动理论。*参见KAL Workshops: The Nature of A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eptember 2011; Reconceptions of Action I,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Lyon, March 2012; Reconceptions of Action II, October 2013, University of Milano。我们可以这样表述第三阶段的研究:上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关于行动本质讨论的大变革,能够多大程度(无论明述还是隐含)支持行动作为行动理论与认知实用主义核心的观点。最后第四阶段,另一个认知科学领域论题也与之高度相关,即概念理论。而这也关涉到当下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争论,即福多与布兰顿之间的争论。*参见KAL Workshop: Concepts and Pragmatism, June 2013,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3年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行动的认知神经研究著作,这可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问题进展的一个有趣标志。虽然它们独立于认知实用主义研究,却又合流于一些极其狭窄的河道。事实上,在认知科学的一脉中,恩格尔(Andreas Engel)与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篇题为《何处安放“行动”?认知科学中的实用主义转向》的论文,该文以上文中所建议的方式梳理了认知实用主义问题与认知科学的关系。第一,他们将之视为认知科学内部发生的转向。第二,他们通过行动的核心地位来界定认知实用主义。认知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的关系则是其次的。第三,他们实际区分了两类问题:解释性问题(interpretive question),即认知科学是否发生了这个转向;规范性问题(normative question),即认知科学是否应该经历这个转向。最后,在最近关于行动的神经认知研究的结果基础上,他们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肯定回答。
选择以行动的核心地位来界定认知实用主义的假说还须进一步的检验。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方面,比之当前的文献,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更为殷实、有说服力的陈述,例如前文提到的恩格尔等人的工作。此外,我也有幸发表过相关论文。*参见J. M. Roy, “Pragmatisme cognitif et énactivisme”。其次,最近出现的不少对这个假说的反对声音都有回应的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发展关于概念实用主义的理论时,认知实用主义是以能力之知(knowing how)的形式介入,而非行动核心论。这个明显的差异引起了如下关键问题:这个能力之知版本的认知实用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和行动核心论版本的认知实用主义有何关联?它们是否有实质的区分,如果是,是什么?它们可能的区分是否使得他们互不相容?如果是,我们应该再多大程度上重审行动核心论的认知实用主义的定义,从而能够容纳能力之知版本的认知实用主义?这些问题十分棘手,有待更为广泛、技术化的研究。尽管这些问题对认知科学整体发展至关重要,当前的研究视野却并未聚焦这些问题,而本文则力图呈现这些问题,并且在一个宽泛维度提供解决方案。
二、 行动核心性假说
(一) 定义以及定义怀疑论
第一项任务主要是形成建立于行动核心概念的认知实用主义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达到。既可以是描述的形式(descriptive),也可以是规范的形式(normative),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此外,我们也可以通由传统的充分必要条件界定范畴的方式来形成定义。再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家族相似性或原型论来界定(由后期维特根斯坦最早提出)。
当我们初步处理什么是定义怀疑论时,以上可能都应该纳入考量。定义认知实用主义是否可能?
事实上,对能否定义认知实用主义的怀疑主要是由对经典定义论的批判着手的。施泰纳在最近编辑的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论文集*参见P. Steiner, “Pragmatisme(s) et sciences cognitives: considérations liminaires”, inIntellectica:Pragmatisme(s)etsciencescognitives, Vol. 2013/2。的导言中发展了一种来自异质性的怀疑主义论证(heterogeneity)。这个论证主要宣称,实用主义这个词项由于异质性程度太高,它不可能具备充分必要条件,换言之,它超越了经典定义理论的限定。施泰纳提到拉夫卓尔(Arthur Lovejoy)在1908年区分了十三种经典实用主义,而施泰纳认为,在当代,认知实用主义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各种形式:改良实用主义、激进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更新的实用主义、分析实用主义、后分析实用主义,等等;鉴于这一持续的纷繁复杂的状况,为普遍的实用主义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几乎成为一种矛盾”。那么,对于实用主义的认知理论也是如此。这样的异质性怀疑论的论证力度是有待商榷的。其一,即使其论证有效,它只能显示,我们无法提供一个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经典描述定义,但我们仍然有可能提供其他形式的描述性定义(例如,原型论),我们也可能提供一个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经典规范定义。此外,从表面的异质性推断经典定义的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除非他能够指出这种异质性不仅是表层的,也是深层的,否则我们无法排除存在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再者,施泰纳的论证中似乎错误地理解了描述性定义。一个描述性定义无法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事实上,我们对一个词项的使用通常由一个规范指引。描述性定义与规范性定义之间的对立反映了两类解释之间的区别,前者尝试呈现规范在事实层面(de facto)上的运作,后者尝试通过建立新法则(de jury)来展开解释。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表明,一个词项关涉的领域的表层异质,并不能取消其深层的同质性,从而否定给出定义的可能性。实用主义这个词项在事实层面的使用形形色色,但并不能推论这些用法都是合法的。通过进一步审查,我们也许会发现这一表层的异质性也许只是(并且仍然是)一种语词的滥用,也就说对这个用法的张冠李戴。通过实际维度使用来规范这个概念的使用,是这个谬误的诱因。也有可能,这些使用包含了多义性,也就是说它的使用由多种规范支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这些不同使用规范分别下一个经典定义。*如下文所述,这似乎是施泰纳最终采纳的结论。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对经典定义论的怀疑是无源之水。我尝试以行动核心性假说来定义认知实用主义,这个定义既包括描述维度,又包括规范维度。
行动核心性假说建立在一些信条上,这些信条旨在支持将行动核心论作为认知实用主义的充分必要条件,从而以此作为评断认知实用主义的标准。我们试图为认知实用主义提供经典定义,也就是说提供一个区分认知实用主义与非认知实用主义的界定方式。立足于这个界定,我们可以说,行动是认知活动的核心,既是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认知实用主义不具备其他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只是这些其他条件不是它的专属。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进一步精细化行动核心论观点的可能性,而这种精细雕琢不会使这个定义陷入困境,相反会使之更为确切。
此外,在关于事实层面的使用上,认知实用主义大多都与行动核心论相关。换言之,这是对这个词项使用的主要规范。而不符合这一规范的使用有两种情况:要么是对这个词项的彻底误用,要么是在多义层面的使用。故此,有些被冠以认知实用主义头衔的理论是张冠李戴,另一种则是在一种与之不相关意义上的使用。
第三,虽然本文尝试提供一个同时容纳描述维度与规范维度的定义,但行动核心论无疑首先是作为一种规范性假说。理论上,即便在描述层面失败,也不影响其有效性。换言之,这个理论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逻辑空间内可以提供一个对认知的可能解释,这个解释将行动放置于核心地位。
最后,有必要指出,以上三个信条,可以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作为实用主义与行动关系的信条。也就是说,这个假说的范畴可以进一步扩大,适用其他任何领域的实用主义理论,只要它宣称行动的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挂着实用主义旗号,却违背行动核心性假说的理论实际上并非实用主义(或者不是在一种相干层面对实用主义的使用)。
(二) 假说的主要内容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捍卫了对认知实用主义给出定义的必要性。但我们仍需进一步澄清、辩护这一假说的内容:行动作为认知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在认知实用主义中借用经典实用主义的名称是否是可辩护的?
鉴于诸多版本的认知实用主义,我们可以对行动核心性假说持有多种表述方式。最普遍层意义上的界定:行动与其他认知现象*或者仅从认知现象出发(如果行动本身也是一种认知现象),出于理论简化考量,我们暂搁置这个区分。紧密相扣,并且影响其他认知现象的本质与功能。
假使这个定义是规范层面的,那么我们应该在脱离其之前使用语境的情况下考虑这个问题,比如,我们不应该将实用主义运动纳入考量,尤其是经典实用主义。但如果要考虑描述维度,那么我们就不能如法炮制。从一种解释性假说角度出发,实用主义这个词项与行动核心一直紧密扣连,这个解释性假说旨在辩护为何行动是认知实用主义的重中之重。鉴于我们之前区分的规范维度与描述维度,这个辩护并不能作为最有利的辩护论证,因为它只是描述维度的辩护。
即便如此,在描述维度,我们还能提供其他的论证。首先,我们来看经典实用主义。事实上,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宣言中清楚地彰显了行动的核心地位。追随皮尔士的脚步,詹姆士在《实用主义是为何意》一文中将实用主义原则论述为关于思想内容本质的理论(表达这些思想语句的意义),而这个说法使得实用主义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难分难解。詹姆士承认自己在实用主义这个传统下,是皮尔士的学徒。从这个意义来说,实用主义将思想的内容(以及组成这些内容的概念)与潜在的行动等同了起来:“……要发展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决定它适合产生何种行为(conduct)导向:这个行为对我们而言是其唯一的意义,……我们不可能拥有撇去实践的意义。”*参见W. James,Essaysinpragmatism,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07/1948。据此,我们可以说,经典实用主义首先(最重要)是关于认知的,它的理论与我们思想内容相关,从而切入到了广义实用主义与认知实用主义的区分。在当代,对此的争论也是依此路线进行的。当代舞台上最活跃的两个人物是福多与约翰逊。福多如此刻画实用主义:“心智的独特功能是由行动指引的”*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p.13。,此外,“对思想更为重要的不是思想与其表征对象的关系,而是其与指引它行动的关系”。*Ibid., p.8.类似的,约翰逊认为“认知是一种行动,而非心智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参见M. Johnson & T. Rohrer, “We are Live Creatures: Embodiment,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the Cognitive Organism”, pp.17—54, p.26。,更具体而言,“一个特殊种类的行动——这是一个运用预见手段的回应策略,为了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实践问题”。*参见M. Johnson & T. Rohrer, “We are Live Creatures: Embodiment, American Pragmatism and the Cognitive Organism”, pp.17—54, p.26。据此可以推断,他们都认为当代认知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三) 类型学定义
上述认知实用主义有多种形式,然而通过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揭示其一般要义;
第一,我们认为“行动”占据核心(essential)地位,于是,与之相联系的有关行动的概念也同样如此。
第二,反过来说,“认知”也具有核心地位。
第三,“行动”以何种方式对于“认知”具有核心意义,即是说,前者在哪个方面对于后者具有核心意义。
在此基础上,认知实用主义的类型学定义即便不是难以企及至少也是高度复杂的。之前提到过,在怀尔(2010)*参见J. M. Ro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the Pragmatist Approach to Intentionality”, inNaturalizingintentioninAction, edited by F.Grammont, D. Legrand & P. Livet,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中,我探究了该类型学定义的一个部分;针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一方面靠的是行动的动力要素(the motor elements of action)与行动的意向要素之间的区分,这一区分已得到广泛接受;另一方面需要聚焦于横跨各认知官能界限的意向性——即使意向性不是一个认知现象的普遍(universal)特征,它也算是一个一般化(general)特征。在这一研究中,我们对实用主义下的认知意向主义(a cognitive intentionalism of pragmatist kind)进行了第一个层面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以此得到了一种认知理论,它既容纳了某种形式的布伦塔诺论题——意向性是认知现象的关键特性,也涵盖了“行动对于意向性具有核心意义”的理论原则。这一认知理论最重要的成果是区分出了“行动核心性”的四种形态以及形态下的子类,我们如下概括:[PI代表实用论意向主义(pragmatist intentionalism)]
PI1:在意向性与认知现象的关联之中,行动具有核心意义。
PI2:对于意向性的本质,行动具有核心意义。
PI2.(1):意向性的本质相关于行动的本质。
PI2.(2):意向性的本质从属于行动的本质。
PI2.(3):意向性的本质整合了某些有关行动的特性。
PI3:决定意向性,行动具有核心意义。
PI4:自然化意向性,行动具有核心意义。
第一种形态认为,在对认知现象进行理论考察时,意向性是否是一个与认知现象关联的性质,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无论是运动(movement)还是意图(intention),两者均起着基础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对意向性具有核心意义。因此在这第一层意义上,实用论意向主义(pragmatist intentionalism)认为,意向性独特地,至少是基础性地关联着我们对行动的探究。
一旦我们有理由建立起意向性与认知理论的关联,则会得到上述第二种形态,即行动对于意向性的本质具有核心意义。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提及第二种形态下各重要子类,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对视觉感知(视觉感知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意向性)的研究都论及了这些子类。
在第一个子类中,我们通过感知的意向性对象与行动目标之间的相关性来刻画行动的核心性。大致可以如此阐述这一观念:当我们在进行视觉感知时,被视物的所有主要特性让某一行动变得可能。换言之,被视物提供了潜在的行动。第二个子类更进一步,认为视觉官能实际上从属于行动,即是说,想让行动变得可能,视觉就要开动起来;“看”以便于(in order to)“行”。第三个子类再追加一步,把视觉归整到行动上,其主张视觉与行动的同一性;虽然这种同一性本身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用“整合关系(integration terms)”来解释这种同一性则最为合理:行动远非与视觉相分离,而是与视觉联系紧密,紧密程度之深则可以让我们把视觉视为行动的要素之一。哲学家诺伊把他所主张的理论称作视觉感知生成论(an enactivist theory of visual perception),我们可以恰当地将其视为感知实用主义的一种理论形式;*参见J. M. Roy, “Pragmatisme cognitif et énactivisme”, inIntellectica:Pragmatisme(s)etsciencescognitives, Vol.2013/2。他在为该理论辩护时,充分地领会了上述区分的重要性,他强调,生成论视角(enactivist perspective)的特别之处,就他来看,并不是要把视觉感知变成行动的仆人,而是要把它变成行动的构成要素。比如他写道:“生成论研究进路的基本主张是,感知者的感知能力部分地由感觉运动的知识(比如,感觉刺激随着感知者的运动进行变化,感觉运动的知识就是我们对其变化方式的实践领会)而构成。生成论的研究进路并不主张,感知是为了(is for)行动或者为了(is for)引导行动。”*参见A. No⊇,ActioninPercep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第三种形态说明的情形是,行动对意向性有约束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行动对于意向性有核心意义,而这种核心意义的主要体现,便是行动为意向性的切实存在提供了可能。以此观之,没有行动能力的实体(entity)同样也没有意向性。
最后,第四种形态构想的是,在把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行动也能具有核心意义。这种核心意义体现在我们解释如下问题的时候,即一个实体是如何通过一些自然属性(无论这些属性是什么)而拥有意向性属性的。这里的解答是,只有具备行动能力的实体才能让理解这两类属性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
只要不断修正和充实我们所涉及的三个参数(对行动的分析,对根本性的分析以及认知现象的类型)的任意一个,怀尔(2010)初探的理论成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向多个研究方向延伸。如果我们保留关于行动的一般观念(我们的理论成果奠基于这一观念之上),同时用意向性代替纯粹的(sheer)认知性,那么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明白,那些认知实用主义的一般类型是如何获得的。在“行动核心性”的第一种形态中,认知实用主义被构建为一种认知理论,其中,要想决定哪些现象可被视为认知现象,行动的维度具有基础性价值。在第二种形态中,认知实用主义的理论主张是,认知总体上相关于、从属于、整合于行动。第三、第四种形态分别认为,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属性(不只是意向性)被行动所决定,它们的自然化过程依赖行动。
三、 质疑行动核心性假说
“行动核心性”试图捕捉认知实用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这些与众不同之处可被理解成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这些独特性质也是认知实用主义的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行动核心性”原则上主要会遇到两类反驳。一类质疑“行动核心性”的充分性,另一类质疑其必要性。实际上,在关于认知实用主义的当下讨论中,“行动核心性”会同时受到这两类挑战。在何种程度上这些挑战确实让“行动核心性”陷入困境?这虽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要务之一是我们应该不断推进对认知实用主义问题的研究。鉴于此,我接下来会分别考察上述两类质疑,它们在我看来尤其重要。
(一) 对行动核心性之充分性的质疑
之前提到,施泰纳引入了一个怀疑论观点,即“我们很可能并不具备界定实用主义的充要条件”*参见A. No⊇,ActioninPercep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12。。施泰纳所使用的异质性论证(the argument from heterogeneity)实际上也在暗自指摘行动核心性假说(他认为行动核心性假说并不满足认知实用主义经典定义的充分条件)。施泰纳确实承认,在对认知实用主义这一观念的实际运用中,作为一个认知理论的认知实用主义要想名副其实,就必须包含行动核心性。但是他不认为行动核心性是认知实用主义的充分条件,也因此不承认它是认知实用主义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性质,更遑论它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性质了。恰恰是施泰纳的这种否定态度让他最终认为,当下的“认知实用主义”是一个极度异质性的短语。
施泰纳质疑行动核心性假说的充分性,而在具体考察其质疑之前,我们需要事先强调两点。第一点,通过分析实用主义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关系,施泰纳尽管推进了他的批判,然而他所设想的行动核心性假说涉及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而不仅仅是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这个区别并未造成任何理论后果,因为他的分析显然针对的是概念上限定性更强的认知实用主义,同时,这个区分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可略去不论。第二点则意义较为深远,施泰纳认为行动核心性是一种界定认知实用主义的描述性假说,而不是规范性假说。根据上文的分析,这意味着在施泰纳看来,行动核心性假说试图描述那些特殊的充要性质,它们事实上规定着“认知实用主义”的实际用法。
施泰纳的批判实际上分为两步,它们互不相同却又十分类似。第一步,施泰纳主张行动核心性假说并不充分,因为我们并未充分澄清行动概念。施泰纳对此并未展开论证,只是指明了论证的主要方向,即持有行动核心性这一性质的诸理论并未澄清行动概念,这事实上导致这些理论难以成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合理地展开其论证:
断言一:如果某些理论启用行动核心性这一性质,但又未澄清行动概念,那么这些理论就不被看作是认知实用主义的理论形式。
断言二:因此,启用行动核心性的理论之所以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这是因为行动概念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而这进一步的澄清使得行动核心性成为一个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
施泰纳还解释道,关于行动概念,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其实是它的语境维度(行动的环境、社会及其经验),同时,我们不能把那些语境要素视为特殊的、可有可无的、补充行动的东西。
推动第二步批判的是一个并未(但是需要)明述的预设:行动核心性假说志于界定认知实用主义,然而上述那般对行动概念的澄清难以让行动核心性假说保留这份雄心,因为经过这般修缮的行动核心性还是难以成为认知实用主义的一个独有的事实上的充分性质;认知实用主义至少还需要一个附加性质。于是,第二步批判为此主张:我们至少要假定一个附加性质。相较于之前一步,施泰纳对该主张的论证更为详实,然而论证逻辑是相同的,因为他同样指出,对于所有那些持有行动核心性同时又充分澄清行动概念的理论,我们难以将它们都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类似于之前的论证形式,他这里的论证仍然可以这样合理地展开:
断言一:如果某些理论诉诸于行动核心性这一性质,同时又充分澄清了行动概念,那么这些理论仍不被看作是认知实用主义的理论形式。
断言二:因此,诉诸于行动核心性且充分澄清行动概念的理论之所以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这是因为行动核心性还至少关联一个其他性质,而就是这种与其他某一性质之间的关联才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所独有。
施泰纳为这一附加性质的必要性辩护;并且,针对这个附加性质的相关问题,他又再次提出了一套相当具体独到的见解。事实上,他首先强调认知实用主义所独有的不只是一个性质,而是一个由七个性质组成的集合,并且,施泰纳细致地刻画了这七个性质,在这里对其刻画细节存而不论。其次,这七个性质只在析取的意义上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只要把行动核心性与其中某个性质组合(combination)起来就足以获得认知实用主义的特有性质了。这样一来,认知实用主义所独有的就不只是一个复杂性质,而是许多性质,至少有七个。最后,施泰纳还认为,并不是那个被组合起来的附加性质展现了认知实用主义的特性,这个特性其实是由行动核心性与附加性质之间的组合展现的,附加性质本身对于认知实用主义并无特别之处。因此,根据施泰纳的分析,认知实用主义的特性存于行动核心性与其中某个附加性质的组合中,而七个附加性质本身难以体现认知实用主义的特性。
施泰纳提供的假说选项区别于行动核心性假说,充分领会两者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两者均承认,行动核心性是所有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必要性质。然而行动核心性假说更进一步,它主张行动核心性是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充分条件,因此也是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而施泰纳的假说拒绝这一步。他认为,第一,在认知实用主义理论中,澄清行动概念要通过分析行动语境而展开;第二,在七个附加性质之中,至少要有一个性质补充行动核心性。这第二点要求意味着,即使行动概念得到进一步澄清,我们一般接受的行动核心性也难以被广泛地当作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同时,第二点要求也意味着,没有其他某一个附加性质能够胜任。这样一来,认知实用主义成为了一个极度异质性的表达式,也就是说,有许多独特的性质一道掌管着“认知实用主义”的用法,而这些独特的性质如何可能则取决于行动核心性与七个附加性质的组合。
我们是否接受施泰纳对行动核心性假说的两重批判?他提出的两重修订版本是否能成为一个替代选项呢?
首先,关于澄清行动概念的问题,我们就有很多理由去怀疑其批判的有效性及其修订的充足性。
第一点理由是,在施泰纳第一步批判中,断言一认为,如果行动的概念没有得到充分的澄清,那么行动核心性就不能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的充分性质;换句话说,在施泰纳看来,行动概念实际上总是和“实用主义”关联在一起,甚至与“认知实用主义”的关联更深。而他的主张看上去犯了过度概括的错误,这源于施泰纳关注的是:经典实用主义背景下,“实用主义”、“认知实用主义”等相关表达式在极度有限范围内的使用。在经典实用主义及其后继者那里确凿无疑的东西,放在当代实用主义背景下,就变得可疑得多,后者对实用主义有更宽泛的理解。
施泰纳的批判基础在于,行动概念的确可以在进一步澄清中得以落实,就像在经典实用主义者那里一样,而从上述对此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种可能是,我们能够便且称作“未定的(unspeified)行动核心性”在施泰纳所描述的情况下的确是不充分的。这造成的结果之一,即是我们得到了一种经典实用主义概念下的认知实用主义,在这种认知实用主义看来,一个理论若仅仅主张行动核心性,它是不足以被称作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比如,在杜威看来,伯格森就算不上一个认知实用主义者。以此观之,行动核心性假说陷入了困境,因为认知实用主义的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带有异质性:有些实用主义者支持“未定的行动核心性”,并将其作为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另一些则主张我们要先通过行动语境来澄清行动概念,以此行动核心性才能作为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另一种可能是,未定的行动核心性可以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的充分条件,而对行动概念的澄清只被当作是让认知实用主义名副其实的手段而已。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典认知实用主义会认为,如果某一理论包含行动核心性,那么该理论就可算作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然而这里所得到的是某种认知实用主义,它以一种语境主义方式更为确切地构建了具有核心意义的行动概念。换句话讲,由行动核心性假说所界定的“认知实用主义”有多种,经典认知实用主义观念只是其中一种。这造成的结果便是,伯格森在杜威眼里是一个与杜威不同类型的、不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以此来看,行动核心性假说并没有陷入困境,因为被引入认知实用主义里的异质性只不过是一个基本性质,它符合某一种认知实用主义的内在要求。因此,这里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排除掉第二种可能性的论证,而施泰纳对此缄默无言。
我们的怀疑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这就是施泰纳不仅没有论证上述第一种可能性为何必要,同样也没有论证相关的行动概念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是认知实用主义的一个独特性质。显然,如果光说有某种行动概念与行动核心性相关,这还不足以说明行动概念就一定是一个独特性质。要成为一个独特的(distinctive)性质,该性质一定是必要的、唯一的(unique),然而必要的、唯一的性质并不能成为独特性质的充分条件,因为并不是所有必要的、唯一的性质都是独特的性质。让我们假说所有的独角兽由于某些必要原因长的都是金角,并且,它们是唯一长金角的物种。然而一只独角兽的独特性质仍然是“只长一只角”,而不是“只长一只金角”,虽然后者是必要的、唯一的。同理,行动核心性也许必然会伴随着某种关于行动的独一无二的性质,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关于行动的独一无二的性质就是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因为这一点需要论证。
然而,施泰纳并没有提供任何我们需要的强有力的论证,如果他那里真有什么论证的话。我们之前重建了施泰纳的第一步批判,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论证很可能意味着:如果与某种行动概念的关联丧失了,那么认知实用主义的实质也将不复存在。换言之,这里好像存在的一个推理是:当某种行动概念与行动核心性相关联时,这一行动概念就必须成为促成认知实用主义的特征,因此也成为其独特性质,介于此,当没有这一概念时,未定的行动核心性自身难以促成认知实用主义。然而,如果“当没有这一概念时,未定的行动核心性自身难以促成认知实用主义”这个事实并不存在,那么这个论证就不是有效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即使有这个事实,论证仍然无效。的确,如果我们假说“没有相关的行动概念,未定的行动核心性自身难以促成认知实用主义”(F)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这会带来多少预计的理论意义呢?我们也许能够说,事实(F)反映的只是一个误用行动概念的例子,虽然这里的误用与之前提到的“滥用”并不相同,“滥用”指的是不恰当地应用一个词项。换言之,既然事实(F)是一个误用行动概念的例子,那么,尽管事实(F)并不支持,但我们也许能够如此主张:包含未定的行动核心性的理论应该被视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这里的理由是,行动核心性作为一个独特性质掌管着“认知实用主义”这个表达式的实际用法。
我们批驳事实(F)的解释,本来是试图从(F)的对立面来分析行动核心性这一独特性质的,而我们只有为事实(F)做一个决断(此“决断”,即没有相关的行动概念,未定的行动核心性自身到底能否促成认知实用主义),才能摆脱我们的对立解释,但是,做这个决断所需要的论证会遇到一个坏循环:我们的论证假装支撑起某个对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的解释,然而这个论证却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实际上需要预设我们对那个独特性质的解释。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怀疑理由是,准确地说,把行动核心性假说视为对认知实用主义这一表达式恰当的描述性定义,这样做意味着许多事实上难以叫做认知实用主义的理论最后都拥有了成为认知实用主义理论的所有理由。于是,那些看上去彼此并无联系的理论,现在有可能变成同一类理论,这个有趣的结果在理论上需要多种说明。
总之,我们首先拒斥了被重构的施泰纳批判的第一个断言,而这接下来会以两种方式影响其批判的断言二。第一种方式是,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可能性:一方面,对行动本质的刻画与行动核心性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未定的行动核心性事实上仍可当作认知实用主义的充分性质,然而,这种可能性不得不被一个尚未提供给我们的论证排除掉。第二种方式是,如果我们执意把澄清后的行动概念当作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那么这将变得毫无根据。另外,已经强调过的是,即使断言一没有争议,施泰纳从中推论的断言二也是有缺陷的,而且断言二的论证有一个坏循环,还需要说明的是,行动核心性假说会发挥一个整合效应,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优势。
所有这些理由组合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施泰纳的批判并不足够有力,我们并不会放弃以下立场,即在一个相当概括的层面上把认知的行动核心性当作我们日常理解里的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施泰纳要求对行动核心性所牵涉的行动概念进行澄清,而这一要求也仅仅是为了界定认知实用主义某个特殊的子类而已,比如经典实用主义下的认知实用主义。除此之外,即使我们对施泰纳批判的拒斥并不完全正确,他的批判还是没有触及一个更为根本的维度,即行动核心性假说的规范性维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说他错误地理解了认知实用主义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解就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出于理论上的要求,他的理解给认知实用主义这个表达式灌入了新的意义。
在施泰纳的批判中,第二步的论证与第一步极为相似,因此我们对第一步的批驳同样可应用于第二步,因此没必要再重复了。施泰纳的基本主张是,仅凭行动核心性,甚或加上对行动概念的澄清,都难以成为实际运用中的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现在再看这一主张,它就不仅仅只是可疑了。之前我们所介绍过福多对认知实用主义的解释,现在看来它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行动核心性确与某一附加性质相关”的可能解释,我们说,这里的附加性质只是某个特别类型的、在一般意义上由行动核心性所界定的认知实用主义的独特性质而已,同样的解释仍然适用于福多。于是,关于提供论证以排除这种可能解释的必要性,我们上述所论也同样适用于福多。并且,鉴于这些解释看上去完全建立在他的基本主张之上,那么,拒斥施泰纳的基本主张的确会影响他针对上述问题所提供的解释。即使我们不去怀疑这一基本主张,施泰纳的推理也总会存在一个坏循环,这与第一步如出一辙。最后,一方面,行动核心性假说在第二步批判中仍旧提供了一根理论准绳,把本来并无关系的理论捆在一起,另一方面,施泰纳的批判并未触及行动核心性假说的规范性维度。
(二) 对行动核心性之必要性的质疑
有的批判也许比施泰纳的批判更为极端,它甚至质疑未定的行动核心性对于认知实用主义的必要性,并以此来指摘行动核心性假说的有效性。显然,这种质疑可能有很多理由,但是在认知理论的某个具体领域,回应这种对我们当下所倡导的认知实用主义观念的质疑就显得尤为必要,鉴于此,我们在这里就只处理这一具体领域:概念理论(the theory of concepts)。福多和泽农·派利夏恩(Zenon Pylyshyn)把这一领域看作“认知科学的心脏”。*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p.VII。这解释了我的关注点:福多对实用主义概念理论之特性的理解与我们的认知实用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的问题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关于“概念实用主义”的相关观念上去,即便不会牵涉到关于概念实用主义的全部问题,也至少会牵涉到与福多存在争论的布兰顿概念实用主义,这在前文已有所述。如果说两者的严重分歧关涉的是概念实用主义的理论价值,那么我们有理由说,在什么是概念实用主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关注福多的案例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由于他接受行动核心性假说是认知实用主义的一般定义,因此,对于他来说,与我们的认知实用主义的冲突是一个内在其理论中的冲突。福多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这种行动核心性,在他看来,实用主义的概念观应该主张: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具有“引导行动的独特功能”。福多用行动导引(action guidance)来理解行动核心性,尽管这种理解显得很狭窄,然而更为一般地说,他的理解来自于这样一种行动核心性假说:概念实用主义的特点一定是行动以某种方式对概念化过程起着核心作用。
这里也有困难之处。实用主义概念观是福多展开其批判的出发点(他的论敌对这一概念观本身的界定看上去与福多相同),然而我们发现福多这里的实用主义概念观并没有鲜明地赋予行动以核心地位,行动被视为概念化过程(或其他过程)的目标。实际上,我们有更为棘手的困难:在福多与布兰顿的论辩中,双方所界定的概念实用主义其实非常单薄,因此,在评价概念实用主义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行动核心性之前,我们的初步难题就是要澄清对概念实用主义的理解。解决这一初步难题事关重大,因此接下来我将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论证的具体细节已在另外的场合有所阐述,*2013年6月,在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概念和实用主义”工作坊中,我做了题为《什么是概念实用主义:福多vs布兰顿》的讲演,其中对该问题我做了具体的论证。故此不再赘言。
我最基本的观点是,福多对概念问题的思考十分广博,对其进行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福多眼中的概念理论有五个主要议题,同时,针对每个议题,我们需要在相互对立的答案之间进行决断。第一个问题福多关注的是所谓概念结构,这里我们需要在两种答案之间做出选择:原子主义(基本概念在结构上互相独立)和整体主义(概念在结构上并不相互独立)。第二个议题处理概念结构的一个特别方面,主要关注的是概念的实体类型,我们的答案也有两种:概念作为个殊(particulars)和概念作为能力(abilities)。第三个议题关涉的是概念内容,这与概念结构相对,我们的答案有:用法理论(概念的内容就是概念的用法,用法造就了概念,特别来说,这种用法就是在推论和分类过程中概念所起的作用)和信息理论(概念的内容就是概念所体现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发生在概念物种[the creature endowed with it]的周边世界里)。第四个议题事关概念持有(having or possessing concepts),相关的答案是:对概念持有之本质的命题性知识分析(know-that analysis)和能力之知分析(knowing-how analysis)。最后第五个议题处理的是,概念持有的议题在理论上是居先于或还是置后于概念具体化(the individuation of concepts)议题;在福多那里,最后这个议题与关于概念本质的议题没有实质差别,同时也覆盖了关于概念结构和概念内容的议题。
以上我们重建了福多针对概念提出的理论议题,从中自然会生发这样的疑问:福多如何定位实用主义概念理论的特殊性?它被定位在了某个或某些他所提出的理论议题之中,然后将其等同于上述的某一种解答?我的假说是,在福多看来,概念实用主义的特殊性只是体现在“概念持有之本质”这个议题上;于是,概念实用主义对于他来说是概念持有议题上的一种理论主张,有了这一主张,概念理论里其余议题的理论主张自然也会纷至沓来。由于福多在很多方面的论述并不系统确切,我们很难看清概念实用主义与其余议题上的理论主张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的假说需要一个补充,即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必然关系就是简单的相关性关系,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种情况,某个议题下的相关理论主张都不会被要求用来界定概念实用主义的特殊性。因为当概念持有的实用主义分析支配那些相关理论主张时,那些主张与概念实用主义并无特别关联,当实用主义分析暗示那些主张时,它们其实并不必要,因为它们在理沦上可以采纳概念实用主义的形式。
那么,在概念持有作为能力之知与概念持有作为命题知识之间,福多将概念实用主义立于哪一边呢?这个问题仍然是十分复杂的,完全正确的回答也许是:立于两边。因此,我的假说还有第三个方面,即福多对概念实用主义进行了双重刻画:狭义(proprio sensu)的刻画和广义(lato sensu)的刻画。要想理解福多那里的概念实用主义到底什么意思,第一种所谓狭义概念实用主义看似尤为重要,因为广义概念实用主义只是狭义概念实用主义的衍生品。福多也建议,只有更为一般化的关于概念持有的观念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曾用来意指概念持有的狭义实用主义观念才能扩展到这种一般化的类型。因此,概念实用主义的要点便在于狭义概念实用主义的特殊性。但是,如果从理解福多的概念理论出发,那么广义的概念实用主义就显得重要了,因为实际上对于福多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狭义概念实用主义与他所谓的概念笛卡尔主义之间的对立,而是广义概念实用主义与概念笛卡尔主义的对立。而且,为了把握福多眼中的概念实用主义的真正本质,广义概念实用主义实际上重要得多。
首先,如何理解“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概念实用主义是指,持有一个概念就是掌握这个概念的用法,该用法由一条规则所确定,并主要体现在进行推论以及分类的过程中。因此,持有一个概念被看作是拥有一项能力,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项做某事的能力。进一步,这种对概念用法的掌握被分析成一种知识:掌握一个概念就是知道它的用法。这种知识属于能力之知,即如何使用概念的知识,因此也是何以用概念做事的知识,比如进行推论和分类。福多写道:“持有一个概念体现在你能以该概念做何事之中,认识论上说,这是某种能力之知。”*参见J. A. Fodor,Concepts:WhereCognitiveScienceWentWrong,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强调以下这点非常重要:这里涉及的是强的能力之知概念,这意味着能力之知既区别于命题性知识,又不依赖于命题性知识。*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p.36。换言之,狭义概念实用主义宣称,持有一个概念就是拥有一项遵从该概念用法的能力,这意味着,遵从一条规则并不依赖于我关于这条规则所拥有的命题性知识。这告诉我们,根据“对遵从规则的实用主义解释”*Ibid., p.36.(其与“对遵从规则的理智主义分析”*Ibid., p.40.相对),知道一套规则就是能够按照这条规则做事*Ibid., p.36.,而不是把这条规则“变成作为心智状态的意向对象”*Ibid., p.38.。福多甚至更为具体,他用倾向性(disposition)来刻画能力这个概念:知道如何在推论中使用一个概念就是“倾向于根据规则进行推理”*参见J. Fodor,LOT2TheLanguageofThoughtRevised, p.36.。比如,掌握“和(and)”这个概念,就像是“倾向于让‘和’以符合其用法的方式介入到相关推论之中”*Ibid., p.35.。
广义概念实用主义更为复杂。实际上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可能。根据第一种解释,如果某理论把概念持有看作是一种知识(无论是什么知识,包括命题性知识),那么它可算作是概念实用主义形式的理论。如福多(2004)所言:“‘知道’、‘相信’这类词必须放到叙事中进行理解,持有一个概念所必须知道的所有事情实际上构成了概念的内容。”*参见J. A. Fodor, “Having Concepts: A Brief Refut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Mind&Language, 19(1), 2004, p.1。因此,持有一个概念就是处于一种“认知状态(epistemic state)”中,无论是哪种认知状态。福多在此还评论道:“大致来说,几乎所有对能力之知的强调都暗示着:‘概念持有是一个认知条件’这一观念是实用主义的一个类型,这一类型是实用主义的常态。之后我将沿用这一看法”*Ibid., p.2.。福多试图扩展概念实用主义,他将任何“在认识论上分析概念持有”*Ibid., p.3.的理论进路都归在概念实用主义门下,而上面引述的这条评论支撑并辩护了这种扩展。同样在福多(2004)中,福多写道:“……概念实用主义或者包含或者本身就等同于这样的主张:概念持有由某些认知能力构成。”*Ibid., p.5.这里并没有提到一种特别的、强的能力之知的概念。如此构建的概念实用主义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合理的层面上理解它与概念笛卡尔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概念笛卡尔主义在这里则被界定为“并不是命题性知识或能力之知决定了你能持有什么概念,持有什么概念是由你能够思考什么这一点来决定的。”*Ibid., p.3。
然而,随着福多对理论的不断深化,我们对广义概念实用主义可以采取更严格的解释(第二种解释):概念持有依然是关于能以概念做何事的知识,然而这种知识的模态(modality)不再必然诉诸强的能力之知概念来分析了。可以肯定的是,强的能力之知会牵涉到两个不同的方面,而这两方面之间的区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能力之知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正如我们所论证的,它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而是关于做事能力的知识,这也许让它成为了一种实践知识。另一方面,如此刻画的实践知识具有关于其知识对象的模态或形式。借助这个区分,我们对福多广义概念实用主义的第二种解释则可表述为,概念持有就是关于使用概念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一种关于概念的实践知识,然而这里并不承诺这种知识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用理智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福多的广义概念实用主义,把使用一个概念的能力之知建基于命题性知识之上,特别是把它建基于关于概念使用规则的命题性知识之上。这两个方面的区分很重要,因为与第一种解释不同的是,第二种解释通过这一区分排除了那些不把概念持有当作实践知识(关于用概念来行事的知识)的概念实用主义理论。*因此,我提议主要保留意指实践知识、其形式区别且独立于命题性知识的能力之知,也就是说,我们要保留我所谓的强的能力之知的概念。有相当确凿的一部分福多文本可以印证第二种解释。特别是在《思想语新论》(LanguageofThoughtrevisited)中的“概念实用主义:式微与衰败”这一章里,福多清晰地分析了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之间的对立,并通过将两者与概念内容的用法理论联系起来,将概念持有解释为概念使用之知识。而且,在同一章的最后,他提到了把笛卡尔的概念观等同于某种形式的概念实用主义的理论企图,当他试图批驳这一企图的时候,他把这种理论企图表述为“能够思考概念本身就是知道如何使用概念的一个例证”。*参见J. A. Fodor, “Having Concepts: A Brief Refut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Mind&Language, 19(1), 2004, p.47。只有不在不强的意义上理解能力之知,也就是将之视为实践知识,福多的论证才能得到理解。
福多坚定地拒斥概念实用主义,他的很多讨论就是借此充分展开的,第二种解释之所以更具说服力,就是因为它能更好地反映福多的那些讨论。福多扩展了概念实用主义这一术语的意义,第二种解释也让这种扩展变得更容易理解,否则他所使用的“概念实用主义”会显得非常随意。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第二种解释所揭示的概念实用主义观理论上更具区别度、更为关键,它围绕着一种更为实质、更一般的实践知识观而展开,既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也与某些理论分析所预设的能力之知区别开来。基于上述原因,我将坚持第二种解释方式。
基于上述对福多概念实用主义的所有解释,我们会发现,在他看来,行动核心性所遇到的主要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实践知识里蕴含着行动核心性?的确,行动核心性假说一方面在概念理论里强调实践知识的核心性,另一面在一般的认知理论里强调行动的核心性。于是,问题就在于,两方面的理解是否真的契合,而这种契合意味着前者要是后者的一个具体例证。
更准确地说,它们看上去契合,而再一想,这种契合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看上去契合,因为一眼看上去,主张用概念做事的知识对理解概念持有具有核心意义,也就是更间接、具体地主张行动对认知有核心意义。看上去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直接隐含地假说,用概念做事的知识就是用概念如何行动之知的一个特殊形式,根本上说,做(doing)与行动(acting)是一回事。然而仔细捉摸,这种双重假说就很成问题了。
的确,认为持有一个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知道用该概念做何事,是否真的等同于认为持有一个概念就是知道能以该概念展开哪些行动?这种等同十分可疑,同时也指向了一个难题:做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一开始仔细考量两者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做都是行动。我做某事的时候,比如用一个概念做某事,如果说我这是在完成一个行动,就显得十分怪异。当然,把认知上的筹谋(cognitive operation),包括对概念的使用,构想为行动,在理论上也不是不可能;实际上,讨论心智行动(mental act)的整个理论传统与当下的认知行动理论就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但这需要严肃的论证,而不能只是轻易地假说。同样,我们也不是在否认,某些形式的实践知识确实可以关涉真正的行动,事实上某些版本的认知实用主义能够容纳行动核心性假说,靠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实践知识。诺伊的生成理论就是如此,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行动对视觉感知有核心意义,这一观点的基础便是他预设看(seeing)事实上就是强的能力之知(knowing-how),具体说来,这种能力之知是指视觉的知觉要素如何在意义上(nominally)依赖行动的动力要素。*在“Pragmatisme cognitif et énactivisme”(2013)一文中,我主要辩护的观点就是诺伊版本的生成主义应该算作认知实用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认知实用主义主要建立在强的实践知识之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实践知识都能被假说为(我们姑且可称作的)实用性知识(pragmatic knowledge),后者可以被理解为牵涉到行动因素的关于做某事的知识,我们需要证明这一点,特别是在概念理论这个例子上。*实际上,一些诸如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主张的概念理论明显就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因此现在的情形是,借助实践知识核心性来界定的概念实用主义,无论其中是否包含强的能力之知,都向以下理论假说提出了真正的挑战:在一个最为一般的层面上,认知实用主义可以通过“行动以某种方式对认知具有核心意义”这一点来界定。初看上去,我们打开了某种理论可能:行动核心性甚至并不要求我们主张某种特殊形式的认知实用主义,即概念实用主义。这不仅是在严肃地反对行动核心性假说,也是在焦虑不安地呼吁新的选项。根本上说,这新的选项就是要用“行动”的概念替代“做”的概念,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展开这一理论选项。第一种方式是延续福多的概念实用主义,于是这里的认知实用主义就意味着把先前界定的实践知识看作一般意义上的认知(cognition)的核心。第二种方式即是把做本身,而不是关于做的知识,看作是一般意义上的认知的核心。这两种方式均能容纳以下论点:行动是做的一种特殊形式,行动的知识是实践知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行动核心性假说或行动知识假说就跟着成为了一个例示。
对行动核心性假说的极端反对是否会对该假说造成致命打击,可能的理论替代选项是否可靠,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行动的概念,特别是行动与做的关系,也同样需要厘清实践知识的概念。换言之,在我们的初步探索之后,要想继续推进对认知实用主义的研究,这取决于在行动理论以及在实践知识理论方面的进一步开拓。
(责任编辑:韦海波)
作者简介:让-米歇尔·怀尔(Jean-Michel Roy)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黄远帆、胡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