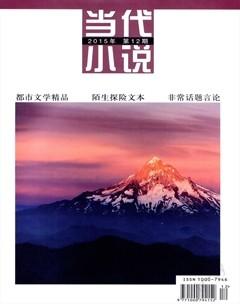买台机床安在家
李治邦
一
我家住在河西后街,那里住的全是机械厂的职工家属。
我爸爸是1958年从郊区招工到机械厂的,进城前,我爷爷把家里最好一床厚棉被子让他带走。临走时一再叮嘱我爸爸,嘴巴是吃饭的,也是招祸的,你是农民,记住了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多干活。这是咱农民的本分,也是你能活下去的本钱。我爸爸照爷爷的叮嘱少说话多干活,最后熬到了八级钳工,在这行当里算是顶天了。论手艺,爸爸在机械厂堪称是一绝,做出来的活儿讲究,地道精细。他人也出奇的老实,厂里随便找出个人就能管他,是人不是人的都敢戳着他的脊梁骨。他也不恼,对谁也只是嘿嘿一笑。厂里烧锅炉的有个坏小子叫嘎乌,总是欺负我爸爸。我爸爸中午吃完午饭总爱睡一个小觉,嘎乌就偷偷在我爸爸的鞋里撒尿。我爸爸起来迷迷糊糊地穿上就走路,吧唧吧唧的,周边人都哈哈大笑。我爸爸知道是嘎乌使的坏,也跟着笑笑,然后脱下鞋在水管子那冲冲,晾在他的机床前,就这么光着脚丫子干活,地上还有许多碎铁屑。等到晾干了他再穿上。后来嘎乌看着我爸爸的脚冻得跟紫芯萝卜一样,就不再发坏了。他对周边人说,欺负老实人就会得报应的。
我爸爸是1961年结婚,他还没结婚前,在厂里闹出了一桩事儿。在人们肚子没油水的年月,车间主任领着几个人偷偷把保卫科的看厂狗给宰了,晚上炖狗肉打牙祭,碰巧让爸爸看见。这事也该着是我爸爸倒霉,白天在班上给的活多,他没干完,回到宿舍后觉得怎么也不安生,吃完饭抹抹嘴,又溜回车间接着去干。他先看见的是那条被肢解的狗,还有狗脖子上戴的那串铃铛。说来,我爸爸很喜欢这条狗,虽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的粮食都是定量,他也把自己的口粮留下一部分给这条狗,那年月吃不到肉,他也是舍得把仅有的一口肉给这条狗吃。狗不吃,我爸爸就硬逼着它吃,吃完以后,我爸爸竟然发现这条狗流泪,眼睛里都是感激。还有,那串铃铛也是我爸爸给它拴上的。说起来这串铃铛是我爷爷给我爸爸的,说你要是想我了就摇铃铛。我爸爸给狗起名叫豹,因为这条狗很是凶猛,晚上吠起来的声音会在厂里各个角落都听见。我爸爸看这被肢解的狗,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愤怒地拿起那串铃铛在车间里一路狂走。看见车间主任一伙人正往热腾腾的大锅里掰着大蒜,狗肉的香味儿已经蹿出来。我爸爸戳着车间主任说了一句话,你们怎么还不如狗呢!
转天,我爸爸将这事汇报给厂长。厂长拍拍他肩膀,紧绷着脸,小声地叮嘱我爸爸,你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再给外人讲了。我爸爸放心走了,他以为厂长会狠狠处理车间主任,因为厂长是个很严厉的男人,我爸爸有次干活儿稍微差了一毫厘,厂长就不高兴了,说,你是八级钳工,这是你干的活儿吗,你拿工资比我都多知道吗!哪料想,事过之后,车间主任还是车间主任,倒是我爸爸总干重活和累活,每月粮食定量还减少了三斤。车间主任说他吃不了那么多,给吃多的匀点儿。自打这次事后,我爸爸更是少言寡语,车间里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闷葫芦”。后来厂长有次吃饭跟我爸爸一个桌,一起吃的焖饼,厂长碗里有肉,我爸爸碗里有白菜。厂长对我爸爸说,你做得对,我批了车间主任,这王八蛋是个大馋虫,早晚会毁在嘴上。我爸爸没有表情,就是低头吃着焖饼。厂长悻悻地说,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没有动静。我爸爸端着饭碗子站起来走了,厂长背后喊着,你他妈的是个哑巴呀!
二
我爸爸1961年结婚时,没邀请几个人。我爷爷从郊区过来,扛着一袋白面,还有一张猪脸。我妈妈是厂里食堂窗口卖饭菜的,就是因为在窗口看中了我爸爸的老实憨厚,每次都给我爸爸多打一勺菜,多添一口饭。我爸爸不知道,有次跟她说,我怎么就比别人多那一点儿呢。我妈妈生气地说,你傻呀,那是一点吗,那是我的心。我爸爸明白了,呵呵一笑。参加我爸爸妈妈婚礼的就是一桌,我妈妈炖了一张猪脸,香飘整个机械厂的宿舍。车间主任也闻着香味凑过来,带着几个馋嘴的。我爸爸也不谦让,我妈妈给了每一个人一勺子肉,其中给了车间主任一个猪嘴。车间主任吃得满嘴是油,他对我爸爸说,别记我仇,我这个人过去就完,我就是讨厌背后告状的人。你有什么当面跟我说,骂我娘都行。旁边的人也说,那条狗解了我们馋,知道我们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有,放屁都油不过裤子。车间主任说,你要是还有怨恨就当面骂我们几句,骂完了你也痛快了,我们也痛快了,省得你天天跟哑巴一样憋着。你这么憋得难受,我们也憋得喘不过气。我爸爸还是不说话,就是跟车间主任碗里放了一块舌头,这舌头是我妈妈给我爸爸碗里盛的。车间主任细嚼慢咽吃完了以后,咂了半天的嘴,才说出一句话,吃完了这根舌头,我现在死了都不遗憾。那天,我爷爷喝多了。那酒不是什么好酒,就是地瓜烧出来的,黄颜色的,喝完了以后烧肚子,辣嘴巴。爷爷搂着车间主任说的都是酒话,我儿子就是一个废物,你就得当成哑巴看。可我儿子能干活,这就是本事呀。现在这世道不是缺能说的,是缺能干活的,对吧。车间主任激动地握着爷爷的手说,对呀,靠嘴巴就是吃饭,还有跟女人亲嘴儿,干活才是咱工人的正当呀!爷爷高兴,车间主任也高兴。爷爷喝多了喝尽兴了就唱秦腔,他说,我是从陕西汉中来的,没别的本事,就是能吼几句秦腔。大家听完一起鼓掌。爷爷涨红了脸色唱道,“赤壁杀兵战争苦,诸葛亮七星台上借东风。曹孟德人马八十三万,大火烧得只剩七千零。见李典少盔无甲露膀背,见乐进战马光秃无毛鬃。见许褚胡须烧个刷箸样,见夏侯■只剩下一个眼睛。念只念东风喜欢那诸葛亮,才换来人世间老百姓得太平。”爷爷的嗓子像野马奔驰过草原,高腔跟冬天里北风吹的一样,特别有劲儿,呼呼的。一嗓子吼下来,机械厂宿舍多远都能听清楚。车间主任最后被我爷爷架走的,那几个人也都东倒西歪地走出新房。
在新房里,我爸爸喝得有些头晕,他在院子里上完厕所以后回来,我妈妈没理睬他,也去院子上厕所。我爸爸的身上发躁,他走近窗户,看见天空一片橘黄色,他知道那是机械厂上空的灯光罩。那几年,机械厂很忙,都是在做小型拖拉机。说是国家机械部安排的,给农民用的。好半天,我妈妈才从院子外边走进来,说,为了你,我吃药提前来了例假,今天刚利落了知道吗。我爸爸不懂,但也懂得点头。我妈妈拉了屋里的灯,但从窗户外边折射出来机械厂的灯光还是在四壁影影绰绰。我爸爸呆坐着,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我妈妈给我爸爸解开的衣服,然后把我爸爸放倒在床上,我爸爸就觉得身子跟棉花一样的软。他觉得那床铺很软,像一个陷坑。这个新房是厂里给的,当时有规定,只要两个人都是本厂职工就给一间房子,然后给一张双人床。我爸爸一直住在单人宿舍,睡得都是硬木板床像是机床。我爸爸突然睡到双人床,主要是被我妈妈铺了两层的厚棉被。那是我妈妈新絮的棉花,柔软得像是蚕丝织成的。我爸爸不好意思地躲着我妈妈的眼神,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因为他觉得我妈妈不可能跟他结婚。我妈妈是机械厂出名的美人,丹凤眼,嘴唇薄薄的,红得跟樱桃一般。我妈妈特别爱说,跟谁都能聊得上来,不拦着能跟人家说几个晌午。厂长说她是碎嘴子,只要食堂是我妈妈在窗口,厂长就会用手指头封住嘴巴,告诉我妈妈,打饭,别说话了。我妈妈就特别委屈,后来厂长再来我妈妈就说,知道知道知道了,我不说话,你就憋死我!
我妈妈把灯关上,屋里暗下来。她问我爸爸,你跟女人有过事吗?我爸爸说,没有。我妈妈说,今天我教教你,教你怎么样跟女人办事儿。我妈妈脱光衣裳,我爸爸觉得眼前一团白色。她纤细的手不断地抚摸着我爸爸,弄得我爸爸身体都失去控制。他的手被我妈妈引导摸到她的腿,凉丝丝的像是杭州上等的绸缎子。我妈妈腿很长,小腿肚子很丰满,细腻而柔和的皮骨渗透着凉气。我爸爸为自己悲哀,他觉得自己活了二十多岁才摸到女人,才知道女人的身体是缎子做的,才知道女人的腿是有温度的,摸到了就能烫手。我爸爸笨拙地跟我妈妈在床上翻滚着,我妈妈喊着,你王八蛋狠点儿啊,你这么没有劲头儿女人能享受吗?就是瞬间,我爸爸就觉得水库里的水没了,然后泥一般地瘫在我妈妈身上,我妈妈怨恨地说,笨死你,今天是我受孕的日子,我想让你给咱留一个种儿。你就这么一点儿能耐,够不够留种的呀。说完,我妈妈穿好衣裳推门而出,我爸爸喊了一句,你就这么走了?我妈妈说,我饿了,你也饿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吧。
我爸爸看见窗外有了月亮,看见我妈妈如云彩般地飘走了,只剩得他面色如灰。清冽地风从窗外吹进来。他竟然呜咽起来毫不克制,满脸都是泪水,任凭风吹而心不动。我妈妈端着两碗羊肉泡馍走进来,然后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端到床上,看见我爸爸在流泪,不由惊诧地问,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我爸爸吭哧半天才说,我怕给你的不够留种的,我太笨了。我妈妈笑了,今天你给得不够,明天你再给我多点儿呀!我妈妈吃羊肉泡馍就是表演,她把锅盔般的馍掰得就跟黄豆粒那么大,而且掰的时候很随意,一边跟我爸爸叨叨一边掰出来。那两只手就像是弹钢琴,十指尖尖,灵活而自如。我妈妈说着,回手给两个碗里舀上心肺羊肚羊血羊杂,然后再搁上香菜和葱花。我爸爸看傻了,吃呆了。这时候,我妈妈飞快地跑出去又迅速地跑回来,再添上一勺子热热刚出锅的辣椒,浇上以后■■做响。那馍是白的,汤是红的,菜是绿的,血是黑的,搭配得很是赏心悦目。我爸爸吃得满头大汗,边喊着辣还不住地朝嘴里填着。我妈妈说,你爹说是陕西人才吹,唱那秦腔就是吼,秦腔不是吼出来的。我才是陕西铜川人,我给你唱地道的秦腔气气你爹。说着,我妈妈就吃着泡馍唱着秦腔,“看那穆桂英,柳叶花的眉毛弯又细,葡萄花的眼睛水灵灵,悬胆花的鼻子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口内盛,元宝花的耳朵灯笼花的坠儿,太阳一照放光明。”我爸爸被我妈妈唱蒙了,我妈妈生气问,你怎么跟我也装哑巴,你倒是说几句话呀。我爸爸支吾半天说,现在自然灾害的当口,这些好吃的你都是从哪儿拿来的,你别是偷来的吧?我妈妈掉脸子了,说,今天是我大喜日子,你别给我添堵懂吗。我筹备这些好吃的有好几天了,都是挤自己牙缝子钱弄的。你小子吃着好东西还有坏心眼儿,你他妈的就是没屁眼的男人。我爸爸笑了,说,好,我少说话多做活儿。说完就把我妈妈压倒在身下,我妈妈不耐烦地喊着,你小子倒是多做活呀!
三
时间晃了晃,爸爸的头发由黑变成灰白,车间主任也不知换了多少茬儿。在1988年的深秋,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我爷爷去世,我爸爸带着妈妈回老家奔丧。两个人站在我爷爷的墓碑跟前,我妈妈不断地说着我爸爸的窝囊,说我爸爸的嘴太笨,说我爸爸的少说话多做事害死了他。他徒弟的徒弟都是厂里的头头脑脑,你儿子现在屁也不是,还在那忙死忙活地干活。我爸爸就这么低头抹着眼泪,一句话都不辩解。我妈妈越说越气愤,最后用力扯着我爸爸的耳朵说,现在不说话行吗,不说就没人知道你。你连说句好话都不会吗,好不容易说一句都是捅人家肺管子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得见什么官说什么话,懂得说出话来得让人家爱听,能记住你小子。你说你多干活顶个屁用,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钳工。你在文革给厂长说句话,说他是一个好人,结果你不是陪着厂长挨斗吗。后来,厂长解放了,管你了吗,不是把你忘到了后脑勺。我爸爸突然问,我要见到的不是人,是鬼呢?我妈妈烦躁地喊着,见鬼也要学会说鬼话,现在哪有这么多人话呀。我爸爸紫红着脸接着说,你在我爹面前这么叨叨有什么好处,你说我的这些话,我爹都不爱听,我爹可是会咒你的!我妈妈挥了挥手,喊着,我怕什么,我死了你就知道我说的这堆话到底是为了谁了!我妈妈说完气呼呼地转身走了,我爸爸跪在我爷爷的墓前大哭着,用力拍打着碑石,说,你非让我少说话多做事,我就记住你这句话了,可有什么用呢……
我爷爷去世转年的春天,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晚,四月了还没有花开。机械厂的生产走了下坡,车间主任换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姓唐,原先是我爸爸最小的徒弟。这个人挺傲气,也霸道,总跟别人吹,说唐姓是中国一个旺族,老祖先在唐朝掌大权呢。后来有明白的人说,唐朝是姓李的当皇帝,唐主任还翻白眼。我妈妈说唐主任走路跟鸭子似的,一■一■的。于是,车间有人就给他起个绰号“唐老鸭”。厂里生产不景气以后,人一闲着就得找事或者生事。唐主任闲得无聊在班上找几个人打麻将,我爸爸领料时正巧碰上。他背着手,站在唐主任跟前,胸脯呼呼地起伏,眼睛死死铆着桌上一堆堆钞票。唐主任也不错眼球地瞅着我爸爸。两人相持一会儿,唐主任咧咧嘴说,师傅,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在这跟邮筒傻戳在这儿,碍我的眼。旁人有些紧张,忙收拾着桌上的钞票要溜。厂里三令五申,谁上班打麻将,扣除全月的工资。唐主任笑笑说,我师傅老实得三脚踹不出个屁来,那嘴就是个钢闸,咱们就放心打。说完,他故意把麻将推得哗啦哗啦山响。我爸爸摇摇头,叹一口气背着手闷闷走了。我爸爸在冷落的厂房之间走着,看每间厂房大门都敞开着,男人打牌,女人织毛衣。他走着走着停住脚,然后蹲在地上。觉得脸上有些热,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流泪了。按季节,现在厂里的那一片腊肠树该开花了,有白的有红的有粉的,姹紫嫣红,散发着淡淡的花香。那时,我爸爸总爱站在树下歇会儿,有时候我妈妈过来会拿些青萝卜。我爸爸爱吃青萝卜,就在树下吃着。我爸爸对我妈妈说,吃着你拿来的青萝卜,闻着腊肠树的一阵阵花香,那就是一个字,美。我妈妈叨叨着,说我爸爸就是一个高粱花子的脑子,享不了什么福分。
我妈妈在食堂听到我爸爸受唐主任奚落的消息不干了,她眼睛里不揉沙子,是个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女人。她跑到车间堵到了唐主任,溜溜骂了一个多钟点,语言精粹,上下几千年,包括他的唐朝祖先。唐主任干瞪眼就是没辙。妈妈骂完了,觉得还不解气,又跑到厂长那去讨个公道。好在这个新厂长开明,手底下的订单越来越少,工人越来越不好管,工资还不能欠一个子儿地给,他心里也不平衡。听完我妈妈的话二话没说,把“唐老鸭”给免了,凡是打麻将的全扣除当月工资。还写了大字报贴在厂门口的橱窗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我爸爸怯了,跑到“唐老鸭”和扣除工资人的家里,挨个给人家赔礼,说,我那位就是一个臭嘴,别介意。那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听到这个信儿后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劈头盖脸地朝爸爸发了一顿火,问,你为什么不骂那姓唐的几句,想当初他还是你的徒弟呢。这人有脸,树有皮。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你知道吗!你手里没有短,凭什么让他这个王八蛋当面奚落,你给我们丢人,你连我妈妈的一个脚指头都不如。我爸爸朝我嘿嘿一笑没说话,我不依不饶。他半天挤出一句话,说,我这张嘴惹了一次祸,就不想有两回。我妈妈看我这么没鼻子没脸地数叨我爸爸不乐意了,喊着,你他妈的住嘴,他是你爸爸,只能我说!我不耐烦地嚷着,我不学我爸爸,少说话多干活,这是我爸爸从小就教育我的,现在是废话了。我爸爸怔怔地看着我没有张开嘴,我知道他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那天晚上,我妈妈见我回来,特意做的红烧小鲫鱼。端上来后,鱼香满桌。我看见爸爸还低头不说话,为了缓和情绪,我给爸爸特地夹了几块鱼肉。我爸爸看了看我,说,这鲫鱼刺多,你吃的时候小心点,别卡了嗓子。你小时候卡了一次,你妈妈怎么也拔不出,我骑自行车驮你上了医院才拔出来。我对爸爸说,你别这么摆自己好,你就是窝囊。要不是我妈妈给你争脸,你说你在厂里还怎么呆。我妈妈过来扇了我两嘴巴,怒叫道,我说了,只有我能说你爸爸!
我看见我爸爸眼泪滚下来,两腮都是,没有擦。我扭头走出家门,把大门甩得山响。我妈妈在我背后吼叫着,我操你妈!
四
1994年的夏天,蝉不断地在树林子顽强地叫唤,我爸爸退休了。
他是提前两年退休的,被厂里敲锣打鼓地送回家,后来又被提拔起来的唐主任亲自给他戴的大红花。唐主任小声地对我爸爸说,你知道告不倒我的,我不在乎这个车间主任,我以后就是这个厂的厂长。我爸爸疑惑地看着这个小徒弟,因为他就是一个工人家庭,从小也过着穷日子,怎么能当厂长的。唐主任看出我爸爸的表情,说,师傅,我背后有人,有人会给我说话办事。我爸爸不解地问,人家凭什么给你办事呀?唐主任拍了拍我爸爸,笑了,这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我给你争脸了。我万万没料到,我爸爸一进家门,就把胸前的大红花费劲扯下来扔到墙旮旯。从那天起,他整个变了个人。每天的话特别多,好像要把憋了一辈子的话全抖搂出来。而且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使别人干活儿的,唠叨程度远远超过了妈妈。我惊诧不已,悄悄问我妈妈,我爸爸这是怎么了,话这么密,都是让咱们干活的,是不是脑子受刺激了?我妈妈用手指戳着我,说,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少说话多干活,现在退休了,紧箍咒没了,可不就解放自己了。我依旧不懂,怎么退休就变了一个人呢。
机械厂开始酝酿改制,而且要被另外一家公司收购,现在是盘点资产的时候。厂里乱了起来,什么话都有,什么人都站出来指三道四。唐主任居然一变身份,成了厂里资产清理的谈判领导。机械厂宿舍的各种小道消息乱飞,特别是关于唐主任的,说他跟那家公司的老板拉上了亲戚关系。那天晚上,我妈妈回来对我爸爸说,食堂拆了,在那建了一个饭馆。饭馆老板是我的小妹妹,让我过去帮厨,一个月给我八百。我爸爸瞪眼,不去,伺候他们这帮子人丢我的脸,那么大的厂子说完就完了,就是他们坑害的。那钱都流进自己腰包里了,我手里没有证据,我要是有证据就到上边告他们去。我妈妈顿时慌了,说,你别瞎说,你是自己想的。你要是让他们知道,走黑道能弄死你。我爸爸把水碗扔在地上,喊着,我怕什么,我怕过谁。弄死我,我就不信没人管他们了!我妈妈哑口了,央求着,不去了,我不去了还不行吗。我妈妈说这句话时我正好进家,觉得我妈妈突然没有了过去的锋芒,语言那么柔弱无力。我从小就领略妈妈的嘴茬子厉害,这机械厂宿舍大院的居民没有不知道妈妈的名字。有次一个外院的人跑进邻居大院里的厕所,也不打招呼,我妈妈就堵在门口骂了人家半天。最后我爸爸出来拽走,人家才勉强提着裤子跑出来。我妈妈比我爸爸早退休好几年,就在居委会帮忙,也不拿一分钱。我爸爸退休了,我妈妈觉得要给我买房子,就想出来找工作多赚些钱,结果还是让我爸爸死活拦住。
机械厂在1995年的冬天被人家收购了,厂里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都回家了,每个月发一千块钱。唐主任成了收购后厂里的厂长,不再做小型拖拉机,开始改产做各种收割机。说是专门给河南、山东和新疆做的,就是为了收麦子用的。我爸爸退休后总去厂里来回转悠,被人家保卫撵出来好多次。我妈妈问我爸爸,你退休了还跑厂里干什么?我爸爸说,我就是不放心这帮狼心狗肺的坏人。我妈妈惊恐地说,你别这么骂行吗,你我的退休工资还攥在人家手里呢。我爸爸愤怒地嚷着,那是政府给的,不是他们。别给我惹急了,下回再撵我走,我就硬闯。我是厂里的老人,我是八级钳工,我不能让厂里毁在这帮王八蛋手里。我妈妈哭了,叹口气说,你现在怎么就什么也不怕了呢!就因为你这张要命的嘴,只能出气,不能受气。你要是惹祸了,谁能救你呀。我爸爸挥舞着胳膊不服气地,我谁也不要救我!
当晚,我从单位被我妈妈叫回来。那年我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并且有了自己房子。我妈妈把我叫到屋子外边,天黑了,风有些硬,拍在脸上像是小刀子在慢慢地割。我妈妈穿得少冻得瑟瑟的,我说回屋说吧。妈妈说,你爸爸喝酒呢,咱娘俩说的话不能让他听到,听到他就跟我急。妈妈那张嘴,我从小听到大,倒习惯了。有时听听数叨也是享受。可爸爸退休后那张烂嘴,叫我真忍受不住,有时会毛骨悚然。妈妈搓着手,我觉得你爸爸是不是脑子有病了,你有时间带他去医院看看。我摇头,我要是跟他说看脑子,他不得疯了。妈妈说,你傻呀,你就说看头疼,他最近总喊头疼。我无奈地说,那就试试吧。妈妈哭了,抽泣着,现在你爸爸的徒弟唐厂长掌权,你爸爸跟他死对头,总上厂里转悠,弄得人家总撵他,还说再去就开始不客气了。我纳闷地问,转悠什么呢?妈妈说,怕唐厂长毁了厂子,他经常在他那机床前站着看着,弄得人家都不敢干活。我恼了,问,那机床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已经不是他的了。妈妈叹着气,他说能离开厂里,但就是舍不得那台机床。我悻悻地说,他就是机器。妈妈抱住了我痛苦地说,儿啊,你爸爸变成这样跟我有关系,我以前待他太厉害了,现在他这是找我偿还来了。
这时,我听到我爸爸在屋子里撕破嗓子吼着秦腔,“赤壁杀兵战争苦,诸葛亮七星台上借东风。曹孟德人马八十三万,大火烧得只剩七千零。见李典少盔无甲露膀背,见乐进战马光秃无毛鬃。见许褚胡须烧个刷箸样,见夏侯■只剩一个眼睛。念只念东风喜欢那诸葛亮,才换来人世间老百姓得太平。”他唱得高昂激越,比我爷爷唱得还好。我听见邻居有人出来对我妈妈说着,你那口子天天晚上都不安生,吼什么吼,还让人家睡觉不睡觉呀。妈妈赔着笑脸说,回去说,回去不让他唱了。邻居说,你管得了吗,说多少次还不是照样唱。唱得好就凑合了,天天跟杀猪这么叫唤。再这么折腾我们就不讲老邻居的情面,扔砖头砸你们家窗玻璃,看还唱不唱!我爸爸听完这话冲了出去当地喊着,我就唱了,我看你砸我家窗户试试。我憋囚了这么多年,现在不憋囚了!
我爸爸吼叫完了,院子里一片鸦雀无声。
五
我爸爸每天看老厂子生产的拖拉机,天天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于是,他就在烦闷时找我的茬口。我大学毕业后到了一家设计公司,上头看我精明,人也本分,几年的光景提我当了项目课长。按说这是高兴的事,我爸爸反倒腻歪我,心理不平衡了。那次我下班在外面请客,喝酒吃饭,回家晚了。我爸爸端着茶缸子出来,瞥着我问道,饭局是谁掏钱呀?吃公款容易噎着你懂吗?到时候没有人去大牢看你,你就自作自受。瞧你脚下那双皮鞋,脏成什么样子,还■脸能穿出来。别怕省鞋油,没钱我给你。瞧你那身西服,皱皱巴巴的也好意思穿,找你妈妈熨熨啊,熨挺喽,再系个领带,没钱我给呀。你也大小是个项目的课长,那手机也买个新式的呀,带能视频说话的,让我和你妈妈也看见你干什么呢,我一直怀疑你小子在吹。你要是真有钱,你就把你爸爸我这个厂买下来,我就天天给你磕头了。我就问,我买下来那您干什么呢?我爸爸梗着脖子说,我就到我的那台老机床那里干活儿,然后回家喝你妈妈给我烫的老酒,还有羊肉泡馍。
晚上,我妈妈到房间看我,好心劝解我,说,你别给你爸爸生气,你看我说话吗。你爸爸不会给你掏一分钱,钱都在我这把着呢,他就是为了过过嘴瘾。他这么多年就是为他的厂子活着,他的机器,我看他就是机器了。什么也不喜欢,别人养个花钓个鱼,实在不行了就打打牌喝喝酒聊聊天,他就是不喜欢。突然,妈妈认真地对我说,你跟你公司老板说说,把厂子买下来,那些机器都是好的。你爸爸说不少机器都放那不用了,生锈了,他总过去给他的机床搽油。这不是神经了,唐经理跟我说了一次,说要带你爸爸去医院看看。说着妈妈眼眶子湿润了,眼泪在里边打转转,不敢掉下来。我内心一片苦涩,公司老板怎么会买这个厂子呢。那天晚上,我爸爸一犯驴脾气,把我这耍横的儿子给镇住了,竟身不由己地按照他老人家说的去办,花了两千多买了身西服,也知道擦皮鞋了,到公司穿戴从不敢马虎敷衍。公司老板很愕然,说,你小子平常邋邋遢遢的,这些阵子怎么讲究了?我就是笑笑,公司老板说,你去趟德国法兰克福,那里有一个建筑设计交流。你要是不这么讲究,我其实安排了另一个人。说完他哈哈笑着走了。
我真是感谢我爸爸,他或许那句话就改变了我。
我从国外回到家,没想到妈妈和爸爸正在打冷战。因为,我爸爸的嘴已经不满足数叨我了,他开始把视野拓宽到邻居大院。那天晚上,爸爸背着手冲着对面的四愣子吼一嗓子,四愣子,我闻着你那店里的烧鸡味道不正,你小子得把鸡熏透了,你要搞什么歪门邪道的,可就狼心狗肺了,我让街坊四邻都不买你小王八蛋的烧鸡!四愣子怕过谁,已经举着棍子冲到了我家门口,我妈妈玩命儿拽住了他,恳求着,你看我的面子别跟他计较,他就是疯了。我爸爸跺脚嚷着,我没疯,你小子拿棍子打我呀,我还怕你!四愣子的妈妈赶过来,抢过了儿子手里的棍子,然后对我爸爸喊着,你不要命了,他要是急了真把你揍了!那天,我妈妈跟我爸爸犯了口角,这是我爸爸退休后第一次的爆发。我妈妈说,你不好活可以,我和你儿子还想多活几年呢。你要是这么没完没了地到处惹祸,我们出门怎么做人。我爸爸脸色铁青地说,我就是想让人知道怎么做人,你看现在还懂得做人吗!我妈妈说,就你知道做人,我们都不是人,你高兴了吧。我爸爸举起手扇着自己嘴巴子,我就是懂得做人才落成这样,我不能眼巴巴看着这些不朝做人的道上走的人。我难受,我今天看我的机床已经生锈了,有人他妈的朝上边撒尿拉屎,那机床陪着我多少年呀,它就是我的命根子呀!现在四个车间只有一个车间干活,我那个车间就跟一个报废的仓库一样,里边跑着都是耗子。我打了一天的耗子,我打不过来呀。我爸爸疲惫地蹲在地上,我妈妈发火了,这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吃饱撑的!两个人吵嘴,我进来后都不再说话,我愤慨地对爸爸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小心有人半夜砸咱家玻璃。我那天汽车的车胎都扎了。爸爸恼了,谁让你开车回来的,你看咱院子里有开车的吗?我看见妈妈瘫在地上像是一摊泥,脸色苍白。我戳着指头对我爸爸,你看看我妈妈,她跟你一辈子容易吗,你就不知道心疼啊。你现在退下来了,那厂子、那机床跟你都没有任何瓜葛。厂子完了,机床坏了,都跟你没有事。你就是你,还有我和我妈妈。我爸爸毫不含糊,忽然站了起来,高声嚷着,我就要管,这辈子都是别人管我,现在我退下来了也要管管别人。我也急了,呵斥着,邻居们都处得不错,你这不是得罪人吗?我爸爸跳到院子里扯着嗓门,就因为我怕得罪人,这辈子才不敢说这不敢说那的,现在我退休什么也不怕了。再说了别人怎么不怕得罪我呢!我不怕死,我就惦记着我的机床,我儿子有钱了,出国回来了,我就让他给我把机床买下来。我要安在我家里头,我就让机床转起来,我就爱听轰隆隆的声音。这声音比什么都好听,我听了一辈子都听不腻。我爹让我少说话多做事,我就只能跟机床说话,它爱听。院子里的老邻居们纷纷走出来,入秋了,风有些凉。大家就这么看着我爸爸,月光打在我爸爸的脸上好像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银霜,有了一种十分圣洁的感觉。我妈妈站在我爸爸身后,静静地看着他。记得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大教堂赶上做弥撒,那群人感觉就是我妈妈的样子。
六
1999年,厂子破产了,这块地皮被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看上。家属院子位置因为太靠近里边,没有被圈进去。我爸爸对我说,我要把我那台机床买下来,你去办吧。我皱着眉头问着,你买机床安在家里干什么?我爸爸说,我就天天开着它,愿意听它的动静。我说,你不就害死我妈妈,你天天开机床轰隆隆的,我妈妈受得了吗。再说,每天费多少电,邻居们怎么办呀?这些你都想了没有?你不就是神经了吗?!我爸爸青筋暴跳着,我就神经了,你去找唐主任谈,我舍不得当废铁卖了。我和我爸爸争执,我妈妈就坐在那看电视,好像什么都不管,好像跟自己没有关联。我对妈妈说,你的意见呢。我妈妈说,你爸爸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恼火了,我爸爸要买机床安在家里,天天吵着你,你没有意见!再说,你看看咱家的地界儿就十几平方,那机床放在哪呀。我爸爸说,放在中间。我说,放在中间还怎么进进出出,谁家摆着一台机床呀。我爸爸愤怒地说,我不管你说的那个,我就是起床能看到我的机床。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我脑门子一直在蹿火,说,我要是不办呢。我爸爸跑到厨房抄起菜刀就架在脖子上,我就抹脖子!我妈妈连忙跑过来拽住我,说,你就说你能办啊。我死硬不吭声,我爸爸不依不饶,对我妈妈说,说能办不行,得办成喽!蓦地,我看到我爸爸手下一用力,脖子上已经溢出一泓鲜血。我妈妈对我瞪着眼睛,你是想杀了你爸爸吗!我无奈低下头,有气无力地说,我一定把机床买回来。我爸爸说,我要我那台机床!
冬天了,老天一直没有下雪,总是阴着天,似乎是在憋着。
我好不容易在杂乱的厂房里找到唐主任,他看见我就说,不要提你爸爸买机床的事,现在厂里都说这件事。他神经了,你不会神经了吧。我坐下来,和蔼地对唐主任说,你这个厂子破产了,可你没有。你这块地皮值不少钱,我给你算完了。至少你能赚个六千万。唐主任看着我笑了,你给我算了,我还欠人家七千万呢。我说,我爸爸买台机床算你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不能计算的小零头。唐主任说,已经放在赔偿费里了,二十台机床,合同里一台也不能少。我都给人家签合同了,这就是违约。我问,平均一台多少钱?唐主任说,十万,你掏吗?我被他这句话噎住了,十万在当时就是一笔巨款啊。唐主任说,你爸爸买台机床安在家里,你说天底下有这么样的吗!那是丢我的丑,你现在即便给我十万,我也不会扇自己耳光子,我眼前够丢人的了。说完,他颓然地坐在沙发上,电话不断,听出来都是要钱的。唐主任喊着,我破产了,要钱找法院要去别找我。我只好退出来,见我妈妈在门口堵着,对我说,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说着推开我大脚步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我听见里边她对唐主任的叫喊声,声嘶力竭,以前风风火火的妈妈又回来了。我心酸心痛,觉得好像有小锤子在敲打着我,有小刀子在割裂着我,有粉碎机在搅拌着我。我实在忍耐不住,推门进去,看见我妈妈竟然跪在了唐主任跟前。唐主任对我说,扶你妈妈起来,我卖就是了,三万吧,算我赔了,也算我给老师傅面子了。我看不是他神经了,是你们一家人都疯了。我从提包里拿出来现金三万,这是我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当时银行不给取,说只能给一万。我是找了银行老同学斡旋才取出来,这就是我的全部储蓄,准备娶媳妇的。
我爸爸的机床从厂房里抬出来,然后又搬进我家,这都是我爸爸徒弟们帮助干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用过的机床,碧绿碧绿的,像一个大号的邮筒,又好像泡在海水里。我爸爸上前看了半天,徒弟们说都给师傅您搽好了,也润好了油。我爸爸眼泪汪汪,娴熟地摇了摇拉杆,然后按动了开关,就听见咚咚的声响。院子里都是人,家里只是我爸爸一个人,因为机床把家里的空地都占住了。我爸爸在家里究竟怎么操作的不知道,就听见咚咚的声响传得很远。已经是夜晚了,我看见邻居们都关着灯,院子里黑乎乎的。我问四愣子,怎么不开灯啊?四愣子说,我爹说了,你们家的电量不够,开动机床得把全院子的灯都关上,把电都给你们家才行。我慌了,想进去告诉我爸爸别再开机床了,让四愣子一把攥住,攥得我胳膊生疼。四愣子说,让老爷子过过瘾,这也是我爹的意思!
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飘下来,随着咚咚的机床声悄然而至。院子里白了,没有树叶的枝桠有了绽开白牡丹的感觉。
七
半个月后,我妈妈得了尿毒症。我爸爸不再开机床了,他瞒着我们,三万块钱卖了机床,给我妈妈看病。几天后,我爸爸主动去了街上当了交通协理,说每个月能有补助两千块。我跟我爸爸说,不用,我有钱。我爸爸说,你有多少钱是你的,我要给你妈妈花我挣的钱。我妈妈总是流泪,她对我说,你爸爸胳膊上戴上红箍,负责在街上维持交通。他天天很早就走,很晚才回来。谁路过他维持的那条街上,都会听见他那大嗓门吆喝,见他在街口来回走动,指挥着车辆和行人,比那正经八百的交警都忙碌。你劝劝你爸爸,不用给我挣钱,我活不了多久。你知道,那天抬走你爸爸的机床,你爸爸没有掉一滴泪。三万块钱让我数了一晚上,总问我少没少。他说,你要是走了,我也陪你走。我问他,是机床重要还是我重要。你爸爸说,你重要,二十台机床也比不上你重要。我妈妈总是要到医院做透析,每次都是我爸爸陪着,他不让我去,对我说,每次陪你妈妈去透析,就是给我赎罪。你妈妈得这个病,就是让我气的。我要是还是不说话多做事,你妈妈不会得这个病的。你爷爷的话我忘了,这就是对我的惩罚,结果让你妈妈承担了。老天不公平呀,让我得这个鸡巴病不就完了吗。我妈妈总是恶心,不断地呕吐。我爸爸就不断拿毛巾给她擦嘴,有次我妈妈呕吐来不及拿尿桶,我爸爸就用衣服兜着。我妈妈哭,说,让我死吧。我爸爸就笑着说,你死不了,有我呢。我很少见过我爸爸的笑,没有想到他能笑出来,而且十分灿烂。
那天黄昏,夕阳大大的,像是一粒西红柿。我没开车,是坐公共汽车下班回家,在车上看见我爸爸在指挥交通。人群中有个人议论,说,你们知道那戴红箍指挥交通的老头儿吗,先前是个工人,一辈子没当过官,现在到这过他的官瘾来了。我盯着那个人,那个人看我的眼睛有些发拧,不知所措。我说,他是我爸爸,他就是想过官瘾,你管得着吗。你再说我就抽你,你信不信。那个人说,我不信。我过去就要抽他的嘴巴子,被几个人拦住。那个人下了车,在车窗外跳着脚骂我,说,你爸爸就是当工人的臭命,你就是捡破烂的身子,你们一家就是要饭的。我眼睛红红的,车已经开走了,我发现我的身子在不断抖动。有个老奶奶攥住我的手,颤巍巍地说,不生气,我也是你爸爸那个厂的,你爸爸是好工人。回到家,我爸爸也下班嚷着要喝两盅,说自己怎么没发现自己嗓门好呢。趁着我爸爸高兴,我和他对喝几两酒,妈妈在床上躺着笑着看我们喝酒,桌子上就有一盘炒花生仁儿。爸爸喝痛快了,青筋在额头处蹦来跳去的,那话匣子也打开了。从他小时候到河里抓鱼,讲到当初怎么跟我妈妈恋爱。我忙问,您以前为什么不爱说话,现在话怎么就多起来?我爸爸笑了笑咂一口酒,晃着脑袋缓缓地,我还问自己呢,怎么退下来这嘴就变成你妈妈的了呢。我妈妈又要吐,我爸爸拿起来一个空碗就端在她跟前,吐完了以后出门倒在厕所,回来以后拿那个碗继续喝酒,不断地给我讲我妈妈的笑话。其实,我知道我爸爸心里很苦,因为他的笑话一点也不可笑。
我爸爸喝多了,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打起鼾声。我妈妈给他盖上一条毛巾被。我觉得有些没趣,正要离去,妈妈冷冷地对我说,你爸爸一直在哄我,你告诉我,我还能活几天?我不好说话,我妈妈逼问,你给我说实话,这病后来是不是会肾衰竭。我说,是的。我妈妈凑过来问,还能活多久?我哽咽着,真不知道。我妈妈咬着牙说,你去医院,必须告诉我能活多久。我问,你想干什么?我妈妈垂下头,苍白的头发遮住她憔悴的脸,呜咽着,我不想让你爸爸这么为我难受。我说,那你也不能死呀!我妈妈说,我死了以后,你不要难为你爸爸懂吗,你就让他开心。还有,你要找你爸爸卖的那台机床,那是他的命根子。花多少钱也要买回来,我陪不了他,我也要让机床陪着他。我说,他卖给谁了我问不出来,问急了就跟我嚷跟我拼命。我妈妈说,那你也得去找,这么大家伙不信找不到。我回到自己房间,很久很久没能入睡,从我妈妈话里悟出那份老夫老妻的情感,那是生死不离的缘分。突然,我看见窗外一片白茫茫,我走过去,看见又下雪了。我看见一只流浪猫趴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我总是把窗户开开一条缝,我不想屋子太热,其实也是给这只流浪猫留着一缕温暖。
半夜,妈妈突然晕厥过去,脸色苍白,嘴唇哆嗦,我给她嘴里填着药。我爸爸傻傻地在旁边,抽冷子把我妈妈背起来,撒丫子往医院疯跑。到医院急诊室,检查完了,大夫看了一眼气喘吁吁的我爸爸,是你背来的?爸爸忙点头。大夫说,她是你什么人?我爸爸说,我老婆。大夫说,她吃了大量安眠药,准备后事吧。我爸爸听完扑通跪下,狠狠扇了自己几个嘴巴子。
凌晨五点半,我妈妈与世长辞。我爸爸守了妈妈三天三夜,他没再说一句话。邻居们和厂里的徒弟们都来了,都是我接待,他就这么木木地戳着。谁要是宽慰他,让他节哀时,他就如牵线的木偶一样点点头。唐主任也来了,握着他的手,说,师傅,现在想起来,您是咱厂最好的工人啊。我爸爸没有反应,若在以前,他一准美得屁颠屁颠的。四愣子的妈妈觉得不对劲儿,拉过我悄悄地说,你知道婴儿出生时得打一下屁股,这样就能让婴儿哭出声。我惊诧地问,您这是想说什么?张大婶说,我是想让你爸爸说话,你没看他哑巴了。我突然气恼地说,就是因为他爱说话,弄一台机床摆在家里,天天堵我妈妈的心,我妈妈才走的!四愣子妈妈瞪着我说,你不能这么说话,要让你妈妈听见不得揍你!
第四天,我送妈妈去火化场。我爸爸张口说了头一句,我要送送她。四愣子的妈妈忙拦说,你别去了。我懂得大妈的意思,这里的风俗是不让男人送去世的女人,因为送了就意味着男人不能再婚。大妈显然是为我爸爸着想,眼睁睁爸爸才不到七十岁,身子骨还很结实。我爸爸摇摇头,说,我一定要送她。火化前,我爸爸拽下来我妈妈的一根头发,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然后拉着我妈妈的手,颤巍巍地说,我害了你,我不该退休了说那么多的话,管那么多闲事,还折腾着把机床买回来。我应该还和从前一样,少说话多做事。这话还得由你一人说,我抢了你的话,我痛快了,你就憋囚了。说罢,两粒混浊的泪水凝聚在我爸爸的眼角深处。
八
半个月以后,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天气有些回暖。
我爸爸在街上维持交通,红箍底下压着黑箍。有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撞了个过路的哑巴,两人冲突起来。我爸爸过去,指着小伙子呵斥着,他是哑巴,你这不欺负人家不能说话吗。小伙子和我爸爸闹起来,情急之下,小伙子拿摩托车撞倒了我爸爸。这一撞,我爸爸就没再起来。我在清点爸爸遗物时,发现上衣口袋里有我妈妈一根头发,用红布细心地包裹着。大妈说,这是你爸爸和你妈妈上辈子就定下的结局,要走两人一起走。我说什么也不信。我妈妈在黄泉见到爸爸,是不会饶恕他这么轻而易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上百个交警主动去送我爸爸,每个人胸前都戴着一束白花,场面感人。有一个年轻的交警哭着对我说,每天我听着你爸爸大嗓门吆喝,好听,也有韵律,就是享受。人也显得踏实,腰板就能挺直。现在听不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
2009年,春天来得特别早,空气燥热。
我已经是设计学院的副院长,成家立业。担负了工业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并且为此获得了国内著名设计奖。开馆那天,我戴着红佩带走进馆里,在三楼意外发现了我爸爸那台老机床。我几乎是扑过去的,眼泪夺眶而出。陪同我的人面面相觑,我说,这是我爸爸开了三十多年的机床。我说,能不能在机床前摆上我爸爸的照片,因为他曾经把这台机床买回家,在家里天天擦洗。为了治我妈妈尿毒症的病才卖给人家。这时候捐献这台机床的人慢慢走过来,我才看清楚,竟然是唐主任。他说,这是你爸爸的机床,也是我的机床,我从你爸爸那买走就是给我证明。我的企业可以破产,但我的机床还在我手里。我喊着,我要摆上我爸爸的照片,我要我妈妈知道,我找到这台机床,我让我爸爸始终陪着它!所有人都被我的喊声震慑住了,包括唐主任。馆长走过来说,一定,你把你爸爸的照片给我,我们将放在这台老机床跟前,告诉参观者,这台机床的主人是谁。有人认为中国导弹都上天,可以精确打击了,可就是细小的零件造不出来。一个外国公司在中国需要轴承,要求精度很高。可是谁的车床的能力都达不到精度,最后有一家用轧的手段才基本符合要求。国外专家看过之后摇头,说不行,技术太粗糙,轧出来表面有应力,时间长就根本不能用。最后是用的金刚石刀具才解决了问题。这台机床是美国三十年代的,应该说保存得相当不错,这跟你爸爸有关系。我们找专家研究过,你爸爸使用这台机床的能力十分厉害,没有磨损任何部件,现在像你爸爸这样的技术已经没有了。
听完馆长这句话,我给机床跪下,我眼眶充满泪水。恍惚中,看见我爸爸和我妈妈走过来,然后就觉得眼前都是湛蓝色。我掉进了一片浩瀚的大海之中,波涛澎湃……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