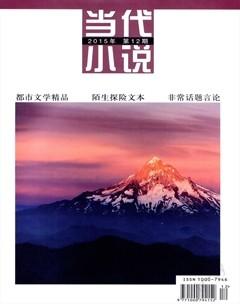孤魂
杨袭
1
那个标有“于小聪”的女尸,是在一个阳光近于焦灼的正午,被我的大嫂马小买发现的。
马小买不厌其烦地、反复对我讲述当时的所有细节。那时候最后一场秋雨已经在几天前浇透了大地。泥河两岸潮汐一样涌伏的苇荡早吸饱了雨水,然后决绝地把自己的腰身压垮。又经过了几个阴霾的天气,由褐黄变作灰蒙蒙一片。在突然高爽起来的天空中,几枝不肯屈服的苇秆迎着渐起的东北风,很有傲骨地挺立着,在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的寒流中瑟瑟发抖。
马小买从下河的娘家回来,急匆匆走上河边野径,行至沿河路尽头,向北转上大路时,被草丛间一只惊起的树鹨吓了一个趔趄。那只轻灵的树鹨,大约是受了马小买的惊吓,从灰褐色的枝丛中乍然飞起,背颈间橄榄绿色的条纹为初冬沉闷的原野划上一道轻浅的亮光。马小买抓起身边的一把苇秆子,拍着胸口,目光于惊魂未定间跟着那道弧形的绿光,瞥见了汤汤河水之上那块绿色的浮物。
须臾之间,马小买就断定是具尸体——这几年,泥河从上游带来的,除了在河的另一尽头巴颜喀拉山麓溶化的冰雪和黄土高原的沙土,就是尸体。早年间,三五年间,漂来一具,都是须发蓬生、衣不蔽体,一看不是流浪汉就是精神病人。总之,引不出泥河人太多的感伤与惊惧。但这几年不同了,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河水开始将各式各样的尸体送来下游,漂在河面上,冲到河肚子的浅滩里,搁浅在河海交汇处的沙洲上,或者,干脆用长头发、手脚、衣物上的钩或者碰巧了的哪一处挂缠住下河游泳或捕鱼的人的腰脚,让他们在一阵忙乱的纠缠之后吓得三魂六魄先出了七窍。
“王母娘娘、玉皇大帝、土地爷爷、泰山老母……”
马小买拍着胸口颠倒地念着众神的名字,拿两只胖手搓着额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珠。四周风吹芦苇和兀立其间的绵柳树和荆柳丛。适才还风清日丽,眼下似处处鬼魅憧憧。马小买裹紧暗紫色的薄呢子外套,迅速拐到了通往泥河大街的稍宽一些的路上。边走边感觉头皮发紧,后背发虚。好不容易出了王家巷子拐上大路,置身熙熙攘攘的泥河大街上,马小买松了口气,努力地调整表情,与相熟的街坊们搭过话,朝东走了几步之后停住脚,又转身朝西,走了一百多米,走进徐三麻纸草铺。
我的大哥吕建功傍晚回家,撞见马小买在院子的一角烧纸钱。吕建功发现在明明灭灭的火光中,马小买神情恍惚。非初一非十五的烧纸,马小买的举动和神情都让吕建功非常不解。在后者的再三追问下,马小买说了下午在泥河边看到浮尸的事。
吕建功听后先是问马小买有没有报警。待马小买恍然大悟,赶紧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时却又朝她摇了摇头,告诉她“先沉沉”后,转身走出家门。
事后,马小买有些得意地告诉我的母亲:看他整天呆头呆脑的,关键时候,我没想周全的事情,倒让他先想到了。咱们自己用不到,说不定哪天谁家用到,到时候,咱们至不济,也落个大人情呢。
2
我伯父在五年前的三月,桃花正盛之际,失去了伯母。从此开始了孤独的老年生涯。伯父青年入伍,上过军校,转业到县教育局。五年前退休后,带着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伯母回到泥河,修葺了旧院,安居在了我童年时就已经有些阵势的五棵大枣树下,开垦了近处的、被我父亲多年来因在外谋生荒弃的一亩六分自留地,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农夫。
因为他家的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的大哥二哥,没有顺利接到他在教育局的班,对他们的父亲、我的伯父就有些气。平时没地儿出,伯父想回老家找他们要回旧院时,他们就找到了讨回并不曾失衡的公道的办法。赶在伯父回乡之前,两人做主,凑钱翻盖了老屋,租给街面上太平洋网具店当仓库。伯父无奈,只好朝自己的弟弟、我的父亲开了口,最终安居在我们家的老院子里。
在老家落稳脚两个多月后,窗前的石榴花初绽之时,下午一点左右,伯母身穿浅灰底儿上面缀着空心白星星的短袖上衣,下身着浅灰色的麻布长裤,穿着一双黑色镂空面的软皮鞋,提着一只卡其色小帆布包走出家门,一去不回头。当时伯父正穿着马夹背心,手里挥舞着一把新瓦刀,在大门后面翻新鸡窝。伯母在打开大门时,伯父以为她要到对门“吓小猴儿”,这是一种对门的奶奶为哄我伯母高兴即兴创造的小游戏,那些日子伯母乐此不疲。为此,伯父为表达谢意,送了对门的奶奶一床夏凉被,这是教育局送给他的退休礼物。对门的奶奶收下了凉被,送了我伯父一些笨鸡蛋。并鼓励我伯父也自己养鸡,我伯父早就知道笨鸡蛋与市场上面买回的鸡蛋的种种不同处,这次受到鼓励,便立即行动起来,买回一三轮车新砖头和沙子水泥,有模有样地盖起了鸡窝。我伯父叮嘱正要出门的伯母“早回来”,我伯母则斜着眼看了伯父一会儿,笑了笑走了出去。我伯父也笑了笑,回身继续盖鸡窝。伯父在下午四点半(伯父有随时看时间的习惯)砌好了鸡窝,收拾好工具,打扫好战场,洗把脸,穿上衬衣到对门接伯母,才知道伯母那下午根本没过去。这时候伯父还没有警觉,以为她到了大街上的某个店里。伯母来泥河后,有几次到街上的店铺里,站在货架之间,对着五颜六色的商品和川流其中的顾客嘻笑不已,表现出了极浓厚的兴趣。
那天,伯父从街东头找到了街西头,急躁情绪在站上街西首的小石桥时达到了顶点。伯父掏出手机给我们叔伯兄弟姐妹都打了电话,伯父在电话里说:
“回来吧,都快回来吧,小娟丢了。”
不管对谁,伯父都称伯母的名字,小娟。这是伯父对伯母特殊的情感吧。伯母自小生在城里,一辈子都不情愿到泥河来。在她的印象中,我的家乡泥河始终与脏乱和粗鲁联系在一起。
这个与泥河格格不入的女人,到了晚年,在最讨厌的土地上把自己弄丢了。
我们找了两天才想起报警,又在街上贴了告示,还重金登了电视寻人启事。到后来,离我伯母失踪两个半月时,大哥吕建功在入海口的一片沼泽地里寻到了我伯母的一只鞋。站在家门口盼归的伯父看到了这只鞋,知道伯母再也不可能找到了。
在泥河,所有精神有问题的人都爱朝东走,如果没有被家人或者乡邻及时阻止,就会一直向东,顺着泥河的方向,和泥河水一样扑进渤海,最终,与澄蓝的海水和浑浊的河水化做一体。运气好的一段时间之后,骨架会被冲回到浅滩上,远远地看去,像只惨白的原木茬脸盆架;再好运的,尸身在未被鱼蟹吞吃之前,再一次被浪头冲回到岸上,家人就念着“阿弥陀佛”收了尸好好安葬。伯母是最不幸的一种,只留下一只鞋。不过大嫂马小买说,这也是幸运了,如果冲回一具尸骨被伯父看见,“那真是要了他老人家的命了。”
伯父将这只镂空面的皮鞋狠狠地摔到地上,说:
“再让你跑!再让你乱跑!”
说完回到院中,很长一段时间,不肯见人。
伯父很快瘦下来,也长了更多的白头发,两年后的八月十五,我们回家看他时,远远地看见他站在胡同口,耸着肩膀,前一年正合适的西服架在他身上,像临时捡来的比他高大太多的人的衣物。他见我们走近,突然跑上前拉着我母亲的手回到家门口,弯腰在地上找来找去:
“哎,哎,那只鞋呢?”
我母亲吓白了脸,伯父则暂时放开母亲的手,摊着两手对我父亲说:
“我刚刚摔在这里,转头就——哎,准是被哪家的孩子——”
伯父在低头找鞋时发现我母亲两只脚上都有鞋子,伯父慢慢地由下而上看清了我母亲的脸。伯父怔在当地,不安地搓着手,好像再也想不起自己刚刚做错了什么事。
那天,我母亲说,该给伯父找一个老伴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父亲则担心我的哥哥和嫂子们不同意。但出我父亲意料的是,对我母亲的提议一致通过。我的大嫂马小买还马上站出来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她说吉林(泥河镇的一个村名)她有个表姨,去年刚刚守了寡。马小买形容她的表姨,平头正脸,面目和善,身体也好,年龄也相当。我们全家人一致同意,说先让老人见个面,如果感觉合适。我们就好好成全,希望他们也彼此照顾,安度晚年。
三天后,我母亲接到了马小买的电话,说两个老人已经见了面,彼此都说还好。我母亲很高兴,说找个日子,家里人都回去,请她表姨吃个饭,认识认识。马小买也挺高兴,又说了通家长里短的话,约好了回去的时间,就定在九月九,重阳节这一天。
我父亲对母亲说,也许,建功和建业知道自己做得过了,想在这件事儿上好好弥补。我父亲还夸他们进步了,知道反思了。还说一个经常反思的人,心地不会差,心地好了,运气就不会差,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在重阳节前一天,我母亲又打电话给马小买,问好了她表姨的身材,到商场买了件开身的羊绒衫,算是见面礼。我母亲也挨个嘱咐我和姐姐,说明天回去,都要准备点东西,不必太贵重,哪怕是吃的呢,别让人感觉咱们拿人不当回事儿,也失了礼数。
重阳节我见到了马小买的表姨,姓刘,我们后来都叫她刘姨。确实如我大嫂马小买说的,圆脸,长得和善,人也喜相,吃饭时为我伯父夹菜,自然流畅,俨然已经是老相熟。陪她来的是她的大儿媳,看当天的样子,也比较满意。
我们一家人,以为这事儿就成了。
母亲可能感觉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女人,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吧。所以,在我伯父找老伴的事儿上,很上心。重阳节的第二天,我母亲打电话给马小买,问是不是要择日办喜事儿了。
马小买告诉我母亲,中间出了差错。我母亲一听,心一急,连着猜了好几猜,诸如是不是人家嫌咱们家人多,或者,是不是看出我伯父有什么不对付处,甚至,母亲怀疑是不是人家嫌她这个做弟媳的拿的礼物太不够“意思”。
都不是,马小买费了好多的口舌。才对我母亲解释清楚。
3
伯父和刘姨,是没问题的。两个人还算是投缘,不断的接触中,彼此都有好感。
一开始,双方的儿女,也是没有异议的。这年头,有几个想不开的,只要对老人好,就行了。
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这问题是从假设伯父比刘姨晚离世开始的。
那边的二儿媳妇,也就是马小买的二表嫂提出了异议。她说,那这事儿成了后,如果我伯父先离世,问我们这边是不是继续对刘姨行赡养的义务呢?
之后,我伯父家的两哥和一姐都表了态。说这个请他们放心,要真是伯父先走,只要刘姨再不改嫁,就一定好好赡养老人,说但凡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老人。
马小买原话传达,那边还算比较欣慰。但刘姨的二儿媳妇马上就听出了问题。她说,什么叫“不改嫁”?还问马小买,难道,伯父和刘姨的事儿,还得三媒六证不成?
马小买也马上从她二表嫂的话中听出了端倪。她接上话头表达了我们这边的观点,说,难道,让自己的老人临时凑个伙?不当个正事儿办?
马小买的话也藏着厉害,什么叫临时凑个伙儿?什么叫不当正事儿办?那边立即说,看你这话说的,这不叫不当正事儿办。老人也这个年纪了,两边都是一大家口,儿子孙子一大堆呢,打断骨头连着筋,有些情分是割不断的。
马小买对她表嫂说,明人不说暗话,你就明着说吧,反正,都是为了老人。
那边就表明了态度,说他们那边对我们这边在对赡养老人的态度上非常满意。还说这样吧,只搬到一起搭伙住,叫着亲戚朋友吃顿饭做一个证,就不领结婚证了。
马小买对我母亲说,你看,他们多毒啊,还留着这样的后手。话中完全没了亲戚间的情分。
我母亲就明白了。
现在,在泥河,随着老人再婚的现象渐增,形成了个不成文的习俗。领了证,女方身后,骨灰就留下,与男方合葬。否则,身后就回归再嫁之前的本家,与原配合葬。相对照的,如果是领了证,来到男方,而男方又先走一步,男方的子女就要对尚在世的女方尽赡养义务。像我伯父这样的,伯父身后,她还要领一部分政府发的抚恤性的补贴。相对的,没领证,男方先走,女方就回归本家,由原来的子女赡养,或另外自行想办法生活。
按照马小买提供给母亲的信息,刘姨的子女们,既想让我们这边赡养刘姨,直到终老,又不想领证,也就是,刘姨身后,骨灰得还给他们,与他们的父亲,刘姨的原配合葬。
而按我的老家泥河的风俗,埋孤坟,对儿孙来说,是很不吉利的。是“妨子孙”的。
后来我母亲私下里对我说,这也许是,我伯父家的哥、姐们,急切地想为伯父找个老伴的另一个因素。
我母亲立即在电话中表达了愤慨,我母亲说,哪有这样的,既想——又想——。我母亲想起了那句很难听的话,但可能想着那边和马小买的亲戚关系,没有完整地说出口来。马小买也说,可不,这真是既想什么又想什么了。不行就散屌伙!
马小买最后在电话中说了句粗话。
我们都寻思就这样散伙了,一拍两散。但事情最终不是这样,两个老人一直在交往着,一起在伯父小院子中做个饭吃个饭,到镇后的水渠边散个步,互送个什么小礼物,你来我往的,感情稳中有升。
直到有一天,我伯父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大哥吕建功,他要同刘姨去民政局领证了。讲话一向直白的大哥吕建功,就把前阵双方子女的话告诉了伯父。一向沉稳有余的伯父这回傻了眼。但最后,伯父片面地将双方的争执归总在了经济问题、刘姨的赡养上,他跺着脚说,再不行,到我们不行时,一起喝药,都死球算了。
那也不行。吕建功坚定地说,死了,她的骨灰还是要还回去。
这一下,我伯父再不说话了。他后来对我小姑说,他突然想起我伯母。他突然想,小娟,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她还光着一只脚……
我伯父的眼中霎时充满了泪水,也一下子明白了他再婚的所有意义。
明白后的伯父还与刘姨交往着,但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少笑了。这是后来刘姨对我母亲说的。
也有三年不少的时间了,刘姨和我伯父就这样半冷不热地交往着。刘姨那边的子女们通过马小买向我们这边表达过多次愤怒。说要再这样下去,他们就来泥河,找我伯父的“麻烦”。
一个傍晚,马小买看准刘姨要回去时,在后面跟上她,走出泥河大街,转到去吉林的小路上时追上她将现下的状况说给了她。
刘姨听了马小买的话,落了几滴眼泪。但很快,就平复下来。刘姨对马小买说:
你小姑子现在也正处着对象,你没有问问她,是不是可以不领证,就搬到人家家里去,给人家当媳妇?
刘姨又说:
小买,别说我刻薄,在我看,这事儿,不论老少,天下一个理儿。
刘姨一句话堵得马小买喘不过气来,但马小买“没有跟她一般见识”。马小买又紧跟了几步,同她说起骨灰的事。刘姨听后,盯着马小买的脸说:
什么骨灰,我死后,你们(我想是包括了双方的子女吧)就把我拖出去喂狗好了。
马小买被气得不行,给我母亲打电话。恰巧,那天我母亲不在家,这电话就被我接到了。马小买冲我反复强调了好几遍,马小买说:
你说,这叫什么话,什么叫拖出去喂狗?她这不是老糊涂了,悖晦么!我在跟她说正事儿呢,她倒这么戳我肺管子。我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他们么!为了这个家么!我图啥呀我!
我不是我母亲,无论是对我的这些嫂子们还是对姑姑们,总是有适当的话来安抚。我只能反复地小声说,是啊,是啊,对呀,对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马小买却好像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最后说:
哎呀,想不到,咱们吕家这么一大家子,还是你这个小姑子最知道嫂子、心疼嫂子。
4
按照马小买的说法,“于小聪”就是上天送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后来,我听母亲说,在这之前,吕建功和吕建业曾经去扒过一个孤坟,是十多年前死去的、来泥河十六队谋生的一个齐河女人,来时带着个八九岁的闺女。闺女大了,和来镇上打工的一个外地青年搞恋爱。最终不顾她的坚决反对,跟着那青年,到了东北一个叫虎林的地方,据说是个农场。后来,齐河女人好像又为此非常骄傲,对人说,人家是农场的,俺闺女一嫁过去,就能吃公家饭。泥河街上的人,对她的说法半信半疑——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还来这里打工?可谁会拿出工夫和精力计较这个呢,时间一长,什么说法也随风飘散了。只是女人,在六十多岁上,得了一种叫“老鼠疮”的病,病中一直找人按照闺女走之前留给她的地址写信过去。从没收到回信。生前,她一直在骂邮电局的人,说他们将她闺女给她的信弄丢了,咒他们不得好死。每次见了镇邮电所的小刘,都追着骂好远。她病死后,还是邻居们搭了把手葬的,就葬在镇北四五里外的黄河坝下。吕建功和吕建业寻找好位置,夜里带着手电筒和铁锨将坟挖开。
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半爿折断的薄棺材板。
——齐河女人的尸首,早被人盗了。
早不知道与哪个可怜人做了生前从未谋过面的夫妻。
先下手为强。
那天,我的大哥吕建功在街上五金店买了个铁钩子藏袖子里,又在劳保用品店买了一大块黑塑料布。鬼鬼祟祟地转到河边,他看到,马小买描述的“绿鼓囊的东西”已经在河肚子里被翻到河那边。吕建功沿河向西,翻过水泥桥到了河南边的野地里,他弯着腰,尽力隐在草丛中,靠近鼓出河面的绿衣服。靠得足够近时,抽出袖子中的铁钩子,将河中的尸体翻了个身。
他看到了女孩的脸。
紧接着,他迅速将女孩拖到了岸上,展开黑塑料布将她蒙住,在草丛中安置好。按照我家乡泥河的说法,死去的人见了光是不得超生的。吕建功还是想尽量对得住她。蹲在草丛中摸出手机,让我的二哥、他的亲弟弟吕建业扛上两张铁锨赶紧过来。
吕建功掀开黑塑料布的一角,吕建业第一眼没看清楚。拿手又往上掀了掀,吓了一大跳。同时看到了女孩衣领外面心形的链坠,吕建业避着身子将手伸到黑塑料布下面拿过来,凉洼洼的,瘆人。一捏之间,小坠子打开了,张开的两面一面是张尚未被水浸透的大头照,一面有三个字:于小聪。
兄弟两人对视一眼。
可怜的闺女。
吕建业说。
幸亏遇到你嫂子。
吕建功说。
不然,还不知道会漂到哪里去。
最后一句话让他们同时想起了他们自己的母亲。
兄弟俩挨过了好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在草丛中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和存在的几种可能性。最后,吕建业说:
你给嫂子打电话吧。让她跟那边说。我们都替他们找到了。这个人情他们该领。他们要愿意,我们在天黑透后给他们埋上。
于是,吕建功就让马小买打电话,让她跟刘姨的二儿媳妇“交涉”。大哥吕建功用了“交涉”两个字。我觉得有点别扭,但又说不出因为什么,本来,就是双方在“交涉”么。
马小买那天的“交涉”很艰难。
她费了好大工夫才让对方听明白——有个机会,既可以使老人顺利登记领结婚证,使我们这边能接受为刘姨养老送终的问题,又不会让他们家出现孤坟。费用我们这边出。只要他们同意我们这边在合适的时候为他们的父亲找个“阴亲”、与他们父亲合葬就可以。
啊,你这不是让我们卖娘么?我们娘好好的,我们找什么阴亲,你们这是在骂我们吧。
刘姨的二儿媳妇说:
别看我们土里刨食,但婆婆我还是养得起。
马小买也激动起来:
——养得起你还让我们养?
——让你们养是因为你们爹哭着喊着要娶。
——我们娶就要领结婚证!
——我们不卖娘。
——不是你们要卖娘,而是你们娘自己要到我们家来。
——去就去吧,她的户口本身份证在我们手上呢,生是你们家的人,但死——
马小买哈哈大笑着告诉我,刘姨的二儿媳妇这句话没说完。一个聪明人是不会允许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的。马小买笑归笑,问题最终没解决。
——因为,当刘姨聪明的二儿媳妇挂了电话,意识到他们那边要占主动权,来到泥河我伯父家里想把刘姨找回去时,发现我伯父的大门紧锁着。刘姨的大儿子翻墙到了屋里,屋中空空如也,家具、生活用品一件没有,墙上连张画都没留下,干净得像从来没有人住过。刘姨的两个儿子见砸无可砸,激动中挥铲劈坏了我们家的五棵大枣树。
我大哥吕建功在泥河岸边接到了大嫂马小买的电话。马小买对吕建功说:
你快回来吧,他们俩私奔了。
吕建功先是一惊,后来耸了耸肩膀,指着“于小聪”对吕建业说:
没地儿埋喽!可怜的闺女。
但最终,经过商议,吕建功和吕建业还是将“于小聪”埋在了泥河南岸的红荆林中。
然后,扛着铁锨回家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