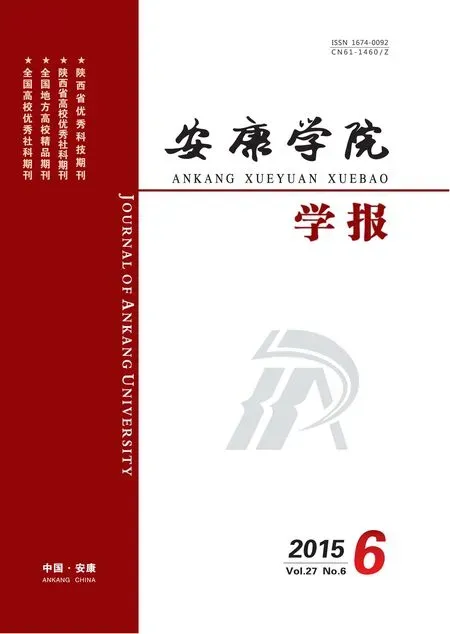宋词中的繁荣都市——以柳永词为例
杨麟舒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唐代及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大都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都城宏伟富丽,如齐之临淄,楚之郢都,赵之邯郸等。汉代以后,长安、洛阳、建康(今南京)等地更是成为繁华城市。经过发展积淀,到了宋代,“城市数量、规模以及城市居民数量和生活质量,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国家和地区,也超过了宋代以前中国的所有朝代。”[1]6唐代及以前,诸如长安、洛阳、成都及建康(今南京)等大都会虽然很繁华,但是,城市的商业区和居住区是各自独立并实行封闭管理的,即“坊市制”。拿唐长安来说,城区街衢绳直,整齐划一,“南北向的11条大街和东西向的14条大街纵横分隔为110坊(包括两市)……白居易形容这种布局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而且,坊与坊之间筑以高墙,坊内亦设有东南西北四市,加之宵禁制度,城市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宋王朝建立后,与辽缔结“澶渊之盟”,“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3]4163,迎来了太平盛世。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代城市众多,其中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而且,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说,京城市民的资产在十万以上的比比皆是,家产百万者不足为奇。在这样一个兴平之世,繁荣的都市作为市井之民的舞台,展现着太平繁华。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宋都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4]1。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亦直观地展现了宋都汴京的民康物阜。
一、承平盛景
有宋一代,城市繁荣,经济发展,加之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的政策,市民阶层渐渐壮大,享乐之风极为盛行。而词作为宋代的重要文学形式,自然也成为了描绘承平盛世的画卷。宋太祖得天下后,为防止“黄袍加身”之事重演,收兵权于诸将,对待士大夫也极为优厚,据《宋史·石守信传》载:“士大夫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3]8810宋代社会,宴饮游乐成为社会风尚,蓄妓得到政府许可,不论是公宴还是私宴,都会请歌妓唱词助兴,酒楼茶肆也会有歌妓唱词招客。市井生活的丰富促进了词的发展,许多词人都留下了不少描绘都市生活的词作,如欧阳修的《生查子》,李邴的《上元》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等。几乎在所有词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都市风光、市井生活和节日盛况。但是,“如果把写作的年代、作品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这些要素综合起来进行打分的话,毫无疑问,柳永是宋代写民俗的第一词人。”[5]
柳永生活在升平时代,作为词坛巨匠,亲眼目睹了都市的繁荣盛景,他用词作展现了这承平之世的艳阳美景、朱门院落和狂欢极乐的民生百态,亭台楼阁、山程水驿、市井红颜……无所不包。在《长寿乐》中,他写道:“妆点神州明媚”①本文所引柳词皆出自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将京都的热闹繁忙描摹得生动可喜,“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何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又展现出了盛世文人的热情和轻狂。在柳永笔下,苏州的风光是“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红楼”(《木兰花慢》),“万井干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搂”(《瑞鹧鸪》);扬州的风光是“酒合花径仍存,凤萧依旧月中闻”《临江仙川》);成都的风光是“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一寸金》)。物华天宝,繁盛富丽,种种气象令人心向往之。在柳永的此类词作中,最令人称道的当属写杭州的《望海潮》。在宋代,浙江一带“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3]2177,杭州作为北宋的大都市,更号称“天堂”。柳永的《望海潮》华词丽句,道尽杭州繁华,据说金主完颜亮听闻此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6]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加之坊市制度被打破,人们活动和交易的时间限制、地域限制被逐渐解除,新兴市民阶层扩大,都市酒楼茶肆沿街林立,勾栏瓦肆和青楼楚馆蓬勃兴起,街市的商业和大众的娱乐兴盛起来,市民在一派繁华安逸的气氛中享受着盛世之欢。在风雅舒适的都市,节日盛典层出不穷,“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时节相次,各有观赏”[4]1。宋代的词人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节日的升平气象和游乐盛况都有所展现。赵长卿的《探春令·早春》、郭应祥的《鹊桥仙(立春除夕)》记述春节;欧阳修的《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和张先的《木兰花(龙头舴艋吴儿竞)》是描画清明春游;黄裳的《减字木兰花·竞渡》及吴文英的《澡兰香·淮安重午》书写端午民俗。在柳词中,《木兰花慢》中“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翠管,万家竞奏新声”写清明冶游;《二郎神》中“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鬓相亚”述七夕望月穿针;《应天长》中“偶露凄清,正是登高时节。东篱霜乍结。绽金蕊、嫩香堪折。聚宴处,落帽风流,未饶前哲”抒重阳之感。在这些词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宋代繁华都市的市井风情、升平气象和精致生活。由现存词作来看,上元佳节无疑是宋代最热闹的节庆,“赵匡胤在乾德五年正月甲辰,以年丰米贱无边事为由,特召开封府在上元节时,更放十八、十九两夜,宜纵士民行乐,自此便为惯例。”[7]许多词人都作词言汴京元夕之热闹华丽。宋祁在《鹧鸪天》中说上元的汴京是“车如流水马如龙”,李清照回忆中的上元节是“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永遇乐》)辛弃疾描绘的元夕景象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青玉案·元夕》)而在柳永的词作中,上元之时,整个帝京“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此番游乐盛况,是当时市民生活的真实展现。
二、帝京情结
宋代词作中,很多词人都对帝京情有独钟,宋祁曾写过:“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玉楼春》)欧阳修曾作下:“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御带花》)李清照更回忆道:“中州日盛,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而对于柳永来说,帝京在他的词作中,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即使是离开了都城,他对于这座王城仍旧没有忘怀。漫游客居在外,柳永的心是飘荡不定的,京华岁月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国文学并不乏羁旅宦游、怀恋帝都的作品,京都在文人心中,大多以政治、权力中心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人士子心中,博得功名、出仕做官是人生价值所在。京城作为中央集权的中心,有众多的仕用机会,在帝京任职、被帝京接纳,就代表仕宦前途成功与否,而“远离京都,隐居乡野,则象征着脱离政治、无意功名;而被贬出京、谪居偏远,往往关联着政治失意和生命惩罚”[8]。从某一层面上来说,京城就代表着文人士子人生价值和毕生理想。柳永作为广大士子中的一员,作为仕宦之家的后代,他的理想也是求取功名、立身朝堂。滞留京华,柳永无疑是想要跻身朝堂的,但是天不遂人愿,柳永长期混迹市井青楼,作下艳词俚曲,在初试科举失败之后,还失言吟出“明代暂遗贤,如何向”。这些放荡轻狂的举止当然使他见斥于统治阶级,26岁应考,直到51岁才终于及第。坎坷的仕途对于柳永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在柳永的身上,除了传统士子的入世精神,更多的是一种“争不恣狂荡”的反叛色彩。滞留京华的岁月,流连坊曲,沉溺娼馆,他的身上沾染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因此,柳永的怀恋帝京之词,大多和功名朝堂、政治生活无关,而是回忆帝京风物,书写对城中歌舞爱情的怀念。在离开京城漫游天下的岁月里,他甚至“创制了以对帝京的‘梦’和‘忆’直接为名的词牌﹙如《梦还京》、《忆帝京》﹚……对当时的时代风貌、社会文化亦有着充分而深入的描绘。”[9]在众多的篇章中,《戚氏》是柳永自创的长调,在作者的追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帝京的生活风貌,不仅有如画风光,还有宴饮歌舞。知交好友尊前作乐,交游吟唱,绮陌红楼,佳人相伴,柳永的“暗寻思、旧追游”是对宋代社会生活侧面的展现。在《宣清》中,词人也对“神京风物如锦”作了以下描述:“念掷果朋侪,绝缨宴会,当时曾痛饮。命舞燕翩翻,歌珠贯串,向玳筵前,尽是神仙流品,至更阑、疏狂转甚。”
柳永的羁旅行役词流露出了极强的恋都情绪,但他追忆缅怀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帝京风物、民生百态和感情生活。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评论道:“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10]在羁旅行役词中,他描画的风光更为广阔清丽,视角也更加开阔成熟,其中的感情也更加纯澈动人。从中,我们可以跳出“词为艳科”的定位,作为史料的补充,感受柳永笔下的民生百态和帝京风貌。陈振孙形容他的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11],黄裳也曾评价其词“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12]
三、盛世红颜
“作为一个朝代,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强厉攻势下,军事上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战争只是生活和历史的一小部分,宋朝也不是一个因军事实力称霸于世的朝代,它是一个因城市繁华、生活品味精致而称名于世的朝代。”[1]135在宋人眼中,美景风光、宴会佳节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红颜美人和琴弦筝歌使生活更加精致。以卖艺为主的歌妓,“既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里供职,也可以在营业性的酒楼妓馆里从业,还可以在私人家庭里服务”[13]。作为一种职业,歌妓就是当时的歌手艺人,她们出入歌宴舞席,侍奉权贵,或者结交文人士子,在各种宴集中唱词侑觞,洪迈在《夷坚志》中曾记载了一次宴会,宴会上,“侍姬十数辈”,“分列左右,或歌或舞”[14]。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专设“京瓦伎艺”一章,其中提到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等众多著名艺人,从名字来看,他们大部分应该是女性。这些佳人美姬是繁华都市最富生命力的一部分,甚至是都市娱乐精神的灵魂。柳永早年困居京华,流连坊曲,混迹青楼。青年放纵,管弦新声和红妆歌舞在柳永心里代表着对盛世的歌颂和及时行乐的追求。在经历科场败北之后,柳永曾自诩为“白衣卿相”(《鹤冲天》),生活放荡,沉溺于歌楼舞榭,歌儿舞女、秦筝弦歌、追欢买笑在柳词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以至于世人皆把柳永看做风流词人。其实听歌观舞是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孟元老说:“燕馆歌楼,举之万数。”[4]452许多权贵和文人在宴会上都会与歌女相伴,晏殊、苏东坡、范仲淹都有香艳轶事传世。柳永写为众多美姬作词,自然也是无可厚非。无论是“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还是“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看花回玉磩金阶》),柳永的词作总能反映出市井生活最香艳的一面。但须知柳永是个极悲情的落魄才子,他是不得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这些艳词俚曲和歌妓的情意是他坎坷人生中仅有的慰藉。所以,柳永写女子,不再如花间词人,把女子当做物品赏玩,也不像达官权贵,将歌妓视为贱民玩物,他与歌妓惺惺相惜,为之作词谱曲,引为良友知音。柳永同情歌妓的悲苦境遇,他尊重妓子的所思所望,也懂得女子的悲欢愁苦,他抒写的女性的心曲和对爱情、对生活的向往细腻真挚。柳词之中,有一部分女性代言体词,在这些词中,他以女性的身份传达了民间歌妓的呼声(如《迷仙引》)。在他的心中,歌妓不是自甘堕落的贱民,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理解她们对于正常家庭生活的向往,将同情的目光转向她们“一生赢得是凄凉”的凄苦身世。在《少年游》中,柳永替她们道出了“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的悲苦心声。在《集贤宾》中,他大胆真诚地将歌妓引为知己,真诚希望与歌妓虫虫结成婚姻。甚至,他还为离世的歌妓写下悼念之词(如《离别难》《秋蕊香引》),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对待妓子,毫不避讳与妓子结下深厚情谊。
总之,柳永都市题材词作,不仅是宋代文人生活的缩影,更是兴平盛世之欢的折射。“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15],他的词集中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繁华都市。从城市风光到节日盛典,从帝京情怀到如花美眷,我们可以看到“汴京的都市生活为宋代词人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养育了大批‘都市词人’,宋词再现了宋都的繁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北宋汴京那种极为普遍的都市生活。”[16]
[1]吴琳.词中城市:品读宋词中的人文景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2]盛会莲.唐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99-102.
[3]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5]曾大兴.柳永《乐章集》与北宋东京民俗[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34-40.
[6]罗大经.鹤林玉露[M].孙雪霄,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0.
[7]伊永文.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宋代城市风情图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53.
[8]曹志平.都市的沉沦与挣扎——论柳永的恋都情结及其文化心态[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1(5):47-51.
[9]贺闱.柳永节日词研究——兼议其帝京情结[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80-86.
[10]吴曾.能改斋漫录(下)[M].全宋笔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88.
[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6.
[12]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王兆鹏.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J].文学遗产,2004(6):51-64.
[14]洪迈.夷坚志[M].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765.
[15]叶梦得.避暑录话[M].全宋笔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85.
[16]董浩麟.汴京与宋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