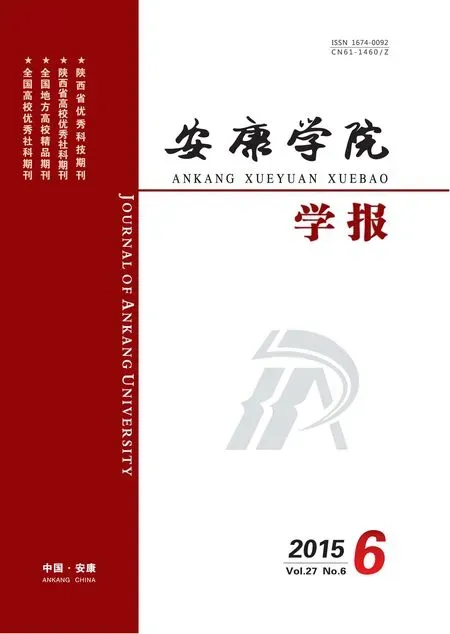时代叙事的“悖论式”彰显——鲁迅《伤逝》解读
薛晓霞
(榆林学院 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在通读《伤逝》之后,我们会为文本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感情所震撼。但当笔者仔细研读小说文本时,却发现在忏悔者的这份手记中存在着一种无法逾越的文本形式与叙事语言的悖论现象,本文即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一、叙事文本的悖论
小说文本形式的悖论在叙事学上就是叙事的悖论,对此进行解读与探索,我们便会发现文本叙事更为深层的意蕴。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借用语言学中的语气(mood)和语态(voice)对“观察点”进行分解,指出观察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视角研究谁看的问题,即谁在观察故事,声音研究谁说的问题,即叙述者传达给读者的语言。简单说可以概括为“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则是叙述者的”[1]107。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且在区别与联系的关系中造成了人物与叙述者的距离,也构成了叙述的层次与空白。一般来说这两者在叙事文本中不会成为一个实体,但在日记、手记等形式的叙事文本中往往会合二为一。这种情况下,视角与声音所造成的人物与叙述者的距离,叙述的层次与空白便会落在一个实体上,从而造成文本形式的悖论。《伤逝》作为“涓生的手记”,在叙述过程中将视角与声音都担负给涓生。在前后文本中涓生作为文本的叙述者(声音)突出了他叙述者的性格,他在实践与智力上往往对人物(视角)有一种优越感,对过去的欢乐与痛苦有一种理性的思考,所以他在前后文本叙述中突出了自我忏悔、理性思考的性格,传达了故事创作的动机和意义。而作为人物(视角)的涓生在中间文本中突出的则是一个经验自我的性格,在中间文本中叙述者陷入了故事的发展情境之中,身临其境地强调理由为自我辩护,从而使中间文本背离了前后文本叙述者的叙述基调。这也就形成了《伤逝》中前后文本与中间文本之间的悖论。也正因如此,人们经常会生出“涓生爱不爱子君”的疑问。其实关键并非爱与不爱,而是这种文本形式悖论所蕴含的深层意蕴。
《伤逝》文本形式的悖论给我们构成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叙事裂痕,如果将原因追溯到承担者涓生身上,我们便会发现这种叙事裂痕的背后贯穿着一条隐蔽的线索,它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弥合了文本形式的悖论,这线索便是涓生作为一个觉醒的“行走者”对生的意义的不断追求。热奈特在谈到叙事语式的复调式时曾这样说过:“自传的叙述者没有任何理由缄戮不语,因为他无须对自己守口如瓶。他必须遵守的唯一聚焦是根据叙述者当前的信息,而不是主人公过去的信息确定的。”[1]186同样,《伤逝》作为叙述者的“手记”,它的叙述基调是根据叙述者当前的信息而展开的,小说中叙述者表达的一切情感,不仅是对死者的缅怀与忏悔,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心灵的安慰,对自己未来出路的一种祈望与探索,大有死者已去,生者应该更好地活下去的味道,这其中隐藏着主人公追寻希望的一种隐秘心理。这在文本第一句便可以体会到,“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2]3。其实这里叙述者强调的更多的是后者,即“为自己”。因为涓生在失去子君后重新又觉得“寂寞与空虚”特甚,所以他借这份忏悔来弥合空虚与寂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寞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2]3这是一个倒装句,我们大可以说成:“仗着她逃出这寂寞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所以我爱子君。”可以说在原先的寂静与空虚中涓生借子君勇敢的爱找到了生存的新路,然而现在子君永远不再回来了,这“寂静与空虚”复又占了他的心灵。接着作者在文本结尾处又说“我活着,我总的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他复又开始寻找新的生的希望了。为着自己新的生路,“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2]19。这样,在《伤逝》的前后文本系统中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系统:“生的无意义——寻找意义——复又无意义——再次寻找”。同样在中间文本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线索。涓生以爱子君或被子君爱而逃出了无意义的生活,子君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5直呼而出,涓生听后却“说不出的狂喜”[2]4。子君的话明显还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她也不是涓生的!这对热恋中的人来说好像有点不合时宜,然而涓生终究还是狂喜。因为他从这句话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作为启蒙者的信念,也看到了自己生的希望之所在。后来在他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子君的身体和灵魂后,隔膜便产生了,最终却真的隔膜起来了。他觉得是“盲目”的爱夺走了他“人生的意义”[2]12,所以他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2]14的希望建立在离开子君的基础上。这才会有当他说出真相后,便真的“预感得着新生命便要来到了”[2]15。然而生活仍旧如梭循环,前方等着自己的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由此可见,本文形式上的悖论投射到涓生身上时已经不复存在了。涓生努力寻找人生价值的深层需要使得这种文本形式层的裂痕在更深层次上得到了弥合。
二、叙事语言的悖论
在叙事方式上,《伤逝》存在着一种文本形式的悖论,这对小说审美空间的开拓提供了广阔的场所。而在叙述语言上,《伤逝》也有其独特之处,即悖论语言的成功运用,这同样大大拓宽了语言的审美空间,也使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更为深刻而丰富。悖论也译为诡论、反论、自否、似是而非,新批评家克林恩·布鲁克斯在1947年发表的论文《悖论语言》中认为悖论语言的运用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最根本的特点,诗歌语言的“各种平面在不断地倾倒,必然会有重叠、差异、矛盾”[3]。在叙事文本中,悖论语言的运用可以给文学文本提供更为独特的审美空间。
创造悖论语言的方法是对文学语言进行反常处理,将逻辑上不相干或语义相互矛盾的语言组合在一起,使其在相互碰撞和对抗中产生丰富而复杂的审美空间。具体在《伤逝》这篇叙事文本中,语言的悖论主要表现为文本表层模糊语言的运用和文本内蕴真挚情感的表露所形成的一种对峙,具体表现为语言对情感的自否和似是而非,从而使语言除了表层的意蕴之外,有了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说:“语言越不精确,暗示性就越大,它的含量也就越大。”[4]小说中,涓生对子君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他为了忏悔和自责写下这篇手记,但是在文本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即使如求婚这一爱情中的重要一环,涓生事后也变“模糊”了,两个月后更是踪迹无存,只是“仿佛”记得当时子君的脸色转成青白,尔后变成绯红。爱情尚且如此,现实生活的琐碎,如子君从庙会买回来的巴儿狗,当然就只能“似乎”记得它好像有名字了。这“仿佛”“似乎”所透视出的感情基调,与涓生的“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的真挚表述形成一种相互的拆解,这种语言形式的悖论,看似不可理喻,却正是叙述者真实心迹的表达,它同样可以在涓生追求生的意义这一点得到完整的弥合。这种和叙述感情相互矛盾的语言组合构筑了丰富的叙事意蕴,也赋予了作品一种令人着迷的深度和张力。
三、时代叙事的审视
“鲁迅的艺术力量似乎有一种罕见的品性,它能够把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灌注到作品描绘的那些独特而真实的性格和情境中,使作品表现的人生摆脱所依赖的事实……把一种现实的描绘转化为一种深邃的人生思考。”人们同时认识到,“经验与思想,生活与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在鲁迅小说中所达到的是一种“隐秘的融合”,他“对心里意识深处的冲突的挖掘”又总是与“形式上的试验”相联接的,“研究鲁迅小说的人生哲学”“应紧密地联系着小说的全部叙述过程”[5]。
《伤逝》完成于1925年10月21日,当时正值“五四”退潮之际,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由积极参与社会革命活动陷入了个人的苦闷、彷徨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涓生,一直以一种启蒙者的角色自居,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并不如自身所想象的那样力挽狂澜,个性解放带来的苦闷和彷徨总是多于喜悦,启蒙并未给大部分人带来新生,而是使其陷入了无法自拔、空前虚空的状态之中。爱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只是爱情本身,它被卷进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社会文化运动的试验场。《伤逝》小说文本形式与叙述语言的悖论,不仅单纯悲伤于涓生和子君爱情的逝去,更是对当时作者处于五四运动退潮期曾寄予希望但终究消逝的五四精神的哀悼与眷恋,更是对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自身性格弱点的反思和心灵搏斗,完美地体现了“五四”人反抗“绝望”、不断“行走”的生命形态。其实涓生身上的悲哀是这一过渡时代不可摆脱的“时代病”的一种典型体现,是整个“五四”时期“社会的悲哀”。涓生在小说中只是时代中一个小小的执著的探索者和攀登者,他努力地寻找生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这新旧
交替之际,这样的努力始终无法得到圆满的答案。德国戏剧家莱辛曾说过:创作“不是让人一看了事,还要让人玩索,而且长期的玩索”[6]。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同时也作为一个“形式的试验者”,他将这种对个体生命、社会生活、国家民族的思考不留痕迹地融入到他所创造的新的形式与叙述过程中。有的论者将《伤逝》中这种文本形式的悖论归结为涓生的“悲哀”,这无可厚非。然而他们进而将这种“悲哀”归罪于涓生本人道德层面的问题或自身的愚蠢,这显然言过其实了。鲁迅在文本中将涓生放在一个荒诞的位置上,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叙述过程,从而将时代特色完满地呈现出来,给人们留下了更多更广阔的审美空间。
[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鲁迅.伤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3]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13.
[4]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82.
[5]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上)[J].鲁迅研究动态,1988(9):4-12.
[6]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