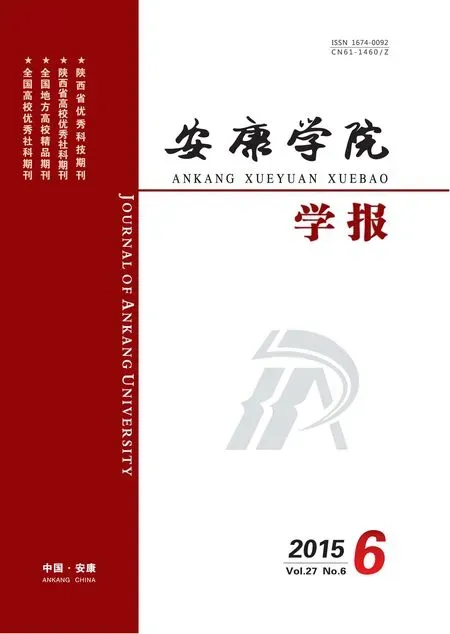陕西作家文学想象中的河南形象——以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为例
石长平
(许昌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许昌 461000)
一
严格意义上的形象学是比较文学中的新兴学科,研究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主要是外国文学文本中关于中国人形象的问题。中国的形象是针对于西方而言的,是一种“西方”的中国形象。从形象学的学理出发来解读河南之外的作家文学实践活动中的河南人形象也是恰当的,因为区域之间的比较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而且从历史来看,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诸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各国之间的形象已经成为相互认知的第一直观方式。像“晏子使楚”“杞人忧天”“郑人买履”等故事中已经明显可见区域居民的形象问题。地域形象是一个行政区域居民在本地区特别是外地区人心目中的大致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会有世代相传的可能,因而具有传统文化的先在性特点,成为评价该区域居民人格秉性的一种最直接的标尺。地域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初期的历史过程中,诸多域外单个个体印象的反复叠加和积淀,构成了外域人的群体意识,逐渐成为一种为其普遍接受的共识,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不断建构成一种形象印记。近代以降,随着印刷技术的提升和传媒的繁兴,文学文本、历史文本以及新闻报刊等也加入到了地域形象的塑造之中,而在电子技术发展成熟的当今时代,广播、电视和网络空间更快捷更广泛地参与到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当中,成为地域形象构建的最重要形式。
但毫无疑问,文学文本对地域形象的塑成和传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载体。因为主体不同,区域形象的构建方式和言说内容也会有所差异。对本区域内的作家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是“自我”生存社会环境的文本传达,是“自我”形象构建。出于对故土的热爱,这些作家往往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感动人心的正面形象,即使是负面形象也绝少十恶不赦的坏人。就河南而言,这可以在周大新、刘庆邦、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等豫籍作家那里明显地看到;从域外作家的视角来看,这又是一种“他者”形象,是一种实际呈现与想象之中的形象。河南人形象在不少外省作家作品中多有呈现,但叙述较多的自然是那些与河南有地缘关系的省份,陕西是其中之一。由于历史原因,如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特别是日本人的入侵,陕西成为大多数河南人逃难的唯一选择和最佳选择,一批又一批河南人交错出现在秦地的时空中,与当地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给生长于斯的作家们留下了众多的历史记忆和广阔的文学想象空间。因而在三秦作家的文学实践中,有关河南形象的表述较其他区域作家更多,这些都突出地表现在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的作品中。
二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描述了几个河南人的形象,除了一个吹牛骗人的烧瓦罐师傅和一个看人下菜碟儿的列车员不很光彩外,其他的都是正面的形象。如帮助孙少安的打铁师傅和烧窑师傅、孙少平的师傅王世才、最后跟孙少平结婚的河南女子惠英等。作家比较客观全面地塑造了包容宽厚、古道热肠的普通河南人形象,而且文本还对河南人历史上的苦难以及由此养成的勤劳热忱有较多的描述,并且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情的赞扬。
从小说人物的命运转折上看,两个主人公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都遇到过河南人,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关怀,他们最后的成功都与河南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说,离开了河南人,两个主人公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从作品情节转进上看,河南人的出现使得故事一步一步走向作家设定的结局。因而在这里,河南人形象还具有了结构小说、推进情节发展的功能性作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河南人是孙少安在给生产队的牛看病时,因为没找到住处,黑夜走到米家镇一个铁匠铺,一听口音,知道老铁匠是河南人。铁匠热情地让少安留宿在温暖的铁匠铺里。这里路遥作了一段关于河南人的议论:“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飘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了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1]路遥把河南人比作中国的吉普赛人,说他们除了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都是很勤劳的。并且认为河南人由于经常到处飘流浪游,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作品中的铁匠师傅为孙少安提供了住处,表现出河南人固有的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性格特点。这些情节描写,特别是路遥超出故事情节之外,站出来以自己的声音热情洋溢地进行赞誉,传达出作家本人对于河南人的喜爱和尊重。
孙少平来到铜川大牙湾煤矿,在这里“河南话是公共交际语言”。接着作者又用了一大段话介绍了这里的河南人,对他们的性情秉性进行了描述,言辞中充满了理解和赞赏:“河南人迁徙大西北的历史大都开始于一九三八年那次有名的水灾之后。当时他们携儿带女,背筐挑担,纷纷从黄泛区逃出来,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行,踪迹直至新疆的中苏边界——如果没有国界的拦挡,河南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不过,当时这些灾民大部分都在沿途落了户,至今都已繁衍了两代人了,成了当地的‘老户’。河南人豁达豪爽,大都直肠热肚,常用震天价的吼声表达自己的情绪。好斗性,但拳脚之争常常不诉诸国家法律的仲裁,多由斗殴双方自己私了。由于他们有着艰难的生存历程,加之大都在铁路和煤矿干粗活,因而形成了既敢山吃海喝,又能勤俭节约的双重生活方式。”[2]3-4
可以见出,路遥对河南人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理解并同情他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四海为家、漂泊无定的生活方式,赞扬他们的坚韧、勤劳和乐观。在描写矿区的河南人时,他写道:“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使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在路遥这里,河南人即使漂泊在外也是很讲究的,既热爱生活又富有修养。孙少平因第一次体检时血压过高而不合格,他找到体验医生请求帮助,医生告诉他第二天早上去复查前喝点醋对降低血压有一定帮助。但这时已是晚上,商店都关门了,他只好走到一个素不相识的河南人家里买醋。作者在这里又一次赞扬了河南人,认为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主人王世才热情询问了他的情况,不仅免费给了他半瓶醋,而且招待他吃饭喝酒,使他在举目无亲的异地感受到了这家人的亲切热情,由此而感觉到了生活的美好。此后王世才又成为少平的师傅,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王世才不仅为人热情正派,工作也非常认真负责,他最后在井下为了救工友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作品这里很好地塑造了一个热情直爽、勇于牺牲的河南人形象。
孙少安准备创业烧砖前,首先来到河南巩义,在那里买了制砖机,这一新型机械设备在村里面造成了很大轰动。作品描写一群孩子唱歌:“孙少安,走河南,买个东西不简单,嘴里吞下泥疙瘩,屁股后面就屙砖。”[2]98而帮助他烧砖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河南人,他操纵砖机和烧窑,技术都相当不错。在他的帮助下,孙少安获得了创业的初次成功。在这里,孙少安从河南带回了先进的生产设备,河南人又给他带去了生产技术。当孙少安准备扩大砖场时,由于这个师傅已经另找了活,他急于用人,只好仓促地找到了一个卖瓦罐的河南人,但这是个只知道烧制瓦罐而不懂烧砖技术的人,结果使孙少安的制砖窑烧坏了,赔了不少钱。但是孙少安并没有因为这个吹牛皮的骗子而不再信任河南人,反而立刻想起了他最初聘用过的那位烧砖河南师傅,他设法去请这个河南师傅。因为他们相处多时,关系很融洽,这位河南人终于被他说动了心,跟着他返回了双水村。第一批砖出窑后,三天内就销售一空。这个塌垮了的砖场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第二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孙少安成功了,由此他逐渐成为发家致富的模范人物。
毫无疑问,没有河南人就没有孙少安最后的成功。作品描写外部区域的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山西人,在那里孙少安找来了他的老婆,一个是一位安徽人,从他那里他听到了包产到户的消息,而描写最多的就是河南人,河南人贯穿整个小说的始终。路遥对河南人的苦难历史和脾气性格有着深切的理解,对他们的为人处事给予了很高的赞赏。可以说,路遥在塑造了孙少安孙少平两个感人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河南形象,在他的文本中,正面有效地传播了河南人的形象。
三
贾平凹作品中对河南人讲述较多的是短篇小说《饺子馆》[3]和散文《白浪街》[4]。在《白浪街》中,其对河南人有一大段描述:“河南人以能干闻名,他们勤苦而不恋家,强悍却又狡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每三日五日,结伙成群,逆江而上,到五六十里远的地方去买柴买油桐籽。收齐了,他们就在江边啃了干粮,喝了生水。然后便扎柴排顺江漂下。一家几口全只穿短裤,一身紫铜色的颜色,在阳光下闪亮。每到一湾,湾里都有人家,江边有洗衣的女人,免不了评头论足,唱起野蛮而优美的歌子,惹得江边女子掷石大骂,他们倒乐得快活,从怀里掏出酒来,大声猜拳,有喝到六成七成,自觉高级干部的轿车也未比柴排平稳,自觉天上神仙也未比他们自在。柴排靠岸后,连夜去荆紫关(河南西峡县的一个镇子)拍卖了。……三天辛苦,挣得一大把票子,酒也有了,肉也有了,过一个时期‘吃饱了,喝涨了’的富豪日子。一等家里又空了,就又逆江进山。他们的口福永远不能受损,他们的力气也是永远使用不竭。精打细算与他们无缘,钱来得快去得快,大起大落的性格使他们的生活大喜大悲。”
这段描写,写足了做小生意的河南人的形象:性情上超迈豪爽、做事上大大咧咧、生活上潇洒随意、知足常乐。在贾平凹这里,使用了“勤劳能干、不恋家、强悍”等字眼,充满了对河南人的褒奖,即使是形容生意人,作者也使用了“狡慧”一词,并无半点贬损。虽然是写小生意人,但贾平凹的这些表述却传达出了对河南人的整体印象,客观公允地描摹出了河南人的基本特性。字里行间,作者肯定赞许之意非常明显。
贾平凹《饺子馆》是一篇解构文化和文化人的戏谑小说。它以一个河南人和一个西安人为主要故事人物,讲述在商品经济的今天,文化人与生意人合流,利用文化又践踏文化的社会现实。文本开头写到:“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这就向读者讲明了作家对河南人进行文学想象的真实社会环境。
如果说在《白浪街》中,小生意人是知足而乐、随遇而安、随性任情的话,在《饺子馆》里的河南人贾德旺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单纯买卖和单一环境,在都市里面做餐饮生意的他,没有一些生意技巧和攀附迎合的手段是难以成功的。明知西安本地人胡子文在“日弄”他,他也得郑重对付。应对胡子文,如果十分认真了那就是傻子,如果一下子点破了他的真实面目那更是傻子,所以他就只好以胡子文的“日弄”来“日弄”胡子文。在作品结尾处,贾德旺之所以对胡子文亮明自己的“日弄鬼”精神,既是一种自我调侃,也是对胡子文的揭底,因为西安人胡子文才是真正深得这种“日弄”精髓的“日弄鬼”。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贾平凹并没有地域偏见,他所塑造的贾德旺是一个深谙生存之道的生意人形象,而且,他坚守道德底线不卖瘟猪肉;他虽然文化不高,但爱读字典,咬文嚼字,亦有一种文化人的精神。文中还描述了他回乡尽孝,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不管是否完全出于给自己的饺子馆做广告,但他确实真金白银地作了社会公益事业,还算是一个慈善家,因而他并不是一个负面形象,真正的负面形象应当是以文化人自居而干着招摇撞骗勾当的胡子文。
在这篇小说中还有陕西人戏称河南人为“担族”这一情节,这正是陕西人基于历史记忆对河南人的印象。花园口决堤及日军侵占河南后,大批难民挑担逃荒来到陕西,这些一个担子挑了全部家当的人被西安人称为“挑担一族”。灾难面前,当年的陕西人民容留接待了这些河南人,同时,一些过去在陕西做过军政要员的河南人如张钫等,以河南同乡会会长身份,利用其与陕西政界友人的关系,救济和安置了大批难民,使得众多逃荒人在这里安顿下来。这些河南人把陕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与当地人一道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自然会给陕西人留下无数的故事和深刻的印象。而这也为我们理解陈忠实对河南人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历史线索。
四
毋庸讳言,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对河南负面形象描写较多的一部,其中塑造了兵痞杨排长、虐待狂炉头等极不光彩的河南人形象。
作品描写民国时期镇嵩军军长河南巩义人刘镇华,带了一帮由河南人组成的军队来到白鹿原,作品用了“乌合之众、烂货”等字眼来描述他们,说“拗口聱牙的河南口音愈觉别扭”,定性他们是“反革命军队”。当这些穿着黑色军装、打着白色绑腿的“白腿乌鸦”来到关中后,闹得乌烟瘴气,与白鹿原人结下了冤仇。鹿子霖骂道:“这杆子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毬,杀人连眼都不眨。”而当杨排长驻进学校查找纵火犯,白嘉轩问:“这个河南蛋瞎眼了不是?”乌鸦兵走后,田福贤召集开会,“九位乡约再也压抑不住,敞开嗓子嘲骂那一杆子河南蛋全是瞎熊,诅咒他们注定不得好死。”[5]174-187因为他们在逃离时,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给当地人们留下了深重的羞辱和苦难。作者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说话,自然带有当时的愤恨情绪,但作家也写明了“河南连年灾害,饥民如蝇盗匪如麻”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原因。这些描写显然是从历史的角度表现由于河南连年遭灾、兵乱匪祸不断给关中人留下的恶劣印象。
无论是陕西人的集体无意识,还是作家本人基于历史记忆而持有的个人印象,这都与清末民初河南人统治陕西、河南土匪入陕抢掠作孽的历史有关。
1911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根据《临时约法》,各省军队缩编,原秦陇豫复汉东征军东路征讨大都督河南新安人张钫(其父在满清时期入陕西担任州县官吏,清光绪二十八年张钫随父亲迁住陕西)所率的陕军(部分为河南人)也在缩编之列。由张钫出面呈请民国政府,对陕军中的原以王天纵为首的河南绿林军进行改编,因为部队官兵家乡分布在以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周围各县,故名“镇嵩军”。后来该部队由巩义人刘镇华为总司令。1918年,刘镇华由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陕西省省长,直到1925年才结束了他在陕西长达八年的统治。1926年初,刘镇华又率七万大军从河南出发围攻西安城,城内守军拼死抵抗。后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刘镇华战败后仓惶逃到豫西陕州。一场经历了八个月、军民死伤几万人的西安围城战才告结束。《白鹿原》所描写的就是以这一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而在此之前的1914年,由河南鲁山人白朗组成的土匪队伍,由荆紫关入陕,长驱而入渭南,进攻西安,在陕西作乱作害,罪孽不浅。了解了民国时期的这一社会背景,就能理解河南人在陕西人心中的历史记忆,特别是作为兵匪身份的河南人形象了。因此,作为以那一时期为历史背景建构起来的文学文本,《白鹿原》中自然会存在较多的河南人的负面形象。
除了河南兵之外,作品最后在回顾鹿子霖祖先马勺娃的发家史时,也描写了一个河南厨师。鹿马勺少年要饭,后在西安一家餐馆打工,遭到一个炉头(厨师)的虐待,作家把这个炉头写成一个十足的虐待狂,并有意无意地指出这是一个河南人[5]652。应当说,作者完全可以回避对具体籍贯的叙述,但陈忠实在此却明确加以指点,这应当是作家本人的有意为之。之所以安排这样的描写,也许是由于作者想要解释鹿子霖让三娃打骂他是有遗传因素的,而这一因素正源自一个变态的河南人。它传达出作者对于豫陕之间历史恩怨的集体无意识,也体现了作家个人基于河南人形象史而对河南怀有的偏见,这是陕西人“糟蹋”河南人的一个典型片段,它应当源于一种显明的地域歧视观念。
应当指出的是,《白鹿原》开篇写到白鹿书院的历史,表述的是一位吕姓河南小吏调任关中,偶见一白鹿跳跃其间,看中了此处的风水,买下了那块地皮,在此盖房修院安居下来。他的后人后来高中进士,又在这里开讲堂讲学,造福乡邻,他死后,皇帝御题“四吕庵”,后称为白鹿书院[5]22。白鹿书院是白鹿原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象征,而它的起源又跟河南人有关。作者在这一传说中置入河南人,既说明两省之间历史上的密切往来,也反映出其对河南人微妙而复杂的感情。总之,在《白鹿原》中,对河南人形象的塑造,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但总体上是负面形象淹没了正面描写,因而它属于传达河南负面形象的一部作品。
五
在上述陕西作家的文学想象里,河南人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老百姓。它包括三种人,一种是民间工匠艺人,如路遥作品中烧砖窑的师傅、铁匠,《白鹿原》中的炉头(厨师)等;一种是生意人,如贾平凹作品中买卖山货的小商贩和开饭店的小老板;再一种就是煤矿工人、列车员等。另一类是兵匪形象,如在《白鹿原》中的“镇嵩军”匪兵等。从历时性角度看,所塑造的都是20世纪三个历史时期的河南人形象,分别是民国时期、改革开放前后、九十年代。因此,相对于当下而言,这些存现于陕西作家文学想象中的河南人形象都属于历史形象,即使离现在最近的也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形象不再影响当下的人们,不再成为包括陕西在内的外区域人认识河南的一种媒介。恰恰相反,由于文学所具有的认识功能,只要阅读文本,这种塑造和传达就能在每一个接受者心目中建树起来,其影响还是直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文本对于区域人形象的影响是广大而长远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就现实横断面还是历时纵深度上看,文学想象中区域人形象的构建,对于该区域人现实形象为外界理解和接受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地域人形象影响着该区域人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影响着地区的认可度和美誉度。地域人形象是该地域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呈现出来的,尽管文学是一种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和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历史无法重演,但当下现实中的区域人,比如河南人,既应当注意在家乡的表现,更应当在异乡他方检点自己的行为,珍惜自己的个人形象。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很多时候,正是单个人代表了群体人,当下构成了历史。
对于外区域的作家,我们无法要求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文学有文学自身的规律,作家有自己的自由想象空间。但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作家本人要意识到,在对区域人形象的塑造和传达上,把感性认知与理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克制自己可能存在的地区偏见,严肃写作态度,改变叙述策略,郑重对待地域形象的文本想象,尽量减少或杜绝文本歧视。而文学批评也要及时跟进,对于文学文本中出现的形象构建问题,应及时、客观、公允地进行解释评价,适宜地光大正面形象,合理地消除负面形象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形象学理论上来说,区域形象的功能分为对内与对外两种,所谓的对内功能主要是指对于本区域人的引导与教育功能,让其认清本区域的状况和处境,自觉地提升区域民众的凝聚力与自豪感,加强区域形象的“自我”构建;所谓的对外功能主要是指向本地区以外的人展现“自我”构建出来的形象,向域外乃至世界传递本区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以期得到他者的认同。尽管外省作家们所塑造的河南人形象,是一种文学幻象,是“他者”想象与“他者”书写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就是现实本身,但它一定可以成为这个地区人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一面镜子。
[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1-72.
[2]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三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贾平凹.饺子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25.
[4]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39-145.
[5]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