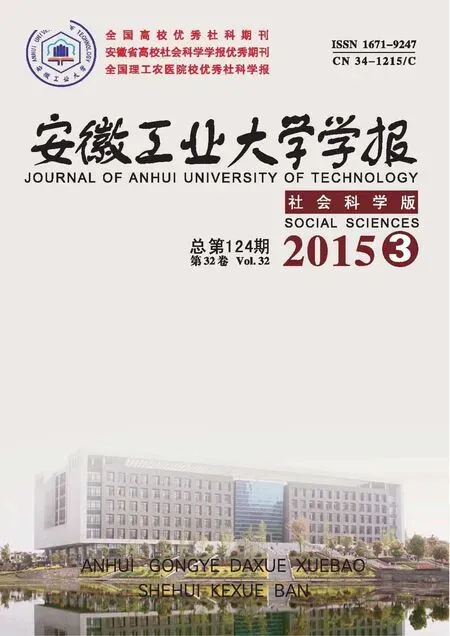浅析《蝇王》中背景和人物象征体系的构建
刘菱馨
(安徽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243002)
小说《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威廉·戈尔丁最经典也最具有争议的作品。戈尔丁本人被西方评论家列为“寓言编撰家”,他的作品被称为“神话”或“寓言”,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就称《蝇王》是关于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这样一部哲学寓言式小说。[1]小说的故事情节简明清晰,二十岁便陷入二战战火的戈尔丁,带着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和内心深处无法磨灭的战争烙印,在其作品中将故事设定在未来的一场核战争中,一架转运孩子的英国飞机在一座孤岛上空被击落,幸存的孩子们在协作与对立、民主与专制、理智与本性的斗争中求生。简单情节之下,是作品中随处可见的象征,巧妙营构的象征体系吸引着读者和研究界不断品读和探究。其独具魅力的视角和表现手法,使得《蝇王》成为英语国家文学课中的必读书目。
象征主义是19世纪初80年代出现在法国,后来遍及欧美的一个文学流派,也是20世纪西方文学普遍遵循采用的一种基本创作美学。[2]正如人物和情节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一样,象征手法将小说的语言表象与主题完美地融合。作品中一个个象征符号看似独立,实则巧妙地呈现了一个完整和谐的象征体系,从而使作品的核心主题——人性之恶,得以不着痕迹地展现,意味深远,犹如海明威所说的文学冰山,引发作者对文字之下所蕴藏的内涵进行深度探讨。
作为一部虚构小说,作品中每一个象征意象的构建均为体现主题而设置,正是通过这种渗透、贯穿小说始末的象征主义手法,让读者在旁观一群未来孩子之间的生存游戏时能够回归现实,意识到人类本性之恶。戈尔丁曾说:“我认为,只有当象征主义手法完全渗入小说的事件、人物和基调时,它才真正奏效。”[3]
一、背景象征
戈尔丁生于1911年,牛津毕业后,曾做过演员和教师,二战爆发后,成为一名将军。战争的残酷在细腻敏感的戈尔丁内心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亲眼见证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屠杀以及对民主与法律的无情践踏,戈尔丁对战争背景下由欲望催生出的人性之恶有了深切体会。
提到《蝇王》这部小说,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巴兰坦的《珊瑚岛》,正如很多荒岛文学一样,作者们在现实环境找寻不到出路时,便会将故事设定于远离现实的真空环境。传统荒岛文学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关注人类在文字历史以来的善与恶之间无休无止的纠缠与搏斗。[4]然而戈尔丁对《珊瑚岛》这部传统荒岛文学所展现的现代文明战胜野蛮这一主题是不屑的,所以他向《珊瑚岛》发起挑战,向传统荒岛文学发起挑战。他将故事设定在同样的孤岛上,却用完全对立的视角来展开情节,孤岛在戈尔丁的笔下是一个没有任何干扰和约束的背景,让孩子们泯灭的童心和内心之恶一步步显现,直至毫无节制地肆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战胜了文明和秩序。由此看来,选择孤岛,作者的笔触是犀利的,用意是明确的。
故事的大背景是假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难看出,这场虚构的未来之战影射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样的利益之争击垮了人类几千年苦苦建立的文明,激发出了文明掩饰之下的人性之恶。虽然读者们面前呈现出来的故事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但戈尔丁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孤岛这个真空的小环境之外,一场血腥的战斗正肆虐全球。岛上孩子们的小小世界正在吞噬着文明和秩序,作品中的未来之战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一切都清晰地映射着现实中作者所经历的文明之殇。一般文学形式所不便表达的主题,在荒岛题材、象征手法和寓言体裁的运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含蓄而不隐晦,贴切而不露痕迹。
尽管战争在文中只有寥寥数笔,并未过分渲染,甚至有些线索只能凭借读者的敏锐嗅觉来感知,但这样的背景设置极大地拓展了这部作品的主题。岛上的孩子们在文明与野蛮之间挣扎,岛外的文明人类正在自己建立的文明之上肆意践踏,正在为自己的欲望和权力之争付出惨痛的代价。
小岛看似孤立,实则与现实紧紧相连,假设没有这场战争,孩子们则无需紧急转移,更不会有飞机被敌军击落迫降荒岛的故事发生。与此同时,是战争带来的爆炸巨响让守夜的萨姆和埃里克遭遇被风吹得噗噗作响的降落伞,最终让他们相信岛上野兽的存在。野兽其实是人们内心之恶和野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戈尔丁缜密巧妙地将野兽、降落伞、人性之恶和战争这些象征意象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完美的背景象征体系。看似戈尔丁努力地将故事的时空概念与现实拉开距离,实则通过精妙设计的象征,非常明确地对现实进行讽喻和影射。
二、人物象征
《蝇王》是一部寓言式小说,每一位人物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些遗落孤岛的小家伙们代表着普通人,大孩子们则象征着统治阶级和政治首领。大孩子对小家伙们的不同态度及变化也相应地象征着对文明的坚守和野蛮的天性。以拉尔夫和西蒙为首的文明派,试图通过自身的力量及秩序的约束来保护小家伙们,而以杰克和罗杰为代表的野蛮派则为了自己的欲望和目的,欺凌弱小,把小家伙们当作干活的工具。在这样的整体象征之下,每一个孩子又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
(一)拉尔夫
拉尔夫是小说的绝对主角,一位十二岁的英国男孩。飞机被击落后,拉尔夫被选为孩子们的头领,他试图团结众人在岛上建立起一个模拟成人世界的微型文明社会。拉尔夫是典型的文明和正义的象征,与小说中的杰克、罗杰一派是对立的。
在被选为头领之初,拉尔夫代表着秩序、文明和权威。当别的孩子们沉浸在没有大人约束的自由中玩乐时,拉尔夫关心的是如何能最大程度增加获救机会,所以他安排孩子们在山顶点火堆生烟求救,组织孩子们在海滩上搭建窝棚……由于拉尔夫表现出的沉着和领导才能,在最初他是被大家拥护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在荒岛的隔离时间变长,他们天性中的野蛮开始一点点吞噬着从文明社会带来的自我约束,拉尔夫的首领地位也逐渐削弱。故事发展到尾声,除了猪崽子追随象征文明的拉尔夫,其余孩子都在食物的诱惑和暴力的威胁下,追随了野蛮残忍、杀戮成性的杰克。当猪崽子也死于杰克之手,拉尔夫成了孤零零的一员,被杰克一伙追杀,那时候拉尔夫甚至想过投靠杰克获取一条生路。拉尔夫在故事中权力的削弱,正象征着人类文明的消逝,而杰克一伙的嚣张正象征着现实中战争制造者们不可一世的张狂。
就拉尔夫这个个体来说,他对文明和道德的信念是很坚定的,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放弃要获救和回到文明社会的努力,在被杰克追杀的过程中,拉尔夫在遇到蝇王寄生的猪头时,他咒骂并击打猪头,将猪头摔碎,拿起穿猪头的木棒来保卫自己,这时的拉尔夫在道德层面是获胜的。
拉尔夫最终也像象征着先知的西蒙一样,真正理解了恶是每个人天性中存在的,无人例外。最初的拉尔夫无法理解追随杰克的孩子们的嗜血、杀戮和野蛮的天性,猎手们满身鲜血、高歌狂舞时,他是困惑不解并觉得恶心厌恶的。但是当他第一次获得猎物,初尝了血腥和暴力给他带来的刺激和愉悦时,他也短暂迷失在疯狂的欲望之中。他在喷香的猪肉面前,也忘却了自己的坚守,加入嗜血的狂欢派对并导致了西蒙之死,那时他就应该看清人性本来的面目了。
象征文明和道德的拉尔夫意识到人人皆恶,长久以来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轰然崩塌,这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是很残酷的,也让他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失望和消沉。不过,拉尔夫毕竟不同于别的孩子,他在意识到内心之恶的力量时,决定用文明与之抗衡,决不让自己在野蛮天性的驱使下迷失,所以他最后战胜了蝇王。在文学作品中,他算是个半悲剧式的人物了。这一切压抑的情感,在看到营救他们的军官时,瞬间决堤,所以他失声痛哭,为泯灭的童心和心性之恶而悲泣。在拉尔夫战胜蝇王时,读者应该会隐隐预感到,拉尔夫会战胜杰克,但是,尽管拉尔夫最后获救并回到了人类文明,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几乎要被杰克逼上绝路,而拉尔夫和孩子们的得救,是归功于一场几乎毁了小岛的大火,一场追杀拉尔夫的大火,一场丧失理性的大火,一场猪崽子眼里焚毁所有希望的大火。毁灭希望的行为却带来了希望,这其中的微妙用意值得读者细细品味。拉尔夫只是小说整个人物象征体系中的一员,但以他为主线展开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体现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作者对生的渴求,历经磨难和绝望却坚信光明不远的意念,伤痕难以抚平生活却要昂首企盼阔步前行的乐观。
(二)杰克
在作品中,杰克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代表和头领,是和拉尔夫直接对立的形象,在象征意义上也完全相反,他象征着人性中固有的野蛮以及对权力和欲望的追求。他一出场就是一个小小群体——唱诗班——的头领,在本身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之上,杰克更加渴望成为整个小岛的一号人物。所以,当他在选举中败给拉尔夫时,他是极为不悦和失落的。但那时的杰克尚未打猎成功,没有更多的筹码来得到孩子们的拥护,加之故事之初,孩子们从成人世界带来的道德和文明的约束力还未褪去,内心之野蛮还未被激发,此时的孩子们在道德层面是更加认可拉尔夫的。杰克作为反面头号人物,与拉尔夫直接对立,在人格上是有成为头领的素质的,那便是坚定与执着,绝不轻言放弃。打猎不成功,杰克便一次次投入到战斗中,选举落败,杰克就利用之后的每一个机会召集拉拢孩子们投靠自己,直到让拉尔夫成为孤家寡人。这些象征着杰克对杀戮的狂热,对权力的执着,进一步象征了人类本性之恶的根深蒂固。
随着杰克一步步褪去文明的伪装,最终沦为真正意义上的野蛮,然而杰克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高。杰克可以让孩子们品尝打猎成功带来的血腥刺激和征服的快感,可以带领孩子们感受嗜血的狂乱和丧失道德的放纵,在这些诱惑面前,除了拉尔夫、西蒙和猪崽子,无一能够坚守文明和道德,纷纷跟随了暴力和野蛮的代言人杰克。这样压倒性的比例,象征着恶势力的强大,象征着绝大多数的灵魂是性本向恶的,通过这样的故事发展,人性之恶的主题得以深度展现和渲染。
另一方面,杰克在取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后,渐渐意识到,孩子们内心对于野兽的恐惧是他控制孩子们的最佳工具,此处正生动地象征着现实社会中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宗教来控制、利用百姓以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小说对杰克的刻画全面而深刻,如果说拉尔夫是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念,那么杰克所代表的就是作者所经历的却不愿意面对的残酷而疯狂的现实,戈尔丁通过两个少年将如此尖锐的社会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立意之新颖,刻画之精妙确实令人叹服。
(三)西蒙
在这部小说中,西蒙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是唯一天性善良的孩子,连拉尔夫也不重视的小家伙们,在西蒙眼里也是平等的,唯独西蒙发自内心地善待弱小的小家伙们。西蒙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如同杰克邪恶的本性一样。虽然西蒙也是正面人物,但他与拉尔夫完全不同,拉尔夫的行为是文明和制约的产物,并非根植于内心和本质,所以拉尔夫也有迷失的时候,而西蒙是岛上所有孩子中唯一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而且并非出于某种约束力的影响。同时,西蒙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岛上的怪物其实是人们内心的兽性的孩子。
西蒙的存在,使作品更加丰满,虽然作者的主要写作意图是阐述人性之恶,但他并不愿意否认人性中善良本质的存在,只是在如潮的恶势力面前,善良那么稀少,那么不堪一击。正如作者虽经历残酷战争的洗礼,阅尽人间惨象,但在作者冷峻的文字之下,仍然有希望、仍然有信念。
西蒙的死亡也独具内涵,拉尔夫和猪崽子的参与,让西蒙之死意味深远。西蒙死于杰克之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象征着文明和道德的拉尔夫和猪崽子也成为了刽子手,这是出乎读者意料的,而这又恰恰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笔,耐人寻味。在作者眼中,人类的文明很多时候是对天性的压抑,对制约力的服从。从小说对人类心理的探究来看,文明的驱动力并不如野蛮的驱动力那样深深地扎根于人类内心深处。[5]
西蒙还承载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他象征着先觉和先知们的下场。人类历史长河中,先觉先知们很难逃脱共同的悲剧下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珊德拉式的悲剧。卡珊德拉是典型的不被众人听信的先知形象,她对事物真相的洞察力让人们认为她是疯子,于是她被隔绝于世人之外。在这一点上,西蒙和卡珊德拉多么相似啊,人类的觉悟和开化之路是艰辛而充满代价的,在小小的海岛上,西蒙就是这样的牺牲品。
(四)猪崽子
在小岛上,猪崽子是最智慧的,他是拉尔夫最得力和忠实的助手,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比如用海螺号召会议,建设茅屋,强调要知道每个孩子的名字等等,猪崽子希望通过这些行为帮助拉尔夫在孤岛上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小社会。相较于拉尔夫,猪崽子务实且缜密,他提议用枝条插进沙子做日晷来了解时间,拉尔夫却嘲笑他,让他再来一架飞机一台电视,可见虽然他们是一派的,但拉尔夫仍然会肆意取笑他,会对他那些听起来不那么有趣的提议嗤之以鼻。生火堆时,孩子们都沉浸在生火玩乐中,猪崽子一再强调生一小堆火就可以了,不能挥霍森林里的柴火,而包括拉尔夫在内的其他孩子们都被自己升起的巨大火堆震撼了,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敬畏和恐惧,此时的猪崽子却在理性地思考着如何维持火堆,并且惋惜那些正在熊熊燃烧的资源,同时他也在担忧着大火会毁掉他们赖以生存和求救的森林,由此,猪崽子的冷静和沉稳可见一斑。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猪崽子自始至终否认岛上有野兽存在,虽然他不像西蒙一样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真正的野兽来自孩子们的内心,但是猪崽子象征着文明社会中的科学和理性,他客观地判断出并没有野兽,然而孩子们并不信任他,可见科学和理性在人们内心的恐惧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猪崽子在拉尔夫与杰克之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拉尔夫一边,捍卫着文明和秩序。但是他和拉尔夫一样,在内心野性被激发时,也把持不住自己,加入了兽性的狂欢,在嗜血的派对中狂舞,并参与了杀死西蒙的游戏。西蒙之死是小说中的浓重一笔,被作者赋予了深远的象征意义,而对待西蒙之死,戈尔丁也对每个孩子的态度做出了细腻的刻画,拉尔夫认为这是一场谋杀,而猪崽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愿意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所以他一直给自己的行为找种种借口。他埋怨天气恶劣,认为是天昏地暗加上闪电暴雨让自己吓坏了,即使拉尔夫反驳他,试图剖析事件真相,但猪崽子一直激动地否定着,并不断强调自己和拉尔夫一直在圆圈的最外面。之后他又解释道自己只有一只眼镜片了,根本看不清楚。最后,他又怪罪西蒙不该那个时候从黑暗的森林中爬出来。这一系列看似严谨的推断,把西蒙之死归结为一场彻彻底底的意外,把自己与这件事撇得干干净净。他用自己的高智商来推理,以掩饰自己在西蒙之死中所犯下的罪恶。故事至此,猪崽子所象征的科学和理性在人性面前已经不堪一击,甚至成为了恶魔的帮凶,让人类的罪恶变得冠冕堂皇。
三、人物象征体系的构建
在《蝇王》这部作品中,戈尔丁用他特有的沉思与冷静,挖掘着人类千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互相残杀的根源。可以说,这是一部揭示人性恶的现代版寓言。故事设置了人的原善与原恶、人性与兽性、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文明、理性的脆弱性和追求民主法治秩序的难度。[6]小说中人物的对立与冲突直接、分明而激烈,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派别都有自己所对应象征的程度和层次,两大阵营的人物也是一一对应。就主角而言,代表文明和秩序的拉尔夫,与代表野蛮和权力欲望的杰克是直接对立的,从故事之初拉尔夫的权威领导到尾声中杰克的绝对势力,从一开始杰克对统治权的觊觎和隐忍到结局拉尔夫的孤立无援,鲜明而残酷的对比和情节发展,生动地象征着野蛮天性如何一步步削弱残存的文明直至完全吞噬它。除了主角的对立冲突,同为助手角色的猪崽子和罗杰,前者忠实于现代科学,对野蛮天性难以接受和正视,而后者是彻彻底底的小恶魔,在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丝毫文明和秩序的影子。猪崽子被杰克抢夺眼镜,利用他的知识,最终猪崽子被罗杰推下山崖的巨石杀害,形象地象征着科学沦为暴政的工具,被利用甚至被践踏。
除了几位主要人物的象征外,其余的人物和群体也均有自己的特定象征,比如象征着残忍野蛮天性的罗杰;比如象征着对权力屈服的双胞胎兄弟萨姆·埃里克;比如象征着普通阶层的小家伙们;比如象征着统治阶级的大孩子们;比如象征着整个人类的政治舞台的这群遗落孤岛的孩子们等等。而这些遗落荒岛的男孩子们作为一个整体,也是戈尔丁精心设计的。选择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是因为他们一个个趋于成熟,天性还未褪去,但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教育,行为中体现着社会的烙印,所以孩子们在岛上的最初时光是文明主导的,文明的惯性驱使孩子们像一个个小绅士,努力建立一个模拟大人世界的小社会。但随着孩子们逐渐体会到无纪律约束的自由和释放野蛮天性带来的快感时,他们就一步步地褪去了伪装自己的燕尾服,一步步放弃了所有善的信仰,跟随内心的欲望,放纵逐渐主宰了大多数的孩子。此时,想想纳粹的灭绝人性的统治,再想想法西斯政权对人类文明的残暴,用这样的人物来表现小说主题,匠心独运,深刻而犀利。同时让读者为这群本应象征着希望的小伙子们感到深深的惋惜。当一场欲望的战争肆虐了欣欣向荣的欧洲大陆时又何尝不让刚刚体会到科技革命带来的美好新生活的人们感受到重重一击呢?
四、结语
《蝇王》是一篇糅合了西方文明、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的多层面、寓意无穷的现代讽喻。若想真正理解小说中所阐述的现实意义,而不是把它片面解读为宗教小说或者儿童文学,就要真正分析出小说里面蕴含的现代意义,对应出小说和现实的镜像关系,从而读懂它处处蕴藏哲理思辨的现代讽喻。[7]单从人物象征这个层面来探析,从每一个个体到每个小群体再到整体意象,戈尔丁精心地营构出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精妙的象征体系,尖锐地映射着当时的社会矛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值得读者和研究者细细品读。
[1]威廉·戈尔丁.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3.
[2]王悦.论《蝇王》中的象征主义[J].安徽文学,2008(1):51-52.
[3]杨文伟.象征主义和《蝇王》的主题表现[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5-26.
[4]杨春芳.《蝇王》之象征体系探微[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18(3):46-48.
[5]BrainPhillips.哈佛蓝星双语名著导读——蝇王[M].郭德艳,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22.
[6]李源.论《蝇王》中象征体系的构建[J].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49-153.
[7]杨雨时,刘春阳.荒岛实验室里的现代启示录——论小说《蝇王》揭示的现代人类社会问题[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55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