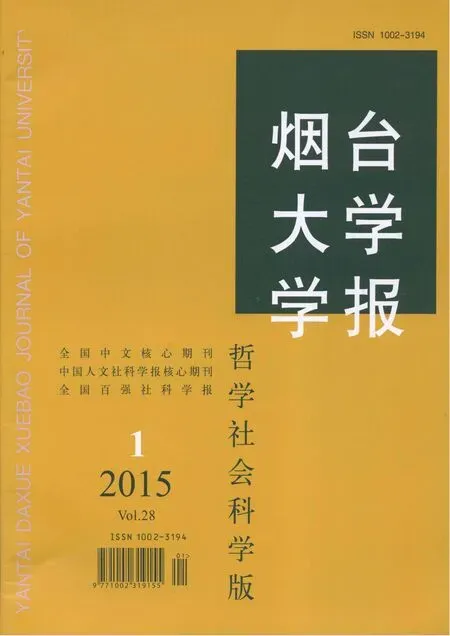巫术与祛魅
——《织工马南传》中的神秘话语
张秋子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巫术与祛魅
——《织工马南传》中的神秘话语
张秋子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传》一向被视作因果报应的道德寓言,其中大量涉及巫术与祛魅的神秘话语却被忽略。这些神秘话语有其深刻的文化意涵,在艾略特的小说叙事中,这一组相互作用的神秘语汇充满传统文化的色彩,微妙地调节着维多利亚时代农村社区的人际模式与道德秩序,是艾略特塑造“快乐英格兰”这一人文理想的必要话语资源。
乔治·艾略特;《织工马南传》; 巫术;祛魅;快乐英格兰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1.010
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传》(SilasMarner,1861)是作者较少受到关注的一部作品。作者在与出版商谈及小说的创作动机时,只用了寥寥数语概括它来自对童年时代一个背着神秘大包的纺织工人的回忆①George Eliot,“The letter George Eliot to john Blackwood”,in David Carroll(ed),George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2000,p.169.;从与其同时代的评论状况来看,《织工马南传》反响平平,《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经济学人》(Economist)等媒体并未像对待《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millonthefloss)、《亚当·彼得》(AdamBade)那样不吝赞词,至多笼统地称作品表现了真实的穷人世界与乡村生活或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诗性正义”②与艾略特同时代的评论有Unsigned review, Saturday Review,vol.13(April 1861),pp.369-370; Unsigned review,RHHutton,Economist, vol.27(April 1861), p.455等,这些评论文章往往以不具名方式发表在主流报刊上,恕不备举。;在近代批评视野中,这部作品受到了更多的责难与忽视,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称作品“它有点童话的味道,而且无论怎么说,都是一部次要作品”③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52页。;20世纪60年代之后,《织工马南传》才迎来了关注与阐释的高峰,布莱恩·斯万从“新神话”角度对作品进行的神话原型解读、罗伯特·唐汉姆从华兹华斯儿童观视角所做的解读都为理解作品提供了新颖的可能性。④Swann,Brian.“Silas Marner and the New Mythus”, Criticism: a Quarterly for Literature and the Art, vol18.2 (Spring 1976),p.101 and also see Dunham, Robert H.” Silas Marner and the Wordsworthian Child”,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16.4 (Fall 1976), p.645.
但是,传统的批评几乎都遵循着利维斯所开创的“道德化”伦理批评模式,《织工马南传》故事层面近似于讽喻寓言甚或童话的书写激发了读者的道德想象,艾略特在信中谈及小说中的“天罚”(Nemesis)*George Eliot,“The letter George Eliot to john Blackwood”,in David Carroll(ed),George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69.似乎更成为对小说因果报应、伦理教化式理解的有力证据。相较而言,小说中大量涉及巫术、巫医、魔法、魔鬼的神秘语言被全然忽视,仿佛这些话语只是乡村地区原始落后的信仰状况的一个客观反映。因而,笔者拟从小说中被忽视的神秘主义话语入手,通过文本细读分析两套相互作用的神秘语汇——巫术话语与祛魅话语——解读其背后的文化表征,意在考察神秘语汇在维多利亚早期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人类关系建构功能,进而探索理想的乡村人际模式与社会秩序,以此塑造“快乐英格兰”(merry England)的文化理想。
一
尽管艾略特声称《织工马南传》具有“现实性”,作品依然普遍被评论界视为一则道德寓言,吊诡的是,小说在叙事上展现出的大量巫术与祛魅话语往往盛行于哥特小说中,它们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意图或道德寓言的文体表现均呈现矛盾之势。实际上,以现实主义写作风格著称的艾略特对巫术、超自然状况、伪科学等神秘现象一直情有独钟。在其中篇小说《揭开的面纱》(Theliftedveil)中,艾略特不吝笔墨地描绘起颅相学、催眠术、通灵术、千里眼等神秘主义现象。在稳定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之内,艾略特的书写存在一股持续的异质暗流。
个体书写的固定偏好有其社会历史的相关动因。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观念在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报纸期刊中进行着权力博弈的游戏。一方面,边缘性的伪科学披着神秘主义的外套大量滋生,时代语境“产生了模棱两可、心神不安的情感,因为个体不再对他们所持有的信念而感到安全,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加速了边缘性科学的发展”*Sherrie. Lynne. Lyons, Species, Serpents, Spirits, and Skulls: Science at the Margins in the Victorian 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9,p.3.。另一方面,神秘气息浓厚的巫术也在启蒙主义冲击的余温中死火重生,启蒙运动并非巫术与魔法的“解毒剂”,“尽管18世纪以来巫术一直被统治者视作无知与轻信滋生的温床,但仍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和地位尊崇的人对《圣经》中明言存在的超自然邪恶力量表现出矛盾的情绪”*Owen Davies,Witchcraft,Magic and culture,1736-1951,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7.,许多人相信巫术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实施着,这种观念尤其在精英、保守党托利党人之间盛行。显然,神秘主义之名下,伪科学与巫术都卷入维多利亚时代观念潮流的角逐之中,身处其中的个人亦不能免俗。
历史地看,艾略特有过数次参与神秘主义活动的切身体验:1874年2月,艾略特与刘易斯一起参加了由达尔文的堂兄韦奇伍德(Hensleigh Wedgwood)在其伦敦住宅隔壁的“罗斯屋”中举办的降灵会(Séance),这种活人与死去灵魂的沟通具有很强的巫术色彩,根据达尔文后来的描述,通灵师使得屋子里“椅子、长笛、铃铛、火光全都跑进我的堂兄的饭厅”*Janet Browne, Charles Darwin: A Biography, Vol. 2-The Power of Pl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405.;1851年8月左右,她结识了知名的颅相学家乔治·孔伯(George Combe),孔伯对她的惊天智力感到很有兴趣,她也表示读了颅相学的相关著作并与孔伯兴致盎然地讨论起来,她甚至专门请教颅相学专家考察自己的颅相,进而推测自己的性格与灵魂状态。*B.M.Gray,“Pseudoscience and George Eliot’s ‘The Lifted Veil’”,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4(1982),p.409.毫无疑问,正是时代催发的个人经验激发了作者创作中的异质暗流。
普通观念中,巫术与边缘性科学关系甚密,有的学者将巫术视作“精心阐释与系统化的伪科学”,甚至直接将两者等同,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身带有巫术的特质,主要体现在对奇迹般的效用专注的追求与科学竞技中那种好胜的心态上”*Randall Styers, Making Magic: Religion, Magic,and science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Oxford Press,2004,p.362.,但是,艾略特却对神秘主义名义之下的各种观念持辩证的批判态度,这一毫不含混的态度是我们理解《织工马南传》中神秘话语的重要依据。显然,她深切怀疑十九世纪风靡一时的边缘性科学活动,它们打着科学的旗号却无从考证,通过《揭开的面纱》,她从存在论的高度对各种伪科学现象做出了深刻批判,同时,她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巫术却持有温和态度,缓和了批判的锋芒。在她看来,披着同一件神秘主义外套的伪科学与巫术的分野重点就在于:前者是现代邪说的一部分,后者则是传统文明的遗产,在农村地区,这一遗产保持得尤为完整。历史地看,“在农村地区,对巫术的信仰在十七世纪盛行一时,到十九世纪仍余韵不绝”*B.M.Gray,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London: Routledge,2013,pp.129-130.。《织工马南传》中,作者屡次强调故事发生在不受新时代风气影响的山林中,盛行巫术的拉维罗村保持着“老式乡村生活风格”*George Eliot, Silas Marner, New York: Airmont books,1963,p.2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作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这里的村民崇尚鬼神之说,常聚在彩虹酒店里谈论魔鬼“老哈利”(Old Harry)(p.58);而被刻画成巫师形象的织工马南身上也有一种自然权力般不会变化、不为所动的古典气质,他仿佛遗民一般保持着“不见新来的人,不见新变化”(p.45)的状态,他所具备的巫医技能也由母亲来传授,充满家内传统的经验色彩,这些叙事都明确肯定了巫术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合理性。
在肯定巫术存在具有合理性的基础上,艾略特通过《织工马南传》巧妙地传达出重建“快乐英格兰”的人文理想:在宏观的文化层面上,巫术的传统文化色彩与“快乐英格兰”的怀旧情结达成了同构,而在微观细致的社会结构方面,巫术与祛魅话语微妙地调节着农村社区的人际模式与道德秩序,和谐的村社人际模式恰恰构成“快乐英格兰”的深层社会基础。
在《织工马南传》中,作者开篇点明故事发生在“富饶的平原中部,一个我们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的地方,拉维罗这个村庄古风犹存,尚未被新声音所入侵”(p.9)。所谓“快乐英格兰”,主要指“国家性或者地区性的年度节庆,人们在公共场所举办仪式或者进行习俗性的消遣活动”*Ronald Hutton,The Rise and Fall of Merry England: The Ritual Year, 1400-1700,London: Oxford Press,2001,p.1.;从文化结构上看,“快乐英格兰”是“理想化乡村”的概念延伸。对古老田园的理想化想象与追忆是英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英国就是乡村”的说法甚至已成陈词滥调。“将乡村理想化,在英国有着漫长的历史,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仍然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国家的统治者在乡村地产上建立基业。”*Martin J. Wiener,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7.工业革命以来迅猛的城市发展更加速了酷爱怀古的英国人对文明的不满。这一怀旧情结不仅盛行在统治阶层内,更弥漫在知识分子、保守党派之间。可见,艾略特对“快乐英格兰”的书写一方面来自于从童年回忆与切身经历出发的回忆式冲动,一方面也深深镶嵌着英国文化中怀旧风气的印记。
“快乐英格兰”的主要是基调是基于传统习俗与丰盈物质基础的宴饮、舞会,历史上,为了庆祝节日,英国某些地区“从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天持续到接下来的星期四,人们不断地吃储存的肉类、鸡蛋、奶酪和其它不能在禁食期间享用的食物。”*Ronald Hutton,The Rise and Fall of Merry England: The Ritual Year, 1400-1700,p.19.小说中,“人们畅快地大吃大喝……拉维罗的宴饮都是大规模的,大块的牛肉,大桶的酒,在冬天会持续很久。”(p.27)同时,以宴饮文化为代表的“快乐英格兰”的社会基础是“睦邻”,在英国文化观念中,“社区和谐”(communal harmony)成为判别“快乐英格兰”的重要指标——“‘理想的快乐乡村’包含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标志地球转动的无尽的四季循环。”*Mark Connelly, Christmas: A History,New York: I.B.Tauris,2012,p.70.在英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乡村集会、访亲探友更是成为对乡村生活描绘的一大主题。因而,对乡村地区人际关系的考察也就成为作者的创作重点。
在给出版商布拉克伍德的信中,艾略特明确谈及《织工马南传》的意图之一是“纯净、自然的人类关系的修复力量。”*George Eliot,“The letter George Eliot to john Blackwood”,in David Carroll(ed),George Elio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p.169.小说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考察突出了马南个人处境的“孤绝”(live in solitude),同时也渲染了拉维罗村公共生活中的“睦邻”(fellowship with neighbor)气氛,词频极高的“睦邻”与马南的“孤绝”构成尖锐张力,马南身上的孤绝不仅危及个体自身存在状况,更损害了农村社区和谐的人际理想,因而,作者对于巫术与祛魅两套神秘话语的运用不仅在宏观层面呼应着快乐英格兰的怀旧气息,更在具体层面成为平衡个体与社群交往模式、修复快乐英格兰社会结构基础的重要手段。
二
织工马南是作为巫师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的。小说的叙事从多个方面暗示着拉维罗村这个外来户是一个巫师。马南面色苍白,身负一个“神秘的口袋”而来,路遇的羊倌虽然“相信口袋里除了亚麻线没什么别的,但仍觉得纺织业虽然不可缺少,但没有魔鬼(Evil One)的协助,总是不可能成的”(p.7)。通过重复性修辞,作者将纺织亚麻这个职业和巫术勾连起来,“对于村民来说不熟悉的东西,总是可疑的……某些手艺习得过程是全然隐藏起来的,它们必然包含着咒术戏法”(p.7)。将特定职业进行巫术化理解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观察到,“令人感到费解的是,巫术的传统特征被发现与某些艺术或者手艺相关联……巫术同样是某些职业的一部分。医生、理发师、铁匠、羊倌、演员与掘墓人都有着神奇法力”*Marcel Mauss,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Taylor & Francis,2005,pp.24-36.,在民间大众的心灵中,特定职业所具备的精细复杂的技术与巫术的超自然能力是吻合的,工具也可以作为图腾意象而被崇拜。
艾略特深谙巫术文化在个体身上的种种表征,对马南的生理特征与外来户的身份特征的叙事再次突出了他的巫师形象。小说写道,“马南那苍白脸上突出的棕色大眼睛,虽然看不清什么不在身边的东西,但怎能确定那可怕的盯视不会给某个恰好经过的男孩带来抽搐、佝偻或者歪嘴?”(p.7)确然,“据说一个巫师能够通过某些特异的生理特征被辨别而出,这深深烙印在他身上,哪怕他想隐藏仍然会被识破,比如一个巫师的瞳孔把虹膜都吞没了……总结起来,‘邪恶之眼’说的就是那些令人害怕或者怀疑的人”。*Marcel Mauss, A General Theory of Magic, Taylor & Francis, 2005,pp.34-38.
《织工马南传》中,马南的巫术气质来自个人信仰的崩溃,这和民间巫术一定程度上源于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同构。马南原本生活在灯笼广场(Lantern Yard),生活平静,信仰虔诚,与邻人有着和谐亲密的关系。小说在描绘马南早年的生活多次使用了交情(fellowship)一词,尤其与他的好朋友威廉有着亲密的交情。但是,威廉的毒计很快打破了这样的人类关系,他栽赃马南并夺走其未婚妻,使马南陷入孤绝之境。随后,不公平的抽签审判令马南蒙冤,不仅使他失去了宗教信仰,更斩断了与美好英格兰社区的有机人际关系,一如小说所写,“他切断了那种有爱和信仰的生活”(p.21)。
当村社秩序被破坏时,巫术成为纾解公正、重建社区原则的重要渠道。小说写道,“这时一件事似乎开启了他与邻居交情的可能性:巫医治病”(p.21)。在现代医学对村民病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马南以巫术医学疗疾,当他看见鞋匠的妻子坐在火边,身患重病,“他心中一阵怜悯,想起母亲曾经用地毛黄配置了一种药水”,用这种药水他治好了鞋匠妻子的病。在患病或者丢失物品时向巫师求助几乎成了一种乡村惯例,17世纪的清教牧师安东尼·博格斯说:“如果人们弄丢了东西,或者遭受任何痛苦疾病,他们会很快跑去找他们所谓的‘智者’”*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12,p.178.,所谓智者(wise man)指的正是巫师。草药在中国、希腊与古代欧洲都有着悠久的治疗历史,“英国的草药变成了迷信活动的中心,中世纪之后草药的重要性达致巅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巫师,每个巫师都有自己的草药与药水。”*H. K. Bakhru, Herbs that Heal: Natural Remedies for Good Health,New Delhi: Orient Paperbakcs,1992,p.17.由此观之,治疗疾病的巫医是村社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构成,其神秘的职业功能补充与平衡了那些现代医学与宗教理性不可企及的晦暗角落。
在成功救治了鞋匠妻子后,传统气息浓厚的巫术话语开始调和农村社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通过这一慈善之举,塞拉斯来拉维罗村第一次觉得,他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能将他从那种使得灵魂萎缩的昆虫式的生活中拯救而出”(p.21),“孤绝”与“睦邻”的尖锐冲突也得以缓和。“巫术信仰帮助维系传统的邻里和睦与慈善关系,尤其在当有社会或经济等其他因素试图削弱这种关系时。”*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12,p.564.人们意识到:“如果你能礼貌公正的谈起那些邪门的事,马南也许会给你省去医疗费。”(p.11)人类学家梅瑞迪奇·斯末也证实道:“一旦巫术在公共视野中现形,巫术的社会运作过程就会强化社区中关于善与恶的概念区分,将道德组织进社会文化中。很多社区成员不仅仅害怕咒语,更害怕巫师的指控,巫术将人们规范在社会准绳中,它是动态的律令。”*Meredith F. Small, The Culture of Our Discontent: Beyond the 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Washington: Joseph Henry Press,2006,p.140.不难理解,巫术扎根于传统农村的社会与历史中,因而它天然带有源自时间纵深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诉求,这种对和睦、慈善的传统义务自觉意识成为重建受损人类关系的重要力量。
三
但是,巫术对于村社人类关系的修复功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很不稳定。巫术话语是在人们对其敬与怕的认知隔膜上建构起来的,民间大众趋利避害的自保心理从客观上达成了巫术与社会秩序的协调,艾略特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她写道,马南逐渐厌烦给人治病,“在短暂的情谊之后,他与邻居之间的排斥又变得明显了,他使得自己更加孤独了。”(p.23)对此,她采取了双重结构的叙事策略,将看似两个相互矛盾的神秘话语并置,通过祛魅话语的表达,对巫术话语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解构:即在文化意义上清洗了巫术话语在村社人际建构过程中负面因素,同时又构成一种积极的建构模式,在微观的社会结构层面中稳固了初步协调的群己关系模式,可以说,看似一反一正两种神秘话语呈悖谬式存在,它们并未相互抵消,而是殊途同归地指向快乐英格兰的健全建构。
通常意义上的祛魅活动是我们所熟知的“巫术迫害”,可以说,从巫术传入英国开始,就有大量来自基督教排斥的声浪,1542年起英国更是制定了针对惩戒巫术的成文法。从建构“快乐英格兰”的角度来看,祛魅话语中的巫术迫害对理想村社人际关系的修复力在于它切断了人与魔鬼的奴役关系,建立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正是艾略特所期待的“纯净的、自然的人类关系”。
与魔鬼建立契约是巫术的一大特征。“如果不借助魔鬼的力量,神秘的巫术不可能实施,通过与魔鬼修订契约,巫师实则使自己变成魔鬼之仆,将全身心投向魔鬼。”*Brian P. Levack, The Witchcraft Sourcebook,London:Routledge,2004,p.60.恶魔盟约不仅使得人类早先通过摩西与上帝在西奈山所定之约受到玷污,更使得社区之中人与人的有机联系降格,这是对自然人类关系的彻底背叛。小说中,马南的手艺早就被视作是与撒旦签订契约换来的,乡邻们眼中马南因癫痫导致的魂不附体视作将灵魂交易、出卖肉身的症候:“他的灵魂脱离了肉身,进进出出,像巢中之鸟一样归去来。”(p.11);这种昏迷不知人事,被大家视为有“撒旦造访”(p.12);对社区规则的回避行为直接被视作是与“恶魔为伍的”(p.105)。显然,在正常的村社生活秩序中,与魔鬼建立关系是对契约精神的偷换与亵渎,对此,小说中的祛魅话语开始发挥其清洗的功能。
首先,祛魅话语对于巫术话语负面效应的解构来自于日常生活对于神秘主义的消解,回归日常生活最大限度地切断了与魔鬼的契约关系。在现代理论视域中,日常生活中那些涉及普通衣食住行的小细节酝酿着革命的种子,它们对被神秘化与异化的生活进行着祛魅。马南丢失金子、获得孩子的情节是其彻底融入农村日常社区的开端。充满本真人性的孩子迫使马南消解与魔鬼的关系,因为孩子“是活生生的造物,有没完没了的需求,寻找并热爱阳光,喜欢一切活的声音,活的动作”(p.135)。为了满足孩子的要求,马南只能从孤独的状态退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原本“喜欢在田野里搜寻毛地黄、蒲公英、驹蹄花”的巫术草药兴趣逐渐让渡给与热心的乡邻给孩子一起置办小衣服、小裤子的兴趣。为了满足孩子需求,原本显得冥顽不灵、避世独居的马南对热心的邻居多丽说:“凡是你们认为对孩子好的,你们只要说了,我一定去做”(p.135)。在孩子受洗当天,原本从不去教堂的马南竟也“穿戴整齐,第一次现身于教堂,参加邻人们所认为是神圣的典礼”(p.134)。此举象征着马南对社群规则与神圣秩序的逐渐认同。
其次,祛魅话语修正了巫术话语所建构的非常态化的人际关系。原本由敬畏与害怕造成的认知隔膜被主动的村民公义救赎心理所替代。在古老的英国,“如果一个巫师落入宗教法庭手中,他最终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邻里的关系。”*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12,p.262.显然,在英国乡村地区,对于巫术的惩戒和审判并不仰赖于来自信仰或司法,而是来自村社中日常生活的人情来往和睦邻基础。法庭的正常程序需要受审人在社区找到足够多的邻居来证明他无辜,为他辩护。这时,主动权由巫师手中转移到村民手中,巫术话语需要极力褪去魔鬼代言人的恐吓功能,以谦卑温和的同类人姿态面向村社,出于和谐社区公义或救赎的心理,村民才有可能主动为巫师辩护。马南的黄金被盗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魔法的丧失,也即巫术话语的失效,他变得与常人无异,甚至成为村中的弱者,人们在“物伤其类”的情绪下开始怜悯他,“这时候,人们开始和善地对他”(p.84)。最终,祛魅话语使魔变成人,马南“也开始理解和支持当地的习俗与信仰”(p.150)。“对孩子的爱将他和外部世界连接在了一起,所以无论老少都觉得他那么不可接近了,在爱中,他与孩子融为一体”(p.141),这暗示着自然人际关系的最终重建。
在文本的后半部分,涉及魔法的修辞大量减少。村民再也不用“魔鬼的同伴”或者“鬼”来形容马南,巫术话语的影响力消弭的同时,祛魅话语逐渐把马南建构成一个村社和睦秩序的顺应者,马南的孤独感也很快让渡给其内心情感与回忆的全面复苏。最终,小说那些一度用“神秘的”、“可疑的”来修饰的事件却变成人物的恍然大悟:“日常生活里的事大概都是不神秘的”(p.188)。这是祛魅话语对巫术话语的彻底肃清,超现实的、使人敬与怕的巫术最终被祛魅话语下的村社日常生活所融化,人与人的关系也彻底取代了人与魔鬼的关系。小说中“快乐英格兰”的最终实现是在马南个人与社群关系渐趋和谐的基础上又加固了一层新的美好关系的缔结:孩子长大成人结了婚。在和谐健全的人类关系基础上,小说结尾再次出现的婚礼宴饮叙事指向快乐英格兰人文理想的最终实现。
总的来看,《织工马南传》的故事呈现出古典而又稳定的叙事框架:马南的信仰经历了信——疑——信的过程,其所视为生命的金子经历了得——失——得的跌宕,而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也经历和谐——破碎——重构的起伏,这些故事层面的叙事框架吻合道德寓言的传统文体特征,它们在文本中重复使用,简单而有力。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小说却传达出艾略特对巫术这一传统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辩证式理解,巫术话语与祛魅话语两者看似互相矛盾、针锋相对,却在实现快乐英格兰的人文理想中以微妙的相互作用达成同构的话语建构力量。
[责任编辑:诚 钧]
Magic and Disenchantment: the Mystic Discourse inSilasMarner
ZHANG Qiu-zi
(Departmentofliterature,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George Eliot’SilasMarner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moral fable about Karma, however, the magic and disenchantment discourses in text are neglected correspondingly. The magic discourse ha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is full of traditional sense in Eliot’s novel, which accommodates subtly the human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moral order in rural area .They are important discourse sources for the author to construct the Merry England.
George Eliot;SilasMarner; magic; disenchantment; merry England
2014-04-23
张秋子(1988- ),女,云南昆明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
I 106.4
A
1002-3194(2015)01-0073-07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