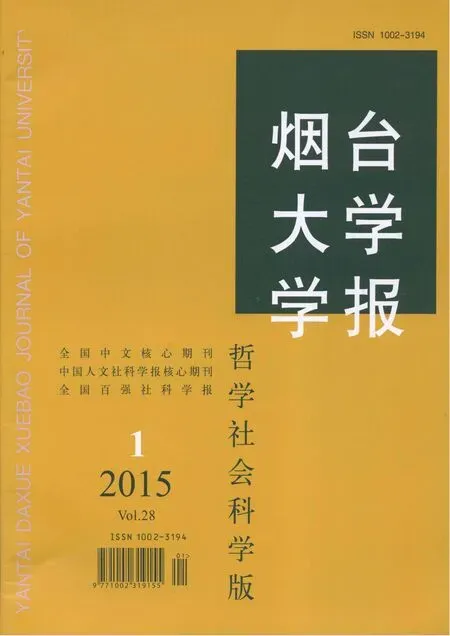奴隶制下的人性演绎:评《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
庞好农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奴隶制下的人性演绎:评《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
庞好农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特鲁思在《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里披露了纽约州奴隶制即将废除之际人性善恶的各种表现形式,性恶、性善和人性扭曲是美国北方奴隶制下人性演绎的三个层面。特鲁思用触目惊心的笔调勾画出人性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异化——贪婪、冷酷和伪善,同时还从迷信型、感恩型、愚忠型和自卫型斯德哥尔摩综合效应的心理视角,抨击奴隶制的非理性,认为人性扭曲是社会扭曲的必然结果。此外,特鲁思还从正义之善、怜悯之善和恶中之善等方面描写白人的多维品性,强调了人性善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索吉纳尔·特鲁思;《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人性恶;人性善;人性扭曲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1.009
索吉纳尔·特鲁思(Sojourner Truth, 1797?-1883)是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传教士、改革家和女权主义的早期倡导者。特鲁思在文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①本文为行文方便,把此后出现的《北方黑奴索吉纳尔·特鲁思叙事》简称为《叙事》。(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A Northern Slave,1850),该部作品率先在美国文学史上掀开了北方黑奴问题的冰山一角。其实,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即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哈丽雅特·A·雅各布斯(Harriet A. Jacobs)等讲述南方黑奴无法忍受奴隶制的苦难而向北方逃亡的故事。而特鲁思的奴隶叙事讲述纽约州1827年即将废除奴隶制之际所发生的种族迫害和种族压迫事件,披露了当时美国北方社会人性的恶与善,讴歌了美国内战前北方黑奴的觉醒和奋斗。美国内战前,文学界关注最多的是美国南方黑奴问题,不少作者把北方美化成黑奴的天堂,仿佛黑奴一旦逃到北方就会脱离苦海,过上与白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但当时的社会情形并不是这样,特鲁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再现了美国社会的北方黑奴问题,揭露了奴隶制的本质,表明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奴隶制就是黑人的人间地狱。本文拟从三方面探讨特鲁思在《叙事》里所展示的美国北方奴隶制下的人性演绎:性恶与人性沦丧、斯德哥尔摩效应与扭曲的人性、性善与人性回归。
一、性恶与人性的沦丧
众所周知,西方社会不是以“善”为人性的本源,而是以基督教的性恶观为思想基础。美国的基督徒以承认个人的“原罪”为出发点,认为人类最基本的天性是“恶”。如果任由人性中“恶”的自然发展,人会做出无限损人利己的事。从“人性本自私”的传统理论来看,人的心理构造就是一个会驱使人自私自利的动力系统;如果当事人做了对他人有益的事,也仅是因为那件事对当事人也有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人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密切相关。马克思把生产关系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中的剥削者为了个人资产的增殖,通常会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演绎出违背社会伦理和道德的各种“恶”。美国奴隶制在本质上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出现在原始社会之后、封建社会之前的那类奴隶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生产方式,在此奴隶制上形成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性恶”社会形态之一。因此,笔者拟用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从三个方面探究特鲁思在《叙事》里所揭示的美国北方奴隶主的性恶问题:贪婪、冷酷和伪善。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贪婪是人性中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我对物质追求的最大化所形成的排他性心理。特鲁思在其作品中揭露了政府法令背后的贪婪、剥夺黑奴人权的贪婪和私吞教堂财物的贪婪。随着美国北方废奴运动的发展,北方的大多数州都颁布了各种废除奴隶制的法令。特鲁思所生活的纽约州规定:从1827年起,40岁和超过40岁的奴隶获得自由,取得公民身份;不满40岁的,需再服役10年,才能获得解放。这个法令有其进步性,但也暴露出奴隶主的贪婪,因为当时的黑奴超过四十岁就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奴隶主的贪婪还表现在对待奴隶生育问题的动机方面。在《叙事》中,奴隶主让奴隶结婚生子的目的不是要给予奴隶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是要通过奴隶生育子女来使自己的财产增殖。为了让黑奴多生孩子,奴隶主查尔斯·奥丁伯格(Charles Ardinburgh)把男性黑奴和女性黑奴集中安排在一个房间居住,结果导致黑奴的乱伦事件和乱交事件不断发生。奴隶主关心的只是女奴是否给他生下了小黑奴,就像农户关心母鸡是否生了蛋一样。奴隶主的财富是建立在对女权的践踏之上,其贪婪是乱伦和乱交的直接致因。正如马克思所言,奴隶主“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发财而发财……完全受发财的绝对欲望支配。”*章海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初探》,《河北学刊》1982年第2期。由此可见,奴隶主作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作为种植园生产的管理者,他关心的仅是资本的增殖。因此,其人性必然沦为反社会、反伦理、反道德的求金欲。
冷酷也是白人奴隶主的本质特征之一。他们把黑人视为会劳动的牲口;为了使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时常会转卖奴隶,无视奴隶的母子之情或父子之情。在特鲁思的《叙事》里,黑奴鲍姆福里(Bomefree)和贝特西(Betsey)生的12个孩子都被奴隶主一个接一个地卖掉了。最后,鲍姆福里和贝特西年老生病而死,死时身边没有一个孩子。老黑奴鲍姆福里在临死前用血泪控诉了奴隶制的暴行,“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奴隶主卖掉!现在,我动不了了,身边却没有一个孩子,连递杯水的人也没有。我活着干什么呀?为什么不死呀?”*Sojourner Truth, 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New York: Dover, 1997, p.7. 本文引自该书此后只标页码,不另做注。另外,奴隶主无视黑奴的情爱关系。黑奴罗伯特爱上了另一个奴隶主的女奴特鲁思,但是罗伯特的主人不愿自己的男奴和其他人的女奴同居,就像不愿让自己的种猪为他人的母猪义务配种一样。于是,那个奴隶主严厉禁止罗伯特与特鲁思见面,罗伯特因为去和特鲁思幽会而被奴隶主打得遍体鳞伤。最后,特鲁思被迫嫁给了她并不爱的黑奴托马斯。奴隶主的冷酷还表现在蛮横不讲理。由于特鲁思从小就生活在荷兰裔的奴隶主家,只会说荷兰语,而不懂英语。当她被卖到约翰·内勒(John Nealy)家为奴时,时常因听不懂英语遭受奴隶主责骂和毒打。
伪善是白人奴隶主欺诈黑奴的手段之一。纽约州在1799年立法废除奴隶制,但解放纽约州境内所有奴隶的工作直到1827年7月4日才正式结束。在《叙事》里,奴隶主杜蒙特(Dumont)借黑奴渴望早日获得解放的心理,以欺骗的方式加大盘剥黑奴的力度。他向黑奴特鲁思许诺:如果特鲁思的活干得好的话,就让她提前一年获得自由。得到这个许诺后,特鲁思比以前更努力地干活。可是,杜蒙特总是找借口延长特鲁思的服役期。由于特鲁思的一只手在干活时受了伤,杜蒙特趁机赖账,声称她干的活达不到提前释放的条件。特鲁思悲愤不已,但也不得不继续为奴隶主劳动。其实,奴隶主杜蒙特的许诺只是一种欺骗。一年后,杜蒙特根本没有兑现诺言。特鲁思最后醒悟过来,“奴隶主给你这样那样的许诺是十分卑鄙的。他们时常许诺:如果你卖力地干了这件事或那件事,就给予你这样那样的好处。一到兑现的时候,你什么也得不到,你会被指责为撒谎,他还责备你没有完成该履行的义务。”(p.18)总而言之,奴隶主是不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的。如果黑奴胆敢强烈要求兑现承诺,可怕的悲剧就可能发生。特鲁思在《叙事》中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奴隶主布罗得赫德(Brodhead)许诺黑奴尼德(Ned):只要尼德拼命干活,就让他获得自由。可是,时间过去了很久,布罗得赫德根本不提此事。当尼德提醒奴隶主兑现承诺时,奴隶主恼羞成怒,抓起一根雪橇棒,敲碎了尼德的脑袋!由此可见,“人的生存环境不足以满足人的需要时,善被恶绑架,恶并不通过善来表现。伪善是那恶的表现。”*王振杰,魏小红:《非正常危机境遇下人性善恶的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奴隶根本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伪善也是美国奴隶制解体时期的独特产物之一。
特鲁思在《叙事》中用触目惊心的笔调勾画出人性在奴隶制社会形态下的异化。正如王钦峰所言,“人性的沦丧即人的本质的异化,它表现为主体与物同时从它们的本原状态中疏离出来,表现为它们之间的相互疏离(这是认识论能够产生的基础)和其现象学的(尚未被抽象思维粗暴干涉的)和谐园地的丢失,主体和物同时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王钦峰:《西方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和社会批判意识:古希腊人性的异化及其现代反响》,《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奴隶主的贪婪、冷酷和伪善给黑奴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白人奴隶主一方面剥夺黑人的基本人权,另一方面又把失去了基本人权的黑人视为野兽。奴隶主的人性经过贪婪、自私和伪善的发酵后演绎而成的是“恶”的各种表现形式。奴隶主的人性异化虽然受到贪婪之心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放弃了人性追求,放弃了对人性的认同和敬畏,在剥夺他人人性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人性丧失殆尽。因此,这种异化本身的最深层内因就是奴隶主对人性的否定和蔑视,从而导致其自身的人性沦丧。
二、斯德哥尔摩效应与扭曲的人性
斯德哥尔摩效应,也称人质情结或人质效应,指的是受害者对罪犯产生了好感和依赖,甚至反过来帮助罪犯的一种现象。*Peter Brian Barry, “Evil and Moral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67.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斯德哥尔摩效应不是某个刑事案件的个例,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或精神病态。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当人们的生存权被一个国家、群体或个体等权威体所攫取时,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道路就会被堵塞;如果反对权威体,他们会直接受到无情的打击、报复和迫害,甚至会被剥夺生存权。因此,出于对生存权的留恋,他们不得不以牺牲个体人格的方式去规避权威体的锋芒,谋求生存权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与权威体的周旋过程中,不少人失去了自我和人格,从权威体的受害者发展到权威体利益的狂热维护者,陷入斯德哥尔摩效应的泥潭之中。笔者把《叙事》里出现的斯德哥尔摩效应分为四类:迷信型、感恩型、愚忠型和自卫型,从而揭示美国黑人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被扭曲的人性。
迷信型斯德哥尔摩效应是人在绝境中的心理反应之一。一般来讲,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易把希望寄托于神,并把自己的一切境况和决定都看作是受神左右的。特鲁思在《叙事》中揭露了黑奴中盛行的迷信现象。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特鲁思迷信上帝,总是向上帝祷告,希望来世远离苦难。即使被杜蒙特太太毒打的时候,特鲁思没有哀求,而是在心里默默地祷告,祈求上帝使她产生抗击毒打的毅力。“当我挨打时,我事先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祈祷。我总是想,要是我有时间用祷告来向上帝求救的话,我就一定会逃脱那顿毒打。”(p.10)在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作用下,她把迷信的无效归咎于自己没能及时向上帝求救。特鲁思总是乞求上帝让自己遇到一名善良的奴隶主,而在其人生道路上,每当她遇到什么困境或难以决策的时候,特鲁思都会在心中向上帝默默地祷告。每当她想出了解决危机的好方法或每当有人来帮助她的时候,她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安排和恩惠。迷信型斯德哥尔摩效应导致受害者失去自我,把虚幻的上帝视为自己的主宰,把自己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虔诚度不够。
特鲁思笔下的感恩型斯德哥尔摩效应指的是受害人把从加害人那里得到的一点好处视为加害人对自己的恩泽,从而对加害者感恩戴德,在生活中不遗余力地予以回报,不然就会觉得自己有愧于加害者。在《叙事》中,伊莎贝拉(Isabella)感激奴隶主杜蒙特在处理凯特诬陷案中的公正,因此,她就带着感恩之心拼命干活,为奴隶主干越重的活、越多的活,心里就觉得越快乐。杜蒙特常向朋友们炫耀,“对我来讲,那家伙(作者注:伊莎贝拉)比男人还行,她晚上洗全家人的衣服洗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去地里干活,她在地里耙杂物或捆绑庄稼都是一把好手。”(p.14)奴隶主的赞扬激起她更大的报恩之心。她晚上不愿休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从而耽误了给奴隶主干活。但在奴隶主眼里,她仅是一个会干活的牲口。在斯德哥尔摩效应中,她把自己和奴隶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如果有人对她提及她当奴隶的不公正性,她会带着蔑视的表情回应他们,并把此事马上报告主人。她坚信奴隶制是正确而荣耀的。”(p.14)她对奴隶主的盲目感恩迷失了人生方向,成为其牟取最大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愚忠型斯德哥尔摩效应是指受害人以伤害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表达对加害者的忠诚。在《叙事》中,特鲁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图解了愚蠢型斯德哥尔摩效应。她养育了五个孩子,由于孩子太小,不能去地里干活,所以,白人奴隶主时常不给小孩足够的食物,认为小孩吃多也是浪费。特鲁思是奴隶主家的厨师,负责整个庄园的膳食。但尽管自己的孩子饿得嚎啕大哭,她也不会把厨房的食物拿给小孩吃。她认为那是对奴隶主的不忠诚。另外,特鲁思的生育观也显示出斯德哥尔摩效应。一般来讲,妇女会把生育小孩当成自己的人生大事,视小孩为比自己还重要的宝贝。但特鲁思却例外,她把自己生的小孩看作是奴隶主的财产,认为自己生得越多,对奴隶主财产增殖的贡献就越大。她为奴隶主财产的增多而高兴,把奴隶主的高兴视为自己高兴的前提。特鲁思在《叙事》中指出,“亲爱的读者,想一想,别脸红,你就想一下,一个母亲如此自愿的,充满骄傲感地在奴隶制的祭坛上生下自己的孩子,‘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呀’,献祭给血腥的摩洛神*摩洛神出现在基督教《圣经·旧约》中,是古代腓尼基等地所崇奉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但是你必须记住,能成为这样牺牲品的人没有‘母亲’的资格;她们仅是‘东西’、‘动产’和‘财产’。”(p.17)在愚忠型斯德哥尔摩效应中,受害者失去了自我,让渡出自己的“母亲”身份,把自己视为加害者发财的工具,并把加害者的贪婪追求作为自己快乐的源泉。
自卫型斯德哥尔摩效应是指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生存权而故意迎合加害者,形成受害者喜欢或热爱加害者的假象。特鲁思在《叙事》里专门描写了一个典型的自卫型斯德哥尔摩效应。特鲁思五岁的儿子彼得(Peter)被白人奴隶主福勒(Fowler)拐卖到南方的亚拉巴马。为了营救儿子,特鲁思勇敢向贵格会和律师求援。在一些白人正义之士的帮助下,法庭受理并审理了彼得被拐卖一案。根据纽约州当时的法律,把黑人卖出纽约州为奴是违法行为。可是,在法庭上,被拐卖的儿童彼得坚决不认自己的妈妈特鲁思,并且还紧紧抓住白人奴隶主福勒的手,声称自己愿意和福勒在一起,并大声叫他妈妈滚开。事后,特鲁思掀开彼得的衣服查看时,才发现彼得的背被鞭子抽得体无完肤,身上其他部位也伤痕累累。原来,彼得在法庭上不认妈妈的行为是斯德哥尔摩效应的表现形式。在开庭前,彼得受到福勒的毒打和恐吓,不敢当庭与妈妈相认。他拒绝与妈妈相认的行为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受害者在高压下的一种无奈举动。这可看作是人在困境中表现出的一种斯德哥尔摩效应。
特鲁思在《叙事》中所揭示的斯德哥尔摩效应表明:人性是一种维护自我生存的潜能,一种推行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势,一种化解外界强力的内在展现,是一个在社会各种力量的搏击中呈现而出的动态发展过程。*吴慧芳:《弗洛姆人性理论探析》,《理论学刊》2003年第4期。特鲁思的创作思想是对传统善恶人性论的一种突破,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奴隶制社会环境里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的扭曲往往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性本是善恶俱存,所谓“人性的扭曲”就是外界与自身互相作用下的“失衡”。在奴隶制社会环境下,黑奴被白人看作是会劳动的牲口,而非与白人平等的人。*Kathy L. Glass, Courting Communities: Black Female Nationalism and “Syncre-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08.唐忠宝和王丽梅说,“无论人性多么复杂多变,它始终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现实,离不开产生它的历史环境。”*唐忠宝,王丽梅:《对人性善与人性恶争论的反思兼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宁夏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黑奴为了在恶劣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不可避免地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顽强地生活下去。特鲁思的这部作品展示了斯德哥尔摩效应中的人格扭曲状况,揭露了恶劣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毒害和践踏。
三、性善与人性回归
从马克思人性观来看,“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因而人性必然是历史的变化着,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人性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具体表现。”*章海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初探》,《河北学刊》1982年第2期。人性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善与恶都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有关,并非基督教所宣扬的“人一生出来就带有恶”。人性回归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形态里,人经历了人性沦丧或异化之后,对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旨在消除人性恶的负能量,修正被扭曲的人性,促生人性趋善的正能量,促使人性从恶到善的发展。简言之,人性回归就是人性善的正能量的坚持和发展。特鲁思在《叙事》中所描写的人性善彰显了人在恶劣社会环境中坚持人性正能量的重要性和可贵性。在美国奴隶制社会里,尽管总体上来讲,白人奴隶主对奴隶非常残忍和冷酷,不把黑奴当作平等的人看待,但是也有一些白人坚持人性的善良品质,能站在正义的角度看待黑奴和黑人问题。特鲁思在《叙事》里对人性恶的抨击和对人性回归的颂扬,就是要鞭挞奴隶主泯灭的人性,呼吁关爱弱势种族,大力弘扬人性中的善。笔者拟从以下方面来探索特鲁思在这部作品里所揭示的性善与人性回归的内在关联:正义之善、怜悯之善和恶中之善。
正义之善是指在不合理社会环境中一些人不畏恶势力,捍卫社会公平的正义之士的善良举措。这样的善是人性向善的发扬,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希望。在《叙事》中,特鲁思的五岁儿子彼得(Peter)在纽约州废除奴隶制的法令生效后被奴隶主卖给福勒(Fowler)。福勒是南方奴隶主,于是他把彼得带回老家亚拉巴马州。彼得被从一个将即将废除奴隶制的州带到一个奴隶制没有废除迹象的地区。特鲁思得到消息后,先是向彼得的原主人求情,无果;然后她去向贵格会求救,在有正义感的白人教徒的支持下,向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特鲁思赢得了法官和陪审团成员的同情和支持,最后法官把孩子判还给特鲁思,并使特鲁思获得了一笔赔偿金。这些白人心中对人性善的坚守才使正义得到维护,特鲁思的公民权才得到真正的捍卫。特鲁思还举了一个事例:杜蒙特同时拥有黑奴家仆和白人家仆。白人家仆凯特(Kate)嫉妒黑奴特鲁思的厨艺,于是就故意在特鲁思做的土豆泥上撒上煤灰,导致特鲁思遭到杜蒙特一家的责备。然而,杜蒙特十岁的大女儿格特鲁德(Gertrude)觉得此事蹊跷,专门藏在暗处,偷窥到白人家仆凯特的恶行,并当着父母的面揭穿了此事,还了特鲁思一个清白。白人小女孩维护正义的举措也是其人性中“善”的一种表现形式,代表了善良白人的道德取向和伦理观念。
怜悯之善是指人在怜悯心和同情心的作用下所做出的善举。在《叙事》里,特鲁思从杜蒙特家逃离后,来到白人维吉尼尔(Wagener)的家寻求帮助。维吉尼尔夫妇收留她和她的孩子。奴隶主杜蒙特上门讨要特鲁思。维吉尼尔只好掏了20元付给杜蒙特,购买了特鲁思余下的奴隶服务期,帮助特鲁思解脱了被追捕的命运。维吉尼尔夫妇的善举表明在白人中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在另一个场景里,奴隶主福勒时常毒打小黑奴彼得(Peter);福勒太太是生性善良之人,虽然她无法阻止丈夫殴打彼得,但是她总是给挨打后的彼得涂抹油脂,使其伤口不被感染。同情和怜悯类情感是人性善的直接表现形式,一些善良的白人给予遭受主流社会歧视、仇视和打击的黑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虽然这些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的苦难,但有助于让黑人感受到人性善的温暖。
恶中之善是指在行恶的时候没把事情做得太绝,对弱势人物或群体还有一些善的举措。在特鲁思的《叙事》中,白人奴隶主奥丁伯格(Ardinburgh)死后,其家族成员在继承其遗产时,谁也不愿要年老体弱的老奴詹姆斯(James),尽管詹姆斯曾在奥丁伯格家辛勤劳动了几十年。白人奴隶主的子孙们商议后决定:给予詹姆斯的妻子贝蒂(Betty)和贝蒂哥哥凯撒(Caesar)自由,责成他们负责照顾年老的詹姆斯。这也不失为白人奴隶主在贪婪自私的社会环境中所做的一点善行。特鲁思在《叙事》中还提及到,杜蒙特每天给奴隶足够的饭,平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打骂黑奴。但实际上,杜蒙特仅是一个自私的奴隶主而已,他不打骂奴隶,是怕损坏了他的“财产”;他给奴隶足够的饭吃,是想让奴隶吃饱饭后更有精力干活。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他对待奴隶的方式会使奴隶在苦难中生活得更为好一些。因此,杜蒙特对奴隶的这种方式也可看作是其人性中“善”的表现。他的这种“善”要远远好于那些既要奴隶干重活,又不给奴隶吃饱饭的奴隶主的“恶”。
白人通常被视为黑人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但不能把所有的白人都视为人性“恶”的恶魔。因此,特鲁思在《叙事》中塑造一些有正义感的白人、有同情心的白人和善恶相间的白人。作者没有把有善性的白人当作纯粹的剥削者、侮辱者和施暴者来做片面的刻画,而是把他们描写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人性的善良是人与魔鬼的区别性特征之一。人性中“善”的一面能给他人带来温暖和希望。特鲁思通过自己在奴隶制社会的各种经历表明:白人总体上歧视黑人,对黑人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但白人并不是一个“恶”的统一体;白人中也有一些善良之士,他们会站在正义和博爱一边给予黑人无私的帮助。*Kathy L. Glass, Courting Communities: Black Female Nationalism and “Syncre-nationalism”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r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67.特鲁思关于白人善举的描写旨在弘扬美国社会的博爱,促使白人消解人性恶的负能量,不断生成人性善的正能量。白人性善正能量的积聚有助于美国社会的人性回归,同时也有助于黑人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斗争。
结 语
特鲁思在《叙事》里以探索人性恶和人性善为中心内容,颠覆了南方种植园文学多以宣传基督教性恶观和美化南方奴隶主与黑奴关系的传统模式,“代之以展现人性中交织的善与恶为主轴,令人在领略世界奇风中,不经意地受到人性善恶的熏陶”。*李景端:《人性回归的文学思考》,《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日第3版。奴隶制社会环境为人性恶的出现和演绎提供了背景和契机,使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充分的表现。奴隶制本是美国社会一项严重的“国家犯罪”,而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白人主体上成为贪婪、冷酷、自私和凶残的代名词,但白人的人性中也有“善”的表现形式。白人中也不乏一些正义之士坚决反对奴隶制,同情受苦受难的黑奴,并给予黑奴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援助。连一些作恶多端的白人有时也有善的举动。奴隶制社会的人性之“恶”导致黑奴的人格扭曲,斯德哥尔摩效应极大地伤害了黑人的身心健康。*Margaret Washington, Sojourner Truth’s America,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9, p. 69.特鲁思在这部作品中揭示了人性的各种异化及其恶劣后果,不是单纯地诅咒白人奴隶主的暴行,而是为了引起美国社会对黑奴问题的重新认识。白人奴隶主虐待黑奴的行为不仅给黑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也退化了白人的基本人性,开了美国社会文明的历史倒车。总而言之,特鲁思关于北方黑奴生存状况的描写填补了美国奴隶叙事的主题空白,与美国南方黑人叙事相映成辉,促进了美国奴隶叙事文学作品的发展,对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美国新奴隶叙事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诚 钧]
The Deduction of Humanity in Slavery:A Study ofNarrativeofSojournerTruth:ANorthernSlave
PANG Hao-no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InNarrativeofSojournerTruth:ANorthernSlave, Sojourner Truth discloses a wide diversity of virtues and evils in the human relations at the advent of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New York State, eulogizing Northern black slaves’ awakening and strife before the Civil War. The evils, virtues and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can be considered three layers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in Northern slavery of America. In a strikingly vivid tone, Truth delineates three types of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slavery: avarice, callousness and hypocris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Stockholm Syndromes derived from superstition, gratitude, blind loyalty and self-defense, she makes invectives against the unreasonableness of slavery, maintaining that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will surely result in social distortion. Furthermore, she presents the multi-dimensional virtues of some whites based on justice, piety and semi-evil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the virtues of humanity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Sojourner Truth;NarrativeofSojournerTruth:ANorthernSlave; evils of humanity; virtues of humanity; distortion of humanity
2014-07-26
庞好农(1963- ),男,重庆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非裔美国城市自然主义小说之性恶书写研究”(14BWW074);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赖特小说之性恶书写研究”(14ZS093)。
I 106.4
A
1002-3194(2015)01-00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