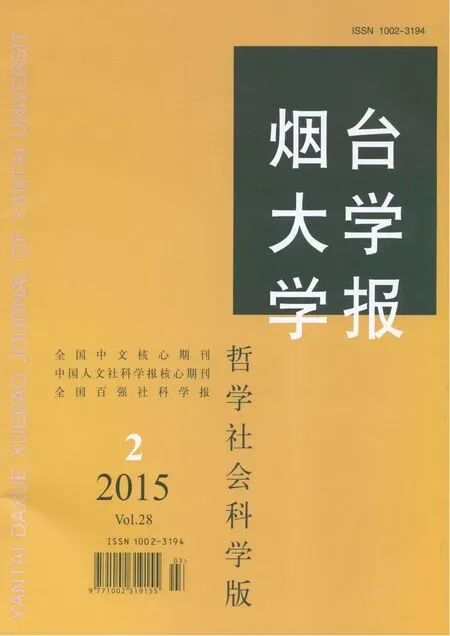走下神坛的美国亚当
——论《边境三部曲》对西部牛仔形象的重构
胡 蝶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走下神坛的美国亚当
——论《边境三部曲》对西部牛仔形象的重构
胡 蝶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麦卡锡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重要作品《边境三部曲》中体现出西部神话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虽然麦卡锡采用了西部小说的传统写作符码和许多经典情节,然而他是通过建构“反神话”话语的方式、从西部神话的内部对其进行揭示和解构。在《边境三部曲》中,麦卡锡秉承后现代解构神话的一贯思想,将神人般的牛仔英雄重构成为一个个在凡间生活的既困顿流离又孤独迷惘的常人和凡人形象,揭露出美国亚当们背后隐藏的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将美国亚当们拉下了神坛,也在更深层次上解构了美国西部神话。
麦卡锡;边境三部曲;美国亚当;人物重构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2.011
科马克·麦卡锡 (Cormac McCarthy)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称赞他是美国当今最优秀的四大小说家之一。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天下骏马》、《穿越》、《平原上的城市》)在人物的设置上遵循了西部小说的传统人物模式,沿用了刘易斯所谓的“美国亚当”作为小说主人公,然而麦卡锡在行文间巧妙地对这些看似神话人物般的主角们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解构。在麦卡锡这三本西部小说中,传统视域下美国亚当自由勇敢、天真无邪的神人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麦卡锡将神人般的美国亚当们拉下了神坛,揭露其背后的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将其神人形象重塑为困顿流离的常人和孤独迷惘的凡人形象,揭露并反映出神话人物在当今社会中的毁灭。
一、美国亚当及其神人形象
“美国亚当”(American Adam)一词首次出现在1955年刘易斯(R.W.B. Lewis)的同名专著《美国亚当:19世纪的天真、悲剧及传统》(TheAmericanAdam:InnocenceTragedyandTraditionintheNineteenthCentury)之中。刘易斯用伊甸园神话中的亚当作为原型来分析在早期美国文学传统中逐渐形成的那些具有独特的美国性的意象和故事。在基督教传统中,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从天堂被贬到人间的经历诠释了人类从天真到堕落的历程。而这一故事的许多意象在美国文学中不断被提及,也成为美国独特性的重要来源。
刘易斯认为美国小说的独特性是基于西部神话的刻板接受。他试图在早期美国文学传统中找寻美国人对于身份和文化的正当性和传承性,揭示美国作家所书写的亚当式人物不同于欧洲人物模式的独特之处。在追溯了19世纪作品中的美国神话模式之后,刘易斯发现,经典作家如库柏、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亨利·詹姆斯等人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一个相似的身份模型。刘易斯把这一模型命名为“美国亚当”。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根据爱默生日志中的描述:“这里站立着古朴率真的亚当,以简单的自我面对着整个世界。”*R. Richardson and B. Moser,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 34.
刘易斯在专著中将“美国亚当”定义为其“形象体现了全新的个性与特征,是新征程中的英雄:一个从过去历史中解放出来的人,快乐地摆脱了先辈束缚,丝毫不受到如家庭、种族等的传统影响,纯粹而自然;他孤军作战、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独有的、内在的智慧来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R.W.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p. 5.在《美国亚当》一书中,库珀笔下的纳蒂·邦波(Natty Bumppo)被认为是美国亚当式人物的起源。在后来的传统西部小说中,牛仔主人公就是美国亚当形象的延续,他们像神人英雄一般无所不能:掌握野外生存的必备技巧,能够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掌控世界的能力;正直、独立、勇敢而富有正义;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追求在广袤的西部草原上自由飞驰……牛仔的这些精神也内化成了美国的民族精神。当时的美国建国不久,政府和人民都急切地需要建立国家身份和文化身份。人们难以掩饰对新生的合众国的狂热,坚信美国及自己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时代中的亚当,正在开创一个新纪元。在这种建设祖国、建立家园的极大热情推动下,美国开始了移民向西部原始森林的拓荒。狂热的人们相信,他们可以拥有甚至超过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所描述的那种力量,而广袤的西部大自然就是精神力量的天然储存地。西部就像是亚当生活的伊甸园,将给美国未来的发展和自己幸福的生活带来无限可能性。“从理论上概括地说,在西部这个地方,受折磨的人性抬起了她低垂的头,良心不再受奴役而法律只是幸福的保障。”*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31.西部牛仔们的高超技术、高尚品质符合当时建立民族文化身份、开创独特的美国精神的浪潮,因而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向往。在更高层面上说,他们也代表了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的整体形象——摈弃传统、自由独立、不畏艰难。
刘易斯定义中的美国亚当,除了拥有热爱自由、勇敢无畏的神人英雄的形象外,还有一个普遍特征就是他们身上“天真”(innocence)的本质,是桀骜的理想主义者。《当代美国英语词典》该词有两种含义,一是“lack of guilt”,即无罪、清白、无辜;二是“naivety”,即天真无邪,单纯,涉世未深。在人性上来说,它是远离道德错误,远离邪恶,远离犯罪的一种“无罪”的清白状态。在道德上说,innocence与狡诈、欺骗相对,缺少经验,缺乏世俗心和不老练,显示出一种纯而白的气质。在基督教神话中,人类先祖亚当就是天真无邪的,他自由生活在天堂伊甸园之中,后来听信了狡诈的蛇的恶言,才失掉了天真的本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中,人类一直秉持着天真纯洁的本质,维护着人性道德的崇高。然而随着文明的进程,人类却逐渐从最初的纯真转向功利,之前单纯的人性不复存在,衍生出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人性。
美国神话把美国人民比作新人类、新亚当,反映出他们对于自身道德纯洁性的认知和天真纯洁的品质之向往。休姆在《美国梦,美国噩梦》中曾经说道:“在19世纪中期,‘天真无邪’已经作为一种解放性的神话繁荣发展起来。它象征着无害和对他人的好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它把美国的仁慈奉为一种信念珍藏着……继承早期的清教定居者的遗产,在新世界天堂的新亚当形象和他的堕落创造了一个野史,以说明大大减少的期望和希望的生活。”*Kathryn Hum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Nightmare: Fiction Since 196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p. 40.
麦卡锡书写自己的西部小说时也塑造了一系列这样的“美国亚当”,他们仿佛永远摆脱和超越了历史和时间的限制,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既没有明确的过去,也不遵从明显的传统。他们就是刘易斯所谓的“空间中的英雄”(the hero in space),在美国西部和墨西哥边境这片广袤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区域里面创造着像神话般的生活。然而,麦卡锡并非一成不变地套用西部小说的传统写作模式,而是在行文间巧妙地对这些看似神话人物般的主角们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解构,将美国亚当们拉下神坛,重塑为困顿流离的常人和孤独迷惘的凡人形象,揭露出神话人物在当今社会中的毁灭。
二、麦卡锡对美国亚当意识形态的揭露
刘易斯认为,美国亚当是从历史、家庭和传统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独来独往,不受任何束缚,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固有价值体系保持距离,追求独立、自由和民主。他们的这种性格特征,反映了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最早源自法语的“individualisme”,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反应。该术语在欧洲有着多重含义:“首先,它指带有人人权利平等的理想主义学说,或称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第二,指反国家主义,广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或经济自由主义;第三,对个性的贵族式崇拜,或浪漫个人主义。”*Koenraad W Swart,“Individualism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1826-1860)”,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3 (March 1962), pp. 77-90.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是其文化精髓,并在美国民族精神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盛行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得到极度的推崇。而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部拓疆运动是美国个人主义成长的沃土。特纳认为,边疆个人主义“主要是自由土地和围绕个人的极大机会造成的结果”,反映出当时美国社会强烈的个人发展祈愿与对政治经济平等的民主要求。*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7, p.274.
麦卡锡西部小说中的那些美国亚当们,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美国亚当对家庭的游离,企图摆脱家庭所施加的约束。美国个人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个人的首要任务是自主地发现自我。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与自己的家庭分离,更要从构成个人历史的那些宏大的共同体和传统中抽离。三部曲中的主人公约翰就拼命地想要逃离母亲对自己的控制,为了不用听从母亲的安排进城去接受教育,他选择离家出走,像老牛仔一样凭借自身的努力,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自由地生活在西部边疆。特纳曾说,“在西部边疆,人们从过去的束缚中获得了解脱,他们批判旧世界的落后、厌倦于它那些陈腐的清规陋习和思维方式,并对其所谓的经验教训失去了兴趣——人们无拘无束、自由独立,在自由边疆创造着自己的美好新生活”。*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Wang Bo (ed) , A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19th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6-217.美国的个人主义思想又要求美国亚当们追求民主和平等,因为只有在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才能得以实现。美国亚当不畏强权,敢于为正义献身,以此来追求民主的社会和平等的权力。约翰在被牵连入狱后,面对黑势力头目的威胁,宁死不屈,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出狱后,为了追回属于自己和朋友的马,约翰对握有生杀大权的上尉丝毫不感到畏惧,而是挟持了上尉。经过一番周旋后,约翰最终追回了马。但是以暴力来换取正义,获得民主和平等,并不是值得提倡的做法。
美国亚当身上还体现出美国意识形态中的帝国主义思想。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认为,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康拉德、吉卜林、纪德和洛蒂等欧洲作家对殖民主义的描述中早有揭露。他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似,“所有追求统治全球的宗主国都说过、做过同样的事”;而且“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关于‘世界新秩序’的修辞,它那种孤芳自赏的气味、难以掩饰的胜利情绪和它对责任的庄严承诺,都是康拉德在霍尔洛德身上描写过的:我们是老大,我们注定要领导别人,我们代表着自由和秩序,等等。没有美国人能逃脱这种感觉体系”。对土著居民和其他弱势国家及其不同肤色的人民之压迫、侵略、干涉内政等都包裹在自己国家利益的外衣下。当遭遇反抗时,帝国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就如同萨义德所说,“在干涉小国的事物时,总会诉诸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托词;每当出现了麻烦时,或当土著纷起反抗,拒绝一个被帝国主义扶持的言听计从不得人心的统治者时,总是有一种毁灭性的冲动”。*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xxvi-xxvii页。历史上这样的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行为在不同帝国主义国家身上屡见不鲜,当美国成长为强国之后也脱离不了帝国主义的桎梏,走上了为世界订立规则,而自己又凌驾于各种规则之上的帝国主义老路。以国际共同利益为旗号,大刀阔斧地重塑别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斯珀金看来,传统的美国边境神话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边疆经历铸造了由热爱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国家,他们致力于将民主的而非帝国主义的征战带去世界其他区域”,而为了配合这一观点的正当性和正确性,作为叙事体系的神话就“必须仔细地忽视或掩盖美国在国外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那些历史上欧洲人成功扎根美洲的侵略、征服和殖民化行为”。*Sara Spurgeon, Exploding the Western: Myths of Empire on the Postmodern Frontie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长时间以来在这种叙事策略的故意掩盖之下,美国被塑造成了拥有无限可能的新世界,美国人民是自由、勇敢、独立的英雄。麦卡锡也注意到了美国亚当的帝国主义思想,并将对帝国主义思想的揭露融入进三部曲的故事当中。在他的笔下,神话的帝国主义叙事也渗透在三部曲的主人公身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无不透露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身处在异国他乡,不知不觉中以帝国主义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并试图像传说中的那些神话英雄一样,靠着自己的坚韧与英勇,最终征服这里,完成足以流芳百世的伟大基业。在萨义德看来,“在一切以民族划分的文化中,都有一种想握有主权、有影响、想统治他人的愿望”。*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17页。三部曲的主人公之一约翰也打心里有着这样的欲望,他并非像先祖亚当那样天真纯洁,目标和追求背后掩藏着与生俱来的征服和权力的原始欲望。在面对这样的意识形态时,麦卡锡决心通过将神人形象的牛仔拉下神坛的方式,将其塑造成困顿流离和孤独迷惘的常人、凡人,从而解构美国亚当神话。
三、走下神坛的美国亚当
作为现代美国亚当的化身,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们继承了早期西部牛仔英雄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在自己的流浪生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勇敢面对恶劣的荒野环境,掌握野外生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同时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和毅力。年少的比利捕获过狡黠凶狠的母狼;受伤的约翰能在马上轻易套住小牛。除了杰出的能力和勇气,他们身上还体现了自纳蒂·邦波以来的西部小说主人公惯有的品质:尽管文化水平有限,却有十分高尚的道德境界。麦卡锡刻意着墨的这些牛仔形象“消解了当代文学众多‘反英雄’人物身上的阴柔、滑稽或怪异的审美特征”,体现出美国亚当们的传统特征,赞扬了美国边疆精神孕育的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坚守正义等美国核心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当时美国大众迫切需求的文化心理。*江宁康:《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与经典建构——论麦卡锡小说的审美特征及银幕再现》,《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麦卡锡在汲取西部文学传统营养的同时,有意远离既定模式和宏大叙事,倾情于对神人般的牛仔英雄日常生活困境和精神迷途的叙述和营构,将臆想中的神话拉回冷峻的现实。
刘易斯在定义“美国亚当”时,曾把纳蒂·邦波之类的人物描述成“空间中的英雄”,因为他们仿佛不受到任何空间的限制,摆脱了家庭或祖辈的束缚。三部曲的主人公们个人的生活始终充满着不安定的因素,无论他们怎样试图摆脱这种不安定对自己生活造成的影响,或者通过其他别的方式构建稳定而安全的个人联系,他们都无法取得成功。麦卡锡在三部曲的世界中,所构建的、被称为家园的建筑,往往都是阴暗而破败的。居住在这些建筑里的人也如同建筑本身一样,散发着颓废和不幸的气味——约翰家传的牧场因为外祖父的去世而拱手让人;比利也遭遇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他们都试图重建一个新的家园,不仅能够抚慰自己的心灵,还能重新赋予自己的身份,给予自己归属感和安全感。然而,事情往往事与愿违。如约翰总是以为凭着一己之力能够建立起稳定安全的家园,然而即使在自己的老宅里,拥有整个家的也是他的外祖父,他只是被当作一个受宠的孩子而已,并没有参与决定家庭命运或者拥有实际权力的决策者。对家的强烈归属感和占有欲与参与感和决策力的缺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显示出约翰对于家的主张和看法与真正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后来在罗查庄园,约翰在马棚边上的“自己的”小屋里与阿莱詹德拉幽会,试图找到爱人建立起自己的家庭,然而美梦却被女孩的父亲罗查先生粉碎殆尽。约翰也曾拼死拯救玛格达琳娜,不辞劳苦试图建造一个“温暖而亲切”的家,然而他努力建造的这个破烂小屋里的微弱暖意始终无法抵抗“一片漆黑”的外界中的“寒气逼人”。*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李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97-228页。
美国亚当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屡次的失败使得他们意识到现实的强大与自己力量的渺小。那片被无数人称作是“充满自由、让人洗心革面、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地方,却不是他们最终的伊甸园。*Megan Rileyc Gilchrist, The Western Landscape and Culture in Cormac McCarthy and Wallce Stegner: Myth of the Fronti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47.于是他们放弃了原本追寻的新世界,想要回到原来世界。只是,“一个竭尽全力却终于失败的计划常常把人的生命分成两个阶段——过去和现在”,原来的世界便是永远也回不去了。在无法抗拒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巨大影响下,美国亚当们也只能在现实生活中饱尝漂泊失意的滋味。*R. Richardson and B. Moser,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 125.
麦卡锡西部小说中构建的美国西部边疆和墨西哥边境地区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地域的边远和游牧文明的根深蒂固必然导致民主政治普及的滞后;同时工业文明入侵后,那片土地上开始出现但还未成熟的都市文明又遭遇后现代文明的强势挑战,这些必然会对流浪至此的美国亚当们的心理产生强大的冲击。亚当人性中单一而完美的“静态”结构必定会解体,催生出人性的多面性,包括暴力抗争与滥用暴力。所有的存在和冲突汇成一股强大的对人性的压迫性力量,导致人进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困境。虽然这种精神困境产生的契机是社会文化大语境,但追根究底内在的根源却是人性固有的黑洞,这些黑洞是主体即使自觉意识到了却无力抗争的客观存在。因此,麦卡锡在书写西部故事的时候,人性中的“疏离”、“迷惘”、“焦虑”、“孤独”等精神困境也成为小说着力表现的对象,“虽然从生物学来讲人是完整无损的,但在实质上他却被走投无路、失意、自卑和恐惧所困扰。表面上,人类可以装作满意和坚强;但在内心,他却是贫困的、匮乏的、软弱的,经常处在苦难的边缘,动辄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挠一下他的皮肤,你会感到他的悲哀、忧伤、恍惚、恐惧和痛苦。……的确,它常常是一种沉寂的绝望的生活”。*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正如后现代学者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所言,“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从来没有谁能忘记自己整个精神的突然贬值,因为它的匮乏太令人触目惊心了”。*谢有顺:《话语的德性》,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88页。麦卡锡将对西部人民生活的关注从形而下层面转移到了形而上层面,在对外在生活困境表达同情的同时更不忘内在的精神困境,并在不断的意义探寻下,勾勒出西部人民所经受着的精神本真图景。
麦卡锡笔下的美国亚当们像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一样,失去了天真和纯洁,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中,变得迷惘且孤独。他们开始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到陌生,感到无法理解。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特别的荒诞之感,“与荒诞相伴的是绝望、无出路的感受,对阐释人类当前存在的一切世界观和各种理论的崩溃的体验”。*文聘元:《人生与虚无: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第18页。麦卡锡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揭露了一种当前社会中的人类生存状态之现实,即伴随着传统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道德价值观念的解体,美国人民对于自己能够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信心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人们对世界也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一切都变得不可认识和难以解释。加缪曾言,“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真正构成荒诞感”。*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页。
昔日的牛仔英雄们在各自的流浪生活中不断体验着这份迷惘。对于美国社会,他们虽然能够感知到西部社会正在急剧转型的事实,然而却无法理解抑或干脆拒绝理解,他们也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种变化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又无所适从。三部曲中的比利曾感叹道,“一个人在小的时候,对将来的事情总有好多的想法和打算……可每当你长大一点,你就往后退缩一点。我觉得这其实是为了减少一些痛苦。不管怎么说,这块地方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什么东西都不是原样了……一切都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永远不再会是原先那样了”。他开始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开始随波逐流,开始忘记自己的理想和想要过的那种生活。比利说,“我做小孩的时候想要的东西和我现在想到的东西真的不是一回事了。我想我那时想要的,其实并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利的这番话看似表明了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之清醒的认识,听起来貌似心中很澄明,然而这只是假象,现在的他想要的是什么自己却并不知道,他一直处于迷惘混沌的状态中,如他所言“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从来就没弄明白过”*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第74-75页。。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下,美国亚当注定了会在生活中碰壁甚至遭遇失败。三部曲中的约翰试图用完美的爱情来构建自己田园牧歌生活的乌托邦,最终徒劳无功、一无所获;比利虽然看似接受了西部现实,却完全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变化,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苟活人世。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寻找——迷失——寻找迷失”的恶性循环。比利终其一生都不懈地努力寻找着亲人,试图恢复失去的家园,但故事中不时出现的“迷失”情节作为隐喻,揭示出比利的悲剧命运,以及他精神世界的彷徨无依、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迷惘状态。
美国亚当们一直向往和寻找美好的事物,然而“美好的事物每每总会变成人生的失落和痛苦”。*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第68页。而“这个世界的美丽与丑恶、幸福与痛苦正以相同的程度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曾经饱受宠爱的美国亚当们在现实中日益“感到自孩提时代以来从未感受过的一种难言的孤寂”。*麦卡锡:《天下骏马》,魏铁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82页。“小说中弥漫的徒劳感和无望感”是美国亚当们在这个他们难以理解的世界中的真实体会。*Megan Riley McGilchrist, The Western Landscape and Culture in Cormac McCarthy and Wallce Stegner: Myth of the Frontier, p.152.麦卡锡的西部小说中,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荒诞与虚无,人们置身于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不可避免地会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一种根本性焦虑,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根本依据、目的或者意义。麦卡锡笔下几乎所有人物都处于这种丧失自我的焦虑和困惑之中。在小说的尾声,麦卡锡试图概括和归纳他在“三部曲”中的种种思索:“可你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你能看见它吗?生活一出现,马上就开始消失,一点一点地,一直消失到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你仔细看看这个世界,在什么时刻你看见生活中发生着的东西变成了你记忆下来的东西了呢?这两者又如何区分呢?生活,你既不能拿在手里让人看,又不能标在地图上,也不能表现在你画的图形里。而我们又只能努力去做这一切”。*麦卡锡:《平原上的城市》,第267页。
麦卡锡在三部曲中采用了传统西部小说的整套写作符码,安排了西部小说的经典情节和代表性人物,讲述的故事也无非是牛仔英雄的流浪和爱恨情仇。从表面上看,三部曲只是西部小说传统写作模式的延续;然而麦卡锡采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从西部小说的内部解构其传统模式和意识形态基础。麦卡锡以“反神话”书写方式在对美国西部神话进行批评,从人物塑造上看,麦卡锡在《边境三部曲》中通过讲述几位美国亚当的故事,揭露出他们背后隐藏的个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书写了他们如常人、凡人一样,遭遇的现实生活的困顿流离与精神上的孤独迷惘;解构了神人般的美国亚当的传统形象,批判了美国亚当神话。正如斯珀金所说的那样,“他不仅重写而且批判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他在复杂的后现代视野下展望被鲜血束缚在神话过去中的人类未来,既使传统修辞问题化,又使其浪漫化。他的声音与其所塑造的边疆英雄们是西部文学传统的延续,也是其复杂的对照”。*Sara Spurgeon, Exploding the Western: Myths of Empire on the Postmodern Frontier, p. 17.
[责任编辑:诚 钧]
American Adam Descending from the Altar——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gure of Western Cowboy inTheBorderTrilogy
HU Di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estern writers in American literary canon, Cormac McCarthy devoted his time and energy to looking into the so-called “myths of the American West”, a systematic discoursal construct which exerted extensive influ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and even the spirit of the whole American nation. Honoring McCarthy with great fame,theBorderTrilogyreveals his meditation of those myths. This paper aims to point out thattheBorderTrilogycriticizes the myth of American Adam. Adopting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McCarthy deconstructed the super-hero figure of Adamic heroes and reconstructed them as everyman living in the mundane world, homelessly, helplessly and hopelessly.
McCarthy;TheBorderTrilogy; American Ada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gure
2014-09-26
胡蝶(1989- ),女,重庆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I
A
1002-3194(2015)02-008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