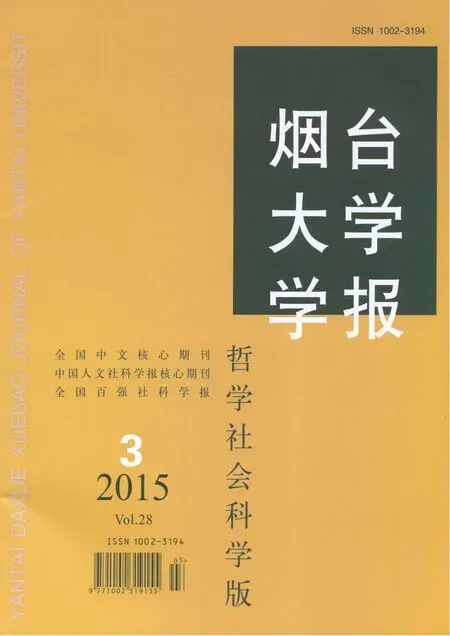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法律逻辑*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法律逻辑*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宅基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宅基地的分配也就体现着福利性和公平性,只要是本集体成员,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均有权无偿申请取得宅基地,“一户一宅”政策具有正当性;在供地紧张的地区,可以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但宅基地的福利性并不能抹杀宅基地使用权本身的财产属性,农民无偿地创设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之后,即享有这种被《物权法》确认为用益物权的财产,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或处分是宅基地财产属性的题中之义,无论是否承认宅基地的保障功能,都不影响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在目前社会发展现状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主要体现在:慎重稳妥推进农户住房财产权抵押、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在受让人取得住房所有权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权。
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流转;房地分离;法定租赁权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3.004
一、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基调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即将进入试点阶段。
《意见》指出,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兼顾效率与公平,围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目标”,“发挥法律引领和推动作用,着力政策和制度创新,为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践经验。”这些指导思想都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指明了方向。针对农户宅基地取得困难、利用粗放、退出不畅等问题,《意见》指出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是:“要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对因历史原因形成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和一户多宅等情况,探索实行有偿使用;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发挥农民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
为了保证改革试点工作的依法进行,《意见》指出,“试点涉及突破相关法律条款,需要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允许试点地区在试点期间暂停执行相关法律条款。”2015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暂时调整决定》),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4款、第62条第3款关于宅基地审批权限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44条第3款、第4款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本条第2款、第3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第62条第3款:“农村农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44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下放至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呈渐进式趋势的大背景下,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学界所倡导的还原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本性,依市场化规则建构相关制度的建议,自无采行空间。我们的思路便集中于:在契合当下宅基地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如何较为充分地实现其财产功能。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暂时调整实施的宅基地管理规定仅及于审批权限,*在立法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常委会委员建议,宅基地制度改革还可以再放开一些。但法律委员会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改革试点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稳步推进是必要的。建议对委员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试点工作中进一步研究论证。”陈丽平:《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很有必要》,《法制日报》2015年2月27日,第3版。并不及于《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其他规定,*《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农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第1款)“农村农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第2款)“农村农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44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3款)“农村农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4款)但并不影响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就宅基地财产功能方面进行突破。《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1款关于“一户一宅”和宅基地面积的限制、第2款关于宅基地的规划控制等规定,即使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亦应坚持,并不构成改革的障碍,无须暂时调整。第4款“农村农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的立法意旨在于:“防止农村农民以建住宅为名搞房地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出租,只是转让、出租后不能再申请宅基地,“此种法律效果仅在出卖人与宅基地审批机关之间发生,管制对象仅仅是作为出卖宅基地以后再度申请的农村村民”,*王卫国、朱庆育:《宅基地如何进入市场?——以画家村房屋买卖案为切入点》,《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也不构成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障碍。由此,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就成了宅基地改革试点的一个主题。“一个符合我国现实社会需要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既不可能由其他制度取代其保障功能以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又不能完全不顾及宅基地制度的利用效率。两大价值目标必须在同一个制度之中得以实现,是现代社会公平与效率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刘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
二、宅基地的福利分配与财产属性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户籍制度构造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完全惠及农村,而农民又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改之以宅基地和承包地来替代。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不过是身披私权外衣的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充任着社会治理手段的角色,其中所奉行的,自然不可能是私法逻辑。*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4页。宅基地的这种保障功能,及其对农村社会稳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几乎是宅基地制度设计时的主要政策考量。
宅基地的分配,虽然在私法上具有创设宅基地使用权的效力,但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现有规则不合他物权设定的基本法理。*参见高圣平、刘守英:《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7年第2期。按目前的宅基地分配程序,农民申请宅基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宅基地申请者无偿提供宅基地,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在试点的33个县(市、区),根据《暂时调整决定》的规定,下放宅基地审批权限,其中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批;使用新增建设用地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广受诟病的审批规则过于复杂的问题。*关于对目前宅基地审批程序的批判,参见申欣欣:《宅基地使用权审批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宅基地分配时的审批有其正当性:宅基地申请是否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可以将审批解释为宅基地使用权设立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参见蔡立东:《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法律结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但过于强调审批的作用,忽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在乡(镇)、县人民政府对具体宅基地申请普遍不大了解的情况下,审批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宅基地使用权本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上所设定的负担,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意志在宅基地的分配中应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基于此,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宅基地审批制度,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这里,回避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提法,改之以“村民自治组织”。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组织是指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在我国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够明确,*虽然《物权法》第59条第1款规定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本集体成员”,但何为“本集体成员”,学界争议不断。参见高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以下。由村民自治组织代表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既与《物权法》的表述相一致,*对于集体土地等自然资源,《物权法》第60条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至于如何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管理作用,本文以为,应当更多地强调村民自治组织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的作用。例如,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在众多的申请者中如何选定拟分配宅基地的申请者,则应由村民自治组织依合法有效的议事规则或村规民约来加以解决。
唯应注意的是,宅基地的分配体现了身份性和无偿性的特点,只有本集体成员才能无偿地取得宅基地、无期限地使用宅基地,具有浓厚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基于成员权获取的集体共有财产,同因身份权相联系的福利分配相对应”。*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本集体内部,成员平等,每个成员分配宅基地的权利也是平等的,亦即只要是本集体成员,均可公平地要求集体分配宅基地。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行法上“一户一宅”的正当性,这也就成了当下落实“一户一宅”政策的逻辑前提。“一户一宅理念的住房(地基)分配制度亦反映了数十年的社会政策。”*郑尚元:《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中国法学》2014 年第 2 期。但在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下,“一户一宅”政策无法得以贯彻,尤其是对于已经没有符合规划的宅基地可供分配的农区。由此,《意见》提出要完善宅基地取得方式,“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这就是说,要以多种形式贯彻“一户一宅”政策,公平地实现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这一任务是在宅基地制度改革分类试点的理念下提出的,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的传统农区”,继续实行“一户一宅”的宅基地分配制度,对其中人均耕地少,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探索实行相对集中统建、多户联建等方式,落实“一户一宅”,原则上不再进行单宗分散的宅基地分配;而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的农区”,通过集中建设农村公寓、农民住宅小区,以“户有所居”落实“一户一宅”的住房保障功能。已没有新增宅基地可供分配的地区,可以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集中建设公寓式住宅,落实宅基地权益。*参见《宅基地改革方案初成 7000万套小产权房转正无望》,2014年10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0/26/c-127141268.htm,2015年3月10日。
在宅基地公平分配观念之下,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和“一户多宅”等情况如何处理,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中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意见》指出是要“探索实行有偿使用”。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其一,如何与现行法相协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76条的规定,“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其法律后果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实践中,责令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农民拆屋退地,十分困难。如完全改之以收取宅基地使用费的方法,尚不能涵盖超占宅基地的所有情形。具体措施还要符合比例原则,如超占宅基地的面积很大,仅靠收取宅基地使用费的方法,并不足以惩戒非法占地行为,还应直接适用《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不宜以收取宅基地使用费代之。而对于超占面积较小、违法程度不大的情形,拆房退地确实存在浪费社会财富的问题,则可以采取收取宅基地使用费的方法。宅基地使用费标准的确立既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遏制超占宅基地行为的需要,只有在收取宅基地使用费已经使得超占者得不偿失时,收取宅基地使用费才有意义。
其二,宅基地使用费归谁所有?如何分配?如果宅基地超占使用费由相关行政机关征收后进入地方国库,超占就形成了农民集体内部的分配不公。超占宅基地不仅构成行政违法,同时也是侵犯了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宅基地超占使用费既可以看成是行政处罚,也可以看成是侵权赔偿。如果强调宅基地分配的公平,宅基地超占使用费就应当作为超占者对于农民集体的侵权赔偿,理应由本集体成员共有。当然,并不一定采取每笔宅基地超占使用费都要现实分配,也可以作为集体资产的组成部分,满足本集体的特定需要。
其三,因房屋继承原因所引起的“一户多宅”问题是否亦应适用本规则?“一户一宅”所针对的是宅基地的公平分配,亦即是对宅基地使用权创设取得的限制,而不是对移转取得的限制。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农民房屋的继承,自不应禁止农民通过房屋继承等方式取得两处以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参见高圣平、刘守英:《宅基地使用权初始取得制度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7年第2期。因此,因房屋继承所造成的“一户多宅”,并不违反宅基地的分配原则,不应适用收取宅基地使用费的方法。总之,要通过改革试点,探索健全“依法公平取得、节约集约使用、自愿有偿退出的宅基地制度”。
但是,宅基地分配的福利性,并不能抹杀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我国《物权法》上明确将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种他物权(财产)加以规定,其财产属性至为明显。也就是说,即使农民分配宅基地是其应享有的福利,但已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当属农民的私人财产,两者并不矛盾。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均一再强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的本意即“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物权法》第117条)。在现行宅基地制度之下,农户对宅基地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因其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极受限制,收益权能即有名无实。如此,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应沿着如何完备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而展开。*国土资源部胡存智副部长即指出,“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探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子,不是为了解决建设用地指标,也不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要。”参见张达:《自由买卖不是宅基地制度改革方向》,《证券时报》2013 年12月13日,第A02版。
在现行规则限制宅基地流转的情形下,农民无法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目前限制宅基地流转的主流观点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具有身份性质的权利,只有本集体成员才能享有,如果宅基地向本集体之外流转,则与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不符。此外,宅基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如允许宅基地的流转,则可能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的状况。
就此,本文作者不敢苟同。
第一,宅基地分配的福利性,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具有身份性,这仅仅只是针对宅基地分配,即宅基地使用权创设取得而言的,并不表明非本集体组织成员不能依法移转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已被分配宅基地的农民自可处分其宅基地使用权,他人基于合意仍可移转取得该宅基地使用权。此时,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即已彰显,农民据此可以取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宅基地的福利性和无偿性是针对宅基地的分配环节而言的,仅此不能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
第二,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虽然不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当然内容,*因为现行法上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并无权利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的规定。但宅基地事实上起着社会保障的(替代)作用。从逻辑上讲,当宅基地使用权以转让方式流转时,受让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而让与人丧失宅基地使用权,此时原农民(让与人)即无宅基地。但若该转让充分实现了宅基地的市场价值,该农民可以以转让所得财产性收入投入生产经营,以此营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远比禁止宅基地流转时的消极保障功能要更为积极。即使经营失败,该农民亦可借助已覆盖城乡的基本生活社会保障得以生存。这本是自罗马法以来“自己责任”的当然之理。
第三,认为宅基地因承载社会保障功能而禁止流转的逻辑前提是,原农民可能丧失宅基地。限制宅基地流转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但实际效果是试图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在市场条件下,农民作为理性人,完全有能力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马晓勇:《理性农民面临的制度约束及其改革》,《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7期。在“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即使是进城务工并已经在城市安家的农民也不会轻易选择放弃农村的房屋及宅基地。*参见李文谦、董祚继:《质疑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正当性——兼论宅基地流转试验的初步构想》,《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3期。而且,如果制度设计本身使得宅基地之上的农村住房流转后,原农民并不丧失宅基地,禁止流转的这一理由即可破解。如农村住房转让、出租、抵押之后,受让人或承租人仅仅只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租赁权,原农民并不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租赁期间届满,原农民即恢复行使宅基地使用权。
综上,宅基地分配的福利性,并不能否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已分配的宅基地构成农民的财产,农民自可依法加以处分。只不过,在当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农民处分其宅基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这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自有其正当性。只要农民处分其宅基地使用权最终并不导致其丧失宅基地,即可在满足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前提下,取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充分建立的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即指日可待。
由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属性出发,农民以出租、转让、抵押等形式处分其宅基地使用权自无禁止之理。调整宅基地法律关系的主要法律——《土地管理法》就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无禁止性的规定,已如前述。但199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指出:“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2004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亦规定:“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2007 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再次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租用、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这只能说明,在现行宅基地制度设计中,宅基地的保障功能被优先考虑,而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财产的经济效率功能几乎是被忽略或者说是被冻结的。*参见陈龙江:《制度功能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探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下,《意见》指出要“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这里,虽然承认了宅基地的财产属性,但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人局限在“进城落户农民”,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不利于宅基地价值的发现。不过,这一限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影响,会随着下述“房地分离”原则的承认而大为降低。
三、农民住房与宅基地之间的利用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关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论述中指出:“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里将“抵押”、“担保”相并列,实有不妥。在现行法之下,“抵押”是“担保”之下位阶概念,“抵押”只是“担保”的一种形式,“担保”即包括“抵押”,两者在逻辑上无法相并而称。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只言及“担保”(此时包括了“抵押”),或“抵押担保”(此时抵押只是担保的一种类型)。但就宅基地制度而言,并未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而仅提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虽然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本意,包括了农民处分宅基地使用权本身,即农民可以转让其宅基地使用权,亦可以以其宅基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但是,从官方的解读来看,却无法得出这一结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而不是指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胡存智:《宅基地改革方向是扩大权能而非自由买卖》,《国土资源》2014年第1期。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抵押担保、转让,但要慎重稳妥地推动农民住房抵押担保、转让,以探索宅基地上农民住房的财产性收入的路径。这似乎意味着农民住房与其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分离。
从讨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大量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讨论逻辑:因为宅基地流转受到限制,在“房地一致原则”之下,宅基地之上房屋的流转也同样受到限制。只有解决了宅基地流转限制的问题,农村房屋的流转才具有了可行性。但这一逻辑是否具有规范性基础,亦即我国法上是否就宅基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一致做了规定?至少在目前看来,尚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
最早对农村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作出分别规定的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其中第21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45条规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第1款)“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社员出租或者出卖房屋,可以经过中间人评议公平合理的租金或者房价,由买卖或者租赁双方订立契约。”(第2款)这些规定表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土地的公有制,宅基地的所有权当然属于集体,但房屋属于农民的生活资料,自应属于农民个人私有,并可进行交易,但这里并没有言明房屋所有权的转让对宅基地权利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2月)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原修正草案作了修改。其中,第7条第3款规定:“农村土地包括宅基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48条规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还要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合乎卫生、尽量不占耕地的原则,做出建设居民点的统一规划,可以由集体建房社员交房费,也可以由社员自己建房。”第50条第4项规定:“社员合法私有的房屋、农具、工具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这些规定再次明确了“房地分离”的态度。由此可见,在我国,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权利本来就是分离的。
现行法上就房地一致原则的规定始于《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其中第23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时,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随之转让。”第24条第2款规定:“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由此传达了“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双向一致规则。但该条例规定了两个例外,即“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批准,并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第25条第2款)“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但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第24条第2款后段但书)。自此,“房地一致”原则为此后立法所遵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1条、*该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担保法》第36条、*该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应当将抵押时该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同时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物权法》第146条、*该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第147条、*该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第182条*该条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等均对此做了明确规定。
但这些规则无一例外,均属对国有建设用地及其地上建筑物等之间物权利用关系所作的规定,并不涉及宅基地及其上房屋之间的关系。虽然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均属在他人土地上设定的以建造并保有建筑物等为目的的物权,但两者之间物权变动规则迥异。《物权法》上,“建设用地使用权”章中上述关于“房地一致”原则的条款,在“宅基地使用权”一章中并未见类似规定,而《物权法》第153条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规定,似乎有排除了将上述“房地一致”原则的规定类推适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可能,因为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则所适用的是“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很明显排除了《物权法》本身,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并未就宅基地使用权与其上房屋所有权的一致性做出相应规定,宅基地与房屋之间的物权利用关系即成为法律漏洞。
就该漏洞的填补,类推适用《物权法》“建设用地使用权”章规定的“房地一致”原则自是可采路径,但并非唯一选择。在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之下,宅基地因承载社会保障(替代)功能,流转极度受限,但农村住房却是自《宪法》到《民法通则》、《继承法》、《物权法》等均予明确肯认的私人财产,其流转自不因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宅基地流转受限而受到影响,“房地分离”也就成了目前可采路径之一。就农村住房买卖后的土地权源问题,我国早已有学者主张采取法定租赁权*参见韩世远:《宅基地的立法问题——兼析物权法草案第十三章“宅基地使用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5期;刘凯湘:《法定租赁权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与构想》,《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或(法定)地上权模式*参见王卫国、朱庆育:《宅基地如何进入市场?——以画家村房屋买卖案为切入点》,《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汤文平:《宅基地上私权处分的路径设计》,《北方法学》2010年第6期。予以解决。*本文作者主张宜采“(法定)租赁权”模式。就此拟另文专述。在我国,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本身就是分离的,所谓“房地一致”仅仅只是房屋所有权与相应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一致。在目前宅基地制度无法改革到位的情况下,“房地分离”既不与现行法相违背,也为农村住房的市场化流转提供了路径。这也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目前各地试点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关于“房地一致”、“房地分离”的各种理论主张,*关于“房地一致”和“房地分离”的介绍,参见陈甦:《论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关系》,《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6期;曾大鹏:《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高圣平:《土地与建筑物之间的物权利用关系辨析》,《法学》2012年第9期;彭诚信、陈吉栋:《农村房屋抵押权实现的法律障碍之克服——“房地一致”原则的排除适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均有其正当性,只要相应配套制度设计合理,两种模式就没有优劣之分,尤其是我国本来就坚持房屋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不一致的情况下,“房地分离”,各自进入市场,没有理论上的障碍。
“房地分离”模式较好地契合了目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受限的政策目标,但相关交易规则较“房地一致”模式更为复杂。
第一,在“房地分离”的模式下,农村住房的流转对象就不应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受让人并不取得该住房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而仅取得该宅基地使用权的租赁权。这也是宅基地用益物权的实现方式和途径。正如学者所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这一改革目标即是针对农民将住房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的。如此理解也符合《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设定的改革目标,即“建设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参见王崇敏:《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现代化构造》,《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
第二,农村住房所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由他人取得租赁权的,租赁期间和租金标准由当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20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法院酌定。期限届满后未续期的,地上房屋可以约定折价归宅基地使用权人,也可以拆除。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法院参酌具体情形分别处理,总体上以不浪费社会资源为原则。
第三,在“房地分离”的背景下,农村住房抵押权实现时,方式可以多样化,根据担保债权的数额以及房屋买卖或租赁价格之间的对当关系,选择不同的抵押权实现方式,例如,就城市郊区的农村住房,担保的债权本身如不大,1年或2年的房屋租金就足以清偿,此际,就可以不采取变卖农村住房的方式实现抵押权,完全可以采取强制管理的方式实现抵押权,由执行法院或其聘请的管理人直接将住房出租,以租金清偿债务。农村住房抵押权实现时,房屋买受人或承租人基于身份的限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但可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租赁权(承租权),以使其取得的住房权利具有正当的土地权源。在这一方面,采行“房地分离”模式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制经验值得重视。当然,这些国家或地区所采取的法定地上权、借地借家权模式等无法在我国移植,但推定租赁的模式(法定租赁权)在我国法上并无障碍。当然,为使农村住房抵押制度真正落地,达到政策设计的目标,配套制度的跟进至为重要,这也是控制抵押风险、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住房抵押贷款的关键。例如,登记制度、抵押财产评估制度、抵押权实现程序等等,均应及时配套跟进。
第四,由于农户取得宅基地并未支付对价,在农村住房出租、转让(包括因实现抵押权而出租或转让)时,宅基地使用权的租金应在国家、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标准和比例应参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租金数额、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等综合确定。针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不够等问题,《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与集体之间、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和相关制度安排;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就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租金而言,国家以税收方式参与租金的分配;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集体的收益就是宅基地价值增值收益;农民因自己投资所致的价值增值部分从集体收益中分配。*参见李文谦、董祚继:《质疑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正当性——兼论宅基地流转试验的初步构想》,《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3期。
应当注意的是,“房地分离”模式是我国目前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下的权宜之计,但可能会造成规则设计过于复杂、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增加等问题。*参见高圣平:《土地与建筑物之间的物权利用关系辨析》,《法学》2012年第9期。正是基于此,台湾学者在分析分离模式之后,即认为,“中国大陆在立法上强制规定,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应同时移转或设定抵押,以使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主体一致,颇能防止占有与土地产权分离之现象,值得吾人参考、借镜。”*黄阳寿:《论合建房地异主时房屋所有人之基地使用权》,见赵威主编:《国际经济法论文专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在采取分离主义模式的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建筑物和土地视为两种独立的不动产是土地制度设计中最大的败笔”,并建议“导入将土地和建筑物视为一体的法律制度”。*藤井俊二:《土地与建筑物的法律关系——两者是一个物还是两个独立的物》,申政武译,见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四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宅基地使用权完全市场化之后,其法律地位应同于建设用地使用权,此际,即应坚守“房地一致”原则。
四、宅基地强制退出与自愿退出的关系
在现行宅基地管理制度之下,宅基地无偿取得和无偿使用导致了大量宅基地闲置和低效利用。如何构建宅基地退出机制,盘活这些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无疑是目前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中的重要一环。就此,《意见》指出:“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这里,将宅基地的退出局限于自愿退出,将退出的主体限定于“进城落户的农民”,将退出的范围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但《意见》的表述不应被解读为进城落户的农民仅能以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转让宅基地的方式,有偿退出宅基地。进城落户的农民将宅基地自愿退回集体,亦应包括在内。同时,宅基地退出包括宅基地的强制退出和宅基地的自愿退出两种,其中,前者系指宅基地使用权在法定情形下被强制收回;后者系指宅基地使用人将其宅基地使用权交回集体或依法将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意见》虽未提及强制退出的问题,但现行法的相关规则并未被《暂时调整决定》暂时调整实施,自有适用可能。强制退出与自愿退出之间各有其适用情形,应属并行不悖。但实践中在强制退出机制运行不彰的情况下,自愿退出机制也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一)宅基地的退出条件
现行法上,宅基地退出规则主要是《土地管理法》第65条。*该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这里,虽然不是直接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强制收回情形,但在现行《土地管理法》之下,土地使用权概指使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从事建设或农业生产的权利,既包括了具有物权属性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又包括了具有债权属性的土地租赁权等。*《物权法》施行后,现行《土地管理法》上“土地使用权”的称谓即面临着修改。参见高圣平、刘守英:《〈物权法〉视野下的〈土地管理法〉修改》,《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7期。《土地管理法》第二章的名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具体的条文均证成了这一点。*《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1款即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第13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准此,《土地管理法》第65条适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没有解释上的障碍。但这一规则却面临着以下困境:
其一,“收回”的性质如何界定?
依该条之文义,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几种情形之中,“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而收回,类似于土地征收(该条第2款还规定了此种情形下的补偿机制——适当的补偿,其文句亦与土地征收规定极为类似);“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而收回和“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而收回,在解释上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此时的“收回”是一种行政处罚,即宅基地使用人违反《土地管理法》这一行政法律所应承担的行政法律后果;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时的“收回”是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即宅基地使用人违反了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宅基地使用权设立合同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现行《土地管理法》上的收回规则的性质并不清晰,可能是行政行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征收,也可能是民事行为——追究违约责任,由此而导致收回的程序设计和责任机制并不明确。如果收回的性质是行政征收,则应按照法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并给予宅基地使用人以足额的补偿;如果收回的性质是行政处罚,则应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并且无需对收回宅基地使用权本身进行补偿;如果收回的性质是追究违约责任,则应按《合同法》等法律的规定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如此复杂的情形,无法使收回宅基地使用权落到实处。
其二,“收回”的主体是谁?
依该条之语句结构,虽然要经过“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但收回的主体仍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此而出现了解释上和实施上的困难。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规定的四级行政机关包括:中央、省、县、乡(镇),并不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没有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并不享有行政执法权,如上所述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如何而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无权行使这些权力。如果将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解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追究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违约责任,但宅基地使用权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没有合同,其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依县级人民政府的审批,何来违约(违反合同)而言?二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宅基地使用权也无法得到实施。正如许多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不明确的权利主体,在《民法通则》不能找到其适法地位。其虽然是一个组织体,但其意思形成、意思决定和意思表达机制并不明确。由此而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决定收回宅基地使用权?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哪些人组成的什么机构依何种程序、标准而决定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目前并未明确规定。此外,在广大农村这种熟人社会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才能有动力去收回宅基地的使用权?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的存在,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制度基本失效,实践中真正收回宅基地的情形寥寥无几。*参见欧阳安蛟、蔡锋铭、陈立定:《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10期。
本文作者以为,在宅基地的退出规则设计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在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性之下,权利主体的成员身份的丧失,宅基地使用权即应被强制收回。既然宅基地使用权只有本集体成员才能享有,只要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不再是本集体成员了,就不应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就权利主体的成员身份的丧失,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难度,因为,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是“户”,是另一个在民法上没有得到确认的“主体”。依现行规则,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由此可见,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居民以“户”的名义享有的权利,即农民家庭享有的权利,而不是个人享有的权利。*参见孙宪忠:《物权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这里的“户”是农村自然户而非农村承包经营户,只是为了申请和管理的方便而由国家和集体认可的单位。此种情况之下,宅基地的强制退出条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其一,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户”的全部成员的户籍均迁出,不再具有本集体成员身份时,宅基地应退出。*如《周口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14条即规定,户口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房屋损坏不能利用,应当退还的宅基地,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县(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门提出申请,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收回。但也有地方基于宅基地和房屋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镇江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户口全部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但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农村居民,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只能原地翻建,并不能超出原建筑面积。但是,在规划撤并的居民点不得原地翻建。”其二,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户”的户主死亡,但其继承人均不具有本集体成员身份,此时,继承人因继承房屋所有权而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定租赁权。虽然户主死亡,但该户的其他成员仍然具有本集体成员身份,则不发生继承关系,由该户其他具有本集体成员身份的人继续使用该宅基地,不发生收回宅基地的问题。其三,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体“户”中的成员死亡但无人继承的宅基地,应当收回。对此,《继承法》第32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死者生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宅基地使用权也因混同而消灭。*参见孙毅、申建平:《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315页。例如,《海口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第30条即规定,无人继承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并由发证或批准机关注销其土地使用权证书和有关批准文件。
第二,宅基地使用权人长期闲置宅基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有权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长期闲置是否属于《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第3项所称“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情形,仍需要解释,但依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52条的规定,“空闲或者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在现阶段,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仍然必须坚持福利性,而适时利用宅基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既是物尽其用的表现,也是农民安身立命的需要。*崔建远:《物权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3页。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意长期闲置、逾期未使用宅基地,本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宅基地,有其正当性。不过,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一旦规定闲置两年的农村宅基地可由集体收回,很有可能对一些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造成伤害。论者进而认为应该在增加耕地和保护农民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强制收回,如允许农民用宅基地换房或给予农民补偿。*参见肖华:《宅基地收回切莫伤农》,《西部大开发》2009年第1期。本文作者认为,闲置宅基地的收回并没有完全剥夺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在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因闲置而被收回后,如其回村需要使用宅基地,仍然可以再提出申请,重新依照宅基地取得的相应程序予以办理。相关地方规范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根据宁夏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自治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意见》,对已经取得《集体土地使用证》,但至今闲置的宅基地,《意见》规定,已满二年未建房的宅基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报市、县(区)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农户再申请宅基地建房时,重新依照审批程序批准,待房屋建成并实地检查合格后,按照有关规定登记发证。参见税玉海:《宁夏:宅基地两年未用要收回》,《中国国土资源报》2009年3月24日,第2版。
第三,除因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而强制收回宅基地,类似于土地征收,其程序应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之外,因其他原因而强制收回宅基地,在性质上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的行为。此时,只要满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民主程序以及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房屋进行合理补偿即可。应当注意的是,此时的民主程序对多数决的要求只需达到村民大会或村民委员会过半数同意即可。应当注意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收回宅基地使用权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在现行制度之下,人民政府的作用是批准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亦即经人民政府批准的,才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未经人民政府批准的,不得收回。本文认为,人民政府应当退出宅基地使用权的收回程序。不过,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问题,则不属本文所能解决的,这主要涉及到土地管理模式的创新,例如,对于“一户多宅”现象严重,大量闲置、低效利用宅基地的,在安排年度用地指标时予以相应减少或停止安排;*黄星:《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思考》,《国土资源导刊》2009年第6期。在保持宅基地分配审批制的情况下,对于上述情形,审批宅基地时应少批或不批,对于存在废弃、闲置宅基地的农户,在缴纳拆旧履约保证金后才审批新的宅基地,以督促其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防止新的“一户多宅”现象出现。
第四,现行法上对于宅基地自愿退出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依法理,宅基地使用权是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上所设定的权利负担,自可由宅基地使用权人与土地所有权人之合意而解除宅基地使用权设立合同,使土地所有权之上的权利负担得以移除,回复土地所有权的圆满状态。此外,宅基地使用权既属权利,当然允许权利人抛弃。准此,宅基地的自愿退出并无法律上的障碍。《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文件)第十条中即提出:“加大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力度”;“对一户多宅和空置住宅,各地要制定激励措施,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这一意见明确表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鼓励宅基地的自愿退出。但是,在相关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建立之前,宅基地自愿退出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其一,长期以来,宅基地无偿、无期限使用制度不仅在客观上助长了超标准占用宅基地的趋势,*参见张德松:《关于建立健全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探讨》,《浙江国土资源》2009年第10期。而且对于已经取得的宅基地,农民也不会主动将其交回集体。其二,目前法律政策层面之下,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对象仅限于本集体成员,使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无法实现,农民转让宅基地及其上房屋的积极性不高。
(二)退出宅基地的补偿
在现行法之下,只有在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而收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才给予适当补偿。大多数学者认为,宅基地退出应当给予补偿,无论是因一户多宅、超占而退出,还是因闲置而自愿退出,但也有学者认为,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制度是以当事人取得宅基地的合法与否为前提(包括因继承、转让等合法途径取得的多处宅基地),对于取得不合法的,原则上应当无偿收回。*欧阳安蛟、蔡锋铭、陈立定:《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10期。本文作者认为,宅基地退出时,并不是只有符合《土地管理法》第65条第1款第1项的情形才给予补偿。*例如,2008年12月31日颁布的《日照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就做出了不同于《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该办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一)为实施村庄规划进行旧村改造需要调整住宅,新房建成后,逾期无正当理由不拆除旧房、退出原宅基地的;(二)因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国家建设征收或征用土地等原因确需占用宅基地的;(三)因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宅基地的;(四)未按照批准用途使用宅基地的。由于本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原因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根据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格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给予相应补偿。”对于“因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宅基地的”情形也规定了补偿。该办法第19条还规定:“对符合第十八条第(一)、(三)项规定,宅基地由村集体依法收回而拒不交回的,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由村民委员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有偿使用,有偿使用费标准为每年每平方米1~5元。但影响村庄规划实施的,必须依法拆除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腾出宅基地。除前款规定情形外,不得随意扩大宅基地有偿使用范围。”宅基地退出时补偿机制的建立可能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更多的是掺入了公共政策的因素,诸如激励“一户多宅”、超占宅基地的农民退出宅基地。
宅基地退出时的补偿标准,理论上按市场价格确定最具合理性,但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是权能颇受限制的特殊用益物权,市场价值难以显现,市场价格普遍偏低,农民不可能接受在限制流转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价格。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当是基于宅基地的住房保障特点,以农民放弃宅基地在城镇或社区新村获得相当住房保障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应以当地农民占用耕地建房实际所产生的成本价或复垦指标的政府收购价作为宅基地的有偿退出价。*陈清波:《关于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流转机制的探讨》,《中国改革报》2008年8月12日,第6版。就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株洲市区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在政府实施土地整治、‘城中村’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项目范围内,项目实施单位对农村村民自愿退出宅基地的,给予补偿:(一)农村村民按规定一户一宅,将多余的宅基地退出的,地上附着物按照株洲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征购标准给予补偿;(二)农村村民拆旧建新进入农村住宅小区并退出原有宅基地的,在农村住宅小区内无偿提供住房用地,地上附着物按照株洲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征收标准给予补偿;(三)农村村民进城购房,退出原承包土地及原宅基地的,地上附着物按照株洲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征购标准给予补偿并参照被征农民社会保险标准给付保险金纳入社会统筹;(四)农村村民采取宅基地换房方式自愿退出宅基地,由项目实施单位统一兴建公寓式安置房。拟换房的村民向村委会提出换房申请,村委会制定村民宅基地换房办法提交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通过。村委会与村民签订宅基地换房协议,村委会再与项目实施单位签订本村村民宅基地换房总体协议。”本文作者认为这一规定区分了宅基地退出的不同情形,颇值参照。
目前,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农村建设用地尤其是农村宅基地资源,试图从中寻找新的活动空间。国家政策层面一直鼓励农民腾退多余宅基地,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但经过30年市场经济的洗礼,农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一味的行政命令无法取得实效,在缺乏相应退出机制的情况之下,农民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不仅可以激励农民主动退出超占和闲置的宅基地,促进农村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而且可以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总量的前提下缓解发展用地矛盾,对于推进城市化、实施新农村建设、实现现代高效农业以及维护农民利益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应注意的是,影响宅基地利用形态的根本原因是“小农家计模式”,通过有偿退出方式解决宅基地利用问题,不仅政策效果微弱,而且会带来诸多现实问题。*参见刘锐:《农村宅基地退出问题再探讨》,《中州学刊》2013年第7期。
五、结 语
宅基地使用权虽已被《物权法》确立为“用益物权”,但是,农民宅基地权益维护绝非简便之题。*参见郑尚元:《宅基地使用权性质及农民居住权利之保障》,《中国法学》2014 年第 2 期。“法律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体现了从只重视宅基地管理到既重视宅基地管理又关怀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财产权利的保护的理念的转变。”*王崇敏:《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取得制度的现代化构建》,《当代法学》2012 年第 5 期。也许是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攸关农村社会的稳定,相关政策也是在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和财产属性之间左右摇摆,并未形成主导制度改革的相对一致的观点,这可能是宅基地制度改革要先进行试点的原因。在“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设计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对于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分地区分类试点的模式下,各试点地区可以设计出不同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方案,同时应注意和其他制度的改革相协调。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目标之下,相关方案的设计更应置重于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对农民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不能通过限制其法律权利的行使来实现,而应当采取政策扶持等方式。”*李文谦、董祚继:《质疑限制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正当性——兼论宅基地流转试验的初步构想》,《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赵守江]
On Legal Logic of Trial Reform of Rural Homestead System
GAO Sheng-ping
(CivilandCommercialLawInstitute,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Homestead is the farmers' basic life safeguard (housing safeguard).So, the distribution of homestead also embodies the welfare and fairness. As long as he is one of the collective members, he will have the right to apply for homestead free of charge on the premise of conforming to the planning.“One household one homestead” policy has its legitimacy. However, in the region of land tension,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farmers housing safeguard in various forms in different areas. But the welfare of homestead can not kill the property attribute of rural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After the farmer is distributed the rural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free of charge, he shall enjoy this kind of property which Property Law has identified as usufructuary right, and shall of course have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or transfer the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No matter whether the land safeguard function is admitted, it does not affect the transfer of the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Under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prudent and steady rural housing mortgage or transfer to explore farmers to increase income from property. The assignee of home ownership obtains the statutory leasehold over the rural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rural homestead usufructuary right; usufructuary right; separation between the building ownership and the land use right; statutory leasehold
2015-03-17
高圣平(1968- ),男,湖北仙桃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金融担保创新的法律规制研究”(12SFB203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13JZD007)。 *本文系作者参加国土资源部相关会议以及烟台大学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时草就,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的讨论激发了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在此一并致谢。
D
A
1002-3194(2015)03-00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