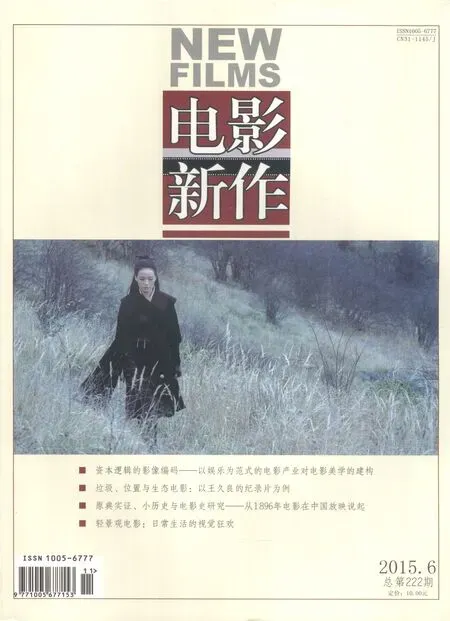夏衍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及家国同构思想
王 侠
夏衍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及家国同构思想
王侠
夏衍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已超越了本身的功能与意义,成为一种文化身份与阶级秩序的象征。在政权更迭、革命浪潮波谲云诡的创作背景下,透过“父亲”这个具有指涉性话语的窗口,看出夏衍对以遵循封建家族伦理秩序为中心的家国同构模式的质疑,体会其在民族危机和家庭罹难之时,对家国同构思想重建的努力。而当他回首“历史之父”的沉重负荷,试图为新中国的美好图景加以影像化的诠释时,却遭受了一时的困境。
父亲形象父权重建家国同构
关于夏衍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向来是学界研究的弱点。而夏衍中的父亲形象更是鲜有提及。实际上,父亲不仅占据着家庭中的重要一席,他还成为考察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诚如杨经建指出的:“鲁迅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杂文,在这里,‘做父亲’其话语本身也许并不深奥,但‘父亲’和‘做父亲’的所指含义丰厚无比——它甚至牵涉到整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父亲’带领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程。”①通过“父亲”这一代表着特定时期民族、文化、伦理、道德、心理层面的形象来考察夏衍的电影,从中体会夏衍对解构与重构、传统与现代、守成与前卫、退守与革命、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形象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功能与意义,成为思考家国问题的重要对象,“父亲是中国电影中关于家庭、国家、社会和文化想象的重要能指符号,对父亲角色的定位和评价是中国当代文化身份和认同中的一个重要指标。”②对夏衍电影中父亲形象的挖掘与考察,“父亲角色的定位与评判”成为切入夏衍电影思想内部,窥看他人生哲学、文化伦理、道德诉求的窗口。
一、父权的颠覆与陷落:家国同构的破裂
夏衍是以一个颠覆者同时也是建构者的身份走上电影创作之路的。带着党的领导者瞿秋白的“万事留心”的嘱咐,夏衍等左翼人士开始打进了向来被资本家操控的电影界。他的首部电影剧作《狂流》(1933),一改当时电影界普遍流行却不被看好的武侠、公案、伦理、爱情等与时事相悖的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被誉为“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③。在《狂流》中,夏衍对传统家庭中延续的“父本位”思想、父慈子孝命题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影片中的傅伯仁是个巴结权贵、唯利是图,置女儿个人幸福于不顾的无耻父亲。剧作侧重于展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表现封建家庭内部、父女关系的矛盾方面尽管着墨不多,但只要将父女共置于同一画面,面临同一件事,都会出现一喜一忧、一乐一痛这两大情绪的反差与对抗。父亲接收县长之子的彩礼时喜上眉梢,对应的却是秀娟羞恼、痛苦的表情;筵席间父亲被质问后“狼狈愤怒”,秀娟却面露喜色;傅家一家在江中观水景的画面中,面对“卖妻救父”的贫女秀娟,父亲色心萌动,想占为己有,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被姨太太识破后,只是“狼狈地笑”,而秀娟却内心凄然,“泫然泪下”等等。作为被禁锢在“高墙的大院下”,恪守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地主阶级小姐,秀娟身上彰显得更多的是旧式女子的气质与家庭观念,尽管对父亲对自己强制安排的婚姻抱有不满,但也没有勇气像子君般为追求婚姻的自主离家出走。直到父亲的为富不仁、阴险毒辣、虚伪自私的面貌暴露无遗,她才有了觉醒与反抗的意识。
秀娟最终背离父亲,投向爱人铁生的怀抱,显示出夏衍试图借助秀娟的选择对家与国命运与前途的思考。恩格斯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④秀娟对父权/家庭的抵制与反抗,暗示着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父子家庭结构遭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原有稳定和谐的封建家庭关系受到破坏,这种家庭不再是工农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新社会”的子细胞,而表现为一种没落乃至僵死的状态。这根源来自父亲形象的猥琐不堪与子辈对父亲权威的置疑,将子辈对父亲的反抗引申为对家的反抗,以及对庇护着那个家的社会制度的反抗。使得这种“家”与即将建立的“国”之间不再是统一的关系,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如果将稍早于《狂流》上映的《人道》作为对比参照,便更能看出其中的意旨所在。
由金擎宇编剧,卜万苍导演,“联华”一厂出品的《人道》(1932)塑造了一个集慈祥、敦厚、牺牲等所有美德于一身的父亲。他爱子心切,愿“出其历年积蓄,送儿登程”,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生活,他含辛茹苦,忍受清贫。即使面临“天灾”,入不敷出,但他仍然“不敢告民杰(儿子),恐其焦急而损其学业也”⑤。直至最后饿死。他的教子成名、舍己为子的精神,宣告了他对整个封建伦理秩序与宗法制度的维护与坚守,民杰最后的回家长跪,是对他父亲这一精神的呼应与延续。他对家的回归与认可揭示了他对整个社会制度的认可,对国民党统治政府下的国家的认可。无怪乎,影片受到“大官僚许世英、熊希龄等人的支持与称许,为其向南京政府‘教育部’申请‘嘉奖’。”⑥左翼人士则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⑦。夏衍的《狂流》正是用具体的实践,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对《人道》中的价值观进行颠覆与消解。
两个父亲形象,一猥琐一高尚,两个子女一逆家一归家,以父喻家,以家拟国,从而形成了两种完全对抗的思想,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一方试图通过慈祥仁爱、乐于牺牲奉献的父亲来教导子女,感化子女,最终让在外贪图享受、奢靡淫乐的子女迷途知返,重回家庭,以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实现家国同构的理想。被冠以在“反动派阴谋操纵下拍出的反动影片”之名的《妇道》(1934)《重婚》(1934)《天伦》(1935)等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一叙事模式,这是国民政府借用电影这一话语机制实现对父亲权威的建构,以此树立国家威信的策略。与此相对的左翼人士,则试图塑造顽固保守、自私虚伪、蛮横专制的父亲,让子女对其进行坚决的抵抗与背叛,直至离开这个被父权布满阴霾的家,将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家庭的决裂等同起来,用逆家离家的方式,宣扬子一辈对现存制度与国家形态的不满,破除国民党政府借此实现的家国同构的理想,让“家”与子辈努力的新目标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实现子辈在精神上的“弑父”过程。这样的叙事模式中,“父亲身上的阶级性或政治本质常常遮蔽了形象本身的‘父性’,‘弑父’与‘反弑父’的冲突因此也演变成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弑父的实现更多的是凭借政治批判来完成的。”⑧由田汉编剧的《母性之光》(1933)、史东山编导的《人之初》(1935)均采用了通过生父与养父的身份来代表两种阶级的叙事方式,生父无一例外都是指涉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者/工人,而养父均是虚伪奸猾、心狠手辣的资产阶级代表,从而借用“父亲”的形象,达到阶级对立的政治批判目的。
类似的,以“父亲”形象作为阶级属性的划归还体现在夏衍的剧作《时代的儿女》(1933)(与郑伯奇、阿英参与合作)和《自由神》(1935)中。《时代的儿女》中的父亲不惜以装病欺骗儿子归家,试图用软硬兼施的举措让专制的父权再次发挥效力,以掌控儿子的婚姻与人生,沿袭其惯有的支配权力。但这并不是建立在爱子心切的基础之上,他的一句:“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也能背信吗!”⑨明显看出,其真实目的只不过是维护自己作为家长的自尊与社会上的地位。在《自由神》中,夏衍同样从这个层面来考量父亲。比《时代的儿女》中装病骗儿子归家的父亲更为过激的是,《自由神》中的父亲直接到女儿学校来“抓”她回去,一场父女的冲突通过话剧的形式展现了出来,父亲的一句:“我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要顾面子的!”⑩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两部影片中的父亲并不顾及子女的真实需要,而是都不约而同地从“我们这样的人”出发,确立自己的阶级属性与地位,以期将子女拉回他们沾沾自喜的阶级范围中,使他们获得优越的身份归属感。而这是夏衍坚决抵制与打击的,他对这种父辈们的期望予以无情的奚落与嘲讽,表现在他让子辈们的反抗意识与决心比《狂流》中的秀娟更具彻底性。如果说《狂流》中最后秀娟与铁生一起抗击洪流,只是隐晦地暗示地主阶级小姐与农民阶级的“合流”,那么,他在《时代的儿女》与《自由神》中则直接通过子辈进入工厂、投入革命的人生选择,对父辈试图延续他们基业,找回他们的阶级优势的想法给以致命的一击。子辈们用自己的行动,使得父辈们竭力维护的神圣、权威、尊严轰然倒塌,变为一堆废墟,他们再也难以维持“家”的体面,再也无法在现有的“国”的庇护中尽享生活的富足与晚年的安宁。
这是夏衍通过“逆子”颠覆父权的方式反思“家”与“国”问题的独特思考。除了这个角度,夏衍在《风雨江南》(1949)中还用讽刺喜剧的方式塑造了将“子”作为最后筹码,以维护风雨飘摇的小家的父亲形象。面对新的国家形态的对已有家园的冲击,这些“护家运动”的父亲们做着垂死的挣扎,企图以欢迎的姿态接受新国家政权的领导阶层,做着“旧家”与“新国”同构的美梦。两个地主恶霸父亲,无论是争抢着牺牲女儿的幸福来换得与新政权的融合,还是竭尽全力地将曾经他们任意凌辱的“下人”认作干女儿,都体现了他们内心的轻薄、丑陋与恐慌。其上演的一幕幕可笑的努力终归化入历史的烟雾中,成为新中国来临之前的典型祭品。至此,夏衍用“逆子”叛家、颠覆父权、丑化父亲的形式打破了自古以来延续的家国同构的传统。但有国才有家,有家必有国,打破了旧的家国同构传统,就意味着必须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重新将家国同构的传统捡拾起来,他又是怎样使“家”“国”开始新的同构呢?
二、父亲的缺席与置换:家国同构的重建
如果说夏衍在电影中,用阶级分析的立场,塑造冥顽不化、贪婪自私的地主阶级父亲形象,是对传统中“家国同构”思想的打破,那么,他将传统家庭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父亲角色抹掉,让父亲缺席,形成苦儿弱母/无父无母型的叙事模式,则是他建立新型“家国同构关系”的策略性选择。《上海二十四小时》中(1933)受伤的童工没有父母;《脂粉市场》(1933)在开端就让承担父亲义务的哥哥丧命,翠芬只有寡嫂和病母;《风云儿女》(1935)中的阿凤也只能和弱母在困窘的生活中相依为伴;《压岁钱》中的父亲甚至在吃团圆饭的除夕之夜也不在场;《人民的巨掌》(1951)中主人公的家庭组合模式也是兄妹加母亲;《祝福》(1956)中也只有祥林嫂和婆婆、小叔进入到叙事机制中。
毫无疑问,夏衍电影中父亲的缺席,与他年少失怙不无关系,他3岁时,其父因为中风突然逝世,只能靠母亲独自一人担负起抚养六个孩子的重担。他过早地尝试了寡母育子的困顿与艰辛,成为他日后在电影中创作苦难家庭的心理动因。进而可以揣测,夏衍实际上是通过想象性来填补父亲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用虚幻性来界定他对父亲形象的态度。在他这里,父亲的形象已沦为一种指涉性的文化符码,用来诠释他的文艺观念,实现他“打进资本家的电影公司”中宣传政治思想的目的。一是,他把父亲的身份定位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父亲们让家庭中充满了腐朽的气味与没落的因子,他们是即将僵死的一代,借用子一代对他们的抵制与对抗,来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启蒙主题,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任务,为新的政党、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政权成立张本。在这类电影中,基本上遵循着弑父——离家——建国的叙事逻辑。用子女反抗父亲,离开腐朽之家,投向工农阶层的形式实现了他对现有国家体制的置疑。一是,他侧重在无父的家庭中,展现苦女弱母现实的苦难遭遇与生存的困境。作为雄悍有力、独当一面,充当家庭顶梁柱角色的父亲不再到位,由父母、子女这两个最基本的成员组成的家庭格局不复存在。夏衍正是用这种残缺不全的家庭模式,来揭示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对个体及家庭所造成的双重戕害。其中深刻的内涵在于,用“家”的残缺指涉着“国”的破败,用家人的痛苦寓指着民族的危难。这类电影的叙事策略就此可见端倪,即遵循着缺父——家苦——国难的逻辑,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大众以现实的警醒,为青年人的何去何从指明前进的方向。
这里就涉及青年人关于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他们的道路选择直接显示了夏衍关于家国同构重建的努力。老一辈的父亲或者是顽固保守的化身,成为僵死的朽木,或者羸弱不堪,成为“无能的承担者”与“无力的抵抗者”或者干脆缺席,退出家庭的日常生活视野,子一辈再也无法因袭父一辈的道路,只能在孤独、迷惘的求索中寻找新的道路、融入新的集体中。“个体生命的寻找、追求之路,如果不想遭到历史的无情放逐,就必定要融合于阶级/集体/革命队伍中,就必定要献身于革命/党的事业。”而怎样很快融入队伍当中,踏上革命的征程,就需要领路人的指引,这里的引路人往往是首先往前冲的子一代自己建立起来的。李道新称这种现象为“父子角色倒换”,他指出:“无家或弃家的选择,失父或弑父的结果,使子一代逐渐树立起了自身作为父亲的威信和尊严。”在夏衍的电影中,这种由子一代“化身”的知识分子/革命者,置换了本该是“父亲”承担的角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责任功能,对比自己弱小的同辈进行扶持与帮助,自觉地将本该是父亲应尽的义务承担起来。另一方面是作为革命者或英雄人物,真正的身份只有一个,即为建立新的“国”而疲于奔命,全然不顾自己的“家”,永远置换掉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普通“父亲”的身份,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战斗英雄,指引着同一辈与新一辈的努力方向。
就前者而言,最明显的体现在电影《风云儿女》中,这是一个关乎子一辈在战争的环境中陷入困境、迷惘、挣扎,最后找到新方向的故事。在这样一个故事模型中,贫苦女子阿凤因为父亲“一生的事业跟生命,都在‘一·二八’毁了”,与母亲流落在上海,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之中。青年知识分子辛白华与梁质夫起初替他们母女交房租,只是显示出强者对弱者投以的人道主义式同情。及至阿凤的母亲病逝,使辛、梁二人直接由旁观式的同情者转化为阿凤的庇护者,将阿凤收纳在他们二人构筑的“小家”中,如果说只是出于一种同辈之间的友谊,那么,辛梁二人为阿凤日后是进学校读书还是做工的争论,则与普通家庭中父母为子女未来前途的争论构成一种潜在的对位关系。无疑,阿凤在这个“家庭”中找回了本该享有的权利,她不再为紧逼的房租,病弱的母亲而愁眉苦脸。相反,她也和其他女孩一样“穿上朴素大方的学生装”去上学了。实际上,辛白华不仅巧妙地移植了阿凤“父亲”的义务,他还以一个知识者的身份对阿凤进行启蒙。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被启蒙与整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辛白华通过让阿凤接受教育,以成长为“一只新凤”,将新的家国同构梦想变成了的可能。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与局限,使得他的行动方向渐趋游移。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阶层时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在辛白华身上正显示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面对梁质夫的被捕,他选择了逃避在史夫人的温柔富贵乡里,直到又重新遇上了阿凤。被救助、被启蒙的阿凤如今真正成长为“一只新凤”,反转为辛白华的启蒙者,就此,二人的精神世界开始走向趋同。辛白华对阿凤曾有的“父性”责任瞬间瓦解,化解为同辈式的友谊,他们一起为保护共有的“家”,走向了救助民族危难的战场,新的家国同构由此得以完成。
与《风云儿女》中假想式的“父对女”承担的义务相反的是,《革命家庭》(1961)中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父亲”,却因革命的需要而舍弃了家庭的需要。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已不复存在,母亲一个人将孩子抚养长大,父亲成为家庭中存在的缺席。以“父亲”身份存在的他,只是“父之名”的占有者,在绝对意义上,他已上升为共产党人与革命英雄的指称。在他这里,“‘小家’固有的血缘亲情、人伦关系,也被投射、放大至‘革命同志’及革命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即使偶尔出现一家人团聚的局面,作为父亲的他不是给妻子剪头发,让她变得也“革命一点”;就是把家当成革命的战场,让妻子成为放哨、望风的战士,儿子当起送情报的交通。他最后的英勇就义,不仅诠释了共产党人死而后已的精神境界,而且在前赴后继的意义上,为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了一个空位。这个普通的家庭至此置换为党的家庭/革命的家庭,被共产党的代言人称之为“也就是我们的家庭,党会照顾你们……”共产党集体对他们家庭的接纳、认可、“照顾”,实质上延续的是父亲的使命。影片正是采用这样的叙事策略,巧妙地将个人与集体统一起来。在父亲/革命者的相互置换中,“将其置于共产党/国民党、善/恶王国争夺的价值客体”之上。而这种叙事诡计依然是个人实现家国同构理想的有效途径。
三、历史视域中的父亲:家国同构如何可能?
当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凋敝、残破的老中国面临崩溃的边缘,由共产党领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时,夏衍试图通过电影,对自己及战友所走过的路途进行历史性的回瞻与反刍。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时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时代”诞生于1949年的《恋爱之道》与1959年的《林家铺子》正是在新中国的两个重要节点上,夏衍开始对历史进行重读与对话。《恋爱之道》以抚今追昔的叙事技法,将当下现状与历史景观拼贴起来。被述的年代从1925年大革命即将成为席卷之势开始,到大革命惨败,到1928年国民党吞并革命果实、劫夺政权,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后,再回到当下而结束(即蒋家王朝溃败,新中国宣告成立)。影片在对这段历史的回溯中,自然延宕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物及特定事件的意义。《林家铺子》同样以忆苦思甜的方式将当下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一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三十年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中。”以一个限定在“九·一八”“一·二八”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衰败故事,来回馈新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景观。影片的真正价值因此不言之明地陷入政治的潜意识范本中。本部分着力从夏衍对历史事件的重述中,窥看“父与女”的微妙关系,从中得以表明“历史之父”所背负的沉重负荷以及夏衍本人在实现家国同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扰。
《恋爱之道》可以说是夏衍唯一的一部将父女之情处理得温馨动人的影片:
(女)元珍:“咦,爸爸,你看我同你一样高了!”
(父)家浩:“嘿嘿,你还差一点儿吧!”
元珍站到路基上:“瞧,比你还高!”
他们绕过小山坡。
元珍:“爸爸,我又收到了新歌曲了。”
家浩:“好哇!什么歌曲呀?”
元珍:“叫《垦春泥》。”
家浩:“好听吗?”
元珍:“很好听的。”
家浩:“噢?回头唱给我听啊!”
用这么精致、细腻的笔墨描述父女之间的对话,在夏衍这里还是唯一一次,了了的几句对话,就真切地传达了父女之间所流淌的脉脉温情。为后文父亲在正义与女儿之间的痛苦抉择埋下了伏笔。女儿的急性肺炎需要大剑黄才能救治,而有大剑黄的只有奸商张鸿昌。这意味着救治女儿的前提必须以满足奸商运送私货的要求,将难民与国家利益弃置不顾。自然,爱女心切又正义凛然的周家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小家”的幸福与“大国”的危难之间他做着困兽之斗。按照一般影片的叙事路数,本该是既能让主人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得以传承,同时也让“英模人物”的女儿保全性命,最终得到幸福的馈赠。然而,影片将故事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危难当头)注定不会延续普通影片的叙事逻辑,周家浩女儿的性命得以保全,而“大国”的利益却受到了重创,张鸿昌一行盗取了火车,实现了邪恶的目的。周家浩的维持正义、“护家(表现为护女)又卫国”的梦想破裂,一腔英雄的热血顿时化为虚无。怎样才能让自己“小家”得以完美幸福,又能以正直、勇武的身份成为“国”的战斗英雄,让那段屈辱“丧国”的历史不再复演,成为这个以过去完成进行时写就的剧作的考虑重点。即通过支持女儿选择工人阶级出身的小王,而不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小陈,从而巧妙地使个人“小家”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大“国”得以有机融合。曾有论者指出:“这里既有对于过去的概括,也有对于未来的启示。”而站在时代的潮流中追述历史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苦难的历史让父亲无法安顿他的“家国梦想”,只有在国家权力转换的前提之下,这一梦想才得以实现。
相比于《恋爱之道》中温馨感人的父女之情,《林家铺子》中的父女之情处理得较为节制、含蓄。夏衍结合时代语境,改变了茅盾原作中林老板的性格,着意突出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见着豺狼,他是绵羊;见着绵羊,他是野狗。”这点两面性,也从他作为父亲,对女儿的态度上体现出来。一方面,他毫不在意女儿的情感变化,“发觉她有点不正常”,也只是“斜看一眼”,不作任何关心的表示。女儿在学校被指责穿东洋货,满心委屈,他却淡定地说:“干脆不要念书了……”他更多的身份是个冷酷自私的店铺老板,而不是具有人伦之情的父亲。但另一方面,当他的女儿被国民党官僚打主意时,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反抗与抵制。他的最后携女逃跑与其说是宣告“林家铺子”的破产,不如说是他作为“父性”的回归。夏衍正是通过展示这个店铺老板的人性、父性的复杂多样性来窥看一个铺子/家庭的风云变幻史,借此“使正在改造中的资本家回想一下过去,使他们了解,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这其实是夏衍通过揭开掩藏在历史迷雾之中的“小家”的伤疤,让当下的资本家踊跃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改造中来,指引他们实现家国合一的有效性途径。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影片,影片再次成为改编名著的经典,上映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得到一致的赞扬一致的好评”。
然而,时隔五、六年后,赞扬之声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林家铺子》成为众矢之的,由江青策划的关于《林家铺子》的批判文章多达“一百四十多篇”。电影《林家铺子》成为“丑化工人形象”“宣扬奴才哲学”“美化资产阶级的”“歪曲时代风貌”等等的范本,其矛头、火力直指影片的创作人员,而夏衍自然成为“罪魁祸首”。于1965年初,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他彻底背上了“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的罪名。一心将党的事业、共和国的建设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夏衍,却被逐出了“理想之门”,家国同构的梦想陷入断裂。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夏衍才以合理、合法的身份重回共和国的怀抱中。当有人提及,要夏衍将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四人帮”的罪行写出来时,他拒绝了,理由是不想让“国耻”被外国人笑话。在他眼里,国家形象已经与自己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得失、家庭的荣辱全赖于国家的兴旺繁荣的程度。家国同构的思想早已成为支撑他奋斗的不竭动力,直至终老。
【注释】
①⑧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M].长沙:岳麓书社,2005:74,128.
②陈犀禾.从International到National——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和文化建构[J].当代电影,2005(5):8.
③⑥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204,191.
④[德]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
⑤郑培为、刘桂清编选.中国无声电影剧本选下卷[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2309.
⑦具体参见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中第192页中的相关论述。
⑨夏衍.时代的儿女[A].夏衍电影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84.
⑩夏衍.自由神[A].程季华主编.夏衍电影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335.
王侠,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