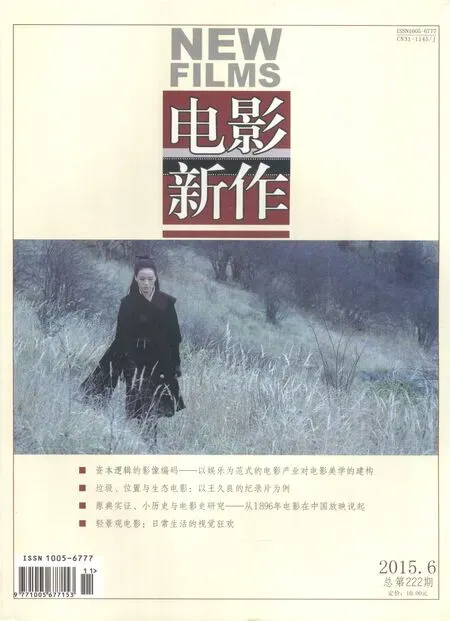垃圾、位置与生态电影:以王久良的纪录片为例
龚浩敏
垃圾、位置与生态电影:以王久良的纪录片为例
龚浩敏
王久良的生态纪录片《垃圾围城》探讨了垃圾这个问题和话语之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消费主义社会的生态意义。笔者以垃圾话语中位置这个议题为中心,解析当代城市化、商品化、消费化如何定义垃圾的地理位置并构建它的社会位置。在当代中国,垃圾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人们选择忽视却无可逃避的环境危机,也映照出构成该危机的当代社会与文化情境。
王久良垃圾围城生态电影位置性消费主义城市化
“污秽乃失位之物。”(Dirt is matter out of place.)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1694-1773)
“我也认为,所有的废物是存在于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的东西……”
——迪尔洪恩子爵《格莱格森报告》(1981)①
“垃圾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王久良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洁净与危险》(1966)一书中,引用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上述名言,阐释了“污秽”的社会性构建——即,任何事物并非天生肮脏,之所以“成为”污秽,是由于它被置于不属于它的位置,如“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②道格拉斯认为,切斯特菲尔德的上述名言“暗示了两个情境: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③进而言之,无论是对污秽的进行归类的有效机制,还是对这种归类机制的挑战,都是由人们彼时所处的社会组织和系统所规定的,都是某种社会性的行为和过程。苏珊·斯特拉瑟也言:“垃圾是由分类所产生的。”④
在此,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对事物进行归类的过程(同时也是某些事物溢出其类别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赋予事物特定秩序中其位置的过程,不仅是我们整合外部世界的过程,也同时是我们整合自我和内心的过程;也就是说,这既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性的过程。诚如美国著名生态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所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⑤可以说,生态问题根本上是我们文化的问题。
本文将以垃圾的“位置性”问题为出发点,以王久良的生态纪录片《垃圾围城》为例,来探讨垃圾这个问题和话语之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消费主义社会的生态意义。具体而言,笔者将围绕垃圾话语中的“位置”这个议题,解析影片在叙述、影像、象征等诸多层面上,是如何展开对垃圾所造成的生态问题的揭露与思考。笔者提出,垃圾作为一个生态问题和社会性的现代性话语,是当代城市化、商品化、消费化的产物。后者不仅定义了垃圾的地理位置,更构建了它的社会位置。在当代中国,垃圾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人们选择忽视却无可逃避的环境危机,也映照出构成该危机的当代社会与文化情境。

一、《垃圾围城》的位置
《垃圾围城》是生活在北京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于2008年10月至2010年期间,历时两年、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对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大大小小的垃圾场进行实地调查过程中所拍摄的一部系列摄影作品和纪录片⑥。作品以强烈的纪实性手法,记录了北京的城市生活、建筑和食品垃圾的粗放型处理过程以及其背后许多鲜为人知却触目惊心的真相,展现了现行的垃圾处理机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以及对城市和依附城市的人们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如评论家李楠在谈到《垃圾围城》摄影作品时所言,这部作品“不仅解剖了京城繁华文明之下鲜为人知的垃圾部落之隐秘生存法门及其利益链条的重重勾结,由此辐射到环境污染的全球性问题;更可贵的是,它还显示了当下毫无背景的民间独立摄影师在商业文明和消费至上时代坚守的专业品格和揭示问题的能力。”⑦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家以《垃圾围城》摄影作品在2009年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获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以及2010年色影无忌年度摄影师大奖。
其实,《垃圾围城》中所揭露的北京的垃圾处理问题,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也正在同样地面临着,而且有些地方的境况尤过之而无不及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垃圾围城”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评论家对《垃圾围城》不吝赞誉与评论,在此不赘。本文中,笔者希望另辟“位置”这一视角,来考察作品中垃圾作为一个“话语”所传达出的生态意义。之所以选择“位置”这一批评的角度,是因为如众多学者所指出,在生态意义上,垃圾之为垃圾,并不仅仅在于某事物其物质层面上的功能性的消亡,而更在于其社会位置的丧失。诚如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所言:“在社会状态下,每一件物品,必须存在于一个功能性的语法链条中。也就是说,物一旦没有恰当的社会功效,一旦在社会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它就可能在垃圾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物的社会进程被中断了,才转化为垃圾。”⑨因此,对垃圾的社会位置(或失位)问题的关注,迫使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生态环境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层面上关注和理解垃圾问题,而且更让我们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探索垃圾是如何为我们的城市化、商品化和消费化社会所构建、如何深远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态。
于笔者而言,影片的整个叙述显示出极强的位置感。首先,影片“围城”的主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空间感的意象,且这一主题在影片的开始与结尾处,以具体的视觉图像进行了空间展示:在这两处,北京周边或显或隐的大小垃圾场,以带有警告色彩的亮黄色在北京城暗灰色谷歌地图上以大举围城之势一路标举出来,如同一道恶毒的箍咒扼住一个肆意膨胀的幽灵。
其次,影片中每一个记录片段,每一处场景的更换,均以精确至分秒的经纬度数和具体方位表明,给观众以强烈的空间感和现实感的提示。具体且精确的位置,是构成该纪录片冰冷的现实感与现实的残酷感的基本要素。导演似乎在不断地提醒着我们,画面中的人和事是在我们共同居住的同一个地球上的某一处曾经确然存在过和发生过的。这种具有冲击性效果的真实感,确是生态电影对现实介入和激发行动的政治使命所不可或缺的。
进而,如果我们将影片的这种精确的现实感,联系至博尔赫斯小说《关于科学的精确性》中“精确至极”以至失去意义的地图,我们更可看见影片对现代垃圾话语构成的质疑之可能性。齐格蒙·鲍曼将小说中地图遭弃,阐释为其未被理性“鉴别”——即未能有效地存留“有用”的部分而摒弃“垃圾”,因此遭遇认知,特别是现代性认知困境的结果⑩。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建立,是基于其对“有用之物”与“垃圾”的“有效”划分之上的,而这一过程也正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构建的过程。那么,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将王久良类似极尽精确地标识地理位置的举动,视为对鉴别“有用”与“垃圾”的现代理性构建过程的一种质疑?换而言之,如果《垃圾围城》中惊人的现实感与精确度可视为对所谓现代“理性”区分行为的反动,那么现代理性框架内构建“垃圾”的过程将需要重新进行反思。
影片在叙述层面上的位置感,似乎在提示着我们“位置”之于垃圾的某种特殊意义。在下文中,笔者将就城市化与商品化/消费化这两个当代中国主要的社会话语中垃圾的位置性问题展开讨论,力图揭示垃圾的位置如何映射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位置。
二、“不是垃圾围城,是城市包围垃圾”:城市化与垃圾的位置
《垃圾围城》首先将垃圾与当今中国高速的城市化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诚然,垃圾的出现并不始于城市化,城市化之前,人类就生产过垃圾;但是如法国生态专家卡特琳·德·西尔吉所指出,正是城市化的发展阻断了前城市化时期垃圾的自然生态的循环。前城市化阶段,垃圾基本上被大自然所消化掉,然而城市化进程使得这一过程变得不再可能。或许我们可以说,在社会学意义上,前城市化的“垃圾”算不上真正的垃圾,而称为“功能失效品”或更为准确,因为那时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其自身的位置,让它们通过循环重新回到自然中去。而城市空间的发展却没能为功能失效品提供类似自然界可供其循环的位置。因此,如汪民安所言,“垃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自身制造出来的,是城市排斥性的硬朗表层结构所创造出来的。”
然而,城市地表排斥功能失效品进入自然循环体系,却并不意味着后者就立刻成为垃圾。人们在创造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同时创造了符合城市生活特点的垃圾处理方式,如垃圾的分类、收集、转运、回收、分解、填埋、焚烧等等。这些处理方式正是将前城市化的自然循环转化为城市化的人工循环的努力。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这种努力也是一种赋予功能失效品以其位置的行为。然而,现实生活中,这些努力因为种种原因往往未能达到其效果,使得功能失效品失去其社会位置而成为真正的垃圾。这时,垃圾不仅仅成为一个生态问题,更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因为它表征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对于生态和自我的认识中的盲点和偏见;而这正是导演介入垃圾问题的一个路径。
在《垃圾围城》中,导演将功能失效品垃圾化的根源指向了我们商品化的社会,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作详细的分析。在这里,笔者将集中分析体现在“围城”这一影片的中心主题和意象中的垃圾与城市化关系中的位置性问题。
汪民安在分析了中国城市由前现代时期以城墙与护城河为边界、转变为现代以垃圾场为边界的过程,感叹“垃圾在安排城市的结构。”诚然,城市生产垃圾,然而垃圾却“定义”着城市。在此,笔者是在“划定边界”这一词源学意义上使用“定义”一词的;然而“垃圾定义城市”却不仅仅是从空间位置的角度来呈现垃圾围城这一略显诡异的意象,更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社会垃圾化的问题。这一反思与“文明”“教化”等垃圾的对立面相关,但更重要的是指向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发展主义的历史冲动。
影片中,“围城”与城市的疯狂扩张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一方面城市的高速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空间,因而以摊大饼的方式向四周急遽扩展;而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扩张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垃圾则需要更多更大更远的垃圾场来消化,而这些垃圾场的存在却束缚着城市扩展的脚步。影片中导演所展现的建筑材料与建筑垃圾同处一地的吊诡场景,极具张力地反映出这种历史的反讽——发展的冲动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建造与摧毁仓皇却必然地同台上演,激烈却命定地争夺着同一空间。
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主义的力比多与其排泄物构成了一种纠结的反讽:愈是高速的发展,愈会带来更多的垃圾,从而也愈将束缚发展的空间。于是,人们便选择草草掩埋垃圾,且匆匆于此之上将各类建筑拔地而起,以地面之上的高耸之体量,来彰显发展主义的男性特质之雄伟,且将不愿视之的污秽之物,自欺欺人地掩盖于地面之下,似乎无可争辩且一劳永逸地完成了一次宏大架构对卑贱之物的征服。
在这里,带有强烈线性发展目的论的发展主义观,显然与生态主义的循环论调格格不入。或者说,发展主义正是在对循环观的压制过程中,才得以确立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然而,吊诡的是,这被掩埋的卑贱物,如茱莉亚·克莉斯蒂娃所言,在边缘和阈界之处,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其自身的存在,如同一道幽灵以各种形式时时回到我们身边,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饮用的水中、食用的蔬菜、牛奶和肉制品中。这道幽灵提醒着我们整饬之外的不洁,或者说是整饬之“内”的不洁,因为我们所见之整饬正是基于对不洁的掩盖和压抑,这让我们常常不安。
如此,垃圾包围城市,是以城市定义垃圾为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国际先驱导报》中所说的“不是垃圾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包围垃圾”。正是我们过度的城市化进程让功能失效品找不到其位置而成为垃圾,强迫循环的生态逻辑服从线性的发展逻辑,用自欺欺人的掩盖成就发展主义的神话。然而,就如任何定义一样,被定义者总会在不经意时溢出边界,提醒着定义者,无论定义的权力多么巨大,都无法使被定义者完全顺服。
从“垃圾围城”到“城围垃圾”,这个主客体的位移让我们认识到城市并非只生态问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生态问题的制造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推动城市化的人和社会制造了生态问题,如导演王久良追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吗?”

三、“垃圾是商品的尸体”?消费社会中商品的失位
在影片的结尾处,导演采访了几位拾荒女,她们用垃圾场的废旧材料就地搭建起简陋的房屋,一住就是十多年;身上穿的,里里外外,全都是从垃圾中捡来的;甚至连有些吃的东西都是捡来的。其中一位说,她捡的这些衣服都是住在高档小区的有钱人丢的,“有时候捡的一包一包都是崭新的。”言语之外,一种复杂的感情难以掩饰。当然,这种不负责任的消费方式在当今中国并非社会常态;然而,该现象的出现显然已向我们表明,垃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量的涌现,与我们当代日益加速发展的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垃圾与商品消费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汪民安在他对中国商品社会的垃圾问题的研究中提出这样一个初步论断:即商品“一旦功能枯竭,它就会以垃圾的形式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垃圾正是商品的残余物,是商品的尸体。”这一论断将垃圾置于商品的对立面,从一个人们往往忽视,或不愿直视的角度映照这个社会的面目:“商品总是被展示,而垃圾总是被掩盖”;“现代商场是物的盛世王国,而垃圾山则是这个盛世王国的倒影。超级商场和垃圾山,这是现代城市的两个极端,它们在城市内外遥相呼应……商品的王国和垃圾的王国在城市内外的并置,是现代都市的奇观之一。”在这里,垃圾是城市商品经济景观的一个镜像,以其挥之不去的不堪,倒映着后者金玉其外的整饬。正如影片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所示:被垃圾充斥的温榆河水面倒映出一架掠过其上空的飞机。或许如作者所说,我们可以“从垃圾的角度来写一部人类活动的历史。”
然而,如果仅仅将垃圾视为商品功能性消失后的存在形态,将它们以先后顺序置于时间之轴,将不免落入一种功能性和物质性的迷思,而忽视了垃圾的社会性构建之维。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垃圾显然不仅仅是商品功能消亡后的产物。斯特拉瑟已向我们展示垃圾与物品的功能并无直接联系:有些物品的功能性已然消亡,却被保留、修补或者功能转换而没有成为垃圾,而有些物品其功能性尚存却被遗弃为垃圾——这与社会和文化有关。可以说,深刻影响着今天垃圾之于人类的意义的社会文化,是当今几乎渗透至世界每个角落的全球消费性社会文化。如果说城市化进程让物品在其功能失效后失去其位置而成为垃圾,那么消费化社会则更让商品在其功能尚未(完全)失效时便失去其位置,过早地沦为垃圾。而这一过程进一步地表明,垃圾与其是否有用无关,而是由其社会位置的丧失所决定的。
《垃圾围城》中,垃圾的位置性之于商品消费社会,至少在两个互为表里、相互交织的方面有着重要的体现:即(一)垃圾和自然在商品消费社会中的位置;(二)人在垃圾话语中的位置。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着重探讨第一方面。
首先,商品生产是垃圾大量产生的一个物质性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商品”生产改变了垃圾之于人类和自然的意义,如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生产有别于一般物品的生产,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品的社会性质,从而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如笔者在下面所要分析的,也深刻地影响了人与垃圾的关系。或许意识到这一点,在当代垃圾话语的讨论中,无论是从功能性还是社会性的角度,批评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垃圾置于“商品”的政治经济话语之内考察,或视垃圾为商品的对立镜像,或视其为商品经济体系的建构;而生态电影,如史蒂芬·拉斯特与萨尔玛·莫纳尼所指出,其一核心理念便在于对商品经济和消费社会的介入和反抗。
商品的生产,其核心逻辑是以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将人类劳动抽象为劳动力,视人类具体劳动产品为可自由交换的等价物,由此异化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当人仅仅视物为可用一般等价物(金钱)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商品,从而遮蔽了人类具体劳动与其具体的劳动成果之间的特有关系的时候,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便失去了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因此,人类在占有与遗弃它们的时候,便没有了类似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光晕”(aura)的体验,这是垃圾大量产生的条件之一。如斯特拉瑟为我们所描述的,保存、修补功能失效品,即使得物品继续保留其社会位置的人,往往对物品怀有某种特殊的理解与亲密之情。换而言之,当人们建立和恢复对物品的具体独特而非抽象宽泛的关系时,物品才能得以更持久地保持其社会位置,不至于沦为垃圾。而商品社会不可避免地摧毁着这种关系,以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构成商品物化体系与拜物教的基本价值观;然而吊诡的是,拜物的结果是加速了对物的遗弃。
其次,商品社会中垃圾作为“无价值之物”是基于其交换价值的失位而非使用价值的丧失。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讨论必然指向事物的价值问题。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区分出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一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普世的、经典的价值,即“真”“善”“美”(对应文化价值中的认知、美学、伦理这三方面);二是那些“轻俏而无实质”的东西,它们“媒介(mediate)那些无法自我呈现的差异”,使我们观察到交换中的劳动与商品间的联系。换句话说,第一种价值体现事物所拥有的内在特性(尽管它也必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得着体现),而第二种价值则对应我们所说的交换价值:事物被置于一个交换的示意链(signification)中,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于可交换的与他者的不同之处。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在于它能与他者交换,那么垃圾则是跌出示意链、失去其位置的“无价值”之物。可见,商品社会中,垃圾之所谓“无价值”,并非是没有用,而是不能交换;并非其经典意义上的内在价值的丧失,而是因为不再拥有市场这一具有“神奇魔力”空间中的位置而被遗弃。
第三,对于自然世界来说,其“生态价值”也同样为商品社会所定义。垃圾对于自然生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片从头至尾所展现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图景已然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从垃圾所在的商品社会的内在逻辑来看,那些触目惊心的图景背后的社会机制则更让人深思。商品社会不可避免地将也大自然纳入其无处不在的商品生产方式之中,也就是尼尔·史密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自然生产”(capitalist production of nature)。商品社会中的自然生产将自然作为一种可交换的资源,同样以一般等价物的金钱来衡量其价值,而无视其作为非交换物的独特价值。大卫·哈维指出,这种商品社会对自然世界的价值衡量不仅是因为金钱是我们现今所拥有的普适性的衡量标准,更是因为金钱是社会权力的体现。以金钱作为衡量自然世界价值的标准,不仅会庸俗化自然世界,更是会对自然世界造成直接伤害。影片中有一段俯拍隐藏在北京市郊山区中采石场的鸟瞰镜头,其中呈现出的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裸露的矿坑,有如在大山青翠丰盈的肌体上剜出的道道痕迹,令人无法释怀。
而当那些已然失去价值的垃圾也被金钱化,其后果则更是触目惊心。那些包围北京城的四五百座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垃圾填埋场和倾倒场地,承载着北京一千三百多万人口每天所产生的三万多吨垃圾,而这些垃圾大多都缺乏分拣和无害化处理,如某处理厂工作人员所介绍,他们的垃圾处理无法使他们工厂盈利;而有些非法的垃圾场更是向城市某些单位低价收购垃圾并让垃圾直接倾倒和排放,以逃避政府征收的并不太高的垃圾处理费。如此经济利益的驱动,反映出人们对于生态认识的失衡和自身心理的失衡。而更令笔者心里不安的是在影片开头在垃圾场上放羊、影片结尾处曝光的用城市餐馆收购来的泔水喂猪和提炼地沟油的场景。这样的自然“循环”只能让人看到经济利益如何让人心失去其应有的位置。
第四,更者,当商品社会发展至消费社会,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让位于让·波德里亚所说的“时尚价值”。让我们来看看波德里亚是如何解释这种“时尚价值”的:
……这种豪华的浪费、这种高尚的浪费被大众传媒推到前台,从文化上只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为根本的、更为系统的浪费,一种与物质财富同时由生产产生出来的、也纳入其中的、必须作为消费品的质量之一的功能的、官僚主义的浪费而消费掉:易碎、陈旧、时间的确定、昙花一现的命运。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对有关用途、需求等的整个经济学“理性的”公诉产生怀疑。不过,人们知道生产秩序的存在,是以这种所有商品的灭绝、永久性的预有安排的“自杀”为代价的。这项活动是建立在技术“破坏”或以时尚的幌子蓄意使之陈旧的基础之上的。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惟一的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去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
波德里亚的这段叙述为上述拾荒者捡到一包包崭新的衣物的片段作出了一个有力的注脚。这些衣物之所以成为垃圾,显然并非其功能已丧失,而是它们在价值的交换示意链上过早过快地被其他时尚品所取代,从而失去其位置;而取代者亦无法逃脱同样被他者取代的命运,而这一切其实早在商品的生产阶段便已然被决定,消费社会的生产正在越来越远离使用价值。消费社会的一个悖论在于,时尚价值的意识形态使得“浪费式的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而社会的富足“在浪费中才有实际意义”。浪费,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失位,在迷眼撩人的物质海洋里,在潮去潮来时尚季风中,无可避免地垃圾化了我们的生活。
四、“垃圾最后成为政治”:商品消费社会中人的位置
浪费,即生产垃圾的“能力”,又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定义了人的等级关系与其社会位置。如斯特拉瑟所言,对事物的归类或归位根本上“是一个阶级问题:制造垃圾的行为以经济地位的不同制造并强化了社会差异。”类似于当代美国的情形,在当代中国,“有能力浪费被鼓吹为一种使人感到富有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垃圾“确定了整个体系的方向”,塑造了我们的社会。

《垃圾围城》中鲜见有制造垃圾“能力”的人,他们的存在似乎更多地以代表他们的物的形式出现:海量的生活垃圾,其中包括大量的被浪费的物品、拔地而起的高层商品房以及其所产生的体量巨大的建筑垃圾、还有那代表开发商的拆迁执法人员。这些人或许不是本片的焦点,然而他们所代表的“能力”或“权力”却是制造垃圾政治的源头。
影片更多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群群没有“能力”的“垃圾人类”。他们的位置似乎和与之为伍垃圾一样,如鲍曼所言,“垃圾人类与消费盛宴的垃圾相遇的舞台已然布置完好,它们似乎是为彼此而生、彼此而造”。在鲍曼的论述中,垃圾人类是现代性的产物,他们是所谓“现代设计”中为呈现现代的光彩而必须生产出的不光彩,是经济发展而被淘汰的一部分,是全球化浪潮中被冲刷掉的废物。
垃圾人是城市版图上一个个不存在的存在,也是城市生活中看不见的一群。影片开头处垃圾工人在人群中与其他人一起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这一镜头似乎在向我们表明,在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上,他们同其他中国公民并没有不同,理应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而待仪式结束后,他们便从这城市(乃至中国)的中心悄然离开,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而最终回到他们被人们有意选择看不见的地方。
而这些垃圾工人相比于常年生活在垃圾场上的拾荒者,还是城市中尚能显影、具有一定“身份”的人;而后者则除了垃圾以外与城市毫无关系。从拾荒者位置的象征意义上来说,他们虽然从边远的老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国的首都打拼,似乎与中心更为接近,然而这种地理上的靠近却无法给他们带来社会上的接近;相反,离开了家乡暖老温贫的生活经验,来到他乡异质生冷的生活环境,虽然经济条件抑或有所改善,然而在心理上与社会上则更加疏离了原有的踏实。拾荒者往往不愿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怕被家乡的人知道他们现在干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可以说,影片中的拾荒者永远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活的边缘。如果说从商品到垃圾、从城市中心到城郊垃圾场构成了一个时空的等级链条,那么拾荒者是这个链条末端的一个存在,不被他人看得起,却补偿并构建着上端人群的体面生活。在中国,正是这千千万万的拾荒者完成了绝大部分废物分类和回收的工作,但情形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如西尔吉所言,如果在源头,即人们倾倒垃圾处对垃圾进行分解,则不仅可以减少垃圾产生的数量,还可以恢复人们的环境居民意识和与环境的和谐。但中国的现实是,分解的工作下移至填埋阶段,创造出一个与之“匹配”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别人远离和遗弃的地方建造自己的家:如影片所展示,“他们靠着垃圾场生存,在垃圾场上构建自己生活的梦想”。但即便如此,他们还常常面临被警察和其他权力机构驱赶的威胁,成为政治游戏的替罪羊,有权者合法化自身权力的道具,而沦为彻底的“看不见”的人。
影片后段着力展现拾荒者的边缘生活,其中两个片段相较于全片冷静的叙述语调显得有些动情:其一是展现拾荒者携妻挈子在垃圾场上建造自己并不舒适的家、构建自己不太奢华的梦想;一帧帧记录日常劳作、家庭温暖、渴慕未来的照片配上幽婉的背景音乐,构成影片唯一“温馨”的时刻。其二是一位隐蔽于垃圾山深处、在自己用垃圾材料精心搭建的小屋中生活的拾荒老者,某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悄然离世,孑然一身地躺在垃圾之中,完成了一生“垃圾”一般的生活。
导演如此,并非是要浪漫化作为底层的拾荒者。因为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是我们社会垃圾话语的受害者,同时在某些层面上他们也是环境问题的帮凶:他们随意处置垃圾污染环境、在垃圾场上放羊、用回收的剩菜喂猪、用污染的水种菜,客观上让污染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之中;更者,有些人利用泔水制造地沟油,买回给城中餐馆供人食用,行不法不道德之事。导演王久良承认,在拍摄(偷拍)这些段落时,他陷入了一种道德上的两难:一方面明知他们所做的这些事于理于法均不可行,而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如果将他们曝光,则会让他们的生活陷入更边缘的境地。导演在影片中没有给出他的解答,但这道德上的两难促使我们思考造成两难的原因,反思我们当今生活于其中的现代性给我们制造的种种悖论。当代的垃圾话语是现代性的一面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人类毫无节制的欲望。当无数的资源与能源因为我们一个个可有可无的需求而变成巨量的垃圾,当我们面对着垃圾的围城,面对着垃圾的吞噬,我们是否认识到:重新审视我们的消费主义已是迫在眉睫!”
五、结语
《垃圾围城》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位置”,或者说“失位”和“错位”的生态纪录片。在不经意的时候,它常常给观众带来一种错位后的反讽甚至荒诞之感,如影片中一对新人在从污染处流淌过来的温榆河畔拍摄婚纱照片,还要求抱起一只正好在身边吃草的小羊羔作为拍摄的道具,这不禁让人想起影片前段羊群大快朵颐垃圾的场景。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和新生的象征,而另一方面是污秽丑恶与死亡的隐喻,两者吊诡地相遇,构成一种强烈的讽刺的张力。如此种种的错位,指向的是我们社会的失位、文化的失位与人心的失位。
作为生态纪录片,《垃圾围城》又恰如其分地找到了自己对于社会的位置,即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介入,“我们的作品就是话语,我们是想靠作品和话语去传播我们的理念,通过作品,通过这么多劳动,去促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事情的改变。”作品完成之后,在社会上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虽然之后出现了一定的曲折,但相关部门还是迅速采取了行动,整治了影片中暴露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的介入是有效的。
最后,《垃圾围城》作为生态电影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意识,即垃圾作为一个生态问题,其位置性问题并不囿于其在地的有限的范围,而是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到生态地球村中的他人。影片中一个有意思且别有涵义的镜头是,一辆垃圾转运车的背后印着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向观众缓缓退来,它似乎在提醒着我们,这“同一个世界”不仅仅是那以光彩夺目的美好形象呈现给我们的那个世界,它同时也是那不愿被人直视人们却无法逃避的那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说,后面这个世界更让我们无可回避地联系在一起。
【注释】
①引自:Thompson, Michael. “Th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 and the Hazards of Wasteful Management.”In Hannah Bradby, ed., Dirty Words: Writings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Pollution. 2nd ed. London: Earthscan, 2009:124.
②③[英]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建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45.
⑤Worster, Donald.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7. 引自:王诺. 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 [J]. 文艺研究, 2002(3): 48-55.
⑥对垃圾问题介入的生态电影还包括David Fedele的E-Wasteland《电子垃圾场》(2012),Kunal Vohra的The Plastic Cow《塑料牛》(2013),Angela Sun的Plastic Paradise: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塑料天堂:大太平洋垃圾带》(2013)以及Philippe和Maxine Carillo的Inside the Garbage of the World《世界垃圾之中》(2014)等。
⑦Jack. 2010色影无忌年度十大摄影师揭晓[EB/ OL]. http://www.xitek.com/html/expert/award2010/ news/201012/14-56050_9.html. 2010年12月14日.
⑧例如,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在2014年底至2015年初,连续播放了以“破解垃圾围城”为主题的专题节目,报道了全国许多地方,包括湖北武汉、三峡大坝、丹江水源、四川乐山、海南海口以及东南沿海城市等垃圾污染的情况。
⑩Bauman, Zygmunt.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Cambridge: Polity, 2004. 18.
龚浩敏,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