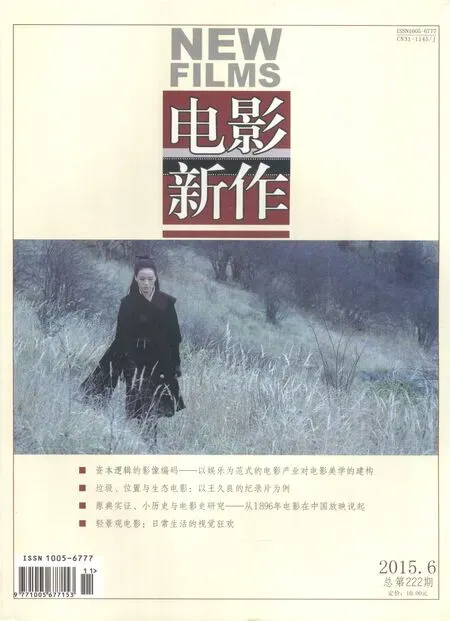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与其基本的伦理底线——以姜文导演《一步之遥》为例
张卫军 曲春景
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与其基本的伦理底线——以姜文导演《一步之遥》为例
张卫军曲春景
严肃电影批评的缺失,使当前中国电影生产中毫无伦理底线的叙事行为有越演越烈之势。叙事关乎人类的公正与尊严,电影叙事尤其如此。不受伦理规约的叙事行为,会对整个社会撒播下恶之花的种子。姜文电影《一步之遥》,借一桩并不存在的凶杀案,抛出了对电影叙事行为的思考。此故事警示我们,电影导演的叙事行为应尊重起码的伦理底线,为推高票房而选择没有伦理底线的叙述行为,不仅伤害社会文化和助推不良民风,最后也会伤害到我们自己。
电影叙事伦理底线《一步之遥》
当中国商业大片始终走不出高票房和低口碑的时候,是不是该想想我们的电影怎么了。姜文的《一步之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电影叙事应不应该有其边界和底线?或者说叙事需不需要有一定的伦理规约?再具体一点说,我们强调电影工业、强调票房,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能调动观影热情推高票房,电影导演作为影片的主要叙事人,使用什么样的叙事手段都可以?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目的正当性不能取代手段的正当性;想提高生活档次而去谋财害命显然是在犯罪。但是,在电影生产领域里,为推高票房,导演可以毫无底线地运用各种叙事手段。如近年上映的商业片中,凶杀偷窃嫖淫等展示负面行为的中近景镜头在影片中经常招摇过市,并成为电影市场特有的吸金手段,且构成一条无人能批评的潜规则。尽管电影批评在国际范围内都面临困境。但是,不择手段且无视批评的状况却是中国电影生产中的特殊现象。
这种中国特色缘起于“文革”之后,或可称“后文革”现象。30年前,因为极左思潮曾经把电影批评作为打压编剧导演的工具,“文革”后,不仅这种行为受到批判和清算,还有一些批评家为了与其对立,而采取保护编导的行为。相当一段时期,电影批评者因担心被认为有极左倾向,而不敢轻易对电影创作进行严肃正常的批评。这种风气和氛围因此导致了相反情况的发生,即有一定话语权的电影批评家,很少有人敢于大胆批评导演,很少有人敢于从正面指责其不择手段的叙事行为对社会文化造成了危害,甚至相反,还有人对此进行维护纵容,形成了电影生产与批评领域里明显的“后文革”症状。但是,已经30多年了,电影在创作机制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融资方式几乎完全进入市场化运作。影片生产及创作手段无奇不有,而严肃的电影批评,仍然被看做打压艺术创作的同义语。中国影评人对导演创作只能有肯定和表扬一种声音;除了炒作需借力点火的批评话语、或者一些影迷的口水仗之外,对电影生产很难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活动。因此,这个本来简单的逻辑,在电影生产中被人们刻意回避掉了;形成了不敢批评和不能批评的现象。特别对有点名气的导演作品,稍有批评,导演或剧组就会用大把的粗话把你砸回去①。致使近年来中国电影一直在叫座不叫好的现象中徘徊。一些导演为了推高票房在叙事中极力运用迎合观众的技巧和手法,或展示杀人细节或呈现偷盗过程或授受泡妞嫖妓技术,只要政治上不触碰敏感问题,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毫无顾忌。导演作为影像叙事的负责者,但在故事的讲述和建构中,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其讲述方法叙事手段毫无底线可言。而“后文革现象”所导致的正常电影批评的缺失,使电影产业界这种无底线叙事行为有越演越烈之势。
可喜的是,姜文导演直接用影像的形式,反思这种没有底线的叙事行为所造成的对社会对他人、最后反过来对叙事者本人所造成的伤害。在影片《一步之遥》中,主人公以生命代价抗争无良叙事的行为,提醒我们:叙事行为同人类的任何其他行为一样,都不拥有绝对的自由性。无论戏剧叙事或电影叙事,都会涉及对观众和他人的影响。影像对社会文化具有很强的形塑功能。电影叙事是一种涉及公众社会的伦理行为,应遵循其最基本的伦理约束,即使有正当的目的,其手段也不能超越基本的伦理底线。《一步之遥》用戏中戏的形式告诉我们,叙事关系到人类的道义与尊严,有其不可碰触的底线,有可为也有不可为,叙事者要为自己的叙事行为套上械具,要尊重起码的伦理底线。叙事者在叙事时必须有怵惕恻隐戒惧之心。无论编剧导演或观众,都应该对抗那些无视伦理规约和逾越叙事底线的叙事行为。
《一步之遥》通过精心设计的“戏中戏”情节,展示了主人公由最初的叙事游戏制定者到叙事游戏的受害者,再到叙事游戏的反抗者的曲折过程。这个故事寓言般的警示我们,不受规约的叙事,不仅会反噬叙事者,也会在整个社会上撒播下恶之花的种子,对社会文化产生恶劣的影响。
叙述者事先设定结局的叙事游戏:“花国大选”
该影片前面的“花国大选”是第一场大规模的“戏中戏”。长达20多分钟的主持人秀与歌舞剧表演,被许多人指责为过于冗长且没有服务于整个叙事。但如果深究这一部分的用意,可以看出它在全片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场由主持人马走日操控其叙述权的盛大“表演秀”。马走日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表演”,实际是在暗中把控着这场表演的叙事走向。同今天司空见惯的此类节目一样,这一表演秀有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结局。“花国总统”名落谁家其实早已确定,但主人公却利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营造出一个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选秀事件。即,先宣布参赛选手完颜英退出竞选,让下面的观众始料不及吃惊不已,接着是完颜英的“裸捐”,塑造出完颜英道德圣女的形象,台下观众被带入煽情的情境感动不已。之后是海外来信的“民意”引导,将完颜英的当选拔到“世界和平”的高度,直至最后水到渠成地在观众的狂热呼声中让“花国总统”桂冠落到完颜英头上。本部分将一个善于弄假成真逢场作戏、玩弄台下观众于股掌之上的叙述者和主持人形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突出展现这位叙事者如何通过讲述行为操纵观众情绪,将台下观众带入事先设定的叙事情境之中,让他们产生如痴如狂欲罢不能的观看效果。
这种声势浩繁的铺垫,其用意在于为后面主人公马走日的故事制造出巨大的反差和张力,即:一个如此在选秀场上玩弄叙事手段及技巧去掌控看客的人物,到后面,他自己成了一个“被叙述者”,并需要通过他配合完成这个虚假叙事来救自己一命的时候,他却表演不下去了,他没法把一个荒淫邪恶的叙事情境安在自己的头上,即使这样能给他换来活命的机会,他也豁出去了。一个习惯于用叙事手段支配别人支配观众的人、一个习惯于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能够翻云覆雨掌控一切的人,当别人把他当作被叙述者、当作叙事手段表演这个荒唐故事的时候,他却无法表演下去,既使通过表演能营救自己的生命,他也选择了决绝的反抗。在这种前后反差极大的对比中,影片抛出了叙事的底线和叙事伦理问题。主人公马走日对虚假叙事的拒绝,对不道德的叙事手段的反抗、对设计好的叙事情境的砍砸,都指向对叙事者不良叙述行为的控诉。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深层是对叙述伦理的诉求。它要求一切叙事活动,均应尊重事关人格尊严的伦理底线。马走日为了坚守这一不可逾越的叙事底线,甚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前后判若两人反差极大的对比,也使马走日的牺牲具有了为守护叙事伦理而献身的“殉道”的性质。
突破叙事底线的文明戏
本片嵌入的另一个“戏中戏”是王天王在“枪毙马走日”文明戏中的叙事活动。这个故事与1921年7月电影研究社拍摄的电影《阎瑞生》(又名《枪毙阎瑞生》)有直接的指涉关系。电影《阎瑞生》的拍摄与当时根据阎瑞生案搬演的文明戏在上海受热捧密切相关②,郑君里说“电影研究社拍《阎瑞生》,用的都是新剧(即所谓文明戏)演员”,他还提到《阎瑞生》一片“旺盛的卖座力”激发了当时电影拍摄的浪潮③,这也说明《一步之遥》中“枪毙马走日”的文明戏表演时那种无比狂热的观看场面并不是姜文的臆造而是有着真实的历史依据。《阎瑞生》一片,以恐怖和暴力影像招徕观众,引发观影热潮,之后明星公司马上拍出了模仿《阎瑞生》的《张欣生》,在血腥恐怖的程度上变本加厉,导致当时的北洋政府发出对此片的禁令,理由是“惨无人道,不忍逼视”④。《一步之遥》中王天王充满暴力和色情意味的文明戏叙事,无疑是对当年的这一波没有伦理规约的电影潮流反讽性再现。
“枪毙马走日”的文明戏,让本来已经潜逃的马走日宁愿被抓也要挺身而出去阻止这个戏的上演。王天王的表演建立在对那场不存在的凶杀案的叙述之上。这一叙事充分激活了凶杀案可能有的所有暴力和色情元素。为了吸引观众眼球,表演者用怪异的造型,赤裸裸的女体,明晃晃的铡刀,疯狂砍杀的动作等,一切能吸引观众的视觉元素都被使用到极致。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王天王,深谙观众心理,熟稔于叙事情境的逼真营造,并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引导观众情绪,像之前马走日参与的那场大选秀一样,王天王的叙述同样也离不开对台下观众情绪的操控与煽动,如不停与观众互动,“这个人砍还是不砍,用哪把刀砍?”让观众帮他选择凶器。同时,它还致力于在凶杀细节上大做文章,并通过展示凶杀前的准备工作,如对凶器的选择,挖坑时与观众的对话,唱被他篡改的《天涯歌女》,使凶杀行为的实施被不断延宕,让观众为之疯狂。性的噱头也是本剧吸引观众的重要方法,如“我们俩本是一对狗男女,她当上总统,挣了钱不让我花,关了灯不让我睡,留着她还有什么用呢”“今天我是只杀不用,明天我是只用不杀,后天我是又用又杀,若想看全我的戏,要连看三天”这样充满性暗示的叙述手段,不断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吊起观众的胃口和期待心理。
王天王的叙述行为,显然包含有某种让马走日无法忍受的东西,否则他不会宁愿被抓也要冲出来痛殴王天王。逼迫他现身的,还不仅仅是这个叙事包含的淫秽与暴力,也不仅仅是它对事实的篡改和伪造。固然,这一讲述是对马走日本人的污蔑和歪曲,但让他忍无可忍的,还不是王天王的叙述是对真相的扭曲或将一个杀人犯的罪名强加于他,否则既已亡命潜逃两年的他也不会因为被污蔑为凶手而在此时出手。逼迫他不得不现身的,是文明戏“枪毙马走日”在其叙述手段中,包含着一种强劲的“邪恶”力量,这力量让死者不得安宁、更让他这个生者寝食难安。在这样的叙述中,因为过失意外死亡的完颜英,本是他心目中自尊高傲体面的人,但不得不被赤裸着身体在舞台上一次次被砍杀死。她的尊严、她死亡所具有的沉重的悲剧性,均被这种叙述手段所摧毁,变成了暴力和色情的奇观。文明戏“枪毙马走日”是一种只为赚钱而完全失去底线的叙事行为。马走日没法与这样的叙述行为和解,无法忍耐它以这种方式继续赢得看客们的喝彩和观众的欢呼。
无疑,王天王为了票房而不择手段的叙述行为,是对伦理底线的赤裸裸的挑战,也是让马走日不堪忍受愤而出手的主要原因。姜文这个影片以形象的方式向人们显示出,叙述行为的伦理性质,它牵涉到对逝者的尊重、对人格良心的维护以及真相的存在方式。当年,类似王天王这样为了票房赚钱而完全失去底线的叙述行为,被民国政府禁止了。但是今天,却成为不少导演为推高票房而继续使用的叙述手段和叙事方式。《一步之遥》中,还有马走日奋起反抗,试图阻挠不道德的叙事对人心的恶意践踏。今天,又有什么力量能与那些使用毫无底线的叙述手段去赚取高额票房的导演们抗争?
叙事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价值中立的活动。跨越伦理界限的叙事,利用各种叙述手段迎合人心中潜藏的对暴力和色情的嗜好,摄取观影心理,骗取大众的欢呼,赢得高额票房。他们带走了利润,却将暴力色情等所引起的对人心的伤害留给这个社会。在戏剧影视等叙事类产品的讲述活动中,叙述手段要尊重基本的伦理底线。诚然,叙事类作品所叙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丧失伦理底线的叙事活动,对心灵及意识的戕害是真实的。客观上,我们无法避免此类作品所具有的对意识的询唤功能及对心灵的化育作用。古人早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识,但如今面对此类现象却无人为之多言。姜文电影展现的那些被王天王叙事所吸引的狂热看客,在暴行施虐的情景场面作用下表现出来的一波波欢呼声,就是被邪恶的叙述手段调动下产生的肾线上亢奋,是看到施虐暴行时身体相应产生的高潮般体验,是看客寻求更加强烈刺激的要求。此时,观众内心的善念被不良叙事建构的“感官反应”驱逐殆尽,观众欢呼和迷恋的是罪恶本身。在不良叙事的引领下,那些没有底线的叙事情景及作恶现场犯罪片段,召唤出早已潜藏在人们心中并且会待机而动的恶灵。姜文影片在这里控诉的,与其说是上世纪初的王天王们,不如说是指向今天所有无视叙事伦理、利用叙事手段戕害人心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当下那些有票房无口碑的电影。可以说,影片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针对当前以色情暴力为买点的一批中国电影,当然也会指向《一步之遥》这部影片本身⑤。
砍向摄影机的刀:对无良叙事的反抗
姜文这部影片的最后一场“戏中戏”是武六拍摄电影“枪毙马走日”的桥段。为了让“枪毙马走日”的叙事更有噱头,项飞田等人以许诺给马走日活命的机会为由,让他亲自饰演凶杀过程。
“枪毙马走日”的片段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强劲的叙事暴力,即叙事所拥有的篡改历史扭曲真相的能力。一桩车祸造成的意外死亡在这个叙事中被改写成图财害命的谋杀,通过画面剪辑与字幕的配合,现实中忘恩负义为了升官不择手段的项飞田,被塑造成正义的化身,“大英雄项飞田,兑现承诺伸张正义”,而马走日则背上了永远难以洗脱的谋财害命的罪名。这就是影像叙事本身所具有的、让视觉表象篡位为社会本体的颠倒功能。这是一种可以借助叙事技巧和叙述手段重造历史颠倒黑白的力量。王天王对这种力量有着透彻的认识:“一个男人的一张脸,一个婴儿的一张脸接在一起,慈祥,一个男人的一张脸接一个光屁股的女人,流氓,所以马走日那张狰狞的脸接上一个断头女人,那就是在杀完颜英。”
如果说电影叙事具有强大的以假乱真吞噬真相的能力,那么武六未拍完的这部电影,他们诱导马走日加入叙事,则呈现出叙事具有的更深的反人道潜能。马走日被胁迫到这个叙事中自我扮演,为了让这个叙事“与世界接轨”,他被换上了SM套装,戴上面具⑥,继续手持大刀。但是,此前具有很高表演天赋、讲述能力、善于迎合观众的马走日,此时却没法表演下去,即便这样做可以为自己换取活命的机会,也无法演下去,“你们不能这么侮辱完颜,她是个体面的人”,这里,叙事手段所具有的反人道的地方在于: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不得不在叙事中再次出现,不断充当暴虐行为的受害者,一次次以充满色情意味的方式反复上演这一死亡。这种不良叙事对暴力凶杀的呈现,满足了不相干的看客们的嗜血或色情欲望,却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这是马走日宁愿付出生命也要维护的底线,叙事活动不能建立在侮辱人格与尊严之上。这也是一切叙事行为应遵守的伦理底线。所以,马走日拿着砍刀,在舞台上迟疑一会儿后,放弃了参与这个为自己换取苟且偷生机会的叙事表演,将用来砍杀女人的铡刀砍向舞台上的摄影机。这个动作极富象征性,摄影机在这里代表了一个不道德的叙事机制,马走日没法向这一叙事妥协,他拒绝配合参与这个叙事游戏,并开始疯狂反抗这个叙事机制本身。他不能参与这个叙事,不能参与对完颜的侮辱。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不只是他自己生命的尊严,更重要的还有爱他却已死去的女人完颜英的尊严,成为他奋起抗争的最大也是最终的理由,为此他已经无法顾忌自己的生命。
没有伦理规约的叙事手段,有着极强的颠覆性、破坏性,这也是影片中项飞田、武七等人极度青睐叙事的重要原因,所以项飞田说:“办大事还是需要搞艺术的”。他们看到了影像叙事所具有的这种篡位功能和颠倒历史的力量。项飞田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叙事,可以在案情明白的情况下,也要将马走日指认为凶手并直接宣判他死刑。在这样的叙事面前,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正如武七一遍遍强调的,“马走日杀没杀人重要吗?”。叙事活动,可以在马走日未曾归案之前一次次将他在舞台上枪毙,从而使马走日的死成为既定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民意”。这种叙事的“邪恶”之力尚不止此,它伤害的还包括无数站在台下的观看者,通过一遍遍对恶行不厌其烦的呈现展示,事实上已经将恶的基因潜移默化地植入到看客们的潜意识之中。这一叙事通过类型化的套路,程式化的表演,让一种本不存在的罪恶现场化、逼真化、写实化,将“恶”的实施过程巨细无遗纤毫毕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并且,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连续上演,使“恶”不断散播和复制,不断刺激召唤和呼应着观看者内心的邪念。
结语
目前,我国电影市场的繁荣与电影文化的沦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单纯的商业目的是催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当然,电影工业就是一种以赚钱为目的叙事活动。但是,无论这一目的的正当性如何坚挺,其叙事手段都应该有自己的戒律和禁区,以展示“恶行”为手段获取票房利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中,都是一种卑劣的不可取的行为。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侯曜《影戏剧本作法》中已经指出过“不宜取做影戏材料的几种情况”,具体列举了32种。这些条款在今天看起来仍然不无警示意义,如他讲“虐待动物”“对于妇女的残忍与酷刑”“儿童之犯罪”“对于罪犯严刑询问的实施情状”“处决及磔刑”“虐待儿童”“诱奸妇女及用恐吓方法而恣意强暴的情形”“各种惨心伤目的疾病”“杀人放火的惨状而足以挑动人的恶意的”⑦……这些内容不适合出现在电影中。侯曜对当时电影人的告诫,都是触碰了伦理底线问题。这些场景展示的残忍画面,如出现在电影叙事中,都会造成对观众心灵不同程度的戕害,或者如侯曜所说,“足以挑动人的恶意”。但是,这位民国电影人所反对运用的叙事手段,在今天的电影制作中,却成为司空见惯的吸金方法。此种现象足以说明,今天电影的叙事底线早已失守。在没有伦理制约的情况下,叙事手段越发达,叙事能力越强大,其产品对社会文化的危害就越大。今天的社会,已经为无视伦理规约的叙事行为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叙事者或‘大影像师’的故事,以迎合观众的私欲和低级趣味为手段,把每个接受者询唤为欲望主体、或不择手段的损人利己者,或者以暴露为手段,制造出更多的窃贼大盗杀人狂等。”⑧
因此,《一步之遥》中马走日以生命为代价所阻止的,正是这种只顾利益而无视伦理底线的叙事行为。在影像传播无处不在的今天,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的叙事活动,或为了还原真相、为了实现正义的审判,还是为了艺术探索等,没有伦理底线的叙事行为,其中所充斥的恶意足以抵消它的任何正面诉求。今天,在电影工业越来越被重视,艺术电影越来越被公开敌视的氛围中,“恶”作为最能吸睛的叙述对象,被一批电影导演选中。他们利用各种叙述手段保留其激动人心、使观众血脉贲张的“魅力”。凶杀、奸淫、盗窃等被一遍遍召唤上场,并不断得到高票房的回应,在一些观众的欢呼声中,恶被洗去了其不道德的色彩,但其具有的破坏性本质被传递和复制,瘟疫般流传,从一颗心到另一颗心。这种传播邪恶以带动票房的叙事手段在电影生产中已经成为常态。今天的年轻观众,被没有伦理底线的叙事手段所挟裹,并为此激动喝彩,为它贡献票房。讲述没有伦理底线的故事,是王天王所做的,也是今天只信奉票房的一批中国电影人经常做的。而反抗这种不道德的叙事行为,不仅是马走日所选择的,是姜文通过这部电影试图达到的,也应该是中国电影批评和成熟起来的电影观众们共同抵制和拒绝的。
【注释】
①例如,2015年6月24号前后网络上纷纷转载了毛尖对贾樟柯新作《山河故人》的两篇评论,说他这部片子不是太流畅没有原先的好看。25号14:01分贾樟柯微博上的回应是:“过去读毛尖老师的影评,觉得幼稚但可爱。今天读了她关于《山河故人》的文字,突然觉得性感,平添了一种淫荡”。贾樟柯一向以温和见长,但对毛尖些许的批评就动了粗口,“性感”“淫荡”这些词都用上了。
②当时此案改编的文明戏成为各大舞台的保留剧目,有“阎戏”之称,“它的‘新闻价值’吸引了上海新舞台,遂将其改编成文明戏,演出半年,卖座始终不衰,竟成为这一年度上海最轰动的剧目”(许道明、沙似鹏.中国电影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39-40.)
③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239.
④当时有人上书教育部要求禁止《阎瑞生》与《张欣生》二片:“近日电影片中于诲淫诲盗外,罪尤加等者有二,一为阎瑞生影片,一为张欣生影片……写者必欲取穷凶极恶,描写尽致,宣扬其姓名,流传于世界,此尤不可忍矣。……以上二影片可否函致警厅迅饬禁止,于人心风俗所关匪巨”(嵩堃.请禁止电影《阎瑞生》、《张欣生》议案.汪朝光.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J].近代史研究.2001 (3):203-226.
⑤同王天王的《枪毙马走日》反复出现裸露的女体(假肢)一样,《一步之遥》开场的舞蹈,同样也是以满场飞奔的女性大腿为噱头和宣传的卖点。
⑥这里有更加明显的自我指涉意味和反身性的对中国电影的批判:为了让中国电影具有世界性的语言,当前的中国电影叙事者也为自己的叙事换上了这样一套西方化的“套装”,按照西方的模式打造一种中国的电影叙事,将色情和暴力的内容进一步发扬光大。
⑦丁亚平.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61-62.
⑧曲春景.蚀心故事与被污染的叙事主体——当前影视艺术的叙事伦理病症剖析[J].探索与争鸣.2014(5):74-79.
张卫军,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博士生。
曲春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电影的叙事伦理批评》(项目编号:15BC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