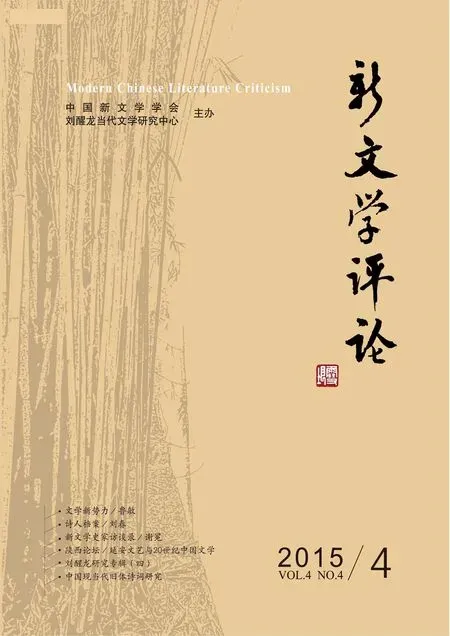现实思考中的人性分析
———评鲁敏长篇小说《六人晚餐》
◆ 李佳贤 王春林
现实思考中的人性分析———评鲁敏长篇小说《六人晚餐》
◆ 李佳贤王春林
“70后”作家鲁敏的小说虽多涉及纠结的婚恋和隐秘的欲望,但却并不流于浮浅,而是氤氲着现实的底蕴和人性的温度,有着沉甸甸的厚重感。这种艺术品质的获得,得益于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隐秘人性的深度挖掘。这里要具体谈到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便是这样一部有着批判力度和思想深度的小说。鲁敏将《六人晚餐》的时代背景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社会转型期,老工业区与厂区人的命运被动或挣扎着随着这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小说中的两个普通家庭便是这时代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爱恨纠葛、挣扎与痛苦深刻地折射出了时代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阵痛。在这部小说中,鲁敏在就国企改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由此深入对中国式发展和阶层差距等问题的批判上。除了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思考,作家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而真实地刻画了人性与道德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六人晚餐”本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单身派对,当然,这一词汇的本义与小说中所具体指涉的“六人晚餐”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前者明显轻松浪漫,后者则沉重尴尬。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词语的多义性,才使得“六人晚餐”的命名更多了些黑色幽默和悲悯的意味。小说中,两个家庭周六的聚餐在增进感情方面收效甚微:“他们的吃饭,是纯粹的吃饭,绝对没有任何的交谈或嬉笑!‘吧唧吧唧’,只有‘吧唧吧唧’,他们挤挤挨挨、专心致志地吃……多少个周末的六人晚餐啊,蠕动着的胃囊,油腻腻的桌面,筷子碰到饭碗发出声音,像是一台小尺寸的旧电视里所播发的画面,像是凡·高的《吃土豆的人》,嘴唇的开合中散发着无限的凄凉之情,一种共同努力着但并无改善的困境,赤裸裸、心知肚明的孤独……”虽然,这“六人晚餐”几乎丧失了社交的功能,但它却是小说中很多故事的重要起源,如若没有这“六人晚餐”,也就没有了晓蓝、丁成功与晓白之间十余年的误会与纠葛,合谋一样的周三恶作剧也不会存在,苏琴与丁伯刚或许也就不会分开……总之,两个单亲家庭每周六亲近而又陌生的聚餐,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场景,也是小说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意象。
细细想来,这两个家庭六个人的组合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他们的相遇源于苏琴出人意料的选择,这选择也最终将苏琴置于道德和阶层的双重困境之中。苏琴的丈夫因肝病去世之后,她非常执拗地保有对丈夫深深的眷恋和忠贞,但汹涌的欲望却是不讲情面的:“魔鬼是丈夫死后开始附身的,这一年,苏琴三十九岁,可是魔鬼才刚刚出世,正是最新鲜最起劲的时候,它喜欢大闹天宫……苏琴真太惊讶了:一个人会这样地为身体所奴。”当然,在90年代,“再婚什么的,算不得什么了”,但奇怪的是,苏琴最终竟选择了“破抹布般”的丁伯刚。这丁伯刚与苏琴前夫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秃顶,酒糟鼻,搓着手的寒碜样,带铁锈味的藏青工作服,眼神躲躲闪闪。”“书本对他而言乃狗屁……除了脏话外他不善言语,并且大部分时间抱着酒杯醉成一只麻袋。”母亲的选择,让儿子晓白也疑惑万分:“厂区这么大,这么多男人,就是闭了眼,也不见得能撞上这样儿的一个来!以貌取人这是不对的,但这跟他们原来的爸爸,差别实在太大!爸爸的俄语说得跟外国人一样。爸爸穿米色风衣。爸爸每天晚上擦他的皮鞋。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却原来,苏琴始终放不下病逝的丈夫,丁伯刚之前,媒人也介绍了不少比丁伯刚强很多的男人,但可悲的是他们身上总有一些特点让苏琴想到过世的丈夫,这让她没办法接受:“不,绝不能是他们,那太让她难受了,好像他们都已经给做上记号,那些记号总会像小箭一样带着哀伤的阻力射到她心里,使她直接或间接地想到丈夫。他依然栩栩如生,在暗处陪伴、凝望着她。”于是,为保全情感上的忠贞,苏琴宁愿选择与丈夫全然不同的丁伯刚。她满以为选择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就能成功地将欲望与情感分割开来,“她打定主意,永远不对外承认与丁伯刚的关系,也永远不会对他施以友爱与真心。她宁可这样终身孤僻”。毫无疑问,苏琴想保有个人感情和生活的私密性,然而,可悲的是,苏琴所固执的私人道德与厂区的公共道德是相违背的:厂区并不在意男女之间“大胆、混乱乃至邪恶的行为”,但厂区亦不承认所谓的“隐私权”,他们需要“敢作敢当、开诚布公”,需要“贴心人般、毫无保留的坦诚与信任,他们最不能容忍遮遮掩掩的假清高”。于是,苏琴的坚守反而将自己推到了公共道德的对立面。这也就决定了苏琴只能瞒着所有人跟丁伯刚搞“地下情”:每周三天黑之后她便去“那边”过夜,然后在第二天凌晨赶在众人醒来之前悄悄地回家。然而,她一切的努力却只是掩耳盗铃,而且还“害得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与口舌来关注她、跟踪她、揭露她,她活在浑浊的语言洪流里,活在一个背德者的孤立里”。苏琴对自己所谓的“忠贞”、个人道德与隐私权的坚持,除了要面临来自厂区人的压力,也必须面对随时准备打碎她幻梦的子女。先是晓白的“发烧”把戏,再便是珍珍或丁成功的“突袭”和“回马枪”,周六两家人的晚餐反而让四个孩子结成了一致对上的“联盟”,这些孩子的轮番捣乱让苏琴的周三夜变得尴尬、混乱。于是,极力坚持个人道德与隐私的苏琴却“感到自己狼狈得像一头雨中的母狗,在不断扔来的石子中东跑西躲。没有任何人尊敬她,包括她自己。一个偏执于隐私的人就等于是个浑身泥水、极端下作的人吧”。
深陷道德困境的苏琴开始觉得自己荒唐,但最终导致苏琴与丁伯刚分手的关键原因却是女儿晓蓝与丁成功的亲近。苏琴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会看上丁成功那小子,在苏琴的眼里,丁成功“除了长相还算斯文,其他有个啥呢?白天光膀子吹玻璃,晚上打桌球赢钱买烟,浑身上下每一个口袋都是街头小杆子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味道”。其实从苏琴选择丁伯刚开始,她便有一个明确的阶层观念。苏琴是烷基苯厂的会计,已死的丈夫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但丁伯刚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虽然都生活在厂区这样的低层社会,但高低的差异毕竟还是真实存在的。正是这阶层的差异让苏琴觉得安全,她觉得横亘在两个家庭之间的差距可以确保她不对丁伯刚动心,这样她便可以继续对已死丈夫的忠贞(事实上,两年多的相处终究还是让苏琴对丁伯刚产生了感情)。所以,当苏琴发觉晓蓝竟与丁成功“搞到一块儿”时,冲上去扇了女儿两耳光,这样剧烈的反应,概是因为女儿的“自甘堕落”与不争气,苏琴是不能容许女儿不向上升而往下坠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决定与丁伯刚分手:“说到做到,我下星期分手。不过,我也要你保证,你不再跟丁成功,永远不要。”其实,做出分手的决定,对母亲苏琴来说也未尝不是种解脱:“这正是个机会!她可以就此摆脱身体的奴役,重新站到透明的公共道德这一边。这孤军之境,她也真的受够了!”阶层与道德造成的压力和困境,最终让苏琴缴械投降了。
颇为戏剧性的是,曾经站在公共道德对立面的苏琴竟然因为与丁伯刚的坚决分手,而获得了道德“加分”,这让她得以在多年后进入居委会工作,成了公共道德的化身。“居委会具有一种泛道德的超越性,拥有对他人隐私无限贴近、无限深入的特权”,于是苏琴得以看到形形色色游走在公共道德边缘的人们,“如此一比,她当初真算个初级阶段的零蛋啊”,这样的比较让苏琴心里宽慰不少。值得庆幸的是,苏琴并没有因为居委会的工作而变成公共道德卫道士,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也曾是背德者,她反而对这些人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悯:“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所有的这些私密,仍然会遭遇到公共道德的围剿与捉弄,被赤条条地挑到半空、撕裂在强光之下——这让她感到深深的不忍与同情,还有警惕!”居委会的工作让苏琴更深地体会到了这公共道德对人性的压迫和对私人生活的强力侵占,也强化了她本就存在的人性与道德的冲突:“道德这玩意儿是不好对付的,是根橡皮筋,看起来宽泛,实际上一直紧绷着,随时会收紧、勒住脖子,让你透不过气,让你生不如死、死亦不得其所!”苏琴最终离开居委会,她不愿再扛着公共道德的大旗去干涉他人的私生活了。但苏琴对这公共道德除了恨也有怕,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其实一直存在于她的生命中,面对儿女她故作开明,但实际上她还是“像从前一样惧怕不合规矩、不符合常情的东西”。
苏琴可能没有意识到,女儿晓蓝虽与丁成功交往,但却始终明确地行走在“通往更高阶层的孤独之路上”。多年后,晓蓝如母亲所愿,考上大学离开了厂区,之后又光鲜亮丽地嫁到了市区,过上了所谓的上层生活。在《六人晚餐》中,阶层的差异是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阴云。鲁敏无疑成功地为小说人物的登场设计了一个黑色荒诞且颇具后现代意味的舞台——“厂区位于城北以北的郊县,算是一块被扔得老远的‘飞地’。其空气,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不是‘空’,而是丰满、拥挤、富有包围感,它亲热地绑架一切,裹挟住所有人的鼻腔、咽喉以及肺部:有时是富足的硫化氢味儿,像是成群结队的臭鸡蛋飞到了天上,或者是甜丝丝显得非常友好的铁锈味,又或是腐烂海鱼般的氮气的腥,最不如人意的是二甲苯那硬邦邦、令人喉头发紧发干的焦油味,像一个顽皮的家伙从背后紧紧扼住你的脖子——依据刮什么风而定,以及风的上游是什么厂而定,有时早晨和黄昏还各不相同,有时还会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气味的混合,好似有个设计师在进行不大负责的搭配”。于是,当市区的人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来到厂区时,“他们嫌恶地暗中诅咒着,尽量屏住呼吸,巴望着早点离开,同时又不忍心似的,看着十字街上尘土里嬉戏的孩子,以及一长排门铺前裸露在风中的油炸点心、碱香馒头,觉得这简直是牲口般的生活……返城的小车子来了,他们仓促地爬上去,急忙驶去的车窗闪过他们皱成一团,变得难看了的白脸”。这里,鲁敏抓住空气这一意象,突出了厂区环境的恶劣不堪,厂区的生活在市区人眼中是“牲口般的”,两个群体生活质量的差距之大不言自明。小说中,两个家庭的悲剧便起于这厂区的严重污染,丁伯刚妻子的贲门癌、苏琴丈夫的肺病都与厂区严重的环境污染有很大的关系。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苏琴要苦心孤诣地让女儿“正确”地向上升,而丁伯刚则是沉醉在“神童”儿子的幻梦中不愿苏醒,乃至丁成功对晓蓝的放手与成全,黑皮的贵族梦,打工妹对丁成功的主动示好,等等,本质上,都是这真实存在的“阶层”所致。丁成功对玻璃痴迷,这玻璃也好像成了他人生的隐喻:“看得见,却永远达不到。”无论是对晓蓝的感情,还是对更好生活的争取,每次都好像近在眼前,但结果却是永远触碰不到。厂区因为拆迁而导致的爆炸,让丁成功的玻璃屋化为废墟,他自己也葬身其中,要打破这阻隔底层人向上的“玻璃”,竟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底层人上升的艰难通过“玻璃”这一意象得到了精准的表达。作者通过这爆炸也批判了盲目无序的中国式发展。
不得不说,这爆炸跟丁伯刚的女婿黑皮大有关系,黑皮通过厂区改制和拆迁发了点小财,但实际上真正从改制获利的却是工厂“中层以上”的人,他们通过改制共同瓜分了厂区的股份。可悲的是,更多的普普通通的厂区人却成为这场改革大潮中被遗弃的失败者,他们被“提前退养”或被“买断工龄”,只能徒然哀叹:“为什么上辈子没有投胎做成‘厂长’、‘副厂长’,否则现在便可以变成为‘经理’、‘副经理’,拥有一夜暴富的股份。”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中,同样的厂区人,却因为身处两个不同阶层,而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这里所体现的其实依然是作家对阶层差距的批判和反省。身处底层的丁伯刚无疑是最能代表厂区人形象的人物。他自认为是工人老大哥,同时巴望着曾经的“神童”儿子丁成功能成为真正的成功人士。但他的生活却实在不如意:妻子早逝,儿子一蹶不振,与苏琴的一段感情又无疾而终,之后经过工厂改制、下岗、拆迁等一系列的打击,使丁伯刚沉溺在酒精的麻醉中,并且逐渐失忆了:“在大部分人看来,尤其是丁伯刚的工友们看来,他的失忆是从厂区改制开始的——国家权力机器的影响,再怎么说,也该大于女人的绵软肉身吧。”丁伯刚的失忆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工厂改制却无疑是最主要的诱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厂区虽然让市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丁伯刚这些生活于其间的工人们却是敝帚自珍的:“丁伯刚喜欢站在窗前发呆——这样的厂区黄昏,丁伯刚多么喜爱呀,以至于他一听到年轻人对厂区的偏狭、落后表示抱怨时,他就会发火,这么温顺、广阔的厂区,还有什么好挑的,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嘛。别以为丁伯刚在说胡话,凡是跟他一样,在厂区一轮又一轮生产高潮、劳动竞赛、比学赶超中度过美好年华的人,都跟他深有同感。他们一直记得,在厂区,他们创造了多少奇迹,那么充实而生机勃勃……”所以,在丁伯刚眼里,甚至工厂烟囱冒出的灰黑的带有焦煳味的烟,都有了别样的美:那烟“随着风形成的弧线如同女人的腰肢,着实使人迷醉”。但工厂改制却剥夺了丁伯刚最后的骄傲:“撕裂与蹂躏的疼痛里,‘提前退养’与‘买断工龄’像两只经验老到的手,剥光人们的衣衫,撕烂人们的内衣,被逼到角落的人们只得像良家妇女一样紧紧护卫着最后的然而一文不值、必将暴露的私处。”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是开天辟地的工人老大哥,怎么能这样卸完磨杀驴吃,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治不了,专拿工人阶级开刀,老大哥耗光了青春、洒光了热血,到头来就这样一笤把扫地出门吗……”厂区的工人们心有不甘,但生活在底层“如蚂蚁日夜爬动”的柔弱个体,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这强悍的国家权力机器呢?于是丁伯刚只能无可奈何地冷眼旁观,他完全把自己沉浸在酒精里,并且逐渐失忆了。需要注意的是,丁伯刚的失忆是选择性失忆,他完全忘掉的是失败的、不快的、纠结的往事:比如妻子的死,比如已不再是神童的儿子,比如和自己分手的苏琴,再比如厂区的改制和之后的拆迁。丁伯刚忘掉了人生中不快的往事,迎来了“人生最为欢乐祥和的阶段”,他成了活在过去的人,拒绝面对厂区翻天覆地的改变,对那些新开的超市和商铺,“他老人家一概有眼无珠、充耳不闻,固执地停留在他熟悉的旧日画面里。他煞有其事地走走停停,跟压根儿不存在的烧饼铺、五金店、桌球小老板、修自行车摊子及来来往往、并不存在的熟人们挥手招呼、指东问西,在原来该拐弯但现在变成蛋糕店的地方,他踏着小碎步在原地模拟拐弯;在地铁施工的围挡处,他心情愉悦地停下,大声说笑,因为那里原本是一株树荫巨大的老树,下面长年支着张破桌子,并总有三五个老家伙在玩牌——这些老家伙们,其中有两个已经故去”。但是,小说里写到的一些细节却让我们怀疑丁伯刚是否真的失忆,比如面对拆迁中的迁坟一事,丁伯刚的呼号分外有力:“哎呀,什么世道,连死人都不得安生了嘛,死了都还要被拎起来!不能这样的呀!这根本不是人做的事啊!从古至今啊,都讲究个入土为安啊,哪有进去了又出来的道理?我一辈子安分守己啊,我是工人老大哥啊,我从不作孽啊……”丁伯刚先知一般的预见到了未来会有更多的拆迁,所以他宁愿把妻子的坟墓留在原地,他自己也拒绝土葬,这
样的丁伯刚分明格外清醒,失忆许是假的吧。但如果他是因为无力面对现实而宁愿选择遗忘的话,这反而更让人心痛。丁伯刚仅仅是国企改制大潮中被裹挟而去的一粒沙尘,但通过丁伯刚的遭遇,我们得以窥见在国家权力大手的拨弄之下普通工人的悲哀和无力。现实中,丁伯刚的幻梦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于是,他宁愿选择活在梦里。对丁伯刚的成功塑造,也让我们看到了鲁敏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和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人的悲悯之心。
小说结尾处,经历了生(晓蓝产女)和死(丁伯刚、丁成功父子之死)的两个家庭,在正式分手十二年之后又再度相聚在一起,“天色渐迟,仓促的野餐有点简陋,只是切片面包、盒装牛奶和一些水果,花纹难看的桌布也有点嫌小,可他们毫不在意,他们所看到的,好像还跟多年前的星期六晚餐一样,消逝了的暖色灯光之下,满桌子的盆盆罐罐五颜六色”。不管怎么互相伤害过,他们最终达成了和解。不同于多年前周六晚餐的尴尬,这次的相聚,除却沧桑之外,却也真正有了难得的家的温馨。作家饱含同情和悲悯地书写了两个家庭数十年的爱恨纠葛和艰辛的上升之路,生活在底层的他们难以对抗动荡的时代洪流,但他们却依然努力地生活着。除却批判精神与悲悯情怀,我们在小说中亦能看到作家与笔下人物逐渐醒悟的罪感意识,无论是苏琴对丁伯刚葬礼的热心张罗,还是葬礼上对丁成功的道歉,或是晓蓝对自己多年坚持的“向上爬”原则的怀疑,乃至珍珍在十字街因拆迁发生爆炸之后的自责,都是罪感意识的具体体现。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鲁敏在叙事上所采用的多视角的叙事模式。我们发现,小说在叙事上虽然使用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视角,但作家却无意于扮演全知上帝的角色,而是分别从多个人物的角度进行切入,不断从不同人的角度去回顾同一件事,这样故事的面目通过各个角度的再现,逐渐清晰、立体起来,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向度。这样的叙事模式,对更深入挖掘人物个性和心理亦功不可没。另外不拘泥于时空限制的极富跳跃感的叙事,更强化了小说的宿命感和悲剧感。
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