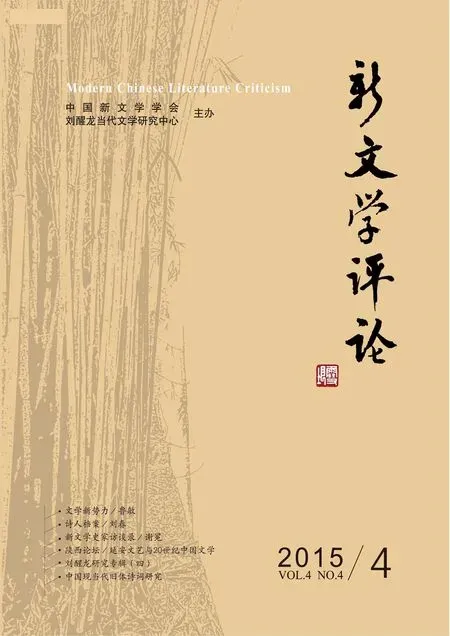爱情的存在与虚无
———评尔容长篇小说《相爱不说再见》
◆ 王新民
爱情的存在与虚无———评尔容长篇小说《相爱不说再见》
◆ 王新民
阳具的“权力”
在长篇小说《相爱不说再见》中,尔容对男人的虚伪和放荡是宽容的,对于男人“阳具权力”的泛滥,尔容往往能够为他们找出许多“人性需求”的理由。至少是默认了“阳具权力”的合理性。铁娃与心泪温馨的婚床,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神话的圆满结局,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爱情“补偿性愿望”的实现,实际上却是对“阳具权力”的一次无奈的妥协。
在传统男性中心批评的模式中,女性主义的批评,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权力,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至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在男权的压抑中反思女性传统或女性自我等课题的可能性。同时,也在此基础上探讨女性作家应该如何在其文本中回答“我是谁?”和“我在和谁说话?”等女性问题。
女性书写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个文化符号,不论女性形象在文学世界里获得何种崇高、独立的身份和地位,一旦落到现实中,都依旧面临强大的压抑性命运;文学世界中的补偿性愿望,一旦落实到现实,便宣告破灭。女性的匮乏再度浮现,即使是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精彩寓言的文学叙事里,也仍然隐匿着无数女性的压抑和苦闷。
在长篇小说《相爱不说再见》中,铁娃的爱情是一笔糊涂账,他的行止完全以阳具的需求为风向标,听任琐碎、零星的瞬间欲望,左右着他的生活轨迹。忠诚与性欲的冲突使他在精神上处于瘫痪状态。在铁娃那里,忠诚爱情与“阳具权力”的边界,是由他自己规定的,铁娃对偷情的喜爱远远胜过婚姻内的快乐,在疯狂中似乎完全可以找到更加强烈的冲动。归根到底,铁娃对婚姻的留恋不舍,其实只有一个苍白的躯壳;他对于水莲的情感,也只剩下零碎、卑俗的欲望。男人要的是女人的身体,女人要的是男人的心。
我们不能把女性作家这种关注女性的叙述,简化为女作家书写能力上的局限,或是过度沉迷于女性情感的一种迷思。尔容也关注一些宏大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比如爱与生,平庸与尊严,底层与大地等等。也希望提示隐匿在婚姻爱情背后女性的愤怒,两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对人类存在的深远影响。《相爱不说再见》的张力,主要是通过二元对立的冲突来实现的,如身体激情与精神渴求,善与恶,神圣与亵渎等等。小说充斥着激情与道德的对立,也表现出对欲望的宽容态度,很多时候,铁娃总是在欲望和神圣间挣扎,但是,铁娃最终还是相信爱与性是接触人性的最佳途径。
香香是“阳具权力”学的试验场,作者对香香开放性的身体叙述,远远疏离了以往那种闺阁话语中有关女性“贞操”的道德说教和“乱性”的责难,真实诉说了女性情欲与权力的正常关系。传统逐渐逝去,道德中心已经消解,永恒存在的是人类饱受欲望困扰的这个话题。事实是,在当今的女性经验本位和女性感觉中,她们已经远离了那种让人感到窒息的“道德恐怖”。所以我认为,《相爱不说再见》的寓言意义在于,香香对于爱情想象的绽放及其终结,不仅仅再一次证明了男人的虚伪和“阳具权力”的冷酷,而且也为男权专制下的婚外女性,提供了无比“苍凉”的启示。
“铁娃现象”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中国文化是一种没有超越,没有拯救的文化。一般的老百姓只关心在世俗中的享受,他们的生活理想也是一种“身体化”的理想:享尽富贵荣华、享受天伦之乐。正是这种世俗理想,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
在心理层次上,尔容的书写深入到了女性潜意识层面,将其力比多转移到文本之中。其实,小说写作本身并非可以随意控制的意识活动,而是潜意识的,连作者本身亦无法知道自身的写作会把她引向何方。从水莲和杂志社社长一刀这两个女性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尔容把女性的压抑指向了集体潜意识,从而勾勒出了知识女性历史和文化的总体面貌。一些女性主义者如肖瓦尔特相信,女性文化模式要比生理、心理分析和语言的理论更为有效。这是由于女性看待自己身体的方式,以及她们对性与生育功能的看法,都与她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息息相关。这种深层次的考虑,亦能进一步协助我们梳理尔容如何书写女性,如何替女性说话,以什么身份替女性说话,以什么名义为女性说话等问题。
女性的梦想
爱情是一种自虐,在自虐状态下,水莲无法忍受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没有见解,她总是试图在精神世界里,寻找与现实世界的对应;她一刻不得安宁,总是想把灵魂从肉体中剥离,却又总是为这种剥离造成的疼痛所折磨;西西弗的命运是诸神施加的惩罚,水莲的命运却是自己在理性殿堂上高声宣示过的抉择,在猥亵的挤压下发出痛苦的吟哦。
水莲希望在追求纯粹之爱的同时,能够塑造男性的爱情品质,而且她希望即使是面对差异,反复离合中这种塑造也最终能够实现。水莲的愿望代表了21世纪中国社会女性主义进化的人性成就,她们已经远远地走出了张洁的时代牢笼,已经不是被动地被选择,而是主动、进取地选择着,选择就是自由。在《相爱不说再见》中,尔容塑造了一个不仅知道自己爱什么、怎样爱,同时具有主体性冲击的“我要”的女性。水莲在情感、人性的不断逃离与回归中实现了自我,却也铺陈了她与铁娃之间的相互距离。水莲在自由的爱情空间里游走,却又本能地逃避着自由的侵扰。这既是女性最终的现实姿态,也是生活本身为女性准备着的理性姿态。
光能合成是植物进行有机物积聚的基石,恶劣环境致使叶绿素含量变化,对光合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因此研究植物叶绿素含量至关重要[24]。研究结果显示,除‘晋荞4号’外,随着胁迫程度的加深,各苦荞叶绿素含量均显著下降(图1)。与正常供磷(P1)相比,在P2、P3浓度处理下,叶绿素含量降幅最大的是‘西荞1号’,降幅达37.46%和52.74%;‘KQ10-11’和‘迪庆1号’次之;降幅最低的是‘晋荞4号’,降幅为5.73%和13.57%。可见,耐低磷苦荞叶绿素含量降幅小于不耐低磷苦荞,且叶绿素含量高于不耐低磷苦荞,更有利于光合作用,对低磷胁迫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与张爱玲那一代女作家的女性写作不同,尔容的写作是具有全新写作内容和文本特点的“新红颜写作”。尔容技巧地表达了中国女性埋藏得很久的生命欲望,而又把这种欲望置于自由的逃避之下。责任、道义、克制等人类美德,似乎瞬间化作来自远古荒原的巨垣,横卧在铁娃、水莲两颗吸引得很苦又分离得很累的灵魂之间,异化为一种伪饰的崇高。尔容把女性生命的焦虑,化作一种崇高,叛逆了个性欲望而服从某种道义。实际上,这种女性生命欲望的自我压抑和逃避,是一种身体的自虐。在《相爱不说再见》中,尔容把婚姻的悲剧,置于残酷的对话系统中去演绎,而把自己间离出来,令人物痴迷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却期待无望。作品的间离状态,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尔容因此也就实现了不仅仅站在狭隘的女性立场,而是在人性的制高点上,对两性关系中东方文化氛围中的种种诘难的俯视。
由于尔容将香香置放在从属的位置中,采取一种让她自由言说自身压抑问题的书写模式,在生理层次上,尔容身为女性作家,相当能够在其文本中发挥本身性别的书写特质。在她的女性身体的书写中,充分表现了她对于女性自我的多重性的认识与肯定。此外,女性身体也成为她的认同对象,供给她模拟和凝视女性自我所需要的原型。在相当程度上,她的书写乃是把女性身体当作集体想象处理。在沉默之中,女性身体在总体压抑中所汇聚到的力比多——精神分析理论中一种能量形式的概念,往往被阐述为焦虑、歇斯底里甚至疯狂的状态。
试图逃脱禁锢的人往往被自己禁锢,这是因为,爱情是一个贝壳,你可以把它撞碎;而你被自己的灵魂包裹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它,即使你也不能。爱情总是把自己说成神话,它许诺给我们超出我们经验的种种希望,而它自己却并不愿意停留在人间;我们通过爱情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那只是爱情让我们看到的爱情的世界。香香由盲目爱恋到痛苦、疯狂、甚至到最后濒临绝望,她的疯狂源自对自身处境逐渐清醒的认识,想有所改变却无能为力,它是社会的某种阶层的生成机制和文化差别的结果。社会强势力量竭力压抑人性中潜藏着的原始力量和激情,而这种原始力量和激情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人际交流的向往和对回归人性的期盼。这些都是人的正常需求,但在涉及社会各种关系的利益机器的运作下,却以一种非正常的歇斯底里式的疯狂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香香背负各种罪名的疯狂是无辜的。
作者将目光和思绪,放在人类社会的现代进程与精神难点上,努力发现并诠释其中的困惑,将爱情、生命的价值,整合为体现辩证、深刻与成熟的精神气场。这个气场,不仅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使人们最终意识到:真正合理的现代生存,除了经济和物质的维度之外,还应当有一种文化和人本的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尔容在《相爱不说再见》中,能够以痛苦、冷峻而无奈的态度,放纵铁娃荒诞地沿着诱人堕落的方向滑落,最后又向爱情的起点回归,留给了只相信“阳具权力”的铁娃一次浪子回头自我救赎的机会。而且尔容自己还不得不成为种种龌龊失范的人间丑行的讲述者、见证者和挽救者。与其说是作者在解读铁娃的堕落人生,不如说是铁娃的堕落人生讽喻式地注解了作家个人的“生存美学”。
清醒的生命意识,带来的似乎是思想的分外沉重,作家在铁娃身上看到了“沉思”与“行动”之间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后,她继续追问:“人该如何生活?”人该如何生活呢?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但不是《相爱不说再见》阅读后的作业,而是一份难得的生命启示。作家尔容在作品中对主人公及其置身的环境,以现实主义笔法予以大面积精确描述,而且总是注意寻找、提取关乎灵魂的元素和信息,追索和逼视现代都市中彷徨的灵魂能够取得自由的可能性,力图以别开生面的“物语”和文体给人以深度抚慰。作家面对铁娃的躁动不安和人性的裸露,不是满足于呈现,而是以一种冷静和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作品主人公的精神变异,从欲望化的叙事中升华出精神的追问。
爱情的虚蹈
真爱始终是水莲内心深处的渴望,是生活品质的保证。在这个一切都显得易碎和易变的娱乐化的时代,水莲希望找到一点温暖的力量,好让她将爱情进行到底。但是,爱情没有逻辑,也没有固定的线路可循,水莲以完美去要求、去寻找爱情,而收获到的却往往是缺失和遗憾。或许,尔容写的并不单是铁娃和水莲的爱情和婚姻,尔容写的是一种生存相,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也许无望的追求。作者敏锐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特有的心理疾患和生存困境,同时尽可能地搜寻着人类走向彼岸的灵魂通道。
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说,“人之所以经常产生荒诞感,是因为这个世界无法满足我们对意义的寻求”。爱情的意义肯定存在,然而它只能出现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既听不到它的声音,亦看不到它的容颜,在世俗、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水莲无法与爱情相伴,她只能像走失的孩子一样踽踽独行。可是话说回来,爱情真的出现在她面前又如何呢?水莲会发现,它身后仍然存在着无限深邃的未知,那里仍旧是一片混沌与迷蒙。我想,这既是西西弗命运的意义,也是人类自身命运的意义吧?令人悲哀的是,加缪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洞察了人类的荒诞和虚无。而这种洞察依然让今天的作家和读者,一次次张大嘴巴,恍然大悟。
爱情是两个精神世界的交融,是精神边界的消失,幸福感正是从这种消失中获得的。人归根结底是孤独的,只有这种精神边界的消失,才终极性地意味着你找到了依傍,有了这个依傍,幸福感就会如同涓涓溪流漫过你的心田;反过来说,如水莲一样,当你明确意识到那个边界的存在、当你强调那个边界的时候,当你不得不在自己这一边过哪怕是一部分精神生活的时候,无论你怎样讴歌,爱情其实也不具备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只是一种幻象,它早晚都会消散为无形,无人能够阻止。
婚姻的诗意从来都是人为了让自己认为活得还像一回事而主观臆造出来的,婚姻本来就没有诗意。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尔容自己也认为:“人喜新厌旧的劣根性,主观夸大情人的性质和价值的冲动性,又让爱情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只可远观,不可近玩。只可想象,不能面对。失望、悔恨、决裂。有人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情感能以如此高比例的失败而告终。这实在怨不得任何人,只怨恋爱中的自己。因为人一旦进入爱情,一切的智慧都被缴了械。”然而十分吊诡的是,世人都能看透爱情的虚幻,但人人又都向往爱情,一根筋地扑向爱情,甚至把爱情想象成为婚姻。
《相爱不说再见》书写的是中年人的生存状态,它呈现了几个中年知识分子生存的全景模式。书中蕴含着作者细细体味的人生奥秘和处世哲学,暗示了人生的神秘、诡谲、阴晦和心理的惊徨,也从侧面反映了人生的复杂、命运的无常,天机的难测。能够让读者从中体悟到人的复杂与生活的阴谋,是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相爱不说再见》不仅蕴含着鲜活的都市气息、真挚的生活体验、细腻的情感倾诉,而且语言清新流畅,自然率真,洋溢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叙事个性。
在人生境遇中,尔容更多思考的是铁娃水莲这一代人生存状态中所面对的种种问题:飘泊与栖居、命运与机遇、道德与欲望、爱情与诱惑、生之意义与价值等等。这里其实潜在地反映了在这一代人心里,有着一种对未来的或过去不可知的时空的无助和依赖。过去、历史、未来、思想、爱情、兴趣、职业、享乐、欲望……一切都是流动的、支离破碎的。铁娃水莲这一代人很不情愿地往返在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经验世界中,同时也受到商业文化所制造的种种神话的诱惑。尔容对生活的拷问,对历史的反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相爱不说再见》中,欲望弥漫于人物与环境之中,营造了一个充满绚烂色彩与流动意蕴的象征世界,在一种救赎氛围浓烈的结局中,传达了生命的空虚与期盼;欲望成为宣泄在文本世界的一种情调,使长篇小说的叙述风格,在整体上体现为一种欲望化的倾向,赋予了这个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以某种精神上的深度。面对铁娃身体的堕落灵魂的挣扎,作家流露了她的惊悚、惶惑与无可奈何的救赎善意,长篇小说的结局于是便在人性荒凉废墟上增添了几分温暖的意味。
《相爱不说再见》引领我们对当下某种“没有重量的生存”,不得不作深入打量和冷静思考,让我们在对人生、对命运的品味中,保持自己做人的从容和自尊;使我们看到自己灵魂的卑微,从而在生活中尽量放大自己的善,放下贪求与欲望,摒弃凡尘俗世的纷扰,给自己一片宁静的天空。
《相爱不说再见》不仅仅是感情、婚姻的叙事和呢喃,更有品味人生百味的悲悯情怀和大爱。尔容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站在芸芸众生里,触摸着时空变幻后漂移的爱情和婚姻,那往往是最容易破碎的爱情和婚姻。作品让我们感受的是生活的艰辛、身心的煎熬和精神的困境;卑微中的伟大和屈辱中的尊严;尔容向我们传递的是真切的宽容、关爱和善良。
尔容的思考
尔容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高大丰满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设计,但是它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有对个体灵魂细致入微的关怀。尔容还通过铁娃不断失落、不断寻找的循环过程,传达了高度物质化、信息化和程序化的现代社会都市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传达了都市人心底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感伤,同时不动声色地提醒:你有没有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吗!
在《相爱不说再见》中,尔容意图重审男性所建构的父系历史体系。以自己对男人的独特理解,书写以女性为叙事本位的“女性历史”,使“她的故事”变成“我的故事”。长期以来,在有关爱情、婚姻叙事文学中,女性常常被认为是历史传统的缺席者,甚至缺席于沉默与疯狂之中。女性的缺席,进一步再度使她们成为隐性的物体,男性的声音则理所当然成为历史唯一的真相。然而,真正的谜底与吊诡则是:阴性的压抑乃是一种总体的文化压抑,不仅压抑女性,也压抑了包括男性本身的阴性气质。
在现代商品社会,当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时,便会产生一些模糊的或骚动的遐想,在遐想中,人们常常会将自己所缺少的各种品质或权力赋予自己。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于是,我们便可以在经济的压迫中找到被羞辱的肉体,在疯狂中找到可以理解的冲动,在爱情婚姻中找到卑微的人生。更可以在残酷的微妙世界中找到自贱自卑的命运。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归根结底,《相爱不说再见》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人性的丑恶纠缠和贬损。从某种意义上说,铁娃传达了尔容对深陷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中,普通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思考:铁娃其实也是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在他那看似疯狂的“阳具权力”背后,也隐藏着一个有一定思想纬度的聪明人。
尔容的笔下似乎“有人性在呱呱啼哭”。小说主题一直都是那么的尖锐、固执,甚至令读者不寒而栗。铁娃所有形而下的“力比多”疯狂,隐藏的是生命的压抑,埋藏的是精神的极端紊乱。小说中的人物既凌空虚蹈,又完全真实,文字比画面更能深入内心,而且作家没有丝毫的矫情。尔容用平和冷峻的叙事手法,向我们讲述了这个看似理性、秩序的世界背后的荒诞、残忍和疯狂。《相爱不说再见》对于欲望以及丑恶的描写,一方面使历史的“真实”隐没在欲望的阴影与暗流中;另一方面也营造出一种浓浓的幻灭情调与虚无色彩。另外,《相爱不说再见》的叙事大含细入,如锥画沙;议论不温不火,谈言微中,间或还流露出佛禅意趣的哲理韵味,也特别耐人咀嚼,引人回味。
阅读《相爱不说再见》,是一个非常流畅的过程,这应该得益于尔容的叙述方式;这部长篇小说里有最忠实的世相记录和描写,当然也有少许的夸张和隐喻。它是一部长篇寓言式的讽世小说。作家把自己最痛苦的思考,藏在一种戏谑和黑色幽默的背后。其实,文学的真实性,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相爱不说再见》的深刻意蕴,就藏在作家的谴责止于了犹未了之中。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才在作家的无意经营中,具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隐喻性和尼采式的寓意色彩。于是,当我们阅读《相爱不说再见》的时候,似乎就能感觉到尔容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噬咬、被撕裂着。作家的心是疼痛的,但是她的笔下却充满着生命的激情,充满着源源不断的情感,复杂而饱满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令她的作品充满了鲜活与灵气。
在《相爱不说再见》中,尔容以性灵文字,化出万千情思和感慨,在女性自我生命体验和女性本体欲望表达等方面,表现得比过去更为内在、明显和豁达。在艺术表现上,更进一步个体化,尔容从儿女情、家务事等庸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这本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但随着社会变革速度的加快,写作已经进入“她世纪”。“她世纪”是女性的世纪,意指女性概念强化,女性意识全面觉醒。她们更加关注身体和性,关注爱情和自我。另外,在《相爱不说再见》中没有矫情和矫饰,只有生活的质感;没有坚硬的张力,却不乏淡淡的哀愁与沉甸甸的深思。尔容在光亮的情感底色上,涂下的是苍凉的文字,那苍凉文字的背后,还有几分无奈的慨叹、思想的迷茫、人生的省悟、生命的思考。
单位: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