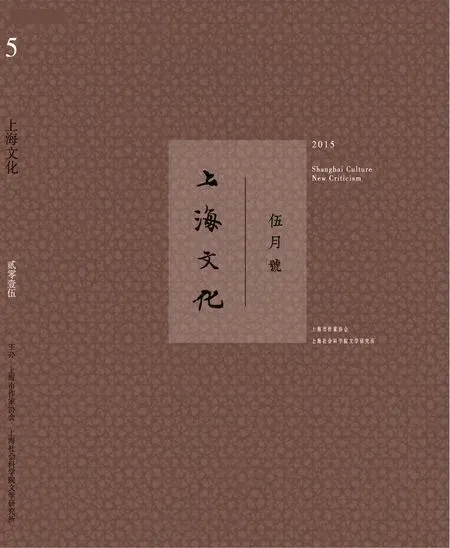再见,阿伦特*
玛丽·麦卡锡 魏忠贤 译
再见,阿伦特
玛丽·麦卡锡 魏忠贤 译
一
她的最后一本书被命名为《心智生活》,计划当作《人的境况》(一开始叫《行动生活》(Vita Activa))的补充,在《人的境况》中,她细致审视了三个概念——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个概念分别对应着人作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技艺人(homo faber),以及公共事件的行为者。而在《心智人生》中,她看到了心智的生活,或者说,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心智也被分为三个部分:思索、意愿,和判断。第一部分,关于思索,早些时候已经完成。第二部分,关于意愿,在她去世前刚刚完成,完成这一部分,一定让她轻松不少,因为她发现意愿是这种官能中最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第三部分,判断,她已经有了梗概,并且写了一些,虽然关于这一部分留下的文字很少(留下的主要是关于康德的),但是她觉得这一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我说“她的最后一本书”——汉娜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将是她最后的工作,或者说,是她的最高成就,如果她完成了它。这本书不仅将补充(行动生活之外的)人类能力的另外一个维度,而且是人类能力最高和最无形的表现:心灵的活动。如果她能够活着看到这本书(两卷,实际上)付梓,毫无疑问,她还将写下去,因为她的天性就是思考,并表达,但同时,她也会觉得,她真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这种感受,对她来说,跟自我实现无关(自我实现,这种想法对汉娜来说,若不是可憎的,也是可笑的),而是一种诫命,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它
二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要来完成一次侍奉或者执行一件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汉娜是虔诚的。她聆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像先知听到圣训,像孩童时的撒母耳,身负圣衣(linen ephod),在大祭司以利的住所,面临圣召。你也可以以一种更世俗的方式看待这件事,认为汉娜感觉到自己身负契约,尽管束缚她的契约另一方,是她那被自然(Nature)赋予,被她的老师们——雅斯贝尔斯以及海德格尔——发展,被历史悲剧性地强化的杰出天赋。这种感受,对她来说,跟自我实现无关(自我实现,这种想法对汉娜来说,若不是可憎的,也是可笑的),而是一种诫命,我们所有人都背负着它,而不只是像那些用生命的轨迹追随机会和命运的天才,比如诗人,追随对缪斯的信念。阿伦特不相信让人盲目的奴性观念(slavish notions),比如个人“责任”那一套(这大概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心智生活》的“意志”部分,她遇到了如此之多的麻烦),但是对于使命感、天职,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效力,她却是积极响应的。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注重私人生活的人,我想(虽然我俩从没谈起过)《心智生活》这本书,她是用来纪念海因里希的,某种程度上,作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完满结束。
海因里希·布吕歇,她的丈夫和朋友,是她的最后一位老师。虽然他只比她大十岁,但是在他俩的智识关系中,有一种类似于父爱的东西,海因里希宠溺着她,而阿伦特像小学生一样,热切,并期望被认同;像她曾说过的那样,他会一边用怜爱的眼神看着她,一边点头,好像幸运女神给他送来了一位超乎想象的聪明女学生,一位非凡的向目的地进发的人(achiever),对他这位从各种意义上都属于哲学家的人来说,他可以嘴含烟斗和雪茄,安心地不去做进发者了。他为她感到自豪,并且知道,她能够走得很远,走向他可以远远看到的高度和广度,他可以平静地在后面坐下,等她找到它们。
对汉娜来说,海因里希就像一副镜片;在获得海因里希的确认之前,她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的洞见。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他们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他的精神气质更偏向于“纯粹”哲学家,而她更关注实践生活(vita activa),不管对于政治还是对于制造——以书和文章的形式铸就持久之物;对于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的生物领域——家务、消费,他们都不感兴趣;虽然他们都喜欢年轻人,但是他们从没要过小孩。在他1970年年末突然去世的时候——虽然她的离去更加突然——她便孑然一身。她被朋友们包围着,却像一位孤独的旅客,独自乘坐在她的思想列车上。所以,在那黯淡的日子中开始动笔的《心智生活》,是为海因里希·布吕歇而构思,而思考,(她一定也希望和他一起写书,)它不是一个里程碑,而是一个像闭合的三面屏风一样的存在,中间包围着神秘的意愿。不过话说回来,这些都是我的猜测,我也没有机会当面问她了。
三
我刚说到了汉娜的无以比拟的成就(crowning),但是汉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野心(说她要创造个什么事业,这是很荒谬的);如果说汉娜曾为一个成就(crown)努力过,那么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她像一个探险家,独自完成最后一步,吃力地到达一个顶点,就是想站在这个顶点上,举目四望。而在她眼前展开的,却是一个黑暗时代,她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承受并目击着这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流产;美国共和制在当下所遭遇的威胁。美国共和制,是她找到的一个新的政治归宿,在这里,她寄予着自己一直念念不忘的自由理念——虽然越来越失望——并像测绘员一样,铺展开她那庞大的概念和洞见之地图,这些概念和洞见中,有些来自悠长的哲学传统,有些则是她自己的发现,它们因得自她所在的高度,所以最起码也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儿。
在观念领域,汉娜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她从来都不信奉那种把前人思考过的问题抛到一边的做法。它们总会有用的;用她自己的方式,她是一个狂热的回收者(recycler)。换种说法,思想之于她,是一种耕种,是给蛮荒的经验赋予人性——建造房屋、铺通道路、筑坝截流、种树防风。因为她是才华卓越的知识分子,是她这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所以降于她的大任,就是将她所处时代的每一种独特经验——失范(anomie)、恐怖、高科技战争、集中营、奥斯维辛、通货膨胀、革命、学校取消种族隔离、五角大楼文件泄露、太空(space)、水门事件、教宗约翰、暴力、公民不服从——系统地加以思考,并且,通过它自身,以及它自己的独特进程,最终实现,将思想内化。
这些概念和洞见中,有些来自悠长的哲学传统,有些则是她自己的发现,它们因得自她所在的高度,所以最起码也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哪儿
“系统”这个词,可能会造成误解。尽管她有德国人的习惯,但汉娜可不是一个系统建造师。相反,她寻求对已经存在的系统进行检视,系统固存于人作为主体与世界和自我进行互动之时。在远古,随着语言的诞生,不,实际上是随着言语的诞生,这和那(比如工作和劳动,公共和私人,强迫、权力和暴力)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已经反映出,人很会分类,如果你愿意,便是“天生”的哲学家,与构建整体相比,分析(separating)的能力,敏锐的分辨力,对人这个物种来说,是更自然的。如果你对汉娜有所理解,就会认识到,汉娜更倾向于多而不是一(这也许能够解释,对于极权主义这一世界中的新现象,她为抱何以如此恐怖的认识)。她没有寻找万能方法或放之四海皆准的通则的意愿,如果她有所信仰,那么这信仰绝不会是一神论的。她的作品向许多方向发散,在每个方向上,都像青嫩的树芽,抽枝延蔓,毫无疑问,这部分地要归因于她对经院学术的喜爱,但与此同时也证明了,在世界的丰富性和强烈的独特性面前,她那充满敬畏的谦卑。
和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完全不是那种雄辩的方式,而是看起来更像一座矿藏、一位悲剧演员
四
不过,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汉娜的思想,我只想试着将汉娜这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重现出来,展现汉娜在这个她称之为表象世界的舞台上的风采,如今,她已在这个舞台上谢幕。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妩媚、诱人、富有女人味,正因为此,我称她是女犹太人(Jewess)——这是一个过去的术语,用来称呼锡安人的女儿们,就像西班牙流苏围巾和她非常相配一样,这个称呼和她相得益彰。尤其是她的眼睛,如此明亮闪烁,当她高兴或激动的时候,一双明眸熠熠生辉,但她的眼睛也很深邃,黑色的眸子,深远的目光,敛着一泊灵性。汉娜身上有某种深不可测的东西,安居于她的目光之中。
她有一双小巧的手,迷人的脚踝,优雅的双足。在我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她很喜欢鞋子,从没亏待过她的脚。她的腿,她的脚,她的脚踝,全都透露着敏捷、决断。只需看看她在讲台上的姿态,小腿,脚踝和双脚都好似要和她的思绪保持一致。当她讲话时,她会踱来踱去,有时双手插入口袋,像在独自散步,沉思。允许的情况下,在讲台上踱步时,她会手拿一支装着烟嘴的香烟,时不时吸上一口,有时候突然一回头,好像被一个新的、未曾料想到的想法攫住。看她对台下的人说话,那些动作和姿态,好像思想的运动可以被看见了一样。她是一个如此随性的人,会在讲课的时候突然停住,皱着眉,盯着天花板,咬着嘴唇,沉思地托着下巴。如果她是在念一篇演说稿,那么就总是会有感叹词,插入旁白,就像她文稿中的脚注一样,布满限定性的条件和附加的说明。
汉娜极富伟大女演员的气质。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她发言——差不多三十年前了,在一场争论中——她让我想到伯恩哈特(Berhardt)或者普鲁斯特的玻尔玛(Berma),一位气势宏阔的歌剧女主角,活脱脱就是一位女神。不是那种梦幻的女神,而是一位神秘的或者热烈的女神。和其他优秀的演讲者不同,她完全不是那种雄辩的方式,而是看起来更像一座矿藏、一位悲剧演员,在思想中上演戏剧,演绎着我和自己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她的书写中常常被唤起。看着她在台前的演讲,会让人觉得,剧场的神圣起源——古希腊的舞台,仿佛近在眼前,作为演员或者作为受难者,她塑造的,是饱受良心和反思之冲突的人类形象,这样的形象总是成对出现,其中一个倾吐心声,另一个回应或者质疑。
但实际上,汉娜也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不过,在教室跟学生们讲话就是例外了,这时候,她会感觉很轻松,就像在朋友们中间。)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而是表现在,举个例子,她会觉得自己还挺懂烹饪的,但其实啊,她才不懂,同样的,挺会撒谎的这一点,也是她自己以为的。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比如假托生病或者提前有约,而让自己从一个社交窘境中解脱。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她觉得不好,依她的一向做法,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五
汉娜身上最有戏剧性的地方,就是当她被一个想法、一种情绪、一种预感攫住的时候,无意识中爆发的力量,这时候,就像演员,她的身体变成了它们的媒介。被这种力量占有的时候,经常是以一下睁大眼睛为开始,然后发出“啊”的一声(这种情况发生在,她盯着一幅画,一处建筑,或者某个恶行的时候),像被电了一下,然后意识从我们众人中抽身出来。她那一头充满活力富有弹性从未变得全灰的深色短发,在这股纯粹力量的刺激下,也在她头上竖了起来。
我想,所有这些,一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天赋的一部分,我说的漂亮指的就是她的容貌和面部表情中的这些表现。汉娜是我见过的人里面唯一一位可以看到她思考的。她会躺在沙发或者午休床上一动不动,双手枕在脑后,闭着眼睛,偶尔睁开盯着天花板。这种状态能够持续——我不知道——从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如果我们无意中走进了她躺着的屋子,我们每个人都会踮起脚尖,蹑手蹑脚从她身边走过。
她是一个不那么耐心、又慷慨大度的女人,这些品质总是一同在一个人身上出现。比如,在一个演讲或者是一篇文章中,她会想要把所有她知道的东西或者恰巧跳进她脑子里的想法都塞进去,就好像她不能集中在单一的主题上,所以她会强行给来访者奉上各种坚果、巧克力、甜姜、茶、咖啡、金百利酒、威士忌、香烟、蛋糕、饼干、水果、奶酪,几乎一次性奉上所有,而不去顾及惯例所安排好的顺序,或者,更多地,是不去顾及是否是合适的时间。就像成堆的丰富食物,被放在节庆用的盘子和容器里,端出来,粗犷地讨好口味不同的所有神灵。有人说,这是永恒的犹太妈妈的做法,但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她并没有打算这些食物对你有好处,实际上,这大多数食物对你来说,显见是有坏处的,汉娜一定对此有所了解,因为她并不坚持让你享用。
对于私人领域,包括他人的以及她自己的,她都报以尊重。我经常和她待在一起——跟她和海因里希——在河滨大道,之前是在晨边大路的寓所,所以我能了解这一点。汉娜的生活习惯很好,比如,她喜欢的早餐,是一个煮鸡蛋,一点火腿或者冷切肉,一块抹上凤尾鱼酱的烤面包,一杯咖啡,当然了,还会有半杯新鲜的葡萄汁或者橙汁,不过有可能这新鲜果汁只有当我这个美国人在她家的时候,才会出现。海因里希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她跑来缅因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让她住在一个单独的小套间里,在车库的正上方。我花了一点心思为她置办厨具——她喜欢一个人吃早餐。我想她在自己家中会用到这些东西,像速溶咖啡(我一般不会常备),这样她就不会为咖啡滤纸而烦心。而且,能在乡间小店中为她找到凤尾鱼酱,也很让人开心。她抵达的下午,当我带着她去看食品柜,对着装凤尾鱼酱的小管子皱眉,好像那时一种让人费解的外国东西。“这是什么?”我告诉她答案。“哦。”她放下它,看起来在思索,并且不知怎么搞的,好像不太高兴。她没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做错了,因为我努力去讨她高兴。她不太希望被以这种窥探的方式,这种有限的、简化的方式被了解。我的所做,是在向她表明,我了解她——一种爱的象征,但是并不总是这样——从而这也证明,说到底,我根本不了解她。
她紧闭双眼躺在棺中,她的头发被从前额梳向脑后,要是她自己,她一定会相反,把头发拉到前额,有时候,在演讲的时候,她还会把头发固定在前额,用来遮住车祸留在头上的一块伤疤——但是即便在那块伤疤出现之前,她也很少露出眉毛。在她的棺中,眼睑遮住她深不可测的双眼,高贵的额头上挑着某种大卷发,她看起来不再像汉娜,而像带着一副18世纪哲学家的死亡面具。在葬礼上,我没有走近去摸摸这个高贵的陌生人,只有那脖颈,那柔软却布满皱纹的脖颈,那支撑着这个公共头脑的脖颈,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找到一个地方,跟她说,汉娜,再见。
编辑/黄德海
*这篇文章,是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在汉娜·阿伦特去世之后,在1976年1月,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一篇纪念文章。麦卡锡是一位在美国当代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作家。她擅长对婚姻、两性关系、知识分子以及女性角色进行辛辣评论,作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麦卡锡是“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美国“国家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她曾获得爱德华·麦克道尔奖章(1982)、美国国家文学奖章(1984)以及罗切斯特文学奖(1985)等多项奖项,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我们时代唯一真正的女作家。”更重要的是,麦卡锡是阿伦特在美国的挚友或者说闺蜜,这段二十余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阿伦特去世,两人之间的通讯集已经出版,名为《Between Friends:The Correspondence of 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1949-1975》。——译注